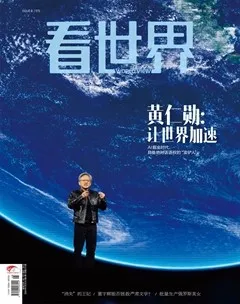我在中国找工作

《洋盘:迈阿密青年和上海小笼包》
[ 美] 沈恺伟 著
于是 译
文汇出版社·新经典文化
2023 年10 月
2005 年,我在一个炎热的夏夜降落在浦东国际机场。酒店派了一辆车来接我,我跟着司机走进夜色,完全不知道我们要往哪儿去,不知道我接下去一年的生活会走向何方。我们走向车的那段路上,潮湿、滞重的空气压得我喘不過气来。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大陆。我只带了一只小行李箱,有一份厨师的活儿在等着我,但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对上海一无所知,对中文一无所知,讲真,对大部分事物都一无所知—当时我24 岁,驶出机场的那一路上,我也几乎一无所见。
夜很黑,高速路边没什么灯光,下高速驶入小路后,两边的灯光甚至更稀疏了。15 分钟后我才搞明白:机场不在市区附近。
找工作
2000 年初,身为年轻厨师的我以背包客的方式游历了东南亚,还顺便去香港探望了家姐。她的客户开着黑色奔驰来接我们,停在一家又脏又破的火锅店前。荧光灯亮得刺眼,男人们吞云吐雾,餐桌笼罩在香烟的烟雾里,端上桌的活虾被插在竹扦上,眼看命数将尽却那么生猛,拼命地摆动腿脚。
别的夜里,我们登上九龙的玻璃幕墙摩天楼,窝在时髦餐厅的座椅里,沉浸在18 楼俯瞰到的中环夜景之中。白天,我们去扫外贸尾单,在旺角吃炸云吞。
我爱死香港了。既不是彻底的西方文化,也不是彻底的中国文化。香港个性独特,是一种“第三类文化”。感觉特别新鲜,我想在那儿闯荡一下。迈阿密让我厌倦了,从小到大混过的城郊让我腻味了,在从未到过亚洲的厨师们手下学做亚洲美食也让我烦透了。我想直捣黄龙。
前一年,我曾试图去利马,但没办成;我在南美洲挨了整整3 个月,想家想得要命,最终还是放弃了。以后再试试吧。香港不错。我说,有朝一日我要待在这里。
坐在车里,驶出机场30 分钟后,我开始紧张地检索自己所知的有关上海的稀少信息,基本上只能归结为8 个字:城市很大,灯火通明。
去过香港后,我回到迈阿密,琢磨着怎样才能跨过大半个地球找到一份工。那时候的互联网还很低级,厨师们又整天待在厨房里,不会泡在网上。
在佛罗里达就没问题。我挑中了迈阿密最好的餐厅,找了个大清早,走进餐厅的后巷,找到了厨房后门,敲了门。开门的是个魁梧的意大利男人,问我想干吗。“找工作。”我说, “我想和主厨谈谈。”30 多岁的行政主厨来了,显然正在忙什么事,却被我打断了。“我想在这里工作。”我说。他歪了歪脑袋,打量我。“我可以不收钱。”我主动提出这个建议。他想了想,叫我第二天再去。我就这样找到了一份工。
我不是那家餐厅里最优秀的厨师—连边儿都挨不上—但我很有自信:免费工作几天后,餐厅肯定会正式雇用我的。我还是挺棒的。果然,他们第二天就雇我了。后来,我在那儿干了3 年厨师的活儿。所以,我暗自揣测,如果我没法联系到半岛酒店的主厨,那就使出杀手锏:直接杀到他的后门,主动提出免费打工。这一招屡试不爽。我卖掉了在迈阿密骑的摩托车,处理掉不太多的几件家什,和亲朋好友告别。我要再试一把。
问题在于:半岛酒店的后门并不通向厨房,而是酒店数百名员工的入口,而且设有摄像头监控。我到香港的第一天就发现了这件事,时差还没倒过来,昏头昏脑,有点茫然,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回到廉价青旅,另做打算。照我的想法,我只需要见到主厨,自我介绍,他显然就能看出来我的天资禀赋,当场就会把我招入麾下。最坏的结果无非就是免费打一阵子工。但我需要面对面地见到主厨。
要想面对面很难,难就难在半岛酒店的主厨身边有很多人—副主厨、秘书、餐饮总监,把通向他的各种途径都堵得严严实实。我打过电话,装成奶酪或葡萄酒的供应商,想骗过电话那头的秘书们。没用。我等在大门外,希望能在主厨上班时堵住他。也没用。我绞尽脑汁,想用别的办法和他说上话。都没用。
来到香港
彻底没辙了。现在回想起来,就算我当时找到了主厨,也不会心想事成。半岛酒店里满是一等一的好厨师—非常优秀的中国厨师—那个酒店根本不需要一个不会说粤语、更没资格在香港合法工作的年轻白人。
一败涂地的我灰心丧气,萎靡不振。我在图书馆泡了好多天,因为我只能找到那地方可以上网,发发思乡情切的电子邮件。我想与住在隔壁客房、吸粉吸到嗨的巴西模特交朋友,但也只是想想而已。夜里比较凉快,我在香港市区瞎逛,每顿饭都是独自一人吃的。钱快用完了,我不知何去何从。
然后,我想到了曼谷。吃泰国食物可以省点钱,说不定我还能在那儿找到工作。我所谓的“计划”就是这么粗线条。转机就出现在去泰国的飞机上。我和邻座的男人聊起来,没想到他刚好也是厨师,加拿大人,在曼谷的一家五星酒店里工作。他说他在这片地区人头挺熟的;仅仅过了几周,他就帮我和某人打了招呼,我立刻飞回香港去面试。
港岛香格里拉餐饮总监的名字我听过就忘了,但永远不会忘记他给我留下的印象。他站在10 英尺高的地方,一身无可挑剔的西装,银色袖扣,衣襟上别着一枚香格里拉酒店的金色徽章;他看着等在大堂的我—穿着本人最好的(打过补丁的)牛仔裤和(脏兮兮的)T 恤—难掩鄙弃的神色。他指了指我,转向他的助手,确认他下来面谈的对象真的是我。“就是他吗?”他问道,带着欧洲口音,然后上下打量着我,在我身边坐下。
我向他讲述了自己的情况,包括之前的经历以及我为什么来香港。他点点头,叹口气。“好吧,我会和我们主厨谈一谈,可能会有什么活儿。但你先听我一句。你必须把自己收拾干净。下次你再到这儿来,”他冲着我用手比画了一下,“要比这次像样一点。”想当初我在迈阿密也是一身邋里邋遢的破烂牛仔、朋克摇滚T 恤,还以此为荣呢。但在重商而保守的香港,这身打扮让我无地自容。
我在图书馆死等,一刻不停地查看邮箱,想等到餐饮总监给我回复。终于,他发了我一个与主厨面谈的日期,我二话不说直奔Calvin Klein 专卖店,掏出最后几张大钞,买了一套新西装—我这辈子拥有的第一套西装。还剩了点零钱,我又去湾仔一家时髦的发廊理发,光剪还挺便宜的。我的样子太可笑了。第二天,我穿着新西装,梳好新发型,二度迈进香格里拉酒店的大堂。
(本文获出版社授权,标题为编者所加)
责任编辑董可馨 dkx@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