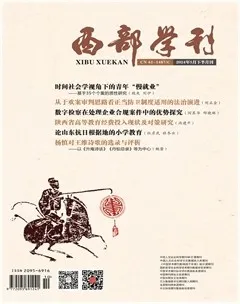天台宗研究视野中的蕅益智旭身份问题考析
马炳涛
摘要:晚明四大高僧之一的蕅益智旭与天台宗的关系历来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通过对智旭与天台宗关系研究的回顾,可以发现强调智旭并非天台宗传人的观点多受限于资料的不完备及研究方法的局限,而近年来对晚明高明讲寺一系天台宗研究的深入,为我们重新解读智旭与天台宗关系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正是缘于晚明天台宗高明讲寺一系的复兴,使得智旭认识到天台教法对于佛教发展的重要价值,他虽不认同单独弘扬天台宗的佛学理念,但仍将天台佛学纳入到其佛法体系建构的核心,也正因如此,后世智旭一系的传承被同化为天台宗传承。
关键词:身份;天台宗;传承
中图分类号:B94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4)10-0128-05
On the Identity of Ouyi Zhix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earch on Tiantai Sect
Ma Bingtao
(School of Marxism,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Guangzhou 510521)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yi Zhixu, one of the four eminent monk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the Tiantai Sect has always been a hot issue in academic research. Through the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ixu and Tiantai Sect,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view which emphasize that Zhixu was not the heir of Tiantai Sect is mostly due to the incompleteness of the data and the limitation of the research method, while the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Tiantai Sect of the Gaoming Temple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in recent years has provided us with a new research ideas to reinterpre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ixu and Tiantai Sect. It is because of the revival of the Gaoming Temple of Tiantai Sect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at Zhixu realized the importance value of the Tiantai Sec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Although he did not agree with the idea of promoting the Tiantai Sects Buddhist philosophy alone, he still included the Buddhism of Tiantai Sect in the core of his Dharma system. It is just because of this reason that the inheritance of Zhixus lineage has been assimilated into the Tiantai Sects inheritance in the later generations.
Keywords: identity; Tiantai Sect; inheritance
晚明以來天台宗的发展存在幽溪传灯和澫益智旭为代表的两种模式,两者虽然在时间上稍有重叠,但在性质上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历来对明清天台宗的研究大多是以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或者正统谱系为依据,从而陷入一种“念珠式”的理解,致使我们对传灯一系的解读相对忽视,也因而不能清晰地呈现蕅益智旭与天台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梳理天台宗研究中智旭身份争议的学术渊源,尝试通过对晚明佛教发展模式的分析来对智旭与天台宗的关系做出较为清晰的解读。
一、蕅益智旭身份的争议
现存通行本中常见的澫益智旭画像,图下配有印光法师(1861—1940)所作的“莲宗九祖颂”。这一画像是印光法师在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请张觉明居士所画的莲宗十二祖像之一,在给张觉明的信中,印光法师详细注明了绘制的一些细节,如要求画像“前标祖师名,后标年时,另纸书,裱于上”等[1]835。弘一法师(1880—1942)在其编订的《蕅益大师年谱》卷首即印有此幅画像[2]1081,或许因此缘故,圣严法师在他研究智旭的大作《明末中国佛教之研究》中认为此画像和底下的“莲宗九祖颂”都是弘一所作,并将画像右侧的题款识文为“清莲宗九祖非天台宗下智旭大师”,并认为弘一在智旭年谱的写作中对“非天台宗下”的说词有“相同的指述”[3]159。陈剑锽在其《近代确立莲宗十三位祖师的过程及其释疑》一文中也沿用了这一说法。
经考证,可以发现圣严法师的这一观点存在两个误区:
第一,联系印光书信中所言及的“前标祖师名”,可以推断,这一题款应为张觉明据印光的要求所写,而且,由于现在所见图像的模糊,圣严误读了这一题款,其文字应识文为“清莲宗九祖北天目灵峰智旭大师”[2]1081,“北天目”即现在的浙江湖州灵峰寺,是智旭的根本道场。这一题款应是直接根据印光所作的《莲宗十二祖赞颂》而来,每位祖师的“赞颂”都是按照朝代、祖位、道场、祖名的顺序题写,如“晋初祖庐山东林慧远大师”,以及智旭画像的题款“清莲宗九祖北天目灵峰智旭大师”[1]1578。
第二,圣严认为弘一主张智旭并非天台宗人,他的依据是弘一在智旭的年谱中有“时人以耳为目,皆云大师独宏台宗,谬矣,谬矣”的叙述[4]10225,并认为这里的“时人”有可能是指清末民初与弘一同时期的天台宗第四十三祖古虚谛闲(1858—1932)等人。我们发现,弘一的这段叙述是转述自智旭的《八不道人传》,在这部自传中,智旭述说其32岁时抓阄注解《梵网经》,因为频得台宗阄,于是究心天台教观,而之所以不肯为台家子孙,则是缘于当时天台宗与禅宗、贤首、慈恩等宗派佛教,各执门庭,不肯和合。《蕅益大师全集》所收录的嘉庆六年(1801年)刊刻的《灵峰宗论》中,这段文字后有智旭一句自评,用双行小字刻出,其文为:“时人以耳为目,皆云道人独宏台宗,谬矣,谬矣!”[4]10224由此可知,弘一只是转引了这段文字,将智旭自称的“道人”改为“大师”,并在文后附录案语如下:
【案】大师法语,《示如母》云:“予二十三岁,即苦志参禅,今辄自称私淑天台者,深痛我禅门之病,非台宗不能救耳。奈何台家子孙,犹固拒我禅宗,岂智者大师本意哉!”《复松溪法主书》云:“私淑台宗不敢冒认法派。诚恐著述偶有出入,反招山外背宗之诮”。“然置弟门外,不妨称为功臣。收弟室中,不免为逆子。知我罪我,听之而已。”[2]1093
这段案语集录了《灵峰宗论》中智旭与天台宗关系的几段文字,皆为智旭说明自己私淑台宗,但又不想归为台宗法派之意。可见,弘一认识到了智旭与天台宗关系的复杂性,故而只是将智旭自己的观点列出,而并未表露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因此,智旭之“非天台宗下”应是缘于圣严法师的误读,但这种误读却恰恰正是其观点的体现。
二、蕅益智旭身份的解读模式
圣严法师关于智旭的研究意在探究其思想面貌是什么,他总结智旭虽然有很多著作涉及天台教学方面,但认为智旭受自天台思想的影响较少。智旭对天台教学的传承主要是天台注疏的方法论,即五重各说、七番共解的解经形式。他认为智旭思想的品格是融通,是“性相、禅教的调和,是天台与唯识的融通,是天台与禅宗的折衷,也是儒教与禅的融通进而统括律、教、禅、密以归向净土”[3]472。因此,圣严认为天台教学虽然对智旭思想的发展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天台教学,则智旭的思想发展,就无法开启”[3]159,但智旭的思想“并不是以天台宗为中心,也不是天台教学的传承者”[3]162。对于谛闲所传的天台宗法卷中将智旭列为继幽溪传灯(1554—1628)之后的天台第31祖的说法,在圣严看来,这“对智旭来说,可能是难以表示赞同”[3]461。
圣严法师对智旭与天台宗关系的看法也有学者不尽赞同,朱封鳌在解读智旭为何被塑造为天台宗祖师的时候,认为“智旭生前虽未受过传灯的‘法衣,但在思想和行动上是努力弘扬智者的教说,绍承传灯的思想的”[5],至于为什么只是“私淑台宗”[2]1093,他认为一是因为当时幽溪传灯已经圆寂,无法再去接法或求教;二是自知有“放肆之习”[2]1093,可能会因为著述偶有出入被認为是“山外背宗”[2]1093。
朱封鳌这一研究的一个重要启发就是,我们应留意智旭同时代的天台宗是什么样貌以及与智旭思想的发展有何关系。而圣严法师所说的智旭与天台宗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受当时文献资料和研究方法的限制,并未对智旭时代天台宗的发展状况做出深入探究。
圣严法师于1975年完成的关于智旭的博士论文被誉为是开启我国台湾对晚明佛教研究关注的经典之作,但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推陈出新、追求真理,当我们再来看圣严法师对智旭的解读时,有以下几点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究的。
首先,荒木见悟曾批评圣严法师的研究是出于传统护法的态度,并没有触及智旭思想的本质以及与同时代人物思想的比较,而主张从晚明佛教复兴运动的思想背景中来评判智旭的出现和思想[6]。由于晚明天台宗研究起步的落后,我们可以看到圣严法师对当时天台宗发展的状况以及传灯的思想并没有相对系统地了解。比如,他对传灯的介绍为传灯的传记数据,非常不完整,仅只《法华经持验记》卷下、《净土圣贤录》卷五中有所记载。只有在安藤俊雄的《天台思想史》中,曾予推断是1554—1627年而已,他对幽溪传灯的著作的研究也很不完善圣严法师在《明末中国佛教之研究》中对传灯著作的介绍主要是以智旭所评者为限;在《明末佛教研究》中主要是探讨了传灯净土学方面的著作,并将其归于“净土教”的人物分类。,因此,不能完整地对比晚明天台宗的教学与智旭之间的内在关联。
其次,对什么是天台宗的理解,正如沙夫(Robert H. Sharf)所言,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教义来看,“佛教”一词都没有一个一致的指代,而是一个各种佛教模式竞争的场所,因此,对“佛教”的解读不应当从一套确定的教义或实践中来探求,而是要深入到其赖以发展的各种不同的文化和地域等背景中[7]。
不同历史时期的佛教宗派都在有意识地根据时代需要而调整自宗的教学,我们不能“脸谱化”地认为佛教是什么样子或应该是什么样子、天台宗有什么特征等。换言之,佛教宗派的每次“复兴”,在继承既有的历史资源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说是立足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需求而重新创宗立派、自我更新的过程。“佛教”是一个模糊的指代,天台宗等宗派的指涉同样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的。智旭教学的立场是出于对时代的需要,他对天台教学的研究既包括历代天台宗巨匠,也包括晚明复兴时期的高僧,圣严法师对此也有过统计,但由于晚明天台宗的研究起步较晚,他对天台宗的理解显然有模式化的倾向,是用从智者大师(538—598)到宋代时期的天台宗的概念来考察智旭的教学与晚明天台宗之间的关系。比如,前文提到他认为智旭只是采用天台宗的解经方法。又如,对智旭《楞严经》注疏的立场的解读,圣严法师一方面如荒木见悟所说,并没有考察对这部经典的注疏是晚明佛教发展的潮流,借诠释《楞严经》来复兴其教学也是当时天台宗的一大特征;另一方面,他对天台宗与《楞严经》关系的认识主要是以宋代的天台注疏为主,没有关注到晚明天台宗复兴时期的《楞严经》注疏,因而认为智旭之如此珍重《楞严经》,却并非受自天台宗山外派的影响所致。他以一个禅者的立场,来承受《楞严经》的教法,后来则由于《宗镜录》的影响,把《楞严经》作为统合禅、教、律、密或性相二流的异说、异见的根本经典。
三、蕅益智旭与晚明天台宗
当以人物为中心来探讨晚明佛教的发展时,我们很可能会陷入这样的误区:过分强调个人的主张而忽略支撑其思想模式的教团。名僧或高僧代表的是某种特定的佛教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多为同一宗系的传承,他们虽然可能弘传于不同地域的寺院,但彼此之间存有密切的互动,甚至发展出姊妹寺院联盟。晚明天台宗复兴的发展模式即是由百松真觉开创,随之由其弟子弘传于各个地域,幽溪传灯只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智旭虽研究过天台一系的发展模式并且与传灯的弟子多有交流,但他的教学却并不限于天台一家,而是博采众长,随之开创自己的教团和佛教发展模式。因此,当我们在比较传灯和智旭的教学时,如果只是探讨两者个人的教学风格的异同,那么朱封鳌和圣严法师的观点自然都有合理之处。相反,如果我们通过两者所属的教团和发展模式来探讨他们的关系,那么,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两种模式的异同以及同构化为单一的线性传承谱系的过程。
智旭佛法探索之路首先接触的是憨山德清,早在17岁时,智旭因阅读德清的《自知录》和《竹窗随笔》而由辟佛转为学佛,23岁时由于不解《楞严经》教义而决意出家,体究大事。到24岁时,智旭一月内三梦德清,但因当时德清远在曹溪,故而从德清的弟子雪岭法师出家。自此,出家之后的智旭开始参访求学,同年夏秋之际,他到杭州云栖祩宏的僧团“作务”,听古德法师讲《唯识论》,古德,讳大贤,晚号一行道人,从祩宏出家,智旭听其所讲的唯识学与《楞严经》似有矛盾之处,古德的回答是“性相二宗,不许和会”[4]10222,智旭对此深感疑问:“佛法岂有二歧耶?”[4]10222正是对这次听法的疑问,开启了智旭自身佛法之路的探寻。
但此时的智旭在思想上还是从禅宗的证悟出发来修行,他向古德师提问入胎受生,如何得脱的问题,但因为无法应对而往径山坐禅。次年春,智旭到高明讲寺拜见幽溪传灯,后来他回忆这次经历说:“葵亥春拜见幽溪尊者时,正值禅病,未领片益”[4]10984。可见此时智旭仍在纠结此前与古德的对应,同年夏天,终于有所证悟,他说:“次年夏,逼拶功极,身心世界忽皆消殒。因知此身,从无始来,当处出生,随处灭尽,但是坚固妄想所现之影,刹那刹那,念念不住,的确非从父母生也。从此性相二宗,一齐透彻,知其本无矛盾,但是交光邪说大误人耳。是时一切经论,一切公案,无不现前。旋自觉悟,解发非为圣证,故绝不语一人。久之,则胸次空空,不复留一字脚矣。”[4]10223虽然与传灯的晤面并没有受益,在此后的几年里,智旭却因为结识了几位曾参学过传灯的惺谷、归一和璧如等人而对天台宗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惺谷道寿(1583—1631),初参寒山德清,但“商究生死一事不甚切”[4]11399,于是转从博山无异,仍是“药病不投,莫能相疗”[4]11399,后参访幽溪传灯,智旭在其传记中记载如下内容。
访无尽法师于天台,见故友归一师,德业俱进,疑法师必有出格钳锤。依之,得阅《妙宗钞》等极则教理。回视昔时慧解,倍觉精细。刘大参延至吴门,从吴门游杭,抵龙居。时予在龙居阅藏,一见即问有著作否,以白牛十颂示之,大悦。遂欲盟千古交,予未以为然。相聚既久,每与予破格大诤,予谓此居士也,未必细察余言。后因归一师同结冬,偶商及耳根圆通法门,归师持公,是師非予。予因虚心再研,旧诤负堕处大半矣。乃共缔千古盟,激令早现僧相。[4]11399是年为崇祯元年(1628年),智旭30岁,因道友雪航智檝之请留住龙居,致力于律学的弘传,此时惺谷尚未剃度。同年冬天,归一受筹同来结冬,受筹是传灯的法孙,《幽溪别志》载有传灯所作的《同法孙受教、受筹灵法游看看云煮茗观瀑有感志怀》一诗。另外,《刘玉受兵宪与绍台道刘昆海为天台幽溪护法书》一文中也提到他说:“高明座下,文心、归一诸名僧”[8]229。智旭曾形容归一受筹对他的影响说:“遇归一筹师,方能照我所短,而夺我所守,然后日有开发。”[4]11072三人遂共缔千古盟,智旭由此二人而方才知晓传灯及天台宗教法的重要性。但也同时从受筹处得知传灯已于同年5月份圆寂,智旭深感痛悔不已,刺血写就《然香供无尽师伯文》。
不肖初游台岭,即睹慈辉。但钦温恭之德,罔窥法海之涯,方且甘暗证而蔑义涂,因门庭而昧堂奥,造罪意地者,匪希矣。后出入禅林,目击时弊,始知非台宗不能纠其纰。台教存,佛法存,台教亡,佛法亡,诚不我欺也。顾于老伯,犹半信半疑。自缔盟筹兄,乃甫倾向,而老伯已往生珍池矣。徒增悲仰,窃聆化仪,惭怀悔志,拟将何裨。呜呼!师弦绝响,野干竞鸣。演教者,舍醇醲而取糟粕,参宗者,先发足而后问津。孰能依教起观,一洗说食数宝之陋,知津发足,解脱盲修瞎炼之纷。老伯实中流砥柱,杲日中天也。悯予小子,不沾法乳于生前,不修微供于殁后。敬以三炷臂香,深达忏摩。三炷臂香,遥伸印手,惟老伯不起寂光,现觉三有,鉴法门婴杵之忧,锡初心止观之佑。苟机感之不讹,必含笑而摄受。[4]11470
从这篇祭文中,我们可以读出智旭对其佛法探索之路认识的变化,这篇祭文也被认为是智旭接续天台传承最重要的依据,他认为非台宗不能救禅林之弊端,而且“三炷臂香,遥伸印手”[4]11470之语更被认为是他希望接法幽溪传灯以弘台教。但联系到智旭此前的求道经历,他先是因性相二宗不能和合而开始佛法探索,此后通过参禅以求证悟,并了知性相二宗本无矛盾,结识惺谷和归一之时,他正转向律学的研究以救时弊。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的智旭乃是从整个佛教发展的立场出发,欲以天台教法和律学来拯救时弊。
第二年春,智旭和归一一同送惺谷至博山无异处出家,又因此结识了传灯的弟子璧如正镐。璧如正镐(1580—1631年),俗名王立(敬)毂,本在仕途为官,未出家时先从云栖祩宏受五戒,法名广镐,后在万历四十年(1612年)跟随幽溪传灯受菩萨戒,改名正镐,智旭在其传记中记载说:万历四十八年(1618年)梦冥王责其破戒,醒后双目失明,故而辞官,“筑室台山高明寺旁。日课金刚般若,并大悲心咒。行法不一年,渐复明”[4]11365,对此《幽溪别志》中也有记载:“葵丑(1613年)八月入幽溪邀十比丘同修大悲忏法七七日,遂学天台教观,究《楞严》宗旨……于性具法门,深有功焉。”[8]234因高明寺临近故乡,故而远走从博山无异法师出家(智旭记载其在楚地出家)。由于归一和正镐此前在高明寺时就有故交,故借此机缘,与智旭相识,谈及律学,两人甚为相投,“因叹近来律学大誵,本以破戒亲受冥谴,久欲留心此道。而历叩名德律主,罕不瞶瞶者。予出《毗尼集要》示之,亟读亟赏,叹未曾有,遂与盟千古交”[4]11396,正镐听说智旭正在阅藏,便嘱以八则事项,其中一项为“《梵网经》,虽有二大士发明,宜补以弥勒戒本,及诸经有相发者,集附本条之下,然后自出手眼,以补前人之缺,亦不失为二大士忠臣。勿以避嫌,失此胜事”[4]11397。
但智旭此时已确立了他性相融合的佛教思想,故而他虽以天台注解《梵网经》,但却并非是独弘台教,在《示巨方》一文中,他说:予本宗门种草,因感法道陵夷,鉴近时禅病,思所以救疗之者,请决于佛,拈得依台宗注《梵网》阄,始肯究心三大五小,愧无实德,不克以身弘道,然于古之妙,今之弊,颇辨端的。盖台宗发源《法华》,《法华》开权显实,则无所不简,无所不收。今之弘台宗者,既不能遍收禅律法相,又何以成绝待之妙。既独负一台宗为胜,又岂不成对待之粗。是故台既拒禅宗法相于山外,禅亦拒台于单传直指之外矣。夫拒台者,固不止于不知台者也,拒禅与法相者,又岂止于不知禅与法相而已哉。[4]10555由于智旭不满宗派之间各执门庭,独守一端,故而矢志融合诸宗。也正因如此,他才说自己只是“私淑”台宗,并评判传灯说:“慕幽溪之中兴台观,不肯学其单守一橛”[4]11636。
但晚明以来,这种组织形式已是佛教界的普遍现象,在智旭的《灵峰宗论》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客问澫益子曰:“出家法派,族姓宗谱也,子为不然,何邪?”
答曰:“世间至亲,莫如滴血;出世至亲,莫如法道。法道本虽名相,岂以名字为派哉?……降而今世,虽法派之说已行,高尚者犹弗屑。……(法派)为师者但贪眷属,为徒者專附势利,遂以虚名相互羁系,师资实义扫地矣,岂不痛哉!”[4]11021从中可见智旭对这种派系弊端的批评和无奈。
四、结束语
由于智旭的自传行文简略,致使我们很容易忽略他和天台门人的“盟千古交”,从《八不道人传》中我们只能读到,智旭“拟注《梵网》,作四阄问佛。一曰宗贤首,二曰宗天台,三曰宗慈恩,四曰自立宗。频拈得台宗阄,于是究心台部,而不肯为台家子孙,以近世台家与禅宗、贤首、慈恩,各执门庭,不能和合故也”[4]10224。这里的作阄问佛,看似智旭以天台注释《梵网经》的决定并非自己的决定,但联系他的这段经历及思想变化,便不难理解他为何要选择天台。
比较智旭和传灯两种不同的佛教发展模式,可以发现两者的分歧在于对“什么是佛教”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传灯认为天台宗所传的教法是最契合如来本心的,他视性具思想为佛陀之传法心印,故而在其理论构建中,处处发明天台教旨意,将其置于理论建构中的最高地位。而智旭则认为佛法本是一源,性相本不矛盾,并以此为根本来建立他思想体系,天台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要服从于佛法全体之根本。由此遂形成两种不同的佛教发展模式,具体表现即是诸宗融合与宗派争鸣两种意见分歧。我们看到晚明至近现代天台宗历史的建构是以这两种模式被同构化为关键点,因此,解读这段佛教历史的关键点也同样在于理清这两种发展模式的异同及其代表的佛学理念。通过这两种发展模式的比较,我们也可进而重新认识明末清初的中国佛教发展史。
参考文献:
[1]印光.印光法师文钞[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
[2]弘一.蕅益大师年谱[M]//蔡念生.弘一大师法集.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8.
[3]释圣严.明末中国佛教之研究[M].关世谦,译.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8.
[4]蕅益智旭.蕅益大师全集[M].台北:佛教书局,1989.
[5]朱封鳌.朱封鳌天台集[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377.
[6]荒木,見悟.張聖嚴氏の批判に答える:『明末中国仏教の研究』の所論について[J].中国哲学論集,1977(3):1-14.
[7]SHARF ROBERT H.Coming to terms with chinese buddhism:a reading of the treasure store treatise[M].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2:1-27.
[8]传灯.幽溪别志[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33册.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