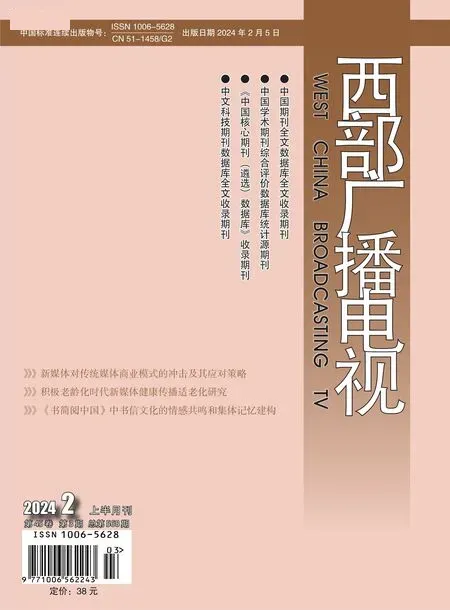视觉修辞视域下普通人物纪录片的视觉表达与情感传递
——以纪录片《四个春天》为例
赵秋实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
1 视觉修辞概念界定与纪录片选题视角转换
读图时代,随着图像逐渐成为主流表意符号,视觉文本也进入修辞学的学术研究视野,成为学者关注的新兴领域。1964年,罗兰·巴特最早提出“图像的修辞”,将视觉修辞包含的信息类型分为语言信息、图像信息范畴中直接意指的外延图像信息、含蓄意指的内涵图像信息三类。国内关于视觉修辞概念的界定最早由陈汝东提出,他认为视觉修辞是一种以语言、图像以及音像综合符号为媒介,以取得最佳的视觉效果为目的的人类传播行为[1]。此外,刘涛也对视觉修辞进行了概念界定:“所谓视觉修辞,是指强调以视觉化的媒介文本、空间文本、事件文本为主体修辞对象,通过对视觉文本的策略性使用,以及视觉话语的策略性建构与生产,达到劝服、对话与沟通功能的一种实践与方法。”[2]这也体现出对视觉符号修辞功能和意识形态内涵的考察。目前,国内学者对于视觉修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视觉修辞理论发展范式、视觉修辞理论在媒介文本中的实践运用、对空间文本和事件文本的视觉修辞应用研究这三个方面。纪录片作为一种影像工具,自然而然参与到了视觉修辞的实践当中,并通过对镜头语言、构图、景别、色彩及画面场景的塑造和呈现,使视听语言符号意义体系更加系统多样,让观众能够感知媒介文本的含蓄意指。
在我国,着眼于普通人的纪录片作品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以吴文光、蒋樾等为代表的创作者,宣传“独立制作”理念,以平视的角度记录百姓日常生活,使纪录片回到现实。这场在新旧世纪之交踏浪而来的“中国新纪录运动”完成了对普通民众的命名,并最大限度赋予这个群体某种主体性。21世纪以来,不少作品以平民化视角来回顾历史、反思现实、憧憬未来。社会大众的审美趣味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倾向于选择那些具有心理接近性的作品,更强调在作品中感受创作者对他们精神世界的关怀,以寻求来自艺术本身和个人本体所需要的审美体验。由此,以普通人着眼的纪录片作品逐渐成为人物纪录片的重要分支。近年来,以普通人群为拍摄对象的纪录片逐步增多,不仅很多成名导演选择将镜头对准普通人群,很多刚刚入行的新人导演也倾向于将普通人群作为拍摄对象[3]。如《人生第一次》《如是生活》《生活万岁》等纪录片都着眼于生活中的普通人,用以小见大的表现手法讲述故事,刻画人物性格、传达情感力量。
纪录片《四个春天》于2019年1月4日在中国上映,以导演陆庆屹居住在南方小城的父母为主角,以2013年到2016年的“四个春天”为故事线,记录了父母及子女在四年光阴里的生活碎片。该片上映一个月后,便获得1 043多万元的票房,这对于国内小成本纪录片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成功。除此之外,该片还获得了第12届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纪录片、第55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和最佳剪辑两项提名。从视觉修辞的视角出发,《四个春天》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离不开对语图文本的巧妙配置和对视觉修辞手段的策略性使用。要想将这些元素符号综合起来,就要充分考虑修辞手法中的语言、图像和综合视觉修辞三个元素。因此,本研究借鉴克雷斯和凡·勒文对于视觉语法的分析路径,和刘涛所提出的关于媒介文本的视觉修辞方法,关注图像体系下的图像视觉修辞和综合视觉修辞,对纪录片《四个春天》的视觉表达与情感营造策略进行分析。
2 视觉图像:基于劝服目的的画面框选
视觉文本作为纪录片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视觉符号中的元素来吸引、锁定观众的注意力,并进而由“眼”入“心”,建构图像故事和意义。克雷斯与凡·勒文将视觉符号的意义体系分为表征意义、交流意义和视觉构图意义三个层次。表征意义主要反映图像文本中元素结构和叙事关系,交流互动意义旨在说明图像作为一种媒介在生产者与观看者之间的交流方式与认知态度;视觉构图意义强调图像整体层面的要素合成逻辑和协同内涵。本文将从以下三方面展开,探析《四个春天》的视觉文本表意过程。
2.1 表征意义:认知维度下的故事叙述
纪录片的表征意义主要通过镜头来展现,镜头中的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环境、整体与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往往呈现出修辞特性,这种修辞也是一种影像作品情感传达的重要方式。
纪录片《四个春天》中,创作者通过对镜头的把控和画面的选择搭建视觉框架,使观众通往图像符号的表意系统。片中有一段是在大姐陆庆伟去世之后,父亲在电视上再次播放她生前唱歌的画面,镜头先聚焦于电视中的内容,随后后移镜头拍摄母亲潸然泪下的画面,通过镜头的调用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至苦呈现在观众面前。与之类似的,还有母亲谈起死亡时,镜头逐渐拉远模糊,给观众渐行渐远之感。
此外,近景和特写镜头的使用,在表现极强的画面张力的同时,也强化了视觉文本的表意性。在《四个春天》中有很多特写镜头,如当姐姐陆庆伟给父亲打电话时,父亲紧捏电话线的手的特写;在姐姐病重时母亲手中不停转动着的佛珠的特写;在姐姐病床前的父亲紧锁眉头的特写,等等。这些镜头的运用将观众带入情感语境之中,将拍摄人物的内心活动传达给观众,同时调动起观众的情绪。
片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对长镜头的使用,这种拍摄手法看似简单,却能达到“清水出芙蓉”的惊艳效果。在纪录片创作过程中,长镜头常常作为一种特殊的电影语言来还原真实环境与现场气氛。如在纪录片《生门》中,导演通过长镜头记录产区医生、病人及家属的状态,带给观众较强的真实感、现场感与参与感。在《四个春天》中,长镜头主要用在一家人日常活动的呈现过程中。如在记录父母登山踏青时,导演采用持续2分钟的完整镜头呈现了父母一路上的欢歌笑语,将父母积极坦然的生活状态展现得淋漓尽致。借助这些一气呵成的长镜头,导演朴素而真切地展现了这个家庭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进一步加深了故事的情感内涵,引导观众思考家庭和生活的真实本质。
2.2 互动意义:对话模式下的观众“入场”
纪录片作为一种传情达意的重要工具,并不只是创作者的“自我陶醉”。创作者是把影像作为媒介,向受众传递观点、态度,进而达到使观众产生情感认同的目的。纪录片生产者与观看者的无接触交流也将围绕纪录片的情节推进而展开,这个“传递—领会”过程中所产生的意义即可称为视觉符号的互动意义。互动意义的构建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其一是影像创作者利用视觉图像传播视觉信息;其二是观看者通过视觉共鸣对信息进行解码并与生产者互动,从而达到类似面对面的沟通交流的效果[4]。
在创作《四个春天》时,创作者通过对图像文本的选择性使用,让受众在观赏中获得其想要传达的图像意义,并通过凝聚特殊情感的共情性视觉符号,使观众产生自我身份的代入与个人情感的映射。如春节前夕母亲亲手制作的香肠、腊肉,父亲动手写下的春联。这些具有共识性的传统文化符号增强了观众内心的熟悉感与亲近感,与观众形成关系连接,使观众成为故事的“感受者”和“亲历者”。
《四个春天》的互动性同样体现在创作者的拍摄角度和拍摄手法上。从角度的选择上,父母家中“回”字形的房屋结构赋予了创作者更大的发挥空间。创作者从“天井”俯瞰的视角拍摄池塘中的金鱼、母亲在院中跳舞、父亲为母亲染头发,等等。这种独特的角度让观众仿佛置身于家庭空间之中,近距离感受方形天井小院中的人间烟火。在拍摄手法上,创作者并没有过多炫技,只是平实地记录下生活的柴米油盐与生老病死,手持拍摄导致画面的轻微抖动不仅没有影响观感,反而带给受众更多参与感,仿佛进入情景之中去感受人物的故事。
2.3 构图意义:整体视域下的符号协同
纪录片作为纪实性极强的艺术作品,画面感、艺术感和审美价值的呈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构图。创作者不仅仅要考虑某单个元素的呈现,更要立足于整体性视角,通过对视觉元素符号的巧妙布局,力求在真实记录的同时增添作品的观赏性与叙述的说服力。
纪录片《四个春天》充分发挥画面构图对于视觉表意的重要意义,通过不同的构图形式将创作者的情感倾向浸润其中,帮助观者解读画面意蕴内涵。在拍摄父母的日常生活片段时,为了体现出父母对生活的乐观与热爱,导演在后期剪辑的时候巧妙地将相同时间下两个不同空间的镜头并行,并以“一堵墙”作为画面的中心线,形成了对称式构图,如父亲在一个房间里哼着曲,母亲戴着老花镜在另一个房间踩着缝纫机。通过后期处理,将父母两人温情且平和的生活表现得淋漓尽致。此外,纪录片还通过对景深的控制以凸显被摄主体,将视觉中心聚焦于被摄主体,引导观众的视线,进而达到突出强调的效果。
光影和色彩的使用,不仅能够增添画面的氛围感和故事感,而且能够把人物融于画面之中,增强画面的视觉感染力与表现力。《四个春天》中随处可见对光影的把控,其中有一处父亲在夜色下拉小提琴的画面,沉醉于琴声中的父亲被微弱却温暖的灯光笼罩,将父亲的多才多艺与对生活的热爱可视化,为观众营造出一种沉浸感。纪录片接近尾声时,两位老人对着阳光吹蒲公英的画面同样利用了光影,温暖阳光照耀下飞舞的蒲公英种子与老人的笑脸交相呼应,也暗示着他们从女儿离开的阴霾中逐渐走出,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与热情。在色彩处理上,影片使用原汁原味的色调,质朴纯真不多加修饰,从而让人更多去关注家庭人物真诚温暖的一面。
通过真实记录和视觉表现的碰撞与交汇,纪录片的构图意义也由此展开,构图、景别、景深、光影的凸显,对于人物个性的强化和情感的烘托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3 综合视觉修辞:情感传递的话语目的
从纪录片的元素构成上看,语言和图像都是其不可或缺的元素符号。语言主要包括字幕语言、旁白语言、音乐语言等;图像即画面中所呈现的视觉内容[5]。在纪录片中,语言和图像是共生共存的,如果说视觉图像的组合构建了纪录片的行进轨迹和发展趋向,那么语言则为观众对视觉图像的解码锚定意义框架和释义范围,它们共同参与了纪录片的意义建构活动与情感传达过程。
3.1 隐喻策略:象征性视觉修辞深层意蕴的显现
影视作品中的隐喻蒙太奇与文学作品中的隐喻有着相似之处,最终目的都是使观众由一事物引起对另一事物的联想,即通过“喻体”来认识“本体”,进而达到喻义、象征等效果。纪录片作为一种影像形态,也可以通过隐喻策略来达到顾左右而言他的视觉效果,创作者可以通过图像、音乐、音效等多方面的协同配合来达到隐喻的话语目的。
在《四个春天》中,创作者通过隐喻策略的使用丰富画面的层次、通过物象符号来辅助影像叙事,使表意更加具体明晰。在片中,家中的燕子四年间来来去去,在房檐上搭窝筑巢,虽然叽叽喳喳,父亲却异常欢喜。在这里,燕子作为一种意象也是对漂泊在外子女的隐喻,燕子飞回也对应着家中儿女每年春节时归家的场景,燕子飞来时是开心激动的,当燕子离开时却又难掩失落,这正是子女们一个个离家时父母心情的写照。这种构成性隐喻将父母对子女的不舍和牵挂自然而然地表露出来,直击观众内心。片中还有父母两人携手去山上踏春的场景,父母哼唱着山歌、穿行在小路上的画面与山间潺潺的溪流并行,这也映射了父母的爱情,两人的相伴相守正是这样细水长流。
通过对视觉元素在聚合轴上的编排和组合,形成不同的视觉感应和观看体验,使得隐喻产生内在意义与价值。
3.2 转喻策略:抽象情感的可触摸化
在视觉修辞学中,隐喻的基础是相似性,具体体现为跨域映射;转喻的基础是临接性,具体体现为同域映射,通过本体与喻体所处的同域范围中的符号发挥指代功能,借用视觉表达出某种抽象内容,理解原本难以表达的晦涩意义。在视觉转喻中,转喻又分为指示转喻和概念转喻两种指代关系。概念转喻即通过编织具体可见可感知的视觉元素,以具象思维来传达抽象的意义内涵。
在《四个春天》中,通过概念性转喻将抽象情感诉诸具体可感的事物,将情感可触摸化,从而强化情感共鸣。如当父亲母亲送别过完年离开家的儿女时,母亲走进去却又走出来,一直目送着远去的汽车直到看不见,虽未言语,却使父母对子女的爱具象化;在姐姐葬礼这一极度悲伤的场合,导演没有刻意营造悲情氛围,而是用两个老人唱孝歌的画面让观众感受到撕心裂肺的伤痛;在第三个春节姐姐已经去世,父母还是习惯性地为她准备了一副碗筷,“把位置留给姐姐”“庆伟来吃中餐啦”,没有过度煽情,仅仅是一句习以为常的惦念就将对已故女儿的思念倾泻而出。
隐喻和转喻对普通人物纪录片发挥视觉修辞意义有着重要的作用。二者的相互勾连与相互作用,使观众在联想机制作用下产生共情,引发观众共鸣,抵达视觉修辞实践的彼岸。
4 结语
笔者结合视觉修辞的相关理论,从纪录片的表征意义、交流意义、视觉构图意义,及视觉修辞的隐喻、转喻策略几个方面对纪录片《四个春天》的视觉表达和情感传递过程进行了分析。《四个春天》刻画了普通人的日常,引发了观众对于家庭、亲情、父母和儿女之间关系等多个命题的深思,彰显出现实主义人文关怀,也为以普通人物为主体的纪录片创作提供了一定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