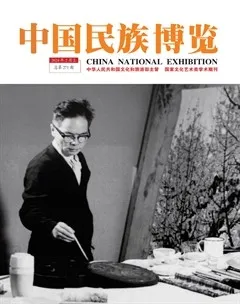“弘治中兴”的革新解读
杨秉岱
【摘 要】“弘治中兴”是自明代以来史学界用于界定明孝宗统治时期(公元1488—1505年)的特定术语,它代表着史学界主流观点对于明孝宗治下达到的“盛世”[1]局面的认可。[2]对“弘治中兴”的政治实践进行剖析,可以发现同明代弘治时期士大夫政治的极盛是分不开的;皇权引导下的士大夫政治在现实政策上进行人事更新和加强监察为主的吏治澄清;在对皇权的约束上强调君德观念的复兴;在对经济政策的调整上要求渗透民本观念。“弘治中兴”因士大夫政治盛行而成为理想实践的标杆,表现出士大夫的精神旨归。
【关键词】弘治中兴;民本观念;士大夫;吏治澄清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4)03—029—06
“弘治中兴”作为明代中后期[3]统治阶层实现“朝序清宁、民物康阜”这样较为成功的治理时段,历来为文人士大夫以至后来的史学界学者所称赞。然而对“中兴”乃至“极盛”的历史印象持怀疑乃至批判观点的,亦不在少数。基于各类文献档案及考古资料,学界从多边视角展开了对以明孝宗与“弘治中兴”为核心的弘治朝研究,不过多着眼于对“弘治中兴”是否名副其实的探讨。在界定明孝宗统治的成果到底是“极一代治功之盛”抑或“都是些溢美之词”[4]之前,也应当能够对“弘治中兴”这一概念被建构起来的原因有所把握。在特定的中国古代皇权政治体制下,弘治时期政治实践的本质决定“弘治中兴”被迅速建构起来的原因。①弘治一朝的为政,本质上是皇帝专制的“政统”与士大夫政治的“道统”达到较为契合的统一,通过“敬天法祖”“勤于民生”的执政措施,以士大夫政治的膨胀为表现方式,最终指向在事实上“海内乂安,户口繁多,兵革休息,盗贼不作”、[5]在精神上“其学独正,其治独隆”的道统实現。这种“活着的祖宗”[6]在成化朝、正德朝的前后对比之下,伴随着明代中后期日渐加深的政治统治危机和社会激变转型进一步放大,持续震铄着整个士大夫阶层。本文立足史学文献,分析“弘治中兴”概念建构与弘治时期士大夫政治膨胀的内在联系,旨在找寻以士大夫阶层为主要动力塑造“弘治中兴”政和人兴之盛景话语的精神旨归。
若言“弘治中兴”是“政统”与“道统”的统一,便不得不对这两种政治观念进行剖析。在较长一段时间的特定政治场域下,中国的历史研究与救亡图存的时代任务紧密联系起来,这使得自近代以来,中国古代政治运行常被以“东方专制主义”(despotisme oriental)为主的绝对君主专制主义观点一以概之。[7]然而当我们将弘治时期作为时间胶卷上切割下来的一角进行政治实践运作的观察,便发现它绝不能以简单的绝对君主专制粗暴概括,“中国之士则自有统,则所谓道统。此诚中国民族生命文化传统之独有特色,为其他民族之所无”。[8]
道统,实质上是以儒家思想为根本价值观的明代士大夫阶层参与政治,在民本观念、忠君观念的方法指引下,规劝乃至谏言皇帝在认知和实践上达到“敬天法祖”“民惟邦本”,完成“得君行道”,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作为衡量准则,为达成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个人政治追求抱负,并最终建立起一个恢复抽象概念中“三代之治”这样理想政治秩序的理想国度的宏伟蓝图。
谨稽经史,伏羲、神农、黄帝号称三皇,盛德大业被于万世,使天下后世三纲正,九法叙,三圣人之功莫大焉。故尧、舜、禹、汤、文、武相承而为道统,孔子、颜、曾、思、孟相传而为道学统,以续其业学,以传其心,后世有天下,百举不违其成法,此其所以继天立极而为帝王之所宗,岂但阴阳医方而已哉?[9]
在明代士大夫的精神观念看来,道统就是从尧、舜、禹、汤、文、武等先贤圣王传承下来并为本朝祖宗所承继的终极法宝。不论是明初宋濂的“其道则仁、义、礼、智、信也;其伦则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也。其事易知且易行也,能行之则身可修也,家可齐也,国可治也,天下可平也”[10],还是杨士奇的“道之体广大光明,配乎天地日月,而其实不离乎彝伦日月之间”[11],明代士大夫自恃为道统的唯一诠释者,并将这一能够启沃圣心的原则始终贯彻在参与政治实践的过程当中,由此形成了以实现“道统”、要求皇帝避免成为“独夫”[12]式的绝对独裁,皈依于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并在道统原则下为政的士大夫政治。这种士大夫政治的内涵,弘治时期以前的方孝孺就已经给出了精辟的总结。
四海之事,固非一人之所能知也,君人者能正一身以临天下,择世之贤人君子,委之以政,推之以诚,而待之以礼,烛之以明使邪佞无所进其谗。信之以专,使便嬖不得挠其功。簿书之事不使亲其劳,狱讼之微不使入其心,惟责之以用贤才,治百官,变风俗,足民庶兴礼乐而绥夷狄。如农之望穑,旅之望家,必俟其至而后已。[13]
与之相对的就是政统,也即私天下观指引下力求实现绝对君主专制的独裁倾向,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君主专制不断发展、皇帝个人权力日益增强的结果。明朝开国之君朱元璋虽然在以祭祀、学校教育、科举考试三位一体下的儒学秩序恢复中提倡“君独用则居职废,臣不任则悬事劳,是度之间,贵在一德一心,以共济天下”,但从其三十一年的为政风格来看,塑造出的洪武式政体,以君主独裁为底色,以士大夫为“皇帝旨意在地方社会施行者”[14]的工具角色,士大夫的主体地位无法得到体现。政统压制道统的政治局势直到“后祖制时代”[15]逐渐发生了变化——以儒家思想渗透的皇储教育在仁宣时代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君臣双方在政统和道统上达成了一致,能够“君臣一体,务始终同心,庶几可以共图利安”。[16]
弘治时期在政统与道统上达成的统一是罕见的,这也是驱使士大夫阶层极言弘治政治之盛,“国家积岁熙洽。鸣吠烟爨,蒸蒸如也,岂不称盛际哉”[17]的主要原因。其政治底色就是政治改良方针同士大夫诉求的完美契合,是政统与道统在政治改良、恢复祖制上达成的空前统一。反映于现实实践,即是:政治上以吏治澄清为朝政更新的主体地位凸显、以君德观约束皇权保证士大夫政治、经济政策上贯彻民本观念。
一、“励精新政”[18]——士大夫主体地位的凸显
孝宗在即位之初的诏书中鲜明地表达了他的政治诉求。“各边开中引盐及籴买粮草,俱不许势要及内外官员之家求讨占窝领价上纳”,不仅这一条明确要求进行革故鼎新[19],通篇即位诏书明确表达了将对前朝弊政进行清理,并以限制势要为核心,也就是限制延申皇权的泛滥——这恰是对成化朝皇帝政治凌驾于士大夫政治之上,因缺乏合理制衡机制造成朝政纠正——其在朝政革新之上明确了以人事更新和加强监察为主的吏治澄清。
在颁布即位诏书后,孝宗即开始布局新政。以李孜省、太监梁芳和外戚万喜为代表的前朝余佞遭到贬斥,不到一个月后,有旨汰传奉官,罢右通政任杰、侍郎蒯钢、指挥佥事王荣等二千余人,又罢遣国师等一丁数百人。巨大的人事变动使得“先朝妖佞之臣,放斥殆尽”。分析孝宗在即位之初的人事变动处理,可以明确其在特定的皇权更替场域下敏锐地抓住了三个核心问题:皇权延伸产生的宦官政治、外戚政治造成士大夫群体的妥协、退让,破坏了士大夫在明代皇权专制下治国的主体地位;皇帝独裁支配人事任免权直接造成士大夫政治参与空间的压缩;皇权支撑下泛滥的文化思潮严重动摇了儒家政治理念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这三个核心问题正是造成士大夫政治在成化朝一蹶不振的主要原因。孝宗上位就以暴风骤雨之势翦除了士大夫在政治、文化上面临的危机;随后与“破旧”相对的“立新”则将扶持士大夫政治,争取政统与道统相统一的改良目的直白地展现出来。
(一)任用贤能,刷新吏治
后世史家对弘治时期“众正盈朝”的描述以肯定居多。任用贤能的方针自孝宗即位就被确立并贯彻始终。在内阁阁臣和吏部尚书两处决定吏治风向的要冲位置,孝宗迫使万安致仕后立即使性格温和宽容,易于凝聚人心的徐溥入阁参预机务,②并使成化年间就因与佞臣小人格格不入而极富名气的王恕火速上任吏部尚书以执铨选。③更新吏治的效果立竿見影,直至“冰谏则有王恕、彭恕;练达则有马文升、刘大夏;考成则有刘健、谢迁;文章则有王鏊、丘浚;刑名则有闵桂、戴珊”;在弘治中后期内阁相继引入刘健、谢迁、李东阳等名弼后,终于形成了“……而王恕、何乔新、彭韶等为七卿长,相与维持而匡弼之。朝多君子”的良好治况。孝宗在人事选择上的主要原则就是能够实现政治改良、引导朝风向善、推动政统与道统契合,这势必与坚持儒家治国平天下理想,渴望得君行道的士大夫共鸣,在政治实践上也势必会造成士大夫政治膨胀、主体地位凸显的结果。
(二)兼听纳谏,强化监察
在士大夫政治得到发展的基础上,为保证士大夫集团的行政能力,孝宗君臣加大了对统治集团内部的纠察力度;一方面广开言路、积极纳谏。孝宗即位之初就形成“是时上更新庶政,封章旁午,言路大开”[20]的良好局面,成化朝被压抑的言路迅速活跃起来,科道官利用强化士大夫参政地位的宝贵机会提出了许多切中时弊的谏言。这种活跃的士大夫政治不仅使当朝官僚陶醉其中,连太学生也积极参与进来:初即位时,孝宗将在万岁山建棕棚,太学生虎臣当即“上疏切谏”。祭酒费訚担心自己受牵连,“银铛系(虎)臣堂树下”。但不久官校传令,把虎臣召到皇宫的左顺门,“传旨慰谕曰:‘若言是,棕棚已毁矣”。费訚听到消息十分惭愧,而虎臣则从此名闻都城,“顷之,命授七品官,为云南知县”。孝宗积极纳谏的事例贯彻在十八年的治政当中,几乎到了只要是积极谏言无不接受听从的地步,如弘治十年(1497年)侍讲学士王鏊以“文王不敢盘于游畋”讽谏孝宗,他并不怪罪,反而对诱导他游乐的宠宦李广说:“讲官所指,殆为若辈,好为之”,之后“遂罢游猎”。对士大夫政治的尊崇甚至不遑多让于仁宣治世。④
另一方面,士大夫集团在孝宗的支持下,进一步完善监察制度,在皇帝通过积极纳谏约束政统局限性的同时,也在尽力保持道统的纯洁性。在孝宗多次指示吏部、都察院“考察进退人才,务得实迹以闻”的支持下,最终弘治十四年(1501年)形成了为“察其行能,验其勤怠,以定黜陟”,在外司府以下官三年一考察,两京及在外武职官五年一考察,两京五品以下官六年一考察的“京察”和“大计”,并一直沿用至明末。
二、“在古罕闻”——君德观念的强化
君德观念在宋明理学兴起以后,本质上是儒家思想以道德约束去削弱君主权威,巩固士大夫政治的制衡手段。道德约束相较“民惟邦本,本固邦宁”[21]的民本观念而言,更富有抽象哲理和惩戒的不可预测性——因为儒家传统政治哲学的道德约束力,大多来自于“天”这一抽象权威和直接关系到君主统治合法性的“祖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22]的观念根深蒂固于专制皇帝心中,这使得抽象的、潜移默化的道德约束力相比远离宫廷的百姓生计,更易为君主所体察和警戒。“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23]正是这种君德观的最好诠释。
弘治时期将君德观约束下的皇帝政治展现地淋漓尽致,其主要表现在对待政治礼仪形式上始终贯彻“敬天法祖”,在君臣关系上坚持礼敬士人,以至于传统史家将他与以礼遇臣僚著称于史的汉文帝、宋仁宗,不但依据功绩称他是“中兴之令主”,更以道德原则认定“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三代而上,成、康、启、甲尚矣。降是,其汉文、宋仁乎?乃予所闻,于明之孝宗近是”。
(一)恢复祖制,强化仪式
孝宗的“中兴”是一种尝试在明中期社会已然发生巨大变迁的背景下将整个国家拉回到洪武旧轨的保守性改革,这一点学界已有许多论证。[24]正如商传先生所言,“弘治朝政治路线的核心是‘法祖用贤,这也就必然决定了弘治朝政治的一定程度上的保守性”。明孝宗九岁开始出阁讲学,至十八岁即位,接受了完整的儒家思想教育,侍讲学士都是谢迁、李东阳等学问深奥的大儒,侍候他的是儒化宦官覃吉。再加上成化朝为缓和社会矛盾大力尊孔崇儒、提倡忠君仁孝的崇儒氛围的熏陶,使明孝宗在思想上受到较大影响。
在为政的路线选择上,孝宗天然地受到儒家思想影响,追求“三代之治”,并将恢复祖制视作达成终极目标必须完成的步骤。恢复祖制实际上就是恢复“敬天法祖”观念下的政治礼仪,强化士大夫的政治话语权,即通过政治礼仪来培育儒家士大夫眼中的圣人君主,完成对皇权的驯化,通过君主的德行来实现道统理想。在恢复祖制的措施中,最为士大夫所称赞的是经筵日讲制度和午朝的恢复。
“经筵之设,所以讲明道学,关系甚重,故侍从皆用文学之臣。”[25]这一为强化皇帝儒家教育、实现皇帝为士大夫政治站台的教育措施,在正统元年设置后,便被荒废;午朝,则是景泰初年为了补充早朝议政之不足,议定“臣民之言事”而设,并“府部奏事毕,撤案,各官退,有密事,赴御前奏”,其后也在成化年间被弃止。这两项被视为“启沃圣心”、也是皇帝勤于向善的标志,都在弘治元年被重新启动,儒臣的治国策略与道德修养对君主的影响明显增大,这表现在孝宗时常在经筵、午朝中得出治乱经验并付诸于政治实践,甚至于开辟文华殿议政,以在早朝与午朝之余的时间召见内阁阁员,与阁员共同商议治国之道,谈论朝政事务。
(二)亲近儒士,礼遇群臣
孝宗深受儒家文化影响,自然对“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君臣相处原则有更深刻的把握。孝宗之礼遇群臣的例子不可胜数,明人对他尊重大臣的举措给予了高度评价:“留心政事,优礼大臣,每賜召对,几如古之昼日三接。此本朝极盛际也。”[26]
即位之初,他即召南京兵部尚书马文升为左都御史,并赐大红织金衣一袭,“盖上在东宫时,素知其名故也”。面对王恕“有不合,即引疾求退”他总是“温诏留之”;刘大夏奏事太久,“欲起不能,上命太监李荣掖大夏出。”;弘治十八年(1505年)戴珊因老病请求致仕,孝宗直言“主人留客坚,客且为强留,独不能为朕留耶?且天下尚未平,何忍舍朕!”动情之处以至掩面哭泣。
孝宗礼遇群臣的态度不仅局限于他绝对信任的左膀右臂,还遍及中下层官吏。弘治十七年(1504年),在经筵进讲时,太监李荣认为讲官讲章中“以善道启沃他”的“他”触犯了忌讳。孝宗听后,根本不把它当成什么罪过,为了避免讲官因此而观望起来,不敢直言规谏,特地召来刘健等说:“讲书须推明圣贤之旨,直言无讳。若恐伤时,过为隐覆不尽,虽日进讲,亦何益乎”,而且又明确要求他们:“传语诸讲官,不必顾忌。”
如此礼贤下士的态度,自然引起了士大夫政治的蓬勃发展。弘治朝士大夫在皇权的肯定下,对自身主体地位的自我认同、对推进道统、政统深度融合导向内圣外王的三代之治有着明代中后期罕见的强烈的责任感。孝宗倚靠的核心官员团体,无不“感殊遇,自奋励”,抱着“圣明如此,臣等敢不尽心”的使命感尽职尽责,左都御史戴珊甚至感动于孝宗挽留情感之真挚,直言“死此官矣”,最终因病逝于任上。而整个士大夫群体亦进言不止,仅《明史纪事本末》中孝宗针对谏言回复的“嘉纳之”就达14处,而表示肯定支持态度的回复则达19处。应当承认,孝宗朝得以持续维持较好的治理局面,同孝宗主动亲近士大夫有着深刻的联系。
三、“泽入人深”——民本政策的奉行
前文已述,士大夫群体期待实现政统与道统合一的理想政治运作,其限制君权或者说是期待君主能够达成的观念即是“敬天法祖”和“民惟邦本”。明人对于士大夫政治实现的追求,在于最终实现道统秩序的“三代之治”,而这种政治理想的精神旨归则一定要指向民本观念。他们要求君主敬重的抽象权威“天”一定要具象化为普天下的民生,从保证士大夫统治地位的合法性出发,他们作为唯一能够诠释“道统”的群体,强调君主要想获得“天”的支持就一定要遵从儒家的治国理念,而“民”正是中和“君”“臣”和“天道”的最佳联系者。
故天之立君,所以为民,非使其民奉乎君也。然而势不免粟米布帛以给之者,以为将仰之平其曲直,除所患苦济所不足,而教所不能不可不致夫尊荣恭顺之礼。此民之情,然非天之意也。天之意以为,位乎民上者,当养斯民;德高众人者,当辅众人之不至。固其职宜然耳,奚可以为功哉。⑤
从稳固政权统治的现实角度讲,“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弘治时期的士大夫们鉴于荆襄流民大起义的前车之鉴,为了避免政权覆灭就一定要缓和阶级矛盾、尽力去照顾民生;而从政治道德的角度讲,宋明理学的道统实现以“为生民立命”为开端,并最终导向“为万世开太平”,不讲求民本观念势必不能达成最终理想。弘治时期的理学名家及内阁主心骨之一的邱浚因此而强调:“‘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之言,万世人君所当书于座隅以铭心刻骨者也。”以至于直言“君之所以为君也以有民也,无民则无君矣”。[27]
因此,孝宗朝君臣的经济更新集中在厚实民生之上,即对于内廷为核心的皇室用度的限制和及时赈济灾民、减税惠民。
(一)力行节俭,约束剥削
孝宗一朝施行的是明中后期少见的针对内廷耗费进行节制的节俭方针。弘治元年,都御史马文升上言:“一应供应之物,陛下量裁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孝宗“命光禄减增加供应”。弘治二年(1489年)十一月,左侍郎倪岳上疏说:“当今民日贫,财日匮,宜节俭以为天下先。”并将具体措施直指内廷,“减斋醮,罢供应,省营缮。”孝宗“俱采纳焉”。然而同时应当看到,内廷消耗与满足皇帝个人私欲直接相关,在皇权专制的时代,即使士大夫政治有所膨胀,亦难以完全阻止皇权强行运行的结果,在孝宗执政中期,宠信太监李广,节俭的方针流于形式。弘治十三年(1500年)户部奏称,光禄寺几年内因大兴斋醮、驱使工役借太仓银达150万两之巨。这种局势直到执政后期随着孝宗重新抑制皇室支出才再次改变:弘治十七年(1504年)“织造,斋醮皆停罢,光禄省浮费巨万计”。与此同时,下令“皇亲及权豪势要之家奏讨土地,敢有安将民间地土投献者,投献之人,问发边卫永远充军,田地给还寺观及应得之人管业,其受投献家长并管庄之人,参究治罪”。兼并现象也得到相对改善,“一时贵戚近幸有所陈请,一裁以法,皆敛不得肆”。
(二)减免税赋,赈济灾荒
孝宗君臣由于大都经历过成化朝的荆襄流民大起义,又怀有“致君尧舜”、实现理想政治的目标,对于缓和阶级矛盾、减轻人民负担,采取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势在必行。终孝宗一朝,“减免数额在 700 万石一下的,只有一年;减免 700 万石到 800 万石的有五年;减免800 万石到 900 万石的有十年;减免 900 万石以上的有两年。孝宗朝所免赋税的数额,为前后朝所不及”。[28]弘治一朝,自然灾害不断频发,是整个明代自然灾害高发严重的时期,涝、旱、雹、虫等多种灾害交替发生,且全国降水量普遍较大,黄河泛滥达10次之多。这就使得弘治一朝因为灾害而免去的税赋总额高居明代历朝之首。同时,弘治一朝针对受灾地区往往减税、赈济双管齐下:弘治二年(1490年)二月十日,“免河南被灾秋粮”;同月十二日,孝宗全部批准户部请免南畿、湖广税粮的要求。弘治四年(1491年)八月,“以水灾,停苏州、浙江今年织造”。弘治六年(1493年),全年中“以灾蠲者,两京外,蠲山西太原诸府平阳诸县夏税,河南开封诸府夏税之半,祥符诸县秋粮。又免沈阳卫屯粮六万四千余石”。弘治十一年(1498年),免南畿、山西、陕西、广东、广西、被灾税粮……这样的免赋、赈济一直持续到弘治朝结束,次数之多、范围之大,使得地方官员亦能以身作责,开展自我接济,如弘治六年巡抚王霁先后请发帑金五十余万,米二百余万石,“凡活饥民二百六十余万”。
通过约束奢靡和减赋惠民,孝宗朝的税赋收入由2500万石增至2700万石,“成为明朝中叶岁入的高峰”;人口由弘治元年的50,207,934口增至十七年的60,105,835口,民本政策见效较为明显。
四、“不急近利”——面向士大夫政治以外的用意
明代自成化、弘治年间已发生着深化的政治统治危机和激烈的社会转型,这一观点已是学界大都认可的。[29] “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已有隐然欲变之势。弘治朝的兴利革弊,必然革及这些变化”,商品经济的发展首先使得一批商人凭借财富的优势,能够使用明初生产力下无法消耗的奢侈品——然而对奢侈品的使用大多也有着等级区分的政治意义;在新的生产力条件下,豪商们突破器物名用等级制度的约束,造就了整个社会日益汹涌的慕富风气,正如马克思所说,“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则”,[30]面对“以庶民而上比公卿;论财之风,以好合而直同商贾”[31]的社会风气,弘治君臣作为小农经济支撑起的旧制度统治阶层,对这种前所未有的时代变化,怀有本能的恐惧。他们在“敬天法祖”的观念下,以儒家思想的观念审视这种变化,便觉维护祖制、强化日渐松动的封建等级限制的必要:“我圣祖宗百有馀年之典制……俾自是而世守之,不迁于异说,不急于近利”,[32] “异说”“近利”自然是他们对这种变化模糊而又警惕的认识;由于豪富大多依靠供给内廷的奢侈品消耗以积累财富,在如此背景下,孝宗君臣强化节俭观念、提倡理学、扬起崇儒社会氛围的做法,自然也有了针对新变化的需要。
以强化节俭应对未知社会变化的方法,在弘治本朝不能说是彻底成功的,当孝宗统治中期沉迷佛道、专设醮行之时,注定了他的节俭对于限制社会前进、商品经济发展是收效甚微的。然而这种措施却被人为塑造出了强大的效果,在嘉庆、隆庆以后的士人文集中,常见到他们以不符史实的弘治追忆来否定现时的人心流变:“俗尚勤俭,民多殷富,男务耕读,女务蚕桑,服以木绵,屋蔽风雨,虽大族巨商婚不论财。[33]这倒也足可见士人们对于强化节俭之于防范社会激烈变化之真意的认同。
五、结语
客观审视弘治时期的政治实践,不论是孝宗统治中期宠信李广,劳民伤财;还是放纵勋贵宗室,致使土地兼并愈演愈烈;抑或革新程度极为保守,在根治顽症上踌躇不前,都不符合传统史家过度褒扬的美誉。应当说,“弘治中兴”本质上是一种人为生成的记忆,是明朝中后期深陷政治危机和晚明社会激烈变革的士大夫群体,在政治上再没能获得有如弘治朝的主体地位、达到弘治时期的士大夫政治的补救,为了弥补这种缺乏,需要生成新的再现性的记忆。
弘治时期达到了政统与道统、皇帝政治与士大夫政治的和谐统一,这实质上满足了士大夫阶层参与政治、实现道统理想的政治追求;孝宗的措施虽然是出于皇权的需要,却在事实上达到了强化士大夫政治的客观结果。孝宗一朝坚持的政治方针,符合士大夫群体对于更张朝策的需要,士人期盼的君德观得到完美贯彻,民本政策在事实上也达到了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经济发展、充实朝廷财富的实际效果,又因其法祖观念的保守性,对商品经济发展导致的统治阶级的本能恐慌有一定的抵制效果,可以说是对士大夫政治理想的一次较为成功的实践。弘治一朝因而被士大夫政治建构起了中兴的话语,并反复传送,直至后世士人浸氲其间,复而成为了一个合格乃至能上承三代的“盛世”,一个满足士大夫主体意识和士大夫政治要求的时代就这样被神化,定格在历史的长河当中。
注释:
①“弘治中兴”的功绩被确认的速度是惊人的,其在统治期间的士人文集就已有“中兴”之时语,而一经孝宗逝世,武宗即位,便在即位诏书中做出了定位,“治化之盛,在古罕闻”.
②据《明史·徐溥传》记载,徐溥“凝重有度”“从容辅导”“人有过误,辄为掩覆,曰:‘天生才甚难,不忍以微瑕弃也”.
③据《明史·王恕传》记载,王恕因其直言纳谏,在成化朝腐朽的朝臣當中鹤立鸡群,时人谓之“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
④仁宣治世下的君臣关系,笔者同王伟《明前期士大夫主体意识研究(1368—1457)》看法一致,即三杨领导下的士大夫政治仍然受到比较严格的皇权限制.
⑤(明)方孝孺.逊志斋集(卷2)[M].宁波:宁波出版社,2000.
参考文献:
[1](明)李东阳,等.明孝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南炳文,李小林.弘治“中兴”述略[J].南开史学,1981(2).
[3]万明.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4]王其榘.明代内阁制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9.
[5](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77.
[6]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北京:中华书局,1982.
[7]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主义说的知识考古[J].近代史研究,2008(4).
[8]钱穆.国史新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5
[9](明)胡广,等.明太祖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0](明)宋濂.文宪集[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社,2005.
[11](明)杨士奇.东里别集·代言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8.
[12](清)黄宗羲,撰.明夷待访录校释[M].孙卫华,校释.长沙:岳麓书社,2010.
[13](明)方孝孺.逊志斋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14]王伟.明前期士大夫主体意识研究(1368—1457)[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2.
[15]李哲武.太监李广之死与弘治朝政治[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19.
[16](明)佚名.明仁宗圣政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5
[17](清)谈迁.国榷[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58.
[18](明)费宏.明武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9]赵轶峰.明中期皇帝的即位诏——从景泰到嘉靖[J].古代文明,2013(1).
[20](清)夏燮.明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1]阮元.尚书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2]周振甫.诗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
[23]阮元.论语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4]李绍强.明孝宗个性与弘治朝政策[A].第五届中国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暨中国明史学会第三届年会论文集.黄山书社[C].1993.
[25](明)刘吉,等.明宪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6](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7](明)丘浚,大学衍义补[M].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8.
[28]沈鹏.明孝宗与“弘治中兴”[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4).
[29]陈二峰.明成化、弘治、正德时期社会变迁研究[D].郑州:河南大学,2006.
[30](德)马克思,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辑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31](明)贺钦.医闾集[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
[32](明)李东阳.大明会典[M].扬州:广陵书社,2007.
[33](明)蔡悉昭.赵州志[M].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62.
——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宋代士大夫群体意识研究》简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