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毛女》:中国现代歌剧史上的里程碑
郑学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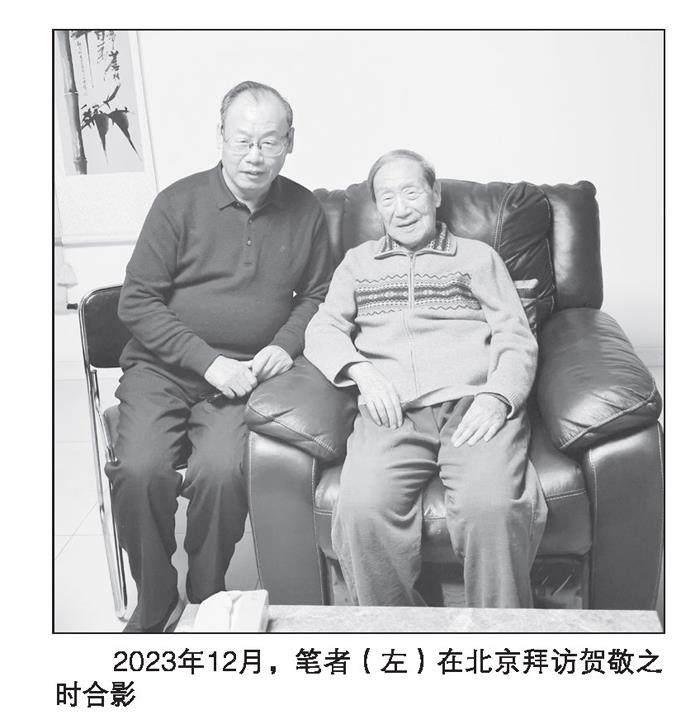
近日,贺敬之文学馆馆藏歌剧《白毛女》在1951年获得的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奖章及证书(2004年由写作者贺敬之捐赠)被山东省文物鉴定中心评为一级革命文物。歌剧《白毛女》是我国第一部现实主义新歌剧,在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是我国歌剧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高度的艺术性,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近80年来盛演不衰,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笔者曾多次拜访贺老,并查阅大量档案资料,将《白毛女》创作始末及产生的重大影响撰写成文,以飨读者。
賀敬之在剧本中融入家乡情结
贺敬之,1924年11月5日出生于山东省峄县贺窑村(现属枣庄市台儿庄区)。1937年秋,考入山东滋阳(现兖州市)第四乡村师范学校。同年底,日军渡过黄河,占领济南,学校只好停课,贺敬之回到家乡。1938年3月台儿庄战役爆发后,他先后流亡到湖北、四川求学,结识了一些进步同学,阅读了大量进步革命文艺作品,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参加“挺进读书会”,与同学创办《五丁》壁报。他还先后在《华西日报》 《大公报》《朔风》等报刊发表散文、诗歌。1940年春,他怀着对革命的追求,与3位同学毅然离校奔赴延安。他先入延安自然科学院中学部就读高中,后经何其芳面试考入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年仅16岁,是该系第三期学生中年纪最小的一个。1941年6月23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贺敬之受命执笔创作《白毛女》剧本时,刚过20岁。关于其原型,他在1946年撰写的《〈白毛女〉的创作与演出》中写道,这出歌剧源于晋察冀边区一个民间新传奇“白毛仙姑”的故事。在20世纪30年代,河北省阜平县某村一老农家有个十七八岁的女儿,聪明美丽,活泼可爱,父女两人相依为命。村里一个恶霸地主看上这个姑娘,想占为己有,便设计逼死老农,抢走其女儿。姑娘在地主家被奸污并怀孕,然而地主喜新厌旧,又打算续娶新人。在筹办婚事时,阴谋害死这位姑娘。地主家里一个善良的佣人得知后于深夜把她放走。她逃出来后藏身于大山中的一个山洞里,白天怕被人发现不敢出来,都是夜间出来觅食,不久生下孩子。由于长期生活在山洞里见不到阳光,又缺少盐,全身发白。她在一天夜里去山上的奶奶庙偷吃供品时,被村民发现,被奉为“白毛仙姑”,常献上供品。后来八路军解放该村后,工作组进村开展工作,得知这一传说。为了弄清真相,工作组的干部和村民兵队长携带武器,在一天夜里隐蔽在奶奶庙神坛一侧暗处,等“白毛仙姑”前来拿供品时,解救了她,将她带回村里。她又重新作为“人”,开始过上新生活。
1942年春,周巍峙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到晋察冀边区宣传演出,搜集到这个故事。1944年4月,西战团奉调回到延安。在鲁艺召开的欢迎会上,有人向院长周扬讲述了这个故事,于是,周扬萌生以“白毛仙姑”为题材创作一部大型新歌剧的想法,要体现劳动人民的反抗意识,以鼓舞人民斗志,去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他把这个任务交给戏剧系主任张庚。张庚立即组成创作班子,对剧本的主题和情节进行讨论研究,商定由西战团成员邵子南执笔,因为他熟悉晋察冀边区的生活和“白毛仙姑”的故事。据喜儿扮演者王昆回忆,她看过邵子南写的“白毛女”题材的一首长诗,是用秦腔配曲的。在首场戏试排时请周扬审看。周扬认为,不能搞成旧的戏曲形式,要写成一部民族的新歌剧。
根据周扬的意见,张庚召集创作组讨论,决定由贺敬之执笔重写。贺敬之、马可曾在1950年《白毛女》再版前言中写道:“邵子南同志,他是这一剧本创作工作的先行者,他曾写出最初的草稿,虽然,以后这个剧本由别人重写,但他的草稿给予后来的人以极大的启示和帮助。”
关于“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剧本主题的提炼,贺敬之认为:“认识与表现这一主题是经过了一个不算太短的过程的。才开始,曾有人觉得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神怪故事,另外有人说倒可以作为一个‘破除迷信的题材来写。而后来,仔细研究了这个故事以后,我们没有把它作为一个没有意义的‘神怪故事,同时也不仅把它作为一个‘破除迷信的题材来处理,而是抓取了它更积极的意义——表现两个不同社会的对照,表现人民的翻身。”
因他未去过晋察冀边区,对故事流传地的生活不熟悉,就找了许多对该地生活熟悉的同志请教,又尽量回忆自己过去的农村生活作为素材,在讨论故事情节时请更多同志参加。所以,白毛女的原型是个综合体,尤其是融入作者家乡的一些细节和情感。笔者曾到贺敬之的出生地贺窑村实地考察,村南不远处有座山叫寨山,据《峄县志》记载,此山“形势高峻,状如覆釜”,上有鸦鹊寨,传为梁武帝所筑,还有当地人建于明万历十七年的“奶奶庙行宫”,旁侧有名为“勺泉”的山泉和仙人洞。洞口不大,里面比较开阔,有残留的香烛和供品。山南面的村庄叫黄楼,听村民说解放前确有一个地主姓黄,现在还存有黄家大院的一间配房,该地主是从台儿庄马兰屯迁来的。村民所言让笔者想起贺敬之的姐姐就是嫁到马兰屯的黄家,黄家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其中就有“仁”字辈。
贺敬之在创作中被喜儿的悲惨遭遇所打动,他是一边流着热泪,一边创作的。家乡的寒夜、财主的逼债、父亲的去世、弟弟的夭折、母亲的辛劳一一浮现在他的眼前,《夏嫂子》《小兰姑娘》《五婶子的末路》等作品中的人物又进入他的脑海,他以诗人的情怀和戏剧家的表述力,夜以继日地创作剧本。由于长时间挑灯奋战,贺敬之的身体累垮了,最后一场戏经他提议,由丁毅来完成。
周扬看过后,热情地肯定了贺敬之、丁毅执笔创作的《白毛女》剧本。
集体创作的经典
张庚在《关于〈白毛女〉歌剧的创作》中指出:“当我们在延安从事创作这个剧本的时候,执笔者虽然是贺敬之同志,但实际上是一个大的集体创作,参加讨论和发表意见的,有曾在发生这传说的一带地方做过群众工作的同志,有自己过过长时期佃农生活的同志,有诗歌、音乐、戏剧的专家,不仅他们,差不多很多的观众,上自党的领导同志,下至老百姓中的放羊娃娃,都提出了他们的意见,而根据这些意见,我们不断地修改,自今天演出这个样子的时候,已经和原来的初稿以及初次排练时的剧本很不相同了。”贺敬之也在总结创作过程时,特别强调《白毛女》是集体创作,“这不仅是就一般的意义——舞台的艺术本就是由剧作、导演、演员、装置、音乐等各方面构成的上来说的,《白毛女》是比这更有新的意义更广泛的群众性的集体创作”。《白毛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民间的口头集体创作。《白毛女》的原型“白毛仙姑”的故事在晋察冀边区流传过程中,经过众人的口口相传,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新传奇故事。西战团的文艺工作者在搜集整理中又是一次创作过程,一路上不断演绎完善才带到延安。
专业集体创作的新形式。周扬将创作演出《白毛女》的任务交给张庚后,他立即成立一个专业创作组。为加快创作进度,剧组采取流水作业方式开展工作,即编剧贺敬之写完一场立即交给作曲者谱曲,由张庚、王滨审定后,交丁毅刻写蜡纸印出,再由导演和演员试排。每幕排完后总排,请鲁艺师生、干部群众和桥儿沟老乡观看并评论,边写作边排演边修改。
中央领导指导集体创作。《白毛女》在延安首演的第二天,剧组党支部书记田方传达了中央书记处的指示:第一,主题好,是一个好戏,而且非常合时宜;第二,艺术上是成功的,情节真实,音乐有民族风格;第三,黄世仁罪大恶极,应该枪毙。田方还就第三点意见作了专门解释:“少奇同志说,黄世仁如此作恶多端,不枪毙不足以平民愤,不判黄世仁死刑,就是犯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剧组根据中央领导的意见作了修改,在以后演出中黄世仁被当场枪毙,大快人心。
群众加入集体创作队伍。贺敬之曾回忆说:“特别应该提出的,是许多老百姓和学校的勤务员、炊事员常常热心地来看排演,他们提出许多好意见,甚至许多细微的地方,他们也发表了意见。当写最后一幕——新社会的时候,我们还请来了在晋察冀下层政权工作的同志来指教。”《白毛女》在延安演出期间,很多群众看完纷纷来到剧组发表意见。有一次,贺敬之去食堂打饭,炊事员一直跟着他说黄世仁不枪毙不行。《解放日报》也收到很多读者来信,评价这部戏并提出一些意见。该报1945年7月17日特开“书面座谈”专栏来讨论,在开栏语中指出:“很想作为一个开端,来展开思想的论争,凡是各方面意见比较多的问题,不论是关于文艺,或是其他部门的,欢迎任何同志发表各种正反不同的见解,发表的方式看情形酌定,希望同志热烈参加。”据贺敬之回忆,从《白毛女》演出起,就接连不断收到各方观众的来信,连同《解放日报》转来的评论文字有40余件、15万字之多。
穿越不同时代的集体创作。1945年10月,剧组来到张家口市,当地文艺工作者又提出不少意见,贺敬之从4个方面作了修改。丁毅在《1947年〈白毛女〉再版前言》中写道:“《白毛女》这个剧本已经在张家口、承德、齐齐哈尔、哈尔滨,还有其他的地方出版过几次了,但每个版本都不相同,都有修改的地方,这说明了它还不成熟,也说明着我们在努力使它走向完善。”1950年,根据将近6年的演出经验,主创人员将原先的6幕改为5幕,并在音乐上进行调整和完善。几十年里,《白毛女》被改编成多种艺术形式上演,其中的反复创作过程是不言而喻的。1951年,导演王滨和水华将《白毛女》搬上银幕,大量日常生活场面得到精彩而形象的呈现。1964年,上海舞蹈学校将《白毛女》改编成芭蕾舞剧,成为芭蕾舞和民族舞蹈结合的典范。在后来丰富多样的版本和艺术形态演变中,再次证明《白毛女》不仅是同时代人集体创作的经典,也是不同时代的艺术家和人民群众共同创作和磨炼出来的经典。
永远屹立于民族艺术之林
1945年4月,歌剧《白毛女》在延安党校礼堂首演。毛泽东和全体中央委员、“七大”代表观看演出,观众都沉浸在《白毛女》的剧情中,有几个女同志甚至失声痛哭。6月10日,《解放日报》报道说:“该剧已演出七场,觀众深受感动,有的同志竟看了五次,他们都认为此戏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有的同志说:‘戏里演的,跟我以前的生活是一样的。有的同志说:‘看了黄世仁欺侮杨白劳,我真难过,我觉得我像被枪打了一样。而过去生长在城市里的同志却说:‘看了这戏,我才知道什么是恶霸。有些从抗战以来便一直在边区及解放区工作、对农民在旧社会所受剥削与迫害的印象已经淡漠的同志,看了这戏以后,也重新激发了对封建制度的义愤,认识(到了)自己对农民所(担)负的责任……《白毛女》中的歌曲,已开始在延安流行。闻鲁艺戏剧工作团应各方观众要求,将在八路军大礼堂、枣园、边区参议会大礼堂等处继续演出。”
延安首演后,在解放区掀起《白毛女》风暴。连续演出30多场,场场爆满,受到热烈欢迎。延安唱红了,陕北唱红了,解放区唱红了,全中国唱红了。
在革命战争年代,演出《白毛女》就是召开诉苦大会,解放区农民观看后,都积极参加斗地主反恶霸斗争,踊跃送子送郎参军去前线。丁玲写道:“每次演出都是满村空巷,扶老携幼,屋顶上是人,树杈上是人,草垛上是人。凄凉的情节,悲壮的音乐激励着全场的观众,有的泪流满面,有的掩面呜咽,一团一团的怒火压在胸间。”演出《白毛女》就是举行战前动员会,部队指战员纷纷要求为杨白劳、喜儿报仇,有的战士甚至在剧场举起枪要打死“黄世仁”“穆仁智”,以致有的部队规定看《白毛女》时不许带枪弹。作家贾漫写道:“从1945年《白毛女》诞生起,到解放后的全国和平环境的土地改革运动。哪一个兵种,哪一个野战军,哪一个兵团的新文艺团体,从中央到地方,哪一个专业文工团没有演出过《白毛女》?平津战役的战前和战后,辽沈战役的战前和战后,淮海战役的战前和战后,哪一个城市没有演过《白毛女》?哪一个部队没有看过《白毛女》?”
《白毛女》还是最早走向世界的中国好声音。1948年5月至6月,香港建国剧艺社、中原剧艺社、新音乐社在香港联合公演《白毛女》,盛况空前,反响强烈。香港1949年5月出版的《华南艺术青年工作概况》指出:“这是港九文化界三年来的纪念碑式的大事,它的演出将港九上下层社会整个地轰动起来了……某国领事在一次国际人士的观后座谈会上承认这是他生平所看的最受感动的歌剧,许多批评家也认为这是中国自有新演剧的历史以来,拥有观众最多的一个戏剧。经过演出,剧场经理不敢再以轻蔑的眼光索要高院租,而以低声下气的音调来请求续演,请求拆账了。演出后快一年的今日,市民们还不断地打听它的重演日期。”《白毛女》的公演,激发了香港民众对新中国的热情期盼,也为西方世界了解中国革命、认知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打开了一扇窗。
1951年至1952年,歌剧《白毛女》赴东欧七国及奥地利演出,巡回152个城市,演出 437 场,观众达 242 万多人次。王昆曾回忆说:“在反抗压迫和剥削、同情和支持弱势人群这些大的方面,《白毛女》是能够被国外人民认同并引起共鸣的。”1951 年 7 月,《白毛女》获得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的第一个特别荣誉奖。苏联和东欧还翻译出版《白毛女》剧本,将它搬上话剧舞台。
1955年,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团长清水正夫和妻子松山树子把《白毛女》改编成芭蕾舞剧,在日本公演。1958年受周恩来总理邀请,首次来华演出。该团先后13次来华演出《白毛女》,直到2011年10月,松山树子还携团在京沪两地演出,留下了中日文化交流的佳话。
历经近80年风雨,《白毛女》一直屹立于民族艺术之林。据不完全统计,演出场次超过一万场,观众人次超过数亿人次,它曾被改编为电影、戏曲、芭蕾舞,在国内外广为传播,它的故事和音乐旋律家喻户晓。一部戏能那样深入普及、脍炙人口、对历史发展产生那样大的影响,这不仅在中国戏剧史,而且在世界戏剧史上都是罕见的。在革命战争年代,它曾鼓舞人民披荆斩棘、砥砺前行。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它仍然激励人民不忘初心,开拓奋进。
(作者系山东省枣庄市政协文史馆馆员,台儿庄区委宣传部三级调研员、贺敬之文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责编 闵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