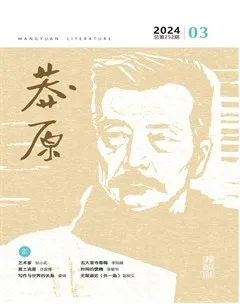南太行荒诞故事(小说)
杨献平
地下历险记
爷爷不知为啥不高兴,先是坐在黄昏的门槛上抽了一会儿旱烟,接连叹息几声,抬头用看不见的眼睛,盯着刚刚显露出来的星星,煞有介事地盯了好久,然后又从喉管甩出一声叹息,起身,拄着拐杖去了茅厕,回来也一句话没说,脱了衣服就躺在了炕上。
我尾随其后,三下五除二,就脱成了一个光不溜儿,挨着爷爷躺下。
我说,爷爷你再给我讲个故事呗。
爷爷没吭声。我伸出胳膊推了推爷爷的肩膀。
爷爷突然说,你小子做啥呢?
聲音奇大,我吓了一个哆嗦。
我也生闷气,觉得爷爷不该那样凶。正这样想着,爷爷翻身趴在炕沿上,装了一锅旱烟。随后是辛辣的焦油味,在整个房间弥漫开来。大致抽了两三口,爷爷突然开口说,刚才爷爷说话声音大了,没吓着你吧,平子?
我有点受宠若惊,赶紧笑着说,没事儿的爷爷。爷爷说,为了给你赔不是,我就再给你讲一个你从没听说过的故事。
我一骨碌爬起来,兴奋地说,俺爷真好!
爷爷呵呵笑出了声来。爷爷敲掉烟灰,躺好,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又缓慢吐出,开口说:从前啊,咱村后边的深山里,长满了几个人都搂不过来的大杨树。有的大杨树长得比现在城市里边的楼房还大,就是全村人都站在下面也还站不严。
很多年以前,咱村里有个人名叫杨老庄,经常到那里放羊。一天中午,吃了干粮喝了水,杨老庄想解大手,沿着斜坡走了一段,到一大片茅草窝跟前,解开裤带,一屁股就蹲了下去,刚痛快完,俩脚向外一叉,突然,嚯嗵一声,还没闹清楚是咋回事,人就往下掉。那还不是一个小土坑,而是一个很深的窟窿,他往下掉得很快,只听得耳朵边风声呼呼,跟坐在大卡车上面一样。
杨老庄心想,这下可毁了,不但没了命,恐怕家人连尸首都找不到了!心里越想越沮丧,后来干脆闭上了眼睛。等他再醒来,睁开两只枣核眼,只见四周黑得像是干了的墨汁。杨老庄心里害怕,转了转自己那只秃脑袋,四处看了一圈,还是一片密不透风的黑。他再活动了一下手脚,幸好还长在自个儿身上,也不疼,又活动了几下,感觉也没啥不对劲儿的。
杨老庄心想,自己肯定死掉了,这地方就是阎王殿了。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自己肯定是一个新死的鬼了。
杨老庄一阵沮丧,想起自己才四十来岁的老婆,今年腊月才满十八岁的大闺女,十五岁的小儿子,还有七十多岁的爹娘,忍不住心里一阵发酸。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这么个年纪就到阎王殿来报到了,余下的孤儿寡母、爹娘以后咋生活呢?
想到这里,杨老庄忍不住叹息了一声,又想,自己这大半辈子没做过啥恶事坏事,也没有得罪过天帝路神灶王爷土地爷山神爷和上面的祖宗,咋就这么短命呢?
可过了好久,也没啥动静。
杨老庄翻身坐起,伸手一摸,地上暖融融的,好像是松针,手指向下刨了几下,下面好像还是厚厚的松针树叶,杨老庄一直刨到胳膊肘子那么深,还是树叶松针。更叫杨老庄感到奇怪的是,坐了这么久,没见一个鬼魂,也没有传说中的牛头马面、扇扇子的钟馗和抬轿的小鬼。杨老庄不由得咦了一声,心中纳闷。
心想,说不定阎王殿里事儿比较多,鬼差们也都忙,暂时还顾不上搭理自己;也说不定自己阳寿还没尽,判官还没在自己名字上打勾画叉……杨老庄一阵高兴,嗖的一声站起身来,把眼睛睁得跟铜铃一样大,四处张望了一圈,见左边的远处似乎有点亮光,其他方向都黑漆得跟锅底一般。
杨老庄习惯性地拍了一下屁股,身子擦着地面,向一边挪动。
地面上还是很软,还有干树叶的碎裂声。挪了好一阵子,地面变硬,感觉就像村边的土石小路。杨老庄不由得咦了一声,站起身来,摸索着向前走,走了大概十来步,他自己的刺刺啦啦的脚步声,倒叫杨老庄猛然醒过劲儿来。老辈子人说,鬼走路是没有声音的,整个身子在空中飘。杨老庄伸出两只长满老茧的手指头,在大腿上拧了一下,忍不住哎呀了一声,声音撞得石头的四壁嗡嗡作响,还传出好远。杨老庄又伸手在自己胸口上捂了一会儿,心还在怦怦跳,胸口还像以前那样热乎乎的。杨老庄又是一阵兴奋,不由加快了速度。
又走了好一阵子,还没到有亮光的地方。大概是急着逃命的缘故,杨老庄一点儿都没觉得害怕。这时候,忽然有光了,尽管很微弱,差不多能看清路面。杨老庄看到,自己所在的地方,是一个阔大无比的山洞,顶上起码有四五十丈高,两边是黑色岩石。空气里有点树叶腐烂的霉味儿。
杨老庄心想,就这么一直走,说不定就能出去了。越是这样想,越是浑身有劲儿。杨老庄大步如飞,他一个人空空的脚步在石头洞里响起一连串回声,出了一身的热汗。也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走到亮光处,杨老庄四处一看,嚯嗵一声又一屁股歪坐在地上。
这是为啥呢?原来,杨老庄到的那个地方,还是山洞,高得像半边天,两边的石墙是褐红色的,有的光滑得像镜子,有的疙瘩不平。杨老庄有心再往前走,可前面又是黑乎乎的,往后退,就只能走老路。
走投无路,是世上最难的光景了。
杨老庄站在那里,正在闷着脑袋叹气,忽然被人拍了一下肩膀。杨老庄浑身一颤,猛然抬起头,先是看见一只白得跟秋天萝卜一样的手。杨老庄喊了一声“俺的个娘啊”,随即就像兔子一样蹦了起来。再回头细看,只见一个瘦得跟麻秆一样的汉子,连一根胡子都没有,眼睛小得跟刀子在和好的面团上割了一刀,嘴巴瘪得跟干柿子一般,似笑非笑地看着自己。
杨老庄和那人对视了一会儿。
老头说,咳,你不要害怕,俺也是人。
杨老庄眼睛呼溜溜地转了好几回,嗫嚅说,你是……
老头叹了一口气,向前挪了一步,一双眼睛里闪着光,看着杨老庄说,你可能不知道,这地方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几千个哩!因为长年不见老烨(方言,意为太阳),人都不长胡子,也没有头发,身上的皮肉跟白菜帮子一样;也不能种地,都靠吃虫子生活。
杨老庄哦了一声。看这个老头确实没有恶意,随即放松了戒备。
老头咽了一口唾液又说,你是在地上面生活的人,得赶紧想办法跑出去,要是让他们抓住了,一辈子也别想出去了!
杨老庄一听,心里一阵发紧,瞪大眼睛说,这……这个咋能跑出去?
老头说,你跟着我走,往前走一会儿,有个出口。不过,那儿有人守着,得趁他们不注意,你能溜出去就没事了。
杨老庄急忙说,那咱们赶紧走!
老头说,你着急也没用,前边就是大厅堂,白天晚上都有人巡逻,得趁他们换岗的时候,偷偷绕过去。
杨老庄说,现在不是黑夜嗎?老头说,错了,这时候还是中午,到晚上,还得一大会儿呢。杨老庄说,那咋办?老头说:先找个地方躲躲吧,跑的时候,越黑越好,趁人不注意了,再溜出去。说完,扭头就往杨老庄来的地方走。
杨老庄犹豫了一下,跟在后面。走了几步,忽然想到,自己来的那地方没人把守,就说,那地方不是没人吗?
老头说,那地方确实没有人,因为那就是一条绝路。
杨老庄的心咯噔了一下,停下脚步。
老头走了几步,扭头见杨老庄停住不动,开口说,不要怕,俺要是有心害你的话,你早就被抓了。
杨老庄站在那里,脑子飞快旋转。老头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又低声说,那地方确实是绝路,离天上百丈高,蚂蚁都爬不上去。另一头有一条大蟒蛇,一张嘴就把人吸到肚子里去了。很多人说了不该说的闲话、办了对不住这里大头目的事儿,不管你是有心还是无意的,都会被扔到蟒蛇洞里。
杨老庄倒吸一口凉气,急忙跟上。俩人一前一后,蹑手蹑脚,越走越黑。正走着,老头忽然又停下,伸手在墙壁上摸了一会儿,再使劲一按,一阵嗡响,坚硬的墙壁上忽然打开一道石门。老头抬脚走了进去。杨老庄犹豫了一下,也跟了进去。
老头从怀里拿出火折子,点着了墙上的松油灯。这显然是一个石室,有两间房子那么大,飘着一股苔藓味道。走到石凳前,老头示意杨老庄坐下。杨老庄嗯了一声,甩屁股就坐了下来。
老头看着杨老庄说,哎呀,外面的日子是好,老老少少的人,都有个正经肤色,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想干啥就干啥。这里的人,只能在这石洞里面来回活动。说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杨老庄说,外面是比这儿好。可有钱才能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没钱就只能当一个“拱地虫”“土农民”,一辈子也去不了县城一趟。
杨老庄说的时候,老头一脸虔诚地听。听杨老庄说完,老头说,那也比在这儿强。干啥事都得大头目允许,就是两口子那点事,也得先报告,批准了才行。
杨老庄忽然来了兴趣,眨巴着眼睛问老头说,你们大头目咋就这么厉害,连这事儿也管?老头说,这里其实就是个大树洞,最开始,好像是闹兵灾,一群人慌不择路,在深山里面见洞就钻,一个不小心,就掉进来了,后来掉进来的人多了,又没吃的东西,人和人之间相互斗殴,饿得不行,就开始人吃人。
到最后,吃人最多的那个人谁见了谁躲着跑,没人敢惹,他说啥就是啥,这里就成了他的天下。他自己死了以后,他儿子又当了头儿。剩下的人,就成了手下人,头儿叫干啥就干啥,不听话的,说头儿这不好那不行的,以前是像猪一样杀了分吃,现在好一点了,不再杀了吃,但有无数办法让他生不如死。
老头说话的口气很平常,杨老庄却听出了一身冷汗。
老头笑笑说,你不要害怕,现在早不吃人了,就是喂蟒蛇。
杨老庄更加害怕,看着老头,一脸惊慌。暗想,这家伙会不会诓骗自己,然后拿去吃了或喂了蟒蛇?
想到这里,杨老庄不由得噌一声,站起身来,对老头说,这时候,天早黑了吧?咱赶紧去找出路吧?
老头没吭声,脸微斜,两只耳朵上下耸动了一会儿,好像在感受和谛听啥信号或者气氛似的。然后神色放松,对杨老庄说,还早呢,这会儿刚擦黑。
杨老庄说,那咱先往出口走呗?
老头说,这会儿外面正在巡逻,不信,你过来看看。说完,起身到石门前,拨了一下,出现一个圆孔。
杨老庄半信半疑地把眼睛贴上去,没看到东西,又过了一会儿,听到一阵橐橐的脚步声,三个人举着火把,铿锵锵地走了过去。
杨老庄安下心来。老头关了小孔,又说,现在得赶紧吃点东西,不然的话,一会儿跑不动。说完,伸手掀开一片沤得稀烂的苔藓,朝里抓了一把,向杨老庄递去,竟然是一堆白白胖胖的虫,在老头的手掌里扭动。
杨老庄不由得一阵反胃,哇的一声,蹲在地上呕吐起来,到最后,把自己在山上吃的那点儿饭都吐了出来。老头露出一口白牙笑了一声,趁杨老庄低头呕吐的功夫,连往嘴里塞了几把白虫,吃得满嘴冒着白浆水。
杨老庄看到,又一阵干呕,差点把胃和肠子都吐了出来。
擦净嘴巴,老头又竖起耳朵听了一会儿,才对杨老庄说,这会儿没人了,准备走。说完,就要开石门。杨老庄忽然说,你为啥要救我?老头怔了一下,看着杨老庄,光顾着说别的,把正事都忘了。俺实话告诉你,我是武安县白家庄人,俺爹叫白老大,俺娘是沙河县石盆村的娘家,我叫白狗剩儿,十三岁那年到这儿来给地主砍柴,一不小心就掉进了这洞里。凭着一张嘴巴,糊弄住了这里的头儿,当了一个更夫。这一晃,也不知道多少年过去了,爹娘兄弟还在不在……说到这里,老头眯缝眼里掉了两颗泪珠子。
杨老庄说,原来是这回事,现在咋办?还有……这么多年了,你咋一次逃跑的机会都没有找着呢?
老头叹息一声,说,不是找不到出去的机会,而是俺有家有口,老婆子和他们是一伙儿的。这不,前些时候,她刚死了,尸体被喂了蟒蛇。
杨老庄半信半疑地哦了一声。又说,那你孩子们呢?
老头抽了一下鼻子,神色悲戚地说,哼,闺女儿子,都被她娘蛊惑了,真以为外面还兵荒马乱,出去就得死!再一个说,他们都是这洞里出生长大的,眼睛一见光就疼得要死。
杨老庄这才有点相信了。
老头说,俺是有爹娘和来处的人,就是死,俺也想埋在爹娘的脚下面!
杨老庄嗯了一声,拍了一下老头肩膀。
老头握住杨老庄的手,眼睛里迸发出一道光。杨老庄看到了,虽然不知道老头心里到底是咋想的,但觉得这个人可以相信。
两人靠着石壁,又坐了一会儿。杨老庄正在昏昏欲睡的时候,老头用胳膊肘子轻轻捣了一下杨老庄的肩膀。杨老庄倏地睁开眼睛,一脸的惊慌。
老头嘘了一声,示意他别出声。然后站起身,小心翼翼地打开石门,探着脑袋左右看了看,压着嗓子说,走!说完,迈开双脚就往外面走去,杨老庄紧随其后。
老头回头关了石门,身子擦着石墙,朝着刚才的方向小步走去。
两人一前一后,小心翼翼地走到刚才的地方,还是一个人没有,又走了一段,依旧鸦雀无声。走到一个小凹槽处,老头蹲下,示意杨老庄别出声。杨老庄说,这不没人吗?老头嘴巴对着杨老庄的耳朵小声说,这墙后边就是人住的地方。说完,指头在石墙上用力按了一下,出现一个小圆孔。
杨老庄贴上去一看,只见另一边正面墙壁下,石洞一眼挨着一眼,都亮着灯光,每眼洞里都有三五个人围坐在地上,从地上抓东西往嘴里填。
左边也有灯光,一连好几盏,照着一个有七八间房子大小的石洞。洞门的两边有人站岗,另外,还有三五个人打着火把,在前面巡逻。杨老庄想,这可能就是那个大头目住的地方了。
老头拍拍他的肩膀,挥挥手,起身猫腰向前疾走。杨老庄紧随在后,俩人奔了好一阵子,远远看到几盏晃动的火把。老头说,那地方就是出口了,过去,就可以逃走了,这个俺花了很多年才摸清楚。
杨老庄哦了一声。
老头又神色诡秘地说,越是这个时候,越是要小心,要是被他们抓住了,喂蟒蛇倒是件小事,就怕被活剥了!说完,靠着墙壁一动不动,杨老庄照葫芦画瓢,后背紧贴在石壁上面,只觉得后背像结冰了一样冷,忍不住打起哆嗦。
这时候,突然有说话声传了过来,在洞壁上悠悠地打着滑旋儿,水雾一样,向远处缭绕。后来是整齐的脚步声,向着相反的方向,越走越远。老头拉了一下杨老庄胳膊,身子就像一支箭矢,飞快向前射去。杨老庄也学着老头的样子,紧随在后。到一面石门前,老头停住,大口喘着气,在右侧墙壁上找按钮。谁知道,寻了好一会儿,也还是没找到开关。老头急得不住擦汗。
这时候,又传来了一阵脚步声。老头双手并用,又在左边摸了一阵子,忽然停住,使劲一按,中间一道石门就嗡嗡地敞了开来。
杨老庄见到,纵身就往门外冲,老头一把拉住,嗔怪说,你这么冲过去不死也得重伤。杨老庄握着拳头,眼神疑惑。老头说,你跟着我,我咋样你就咋样。说完,抬起右脚,探到实地,又来回挪了挪,左脚才迈了出去。杨老庄也学着老头的样子,小心翼翼地跨了出去。
老頭反手过来,在墙壁上按了一下,石门又嗡嗡着返回原位。杨老庄只觉得持续的大风扑面而来,隐隐地,还夹杂着某种吼叫之声。这才意识到,这门外就是悬崖,不由得暗自庆幸。俩人抓着悬崖上的葛条和荆丛,一点一点转到另一面,见没人追来,就在一个宽敞的石岩前蹲了下来。
杨老庄看去,这不就是后山的鹰嘴崖嘛!这个地方,山高沟深,一连好几面石崖,都有十几丈高。平时,无论放羊还是打柴,村里人都不敢到这里半步。他很小的时候,听大人们说,从前时候,村里好几个人到这里挖五灵脂,也就是寒号鸟的粪便,不是绳子断了摔死了,就是莫名其妙地死活不见了。
这时候正是黑夜,星星密集,山沟的树林不时传来狼嚎。老头说,要是找一点葛条编成绳子,咱们就有救了。杨老庄当然也知道,葛条蔓子一般又长又粗,还特别有韧劲儿,几根编在一起,比麻绳还结实。
杨老庄左右看了看,还真的在一边的石崖缝隙里,找到了两根爬山虎一样的葛藤,伸手拽了下来,还挺长,两根编在一起,比一般的麻绳还粗,一头拴在一块岩石上,然后抓住葛藤,向下挪动,没想到,这崖壁有一处很宽敞,长满了黄荆。两人摸索着,不知道走了多久,居然到了村后的棌树林里。
这时候,好像是黎明时候。
刚到了安全地带,那老头高兴地嚎叫了一声,好像被夹了前腿的老狼,也没给杨老庄打招呼,迈开步子,就朝着武安县方向奔去。
杨老庄也不敢停留,一路跌跌撞撞地朝村里奔去。
那石洞里黑咕隆咚的,白天黑夜没啥区别。杨老庄也不知道自己在里面待了多久。可在外面,村里都炸开了锅,一连三天,杨老庄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爹娘、孩子、老婆和村人都以为杨老庄不是被山里的狼群分着吃了,就是从那个悬崖摔下去死了,尸首也被猛兽叼走吃了,但还是抱着希望,发动亲戚邻居找了好几天,也还是找不到杨老庄,就找了他用过的东西穿过的衣服,放在棺材里,准备入土为安。
谁知道,睡到半夜,忽然听到有人在门外喊。一开始,人们还都以为是杨老庄的鬼魂,因为都以为他是横死的,即使做了鬼,怨气不散,肯定会神五鬼六地闹腾几天。可听了一阵子,又觉得不像,胆战心惊地开门,打着灯笼先是看了脸,又摸了摸杨老庄的胸口,还是热乎乎的,这才确认杨老庄还活着。
家人喜极而泣,杨老庄只说自己不小心从悬崖上摔了下去,对石洞的事情只字不提。在家休息了一个来月,杨老庄背了大半袋子小米,到武安白家庄去看望他的救命恩人。
沿着向西南的山岭,一路上爬沟过坎,天完全黑了的时候,杨老庄才一路汗水地寻到白家庄,找到那个老头的家,却没见到那老头。一个自称老头亲弟弟的人说,他哥是一个月前回来了,谁也没想到他还活着,一家人脸上的笑容还没落下去,老头身上就一个接一个地起泡,而且是那种明亮亮的大水泡,用针挑开,流黄豆大的清水。半个月后,浑身上下都是。老头疼得满地打滚,哭爹喊娘。
家人请了好几个大夫,望闻问切之后,一个个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有一天,家人在外屋商量这个事儿咋办,最终达成一致意见,保命要紧,还是要把老头送回去。话还没有说完,只见里屋冲出一个人,像箭一样,嗖的一声蹿到门外,家人还没醒过神儿,老头低着脑袋,已经撞向石墙。
家人冲过去,老头已经脑浆迸裂,一命呜呼了!
杨老庄叹了口气说,好不容易逃出来了,咋自己撞死了呢?
老头的兄弟听了,半天没说话。
杨老庄也沉默了一会儿,在人家家里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一大早,问了老头的坟地所在,又到货店里买了一堆黄表纸和冥币,一个人到老头坟上烧了,才又低着脑袋,一路闷想着,神色沮丧地回到村里。之后的很多年,杨老庄再也没有到过后山半步。
故事讲完,爷爷说,睡吧。
我说,真有那个山洞吗?
爷爷说,好像是有,也好像没有。
我说,那咋和真的一样呢?
爷爷说,不像真的,那就不是故事了!
我又问,爷爷,你刚才咋不高兴呢?
爷爷说,不高兴就是不高兴,有时候人不高兴,连自己都不知道为啥不高兴。爷爷一边说着,一边把身子扭向窗户那边。
山间奇遇
很多年以前,村后的高台子上,住着一户人家,夫妻两个,先后养了两个儿子,哥哥叫张王恩,弟弟叫张付义。
兄弟俩相隔三岁。有一年闹蝗灾,爹连病带饿,抛下他们母子三人下世了,弟兄俩跟着娘过活,平时靠去山里砍柴,再背到大村去卖,赚些小钱度日。那一天,兄弟俩各自背了柴架子,提了斧头镰刀,又到深山去砍柴。
这里所说的深山其实是村后沟,虽是通往武安与山西辽州的小道之一,但远近一带人烟稀疏,再加上灾荒战乱,本来就偏僻的山村就更孤绝了,常年不见一个外来人,好像与世隔绝了一样。兄弟俩沿着走了无数遍的山路,到森林边儿,放下架子,歇了一会儿,便抡起斧头砍柴。
铿铿的砍柴声在深谷里传出好远,在附近沟谷的崖壁上跌宕不休。砍了一会儿,弟弟张付义要去解手,对哥哥張王恩说了一声,就丢了斧头,往森林深处走去。哥哥张王恩继续砍柴,砍够了自己的,又帮弟弟砍。
等张王恩砍够了两个人一次能背动的柴火,弟弟张付义还没有回来。他心头一紧,扔了柴火,提着镰刀就朝着弟弟解手的方向走去。一边走,一边大声喊叫弟弟的名字,可除了沟谷岩壁上的回声,始终没有弟弟的应声。张王恩心急如火,渐生不祥之感。到最后,喊声中都有了浓郁的哭腔。张王恩气喘吁吁地穿过大片森林,还是没找到弟弟的踪影。这时候,落日西斜,眼看就滑到摩天岭背后了。张王恩心想,要是弟弟有个啥三长两短的,回去没办法向娘交代。
越是着急,越是慌不择路。好久后,张王恩自己也不知道到哪儿了。他只是记得父亲在世时说过,后山沟有两个地方绝对不能去,一个是王八盖子山,上去容易下来难,从古到今,村里有好多人在那里丢了,连尸骨都没找见。一处是森林深处的一眼山洞,据说住着一条水瓮粗的大蟒,人进去,肯定会被一丝不剩地吞下去。想到这里,张王恩不禁打了一个冷战,扯着嗓子喊弟弟张付义的名字,仍旧没有回音。
落日下坠,森林里突然一片寂静,偶尔的鸟鸣像是从地底传来的,狼嚎声似乎就在耳边。张王恩打了一个哆嗦,快步回到弟兄俩砍柴的地方——可除了已经捆好的柴火,还是不见弟弟张付义。张王恩心想,找不到弟弟,自己回去娘骂娘生气倒还没有什么,娘万一想不开……再说,父亲去世的时候,一连几遍叮嘱他要好好地照顾弟弟……可现在,弟弟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这该怎么办?
天越来越黑,张王恩也越想越害怕,沮丧至极的时候,就一屁股坐在草堆上放声哭一阵子。等他擦干眼泪,天已经黑了下来,森林更为黝黑,唧唧虫鸣遍地,狼群的嗥叫一波一波传来。张王恩咬了咬牙,腰里别了镰刀,手提斧子,找了一块石英石,打着火,用枯树枝做了一盏松明灯,沿着弟弟走丢了的路,再次向森林的深处寻找。
森林里荆棘遍布,尖石林立,张王恩的胳膊和腿被尖利的树叶和木枝划出了一道道伤口。夜越来越黑,张王恩也不知道自己走了多远,走到了哪里,只是一遍遍地呼叫张付义的名字。
可就是没人答应,只有阵阵的松涛,排山倒海一般响动。走着走着,张王恩忽然看到对面山坡上闪出一道亮光,像家里的松油灯,在漆黑的夜幕中忽闪忽闪,看样子不像是其他不善的东西。张王恩一阵惊喜,一边喊着张付义的名字,一边跑到近前。灯光是从那一座小石头房子里闪出来的,房子修建得很精致,门前还有台阶,四边还有木头做成的栅栏。张王恩犯了嘀咕,心想,从来没听说过这深山老林里还有人家,再想起那些瘆人的鬼怪传说,不由头皮发麻,浑身上下都像是大热天忽然结了一层冰似的。
张王恩屏住呼吸,走近小房子,从窗户往里看。窗户上贴着一层薄纸,里面朦朦胧胧的。像有人,又像是没人,很静。张王恩在舌头上沾了唾液,用手指捅开薄纸,看到一个人的背影,背对着自己,坐在一张小木桌前。从头发和衣饰判断,那人应当是个女的。这是谁呢?是人还是鬼?
张王恩紧张得浑身发软,不知道该怎么办。收回目光,张王恩下到院子里,一时拿不定主意,是敲门询问,还是悄没声息地离开好呢?正在犹豫,背后有人叫他的名字,张王恩急忙转身,看到一个身穿粉红长裙的年轻女子站在门口,眉目含笑地看着自己。
张王恩哦了一声,脸色惊慌。支吾了一阵,张王恩走近那女子,说了寻弟弟的事。那女子笑说,这事儿俺知道。张王恩咦了一声,面露惊诧。那女子又笑了一声,伸出细长的手臂,做了一个请的姿势,示意张王恩进屋。张王恩迟疑了一下,觉得也没有退路了,只好低着脑袋走了进去。
屋里灯光明亮,设施一应俱全,整洁无比,且香味浓郁。
张王恩愈发狐疑,心脏怦怦乱跳。那女子似乎猜透了他心思,说,你不要害怕,我不是坏人,不会害你。张王恩嗯了一声,可还是局促不安。女子看着张王恩的样子,扑哧一声笑出声来。张王恩脸色涨红,搓着手掌,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女子又说,你稍坐一会儿,我去去就来。话还没说完,就一阵清风一样飘了出去。张王恩坐下,又仔细端详房间,这房子除了桌椅之外,还有一张床,被褥齐全,床帏是白色的,分别挂在两侧,门背后,还有洗脸的铜盆,墙壁上镶嵌着一面铜镜。咦,这是哪儿,谁的家?在张王恩的印象中,这一带,大多数人是穷困的,富贵的一千个里面也只有三五家。但如此殷实的人家,住在这里,他好像从没见过,也没听说过。
不过一会儿工夫,那女子又飘然进屋,手里端了一面木质托盘,上面放着热气腾腾的饭菜。张王恩愈发惊异,下意识地退几步。女子将饭菜放在木桌上,示意张王恩来吃。张王恩见那女子毫无恶意,又饥肠辘辘,嗫嚅了一下,也管不了更多,端住饭碗便狼吞虎咽起来。吃完,张王恩抹了嘴巴,向那女子道别,女子道,为啥这么着急呢,现在天又这么黑,路又难走,等天亮了,再去找你弟弟不迟。
张王恩说,家里只有弟弟和母亲,找不回弟弟,回去没法儿给娘交代。女子说,你不知道弟弟去哪里了,怎么找呢?说不定已经被狼群给撕着吃了,再不就是被那边的巨蟒吞噬了。张王恩说,不管咋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说完,张王恩就抬脚往门外面走。正在这时,那女子忽然叹息一声,说,我知道你弟弟在哪儿!张王恩猛然收住脚步,瞪大眼睛看着那女子。
女子走到床侧,伸手拍了一下,墙壁上忽然打开一道门,不宽,但可以容纳两个人并肩进出。女子身影一飘,率先走进,张王恩三步并作两步,也尾随而入。路越走越宽,至此,张王恩才发现,这是一窟很大的山洞,石壁光滑,每隔一段都挂着一盏松明灯。女子脚步极快,张王恩奋步直追。走了好久,女子转向左侧,倏然消失。张王恩走近一看,里面是一处更大的洞窟,无数的松明灯,照得整个洞窟如同白昼,洞里两侧,分别有成排的精致房屋,门前是盛开的花圃,好像是月季花,一簇簇,整齐好看。洞窟的中间,有一条水渠,清亮亮的流水不知从哪里来,但流速不缓不急,一直流向洞窟另一端的黑暗处。
可张王恩没心观赏这些,一边走,一边叫弟弟张付义的名字。
张王恩发现,这里很奇怪,巨大的洞窟中,尽管有很多人来来往往,但没有人注意到他,甚至从他身边走过的,也好像觉得他不存在,风一样飘过。
来来回回转了好几圈,还是没发现弟弟。
此时,那位女子也不见了踪影。正要出洞的时候,女子又忽然出现在眼前。双手捧着一只金光闪闪的盘子,上面放着一些珍珠宝石之类的,那灿烂光华,将山洞映照得金碧辉煌。张王恩哦了一声,看着那些珠宝,兀自呆怔了一会儿。女子笑说,你要是留在这里,这些就都是你的了。张王恩哦了一声,后退几步。想了一会儿,摇摇头说,我不能留在这,娘还在家等我们呢!女子笑了一下,又说,不光这些珠宝,这洞里的一切,包括我,也都是你的。
说到这里,女子微笑着,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两腮荡起好看的酒窝,眼睛里汪了一层涟漪……张王恩心神荡了一下,像在高空飞翔一样。张王恩揉了揉眼睛,又在自己胳膊上拧了一下。抬起头来,看着那女子说,俺还是不能留在这里,从小,娘一把屎一把尿把我拉扯大,现在又上了年纪,需要人养,俺不能忘恩负义。说完,甩开大脚,径直往洞外走去。
身后传来女子的咯咯娇笑,张王恩回身一看,女子身边又多了一个人。张王恩定睛一看,竟是自己的弟弟张付义。张付义好像喝多了酒,躺在地上,手里還抓着一只银色的酒杯,脖子上挂满了宝石项链。
张王恩走过去,把张付义身上的东西摘下,放在地上,把烂醉的弟弟背在背上,快步向洞外走去。身后传来那女子的一声叹息,在空旷的山洞里,像是一枚擦着岩石下落的树叶,又像是金子敲击的声音。
走出山洞,阳光兜头直射,鸟鸣声此起彼伏,这里竟然是自己村子的后沟。
张王恩回身,哪里有什么房子和人?只见一面悬崖下,是一片平坦的草地,众草匍匐,都很鲜嫩。靠近悬崖处,长着几棵红艳艳的山丹丹花。花朵艳丽,在风中轻轻摇着身子,还有几只大黄蜂,趴在花瓣上嗡嗡地吮吸花蜜。
此时,张付义也醒了过来,惊诧地问张王恩,哥哥,俺这是咋的了?
张王恩简单说了情况,然后说,赶紧回家,咱娘在家肯定很着急。说完,二人疾步回到家里。他们的老母亲仍在痛哭,眼睛肿得好像大红枣。蓦然见兄弟两个安然回来,一把抱住两个儿子,使劲拍他们的后背。兄弟二人在母亲面前跪下,也痛哭流涕。
母亲把他们扶起来,说,孩子,咱们不哭了,你们都好好的,这比啥都强!
从这以后,又不知道过了多少年,东边兵来西边兵去,还有灾荒和地震……有一年开春,村人到高台子上去刨地种玉米,有人惊呼,张王恩一家,连人带房子都没了踪影,只剩下院子里的一棵老梧桐,一堆喜鹊在高高的树杈上叽叽喳喳。
奇怪的是,那些喜鹊的头,都朝着后山那片巨大的森林。
责任编辑 丁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