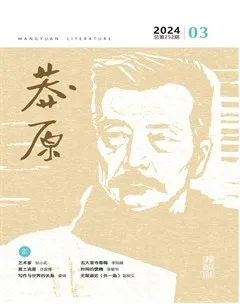环
魏秉倩
母亲从不催我结婚,但她总是不厌其烦地说起我该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正直的,脾气好的,专一的,听得进别人话的……她甚至为该将哪些品质放在前几位而大费脑筋,想要守住最重要的,又不敢奢求尽善尽美。每当谈论起这些,母亲总是沉浸其中,直到给出一个她认为满意的序列,似乎她给出的正确建议将是女儿婚姻幸福的前提。最后总不忘添一句“千万别过得和你妈一样”。
对此我已经习惯了,任由她描绘她认为“应当如此”的婚姻。我们都清楚,这些算不上挑剔的要求当中有许多是我父亲未能达到的,所以她才在女儿择偶这件事上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势必要将她过去二十多年积攒的经验,或者说教训都用起来。似乎只有在我的婚事上超常发挥,才能稍稍弥补她在自己婚姻中吃下的亏。自半年前我接母亲与我同住以来,她对此事的热忱有增无减,不时地暗示我该找对象了,要多经历,多磨炼,才知道什么人适合自己。总而言之,“千万不能像她一样”。
对母亲而言仪式般的谈话于我已如嚼蜡,我为她甘愿拿自己当反面教材的精神而感动,却不认为只要反过来结果就会是好的。但我并不阻止母亲的喋喋不休——除了为我考虑,她也在哀悼自己的婚姻。
“和你说认真的,别总是嗯嗯啊啊的。”觉察到我的心不在焉后,母亲停下手上的动作,朝我转过身来。
正值日落时分,余晖斜穿过卧室的窗子,将桌上那盆兰花的影子投了下来。不偏不倚,正好在母亲略显臃肿的腹部形成一个“Y”字。她鬓角的白发在日光下近乎透明,脸上的皱纹更是有如木刻般,在即将消逝的昏黄中裂出几道深色的阴影。我悲哀地发现,母亲已确乎是一个半衰的女人。
那个“Y”,我家也有一个,那是母亲的环。
母亲的环是在我高考后的那个暑假取下来的,那一年她四十七岁。也是在那一年,她与父亲终于离婚。直到现在,看到如同烙在母亲腹部的那个诡异形状,我似乎才明白她是如何穿越时间站到这里来。
那天是我第一次去医院的妇科。虽然没有太多东西需要准备,但母亲还是一早就起床了。在前往医院的路上,我问她为什么现在去取环,因为看起来她似乎没有什么不适。母亲说自从听说了邻居张阿姨的事情,她就一直心神不宁,决定还是来医院一趟。
“你张姨今年五十三,已经绝经三年多了,一直没想着取环。后来下面一直出血,到医院一查,才发现环已经长进了肉里,子宫都穿孔了。”
“是好久没见张姨了。然后呢?”
“后来做宫腔镜手术才取出来,花钱又受罪的。医生说像她这种情况,有的已经发展成子宫癌了。”
母亲说话时洒水车从旁边经过,被淋湿的地面荡起灰尘,蒸腾的热气直往人的裤脚里钻。风也吹过,一时不知道是凉是热。我和母亲一阵沉默,好在同样无知的我们知道这个故事的时候还不算晚。
我终于想起点什么。“妈,可你不是还没绝经吗,可以现在取吗?”
“拿掉算了,现在留着也没用。而且你都十九了,我上的这个环也快到使用期限了。”
“当初为什么要上这个环啊,不上不行吗?”我不敢看母亲的眼睛。为什么不用别的方法避孕?我羞于说出口。
她倒很爽朗,“傻闺女,我不上环你怎么上户口,怎么上学?”
医院的空气中是令人不安的消毒水味,走廊的墙上张贴着各种普及怀孕、生产知识的宣传图,女性生殖器的示意图赫然在目。一对对男女来来往往,大着肚子踱步的女人身旁几乎都有一个忙乱狼狈的男人,满手的检查单和缴费单。也有无人陪同的年轻或年老的女人,对着电话低语。人们站着等,或坐着等。一个人等,或两个人一起等。父亲说他这几天要到外地出差,于是走廊里多出我和母亲这样的组合。各色木然冷漠的神情几乎让我失望了——这里全然没有电影中那激动人心的情节,没有得知怀孕后喜出望外的夫妇,没有年轻女子神色哀伤地捂着腹部,甚至连产房外也没有焦急等待的男人。大概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明白生活不是电影。
到我和母亲时,前面已经排了五个人。坐在我们一旁的是一个怀抱婴儿的年轻女人,头发随意挽成一个发髻垂在颈后。
小孩还不到会走的年纪,从绣着花边的被单里伸出一只粉色的小脚丫,小腿直蹬,一下下地正好碰着母亲的胳膊。年轻女人看着我们笑笑,紧了紧被子,往边上挪了挪。
“没事的。几个月了?”母亲说着把一根手指放到孩子的手心里,细粉的小手一下合了起来。
“九个月了。”
“看着也像。小手怪有劲的。”
很快她们便攀谈起来。我在一旁保持着沉默,怀孕、生产、哺乳,那是少女尚未触及的、令人羞愧脸红的成年世界中才有的事。从她们的交谈中我得知,年轻女人是来医院上节育环的,眼前的小婴儿原本不在计划之内,她和她的丈夫怕意外再次降临。后来,她们说到牛羊肉的价格,说到哺乳的辛苦,又说起上一辈的农村女人,说那时候不知道节育,家中的女性长辈因为生养孩子吃尽了苦头,一家八九个孩子是常有的事。
我看到过奶奶那几乎垂到肚脐的乳房。它们因脂肪流失而显得越发的薄,像两片肉做的口袋挂在胸前。奶奶曾不得不在夏天拎起它们散热,还说就是这对“妈妈”奶大了八个孩子。“妈妈”是我老家对乳房的俗称,在没有奶粉的年代,没有哪个孩子可以不吃妈妈的奶长大。乳房就是妈妈,妈妈就是乳房。“八九个孩子”,意味着有七八年的时间都在怀孕。我又看到母亲肚皮上密布着的蚯蚓似的妊娠纹,那是皮肤被撑开的伤痕。我不禁感到恐怖了。
诊室内传出母亲的名字,到我们了。里面坐着的是一位五十多岁戴着口罩的女大夫。
“要看什么?”大夫没有抬眼,只是顿了顿手中的笔。
“我想……我想把节育环取掉。”母亲声音低到只有近旁的人能听到。
“多大了,绝经了吗?”大夫看了母亲一眼,几乎是喊出了这句话。
“四十七……没有。”母亲的声音越发沉了下去。我已经很久没在她脸上看到那样窘迫的神色。
“月经结束后三到七天内取环,取环前一天不能同房。今天能做就去隔壁等。时间不对就下个月再来。下一个。”一连串数字赶着从口罩后面蹦了出来。大夫抬抬下巴,以刚好能讓人觉察的最小幅度示意下一个患者填补空位。
“……什么?几天?”母亲彻底迷茫了。她身子前倾,眼神清澈,迟钝而认真。
白口罩机械地重复了一遍,语气中的不耐烦催促我们腾出位子。
我有意放慢语速向母亲解释着,试图用自己的从容维护她的体面。
来到隔壁,医用隔帘后有一张窄床,旁边是放着各式镊子、剪刀和大小玻璃瓶的推车,反射出冷白的光。医生示意母亲平躺到床上。
如此简单。让母亲记挂许久的事在妇科医生看来简直不值一提。这里每天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生产和流产,上环和取环,一切都按照流程冷静而有序地进行着。请勿喧哗。
等待母亲出来的这段时间里,我想象着人们说的“环”到底是什么样子。我曾读过对它的介绍,节育环是专用于女性的节育工具,放置在宫腔里,通过干扰精子实现避孕。它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也就是我母亲那一代的女性普遍使用的一种避孕手段。尽管如此,我还是无法具体地想象这个东西如何被放进一个个子宫,又如何在多年后被取出并丢弃,或者干脆被遗忘,楔入血肉,变成无法腐烂的一颗钉子。她们能感受到它吗?被环锁上的女人会痛吗?她们的丈夫知道这些吗……
母亲从房间里出来时,手里拿着用纸包着的一个东西,是个小小的“Y”型金属。像禾苗,像剪刀,像张开的双臂。我没想到母亲把这个东西带了出来。就是它,在母亲身体里藏了近二十年。环已没有了光泽,褶皱弯曲处还沾染着没来得及清理干净的液体。
“做了個B超,医生说环已经有点移位了,顺便还切了一个囊肿。”母亲有些疲惫,但看起来轻快了许多,说取完药就可以回家了。
近十一点钟了,医院里的人多了起来,各诊室的门口都乱作一团。我和母亲为避开了排长队而庆幸,现在回家还有充裕的时间做午饭。走到楼梯的拐弯处时,一个熟悉的背影从我们前面不远处经过。
不可能认错,那是我父亲。那身衣服、那个体型我都再熟悉不过。同时,他旁边还有一个女人。他的手还搭着她的肩。
我下意识地看着母亲。谢天谢地,她没有看到。此刻她还在谈论着今天的午饭。还好,我只是怔了一下,没有让母亲察觉到我的慌乱。多年后再想起那个时刻,我竟只记得侥幸,一个女儿为自己的母亲不明真相而侥幸。哪怕当时只是我以为。
父亲的谎言并不令我意外。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已经习惯了和母亲两个人在家的日子。起初,他给出的解释是工作忙,但无尽的重复和循环逐渐使所有人都筋疲力尽,于是问的人不再问,答的人也便不再解释了。虽然隔着两道门,我还是从他们压低了声音的争吵中知道了有另外一个人存在,就是那天我看到的那个背影。我无法不去想,他那天去妇科干什么?他知道我和母亲那天也去医院了吗?他知道母亲到了需要摘环的年纪了吗?还有,他背对我们时脸上是不是挂着笑,那许久未对我们流露的笑?我知道总有一天所有的争吵会迎来一个结果,只是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个结果很快就会到来,还不知道摘掉节育环只是母亲计划中的一个步骤。
那段日子里,我多次想要找一个合适的时机不露痕迹地问父亲他那天的行踪,甚至准备好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回答,可我终究没有开口。我的重重心事被母亲看在了眼里,只是当时我浑然不知。我为要不要告诉她那件事而纠结了一个假期,直到离家的那一刻,我还是没能说出口。当我无数次看向母亲时,她都平静地忙碌着,忙着帮我填报志愿,忙着准备我上学可能用到的东西,不见喜怒,甚至连与父亲争吵的次数都少了许多。我疑心事情是否向好的方向发展,直到我几乎已经沉浸在新奇的大学生活而忘记家事时,母亲打电话告诉我她离婚了。在电话里她还说,那天我在医院里看到的她早看到了,而且她看到我看到了。过去的已经过去,她很高兴有我陪她。
大一寒假我回到家,家里已经没有了父亲的痕迹。刚回去的那几个晚上我总是睡不着,黑暗中似乎有一个东西正透过墙注视着我,那个东西对我了如指掌。我学说话的时候,它看着我;我学走路的时候,它看着我;我从孩童到青年的每一个时刻,它都没有离开。它早就到来,只是从未声张。它看大了一个女人,却锁住了另一个女人,见证了她生命中一场漫长的战争。它就是从母亲身上掉下来的环,静静地躺在她卧室的抽屉里。旁边放着的,是母亲曾经的婚戒。
责任编辑 申广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