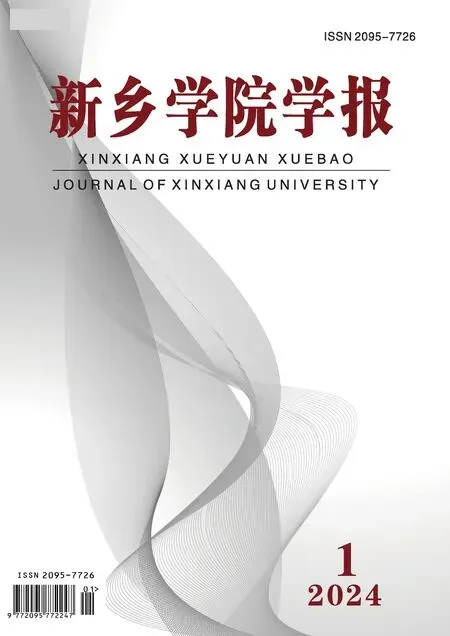论宋代散文的嬗变及其“尚奇”思想
樊宇敏,韩 辉
(新乡学院 人文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3)
在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散文理论和诗歌理论随着作家群的出现较早地展现了独特的魅力,并成为贯穿古代文学批评的文体理论。但是,整体而言,散文理论斑驳繁杂,没有明晰的体系。这是因为“文”在先唐时期一直以杂文学的面貌出现,其内容的广泛性、实用性难以与经学、史学以及应用文体作品区别开来,这就造成了散文理论缺少像诗歌等文学样式所具有的鲜明文体特征。也就是说,“散文”是从经学训诂领域所谓的“词体散文”“语体散文”的阐释中酝酿形成的,一旦步入文学领域,“文体散文”仍然以“词体”“语体”等形式展现其文学特征和艺术形式。唐宋时期,尤其是两宋,较为重视散文中出现的“尚奇”思想。因此,对于“尚奇”的创作观念的肯定与否的态度,影响着散文创作的走向,对于散文创作和理论发展都具有一定的先导作用和实践意义。
一、宋代散文理论的历时性架构与形成语境
从历时性角度而言,“词体散文”“语体散文”及其相关理论萌孽较早。先秦时期对于“言”“文”“章”的论说,聚焦于文章与自然、社会、人性的关系上,不仅没有明确的散文概念,甚至没有散文自己独立的地位。但此时,言简意赅的论说却成为后世历代文论家所遵奉的圭臬。《周易》所称“言有物”“言有序”等观念直到清代还被文论家们引入散文创作论中加以提倡;孔子“文质彬彬”的理想成为千百年文章写作内容与形式和谐相称的标准;老子“法自然”“致虚”“守静”的处世态度对散文理论中崇尚虚静澄思的创作论的形成有积极的导源意义;《左传》关于“春秋笔法”的总结,以及墨子“言有三表”、讲究“义法”的文学理念,均在散文理论的暗流涌动中汇聚一体,成了散文实践的理论先导。
文学自觉时期的文论家们把“文”提升至“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1]的崇高地位,于是文学开始从经学、史学中分离出来,并确立了自己缘情重采的特性。尽管此时已经出现了诗论《诗品》,但散文理论仍不成体系地撒播于文学总论或相关著作之中。如《文心雕龙》所提倡的“明道、徵圣、宗经”的“文之枢纽”观在后世散文理论中得以发扬光大。由于时代风尚和文学审美特性的发现与重视,魏晋时期的文章理论偏向于骈文,论述中倾向于文章的辞采藻饰、骈词俪句。魏晋时期还形成了我国古代文论中对文体特征进行研究的传统,无论是单篇的《典论·论文》《文赋》,还是并存于总集或别集中的《文选序》《金楼子·立言》,乃至系统论述文学理论的《文心雕龙》都对各体文章的特性进行了探讨,其中尤为突出的“文笔之辨”,以行文的用韵与否来为繁多的文体归类,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于文学功用和特征的认识,另一方面对于散文文体特征的确立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隋唐五代是散文创作勃兴的时期,散文至此有了明确的概念,散文理论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元结、李华、萧颖士、梁肃、柳冕等人对文章创作尊崇宗经复古、弃骈就散等原则开始,到韩愈、柳宗元首倡古文运动而蔚然可观;从李翱、皇甫湜继承师学、力将古文运动进行到底,到杜牧、李商隐、孙樵等人修补弊端,倡骈文复兴,唐代的散文理论领域大家辈起,名篇迭出。如韩愈《答李翱书》《进学解》,柳宗元《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李翱《答朱载言书》,皇甫湜《答李生第一书》,李德裕《文章论》,杜牧《答庄充书》,李商隐《上崔华州书》《樊南甲集序》,孙樵《与友人论文书》等,均是专论散文创作的作品,其中尤以秦汉文章为范本的“古文”创作探讨甚丰。此时的“古文”,为别于四六骈体文计,俨然成为“文体散文”的代名词。因此,唐代散文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总结大多经历了一个由骈到散,又复归于骈的发展过程,这既暴露了骈文自身不可避免的缺陷,也反映了散文创作和理论革新过程中以古救今观念的局限,为进一步寻求切实有效的革新发展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经历了雄厚的理论奠基和大浪淘沙般的文学实践之后,宋代散文创作迎来了全方位的革新和发展时期。北宋时期的散文理论在初期表现为严格的复古观,强调对古人文章的字模句拟,如柳开《应责》、石介《怪说》即是。介于柳开、石介和欧阳修、苏轼等人之间具有承上启下作用的王禹偁主张“句之易道,义之易晓”的为文之道,欲以发挥文章“传道明心”的功用,对宋代散文平易自然文风的形成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整体而言,宋代的散文理论成熟于欧阳修和苏轼父子的散文创作中。欧阳修在《答庄充秀才书》《答祖择之书》《送徐无党南归序》《论尹师鲁墓志》等书信序跋中明确提出“道胜文至”“事信言文”的文道观,提倡散文创作“简而有法”,崇尚语言自然,反对模拟。他结合自身的创作实践,建立了宋代兼收并蓄的骈散之美、自然畅达的散文传统。其后,苏轼继其成说,在《岛绎先生文集序》《南行集序》《答张文潜书》《答谢民师书》《文说》等文论篇章中继续强调“道”的认知与实践关系,要求文章“有为而作”,提倡“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的自由创作,强调对客观事物充分的认识和表现,在崇尚自然的基础上发展了古代的“辞达”理论。随后形成的苏派文风漫卷文坛,蔚然成风,从而使得散文理论实现了自身的成熟,他们所确立的骈散结合、自由畅达的艺术表达方式也成为散文的主流文体形态。
二、宋代散文“尚奇”思想源流考
“奇”这一词语最早用于军事领域。“以正治国,以奇用兵”[2]。“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3]。《说文》释“奇”为“异也”。“奇”指战争中的谋略战术安排新奇、有创新,不合常规,能够出人意料,对战争的结果有很大影响。“奇”这一军事学概念在汉代也被文论家们关注并重视起来,被用于品评文章、鉴赏文字。汉代王充最早引“奇”作为散文理论概念,在《超奇》和《对作》中阐述了“奇”作为散文理论范畴的主要理论内涵。《超奇》曰:“故夫鸿儒,所谓超而又超者也。以超之奇,退与诸生相料,文轩之比于敝车,锦绣之方于缊袍也。其相过,远矣。如与俗人相料,太山之巅墆,长狄之项跖,不足为喻。故夫丘山以土石为体,其有铜铁,山之奇也。铜铁既奇,或出金玉。然鸿儒,世之金玉也。奇而又奇矣。”[4]607文中的“奇”指鸿儒的文章所呈现出的特点,即内容宏博,思路巧妙,语言精细,超出常人。王充之“奇”是对文章创作理想状态的一种描述,也是王充对文章进行品评的重要标准,是肯定“奇”的创作观念和作品形态的。但《对作》篇又称:“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词,为奇伟之观也。其本皆起人间有非,故尽思极心,以讥世俗。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语,说虚妄之文。”[4]1179这里的“奇怪”之“奇”,是指创作一味求奇,靠夸饰来引起关注,出新意于虚妄,这样的“奇”则表现为语言诘屈聱牙、艰涩难懂,王充对于这样的“奇”则持以否定态度。《论衡》中的这些论述,以语言文字尤其是文章创作为对象,用“奇”作为评价和描述的概念标准,所述概念明确,内涵清晰,可以作为“奇”范畴在散文理论中成立的标志,也就此确立了“奇”在散文理论中的两个相反相成的重要核心意义——文思超群和虚妄怪异。
其后,进一步将“奇”的概念用于文论,并结合兵法中“奇”“正”对举的特点丰富文论的概念范畴的文论家是刘勰,他以儒家经书典籍为“正”,认为“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而对近世的文章则多有批评,认为其“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5]445。刘勰认为文学创作如果偏离了本原,忽视内心的修养锻炼,只注重文辞字句的经营,就会使文章徒有其表而内在空虚。这样的创作环境也会造成受众心理上产生尚奇求异之思:“然俗听飞驰,职竞新异,雅咏温恭,必欠伸鱼睨;奇辞切至,则拊髀雀跃:诗声俱郑,自此阶矣。”[5]64由此可知,刘勰对于有异于经典的新意奇文颇有微词。因“俗皆爱奇”而“莫顾实理”,以致“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5]150,这些弊端的存在,使得刘勰称宋初的诗作是“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5]61。刘勰有明确的去奇存正的态度。在《体性》篇中,他明确将“奇”列于文章八体之中,“新奇者,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5]256,将“奇”所代表的偏离本原、浮诡空虚的一面作为这一理论范畴的主要内涵。八体中两两为对,有褒贬之分,其中“雅与奇反”,“典雅”为“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5]255。而新奇与之相悖,则是带有贬义的。奇虽与正相对,但奇不一定都是侧诡,经书也有奇观,孟子文章就经常呈现出宏奇的特色,创意造言不同常格,也是奇的表现。因此,刘勰对于奇的态度还是有矛盾的,他的写作目的是要纠正当时文坛竞为新异绮靡的卑弱文风,但作为理性的文论家他又不能不看到奇文采辞的价值:“若乃羲农轩皞之源,山渎钟律之要,白鱼赤乌之符,黄金紫玉之瑞,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5]37站在文学的立场上肯定奇的正面意义,进一步深化了王充《论衡》中界定的“奇”的两种范畴。
《论衡》与《文心雕龙》两部文论著作中的相关论述,确立了散文理论中“奇”范畴的核心意义。唐代的散文创作和理论表述都基本沿着“尚奇”思想而展开。中唐古文大兴之际,韩愈、柳宗元跌宕开阖、奇伟诡谲的文风,皇甫湜对奇的偏执追求和强化,使得“奇”在散文理论中的核心地位和价值益见凸显。但是,随着晚唐骈体尚繁创作风气的复归,散文创作和理论发展又一次出现转折,而文人们对“奇”的认识也随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有宋一代,“尚奇”思想在新的散文理论环境中有了全面的展示和更加贴合创作的深入发展。
三、宋代散文“尚奇”思想的文学实践及其理论革新
北宋的文论家们对于求“奇”的创作观念和新奇的作品特点大多持肯定的态度。曾巩《南齐书目录序》称:“两汉以来,为史者去之远矣。司马迁从五帝、三王既殁数千载之后,秦灭之余,因散绝残脱之经,以及传记百家之说,区区掇拾,以集著其善恶之迹,兴废之端;又创己意以为本纪、世家、八书、列传之文,斯亦可谓奇矣。然蔽害天下之圣洁,是非颠倒而采掇谬乱者,亦岂少哉!”[6]188作者肯定《史记》“奇”的价值是基于《史记》的艺术形式而言的,认为司马迁著录史实的角度和方法独出新意,既能够保存历史真实,又可以丰富史传的创作形式和评价角度,是对于“奇”的正面意义的明确肯定。但正如诗文革新时期的诸多文论家一样,他对于理论概念的认识和态度都显示出理性客观的特点。《读贾谊传》曰:“余读三代两汉之书,至于奇辞奥旨,光辉渊澄,洞达心腑,如登高山以望长江之活流,而恍然骇其气之壮也。”[6]700他将 “三代两汉”的经典文章也归结为“奇”,足见其文论思想的转变基本突破了相对传统的重正道观念。因此,曾巩“尚奇”思想的文学实践和理论创新成了欧阳修“师道尊经”的平稳文风与苏轼“任心随意”的奇旷文风之间过渡的桥梁。
众所周知,苏轼的文章纵横捭阖,奇旷非凡,作文的观点和态度对当时的文学观念影响很明显。苏门学士张耒就对此有着较为通达的看法。他尽管强调作文本理,理胜而文自工:“故学文之端,急于明理。夫不知为文者无所复道,如知文而不务理,求文之工,世未尝有是也。”[7]828然而,张耒仍然注重奇思妙想:“足下之文,可谓奇矣。捐去文字常体,力为瑰奇险怪,务欲使人读之,如见数千岁前,蝌蚪鸟迹所记弦匏之歌,钟鼎之文也。”[7]828他认为这样的奇文正是由于内在充沛而不得不发为文,自然呈现高奇的面貌:“江、河、淮、海之水,理达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沟渎而求水之奇,此无见于理,而欲以言语句读为奇之文也。”[7]829理不胜而欲求文奇,只能在言辞句读这些形式上下工夫,自然不会真正达到奇的效果。
在阐述了“奇”的形成来源于文章“内里充沛、广博多理”之后,张耒对于当世“好奇者”走向歧途的做法进行了批评:“自唐以来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为缺句断章,使脉理不属。又取古书训诂,希于见闻者,衣被而说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句,不知其章。反复咀嚼,卒亦无有,此最文之陋也。”[7]828强调这三种徒有形式而内蕴空洞的表现是作文者需要慎之又慎加以避免的。据此可知,张耒“尚奇”理论基本总结了上古圣贤的经典文章中所蕴含的此种思想:“《六经》之文,莫奇于《易》,莫简于《春秋》,夫岂以奇与简为务哉?势自然耳!”[7]828“奇”本是与“自然”相对的,但是张耒承自苏轼通达的创作观念,将二者有机融合,从而实现了这个理论范畴多重内涵的统一。这对于“尚奇”范畴在散文理论中的核心价值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南宋理学家对于文章创作的态度,尤其是对于“奇”的态度与北宋的古文家不同。楼钥《答綦君更生论文书》认为:“唐三百年,文章三变而后定,以其归于平也。而柳子厚之称韩文公,乃日文益奇,文公亦自谓怪怪奇奇。二公岂不自知,益在流俗中以为奇,而其实则文之正体也。宋景文公知之矣,谓其粹然一出于正。至其所自为文,往往奇涩难读。岂平者难为工,奇者易以动,文人气习终未免耶?《典》《谟》《训》《诰》,无一语之奇,无一字之异,何其浑然天成如此!”“如伊川先生之《易传》,范太史之《唐鉴》,心平气和,理正词直,然后为文之正体,可以追配古作。而遽读之者,未必深喜。波平水静,过者以为无奇,必见高崖悬瀑而后快。韩文公之文,非无奇处,正如长江数千里,奇险一时间见,皆有触而后发,使所在而然,则为物之害多矣。”[8]楼钥不仅强调经典文章都是浑然天成、务为平稳的,而且对于韩、柳二人自认为奇的作品也指出其本质仍是“文之正体”即“心平气和、理正词直”的平稳之作。“称奇”只是学养不足的流俗所见,没有认识到文章的根本,一如阳春白雪必曲高和寡。楼钥的这些观点是出于理学家的思考而产生的,有着明显的重道轻文倾向,是南宋理学渐盛的结果,但却几乎从根本上否定了“奇”的正面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