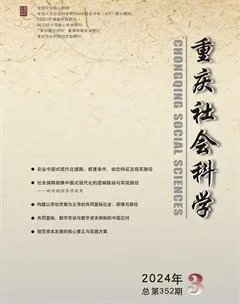构建以劳动贡献为主导的共同富裕社会:困境与路径
陈潜 林子筱 郑博匀
摘 要: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之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构建的共同富裕社会是以劳动贡献为主导的共同富裕社会,而维护劳动正义是构建以劳动贡献为主导的共同富裕社会的关键。在马克思劳動正义观视阈下,生产资料为劳动者占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基础,劳动过程的正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劳动成果分配公平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规定。然而,构建以劳动贡献主导的共同富裕社会面临资本逻辑下的思想束缚、数字经济下的正义阻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的制度制约等多维困境。以马克思的劳动正义观为指引,以批判性视野构建劳动正义的价值共识,推动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正义再塑,完善财富积累机制,着力构建以劳动贡献为主导的共同富裕社会。
关键词:共同富裕;劳动贡献;劳动正义;马克思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马工程重点项目“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关系研究”(FJ2023MGCA009);福建省委党史方志办、福建农林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共同富裕道路的历史经验与现实路径研究”(22FAFUDJ014)。
[中图分类号] F046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4)003-0035-010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4.003.003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促进机会公平。”[1]中国劳动者既是生产社会财富的主体,又是新时代共同富裕的主体。正确理解劳动在实现新时代共同富裕中的重要性,既要承认一切劳动者的劳动价值及全体社会成员参与共同劳动的必要性,又要彰显劳动对新时代共同富裕的重要贡献。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明确,“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1]。因此,不断提高收入分配中劳动报酬占比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而维护劳动正义是其中必要的准备工作。当前,数字经济发展、资本扩张、技术进步等因素使劳动的正义性受到严峻挑战,坚持以劳动贡献主导的共同富裕面临诸多现实困境。目前学界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丰硕,学者们一方面集中在劳动正义对共同富裕价值支撑的研究上,另一方面将劳动正义置于技术进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等视野中考量,这些研究无疑对本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通过回溯马克思的劳动正义观,立足于新时代构建共同富裕社会的现实困境,以期在马克思的劳动正义观对新时代构建共同富裕社会的指引上寻求突破。从劳动正义的角度检视当前劳动的内容与方式,以批判性视野矫正劳动的非正义性因素,以促进劳动解放为目的,助力共同富裕社会的实现。
一、马克思劳动正义观的内涵及其与共同富裕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劳动正义观生发于其对唯物史观架构的进程之中,阐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是损害劳动正义的核心要素。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共同富裕不仅要逾越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也要对资本主义追求财富扩张而忽视主体价值的现代化模式进行扬弃,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对马克思劳动正义观的践行。
(一)马克思劳动正义观的科学内涵
劳动是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内最重要的范畴,正义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中的焦点问题之一。马克思的正义思想以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旨趣,超越了西方自由主义的正义观,呈现了一种崭新的正义形态。何为正义?正义是涉及人们利益的社会行为的等利或等害交换,这种交换行为是否“具有均等、比例性质”[2],成为这一行为是否正义的评判准则。显然,正义是规整人类交换行为的道德准绳,具有规范性与批判性。劳动正义作为偏正结构词汇,是将正义置于劳动的前提下考量。何为劳动?在马克思劳动正义观视阈下,劳动是人们在“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3]162的目标下开展的改造与创造对象世界的感性对象化活动。由此可见,劳动一方面是创造价值与生产使用价值的财富积累活动,另一方面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方式。因此,劳动是一项将人与自身、社会、自然、他人等发生价值关联的内隐性议程[4]。在资本逻辑倏然生成与全面布展的现代社会,劳动正义已然成为一个值得反复审视的伦理概念。劳动正义既内蕴着劳动交往过程中的正义性关怀,也渗透着对与正义脱嵌的不合理部分的理性超越与正义牵引。
马克思劳动正义观是在对资本正义的激烈批判中建构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相信资本主义社会“天然正义”的谎言,马克思则敏锐意识到,资本正义虽然是对主体自由意志的肯定,但其仅仅是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流通,是一种形式正义。所谓的资本正义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5]马克思对资本正义的批判,并不代表他对正义的拒斥,也不代表马克思的思想无任何正义立场,而是变革了正义讨论的理论视角,转而立基于劳动正义的思想态度[6]。理论只有在物质生产的劳动领域深耕,才能真正地理解正义的内涵。在马克思的视野里,劳动无疑是人自由自觉的本源性活动,相对于资本而言劳动具有优先地位,因而马克思劳动正义观以实现“劳动解放”为终极旨趣。具体来看,劳动解放大体包含三重意蕴。其一,劳动是基于自愿的、心情愉悦的联合劳动。其二,劳动解放使得社会财富的源泉从人的直接劳动转变为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其三,劳动解放意味着个人所有制的重新建立,资本主义所有制被彻底废除,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再次合一。不断累积的劳动将展现人的创造性,并丰裕人的自由发展。
(二)马克思劳动正义观与共同富裕的辩证关系
“坚持马克思劳动正义观为通往共同富裕的道路标明了行进方向。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不应过度强调收入分配的重要性,而弱化生产在共同富裕推进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7]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8]假若没有生产力的有力支撑,谈共同富裕是苍白无力的。回到马克思的生产性视角,坚持马克思劳动正义观,方能指引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的正确方向。在共同富裕与马克思劳动正义观的辩证关系上,从生产资料由谁占有、劳动过程是否正义、劳动成果分配是否公平三个方面出发,马克思劳动正义观与建构共同富裕社会一脉相承,马克思劳动正义观为促进新时代劳动者的全面发展,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政策遵循与实践指向。
1.生产资料为劳动者占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基础
社会财富的据有从根本上取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而实现劳动正义的前提就在于解决生产资料初始占有的问题。生产资料的缺失势必导致生产活动的迟滞,共同富裕更是无从谈起。因此,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基础在劳动的前提,即生产资料的占有问题。社会贫富差距的总源头在不合理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是马克思在考察资本积累的过程后得出的重要结论。站在资本积累的历史逻辑上看,资本家通过欺骗、掠夺、盗窃等非正义性的侵占方式完成了私人最初的财产累积,致使广大劳动者被迫与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相割裂,只有通过出卖劳动维持生计。然而,这却相悖于劳动是私有财富的主体本质。在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条件下,社会财富的分配只能采取按资分配的形式,劳动者只能沦落为受资本压榨的弱势群体。总之,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势必赋予私有财产以主体性,资本家的财富不可逆转地不断扩张,社会贫富差距的鸿沟不可避免地加深,共同富裕也就无从实现。从供给侧视角考虑,要将生产资料“解放”这一劳动正义的前提正义推进到社会劳动的全过程。从需求侧视角考虑,共同富裕社会务必保证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的推行[9]。关于生产资料“解放”的实现问题,马克思也指明了基本思路,指出财产私有“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3]182。劳动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消除贫困对于生命的威胁,完全否定私有财产的思想是不可取的。盲目地摧毁私有财产以推行私有财产平均化的行为,只会造成生产力的倒退。而共同富裕社会的实现,要在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扬弃的同时重建个人所有制,构建一个社会劳动联合的共同体。
2.劳动过程的正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
劳动者要想保证自身的劳动正义,在劳动过程中就要拥有优良的劳动环境与和谐的劳动关系,如此才能实现劳动者对其自身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实现共同富裕要在对劳动过程的正义追寻中得到保障。而劳动不再为生计奔波,自主确定劳动目标是共同富裕社会的基本表征。在共同富裕社会中,人的本质存在将得到确证。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劳动正义观与共同富裕社会的价值诉求都指向人本质的解放与发展,二者的内在要求是高度统一的。在资本主义雇佣关系背景下,劳动沦为资本增值的中介。因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本应平等和谐的劳动关系物化成为货币的关系。在此非正义的劳动过程压迫之下,“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3]159也就成为现实,资本制约生产力的发展,共同富裕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生产力基础。在马克思劳动正义观视阈下,劳动的过程正义是自由自主的劳动,对劳动自由自主的追求内在地包含了对劳动关系和谐、劳动生产效率提升的追求[10]。劳动关系和谐是指劳动结构框架内的构成要素间以及要素与整体间的有机和谐关系,表现为人与人间的来往有序,人与自然间的来往有度,以及劳动制度的公平安排。劳动拥有正义的过程是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的先决条件。只有满足了马克思劳动正义观的劳动过程正义,劳动者的身心才能解放,其积极向上的人格才能养成,如此的劳动过程才能实现劳动者物质生产与自身发展的正义性统一,激励着劳动者为实现共同富裕而不断奋斗。
3.劳动成果分配公平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规定
分配正义是“共同”和“富裕”耦合之下产生的命题,正是试图破解人类文明史上未提出合理解决方案的财产分配难关。分配劳动结果的分配问题是涉及劳动伦理的重要问题,也是劳动者劳动的公平性与正义性的映射。劳动的结果正义是劳动者获得合理的劳动报酬,使劳动者通过劳动积累的财富与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水平呈高度正相关,为共同富裕社会的实现提供必要规定。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将劳动与货币的交换视作流通与交换框架内的合法范畴,将这种看似公平合理的交换形式奉为圭臬。然而,马克思却从中发现了劳动结果异化的实质。所谓“等价交换”是一种带有剥削性的、形式化的交换形式,资本主义的劳动分配带有非正义性,成为贫富差距的推进器。劳动分配正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备条件。只有构建共产主义共同体才能摆脱资本主义劳动分配的剥削性,避免劳动成果的个人积聚,使其为全体人民共享。在此条件下,资本与劳动的交换也指向社会共同体对共同富裕的寻求。马克思将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根据劳动者向社会提供的劳动贡献的大小实行按劳分配,如此不可避免地会形成劳动者财富占有的差距。只有到了第二阶段,当集体财富的源泉在社会中大量涌流时,真正的劳动分配正义才能得以实现。
二、构建以劳动贡献为主导的共同富裕社会的现实困境
虽然“共同富裕”与“共同富裕社会”分属两个概念,然而在“共同富裕”概念的使用过程中,渐进地内嵌着“共同富裕社会”的意涵。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1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成为理解“共同富裕社会”意涵的主要遵循。“共同富裕社会”应是一个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反映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以高质量发展为主要发展模式,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渐进式发展的和谐共富社会[12]。當前,技术进步、数字经济发展、资本扩张等因素损害了劳动的正义性,分析劳动正义面临的现实困境,有助于精准扭转劳动的部分非正义性因素,助力共同富裕社会的构建。
(一)资本逻辑下的思想束缚
资本逻辑在现代社会中表征为人的消极发展与物的积极发展的逻辑悖论。在现代境遇中,资本逻辑在技术进步的作用下越发加剧了劳动正义困境,误置了劳动正义的价值诉求[13]。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与技术发展在历史上有密切联系。现代社会中,资本和技术快速发展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受资本逻辑支配的劳动逻辑渐渐转变为技术融合,导致了一种畸形的发展逻辑,使人们忽视了劳动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资本逻辑的“合理性”在技术进步的加持下越发具有迷幻性,人们在强制话语的裹挟中被迫适应劳动的新形式,正尝试放弃追求劳动正义的正当诉求。然而,在社会生产力实现高度发达之前,劳动正义在社会生产中难以实现,这导致了如何实现与劳动本质力量相匹配的劳动正义价值诉求的长期困境。资本逻辑在技术进步中的话语权不断增强,劳动正义价值诉求的误置导致劳动的正义价值逐渐式微,又势必导致人们对这一价值形成共鸣的困难。马克思的劳动正义观要求劳动的最终目的指向人的尊严、自由、幸福。在技术进步的背景下,劳动深受资本逻辑支配,劳动的价值指向被资本力量强行同化,导致了劳动的价值与人生存的价值维度相背离的趋势。技术进步与资本逻辑的共同作用使得生产力的发展成为社会异化的根源,技术进步支撑下的劳动生产往往内蕴着技术背后的资本追求利益扩大化的目的,容易引发技术的“集权行为”,即顶尖技术向资本要素涌动与积聚,进而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共同富裕的目标在技术进步的进程下逐步沦为虚空。
(二)数字经济下的正义阻碍
数字经济时代下,劳动模式有别于传统,正向“依靠数字平台建立的劳动模式”[14]转化,因而娱乐性是数字经济时代劳动的重要特征。在此模式下,劳动者往往不能意识到自己正遭受严重的劳动剥削,反倒以更加积极的态度面对剥削。事实却是,数字资本运作下的劳动,娱乐只是掩盖资本剥削行为的一层面纱,劳动者正在面对更为严峻的正义挑战,落入“自我剥削”与“强迫快乐”的困境之中。其一,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剥削相较于传统劳动剥削更加隐蔽。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生产主要依靠平台进行,与传统劳动严重的精神与肉体折磨相异,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以不限时空的超时空劳动模式为亮点,使劳动形式表现得更加轻松愉悦。这种娱乐化的劳动削弱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加深了数字剥削。具体而言,从事程序编写的“数字劳工”们,剩余价值正在被无酬加班不断侵占;以网络博主、网约车司机等为主体的“数字零工”们,在平台算法的支配下强迫劳动;体验网络游戏的“数字玩工”们,潜在地为游戏公司生产数据,无偿为游戏开发与运维作贡献。其二,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产品与所有权相分离,劳动的前提带有非正义性。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劳动的主要劳动产品,也是现代社会生产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数字底层逻辑的支配下,作为数据的主要生产者,本应归属于数字劳工的数据被数字资本家占有,而数字劳工仅是获得局部数据的使用权。如此,信息匮乏的数字劳工们被囚于“信息茧房”中,信息鸿沟会因“马太效应”而进一步扩大。其三,数字经济时代劳动迫使劳动者自我监视,使劳动与其本质相背离,损害了劳动的过程正义。卷入其中的人们在数字系统中留下了大量数据痕迹,隐蔽地监视着人们,劳动者成为自我监视与自我规训的主体,劳动偏离了自由自觉的劳动本质。总之,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面临着劳动关系紧张、劳动本质背离、劳动分配失衡等正义困境,为构建共同富裕社会带来新的挑战。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的制度制约
拥有合理的财富调节机制是构建共同富裕社会的必要条件,在财富的生产、积累、分配等各个环节,合理的机制保障不可或缺。然而,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按资分配、非公有制经济等因素无法避免地制约着我国现阶段劳动分配的制度安排,我国在财富调节各个环节上的利益失调与贫富分化的现象依然存在,财富调节机制尚未成熟。在财富的生产环节,还存在着劳动报酬与资本要素之间分配失衡的情况。通过财富生产提高人民财富积累量的同时,也要同时控制财富积累量的差距。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是影响财富积累的重要因素,但当前我国财富积累机制尚未完善,21世纪以来我国财富基尼系数呈上升趋势,个人财富积累受其初始禀赋、机会选择等因素影响较大,“坚持勤劳致富”仍存在较大阻力。从流量来看,我国收入结构不合理是导致人们财富积累差异的重要原因。一是不同群体的工资性收入差别较大。有数据表明,我国城镇非私营单位人员的工资均值显著高于城镇私营单位人员,且二者的收入差距呈扩大态势[15]。二是工资性收入的增长比率显著低于财产性收入,劳动同资本在财富积累上的博弈处于劣势地位。从存量视角来看,不同群体间、不同区域间财富积累差异明显。我国顶级富豪占有的财富份额已超过英国、法国等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收入群体的财富份额正不断挤压中低收入群体的财富份额。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也存在显著差异。从代际来看,因为财富继承问题导致的财富差距问题亟待研究与解决。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国居民财富积累时间相对较短,目前财富集中人群属于“新富人群”,财富尚未出现大规模的代际传承。但未来,财富因代际传承的问题导致财富积累差距进一步扩大的问题将逐步显现,相关财富调节机制亟待研究与制定,为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作出政策保障。
三、构建以劳动贡献为主导的共同富裕社会的实现路径
坚持马克思的劳动正义观是解决当前劳动正义困境的重要途径,以批判性视野构建劳动正义的价值共识,推动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正义再塑,完善财富积累机制,着力构建以劳动贡献为主导的共同富裕社会。
(一)共识构建:劳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技术进步背景下,劳动正义的困境逐步形成资本增殖为劳动提供应有权益、劳动为资本增殖创造发展动力的稳定结构,造成资本增殖的“正义性”与劳动正义的激烈矛盾在技术进步中逐渐消解。在施行劳动正义的规范中,技术进步偏向于提高劳动的环境与整体氛围,为劳动者创造减少劳苦等“福利”。但必须看到,这些“福利”只是强调了劳动的结果正义,人们对劳动正义的追寻从对其内在价值的追求降级为对其结果的关注,势必导致现实性维度下对劳动正义过程的忽视。因此,重构劳动正义的价值共识是实现共同富裕社会的关键节点与重要课题,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进行社会治理所必须破解的难题。要想实现劳动异化转化为劳动正义,就必须促进和实现劳动发展逻辑与技术进步逻辑全面超越资本扩大逻辑,这就为技术劳动标明发展目标。技术劳动要在推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中实现正义,就要将劳动正义的价值置于社会发展的现实实践中考量,以特定时期的历史条件为支撑,制定科学的变革策略以促进劳动的辩证转化。劳动的对象化过程决定了劳动的辩证法,即人们要重构劳动正义的价值共识,只有将劳动的对象世界与人的生存与发展发生关联。同时,技术进步促使现代社会表征出个性张扬、物欲膨胀等特征,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要克服劳动正义价值的式微,不断探寻正义价值的真理性,在追求共同富裕的劳动过程中突出正义价值的真理力量。
(二)正义再塑:将正义原则贯穿到数字经济时代劳动的各环节
数字经济时代,劳动的生产性问题成为对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突破口,有必要对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所承受的境遇进行伦理反思与价值审视,旨在守护劳动本应实现的人的尊严与价值。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在非物质生产领域有着重要拓展,这一劳动的历史形变是马克思无从预料的,然而绝非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原典在这一劳动新形态上失去解释力。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使劳动力“商品化”的现象越发隐蔽与深刻。在数字经济时代,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劳动者在大数据的“算计”下付出更多劳动,而其却沉浸于“勤劳致富”的虚幻语境中。对数字经济时代劳动困境的破题,要以实现人的自由解放为根本目标。首先,唤醒“数字劳工”认知,提升“数字劳工”能力。数字经济时代下的劳动依然属于劳动范畴,仍是人主体力量的发挥,因而激活“数字劳工”思维中的主体意识显得尤为关键。要使“数字劳工”认清数字经济时代劳动的本质,帮助其辨明“劳动”与“娱乐”的异质性,确保“数字劳工”在劳动中的主体性地位。同时,增强“数字劳工”的劳动能力,提升其在数字平台与数字设备前操控的能动性,为其在劳动中的主体性地位提供重要保障[16]。其次,推动数据共享,确保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关系平等和谐。数据共享对数字经济时代劳动的价值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数据共享对提升劳动价值、构建和谐的数字经济时代劳动关系、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再次,明确数字经济时代劳动产品的价值归属,推动数据的公正分配。数字经济时代,庞大的数据库是社会财富的重要体现。然而数据生产的主体呈现出多元性,就导致其最终归属往往难以界定。数据生产的主体包括数据产出者和数据加工者,且最终有价值的数据大都是在原始数据的基础上加工而成,这就对资本利用数据生产的多元性侵害数据生产者的基本利益提供契机。保护数据生产者的应有权益,防止数据占有两极分化而导致贫富差距增大,维护数据生产者对其行为数据的支配权,彰显劳动正义。最后,推动数据算法程序贯彻正义原则,實现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自由。用算法分配的劳动呈现出“差别化待遇”,看似贴心地满足了“数字劳工”的个性化需求,但实则以实现商业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的。因此,推动算法程序贯彻正义原则,对数字用户进行“数字脱敏”,助力实现劳动自由。只有维护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正义,方能适应劳动发展的新变化,稳步推进以劳动贡献为主导的共同富裕社会的实现。
(三)机制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以共同富裕为总原则
将财富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新时代,建立财富积累机制应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以共同富裕为总原则。一是完善低收入群体的创收机制。当前我国居民财富结构,与中等财富净值人群占大多数、高财富净值人群与低财富净值人群占少数的橄榄型财富结构仍有较大差距,主要原因是中等财富净值人群偏少。因此,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路径。一方面,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形成科学的收入分配体系与完备的收入分配秩序规范体系。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曾经提倡初次分配讲效率,二次分配讲公平,似乎初次分配可以不讲公平;正是深刻认识到公平正义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因此,我们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更加关注公平,再到初次分配重效率再次分配重公平,再到初次分配也要重視公平[17];这都告诉我们,公平不仅是起点的公平和机会的公平,而且包括过程的公平和结果的公平,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调整收入的二次分配十分必要,但仅靠二次分配不可能逐步缩小贫富差距。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多次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解决好收入差距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18];“要建设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实现收入分配合理、社会公平正义、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9]。另一方面,要着力提高劳动者素质,建立由劳动者个人、用人单位与政府三方联合的劳动培训机制。要不断加强对劳动者的保护,站在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立场上,遏制资本无序扩张,严肃处理资本侵占劳动者工资,拖欠工资等行为,使劳动者获得与其劳动贡献相对应的报酬。二是规范高收入群体的调节机制。从财富的积累与持有双环节入手,通过税收来调节过高收入。要提高房产税、个人所得税等直接税的比重,降低消费税、增值税等消费税比重,适当对个税中综合所得扩大增收范围,使个税的分配调节效应充分发挥。着力引导高财富净值人群置身慈善事业,搭建互联网数字化公益平台,不断提高慈善事业的便利性。不断提升社会公益组织的责任意识与能力,加强对慈善活动与慈善组织的监管。三是规范财富代际传承机制。充分借鉴国际上有关遗产税与赠予税的施行经验,根据自身国情与经济环境制定合理的征税方案,发挥其在代际财富传承中的重要调节作用。
四、结语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同时,构建了有关劳动正义型社会实现的设想。为新时代共同富裕社会的构建提供了理论支撑。马克思批判资本正义并不是要消解正义,而是变更了资产阶级思想家探讨正义话题的地基,其对资本正义批判的过程蕴藏着劳动正义的话语逻辑。马克思的劳动正义观将现实和未来的双重指向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加以统合,实现了对其他正义理论的超越。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用好马克思劳动正义观这一科学理论武器,与西方式的正义话语开展斗争,确立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思想支点。
在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任何社会利益的分配从根本上看都决定于特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20]。因此,构建以劳动贡献为主导的共同富裕社会应该成为以“人民主体论”为立政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政策手段。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从根本上只能寄希望于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基础的初次分配的科学设计上,在深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底色”,厚植“生产性劳动”的“本色”,铸就“创造性劳动”的“亮色”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上落实人民主体地位的正道。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N].人民日报,2022-10-26(1).
[2] 亚里士多德全集:第8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105.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林志友.论马克思劳动正义思想的理论叙事[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6):108-119.
[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744.
[6] 罗凯笛,韩广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正义的批判及其当代价值[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5):112-118.
[7] 高巍翔,刘璐.“共同富裕社会”劳动正义的中国逻辑[J].社会主义研究,2022(2):9-16.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745.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
[10] 毛勒堂.论劳动正义及其对共同富裕的价值支撑[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26-34.
[11] 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J].求是,2021(20):4-8.
[12] 佟新.数字劳动:自由与牢笼[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22:2.
[13] 刘同舫.技术进步中的劳动正义困境及其现实效应[J].教学与研究,2021(12):68-76.
[14] 刘伟杰,王倩.论数字资本“剥削合理”幻象的生成与破解[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3(7):52-60.
[15]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22[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2:127-174.
[16] 閆坤如,李翌.数字劳动正义困境及其价值追寻[J].云南社会科学,2023(4):50-56.
[17] 李可愚.共同富裕也是基础性的教育等民生服务公益化、均等化[N].每日经济新闻,2022-03-09(2).
[18] 习近平.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J].求是,2019(10):4-16.
[19]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深刻认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重要性 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焕发新活力迈上新台阶[N].人民日报,2018-02-01(1).
[20] 陈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科学蕴涵、三重逻辑与实现路径[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8):5-12.
Building a Common Prosperity Society Led by Labor Contribution: Dilemmas and Paths
Chen Qian Lin Zixiao Zheng Boyun
(1,2.College of Marxism,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2;
3.College of Marxism,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601)
Abstract: Common prosperity is one of the fiv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 common prosperity society built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a common prosperity society dominated by labor contribution, and maintaining labor justice is the key to building a common prosperity society dominated by labor contrib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labor justice, the possession of means of production by workers is the practical foundation for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the justice of the labor process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and the fair distribution of labor results is a necessary provision for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However, building a society of common prosperity led by labor contribution faces multidimensional challenges such as ideological constraints under the logic of capital, obstacles to justice under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Guided by Marx's concept of labor justice and with a critical perspective, we aim to construct a consensus on the value of labor justice, promote the reshaping of labor justice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improve the mechanism for wealth accumulation, and focus on building a society of common prosperity led by labor contributions.
Key Words: Common prosperity; Labor contribution; Labor justice; Mar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