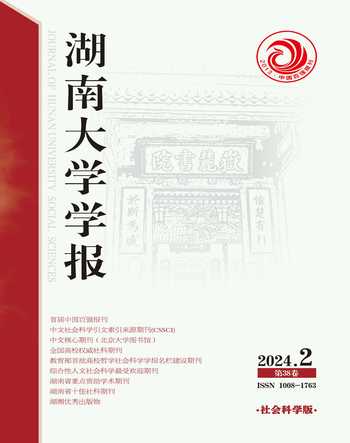《周易》与北宋治国理政思想
[加]贝淡宁,李贺亮
[摘要] 北宋士大夫为复兴三代之治,重建王道政治秩序,主张以经术治天下,重视经学的经世功能。在探索王道的过程中,士大夫以《周易》为经世之大法而推崇备至,并注重运用《周易》义理指导现实的政治实践。他们通过在奏议中引用《周易》经义议论时政,为朝廷提出合乎圣人之道的治国之策以实现儒家通经致用的理想。在北宋奏议中,士大夫不仅以《周易》经义培育皇帝的政治道德,而且还从《周易》中厘定出内政治理原则施用于今,从修己、治人两方面充分展现了易学的经世指向。他们以《周易》经义作为评判现实政治得失的标准,批评并制止不合经义的政治行为,规正政治发展方向,从而使《周易》对北宋治国理政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 《周易》;治国理政;《宋朝诸臣奏议》;士大夫
[中图分类号] B24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24)02-0031-09
Zhou Yi and Ideas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 Study Centered on Song Chao Zhu Chen Zou Yi
Daniel A Bell,LI Heliang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Qingdao266237, 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revive the ideal of Good Governance in Three Generations and to rebuild the political order of humane government, the literati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dvocated the rule of the world by the classics and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thoughts on the statecraft of the classics. In the process of exploring humane government, the literati regarded the Zhou Yi as a great method of governing the world, and paid attention to using the principles of the Zhou Yi as a guide to political practice. They discussed current politics by citing the Zhou Yi in their memorials and proposed governance strategies in lin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sages for the court to achieve the political ideals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In the memorials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literati not only cultivated the political morality of the emperor with the Zhou Yi; they also determined the principles of governance that were applied to the present, thus fully demonstrating the practical orientation of the Zhou Yi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self-cultivation and rule for the people. The literati employed the Zhou Yi as the standard for judging real political gains and losses, criticized and discontinued policies that did not conform to the Zhou Yi, and regulated the direction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Zhou Yi. Clearly, the Zhou Yi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political ideals informing governance of the country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Key words: Zhou Yi; governance; Song Chao Zhu Chen Zou Yi; literati
一引言
北宋是易學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出现了大量的易学名家与易学著述,朱彝尊《经义考》所载录的北宋易学著作就有近200种,为专经研究之最[1]34。易学之所以能够成为北宋经学中的显学,其首要因素乃是统治阶层治国安邦的政治需要。也就是说,北宋易学的发展与当时的政治建设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钱穆论北宋学术时曾说:“北宋学术,不外经术、政事两端……本经义推之政事,则仍北宋学术真源之所灌注也。”[2]5-7此即强调北宋经学注重经世致用,经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乃是“推之政事”。易学自然也不例外。北宋建立之后,统治方针由“武治”变为“文治”,强调“夫经术者,王化之本”[3]314,故士大夫以经治世的观念表现得尤为突出,并以推阐六经之“王道”为己任。六经之中,士大夫特重《周易》,认为“《春秋》《诗》《书》《礼》《乐》,犹五行之更用事,而《易》之为原”[4]1815,以《易》为其他五经之本源。北宋诸帝也甚为崇尚易学,常召易学者为其讲《易》,推言治道。如王昭素为太祖讲《乾》卦,“将人事、时势比附于经书”[5]198;李觉为太宗讲《泰》卦,“述天地感通、君臣相应之旨”[6]12821;冯元为真宗讲《泰》卦,称“君道至尊,臣道至卑,惟上下相与,则可以辅相天地,财成万化”[6]9821;仁宗朝讲《易》更盛,“讲官讲《易》多所发明”[7],亦附以时政。这都说明,北宋易学兴起之内在动因乃是士大夫追寻“外王”的需求。但由于宋初官方所推崇的儒学仍是以唐代《五经正义》为基础的汉唐注疏之学,“穷理不深而讲道不切,学者因其成文而师之”[8]355,宋初士大夫大多笃守古义,鲜有自立新说者,经学与政治实践之结合颇为困难。冯友兰就曾指出,《五经正义》的撰述者“并没有把儒家的经典和当时政治、社会、人生各方面的问题结合起来。他们并不准备这样做”[9]47-48。在宋初封闭保守的经学风气下,易学发展缓慢,总体上对汉唐之旧亦步亦趋,《周易》外王之道未能得到有效的探索。
易学在北宋得到繁荣发展且对政治产生重要影响的契机,乃是仁宗庆历之际的儒学复兴运动。北宋儒学复兴运动乃有激于佛道二教之昌盛,虽宋初儒学在传统注疏之学的束缚下发展缓慢,但超越于政治之外的佛道二教却在三教并行的政策下达到了鼎盛,于真仁之际呈现出“裨灶(佛老)方激扬,孔子甘寂默”[10]23的情景,儒者颇有“儒门失守”的危机感。仁宗时代的士林领袖、宋学的开创者范仲淹有鉴于此便发出“大道岂复兴,此弊何时抑”[10]23的呼声,倡导复兴儒家经世致用之学,重振伦常名教,其为学“泛通六经,尤长于《易》”[11]137。从游于范仲淹的“宋初三先生”孙复、石介、胡瑗更是极力弘扬儒家思想的正统与独尊,猛烈抨击“绝灭仁义,屏弃礼乐”的佛老之学,以三教并行、礼乐不兴为儒者之大辱,《易》与《春秋》是他们论证儒家“仁义礼乐”为治世之本的重要依据。在范仲淹、三先生、欧阳修、李觏等人的不断号召下,士人对汉唐以来“生民不见六经之用久矣,天下国家安治乎”[12]30的激愤感随之爆发,汇成巨流,终于在仁宗庆历时期掀起了大规模的儒学复兴运动以及以“回向三代”为目标的庆历改革运动。士大夫们纷纷怀抱经世之志,以重建天下秩序为理想,以六经之“王道”为改造政治社会的理论依据,指斥注疏之学泯灭圣人之道,倡导义理之学发明经书本旨,经世致用的新经学思潮由此兴起。新型士大夫以《周易》为“伏羲、文王、周公、孔子所以垂万世之大法”[4]245,将此书作为儒学复兴与政治改革的核心资源,在北宋掀起了研《易》熱潮,以《易》立言蔚然成风。诚如余敦康所言,三先生与李觏“此四人游于范仲淹门下,都把弘扬易学看做是配合新政、复兴儒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他们的这种共识,在宋代掀起了一个持久不衰的研究《周易》的高潮”[13]129。北宋儒学复兴虽有激于佛道二教之昌炽,但士大夫研经的使命与深层动力是推阐二帝三王之道以革新政治,“王安石上《万言书》,范仲淹上《十事疏》,以及二次的变法实验都足以证明,原本新儒学的兴起是以‘外王为主要目的的”[14]41-42。因此,北宋士大夫中只有极少数——主要是理学家,比较偏重运用《周易》阐发儒家的道德形而上学以对抗禅宗的思辨哲学,绝大多数所关注的仍是《周易》中的“治世之大法”,力图从中发掘经世济用之学为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提供理论上的指导。这种易学研究与政治实践相结合的普遍倾向,在北宋奏议中有着明显的体现。
南宋儒臣赵汝愚编纂的《宋朝诸臣奏议》汇集了北宋一朝颇为重要的名臣奏议,记载着当朝臣僚的经国之术、安邦之策,引经议政是北宋臣僚奏议写作的基本范式。粗略统计,《宋朝诸臣奏议》中引《易》立论的奏议数量于五经中仅次于专言政事的《尚书》,约117篇,引用频次已远超前代
以同样注重通经致用的东汉为例,根据学者翁丽雪对东汉臣僚奏疏和皇帝诏书中各经引用数量的统计,《周易》仅引用了十余次,是五经中引用最少的一部典籍。(参见翁丽雪:《东汉经学之政治致用论》,永和: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13,44,174.)。其在各朝的分布情况为:太祖朝0篇、太宗朝4篇、真宗朝6篇、仁宗朝28篇、英宗朝7篇、神宗朝37篇、哲宗朝23篇、徽宗朝6篇、钦宗朝6篇。由此可以看出,自仁宗朝士大夫掀起儒学复兴运动之后,《周易》经世之道得到了士大夫的有效探索并被广泛用于参政议政,从而在北宋形成了浓厚的引《易》议政之风,《周易》对北宋治国理政思想的影响亦由此得到体现。当前学界虽有不少学者关注到北宋易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但以往的研究通常侧重于考察儒者的易学著述来阐明易学对北宋士大夫政治思想的影响。
研究成果主要有余敦康:《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Tze-ki Hon, The Yijing and Chinese Politics:Classical Commentary and Literati Activism in the Northern Song Period, 960–1127,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5;姜海军:《宋代易学思想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刘炳良:《北宋易学与变法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姜海军:《程颐的易学诠释及其王道政治理念》,载张涛主编《周易文化研究》(第八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萧汉明:《濂溪易学与北宋中期的政治改革》,《中国哲学史》,1996年第3期;刘炳良:《范仲淹的易学与政治改革思想研究》,《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张毅:《欧阳修的〈易〉学与政治》,《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9期。此类论述主要是以主流易学家的易学著述作为研究材料,通过从解《易》文本中归纳儒者政治观点来揭露易学对北宋士大夫政治思想的影响以及北宋易学所表现出的政治性、社会性倾向。然就易学具体在哪些方面对北宋的治理思想产生了影响,却是易学家的专著所无法回答的问题,也是以往学者未能深入讨论的问题。对于《周易》在北宋政治活动中究竟扮演着何种指导角色,其文本又以何种方式来影响国家治理,却从中难以得知。钱穆就曾指出:“中国政治思想,随时于制度中具体实现。思想之表达,实际已不在文字著作,而在当代之法令,历朝之兴革,名臣之奏议。”[15]475相较于儒者的“传道”著述而言,奏议是在日常政治活动中产生的文本,它不是托诸空言的理论构想,而是切于时事的治道表达,奏中对《周易》的引用与诠释,正是统治阶层以《易》引导政治的直接体现。目前学界对此论者甚少,本文尝试以北宋奏议为切入点,探讨《周易》对北宋治国理政思想的影响。
二《周易》与北宋皇帝政治道德的涵育
北宋士大夫以“君心”为治国理政之本源。司马光说:“夫治乱安危存亡之本原皆在人君之心。”[16]21范祖禹说:“天下治乱,皆系于人君之心。”[16]46
士大夫们普遍认为“正君心”是通向三代之治的最优路径,故在治国理政中以培育德位相称的圣王为核心任务。君德的养成,当以正心修身为始,进而推之家国天下。《周易》经传则是北宋士大夫涵育君德的重要思想资源。
(一)正心修身
北宋士大夫以《易》规谏皇帝正心,主要是从政治层面强调“正本”的重要性。神宗即位之初急于求治,欲通过变法改革实现富国强兵,富弼、范纯仁、韩维、孙觉等大臣劝其求治不可太急,应“以知人安民为大方,以富国强兵为末务”[16]15。神宗不以为然,颇信王安石变法之说,并于熙宁二年二月推行了新法。士大夫们以王安石“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讲五霸富国强兵之术”[16]1190,担忧神宗误行霸道。在程颢看来,王霸道路的选择,归根结底还是君心正不正的问题。程颢引《易》上奏曰:
臣伏谓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者,尧、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义之偏者,霸者之事也……二者其道不同,则在审其初而已。《易》所谓“差若毫厘,缪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审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陛下躬尧、舜之资,处尧、舜之位,必以尧、舜之心自任,然后为能充其道。[16]17
程颢以“天理”和“私心”分辨王霸,以此作为三代与三代而下政治的区别。“审其初”“立其志”皆是针对君心而言,强调行尧舜之道须先有尧舜仁义之心。《易》文所谓的“毫厘”,对于人君而言,正是指君心的正与不正,仁与不仁,即主观动机的良善。程颢在《周易》的指引下,欲从根本处为神宗树立正确的治国观念。
神宗去世后,大臣们为防止年幼的哲宗效法神宗强行推行变法,亦十分重视对哲宗的“正本”教育。如元祐四年五月,经筵官范祖禹上奏曰:
欲治天下,先正其本,其本在于人君一心而已。天下治乱,出于君心,君心一正,则万事无不正……《易》曰:“正其本,万事理。差之毫厘,失之千里。”[16]32
范祖禹的治国观正是遵循的《周易》本正而万事理的思维逻辑。他以君主“正心”作为治国的逻辑起点,并将“天下治”视为“君心正”的必然结果。作为哲宗的老师,范祖禹借助《周易》经义教导哲宗以正心作为治天下之根本,表达了他对君德养成的殷殷期待。
除强调“正本”外,北宋士大夫还常以《周易》指导皇帝修身养性。如陈襄以“利贞者,性情”“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劝谏神宗以养心治性为本。[16]15-17范百禄以“君子以谨言语,节饮食”引导哲宗节欲修身,涵养德性。[16]50诸如此类,都体现了北宋士大夫十分看重《周易》在规谏皇帝正心修身方面的价值。
(二)爱亲正家
萨孟武说:“宋尚儒学,儒家由修身齐家,进至治国平天下……故宋儒汲汲于皇帝齐家之事。”[17]74鉴于唐代“闺门无法”而导致的政治混乱,北宋士大夫特重皇室家内伦序的建设,以《家人》卦作为治家的理论依据,强调“《周易·家人》之卦,乃圣人所以定天下之端本”[16]266。然而现实中皇帝常以私心背离圣人治家之道,这在士大夫看来是一种失德表现,《家人》便是他们规谏的武器。明道二年,仁宗欲废郭后,此在北宋实属首例,御史中丞孔道辅率谏官范仲淹、孙祖德等十人诣垂拱殿覆奏,疾呼“天下之母,不当轻废”。尽管孔、范二人因此被贬出京,但殿中侍御史段少连仍上疏抗议废后:
《易》曰:“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诗》云:“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若然,则君天下修化本者,必自内而刑外也……皇后母仪万方,非有大过而动摇,则风教陵迟……陛下举事为万世法,苟因掖庭争宠,遂行废后,则何以书史策而示子孙?[16]270
段少连以《家人》《诗经》二经义强化了废后一事的严重性,将其提升到国家治乱的层面。在他看来,圣人治天下莫不由正家而始,而正家的关键在于“夫夫妇妇”,即夫妇各自遵循“夫義妇听”的道德规范。段少连认为仁宗以“掖庭争宠”之小事而行“废后”之私,乃“夫不义”之举,若以此形象示天下,不仅榛塞教化,更难以为子孙树立为君的榜样,其弊甚大。富弼亦上奏就此事对仁宗进行了强烈的批评,痛斥其“治家而尚不以道,奈天下何”[16]271,言语间透露的正是《家人》的政治思维。尽管群臣最终未能谏止仁宗废后,但经此一事齐家治国之道已深入君臣之心。如庆历二年,左正言孙沔以仁宗在位近二十年天下未治,疑其治内有失,其上奏曰:
《易》以“风自火出”为家人之象,言号令之行乎外,由中正而明于内,非严风火之威,则难以正于家矣。《礼》云:“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治,国治而天下平。”王政之本,基乎此矣……今朝无专权之臣,上无失道之事,然而阴阳未和,灾变未息,法令不行,恩威不著者,岂治内之道有所未至欤?[16]275
孙沔此奏并未明指仁宗的过失,而是通过灌输《家人》与《大学》中的齐家治国之道令仁宗自行检讨过失。这显然是废后一事留下的“后遗症”,足见士大夫对齐家治国之道的笃定。
此外,《家人》还常被北宋士大夫用以指导皇帝教育子女。仁宗甚是宠爱兖国公主,对其逾越礼法、罔顾人伦的行为多行宽恕,吕诲、司马光、傅尧俞等人均有上奏规劝仁宗要严于治家。如嘉祐七年二月,司马光上奏言:
陛下曲徇公主之意,不复裁以礼法,使之无所畏惮,陷入于恶。触情任性,以邀君父;憎贱其夫,不执妇道。将何以刑四方之风,垂后世之则?《易》曰:“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此言家道尚严,不可专以恩治也……法者天下之公器,若屡违诏命,不遵规矩,虽天子之子,亦不可得而私。[16]324
《家人》九三强调家长治家宜严不宜宽,家教严格能树立家长的威严,家人虽嗃嗃有所抱怨,但能知礼守法,率循善道,故终得吉;反之则吝。司马光以此劝谏仁宗要承担起严父的责任,教导子女向善。他认为父爱之道应当“导之以德,约之以礼,择淑慎长年之人,使侍左右。朝夕教谕,纳诸善道”[16]323,而非纵容子女逾越礼法。况且,法为公器,皇帝怀私而不责亲乃有损“大公”之德。司马光重视正家,仅兖国公主事便上有多道奏疏,仁宗最终为之感悟,对公主施加了相应的惩戒。可以说,《家人》卦所谓的“正家而天下定”正是司马光坚守的政治信念。
(三)忧勤天下
修身、齐家对完善人君道德人格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然作为最高统治者,人君还需具备与其政治身份相匹配的道德素养,即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的仁德。《周易》中蕴含的忧患、勤勉等圣人品格正是北宋士大夫规谏君王的理论依据。
《乾》卦自强不息、奋发精进的精神颇受北宋士大夫的青睐,常作为激励人君励精图治的依据。如景德三年,陈充在《上真宗乞恭勤守治》中引用《乾·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来劝诫真宗“取法上天,勤而不息,是以政教克举,华夏以宁”[16]192。景德三年六月,天现祥瑞周伯星,张知白在《上真宗论周伯星现》中同样引用此语戒励真宗应“不恃太平之基而骄盈,不矜大宝之位而荒怠”[16]354-355。康定元年正月,天有日食,叶清臣在《上仁宗论日食》中则引用《乾》九三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强调“凡言‘无者,言本者咎;以能补过,故得无咎”,劝谏仁宗时刻兢兢业业,反省戒慎,避免因过得咎。[16]393-394
与《乾》不同,《坤》卦充满了对政治危机的警惕,尤其是初六爻辞“履霜坚冰至”被北宋士大夫频繁用以劝诫君主防微杜渐、居安思危。如庆历元年五月,知谏院张方平在《上仁宗乞都知押班奏荫一仍旧制》中引用此语劝仁宗防微杜渐,警惕宦官权大乱政,“都知、押班奏荫恩例,伏乞一仍旧制”[16]669。靖康元年四月,余应求也曾在《上钦宗论中人预军政之渐》中引此语强烈反对钦宗批准宦官王嗣昌预闻军政的请求,强调“自古中人预军政,未有不为患者”[16]705-706。
此外,由于《复》卦含有由悔得吉之意,士大夫也常以此强调悔过自新是人君扭转国家困境的重要品质。如熙宁二年十二月,李常上奏论青苗法,认为青苗法是敛财害民的王莽之政,使“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存,而起为盗贼,卒以败亡”,并援引《复》卦初九爻辞“不远复,无祗悔,元吉”劝谏神宗及时悔悟,尽早废除。[16]1203司马光在《上神宗应诏言朝政阙失》中说:
其上六曰:“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言迷而不复,凶且有灾,于君道尤不利也。[16]1278
司马光批评神宗“迷”于新法,渐失人心,将有“迷复凶”之象,并劝其“及今改之,犹可救也”。《复》卦此语的引用,不仅强调了神宗走上歧路的危险性,而且在其悔改时间上施加了压迫感。
除了以上所引,如《周易·系辞下》“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既济·象》“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艮·彖》“时止则止,时行则行”等,都是北宋士大夫用以劝谏君王忧勤天下的重要资源。这些论点正迎合了北宋士大夫对君德养成的要求。
所谓“究大《易》之指归,见上古之仁圣”[10]750,以《周易》经义作为培育皇帝政治道德的重要依据是北宋士大夫的共同选择。《系辞传》曰:“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崇德即是修己,广业即是治人,《周易》便是教导人君要以修己为本,以德化人。仁宗说:“风教,君德也。”[18]117对于德治主义的儒家而言,人君作为国家的道德典范及风教的核心,其政治道德的涵育正是治国理政中最关键的部分。
三《周易》与北宋内政治理的基本原则
《易经》本依卦爻变化而推演人事吉凶,经过《易传》的诠释而被赋予丰富的人文主义思想,儒家政治伦理学说也得到了阐发。北宋士大夫则从《周易》中提炼出了君臣共治、进贤黜佞、立储定本、节财利民等内政治理原则,将此视为圣人治国之常道而用以指导本朝政治。
(一)君臣共治
君臣共治是儒家理想的君臣关系,直至北宋,士大夫才有资格与地位追求共治。在《周易》中,《泰》卦象征的君臣交感、和谐共治的思想内涵,得到了北宋士大夫的普遍认可。司馬光说:“天尊地卑,道之常也。而《周易》乾下坤上谓之泰者,盖言人君降心以接臣,人臣竭忠以事君,然后上下交而其志同也。”[16]530在北宋奏议中,《泰》卦君臣交感思想常为士大夫郑重提出,作为劝导人君与臣共治的重要依据。如庆历七年,言事御史何郯向仁宗进献治国之道曰:
臣闻兴邦国之治,在通上下之情;通上下之情,在体天地之道。故天地交而万物生,由至和被焉;君臣交而众情达,缘至诚感焉。在《易》有之,上下相交而志同则为泰,盖人情亨通而至也;上下不交而志乖则为否,由物情乖阻而然也。斯道得失,系时兴亡。[16]116
《周易·序卦》曰:“泰者,通也。”“泰”有通畅无阻之意。在何郯看来,只有君臣交感,上下一心,天下才能实现太平,而君臣沟通的重要意义就在于疏通上下之情,防范小人谄上欺下。否则,众情壅塞,人心叛离,将有亡国之患。即如《否·彖》所谓的“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苏轼曾解释说:“夫无邦者,亡国之谓也。上下不交,则虽有朝廷君臣,而亡国之形已具矣。”[16]73可见,何郯欲以《易》告知仁宗,君臣交与不交决定着国家的治乱兴衰。
士大夫除以《泰》卦共治之道劝说皇帝注重疏通上下之情外,还常用以对抗皇帝的独裁专制。如元丰三年九月,文彦博判河南府,过阙入觐,便以《泰》卦戒励神宗不可独任自用。他说:
臣读汉史,晁错之策云:“五帝神圣,其臣莫能及,故自亲事。”臣谓错之言乖缪颇甚,因试论之。夫《易》之《乾》曰“天道也,君道也”,《坤》曰“地道也,臣道也”。天地既位,君臣之象著矣;君臣交济,邦家之治隆矣。而错乃云臣不及君,故自亲事,则古之圣帝明王,安用辅相而致治乎?……若后之人君谓错言为是,乃以一身一心、两耳两目独任自用,以周天下之万务,岂不殆哉?又将使厥后自圣,无复察迩言好问之裕。仲尼云“一言几于丧邦”者,谓人莫己若。[16]19
文彦博通过诠释《泰》卦的交济之道向神宗诉说了君臣共理国政的合理性,并以此驳斥晁错关于“五帝亲事”的乖谬言论。此处虽看似论史,但实则是以论史之机批评神宗才略自任、乾纲独断。在文彦博看来,寡头政治非古圣王治国之道,人君若骄亢自尊不延访群臣,执一己之是非为政,则有丧邦之危。富弼就曾当面批评神宗“内外之事,多出陛下亲批,恐喜怒任情,善恶无准,此乃致乱之道”[19]380。追求君臣共治是北宋士大夫以政治主体自居的表现,意在弱化君尊臣卑的位势,提升自身的话语权,对皇权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
(二)进贤黜佞
北宋士大夫喜于分辨君子小人,强调执政群体的道德纯洁性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公共责任意识。在先秦儒家著作中尽管不乏君子小人之论,但就如何在政治中处理君子小人的关系以达到和谐有序的状态,《周易》阐述得最清楚,故北宋士大夫借《易》劝导皇帝进贤黜佞甚为普遍。咸平元年,时有不逞之徒向真宗陈论闾阎猥亵之事,知虢州谢泌强调此皆小人误国,勿信其言。他以“小人勿用,必乱邦也”为据,向真宗阐述了“用小人则乱,用大贤则治”的道理,并劝其“倚老成之人”,远离“市井之徒、尘走之吏”[16]110。熙宁二年三月,时有言边事者,范纯仁亦以《师》卦此语戒励神宗勿信小人妄言,奏请“妄奏边事,及曾引惹生事之人,不得令在边任”[16]1537。熙宁五年,王岩叟上奏指斥新党为群邪,以《杂卦传》“亲寡,旅也”描述神宗“独立于群邪之中”的危险处境,劝其“得忠贤而用之,尧舜三代不难到”[16]1271。
当然,《周易》中最能揭露君子小人与治乱关系的还是《泰》《否》二卦,士大夫引用得也最为频繁。庆历三年,因谏官欧阳修、蔡襄,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人极谏夏竦奸邪,仁宗罢夏竦枢密使,而重用韩琦、范仲淹等人主持新政。夏竦贬至亳州,上万言书自辩。蔡襄恐仁宗去奸意志不坚,引《泰》《否》经义规谏道:
臣闻《易·泰》之《彖》辞曰:“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否》之《彖》辞曰:“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然则君子进则天下泰,小人进则天下否。陛下退一邪臣,进一贤人,而举国欢欣者,岂以一邪一贤独能关天下利害乎?盖以一邪退则其类退,一贤进则其类进。众邪并退而众贤并进,而天下不泰者,无有也。[16]112
《泰》卦所谓的“外小人”,就政治层面而论,则是指将小人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外”指的是地方或民间,是相对中央朝廷而言。而“内君子”则是指吸纳贤人充斥朝廷。由于君子小人如同阴阳一般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进此则彼消,故而人君欲成善政,必须坚定用贤之志,对奸邪不能抱有任何怜悯之情。蔡襄正是以道消之患警示仁宗坚定去奸之志,打消复用夏竦的想法。熙宁二年二月,昭文相富弼亦曾引用《泰》《否》二卦劝神宗亲贤臣远小人,并进一步强调:
凡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大抵诸圣以意象配君子小人,而分善恶至多,不可悉数也。《易》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也。”夫小人者,圣贤无不鄙而恶之,故《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夫天子无官爵,无职事,但能辨别君子小人而进退之,乃天子之职也。[16]136
为揭露小人的政治危害,富弼以《周易》整部经典的分量来突出圣人对君子小人之辨的重视,并认为人君执政之要正在于明辨君子小人,以进贤退不肖为己任。在富弼看来,神宗用人不贤,一味地相信王安石所提拔的儇慧少年,导致“今所进用,或是刻薄小才,害事坏风俗为甚”[19]381。富弼此奏旨在提醒神宗深明圣人作《易》用心,进用醇厚敦实之人,以贤能治国。
另外,《泰》《否》二卦阴阳共存,也让北宋士大夫意识到君子小人是一种永恒共存的关系。如许翰说:“考观《否》《泰》之象,则知君子小人未尝相无于天下。”[16]524所以,贤人君子当致力将小人逐出中央朝廷,而非灭绝小人。如元祐四年四月,起居舍人范祖禹向哲宗论及小人之害时说:
《易》内君子而外小人,其卦为《泰》;泰者,通而治也。内小人而外君子,其卦为《否》;否者,闭而乱也。天下治乱,未有不由君子小人。君子在位,必无恶政;小人在位,必无善政。圣人为天下,唯能使小人外而不内,在野不在位而已,非能使天下皆无小人也。[16]149
范祖禹通过《泰》《否》二卦认识到国家无论治乱君子小人都共存于世,决定治乱的关键因素是执政群体道德的优劣。所以他积极劝导哲宗效法圣人之治,致思于进君子退小人,而非着力灭绝小人。苏辙认为除了要将小人斥逐于外,还应对其略加安抚,以维持《泰》卦政治形态的稳定性。他在《上哲宗乞谨用左右近臣无杂邪正》中说:
昔圣人作《易》,内阳外阴,内君子外小人,则谓之泰;内阴外阳,内小人外君子,则谓之否。盖小人不可使在朝廷,自古而然矣。但当置之于外,每加安存,使无失其所,不至愤恨无聊,谋害君子,则《泰》卦之本意也。[16]151
在苏辙看来,小人能安存于外而不复谋害君子之心,便达到了《泰》卦的理想政治形态。因此,他希望朝廷对于在外的新党小人可以适当安抚,甚至可以善用有能力的小人“牧守四方,奔走庶事”,而不应该过度打压,使其在外惶惶不安,心生报复。他在《上哲宗乞谨用左右近臣无杂邪正》(系第二状)中便表达了此种担忧:
《泰》之为象,三阳在内,三阴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为,小人奠居于外,安而无怨,故圣人名之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时,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无失其所,则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势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则势将必至反复,故《泰》之九三则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16]152-153
九三因处于泰之极,已经使人产生了物极必反的警惕。君子若陵暴小人,以阳侵阴,则有失位之患。因此,苏辙认为维持《泰》卦和谐有序的政治结构,首先就需要掌权的君子不加剧冲突。然而,苏辙刚刚经历了自元祐四年五月以来旧党对在外新党人士发动的新一轮残酷打击,两党矛盾进一步激化。宰相吕大防等人为调停新旧两党旧怨,则建言引用新党人士。苏辙担忧新党小人得位之后伺机报复,便连上奏疏开陈《泰》道,指出两党矛盾激化的原因,反对吕大防的兼用邪正之策。垂帘听政的宣仁太后读苏辙此奏,认为其言极中理,采纳了他的建言。
此外,北宋士大夫还从《泰》《否》阴阳泾渭分明之象认识到党祸起于君子小人并居。如熙宁四年六月,监察御史里行刘挚在《上神宗乞谨好恶重任用》中评论当朝的保守派和新法派时说:
畏義者以并进为可耻,嗜利者以守道为无能。二势如此,士无归趋。臣谓此风不可浸长。东汉党锢、有唐朋党之事,盖始于斯。在《易》之象,以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为泰,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为否。[16]141
“异论相搅”是北宋王朝的御臣家法,意在使政见不同的官僚“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20]5169。神宗亦善用此道,同时任用政见相左的新旧大臣相互牵制。由于新旧两党政见无法调和,为使君主采纳自己的政治主张,就必须集结一批志同道合的臣僚攻击对方,这便形成了党争,而最终会酿成党锢。刘挚虽未明指新旧两党何党为小人,但此奏“言君子小人之分在义利,语侵荆公”[11]123,实则是抨击新党嗜利之人。
(三)立储定本
北宋皇帝大多孱弱多病,且子嗣多夭折,使得立储问题在北宋格外突出。北宋士大夫以立储为定国大计,认为“自古天下祸乱之始,未有不由继嗣不立”[16]306,并强调“立太子不以长幼,其缓者不过二三年,不然,则必有故”[16]310。《周易》“明两作,离”“主器者莫若长子”是士大夫劝君立储的重要理论依据。
北宋立储之议最为激烈的是在仁宗朝。先是仁宗早年突发重疾,因无子嗣,出于对赵宋社稷安危的考虑,听从大臣建言,暂择宗室子赵宗实养于宫中。数年后,皇子诞生,赵宗实被遣还。然仁宗数年所育三子接连夭折,直到四十多岁仍无继嗣。时太常博士张述开始深忧立储之事,上疏曰:
臣闻“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四方”。离为日,君象也。二明相继,故能久照。东升西没,一昼一夜,数之常也。陛下御天下将三纪,是日之正中也,而未闻以继照为虑,臣诚疑之。夫嗣不早定,则有一旦之忧,而贻万世之患。[16]288
张述认为《离》卦上下两日均是指君王,二君相继不断才能持续明明德于天下。在他看来,仁宗不思继照之意,不立储君,违背了圣人治国常道,将为国家埋下重大隐患。《离》卦九三曰:“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张述正是以仁宗年高,有日昃之凶,先后七上奏疏极力劝谏仁宗早择宗室子为嗣以安社稷。然仁宗坚信自己可再育皇子,无意另立旁支,并未采纳张述的谏言。
嘉祐元年正月初一,仁宗旧病突然复发,病情愈来愈重,以致精神失常,语无伦次。此次暴疾使朝野上下十分恐慌,大臣们纷纷上疏谋划立储之事。谏官范镇认为天下之事莫大于此,遂于五月率先上奏,劝仁宗仿真宗故事,取宗室之贤者养于宫中,“异时诞育皇嗣,复遣还邸”[16]289。范镇的建议虽未蒙采纳,却开立储之议的先声,接着司马光、庞籍、吴奎、赵抃、李大临、欧阳修、包拯等人纷纷呼应,掀起一场规模较大的群体性进谏。六月,殿中侍御史赵抃引《易》谏曰:
《易》曰:“大人以继明照四方。”叔孙通以谓:“天下之本,奈何以天下为戏!”韩愈亦曰:“前定可以守法,不前定则争且乱。”臣不胜大愿,愿陛下……择用宗室贤善子弟……一旦皇子庆诞少阳,位正储贰,事体何损权宜?[16]290
赵抃以《离》卦继照之理为据,警示仁宗不立太子将有乱国隐患。其建议与范镇相同,皆是权宜之策,并不妨碍仁宗将来诞育皇子再立储君。然仁宗坚持己意,不予采纳。不久,都城水灾泛滥,坏庐舍,溺人民。秘阁校理李大临便将此与立储联系了起来,他上奏说:
《汉书·五行志》曰:“简宗祀,不祷祠,则水不润下。”今朝廷祭祀非不恭,时享非不至,而反谓简慢者何?皇嗣未立,主鬯有阙故也。夫水,万物之本;太子,天下之本。今天下之根本未立,上天深示灾变。[16]293
《汉书·五行志》的灾异观对宋人有着深刻的影响,以简宗庙解释水灾并无异议。李大临认为仁宗本人在宗庙祭祀方面并无怠慢,然主掌宗庙祭祀的太子久阙实有不敬之意。他引《易》解释道:
《易》曰:“主器者长子。”又曰:“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四方。”是天子必有储副而天下获安。今储副未定,祭祀几废,故天之示变深切著明也。[16]293
“主鬯”出自《震》卦,与“主器”意同,均指主掌宗庙祭祀,引申为“太子”。《周易·序卦》明确指出太子主掌宗庙祭祀,《离》卦又强调太子不可缺位,那么仁宗在位三十多年不立储副,确实对宗庙大不敬。李大临有力地将水灾与立储之事建立起了联系,对颇信灾异之说的仁宗施加压力。七月,水灾未止,翰林学士欧阳修亦上奏论及立储之事,其论调与李大临同,亦以《周易·序卦》“主器者长子”作为立意根据,劝仁宗早定储副以消弭灾患。[16]413众所周知,欧阳修疑《序卦》非圣人作,但为了打动仁宗,他依然引用《序卦》进行劝说,说明《周易》在北宋政治文化中深具影响力。
嘉祐元年以来,“言者相继,范镇、司马光所言尤激切,其余不为外知者不可胜数也。包拯为御史中丞,又力言之,上未许”[20]4727,立储之议持续了六七年之久才最终落实。若纯粹以历史经验劝谏人主则难以对其造成压力,也使得臣僚进言缺乏可信的理论依据,《周易》中的经典明文便成为大臣进言劝说的理论武器。
(四)节财利民
自真宗朝起,北宋财政形势就发生了转变,财政穷匮的问题变得愈加突出。为改善国用不足,士大夫们普遍主张节流、恭俭,反对以增加赋税和官作商贾的方式弥补财政亏损。《周易》中的理财观点为士大夫确立理财方式提供了指引。
北宋国耗最大的是养兵开支,张载曾说:“养兵之费,在天下十居七八。”[21]358北宋实行募兵制,豢养了一支以流民、饥民为主的庞大军队,不仅战斗力低下,而且财政消耗巨大。北宋理财能臣张方平曾多次上奏强调冗兵之患,主张更革兵制,缩减财政开支。他向神宗上奏说:
臣在仁宗朝庆历中充三司使,嘉祐初再领邦计,尝为朝廷精言此事,累有奏议。所陈利害安危之理,究其本原,冗兵最为大患……今欲保大丰财,安民固本,当自中书、枢密院同心协力,修明真宗已前旧典。先由兵籍减省,以次举其为敝之大,若宗室之制,官人之法,诸生事造端非简便者裁而正之……《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又曰:“变而通之,以尽利。”《节》卦之辞曰:“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故伤财害民之事,当为制度以节之尔。[16]1097-1098
《周易》主张“穷则思变”,张方平将此视为人君治国的客观原则。他认为祖宗以来的兵制、宗室之制、官人之法等都已出现很大弊端,造成了财政的极大浪费,需要因时革新,劝神宗勿以修改祖宗旧典为讳。同时,《节》卦強调制度是节制滥用的最好方法,所谓“不伤财,不害民”正是儒家节用而爱人的政治关怀,这为张方平主张依靠革新制度理财的建议提供了理论支持。张方平的“节流”理财方法依托于儒家经典,神宗即位之初颇为支持。
王安石主政后,主张以“开源”作为解决国家财政困难的主要途径,同时兼顾“节流”的方法。但因与主流的“节流”意识相悖而遭到了士大夫们的责难。如司马光说:“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不加赋而国用足,不过设法以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22]1628王安石主张政府干预经济,主动创造财富,而儒家自孔孟以来往往反对政府管制经济,采取不与民争利的放任态度。[23]418-424在时人看来,王安石的“开源”策略正是违反儒家经济思想的“聚敛之术”。《周易》“以财聚人”“理财正辞”等圣人之言正面表达了儒家的理财观点,士大夫便以此作为抨击新法的有力武器。如熙宁三年三月,左正言李常上奏反对青苗法,强调以义理财:
《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繇伏羲以来,治天下者,未有不以仁守位,以财聚人,以义理财者也……知非义不可以理财,则租赋之入,敛散之方,失其宜,不可行矣。[16]1227
在李常看来,自古圣王治天下皆以财聚民、以义理财,而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乃是掊克民利的聚敛之法,与儒家王道政治背道而驰。他劝谏神宗要以民为本,青苗法于民不利应尽早废除。熙宁六年正月,枢密使文彦博又以“理财正辞”之说反对市易法。他说:
今乃官作贾区,公取牙利,《易》所谓“理财正辞”者,岂若是之琐屑乎?……凡衣冠之家罔利于市,缙绅清议众所不容。岂有堂堂大国,皇皇谋利,而不为物论所非者乎?斯乃龙断之事,孟轲耻之,臣亦耻之。[16]1272
所谓“龙断之事”,是指独占市场交易利润的行为。市易法虽名义上摧抑兼并保护贫民,实则“凡民之所利皆取而专之……而商贾不行矣”[24]74,官商成了最大的兼并者。文彦博抨击市易法“官作贾区,公取牙利”有违道义,破坏了儒家“理财正辞”的原则,并认为朝廷遣官监卖果实与民争利,有损大国体面,更是先贤所不齿之事,请求神宗废止。文彦博不只反对市易法,更反对朝廷的开源之术,他在《上神宗论青苗》中曾引用《节》卦“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劝神宗采用节制的理财方式。[16]1242由于古代生产技术水平低下,王安石的“开源”政策并不能在现有的基础上创造财富,而是依靠权力挤占富民商贾的利益,贫民亦深受其害。
总之,在北宋政治生活中,士大夫经常引《易》中的“上下交泰”“小人勿用”“二明继照”“理财正辞”等理论来指导政治实践,并通过对经义的新诠将《易》理转化为内政治理的客观原则。他们以之臧否政治,规正政治发展方向,辅佐人君通向王道政治,充分体现了通经致用的实践意义。
四结语
如众所知,引经议政由来已久,汉代便已形成风气。自汉武帝置五经博士,经学获得权威地位,“皇帝诏书,群臣奏议,莫不援引经义以为据依”[25]36。但汉代官方易学主象数,“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禨祥……《易》遂不切于民用”[26]1,引《易》多是用来推阴阳言灾异,而非议论人事。魏晋以降,玄学兴起,“学者不本经术,惟浮夸是务”[27]393,至隋唐五代,佛教流行,经学的发展陷入低谷[28]70。此一时期,儒学主体性不明显,易学更是趋向玄理化而与政治生活相脱节,引《易》议政呈衰落之势。故在北宋之前,实际上并未形成引《易》议政的风气,《周易》在治国理政中所发挥的作用相对有限。
北宋右文尊经,以为家法,儒学确立了在政治统治中的绝对地位。北宋士大夫为革除长期以来学政分离、王道不彰的弊病,提倡复兴先秦儒家经世致用之学,重树经学安定社会、治理天下的权威,在“圣人之道,传诸经学者,必以经为本”[29]580,“儒者得以经术进说于人主之前,言信则志行”[29]540的普遍认知下,引经议政之风再度兴起。就引《易》议政而言,与汉儒不同的是,北宋士大夫重在议论人事而非天道,他们力图从经世的角度重新诠释《周易》经义,并以此构建安邦定国、康世济民的政治理论体系来指导政治实践。在北宋奏议中,《周易》不仅是他们用以涵养君王政治道德的权威依据,亦是他们提炼内政治理原则的重要资源,其引用的频次、致用的广度都远胜以往任何时代。北宋重建天下秩序的政治需求引导了《周易》的诠释方向,《周易》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也塑造了北宋的治国理政思想,二者的交互影响与融会,不仅深化了儒学作为一种实践之学的内涵,也形成了颇具易学特色的北宋治理文化。然南宋以降,由于士大夫都将北宋的灭亡归咎于王安石及其变法思想,于是王学衰而理学兴,遂以谈心性者谓之真儒,讲事功者谓之杂霸,经世致用之学逐渐衰微。漆侠说:“宋学之所以在南宋逐步地衰落,宋学之所以蜕变为理学,也就在于经世致用之学与社会政治生活日益脱节,仅限于‘道德性命之类的空谈。”[30]注重人事的解《易》路径更是遭到了南宋理学家的批判,朱熹便批评程颐《易传》“以天下许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中,若作《易》看,即無意味”[31]1650,“将经来合他这道理,不是解《易》”[31]1653。此后的元明清时代,程朱理学成为官方统治思想,士大夫无论是尊崇程朱理学或陆王心学使经学朝向哲理化发展,还是回归汉代考据之学从事经典的整理与研究,“政治致用”都不再是他们研《易》的出发点,易学逐渐演化为一种探讨“性与天道”的学术思想。可以说,与其他时代相比,北宋是《周易》外王之道得到全面探索的时代,也是易学对治国理政思想影响最为深刻的时代。北宋士大夫引《易》议政,将《周易》经义转化为经世之大法,诚为儒者以《易》治国的典范,所追寻的正是孔子罕言“性与天道”的务实本色。
[参考文献]
[1]吴国武.经术与性理:北宋儒学转型考论[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
[2]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钱若水.宋太宗皇帝实录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4]曾枣庄.宋代序跋全编[M].济南:齐鲁书社,2015.
[5]冯晓庭.宋初经学发展述论[M].台北:万卷楼图书公司,2001.
[6]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7]金生杨.宋代君臣讲《易》考[J].周易研究,2004(6):32-39.
[8]苏辙.苏辙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0.
[9]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0]范仲淹.范仲淹全集[M].李勇先,王蓉貴,校点.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
[11]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2]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71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13]余敦康.汉宋易学解读[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14]欧崇敬.中国哲学史:宋元明清的新儒学与实学卷[M].台北:洪叶文化,2003.
[15]徐道隣.徐道隣法政文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
[16]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17]萨孟武.中国社会政治史:宋元明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18]范祖禹.帝学校释[M].陈晔,校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19]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校补[M].王瑞来,校补.北京:中华书局,1986.
[2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21]张载.张载集[M].章锡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8.
[22]毕沅.续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7.
[23]黄俊杰.中国文化新论·思想篇一:理想与现实[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
[24]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101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25]皮锡瑞.经学历史[M]//皮锡瑞全集: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2015.
[26]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7]朱彝尊.曝书亭集[M].上海:世界书局,1937.
[28]张宗友.《经义考》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9]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4.
[30]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J].文史哲,1995(1):3-26.
[31]黎靖德.朱子语类[M].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士大夫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