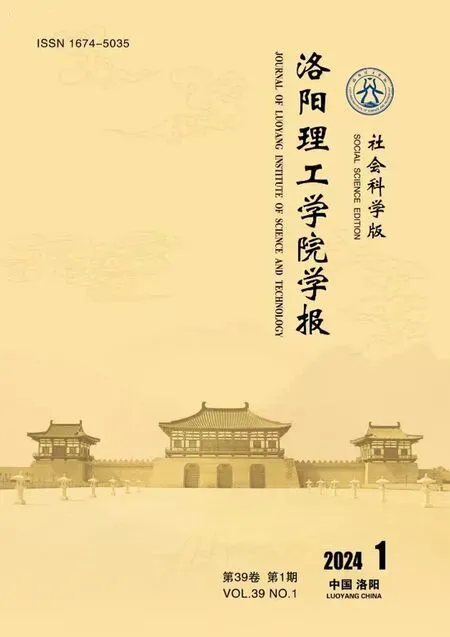论唐五代笔记小说中的韩愈形象
马 怡 茗
(北京语言大学 中华文化研究院,北京 100083)
韩愈是千古名儒,苏轼曾喻之“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1]509。唐五代笔记小说作为韩愈故事书写的起点,其对韩愈形象的塑造蕴含丰富的历史内容,应成为“韩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方面。韩愈认为“神仙虽然有传说,知者尽知其妄矣”[2]332,攘斥溺道求仙,但其被唐五代笔记小说涂抹仙道色彩,甚至被塑造为道教信徒。结合韩愈生平及其诗文中呈现的思想性格,分析唐五代笔记小说对韩愈原本形象的承袭与重塑,可知韩愈形象仙道化塑造有一定的历史依据和深层原因。
一、仙道化塑造的标志
依据向铁生、吴宇轩的统计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中的载录,唐五代笔记小说共有12部载写韩愈故事[3],有近半数对韩愈形象作了仙道化处理,主要见于柳宗元的《龙城录》、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张读的《宣室志》、皇甫枚的 《三水小牍》、杜光庭的《仙传拾遗》等。在这些笔记小说中,作者将神仙色彩涂抹于韩愈身上,行文充斥道教倾向,其对韩愈形象的仙道化塑造,以“能识丹篆”“死后从圣讨伐敌国”“牡丹现诗预知命运”为标志。
(一)能识丹篆
“梦吞丹篆”的故事,载于柳宗元的《龙城录》与张读的《宣城志》。柳宗元记云:“退之常说:少时梦人与《丹篆》一卷,令强吞之,旁一人抚掌而笑。觉后亦似胸中如物噎,经数日方无恙。尚犹记其上一两字,笔势非人间书也。”[4]142丹篆一词初见《隋书·潘徽传》,释义有二:其一,用朱砂书写的篆文,字形近先秦,在隋唐时作为文化遗产和书法艺术存在;其二,仙道之书或符箓,用墨汁或丹砂书写而成,是一种道教法术,可通神变化。柳宗元与韩愈为至交,文中“韩愈常说”,此梦应是韩愈亲传。韩愈好古文、能识古篆,所作《毛颖传》《瘗砚铭》皆以书法为主题,《科斗书后记》中说其向归登学识篆书。韩愈口中的“丹篆”当为第一种释义。韩愈“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2]250,喜爱古篆源自“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2]241的复古文艺取向,其常言少时梦或许暗示复儒使命,与道家旨趣相距甚远。柳宗元对老庄及道教兴趣浓厚,所叹“笔势非人间书”,流露仙道思想。此笔记虽属纪实,但激发了后世小说家的联想。
张读的《宣城志》将韩愈的“能识丹篆”从梦转化成现实故事,并与其治鳄故事相联系,体现写作者欲化幻为真的意图。书载泉州“南山有雷震暴”,而后“其山摧堕,石壁数百例殆尽,俱填其潭,潭水溢流,注满四野,蛟鳄之血,遍君玄黄,而石壁之上,有凿成文字一十九言”。文为科斗书,唯有河南令韩愈识之,曰:“诏赤黑,示之天公卑杀牛人,壬癸神书,急急!”[4]1026-1027除化梦为实外,张读还改写两个方面。其一,为丹篆的现世铺张宏大场面:石壁崩摧、水漫四野、降字一十九言。其中“玄黄”暗指道教中丹药的原料。其二,张读将韩愈治鳄原因改为神降使命,“似上帝责蛟鳄之词,令戮其害也”[4]1027。元和十四年(819),韩愈贬潮时作《鳄鱼文》曾正言受命于天子:“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2]822这些改写皆因张读热衷符箓传说,其《宣城志》记载李生以符箓驱鬼、契虚脱佛入道等多篇仙道神话。从柳宗元到张读,中晚唐笔记小说中“庶族趣味与道教的契合”[5]逐渐加深。
(二)死后从圣讨伐敌国
韩愈死因是学术界的谜题。争议的源头是韩愈攘斥佛老的态度和晚年“金丹别后知传得,乞取刀圭救病身”[6]525,“退之服流黄,一病讫不痊”[7]2273的疑似皈依道教的举动自相矛盾。硫黄是道教仙药,陶谷的《清异录》言韩愈晚年“硫磺末搅粥饭嚥”[8]144,这给了小说家想象空间。张读的《宣城志》始对韩愈之死加以改造。韩公晚年重病昼卧时,梦见一“长丈余,披甲仗剑,佩弧矢,仪状甚峻”的神人言奉帝命,诏其讨伐敌国:“威梓国绝域远夷,部落繁聚,世与韩氏为仇,而乃骋悖肆奸,觊觎中夏。”于是韩愈“遂起,力疾正冠,揖之”[4]1001,先以病虑,后果应之。韩愈醒来思之难解,不久离世。张读暗示韩愈之死是离开人世而随神征讨。成书稍晚的皇甫枚的《三水小牍》基本脱文自张读,但有改动。其一,改威梓国为睢邃骨棁国;其二,让神人自称“大圣”,突显其神通广大,且由派遣使者变成亲往前来;其三,改为韩愈自述梦境。皇甫枚写韩愈之死是“从其请”,明示韩愈飞升成仙。结合史实,韩愈想“讨伐敌国”,维护中央集权是毕生所求。他反复申明“四海九州,罔有内外,悉主悉臣”[2]681。韩愈死前并未转向道教,晚年仍痛斥佛道“倡释老于其间,鼓天下之众而从之。呜呼,其亦不仁甚矣!”[2]304服硫黄则被考证为“声色与疗疾之需”[9],并非“希慕长生之术”[10]13。小说家赋予韩愈的矛盾品格多源于小说家的复杂心理。自安史之乱后唐代边患不断,“夷狄无亲,见利则进,不知仁义,惟务侵盗,故强则寇掠,弱则卑伏,此其天性也。是以圣王以禽兽蚊纳待之,其至也则驱除之,其去也则严备之”[11]6528。这体现了“时人的畏惧之心与华夷隔阂”[12]。自知兴国无望的晚唐士大夫既幻想仙道,又心怀中兴,便让韩愈死后依托仙道力量担负兴国大任。
(三)牡丹现诗预知命运
在对韩愈仙道化塑造中,衍生一段以神仙方术为主题的故事,讲述其与一位精通道艺的晚辈亲戚的交往。故事首见于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书载韩愈之侄“有一艺”,可令牡丹于初冬开花。韩愈奇之,其侄便以阶前牡丹试之。一月后果然花开,且“色白红历绿,每朵有一联诗,字色紫分明,乃是韩出官时诗。一韵曰:‘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十四字,韩大惊异”[4]701。韩愈之侄能通灵植物使牡丹现诗,段成式以此展现道术的神奇。
五代杜光庭的《仙传拾遗》将“韩愈子侄”化为“韩愈外甥”,并串联韩愈被贬后的事迹,讲述其对道教的态度演进。起初,韩愈在长安见其外甥展现神通时,便“甚奇之,问其修道,则玄机清话,该博真理,神仙中事,无不详究”。元和十三年(818)年春,韩愈长安居所由其外甥种下的牡丹开花,每一叶花中皆书:“云横秦岭家何处①,雪拥蓝关马不前。”[13]1140-1143可见外甥已预知韩愈被贬岭南。元和十四年,韩愈贬潮途中遇外甥,“忽见是甥迎马首而立。拜起劳问,挟镫接辔,意甚殷勤。至翌日雪霁,送至邓州,乃白吏部曰:‘某师在此。不得远去。将入玄扈倚帝峰矣。’”韩愈惊异其言,询问其师。杜光庭的改造见于两方面。一方面,为法术增添先知性。《酉阳杂俎》中,牡丹现诗时韩愈已从潮州归来。《仙传拾遗》中,外甥种花时韩愈还未远贬;韩愈贬潮途中外甥已预知并提前等待。可见,从晚唐到五代笔记小说中,道家仙术的强度不断加深。另一方面,韩愈从道术旁观者逐渐成为诚心信服的道教信徒。韩愈在商山路上与外甥重逢时询问:“神仙可致乎?至道可求乎?”其后复见时,则“亦得其月华度世之道。而迹未显尔”[13]1142-1143。可见韩愈欲弃儒从道。长庆元年(821),韩愈《处州孔子庙碑》将孔子与社稷并列。结合贬潮事件与韩愈文章,便知其从未动摇儒家立场。《仙传拾遗》中韩愈的转变源自杜光庭的心理投射。从“牡丹现诗”故事流变中,可见仙道的影响不断加深,士人逐渐“远人世”。此外,韩愈的晚辈亲戚始自宋代刘斧的《青琐高议》被冠以韩愈侄孙“韩湘”之名,位列八仙。自此,“牡丹现诗”的仙道传奇逐渐演化成“韩湘子点化韩愈飞升”的经典故事。
二、仙道化塑造的历史依据
韩愈生前对道教并非一味排斥,有时表现得颇为暧昧。小说家虽沿袭韩愈的复古追求与“大一统”观念,却有意将韩愈由排道者变身为受度者。小说家对韩愈得道的描述虽富于想象,但有其缘由。
首先,韩愈与道中人有来往,并赞赏道士的仙风道骨。如《石鼎联句诗并序》是韩愈记载的一场道士轩辕弥明与校书郎侯喜、进士刘师服的诗作竞赛。轩辕弥明力压侯、刘二人,“其不用意而功益奇,不可附说,语皆侵刘、侯。喜益忌之。刘与侯皆已赋十余韵,弥明应之如响,皆颖脱含讥讽”。刘、侯落败,“尊师非世人也,某伏矣,愿为弟子,不敢更论诗”。次日,“天且明,道士起出门,若将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到门觅,无有也”[6]367-369。韩愈赞叹轩辕弥明有仙风道骨。杨朗认为,韩愈此文应受唐代笔记小说中道教故事的影响,“在那类故事中,主人公在夜晚与陌生人(多为道教之仙人或妖怪)相遇,共同赋诗尽兴,而天一亮陌生人即不见踪影,如唐传奇中《周秦行纪》《东阳夜怪录》《元无有》等篇”[14]。这让人联想《仙传拾遗》中韩愈外甥的告别,“与诗讫,挥涕而别,行入林谷,其速如飞”[13]1142。韩愈散文与道教文学的互文,体现其对于仙道故事的好奇。韩愈的《答道士寄树鸡》中“烦君自入华阳洞,直割乖龙左耳来”[6]391,描绘其与道士畅谈华阳洞故事的情境。王昕曾考证:“受道教神仙观念的影响,汉魏六朝很多地记所言洞窟脱离了现实中的地理地貌,成为宗教化的物质与文化空间。道教典籍之中各地遍布洞穴,是洞窟志怪的重要资源。”[15]可见,韩愈亲近道士、对道教神话具有浓厚兴趣。
其次,韩愈诗歌充斥道教元素。韩愈常悲慨时不我待、生命有限,其对长生与成仙抱有幻想,如《忽忽》中所言:“安得长翮大翼如云生我身,乘风振奋出六合,绝浮尘。死生哀乐两相弃,是非得失付闲人。”[6]22由于道教“具有的幻想性、神秘性和超越性与文学相通”[16],满足韩愈怪奇的文艺追求,其神话意象便涌入韩愈诗歌。《苦寒》中有颛顼、太昊、乌蟾、羲和、炎帝、祝融[6]12;《月蚀诗效玉川子作》中有虾蟆精、黄帝、赤龙、黑乌[6]324-325;《调张籍》中有仙官、六工[6]434,这些是道教谱系中的神怪。在言志主题的《杂诗》中可见“独携无言子,共升昆仑颠”“翩然下大荒,被发骑骐”[6]204等以道教意象寄托情志的诗句。马奔腾认为,“把诗歌作为吟咏性情的工具,把诗歌视为超越功利的途径,这便与道教美学有了契合点。在创作中,道教美学弥补了儒家美学灵性的不足,道教充满诗意的人生向往、瑰奇的想象和绚丽的意象为诗人提供了新颖而丰富的表达材料和艺术手段”[16]。在表达日常性情的诗歌文体中,大量道教元素的出现昭示韩愈的兴趣并不那么“纯儒”。
最后,韩愈祭拜神灵的举动给人以想象空间。韩愈任潮州、袁州刺史与京兆尹时,曾以多篇《祭神文》乞求神灵降福百姓。《祭湘君夫人文》等文中“夙夜怵惕,敢忘神之大庇”“俾民承事,万世不怠,惟神其鉴之”[2]459的表述十分卑微,以至被契嵩嘲讽:“韩子自谓比之圣贤,正直不徇邪,斥佛,何遽乞灵于妇人之鬼邪?”[17]322其实,韩愈祭拜的神灵并非道教神仙,而是传统地方神祇。如李阳冰在《缙云县城隍庙记》的记载:“城隍神,祀典无之,吴越有之,风俗水旱疾疫必祷焉。”[11]4461传统神祇与宗教神仙的混淆,或源于中晚唐时民间祠祀与佛道的合流现象。佛寺、道观因与民间神祠功能类似,逐渐“成为了祈祷与祭祀的场所。在面临人生困境或自然灾害时,人们也向它们祈求保佑”[18]。这使道观与民间神祠的界限逐渐模糊,如南唐升元六年(942)的《南唐太乙真人庙记》[19]1071。杜光庭认为韩愈在贬官后意询仙道。杜光庭在《录异记叙》中言:“怪力乱神,虽圣人不语,经谐史册,往往有之。前达作者《述异记》《博物志》《异闻集》皆其流也。”[20]856他眼中的圣人韩愈并非不信仙道,只是不语,但在其言语中流露端倪,如“有祷于神”“神享其衷,赐以吉卜”“蒙神之福”[2]458等卑辞,皆是韩愈真情流露。
韩愈虽常将“佛老”并提,但他对待二者并非一视同仁。对于佛教,他全然排斥,将其视为外来文化入侵,警惕“‘异端之法’泛滥对‘中国之法’将造成的重创”[21]。对于道教,韩愈将其一分为二看待。对于因追求成仙而抛弃伦理的百姓和因沉迷丹药而惨死的士大夫,他在《谢自然诗》《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等诗文中予以讥讽;对脱胎于传统的道教文化资源,以及富有才学的道士,他却流露亲近的态度。因而,小说家对韩愈形象的仙道化改造,具有一定的历史依据。
三、仙道化塑造的唐代社会文化背景与士人心理
韩愈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对仙道的好奇,但并未皈依道教。《送廖道士序》中韩愈鼓励隐居者入世,贬谪后所作《与孟尚书书》仍坚定儒学的入世立场。因此,探询小说家创作动因,不应停留在被塑造角色本身,而应发现深层次的唐代社会文化背景与士人自身心理的影响。向铁生认为:“笔记小说作为反映时代的一面镜子,社会环境和文化制度自然会在文本中留下深刻的烙印。”[3]
首先,国家宗教政策对文学作品具有宏观影响。统揽唐王朝的宗教政策,道教占据主导地位。“唐皇室在政治上推行了类国师制,以确保道教在李唐皇朝的国教——或类似于国教——地位”[22]。鲁迅说:“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23]18唐代笔记小说作者所处年代的道教政策有所不同。柳宗元活动于唐德宗、唐宪宗年间。唐德宗将《道德经》加入科举。元和八年(813),唐宪宗重修兴唐观。柳宗元有崇道趋向,其行文表达了对非人间世界的想象。《唐国史补》《隋唐嘉话》等笔记小说多记载历史琐闻。牛僧孺《玄怪录》虽载道家法术,但多志怪。张读、段成式生活在重道抑佛的唐文宗、唐武宗、唐宣宗时代。唐武宗登基时即敕老子生日为降圣节[24]398,又召赵归真修金箓道场[24]399、望仙台[24]410,颁布反佛诏令,拆佛寺、令僧尼还俗[24]412。张读、段成式的小说从柳宗元的佛道间摇摆过渡为明确的道教指向,并从现实记载走向浪漫想象。《博异志》《传奇》等以神怪宗教尤以道教法术为主题成书者大量涌现。唐文宗、唐武宗迷信符箓之力,亲修法箓。“符箓,是一个人修道臻于不同境界、身份进入了不同等级的凭证,也是道教徒随身佩带且不可须臾离弃的灵物”[22],这或许是张读《宣城志》把“能识丹篆”赋予韩愈的原因。杜光庭、皇甫枚活跃在唐僖宗年间。杜光庭曾被赐紫袍、充麟德殿文章应制,著有《历代崇道记》,使唐僖宗的兴道记载达到唐代最多。皇甫枚虽未入道门,但其宗教思想深受唐僖宗影响。二人在笔记中创造神幻情节,主题指向修仙访道。由此可见,统治者崇道政策对士大夫思想具有指引作用,笔记小说中仙道元素在中晚唐到五代呈上升趋势。
其次,道教的“凡俗化”和仙道小说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隋唐以来,道教常通过降低成仙门槛吸引信徒,号称凡人皆可位列仙班。詹石窗认为:“任何一种宗教试图扩大影响,总是要为世人开方便之门。……正如道士因为虔诚修炼而掌握了一定的‘道术’一样,其他各阶层的人物,作为道教的信徒,他们在传奇家的笔下大都也是身怀‘绝技’的角色。”[25]于是,信奉道教的小说家通过书写“凡人成仙”故事吸引信徒。韩愈的名望与地位能够为仙道宣传增添正统性,其便成为传道小说家观照的对象。“弃儒从道”的噱头,意在影响儒家思想。李白、李贺、白居易、李商隐等唐代名士,皆在笔记小说中被改造。
最后,小说家在韩愈仙道化的形象中折射其个人境遇,寄托梦想。唐五代笔记小说作者多出身士大夫阶层,其身份仍是儒士。韩愈身为儒学领袖,其人格为众多士子敬仰。安史之乱后唐代社会危机频显,社会动荡、统治昏庸,士人无力兴唐。小说家选择道教,并非厌弃儒学,而是因为儒学难以复兴,唯有在仙道世界中寄托梦想。因此,小说所描绘的道教仙道世界,是作为“士人理想的精神家园”出现的。如《抱朴子》所述,成仙后的世界近乎完美:“饮则玉醴金浆,食则翠芝朱英,居则瑶堂瑰室,行则逍遥太清”,甚至“位可以不求而自致。”[26]58文人乐道,是对无法实现的愿望的心理补偿。葛洪说:“仙人或升天,或住地,要于俱长生,去留各从其所好耳。”[26]58蒋艳萍认为这体现人们对生活状态自由选择权的需求[27]。幻想的实质是弥补现实中的缺憾,“玉露琼浆”对应末世中物质的匮乏,“逍遥太清”对应封建王朝自由的缺失,“将蒙我荣”对应壮志难酬。小说家对凡人成仙的描绘,多流露对世事的不平。杜光庭的《仙传拾遗》中,韩愈对用世绝望转向追求出世,反映作者凄苦心境。李商隐在《李长吉小传》中将李贺英年早逝塑造为绯衣人召其为天帝的白玉楼作记。文中“驾赤虬”“太古篆或霹雳石文”[28]2265的设定与韩愈死后从圣讨伐敌国故事相似。李商隐因卷入牛李党争而一生不得志,对李贺死亡的梦幻描写中深藏自身的不平。
士人无力兴国与求仙避世的矛盾心理,是小说家将韩愈形象转向仙道的深层原因。“唐末五代的社会状况相比于中晚唐时期更加动乱,士人命运更加坎坷,因此矛盾心理逐渐演变成了避世心理。(小说中)韩愈的内心已经从极力排斥道教变为产生了修仙的愿望”[3]。杜光庭亲见唐五代乱象,其为韩愈安排的修仙得道结局,“是士人们在黑暗动荡的唐末五代时期的末世悲哀感的艺术化呈现”[3],也是其排遣苦闷、寻求解脱的写照。梅新林把“仙”的诞生与先人对生命悲剧的抗争联系在一起,“神仙思想的产生实质上即是我国古代先哲在生命悲剧意识觉醒之后为消除生命毁灭感与不自由感而获得永恒与自由的一种不同于宗教的世俗式的独特解脱方式,因为神仙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超越生死与快乐自由”[29]18。韩愈在小说中由人间到仙道的转向,体现小说家对自由快乐的向往。这是中唐后释道兴盛而儒学衰微的原因。“儒、释、道三教在深度调和的过程中儒学地位下移,释、道思想渐趋成为主流话语。伴随社会政治和自身境遇的变化,中晚唐士人在头脑中不断调整儒学入世与佛、道出世的关系,并最终将佛禅、仙道作为超越自己、超越现实的精神工具”[30]。以韩愈为代表的士人形象转变的背后,是中晚唐五代“士人心理的嬗变”,士人避世而求得心灵安宁。道教中承载的“文化密码”仍具有虚伪的内核。马克思说:“宗教对一切已使人受害的弊端的补偿搬到天上,从而为这些弊端继续在地上进行辩护。”[31]218“道教承担了对现实世界进行心理补偿的特殊功能”[32],但难以掩饰其构建世界的虚幻。小说家笔下仙道化的韩愈与历史真实中的韩愈,体现理想与现实的反差,投射末世士人孤独彷徨的身影。
四、结 语
在古代小说史上,对韩愈的塑造经历从“历史的韩愈”到“小说的韩愈”的转变,而仙道化改造是极具影响的一环。卞良君将韩愈小说史中的故事分为中晚唐五代和宋明两个时期,并评价唐五代时期的韩愈故事为:“故事内容比较零碎,没有重点,发展取向不明朗,但为宋明富于仙道色彩的韩愈题材小说的创作做了重要的铺垫。”[33]唐五代文人笔记虽篇幅较短、主旨细碎,但其构写重点与发展取向是明晰的。在20余篇笔记中,小说家在构建韩愈忠君爱国、求才若渴等高尚人格的同时,实现韩愈从“坚定入世的儒学立场”到“弃儒从仙的道家信徒”的转变,并创设许多经典的仙道母题,为宋明时期的文学繁荣奠基。
注 释:
① “处”应为“在”.见王汝涛,赵炯,余润泽,等的《太平广记选》,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11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