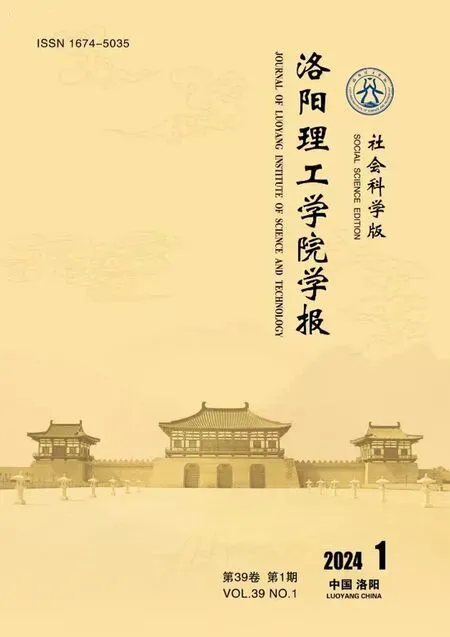关于梁实秋山东大学图书馆藏书问题公开信的考释
王 菲,金 星
(阜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1935年5月28日,北平《世界日报》的《学生生活》一栏刊出一则梁实秋发来的公开信,编辑题为《梁实秋先生来函》。此信系梁实秋对海伦《山大私生活》一文中部分观点的反驳和澄清,因此言辞中带有盛怒的情绪。在梁实秋文学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中,书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梁实秋一生钟爱写信。梁文蔷在《回忆爸爸梁实秋》中直言:“爸爸拿写信当家常便饭,认为是每日工作之一,是款舒情怀之方式,是与世界沟通之桥梁。”[1]121作为《梁实秋全集》失收佚信之一,此信对于梁实秋文学史料整理和生平思想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迄今为止,收入《梁实秋文集》(第9卷)书信卷的信有404封,应少于梁实秋实际写作的总量。因此,考释梁实秋这封公开信,既是对《梁实秋文集》书信卷的一次补充,也能为梁实秋生平研究贡献新材料。
一、《山大私生活》中的“涉梁”言论
《梁实秋先生来函》刊登于1935年5月28日《世界日报》第10版《学生生活》一栏,发信人为梁实秋本人,收信人为“本月24日贵报学生生活栏‘山大私生活’一文”作者海伦。海伦自1935年5月24日至5月29日连续6天在《世界日报》学生生活栏撰写题为《山大私生活》的文章,署名为“海伦寄自青岛”。在1935年5月24日,海伦的第一篇《山大私生活》文章中即涉及梁实秋在山东大学(下文简称山大)的工作与事务,并对其进行批评和指责。
为便于了解《梁实秋先生来函》一信的背景,现将海伦于1935年5月24日发表于《世界日报》学生生活栏《山大私生活》一文的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被遗弃在孤岛上的山东大学,三面环海一面靠山,在寂寥的年月里,不声不响的生长着,外面对于这个孤立在所谓“世外桃源”的学府便因而无从知道它的真像。固然有时也可以从报纸上教育栏内看到关于它的三两的报告,或者从教部视察员口中流露出它的一些消息,可是这些都不过是所谓“公生活”的记载,是表面文章,要想认识一个学校的真面目,想知道它的特殊的色彩,从这种记载里你是看不到的。只有把它的内在的私生活,用摄影师拍照“特写”的手法加以考察时,你方会清清楚楚地了解了一个学校的特殊的校色。下面便是我个人从山东大学的私生活里所拍照出来的几个“特写”的镜头。如果有人说他是“粉饰”或是“歪曲”了“铁一般的事实”的镜头。那我要预先申明,那也许是因为我的“开麦拉”所取的View Point与他趣乎不同,再不就是他另外又安上了有色镜头。
再说我的摄制手法是没有一定标准与次序的,只是眼前碰到了什么刺眼的景物便随手摄制下来,所以有的是“快意的”,有的也许是“不快意的”,好了,废话讲完了——开麦拉!
图书馆中的藏书
图书馆是一个大学的生命线,所以我开头就先说到它。山大图书馆的藏书实在不能算少,在梁实秋先生任馆长时,因了他个人的趣味,把所有的关于莎士比亚的书籍,各种各色的版本,上下古今的批评与注释尽可能的都买来,结果便成功了这种传说,说是在国内大小图书馆里所藏关于沙翁之书籍,以山大为首屈一指。沙翁的书确是不少了,可是关于现世纪人所著的书在这个图书馆里便寥若晨星。不但此也,梁先生还把一大批认为与青年思想有害的书籍检举出来列为禁书不准借阅。但是这儿却有一个奇特的例外,就是被称为“无产阶级的圣经”的The Capital不但未禁,且把它作为图书编目的例子,把书名,作者姓名等等一一清晰的工笔写出来,明目张胆的贴在图书馆墙上。这种矛盾的现象该怎样解释呢?“资本家学乖了要把XXX请进文庙里”,记得从前左派的人这样说过,可不知梁先生是否取意如此。[2]
此篇《山大私生活》全文1 000余字,涉及梁实秋的内容有300余字,主要批评梁实秋在山大图书馆的管理和藏书问题。其中涉及梁实秋的言论可归结为三点:一是莎士比亚相关书籍馆藏过多;二是现世纪人所著的书籍馆藏过少;三是列举禁书存在矛盾现象。虽然署名海伦的作者真实姓名难以考证,但是从这篇仅有千余字的文章能够看出其“别有用心”之处。一方面,海伦借助国民政府对左翼书籍的文网政策,大谈梁实秋购买禁书,大有坐实其“反动”之意。另一方面,海伦借助图书馆“藏书”在后续文章中引出“藏娇”的道德审判,有意借助传统儒家道德对山大教师私生活进行道德绑架。当然,海伦的文章除别有用心的言论外,也能反映当时山大学生的某种真实情绪。无论出于公心还是私心,应将海伦所反映的一些图书馆藏书问题视为历史中“不同声音”的补足。
二、《梁实秋先生来函》中的辩驳与澄清
1935年5月24日海伦文章见报之时,梁实秋在北京大学任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1930年代《世界日报》更是替代《晨报》成为“北京学界的热门报纸”[3]54。在北平执教的梁实秋看到海伦的文章后,顿生不平之气。他立即致信报社,对《山大私生活》一文中涉及自己的观点予以反驳和澄清。1935年5月28日,《世界日报》在第10版“学生生活”连载海伦的《山大私生活》一文时,特辟一个角落刊登《梁实秋先生来函》。书信内容如下:
编者先生:本月24日贵报学生生活栏“山大私生活”一文,有涉及鄙人而与事实不符之处,敬请更正为荷。
(一)“梁实秋……因了他个人的趣味,把所有关于莎士比亚的书籍……都买来。”山大有“莎士比亚”学科,三四年必修,购置参考书不能算是“个人趣味”。关于莎士比亚的书浩如烟海,山大所备不及万一,“所有的都买来”之语,未免幼稚。
(二)“现世纪人所做的书,寥若晨星”。这须有事实证明,山大图书馆有图书目录,现世纪人所著书是否“若晨星”不辨自明。山大购书向由各系教授及主任提出,图书馆长并无权抉择。
(三)“梁实秋先生还把一大批认为与青年思想有害的书籍检举出来列为禁书”。事实不是如此。我奉图书委员会之命,曾把“情书一束”之类及浅薄的三角恋小说之类约三十本从书架上取下来保留。一个大学的图书馆,在开办的第一年就先购置这种东西,我以为可耻。这种东西与“青年思想”毫无关系。我是主张思想自由的,所以马克思的资本论英文中文本都有,这怎么能算是“矛盾”?
山东大学曾经发生过风潮一次,我也在被攻击之列,我的罪状恰似上面我所辩证的那几点。我离山大已一年,不过问图书馆事已三年,竟还有人摭拾流言,横加污蔑。山大只有五年历史,我主持图书馆只有一年,成绩不必说,罪恶也不至于大的使图书馆遭到无可挽救的地步罢?
梁实秋五月二十四[4]
从结尾署名的日期“五月二十四日”可以看出,梁实秋在海伦文章刊发的当天就作了回信,这足以显示他的急切与愤怒。山大的风潮是1932年学生反对修改“学则”的运动。1932年4月4日,国立青岛大学①根据教育部指示,公布了修改后的《青岛大学学则》,其中“学生全学程有三种不及格或必修学程二种不及格者令其退学”[5]138一条,因触及学生的利益而遭到抵制。在当年期末考试来临之际,学生成立了自治会,试图抵制“学分淘汰制”的实施。1932年6月16日,他们向校方提出自己的要求,其中一项就是图书馆购书问题,认为学校只买“新月派”的书籍是某些教员的假公济私。在1932年抵制“学分淘汰制”的风潮中,新月派的闻一多、梁实秋成为众矢之的。由于闻一多支持校方决定,遭到学生们有针对性的攻击。山大学生发表《驱闻宣言》,直斥闻一多为“准法西斯蒂主义者”“不学无术”[6]378。由此可见,1932年山大学生提出的新月派书籍问题,是因为针对闻一多而迁怒图书馆馆长梁实秋。因为有风潮的往事,所以梁实秋在公开信中说“有人摭拾流言,横加污蔑”。
《梁实秋先生来函》针对海伦《山大私生活》提出的批评,逐一予以回应并反驳。第一,梁实秋否认山大图书馆购置莎士比亚书籍是因他个人趣味,且“所有的都买来”之语过于幼稚。1931年3月底,梁实秋出任图书馆馆长,开始管理图书馆事务,这与胡适倡导梁实秋等人翻译莎翁全集一事在时间上吻合,难免使人心生质疑。事实上,梁实秋最初凭一己之力从英国一家旧书店购置书目,“Shakespeare Society Transactions (莎士比亚学会论文集)我就弄到了一大堆,这是相当陈旧的印刷品,但内容极有价值”[7]。梁实秋最初翻译莎翁著作并未借助公职以便私利。梁实秋于1932年8月为山大三年级学生开设“莎士比亚”课程,分2年讲授,成为全国最早在大学课堂讲授莎士比亚著作的学者之一。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梁实秋提供了一定数量的莎士比亚图书。据 1932 年3月14日《图书馆增刊》专栏介绍,国立青岛大学藏有的莎士比亚图书包括“剑桥本”全集,共9册;Tudor本全集,共40册;牛津大学 Addis Wright 编17册;Gordon 编9册;New Hudson 编17册[8]。除莎士比亚原著,图书馆还增订相关期刊以拓展学生视野,“西洋定期刊物如英国之Contemporary Review,Fortnighty,Nineteenth Century,美国之Current History,Foreign Africa之外购整套杂志”[9]376。由此看来,梁实秋为莎士比亚课程准备了比较丰富的图书资料。
第二,梁实秋否认山大图书馆有关“现世纪人所著的书‘寥若晨星’”,并说明图书馆购书事宜非馆长一人决定,而是由图书委员会商定。宋春舫是山大图书馆的第一任主任(馆长),“任职期间,他为该馆先后购藏了万余册优质图书,除在国内搜集善本佳椠,还不惜花费大量外汇,直接从海外订购哲学、经济、文学名著,如德文版的马克思《资本论》,冯友兰的《新事论》,杨端六的《货币与银行》,余长河的《新经济》,以及巴金、老舍、钱钟书等作家的文学作品集,还有不少外文原版书,翻译书籍,以及几十种外文期刊等”[10]63。除新购书籍外,当时许多知名作家、学者曾向图书馆捐赠书籍。梁实秋、闻一多、皮品高、臧克家、王统照、老舍、沈从文等人的赠书中不乏有“现世纪人所著书籍”。相比山东地方志和莎士比亚两类藏书,山大图书馆“现世纪人所著书籍”的数量确实不及两者,但不至于“寥若晨星”。
在出任山大图书馆馆长后,梁实秋主持成立图书委员会,闻一多、杨振声、赵太侔等是委员。图书委员会曾多次开会讨论商定购书事宜,这在闻一多的日志中多有记载,摘录如下:
一九三一年
三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出席青岛大学图书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出席者还有梁实秋,赵太侔、汤腾汉﹑皮品高等。讨论内容有本学年购买图书经费及分配方法,决定购买图书需由本委员会审查决定后,方能进行。(据青岛大学《图书馆增刊》第2号,1931.5.11)[11]406
四月二十八日下午四时,出席青岛大学图书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查各系欲购图书书目。(据青岛大学《图书馆增刊》第2号,1931.5.11)[11]408
据图书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记录,决定购买教育学系、历史学系、中文学系、数学系相关书籍[12]。因此,确如梁实秋所说,山大图书馆购书事宜需图书委员会的各系老师共同商讨议定,图书馆馆长无权个人决定。
第三,梁实秋否认自己单独“列举禁书”的行为,说明自己保留左翼书籍的原因。在公开信中,梁实秋坦言自己是奉图书委员会之命,将“‘情书一束’之类及浅薄的三角恋小说之类约三十本”书籍取下保留。图书馆书架上仍有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原因是梁实秋主张思想自由。据梁实秋晚年撰写的《关于鲁迅》一文:“我曾经在一个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是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13]614由此可知,梁实秋从图书馆下架黄色刊物是事实。早在1928年,梁实秋强烈批判张竞生的“淫秽”书写,他在《时事新报·青光》上发表《取缔淫书》等文章,提出“号召肃清取缔淫书”的口号。可以看出,梁实秋对于“黄色书刊”秉持反对态度,山大图书馆里有此类书籍,他必“以为可耻”。据闻一多日志记载:“四月十四日下午四时,出席青岛大学图书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出席者还有杨振声、梁实秋、黄际遇(任初)、汤腾汉、赵太侔、皮品高。决议‘审查检出旧存无价值之书籍免于陈列’。(据青岛大学《图书馆增刊》第2号,1931.5.11)”[11]407由此推断,此次会议中审查出的“无价值之书籍”应为梁实秋所说“‘情书一束’及浅薄的三角恋小说之类”,也证实梁实秋是“奉图书委员会之命”,“令人取去注销”。
关于图书馆购买“禁书”的问题,梁实秋并不否认。实际上,宋春舫在任职馆长期间就购买过德文版的马克思《资本论》。这些书籍也是梁实秋早年求学时期的重点读物,他主张思想自由的观念与早期的读书经历不无关联。1931年,梁实秋发表《论思想统一》称:“思想这件东西,我以为是不能统一的,也是不必统一的”,“我们正该欢迎所有不同的思想都有令我们认识的机会”[14]429。基于此种观念,梁实秋在山大图书馆留有《资本论》并不像海伦所说是“矛盾的现象”。
最后,梁实秋在公开信的结尾提到与其相关的一次山大风潮,并说明自己在任职馆长期间的成就,其使用“摭拾流言,横加污蔑”等语表明他的愤慨。实际上,此次“殃及梁闻”的学潮对梁实秋在山东大学任教也产生了影响。学潮平息后,梁实秋辞去图书馆馆长和外国文学系主任职务,在杨振声的劝说下继续留在外国文学系任教。1934年10月,梁实秋辞职北上,其外国文学系主任一职由洪深接任,而此时的山大图书馆改由教务处领导。
三、梁实秋、海伦“纸上交锋”背后的新文学学科建设史
虽然梁实秋和海伦的纸上交锋仅有一文一信,但其反映了当时山大复杂的思想背景,师生的紧张关系从中可窥见一斑。《山大私生活》中涉梁言论和1932年学生抵制“学分淘汰制”风潮构成对话关系,而梁实秋也因为与闻一多同为“新月派”而遭到攻击。于是,不难理解山大学生为何针对图书馆提出问题。先是新月派书籍,后有莎士比亚全集,这些实是“指梁骂闻”之举。梁实秋、海伦二人的交锋以及1932年山大学生对图书馆购书问题的关注,为我们研究山东大学新文学学科建设史提供了宝贵资料。海伦针对梁实秋的言论主要聚焦梁实秋担任图书馆馆长时期的行为,是一种舆论造势。若据此认为梁实秋思想出了问题或者假公济私,则难免忽视其担任图书馆馆长背后的新文学学科建设问题。刘子凌认为,梁实秋担任山东大学图书馆馆长兼外国文学系主任一职是山大校长杨振声为谋求“中外文学的沟通”而有意为之[15]。因此,以梁实秋、海伦纸上交锋为切入点,可以更好地探究杨振声和梁实秋在山大新文学建设的策略问题。
首先,稳固白话文学的思想阵地。图书馆是大学新思想传播的重要阵地。梁实秋任馆长期间,大量购进晚清民国时期出版的中外文图书,广泛搜集民间藏书和古籍珍本,呈现沟通中西、融汇古今的倾向。1931年8月,山大图书馆实行开架借阅,即教职工可随时进入书库取阅书籍或固定座位号进行长期查阅。图书馆可同时容纳160余人,为在校师生提供了良好的读书环境。杨振声之所以聘请梁实秋这个富有中外学识和世界眼光的教学和管理人才,是为了让有新文学背景的梁实秋巩固图书馆的思想阵地,并与世界文学展开对话。在杨振声、梁实秋等人矢志不渝地规划和实践后,新文学得以在山大生根发芽。
其次,营造兼容并包的文化环境。杨振声将北大兼容并包的理念和清华重视文学教育的思路相结合。在此基础上,图书馆秉持“海纳百川”的观念,“包容”了马克思主义及左翼书籍。据梁实秋的学生郭根回忆,他曾在山大图书馆借阅柔石的《旧时代之死》、辛克莱的《密探》、日本江口涣的《恋爱与牢狱》等书[16]273。山大相对自由开放、宽容度较高的文化氛围为学生创造了更多的选择和机会,外国文学系学生组织成立刁斗文学社,创办《刁斗》季刊,梁实秋曾刊载文学理论和翻译类文章。由此,新文学以课堂和校内图书、刊物为载体更易进入学生的文化生活和知识结构,并获得他们的认同。在某种程度上,新文学的传播与兼容并包的文化环境形成相互作用的同构关系,但是兼容并包并不意味鱼龙混杂。在需要对学生思想产生不利的书籍进行下架时,梁实秋也能“奉图书委员会之命”,予以注销。此举无疑“损害”个别学生的阅读利益,遭到一些学生的反对,但其背后实际上和梁实秋所受的白璧德新人文主义重节制的思想影响有关。
最后,建构新文学的独立学科。杨振声沿袭清华大学的办学经验,聘请闻一多和梁实秋两位在国学和西洋文学皆深有造诣的新文学家分别担任中国文学系和外国文学系主任,在课程设置上要求两系学生互修课程,真正达到“中外文学系是一系”[17]的办学初衷。梁实秋是以教师和学者的身份在山大立足,他教授“小说入门”等课程,并竭力通过翻译向学生及广大受众引介莎士比亚戏剧等西方经典文学作品。参考书是教学的基础,虽然国立青岛大学成立之初办学经费紧张,但杨振声强调“基础的基础在图书”[18]187。1931年3月,杨振声聘任梁实秋为图书馆馆长,每年拨5万元用于购书,并支持梁实秋前往上海采购图书。一年后,山大图书馆的中外文图书已超6万册,包括古今中外的文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方面的图书。山大成为传播新文学的重要学府,为学生研究中国文学与社会人生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由此可见,杨振声、梁实秋二人将教学活动、图书馆建设与发展新文学联系到一起,并为之倾注满腔热忱,进行了一系列实践。山大逐渐形成重视新文学、新研究的文学学科传统,以及勇于探索和实践的文化风貌。
四、结 语
从图书馆馆长的任命,到中国文学系专业学习方案的制订,乃至课堂内外舆论方面的种种细节,反映了杨振声在国立青岛大学期间的新文学学科建设思路。此种建设思路既有“除旧布新”之意,也反映了杨振声融合图书管理、中国文学系设置、新文学专业学习方案等多元一体的新文学学科建设思路。梁实秋在任山大图书馆馆长期间,无疑成为杨振声新文学学科建设思路的践行者。由此可知,梁实秋、海伦的纸上交锋或许并非简单的舆论造势问题。分析梁实秋在公开信中所呈现的理念和态度,探究围绕梁实秋购书问题背后的新文学学科的建设策略,对于当下图书馆建设及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注 释:
① 山东大学前身是1901年创办的山东大学堂,从诞生起,先后经历了山东大学堂、国立青岛大学、国立山东大学等历史发展时期.1930~1932年是国立青岛大学时期.1932~1949年是国立山东大学时期.1932年,山东大学学生抵制“学分淘汰制”是处于国立青岛大学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