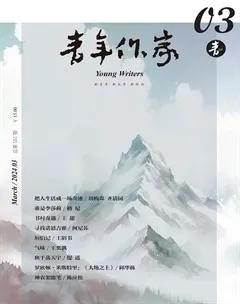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如何积攒写作经验?这是所有写作者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往前追溯三十年,互联网进入中国,自此,社会生活不断发生裂变,现状正处在一个裂变的过程中。同父辈们相比,变化是翻天覆地的,但也可以说,在媒介融合的作用下,当下的一切变得越来越日常化。个体及个体的情感需求不断突显,最终升级为一个社会命题,宏大主题不再成为文学追逐的首要目标,情感认同成为市场上的焦点。这些变化非常明显地映射在年轻作者们身上。
那么,在这个日常化的时代,写作经验是否唾手可得?答案不一定是肯定的。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曾提出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理论——拟剧理论。他认为,社会就是一个巨大的舞台,表演区域分为前台与后台,前台是可以让观众看到的表演场合,后台是演员准备与休息的地方,同时也具备掩饰和隐藏的效果。“当一个人的活动呈现在他人面前时,他会努力表现性地强调活动的某些方面,而活动的另外一些方面,即可能有损于他所要造成的印象的那些行动,则会被竭力抑制。”一个绝佳的表演者,一定拥有娴熟的印象管理能力,他会在前台不断强调必须凸显的事实,而在后台,才会暴露那些被掩盖的事实。同理,一个老练的作者,会巧妙地利用文字技巧,淡化不擅长的领域,掩盖不利于自己的事实,指引读者,顺着他的写作逻辑进入故事情节,找到角色的代入感,实现文字与情感的衔接,最终实现阅读的爽感。年轻的写作者,可能需要积攒足够多的阅历,包括生活阅历与阅读经验,才有可能练就这套熟练的技法,否则,极易让阅读经验丰富的读者发现其蹩脚的演技。
这三篇短篇,三位年轻的写作者,都在努力尝试讲述一个看似独特实则日常化的生活故事,并期望通过这些故事,展示他们对故事内容不同的诠释及对伦理关系异化的个体性理解。《气味》是一个男人精神出轨的故事。男主角婚后时常在酒吧饮酒,酒吧老板询问他原因,他以“烦,出来坐坐,图个清静”作答。他的妻子是一个安静且有志于成为作家的人,几乎不与丈夫吵架或发脾气,甚至连正常夫妻亲密,都是一种轻视的态度,所以男主角生出了一种想要撕裂生活的欲望,顺理成章,他在酒吧遇见了M,并幻想着与M发生了故事,事实上,包括连同M这个简称可能都是男主角的幻想。《路边的大树》则用类似悬疑故事的写法,刻畫了一个失去母亲的孩子。阿弥一直活在孤独中,母亲坟前大树成为了他的朋友。故事结尾接近魔幻,阿弥的身体被大树的根紧紧缠绕,融为一体。《隐》亦是描述了一个家庭故事,尽管也未逃脱家庭伦理,但因作者从她这个年龄阶段来切入故事,所以操作起来,显然得心应手。
作者如何去创作一个与本身生活无关的角色,并且让读者把角色与故事当真?同时,作者还要掩盖创作痕迹,让读者以为“这是个体对情景事实所做的没有自我意识的反应”,这是一个难题。戈夫曼认为虚假的表演分为两种,一种像话剧,不希望观众将演员本人与角色画上等号,只是希望观众欣赏其表演功力,观众也心知肚明,这就是一种煞费苦心的表演;另一种则似骗子,期望观众当真对待,观众也以为这就是表演者无目的的拼凑行为,是其无意识的产物。小说创作更似后者。
《气味》中的男主角,身陷婚姻的围城,却渴望着外界的激情与自由。他在酒吧中寻找心灵的慰藉,试图在酒精和幻想中摆脱生活的束缚。然而,这种逃避并没有给他带来真正的解脱,反而使他陷入了更深的迷茫和痛苦之中。他的妻子,虽然表面安静,但内心却充满了对丈夫的失望和无奈。这种看似平和实则冷漠的夫妻关系,正是现代社会中许多家庭的写照,让人不禁对婚姻的意义和价值产生思考。从写作技巧来看,作者设计的细节非常巧妙。首先,用M这个单词取代出轨对象的名字,既是一个不可说的名字,又似一个完全不存在的名字,一语双关。其次,文章里“气味”的变化,托起剧情的转折,结尾亦是落在“气味”上,“我想象着M那张又漠然又惶恐的脸,感觉一切都变得恍惚了起来。也就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嗅到了那股来源于我自身的气味,竟然如脓血般腥臭。”这种隐喻,直接刺激了读者的嗅觉,引导读者去联想剧情变化,十分有趣。
《路边的大树》中阿弥从小失去母亲,这本是一件悲事。父亲再娶,继母一开始对阿弥很好,“在没有孩子之前,她对阿弥一直很好,可以说疼爱有加。”随着继母怀孕、新生命的降临,阿弥成为家里多余的人,连父亲也不再爱他,悲上加悲。“从今往后都不会再有人庇护他了,他一声又一声地喊着娘,下意识地往后山看去,然而看到的只有一片黑暗,听到的只有猫头鹰阴沉又凄凉的‘呜呜叫声,得到的只有更狠重的打骂。”作者用“丢牛”这件事作为故事悲剧的引火绳,并选择用阿弥的好朋友阿克作为点燃这根引火绳的人,令故事的悲惨色调更加凄凉。这是一个好故事,但是细节处理得还不够饱满,少许转折处可以明显看到作者凿刻的痕迹。
与前两篇不同的是,《隐》中的“我”不是主角,而是一个第三人视角。“我和于薇是在高中认识的,我们一见如故。于薇提及最多的便是她妈妈。”“我”对于薇是抱着羡慕的心态,因为大部分少女的青春期,都会出现母女关系紧张的局面,“中学,无疑是青春期碰上老年期的战争时期,但从于薇口中叙述出来,却十分平静,甚至有点儿温馨。‘我最佩服我妈的就是她能拿住我。于薇说出这话时一脸自豪,仿佛是她拿捏住了她妈妈。”好景不长,幸福的一家三口被一场车祸撞碎,于薇的母亲因车祸离世,于薇被诊断为精神病,“我”非常震惊,渴望知道这一切发生的缘由,抽丝剥茧,终于找到所谓的答案,“说起来,她出事之前刚和我吵了一架。原因我忘了,总之,是些完全不必要的东西。”显然,这个答案并不太符合悬疑小说的结尾,但作为一个还在中学就读的作者,这样的结尾也是合乎常理。前面已经提到过,相较于前两篇,《隐》的作者虽然年龄最小,可是这篇小说中呈现的生活经验却是最饱满的,最大的原因是作者在讲述一个与她自身年龄相仿的故事,并未贪心,去涉及更大的领域——并不是说不能超越自己的生活阅历,而是要让读者感受到,作者在文学创作中的无意识,这恰恰是很多年轻作者们需要弥补的。
当然,也有可取的地方。三位年轻的作者都在勇敢打破常用的写作套路,重新架构故事入口,巧妙设计故事结局,很多细节都很出彩。《气味》跳脱了传统婚内出轨的俗套写作手法,而是把故事情节插入“我”的幻想里,而“我”的幻想恰恰隐喻了“我”受困于婚姻的无力感。这种无力感其实还可以进一步挖掘,是否存在窝囊感?窝囊感又从何处细节体现?这才是真正不幸婚姻带来的困境,所谓“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路边的大树》中的阿弥因为思念母亲,时常跑去母亲的坟墓处玩耍,意外遇到一棵大树,并与大树结下了深厚的情意,“对阿弥来说,这棵大树就是他的朋友,他什么话都对大树说,不仅对大树,还对大树上的虫儿、鸟儿、叶儿甚至是叶片上的一滴雨水说,说个不停,没完没了,自言自语,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不知道的还以为他真的疯了。”这一处细节描写得非常到位,失去母亲疼爱的阿弥把所有秘密都告诉了大树,旁人看他像一个疯子,却不知去怜悯一个孤独的少年。这些细节是否可以衔接得更加丝滑?抑或,如同波浪,呈现一个明显的故事高潮处?《隐》亦出现了一个冷漠的丈夫,妻子与女儿都在极力掩盖家庭中的不幸,只将美好的一面展现给外人,更多的是通过“我”这个第三人的视角去观察,“恕我冒昧,但是您经常和阿姨像今天中午那样,呃,冷战吗?”这些不幸与唏嘘都是通过“我”这个第三人去揭露,反倒更加体现出故事的悲凉性。
无意识的写作状态,是每一位作者都需要追求和锤炼的。它不仅仅关乎写作技巧,更关乎对生活、人性的深入理解和体验。在这三篇作品中,年轻作者们通过独特的视角和表达方式,呈现出了不同的生活经历和写作经验,虽然这些尝试可能还不够完善或深入,但依然带来了新的思考和感受。这种尝试和探索的精神是值得鼓励和肯定的。“存在着两种深沉扮演方式,一种是直接催生情感,另一种是间接利用受过训练的想象力。”尽管这句话是美国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用来观察空姐的情感劳动得出的结论,对于写作来说,同样适用。一个优秀的作者,应该像一个敏锐的观察者,时刻捕捉着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然后将这些碎片化的经验巧妙地融入自己的作品中,使得作品既具有生活的真实感,又带有作者独特的个人印记。这也是所有写作者的必修课。
【作者简介】李敏锐,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师,中山大学文学博士,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第二届签约文学评论家,发表学术论文若干,出版过多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杂文散见全国各大报刊。现居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