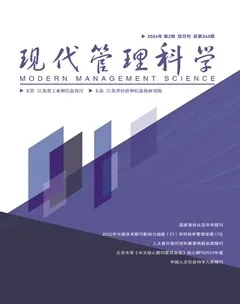数字基础设施政策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
[摘要]促进经济数字化转型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数字基础设施政策的实施效果直接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关技术方案的供给质量。为使数字基础设施政策更好地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采用文本分析和理论分析方法,通过探究数字基础设施政策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过程和理论机理,分析政策驱动过程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优化路径。实践逻辑层面,数字基础设施政策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经历了网络基础设施规模化推动局部端数字化、技术升级和融合发展推动平台数字化、要素市场配置畅通化推动生态系统数字化3个阶段。理论逻辑层面,数字基础设施政策通过解决技术投入市场失灵和要素配置市场失灵问题,激发企业数字化创新动能、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最后,基于政策投入与企业需求的演进逻辑,以及政策驱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加快数据共享机制建设、强化多层次平台支撑、推进政策均衡投入3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数字基础设施政策;企业数字化转型;理论逻辑;实践逻辑
一、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技术是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路径,决定了中国实体经济的效率和质量。当前,学者们就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创新提升以及分工优化等方面的作用已形成共识[1-3],但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并不充分。一是“内部性”因素,企业由于数字化投入的高成本、高风险性而不敢转型。二是“外部性”因素,数字技术易传播、易模仿的特性,会抑制企业数字创新和深化[4]。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市场力量推进存在失灵的情况,因此如何发挥政府作用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成为研究的重点议题。
2023年,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1明确提出,“要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两大基础体系”,“以数字化驱动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变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动力”。数字基础设施政策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基础设施先行”的引导作用。科学有序地规划数字基础设施政策有助于驱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改变传统工业生产底层架构,孕育新的生产要素与生产流程并不断优化资源配置,成为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实体经济竞争力、保障实体经济发展安全的关键力量与战略重点[5]。目前学界关于数字基础设施政策的概念界定并不明晰,王海等[6]指出数字基础设施政策关注于新兴技术与产业的培育,也强调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本文通过政策背景梳理和文本分析发现,数字基础设施政策是政府为支持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而设立的一系列刺激企业研发、提供税收优惠、推动人才引进、保障数字安全、畅通要素流通,支持数据共享等政策的合集。数字基础设施政策不仅可以指导区域数字基础设施升级路径,还具有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潜力。
已有学者就数字基础设施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效果展开了探讨。一类研究以“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为数字基础设施政策的代理变量,发现数字基础设施政策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所有制、企业规模和技术禀赋等方面的差异性[7]。另一类文献探讨了其中影响机制,提出企业经营情况、加剧市场竞争、带动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等为数字基础设施政策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机制[6]。总体而言,当前研究局限于从量化层面进行评估,对问题的系统性研究不足,缺少对政策的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的具体分析。本文边际贡献在于将数字基础设施政策作为制度供给端,以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需求端,搭建基于“需求-供给”的分析框架,从长周期对数字基础设施政策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进行系统分析。相关结论在丰富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的同时,也为理解政府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提供新的视角。
二、 数字基础设施政策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践逻辑
若要探索数字基础设施政策的演进特征,就要对数字基础设施政策同时进行量化和定性分析,文本分析可以同时做到这一点。本文参考王海等[6]的研究,首先通过确定与数字基础设施政策相关的关键词,在各省人民政府网站和北大法宝法律数据库中锁定包含关键词的政策文件,并手动剔除与数字基础设施政策无关的文件。然而,王海等[6]的研究仅对各省份数字基础设施政策数量进行了统计,并未从长周期维度探索政策的演变。本文基于对政策的手动梳理,发现1994年、2015年和2021年3个节点上,数字基础设施政策的顶层设计具有明显的阶段性调整。进一步,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方法,将1994年1至2023年间不同时间段的数字基础设施政策中的词频进行统计,按词频由高到低排列,形成统计云图(图1)。数字基础设施政策呈现以“网络基础设施规模化”“技术升级和融合发展”和“要素市场配置畅通化”为特征的3个阶段。在每个阶段中,数字基础设施政策着力于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的问题,分别通过提升企业数据要素可得性、升级数字技术并推动企业发展新业态、畅通要素市场化配置等方式突破企業数字化在不同阶段面临的约束。
1. 网络基础设施规模化与企业数字化探索期(1994—2014年)
(1)企业数字化探索期:局部端数字化
1994年左右,互联网概念被引入中国,并对企业的经营管理产生影响。20世纪90年代后期,互联网技术兴起,信息技术在推动企业提升效率、拓展经营市场中的作用得到重视,企业进入数字化转型探索期。由于企业数字技术基础薄弱,从投资回报的角度考虑,数字技术自主研发投入高、回报周期长、不确定性较高,转型风险大,不适合大多数企业投资,因此企业通常将基础数字技术与公司业务嫁接,在不同端尝试数字化,这一阶段的关键是数据要素的积累。企业通过引进服务商的资源管理系统,完成数字资产的原始积累,不断培育数字化能力,改进生产、管理等环节的效率,降低运营成本[8]。然而,企业销售系统、财务系统、客户系统、资源管理系统间各自独立,信息不能共享,企业仅能通过技术引进完成局部端数字化。
这一阶段,企业能否跨越这一阶段主要的障碍在于能否顺利引进外部技术。成功引进外部技术的企业能在内部形成数据资产,提高运营效益,完成局部端的数字化转型。然而,在数字化转型的早期阶段,数字基础设施的区域间发展差异较大,还未具有规模化的特征,导致部分地区的企业无法顺利完成技术引进。企业能够跨域数字化转型探索期的政策着力点在于数字技术可得性问题的解决。
(2)网络基础设施规模化推动局部端数字化
自1994年中国引进国际互联网开始,各级政府着手推进骨干网、宽带、光纤等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数字基础设施政策也随之开始顶层设计。这一阶段,数字基础设施政策中“建设”“网络”“信息化”等关键词出现频率较高,呈现“网络基础设施规模化”的政策特征,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完成从0到1的转变提供了技术基础(图1a)。2000年中国邮电部发起企业上网工程,推动企业在中国电信各级电子商务平台上建立主站点,以实现上网企业的经营管理环节广泛应用电子商务。2006—2013年,《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1和《“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的通知》2等文件,進一步提出以宽带基础设施和3G移动通信网络的技术路线及其规模化建设作为主要任务。具体而言,政府通过投融资政策、招投标政策、产业目录设定、频谱分配等政策工具积极干预宽带基础设施和3G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建设,扩大了网络基础设施的应用率和普及率,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在市场主体间的流通速度大大加快,提高了数据要素的可得性,企业引进数字化服务的可能性大大提升,推动企业跨越数字化转型的探索期。随着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化的推进,历年《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3显示,2006年以来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使用企业资源规划(ERP)、人力资源管理(HRM)、客户关系管理(CRM)、企业管理解决方(SAP)等各类数字化管理系统的企业数占比逐年提升,反映出数字化管理系统在企业内得到广泛的应用。
2. 技术升级和融合发展与企业数字化拓展期(2015—2020年)
(1)企业数字化拓展期:平台数字化
“数字化转型”的概念在2015年开始被频繁提及,该概念被认为是企业信息化的升级版。信息化阶段伴随大量数据要素的不断积累,企业开始分配所握有的在不同端的各类数据资产,因此,这一阶段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注点在于如何将不同环节的数据资产联系起来,发挥最大效益,企业进入向数字化平台发展的拓展期[9]。数字化平台能够促进不同环节和不同主体之间的交流,将研发、生产、管理、流通等环节以及生产商、竞争者、消费者、供应商等主体链接起来,为企业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的对接更加顺畅提供有利条件,通过对平台各环节数据的交换和收集、管理与分析,在更大范围内降低沟通成本和协调成本。平台的形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一是中介型平台,链接顾客和厂商两端的平台企业;二是企业内部培育的平台,既包括为提升企业内部有效运转和组织效率而搭建的内部数据共享平台,也包括企业自主研发的用于对外链接行业资源,打造链群式发展的平台。
实现平台数字化转型的主要阻力在于部门之间的壁垒。要实现跨部门的协调与沟通,对数字技术的连接能力和计算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平台化发展要求在各种应用场景终端下的海量数据均能接入网络中;另一方面,平台产生的实时交易、现场直播等场景要求数据传输速度和质量快速提升。企业平台化转型对数字基础设施的连接能力和计算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数字基础设施技术壁垒的突破成为企业向数字化平台转型的关键。
(2)技术升级和融合发展推动平台数字化
2015年被认为是“互联网+”发展元年,数字基础设施政策开始强调技术赋能和新业态的培育。这一阶段,数字基础设施政策中“互联网应用”“数据”“平台”“融合创新”“技术升级”等关键词出现频率较高,呈现“技术升级和融合发展”的特征,强化数字基础设施的计算能力和连接能力,为企业数字化管理、智能化生产、个性化定制等新模式、新业态提供更优化的技术条件(图1b)。一方面,数字基础设施政策推动网络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促使以新模式、新业态为特征的数字化平台转型逐渐浮现。2015年,《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1和《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2中要求“到2025年‘互联网+新经济形态初步形成,‘互联网+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随后发布的《关于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3等文件均在统筹规划创新服务平台的建设,支持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础的融合基础设施建设,为传统企业参与平台数字化建设中提供了技术条件和政策支持。另一方面,数字基础设施政策着力优化数字技术水平,为平台数字化的发展提供有利技术条件。2015年至2020年发布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4和《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规模部署行动计划》5提出,推动5G技术降低延时和IPv6技术标准连接海量端口,围绕数字基础设施现有计算能力和连接能力进行突破,从技术层面助推企业向平台数字化方向转型。
3. 要素市场配置畅通化与企业数字化整合期(2021年至今)
(1)企业数字化整合期:生态系统数字化
数字经济时代,由于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和融合性的特征,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技术创新是由多边合作网络中的企业共同参与而实现的[10]。随着企业数字化程度深化,已有数据发挥的作用呈现边际递减效益。企业自发组成数字化生态系统,进入数字化转型整合期,持续获取数据红利。生态系统数字化是指通过数字技术手段产业龙头企业与伙伴企业共享信息和资源,共同创造价值,分享利润,提高生态系统竞争能力的过程[11]。生态系统数字化与前两个阶段相比对组织整体提出更高的要求,整合期建造生态系统需要在平台之上,通过链接多个平台及价值环上的多个主体,实现平台间资源的共创共建和增值共享[9]。依托产业链、供应链环节的多边数字生态系统能使生态系统中的企业共享其他成员的技术创新资源和成果转化渠道,降低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和技术迭代的不确定风险。
这一阶段最大的阻力在于如何形成开放合作的环境和达成企业间的战略共识。数字生态系统的形成的前提是要素自由流通且具有活力的市场环境,有利于不同类型企业的相互融合。此外,生态系统中企业的共识的达成需要对资源开放共享的规则进行制定。然而,大多数生态系统中的企业并不愿意分享自己的信息、资源和数据,因此在数据共享方面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进而,数字基础设施相关政策围绕数据标准制定而展开。
(2)要素市场配置畅通化推动生态系统数字化
2021年开始,国务院发布的《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6强调数字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清除体制机制障碍,以推进数字化环境建设为导向,数字基础设施政策进入新阶段。这一阶段,通过词频统计分析发现,“服务体系”“数字应用”“数据安全”等关键词出现频率较高,政策呈现“要素市场配置畅通化”的发展阶段(图1c)。《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7提出“通过推动数字基础设施高效联通,有效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新型数据中心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8提出,“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等基础制度,推动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建立大数据产业标准体系,加快建立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等公共机构的数据标准体系”。数据开放共享的市场环境不仅有利于企业间数据共享,還在于政府和事业单位等公共机构数据标准的制定能够形成示范效应,有助于推动数字化生态系统的建设。这一阶段的数字基础设施政策专注于优化服务体系,畅通要素流通机制,尤其是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的强化。相关政策内容包括数据要素确权、数据共享机制建设、数据开放标准制定等方面,为数字化生态系统的培育提供良好的制度条件。
数字基础设施政策在各阶段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践逻辑如图2所示。
三、 数字基础设施政策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理论逻辑
数字基础设施政策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理论逻辑以市场失灵为线索,解决企业在数字化不同阶段面临的市场失灵问题。企业数字化转型早期面临数字技术投入市场失灵的问题,而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深化,企业主要面临要素配置市场失灵的问题。数字基础设施政策通过加大“硬基建”投入解决企业数字资源可得性问题,激发企业数字化创新动能,推动企业完成早期数字化转型。随着技术引进获利空间的缩小,数字基础设施政策由选择性向功能性产业政策转变,通过畅通数据要素和数字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清除体制机制障碍、深化企业数字化转型。数字基础设施政策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机制如图3所示。
1. 数字基础设施政策激发企业数字化创新动能
从实践逻辑看,中国数字基础设施政策取向始终发挥了“基础设施先行”的引导作用。政府制定产业政策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的合理性在于市场的不完善,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发挥主观能动性有助于克服市场失灵引致的效率损失[12-13]。数字基础设施政策解决企业数字化转型在不同阶段面临的“市场失灵”情况,早期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技术投入“市场失灵”的困境。
由于数字技术投入的高成本性和正外部性,早期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面临的是主观能动性不足的问题[4]。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生产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的数字基础设施,企业数字化商业模式的运营质量也与当地信息网络普及程度息息相关[14],数字基础设施等“硬设施”是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顺利开展的关键。数字基础设施政策推进如5G、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中心等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得企业明确数字技术发展的总体方向,降低企业对外部技术不确定性的预期。企业通过技术引进,能够降低数字技术创新风险,提高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成功率。相较于以自我积累为基础的自主创新,以技术引进为基础的技术自主创新多是在消化吸收引进技术基础上对已有技术进行较大的改进,耗时更短,成本更低,所面临的市场风险更低[15],更适合早期数字化转型企业。信息资源理论提出,在信息资源可获取的情况下,企业创新路径可以归纳为“引进—吸收—积累—模仿—自主创新”,数字基础设施政策使得企业能够在较短时间以较低成本进行数字化创新和转型[16]。
数字基础设施政策能够提高企业数字技术资源的可获得性,激发市场主体通过构建数字创新能力,不断深化企业数字化水平。一方面,部分地区实施数字基础设施政策后,能够提高该区域的数字技术可得性,企业获得更多与数字技术相关的创新机会,激发企业数字化创新能力。企业创新能力既与企业自身能力相关,也与企业对外部信息的整合能力相关[17]。数字基础设施政策使得部分地区的企业能够享受数字技术和数字化平台带来的便利,有助于企业发现数字技术创新的机会[18]。另一方面,数字基础设施政策通过推进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打破信息传播的时空约束,促进企业与其他市场主体进行的沟通交流并形成协同创新“合力”,培育企业数字化创新动能[19]。
2. 数字基础设施政策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
中国产业政策历经了3个阶段的演进:第一阶段是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时期的产业政策实践;第二阶段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时期的产业政策实践;第三阶段是新常态、新阶段下的产业政策实践。在不同发展阶段,产业政策实践呈现较为明显的差异性。第一阶段主要实施选择性的产业政策,集中力量进行主导产业的培育和扶持,带动产业结构快速升级。第二阶段同样以选择性产业政策为主,但开始注重市场功能的发挥、完善和强化,同时也越发重视促进技术创新等产业政策的作用。第三阶段面临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技术引进与模仿空间大幅缩小,产业政策实践由选择性向功能性产业政策转变,形成以产业技术和组织政策为主导的功能性产业政策[20]。数字基础设施政策作为一种产业政策,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后期由“硬基建”投入转变为与企业数字能力培育、数字人才引进、数据要素流通等相关的“软制度”的制定与实施,通过畅通数据要素和数字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推动企业数字化水平的深化。
伴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深化,单体化发展已不足以支撑企业获得更多的新知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深化需要良性的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以此实现可持续的竞争优势[21]。数字化生态系统由政府部门、大型科技企业、公众等多方主体驱动[22],不同主体间通过技术交换、知识转移和信息共享,实现互利共生、合作共赢的发展模式。但是,多数市场主体面临资源信息共享机制不完善的问题,导致数据要素的自由配置出现“市场失灵”。要素市场发展滞后不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利于创新,不能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其负面影响会作用于产品市场,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持续性[23]。数字生态网络中政府扮演着权威主体的角色,政府的数字化相关行为会引发模仿和示范效应。政府在数据确权、共享机制构建和开放标准制定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和有益实践会号召市场主体共同参与相关实践,并且研究表明政府政策的示范效应对相邻区域具有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24]。数字基础设施政策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化、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提供有利的制度保障。
数字基础设施政策畅通政策实行区域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同时,数字基础设施政策通过加强区域内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提高地区市场竞爭程度、深化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一方面,数字基础设施政策具有区位导向性,实施政策的某一地区产业发展会促进企业数量的扩张,进而加剧市场竞争。市场竞争加剧挤压企业获利空间[25],倒逼企业推进数字化生产与服务的变革,增强企业数字化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26]。另一方面,市场竞争加剧有利于市场主体间技术交流,促进产业融合和技术溢出,拓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创新边界。
四、 数字基础设施政策持续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优化路径
回顾历史,每次产业变革都伴随着基础设施的更替建设。在世界经济加速重建的新目标下,加快推进5G、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既奠定了数字化时代的产业发展基础,更形成了企业创新发展的生态基础。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下,科学布局数字基础设施政策,有效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既需要持续发挥政策的集中、引导和培育优势,也需要激活市场主体内在创新动力。
首先,加快数据共享机制的建设。在数字基础设施政策诸多保障制度中,数据要素的畅通交易与共享对企业构筑数字化生态竞争优势起到关键作用。一方面,数据要素在企业内部的流通对其他传统要素配置效率具有放大、倍增的效果;另一方面,数据要素在企业间的流通,对整体经济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已有研究发现,数据开放和共享方面存在各个数字共享平台数据标准不统一的问题,这导致隐性数据壁垒的产生,相关人员难以整合系统。大量数据未能被有效利用或造成数据冗余和浪费,数据要素有效价值发挥效率降低。一是建立政务数据开放共享“负面清单”,推进公共数据的分级分类,提高数据要素在不同主体之间的流通效率,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辐射能力,最大限度释放政府数据红利。二是探索数据开放标准的制定。推进政府数据开放、指标口径、分类目录、数据质量、数据交易等关键共性标准的制定和实施。
其次,推进政策均衡投入,避免数字鸿沟的扩大。一方面,由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数字人才存在空间的“虹吸效应”[27],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利于数字经济在区域间均衡发展;另一方面,数字基础设施政策存在显著的部门倾向性。政府在制定数字基础设施政策时,会权衡其政策投入回报率,工业是投入产出效率最高的部门,农业产业资本回报率最低,进而导致工业企业数字转型程度整体最高,而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进度相对滞后。应改善数字基础设施政策投入导致的数字鸿沟问题,进而推动数字化转型企业的有序发展。一是数字基础设施政策应该坚持“全国一盘棋”,前瞻性地统筹谋划,兼顾区域协调发展,推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弥补不均衡发展造成的区域数字鸿沟。
最后,加强多层次平台支撑。已有研究表明选择性产业政策对创新数量具有正向影响,但对创新质量影响不显著[28]。数字基础设施政策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也存在数字技术创新质量的争议。尽管数字基础设施政策能够通过提高数字要素可得性、降低数字技术不确定性的预期,进而助力企业识别数字创新机会和引进外部技术,解决企业数字化转型前期投入大、见效慢等问题。然而,技术引进不等同于技术创新,囿于企业技术基础、学习能力等,技术引进容易形成路径依赖。因此,数字基础设施政策应强调企业数字能力的引导与培育,通过强化多层次平台支撑,打造多层次的数据中心大平台、工业互联网平台、人工智能创新平台数据统一共享交换平台和物联网安全监管平台等,营造健康有序、良性协同发展的产业生态,强化对行业管理和产业发展的支撑能力,促进企业间融通创新。
参考文献:
[1] 赵宸宇,王文春,李雪松.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J].财贸经济,2021,42(7):114-129.
[2] 张吉昌,龙静.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来自高新技术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J].经济与管理,2022,36(3):74-83.
[3] 袁淳,肖土盛,耿春晓,等.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分工:专业化还是纵向一体化[J].中国工业经济,2021(9):137-155.
[4] 余典范,王超,陈磊.政府补助、产业链协同与企业数字化[J].经济管理,2022,44(5):63-82.
[5] 郭朝先,王嘉琪,刘浩荣.“新基建”赋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0(6):13-21.
[6] 王海,闫卓毓,郭冠宇,等.数字基础设施政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还是“负能”?[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3(5):5-23.
[7] 邱洋冬.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驱动属地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J].经济与管理,2022,36(4):57-67.
[8] Goldfarb A,Tucker C.Digital Economics[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19,57(1):3-43.
[9] 武常岐,张昆贤,陈晓蓉.传统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研究——基于结构与行动者视角的三阶段演进模型[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121-135.
[10] 解学梅,王宏伟,唐海燕.创新生态战略与创新效率关系:基于创新生态网络视角[J].系统管理学报,2020(6):1065-1077.
[11] 赵丽锦,胡晓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基本逻辑、驱动因素与实现路径[J].企业经济,2022,41(10):16-26.
[12] Aghion P,Cai J,Dewatripont M,et al.Industrial Policy and Competition[J].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Macroeconomics,2015,7(4):1-32.
[13]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4] 李琦,刘力钢,邵剑兵.数字化转型、供应链集成与企业绩效——企业家精神的调节效应[J].经济管理,2021,43(10):5-23.
[15] 黄勃,李海彤,刘俊岐,等.数字技术创新与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来自企业数字专利的证据[J].经济研究,2023,58(3):97-115.
[16] 郑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创新影响机理探究——基于“宽带中国”战略试点准自然实验的实证检验[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23(4):90-104.
[17] Liu F H,Huang T L.The Influence of Collaborative Competence and Service Innovation on Manufacturers Competitive Advantage[J].Journal of Business & Industrial Marketing,2018,33(4):466-477.
[18] Kohli R,Melville N P.Digital Innovation: A Review and Synthesis[J].Information Systems Journal,2019,29(1):200-223.
[19] Thanasopon B,Papadopoulos T,Vidgen R.The Role of Openness in the Fuzzy Front-end of Service Innovation[J].Technovation,2015(47):32-46.
[20] 楊阔,郭克莎.产业政策争论的新时代意义:理论与实践的考量[J].当代财经,2020(2):3-13.
[21] 杨林,和欣,顾红芳.高管团队经验、动态能力与企业战略突变:管理自主权的调节效应[J].管理世界,2020,36(6):168-188.
[22] 徐雅倩,宋锴业.“数字企业家”如何促进中国数字公共服务创新?——基于三省十四市的实证研究[J].公共管理学报,2023,20(03):24-38.
[23] 面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经济社会重点领域改革研究课题组,刘世锦.“十四五”和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改革的方向与重点[J].中国经济报告,2021(2):5-17.
[24] 任弢,王欣亮,张家豪.政府数字化转型何以提升区域创新绩效?[J].人文杂志,2023(3):121-130.
[25] Haushalter D,Klasa S,Maxwell W F.The Influence of Product Market Dynamics on a Firms Cash Holdings and Hedging Behavior[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7,84(3):797-825.
[26] 张叶青,陆瑶,李乐芸.大数据应用对中国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年报文本分析的证据[J].经济研究,2021,56(12):42-59.
[27] 汤蕴懿,李方卓,梁伟豪.数字经济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理论逻辑、政策过程及主要路径[J].上海商学院学报,2022,23(4):37-50.
[28] 黎文靖,郑曼妮.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宏观产业政策对微观企业创新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6,51(4):60-73.
基金项目:上海市软科学研究项目“科技创新支撑上海率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3692100200)。
作者简介:李方卓,女,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和收入分配。
(收稿日期:2023-11-12 责任编辑:殷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