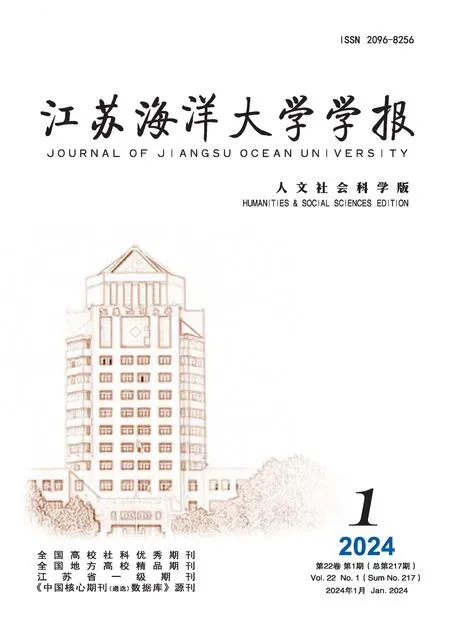论格日勒其木格·黑鹤小说的生态书写*
司国庆
(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北京 100081)
自18世纪中期至21世纪,人类社会在短短三个世纪中接连实现了三次工业革命,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达到空前水平。但与此同时,这种基于不断开发、掠夺自然资源的发展方式,也导致了环境污染、资源匮乏、温室效应、土地沙化、物种灭绝等一系列生态问题。更为严重的是,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伴生物,现代主义思想极大刺激了人类的物质欲望,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思想孽生,人类精神生态的危机逐渐凸显出来。
从根本上说,生态文学是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三重危机“询唤”下的必然产物。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生态文学作品译入、生态思潮引导和本土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现实语境下,我国生态文学逐渐发展起来,涌现出沙青、徐刚、张炜、苇岸、乌热尔图、郭雪波、杨志军、贾平凹、叶广芩、陈应松、邓一光和李进祥等一批生力军。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生态文学的书写重镇大都集中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及边远地区,一批少数民族作家成为生态文学创作的先行者,他们最先意识到生态恶化的危机,直面家园山河破碎的生态现状,反思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与精神根源,并将之投影到文学实践中,表现出强烈的生态关怀意识。黑鹤无疑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
一、自然生态危机的展现和反思
大小兴安岭森林及内蒙古草原占我国近15%的国土面积,资源丰富。得益于这些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历史上北方众多游牧民族如乌桓、鲜卑、室韦等得以在此繁衍生息并形成灿烂的游牧文明。至今,在这片林海雪原中仍然生活着蒙古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等游牧游猎民族。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是一部具有特殊性的自然发展史,从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游牧民族敬畏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理念逐渐被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观念冲击得七零八落,致使森林、草原生态状况急剧恶化。
(一) 森林萎缩,草原退化
大兴安岭森林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原始林区,历史上长期实行封禁政策,仅有少数游猎民族在此生活,较好地保持了森林的原始状态。19世纪末以来,沙俄为攫取我国东北地区资源,与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并于1897年开始修筑贯穿大兴安岭地区的中东铁路,这一巨大的生态宝库开始进入野蛮开发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基于大力开展工业建设的现实需要,曾掀起向森林进军、向草原进军的开发热潮,条条铁路、公路延伸进森林腹地,大兴安岭向人们敞开了她的怀抱,大量木材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各地。但是,随着开发愈加深入,起初“护林为主、采伐为辅”“采伐与更新并举”的方式逐渐演变为无视生态规律的盲动式开发,造成森林资源的严重损失。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后,交通运输更加便捷,人口流动加剧,在经济利益的强烈刺激下,大批盲目自流民涌入林区,滥捕滥猎、盗砍盗伐、毁林开荒。这种毁灭式开发、掠夺式开发使森林郁闭度降低、动物数量锐减、大量植物生长线退缩,生态破坏的严重后果逐渐显露出来。黑鹤的小说就真切地反映了这一严峻的现实问题。
《黑狗哈拉诺亥》中的“黑人”,就是这样一个擅自闯入林区的自流民,他在整片山谷里种满了“错落有致”的罂粟,格利什克老人第一次见到这块罂粟地时大为惊奇,因为鄂温克人知道,丛林深处向来是灌木丛生、物种丰富的。但金钱的刺激极大提升了人的行动力,这些罂粟花正是“黑人”以大量砍伐灌木为代价换来的,一堆堆散落在地上的腐烂的小树和灌木与“红得像经年的血”的妖艳的花儿形成了鲜明对比,“整齐与凌乱”“妖冶与腐烂”的强烈对比颠覆了惯常的审美习惯并传达出前所未有的讽刺意味。所以,与其说是格利什克受花香魅惑而头晕目眩,不如说是大兴安岭森林因生命力流失而表现出的切肤之痛。然而,“黑人”对森林的破坏远不止于此,他还在自己的窝棚外安插了一个栅栏——那是用数不清的各种鹿角、狍子角、犴角和各种兽骨围成的栅栏。鄂温克人世代笃信神山神林神水,对森林中的动物、植物平等对待,狩猎时只取所需,从不滥杀无辜。然而“黑人”却大量猎杀动物并将动物尸骸制成了围栏,他悄无声息地潜入森林,犯下一系列罪行之后却成功逃脱了森林警察的制裁。“黑人”其实正是曾大量涌入林区的自流民的代表,他们在过往数十年中破坏森林的“历史行为”已难以追责,毕竟“历史是过去时,也是由众多的手臂托举过的一片天地。通常来说,那是无人为其承担责任的、仅供现今参照的、由大大小小事件构成的时间序列”[1]44,所以黑鹤将“黑人”的所作所为称为一个“传说”,既讽刺又无奈。
鲁枢元曾表达过关于“森林”变迁与人类命运的喻示:工业文明下“森——林——木”的变化过程也许正是树木不可逆转的命运,但如果人类依旧一意孤行滥砍滥伐,那么“木”终将会变成“十”——一个象征着死亡与寂灭的“十字架”[2]164。这段话语包含的警示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森林是大兴安岭地区的生态与安全屏障,如今这道屏障被撕开了裂口,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种种生态恶果已经开始显现,如河流干涸、沙进人退、火灾洪水、气候紊乱等,警示人们保护森林生态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相较于森林,草原的生态系统更加脆弱。内蒙古草原东起大兴安岭西麓,西至甘肃河西走廊西北端,气候区自东向西大致为湿润区、半干旱区和干旱区,植被类型则分别以草原、沙漠和戈壁为主。辽阔的草原虽然蕴含丰富的畜种资源、植物资源和矿产资源,但由于气候恶劣、土壤贫瘠,也并不总是人们想象中的“水草丰美,猎物极胜”。因此,游牧民族历来注重保护草原脆弱的生态环境,成吉思汗曾在《大扎撒》中规定:“其国禁,草生而地者,遗火而炙草者,诛其家。”然而近现代以来,内蒙古草原经历了同大兴安岭森林类似的阵痛。
近年来,将工矿业开发表述为“进步与发展”,在内蒙古牧区成为一种流行现象。碧绿的牧草下埋藏着“黑色的金子”——煤炭、石油等,此外还蕴含其他有色金属及砖瓦黏土、建筑材料等非金属矿产,“亿万年前的沉积物缓慢而耐心地蜕变,直到有一天人类在地上开出一个纵深的伤口,于是黑色的能源就从这在茫茫的草地中流淌出来了”[3]58。由此发展起来的矿业经济固然为地方财政带来不菲的收入,但同时也给地方生态带来不少问题:大量露天矿场侵占草地,导致草场面积萎缩;大型装载车辆碾压牧草致使沙土外翻,给草场留下一道道“伤疤”,引起草场沙化;矿厂废渣、废水无序排放导致环境污染,此外还极易引起滑坡、地面塌陷等次生地质灾害。在《鬼狗》中,黑鹤对这种无序开发矿产的行为给予了批判:“更多的人类涌向草地,疯狂地钻透地层,在大地上开出更多的伤口。”[3]58“不断有行驶时震得地面嗡嗡作响的大型卡车在院子外面停下,扬起经久不散的灰尘……”[3]58此外,卡车司机们在草地上建立一个又一个中转站,公然进行斗狗、赌博等,把原本静谧纯净的草原搞得乌烟瘴气。如今,草原正面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峻的危机,受矿产开发、过度放牧和无序旅游等影响,草原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退化。“过去,人们通常用生产力标准即现代化程度来衡量一个社会的经济文化的进步和发展程度,但这一标准却衡量不出由生产力进步所带来的不可持续发展问题,更难评价有些历史事件和文化现象的对与错。”[4]草原被游牧民族视为母亲,一定程度上也是游牧民族文化的母体,如果某一天母体被蚕食殆尽,那么一个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也许将会无处依附。
(二) 滥捕滥猎,物种衰减
狩猎是游牧民族一项重要的辅助性生业,是他们得到生活资料的重要手段。狩猎通常具有季节性和选择性,这不仅是因为受生产节奏、社会文化和宗教信仰等因素影响,也是基于自然生态的现实考量。游牧民族在长久的生活中总结出一套独特的生存智慧:维持草原“大命”与“小命”的平衡。草原是“大命”,人和其他动物则是互相平等的“小命”,生命与生命环环相扣,共同组成草原生态的“神性之链”。即使抛开生存意义而就生命意义而言,人与动物也是这个世界上并行的伙伴。游牧民族历来重视与动物的伙伴关系,从众多的史诗、赞词、谚语等口头文学作品中就可见一斑。在通古斯诸民族的“人与动物的神话传说中,他们充分表现出人与动物间有超越自然和超越自我的亲族关系之意识,甚至还描绘出人与动物间建立有人类社会最亲密的家庭关系之情节。如,在猎杀熊的神话传说里,他们尊称动物为‘祖父’或‘祖母’,并以至高的礼仪葬送它。由此展现了他们在过去漫长的狩猎生产生活岁月及特定环境里,所形成的对动物的独特认知态度”[5]。然而自步入现代社会以来,这种伙伴关系已难以维系。
《母狼》和《静静的白桦林》是黑鹤版本的“怀念狼”的故事。《母狼》中,猎人德子故意放走一只怀孕的母狼,这并非是他恻隐之心发作,而是希望待母狼产崽后连同幼崽一起抓获。他为此特意制作了一柄长矛,往狼洞里用力刺戳后再大肆挖掘,最终“如愿”挖到四只狼崽并出售给商人。在本该万物生长的春季,母狼永远失去了生命,几只狼崽永远失去在野外生长的机会,它们将被卖进动物园,永远失去自由,供人观赏。猎人出于贪欲不仅破坏了春季禁猎的传统,还磨刀霍霍伸向幼崽,“猎人扛支空心铁棍,搜寻天涯,切不可见什么打什么”[6]199的教诲被弃若敝履。
而《静静的白桦林》中的杀戮则更为残忍。母狼外出觅食前出于安全考虑把两头小狼埋在沙土里,仅仅露出两个脑袋,猎人巴图趁机抽刀割断了小狼的头,再把它们放回原处。母狼觅食归来,刨开沙土却只见两个头颅滚落下来,绝望的母狼围绕着小狼残缺不全的尸体无助又疯狂地来回奔跑,发出凄惨的嗥叫。躲在暗处的巴图享受着他的杰作,杀戮纯粹变成了一场“游戏”。三年后巴图带着八岁的孩子出猎时再次遇到母狼,显然母狼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它时刻叼着一只袋子,即使后来被巴图一枪毙命,仍然紧紧咬住不松开自己的牙齿。男孩出于好奇查看袋子中到底为何物——那是三只毛茸茸的小狼,它们还不知道自己的母亲已经永远地离开了。男孩亲眼目睹了杀戮过程,“他感觉自己身体里有些温暖的东西就那样慢慢地失去了”。现实世界遽然变成一个死亡深渊,风吹过白桦林发出的簌簌声响,那是生命和童真的挽歌,孩子和小狼就此一并成为“美丽世界的孤儿”。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悲剧的本质是悲剧主体的苦难或死亡,“这苦难或死亡即使不显出任何无限强大与不可战胜的力量,也已经完全足够我们充满恐怖与同情”[7]33。在残忍的猎人面前,原本凶悍的母狼被玩弄于股掌之间。黑鹤以孩子的视角,透过冷静的语调和巨细无遗的细节描写,传递出令人恐惧的阴冷气息,这则丛林中的悲剧格外发人深省。
如果说贾平凹的《怀念狼》是防止文明时代人类整体或民族的“种的退化”,贾平凹“对原始生命力的丧失,形成了柔弱的中国国民性”怀有深深的忧虑与恐惧[8],那么黑鹤则表达了对背弃本民族传统的猎人丧失精神信仰、敬畏之心而成为“异化”人的深深忧虑。失去敬畏之心的猎人,不仅将屠刀伸向了狼,还对黄羊、狼獾、天鹅等痛下杀手,导致草原上的物种迅速衰减。人类率先撕毁与动物之间的无字契约,也必将招致动物的反扑:艾特玛托夫的《断头台》中,母狼阿尔巴拉和公狼塔什柴纳尔在幼崽被偷后,叼走了波士顿不满两岁的儿子,最终孩子与母狼一起倒在波士顿的枪下;满都麦的《人与狼》中,红卫老汉扒去一头狼崽的皮,这头无毛狼竟奇迹般地存活下来,并在20多年后出于报复咬掉红卫老汉儿子的生殖器,显然作者想要表达“人对狼赶尽杀绝也就是自掘坟墓”的观念;叶广芩的《长虫二颤》中,老佘为了取蛇胆泡酒、做蛇肉羹,斩去了一条名叫二颤的老蛇的头,最终却被还未僵死的蛇头咬中,失去了一条腿。无数类似的案例警示我们,人不是万物的主宰,所有的生命都在共享这个世界。如果人类对其他物种不加爱护,一味地滥捕滥猎,结果一定会像吉狄马加借雪豹之口高喊的那样:“那最后的审判/绝不会遥遥无期……”[9]146
二、精神生态的异化和污染
现代社会用科学战胜了愚昧,用理性征服了非理性,自然、神性被祛魅,但好景不长,现代性在谋求发展中很快走向了自身的反面,出现了科技吞噬人性、物欲迷惑心灵等现代性危机。人类精神世界、心灵世界遭遇了生态学意义上的“污染”,出现了精神“真空化”、行为“无能化”、生活风格“齐一化”、存在“疏离化”、心灵“拜物化”等现代社会精神生态恶化的典型征候[2]149,不仅给人类自身,同时也给大自然带来无穷的危害。
(一) 精神冷漠,放逐生命
动物竞技是一项具有悠久历史的民间娱乐性体育运动,我国民间自古就有赛马、斗蟋蟀、斗鸡等活动。竞争是人与动物的本性,一般认为,以动物的争斗代替人与人之间的角斗,是人类精神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文明进步现象,动物竞技的观赏性、娱乐性也是人们调节生活的一项手段。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项活动自产生之初就存在畸形化发展的问题,并滋生出“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啄”的赌博行为。
黑鹤作品中提到的驯狗、斗狗情节,生动反映了动物竞技的畸形发展以及现代人精神异化的问题。《黑焰》与《黑狗哈拉诺亥》中的“黑人”和《鬼狗》中的德子在一定程度上是异化的现代人“心狠手黑”的象征,他们独有一套驯狗的野蛮而残忍的“智慧”。为了锻炼“鬼”的耐痛力,德子和工人们动辄抡起棍棒铺天盖地打过来,“鬼”越反抗越能激起他们施虐的快意。为了锻炼“鬼”的敏捷度和力量,德子把一只猫吊挂在横杆上,杆子的一头连着“鬼”的链子,“鬼”一次次向前扑击,又一次次把猫向前推离,猫与狗互相折磨,不断滋生仇恨和恐惧情绪,这种情绪慢慢地渗透进彼此的身体和血液里;这种践踏动物生命的训练方式令“鬼”变得更加暴烈,撕咬、吞噬的疯狂逐渐成为它的本能。为了锻炼“鬼”的颈部肌肉,“黑人”把重达一百余斤的铁链一圈一圈地箍在它的脖子上,把它拴在自制的“跑步机”上一跑就是五十公里,直至它的爪子已经麻木得感受不到不断滚动的皮带。在如此惨无人道的训练下,另外两条狗“贝贝”和“黑狮”很快发疯毙命,尽管“鬼”凭借强大的生存本能坚持下来,但它的心灵已经扭曲,精神接近崩溃,丧失了一头牧羊犬的优秀品质,变成一头嗜血的斗犬。而为了“培养”牧羊犬的嗜血特质,在《黑狗哈拉诺亥》中“黑人”更是直接以生命献祭:将九只幼犬关进山洞,不定期投放不足额的食物,引导它们自相残杀,最终只有靠吞食兄弟血肉存活下来的两只幼犬才有望成长为“獒”,其歹毒程度比《赵氏孤儿》中屠岸贾豢养西戎“神獒”攻击赵盾的行为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人为安排的“优胜劣汰”,具有浓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将部分现代人伦理道德感丧失、凶狠冷漠的精神生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黑焰》《鬼狗》和《黑狗哈拉诺亥》中的斗狗场面则更加血腥。矿场工人把斗狗当作酒后消遣的工具,旅游景点把斗狗作为招徕游客的手段,人与狗共同完成一场场触目惊心的“表演”:“鬼”甫一被牵进斗场,围观者便扔石头、酒瓶等来激怒它;当一方出现落败迹象,观赏者便疯狂地呼喊号叫,期待接下来血肉横飞的场面;一旦任何一方倒下,他们就鼓呼呐喊,对落败者轻则断腿残废、重则命丧斗场的后果漠不关心,只沉浸在血腥杀戮带来的快感中,只有亲眼目睹“鬼”把落败者的尸体一块块撕咬吞食殆尽之后,他们体内的快感才会慢慢退却并饶有兴致地回味刚刚发生的一幕幕场景,“那些观看了斗犬比赛的游客脸上都挂着一种近似痴呆的表情,很像春天在森林里游荡的动物彻夜狂欢之后那种放纵的颓败”[3]121。这种血腥争斗让人不由得联想到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中,隐喻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期的美国人与人之间相互压榨、倾轧的斗狗情节,狂热的围观者更是让人想起鲁迅笔下痴迷“看砍头”的看客。一百年如白驹过隙,国人摆脱了落后病、软骨症,但依然存在着精神冷漠病,就像黑鹤不止一次在文中提到,毫无人性的训练使牧羊犬“身上有些东西已经永远损坏了”,其实,看客们健康的心灵和人性何尝不是同样永远损坏、消失了呢?
E农1S是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以广占 63-4S[1]为受体、以抗稻瘟病品种 GD-7[2]为供体,通过杂交、回交和自交,结合分子标记辅助选择技术选育的携带抗稻瘟病基因Pi1和Pi2的两系不育系。2016年通过湖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品种审定编号为鄂审稻2016028。以E农1S为母本配制的杂交组合目前已有E两优476[3]、E两优186[4]和E两优222通过了品种审定。
(二) 狂热拜金,幸福匮乏
现代社会犹如一部高速运转的机器,作为零部件的个体在日复一日的机械化、同质化生活中难以找到自身的价值和定位,经常处于幸福匮乏状态,这就使得金钱与物质成为现代人的共同信仰,并导致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等思想大行其道。消费主义使商品逻辑成为整个人类社会的逻辑,并制造出关于消费行为的一系列虚假想象,“人们在消费商品时已不仅仅是消费物品本身具有的内涵,而是在消费物品所代表的社会身份符号价值。诸如富贵、浪漫、时髦、前卫、归属感等象征衍生价值就像幽灵附身于商品上,散发出身份符号的魅力迷惑着消费者。消费者在一种被动迷醉状态下被物化成社会存在中的符号——自我身份确认”[10]。在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理念的驱使下,人为赋予的“商业价值”“实用价值”“科学价值”“文化价值”等遮蔽和掩盖了事物的本体性价值,导致出现种种反生态行为,其中对“沙图什”的热捧就是一则典型例子。
“沙图什”是一种用藏羚羊绒毛织成的披肩,一条沙图什围巾售价一度高达上万美元,被认为是上层社会人士地位显赫、品味时尚的象征,但这种所谓的“显赫”“时尚”实则是用藏羚羊血淋淋的生命换来的,每生产一条沙图什围巾,就需要牺牲三至五头藏羚羊的生命。但在巨额利润面前,人们往往置动物的生命于不顾,对沙图什的虚荣追求导致了盗猎藏羚羊行为屡禁不止。黑鹤的短篇小说《黑眼睛》就极有可能是以此为背景创作的。“我”跟随志愿者队伍巡视藏羚羊生态区,亲眼目睹了藏羚羊被杀戮的惨状,“成片地被剥了皮的藏羚羊尸体铺满了足有一个足球场大小的谷地,血腥味夹杂着腐尸味扑面而来,几乎让人睁不开眼睛”[11]49。而盗猎者的罪恶行径还远不止此,面对国家的明令禁止和保护藏羚羊队伍的干预,他们甚至还肆意开枪杀人。在《黑焰》中,韩玛跟随“野牦牛队”巡查时遇到盗猎团伙,走投无路的盗猎者向韩玛举起了枪,关键时刻如果不是格桑突然出现并将盗猎者的枪摔到地上,韩玛可能已经当场牺牲。小说中的情节绝不只是文学性的夸张,在西藏、青海、新疆三省(自治区)组织的反盗猎行动中,就有杰桑·索南达杰、段兴浩、罗布玉杰等志士在与穷凶极恶的盗猎分子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生命。
消费主义对人类思想的侵蚀不仅表现在穿着上,还表现在饮食上。时下人们已不再满足于“吃饱”,还追求吃“好”——四处搜罗价格昂贵、物种稀有的食材,于是各种动物被端上人类的餐桌。《天鹅牧场》中,原本高贵俊美的白天鹅被猎人毫不犹豫地扭断脖子,“在他们的世界里,天鹅仅仅是更大的鹅而已,只代表着可以吃的肉,事实上,在他们看来世间万物最终都是要从人的嗓子眼通过的”[12]55。《狮童》中,鼬、鸽子、兔子、跳鼠甚至还有狼都一一滑进阿尔斯楞的肚囊,草原小镇上到处都有狗肉馆,人类忠诚的伙伴最终也难逃被吃的命运,正如郭雪波的《沙葬》中云灯喇嘛所说:“人是个太残忍太霸道的食肉动物,你看看你们这些不信佛的人,啥不吃?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吃得那个全乎。那个贪劲……人啊,早晚把这个地球吃个干净吃个光!”[13]79直到有一天,人类连动物都吃腻了,也许会转头向人类自己开刀!莫言的《酒国》就讲述了一个消费主义心理畸变的酒国市地方官员食用婴儿的触目惊心的“吃人”故事。自鲁迅以后,“吃人”主题在20世纪末期重现,不同之处在于,“鲁迅是从启蒙主义视角发现了人的历史性被‘吃’的命运,莫言则从消费主义的帷幕里,揭开了‘人’被异化为‘物’(美食)而被‘吃’的真相”[14]183。
总之,在消费主义、拜金主义思想的蒙蔽下,人们总是将物质与身份、金钱与幸福划上等号,但消费主义的虚假泡沫并不能使人们真正摆脱幸福匮乏状态,也许小说中韩玛的经历能够给予我们一定的启示,相较于富足的好友杨炎,韩玛并没有华美的别墅和庞大的家业,他能做的只是和格桑一起参加保护藏羚羊活动,去孤儿院服务,到草原小镇支教,在奉献中收获了人们的尊敬与爱护以及格桑矢志不渝的陪伴,同时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意义。
三、重回和谐的追求与可能
中华文化向来重视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统一,儒家讲求“仁爱万物”,要求“钓而不纲, 弋不射宿”;道家奉行“道法自然”,倡导“天地与我并生, 万物与我为一”;佛家则遵奉“戒杀护生”,教导民众奉行“不杀生”“素食”和“放生”等行为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儒释道三家都把“天人合一”作为共同的哲学基础,彰显了古人对于自然万物的共同感悟。随着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率先打破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约定,最终招致自然的报复,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使人类认识到,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于是倡导人类重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呼声愈发高涨。
(一) 树立生态整体观
自然界中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单独存在的,日月山川、鸟兽虫鱼,所有的有生命体和无生命体共同构成了和谐统一的地球生态系统。人类必须从整体和全局上观照自然生态问题,即秉持生态整体主义思想,客观全面地看待人与动物、动物与动物的关系,理性对待生命的生死消亡,把不破坏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动态平衡作为最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当作最高目标和终极目的。对此,黑鹤有着清晰冷静的认知,这主要来自游牧民族经过生活积累而总结出的生态智慧,一切以保证草原“大命”的整体平衡和谐为准则。
獾是草原上一种并不起眼的食草动物,但当它们数量过多时,不仅与家畜争夺草料,还到处打洞破坏牧草生长,牧人骑马一旦陷进洞里极容易别断马腿产生危险,所以在《猎獾》中,扎布不惜用两头羊去换一只可以捉獾的牧羊犬萨合乐。萨合乐成功钻进獾洞并咬死三只獾,但扎布并没有让它赶尽杀绝,而是给獾家族留下幼小的成员,因为獾不仅可以控制草原上老鼠的数量,还会食用腐烂的动物尸体,间接保护其他牲畜免受病菌感染。
死亡是自然世界不可回避的一个话题。在《狼獾河》中,“我”外出狩猎遇到一头被狼獾猎杀的驯鹿,“我”并未因驯鹿的死而过分悲痛并对狼獾深恶痛绝,而是冷静甚至略带调侃地描述“它那凝固的目光带有一种傻呵呵的不知所措的古怪表情”,并把驯鹿的死归结为命里注定的事。在这里,黑鹤关注的不是个体生命的消长,而是系统生命的延续,驯鹿固然是一条宝贵的生命,而且似乎处于“弱势”地位,理应获得同情和怜悯,但狼獾的生存权利又该如何保护?如果为了保护驯鹿而不惜消灭其他动物,势必会导致生态链条的断裂,那么系统的延续也就无从谈起。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面对狼与狼獾、狼与熊、熊与驯鹿、狼与羊群之间的争斗,“我”从来都是选择“冷眼旁观”。在自然世界践行人类社会“惩强扶弱”的道德观念,本质上是一种有悖于生态道德的行为。如果从生态整体观念来看待,死亡的意义便获得了超越,“羊食草,狼食羊,狼化尘土,滋养青草”,个体“小命”有消有长,但草原的“大命”得以生生不息,这样生命才得以最终达到理想的和谐状态。
(二) 人与自然“有距离”地同行
黑鹤在一次访谈中曾谈道:“动物是与人类并行的精灵,所有生命都是平等的。我写小说就是想让读者知道,除了城市,其实仍然还有荒野。在荒野之中,人类和其他生灵是可以和谐共处的。”[15]黑鹤的小说启示我们,人类应该善待并尊重其他生命,这样才能换来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例如《雪地》中,“我”去森林滑雪,“我”的滑雪板可以翻开雪层,使藏身雪下的林鼠“抱头鼠窜”,从而为乌鸦和狐狸提供了食物,并得以与乌鸦和两只狐狸交上了“朋友”。而《额尔古纳河的母狼》《红色狼谷》《老班兄弟》以及《风之子》讲述的都是“救助——报恩”的故事,一来一往间彰显人与狼、人与熊、人与马之间的笃厚情谊。在这几则故事中,“我”作为人类,并未对野生动物抱有成见,而是勇敢地战胜恐惧,或帮母狼取下钢夹,或从“老班”大张着的熊口中取下鱼钩,人类付出了真诚并成功收获动物的友好回馈,确证了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可能。
需要注意的是,人与动物在荒野世界的邂逅毕竟是短暂的、偶然的,人类与动物虽然分享着同一个自然世界,但主要活动空间却又迥然有别,任何一方的贸然闯入都可能酿成冲突引发流血事件。所以,黑鹤在作品中频繁提及“教训”与“距离”两个词,意在提醒人类与动物应该保持适当距离。
黑鹤在《黄昏夜鹰》中写道,“我”曾惩治过一只到营地偷取食物的松鸦并坚信这对它是好事,否则它早晚会被人类捉住。果不其然,营地中一只夜鹰的经历不幸验证了“我”的判断,它每晚定时在营地上空发出急骤的叫声,在“我”没来得及驱赶它之前,就被一个鄂温克男孩用枪打死。在《艾雅苏克河的猞猁》中,一头猞猁进犯鄂温克人的营地并捕杀了驯鹿,维加和“我”决定带领牧羊犬驱赶猞猁,并用猞猁幼崽作威胁,最终它带着一只受伤的耳朵和幼崽永远离开了,“对这头猞猁而言,这是一次刻骨铭心的记忆,以后,它会带领着自己的幼崽远离人类的营地”[16]36。
这种主张通过“距离”和“教训”而非一味用“爱”或“信仰”来拯救失范的自然世界的思想,在《美丽世界的孤儿》中有更加明显的体现。在可怕的森林大火面前,人与动物结下了深厚友谊。首先是柳霞不顾生命危险寻找跑丢的驯鹿幺鲁达,随后一人一鹿的逃亡队伍不断有新角色加入:两头熊(在鄂温克神话中,人与熊本来就是兄弟)、一头犴、两只狍子、狐狸、野兔、林鼠甚至还有狼和狼獾,所有生灵井然有序地跟在熊的身后撤退,这时“捕猎与奔逃突然间退到次要的地位,林地间呈现出天堂牧场一样和谐的景象”[17]161。很快,两头熊就确定了逃离火灾的方向,前方是一棵折断了的巨树垂落地下形成的一个三角形的门,“此时,这个天成的大门正在燃烧,两头熊毫不犹豫地从火门下穿过,它们厚实的身影像蜡样在火中熔化了”[17]163,其他动物随后也一一穿过火门。但此时,柳霞和幺鲁达却犹豫了,随后火门轰然倒塌,两头熊和其他动物随即失去踪影,人与动物未能同行到最后。
在鄂温克的民间信仰里,火具有洁净与再生的功能,那道熊熊燃烧的火门就像一道生命之门,阻隔了属于荒野世界的熊、犴等一众动物和属于人类世界的柳霞和驯鹿,但阻隔线也是安全线,如果柳霞和幺鲁达贸然穿过即将倒塌的的火门,那么后果也许不可想象。幸运的是,经过大火的“洗礼”,幺鲁达体内那远古的罗盘被唤醒,随后成功带领柳霞逃离了火海,他们同样获得了“再生”。人类尽管未能与动物同行到最后,但还是通过短暂的邂逅共同创造了生命的奇迹,人与动物达到真正生态意义上的和谐状态。
四、结语
毋庸讳言,黑鹤的生态思想及生态理想主要是基于游牧民族生活传统以及现实生活经历之上的主体性自觉,并未形成系统的生态理念,也就不能就现实存在的难题给出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事实上,这也是当下我国多民族生态文学创作中存在的主要弊病:或是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地焦虑、呐喊,或是千篇一律地说教、训诫,或是对西方生态理念亦步亦趋,将罗尔斯顿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说”和史怀泽的“敬畏生命”伦理等奉为圭臬,总之,是在一种“前现代守成、现代性诉求、后现代性批判”[18]的境况中戴着镣铐跳舞。也许,“生存”与“生态”不必存在根本上的对立,肖亦农在《寻找毛乌素》一书中已经向我们证明,以“工业化思维”治理生态问题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郭雪波在后期的文学创作中也尝试给出了“科技+人性”的解决方案。所以,现代化和科技化本身也许才是现代性难题的突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