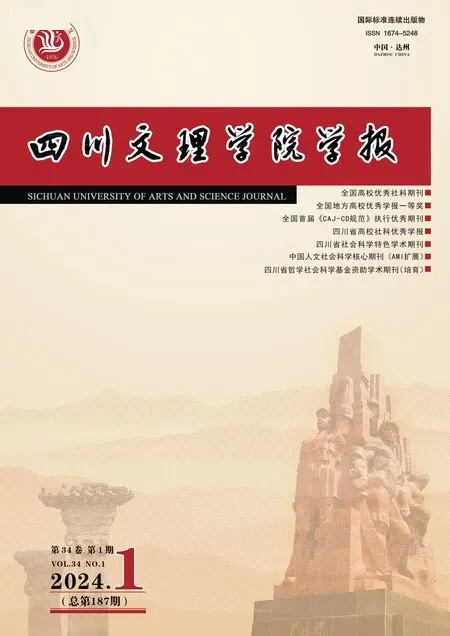古今中西会通视阈下的潘知常生命美学研究
——读潘知常《我审美故我在——生命美学论纲》
杜 璇,张久全
(淮南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南 232001)
被誉为“崛起的美学新学派”的代表中国著名美学家潘知常教授以四十年磨一剑的学术精神构筑的多达200 余万字“生命美学三书”——《信仰构建中的审美救赎》《走向生命美学——后美学时代的美学建构》与《我审美故我在——生命美学论纲》,标志着他生命美学研究的一个阶段性范本,也标志着他所力主的生命美学成熟,尤其是他最新出版的70 多万字的《我审美故我在——生命美学论纲》视为他在近40多年中关于生命美学思考的一个阶段性总结,更加凸显出作者以孤勇者的勇气承担把美学摇醒的使命;凸显作者不随波逐流落入“从1到99”的项目学术的窠臼,而毅然决然的开创“从0 到1”的创新之路;凸显他经过40年的艰辛,已经把首创和独创的生命美学体系已经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凸显他已经构筑一座属于自己、属于时代、属于未来的生命美学大厦,也迎来了学术和人生的巅峰。
潘知常提出的生命美学首创和独创于1985年,生命美学的全称是“情本境界论”美学,其中“情本”(兴)、“境界”(境)、生命(生),都正源自于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范畴——兴、境、生,认为美学的奥义在人——人的奥义在于生命——生命的奥义在于生成为人——生成为人的奥义在于生成为审美的人,提倡“自然界生成为人”而非“自然的人化”提倡“实践的人道主义”而非“实践的唯物主义’;提倡爱者优存并非适者生存;提倡我审美故我在并非我实践故我在;提倡审美活动是生命活动的必须和必需而非审美活动是实践活动的附属品、奢侈品。它从立足于“实践”转向了“生命”,从立足于“启蒙现代性”转向立足于“审美现代性”,从“认识——真理”的地平线乾坤大挪移到了“情感——价值”地平线,从小美学走向大美学,生命美学就是“万物一体仁爱”的生命哲学+“情本境界论”审美观+“知行合一”的美育践履传统。在虚无主义泛滥的时代,潘知常的生命美学担当起时代领航的光荣使命,在美学界中大放异彩,极大了推动和促进了当代中国美学的繁荣壮大。
一、热美学:“生命”视界中的美学
在《我审美故我在——生命美学论纲》中,潘知常提倡的生命美学不仅是中国古代的生命美学传统与西方近代开始的生命美学以及中国现代美学“美美与共”,而且“各美其美”,其中的关键就是将美学作为一个即将莅临的全新大时代的主导价值、引导价值的引领者来思考,即“美学热”与“热美学”的遥遥指向。
他目光独具、别出心裁的认为正是源自生命本能和生命本源的强大动力对于传统美学的反叛,才有尼采“超人”论的异军突起,才有柏格森的生命绵延说的横空出世,才有狄尔泰的“生命体验”的空谷足音,才有弗洛伊德“力比多”的迅猛发展,才有海德格尔“生存空间”的凌空高蹈。叔本华用生命意志论横扫康德学说与基督教神学之余绪,继对中世纪神权专制愚昧落后,黑暗腐朽文艺复兴与近代启蒙运动的反叛之后,再次唤起了人类内心生命之觉醒,开启了全新的西方现代美学的先河。正是以他为开端,美学才真正按照其尊严来探索。传统的西方人在宗教的统帅下生活,没有真正洞察生的意义、死的价值,从叔本华开始才逐渐开始醒悟并立足于人类自身的生命揭示人不仅要活着,还要洞彻为何而活。然而,叔本华的意志统率理性、复活了理性美学,但是这种意志仍然是精神的,还残留浪漫主义的成分,还局限与康德的“无功利关系”论,并没有彻底回归到生命本体。尼采认为叔本华的意志仅仅局限精神,他振聋发聩地呐喊“上帝已死”,意味着传统价值体系完全崩溃,意味着一个人有限的生命能够在上帝保护下得到精神慰藉的存在方式完全崩溃,意味着以神为标准尺度对人的存在进行最高价值判断的标准完全崩溃,他认为传统美学把形而上观念视为所有问题的出发点,就无可避免的导致虚无主义。尼采认为“生命是某种存在或不存在的基本尺度,我们无法设想还有什么存在观比这种在生命意义上理解存在的存在观更生动,更有活力”[1]生命是一种积极扩展、蓬勃发展、不断超越自己而繁荣发展的强力意志。假若黑格尔提出的是“精神形而上学”,那么叔本华提出的“意志形而上学”是盲目的、不可阻挡的、渴求生存的欲望冲动,那么尼采提倡的是生命“生命形而上学”,本体是以充溢的生命本能的“强力意志”为特征的,生命的本质就是不断抛弃旧我、超越自身、重塑新我,“强力意志”塑造的是有勃发生命、健康强大、活泼活跃、傲睨一切、富有创造力的超人。
生命美学家们大都关注人生的生成性问题,而潘知常则认为尼采首先将“人生”与“生成”这两者巧妙地结合起来,并首先关注的个体生命本体问题和生成性问题,并且突出地表现出超越欲望、超越本能、超越冲动的大写的意志,这是对于人生自我维持、自我创造、自我疗救、自我崛起的深层肯定,所以,与其说尼采是现代文化激进主义者,不如说他是生命本体论的激情主义者;柏格森从精神深处出发,首次提出“生命冲动”,以“绵延说”克服机械主义论与唯理主义论的局限,继而影响法国现象学与存在论美学。弗洛伊德同传统理性主义分到杨彪,直接进入本能、欲望、冲动、潜意识等个体生命深层心理中,由此推翻了人们对意识自我的认知、颠覆了人们对理性的理解、否定理性在人内心世界中的核心地位;海德格尔指的“生命”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体结构或近代哲学倡导的观察、思索、抽象、总结的学科,而是承载了占有性存在体验的生命本身;不是对人生进行反思性的理解,而强调自我与世界整体性的联系,他用“生命”概念阐释“返回事物本身”,即回归生活原初,而非复归意识本身。
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和海德格尔是潘知常研究西方美学的核心,他不仅对西方美学研究的新发现的概括总结,还为中国当代生命美学的研究提供新的思维方式、新的研究视野和新的精神资源。
潘知常认为美学的奥秘在人—人的奥秘在生命—生命的奥秘在“生成为人”—“生成为人”的奥秘在“生成为”审美的人。或者,自然界的奇迹是“生成为人”—人的奇迹是“生成为”生命—生命的奇迹是“生成为”精神生命—精神生命的奇迹是“生成为”审美生命。再或者,“人是人”—“作为人”—“成为人”—“审美人”。因此,生命美学对于审美生命的阐释其实也就是对于人的阐释。生命美学关注的不仅仅是审美活动的奥秘,而且更是人的解放。而人与世界之间在如下维度上发生关联:首先,人与自然的维度,这是第一路径,指的是我—它关系;第二,人与社会的维度,这是第二进向,指的是我—社会关系;第三,人与他人的维度,可被称为第三路径,涉及的是我—他人关系;假若前两个维度体现的是现实维度与现实关怀中实体对象的实际用途,指涉的是人类生命活动中的利润利益、在此岸的有限性、形而下的求生性,被有限所限制,而第三个维度超越了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关注的是彼岸的无限性,是形而上的理想形态与心灵沟通与对话,这奠定了审美活动的基础。潘知常认为审美活动禀赋着人的存在价值、承载着人的美好未来、依附着人的梦想希望,从超越维度与终极关怀维度角度关注人类具有形而上意义的价值性的生命活动。正是意义,才能使人得以看到苦难背后的坚定、仇恨之上的热爱、绝望之上的梦想;正是价值和意义,才让人默许无限、超越无限、融合无限,从而触摸到生命的尊严和尊荣、生命的完好和美好、生命的光辉和神圣,正是通过这种人之为人的绝对尊严、绝对权利、绝对职责构建起全新完整的阐释生命世界的艺术模式。
二、多元化的审美模式的会通
潘知常在中西方美学、中西文论会通中重建美学文论,一方面,他引进马克思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美学资源,另一方面,他从印度教、儒家美学、道家美学、明清美学等汲取美学营养,融会贯通,建立别具特色、富有智慧的中国生命美学宏大体系。
首先,受到禅宗精神的影响。潘知常认为,中国美学的智慧在儒家美学中诞生,在道家美学中成熟,在禅宗美学中完成。总体上看,禅宗美学为中国美学所带来崭新的精神财富和审美智慧,真正的、切实的揭示出审美活动的纯粹属性、生命属性、爱的属性、自由属性,真切的把审美活动完全等同与自由。
第一,从对象性的实体到非对象性的空无。假若实践活动是面对交易、推演、计算的现实世界时,人们在功利主义支配下为满足实际需要通过消耗单调的体力或者智力而占有、利用、改造现实客体以维持人的肉体生存,受到外在目标、外在必然性的、外在生存性动机规定和限制、追求合规律性或者合目的性,这种纯属外在于人的、与人本质截然对立的、不得不听命于他者的被动消极的活动,使人以物而非人的面目出现,只体现人的片面发展的本质力量。
第二,从神思到妙悟。从孔子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与乐”到庄子的“物物而不物于物物”,都是经验式的审美,而禅宗所提倡的“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苏轼《送参寥师》)”、达到“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乃至到来无一事,庐山烟雨浙江潮。”的“承当”式的生命澄明的审美境界。禅宗先驱僧肇对妙语的见解堪称经典:“玄道在于妙悟,妙悟在于即真。即真即有无齐观,齐观则彼己莫二。所以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涅槃无名论》)。潘知常认为,正是这种对妙悟的奉若神明奠定了中华民族的美学精神和艺术灵魂。妙悟是对真实、鲜活、本然生命的呈现,“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此。”(《诗经》)。区别于道家,禅宗既不以物观物;也区别于儒家,也不是以我观物,而是物我双照,不存在独立的主体和客体,只存在互相决定、互为倚重、互为表征的审美自我与审美对象,因此,曾经失去纯真纯正、天真天然、清纯清美的生命全部被打捞和救赎。
其次,受到儒、释、道、佛教等的“生”与“仁”的启迪。儒家爱生、道家养生、墨家利生、佛家护生,小到部落种族、大到整个宇宙的生生繁衍体现中华美学的“生命在世”“生命优先”,潘知常提出的万物一体仁的“爱的智慧”的生命美学,认为爱即生命、生命即爱、因生而爱,因爱而生是其主旋律,这种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难舍难分。无论是孔子的“仁者爱人”、孟子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 尽上》)、庄子的“泛爱万物、天地一体”(《孟子 尽上》),还是宋代道学构建“万物一体之仁”,尤其是王阳明把“归仁说”和“万物一体说”巧妙结合起来,以仁为基础的万物一体的“万物一体之仁爱”、以现代意义的爱去重新阐发人,使“仁”走向“仁爱”,使“万物一体之仁”仁走向“万物一体之仁爱”,为潘知常的生命美学的深化带来一定的启发。潘知常认为,曹雪芹的《红楼梦》达到中国传统美学的顶点,发出了“万物一体仁爱”的先声因为这是从儒家的“发乎情、止乎礼”、道家的“发乎情、止乎游”、禅宗的“发乎情、止乎觉”转变为明清的“发乎情、止乎情”,最后的“情”就意味着爱,意味着中华民族大彻大悟“止乎情爱”的千年谜团;意味着重视作为内在保证的生命的自由建构、生命的自由生成、生命的自由意志、生命的自由权利;意味着从儒家无自由的意志或者道家无意志的自由、对自由感觉的觉醒走向对自由意志的觉醒,从以人为本明确转向以仁爱为基础,以人为本。由此,情感远远高于理性、生命远远高于智性、直觉远远高于理念、自由远远高于本质。
最后,受到知行合一的启迪。基于自我生命体验,以“心体”为核心,“知行本体”“以行为本”“价值诉求”“多重合一”等丰富的维度构成了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有机理论体系,成为中国哲学史上处理“知”“行”关系的典范,他认为心的本体或人性是无善恶,阳明“万物一体”的“致良知”不仅是道德主体,同时可以达到与天地万物、宇宙生化为一体,只有省查自身、悟天德与本心、知天理在己,良知体之于身、存之于心、扬其之用,通过克己、立德、彰义、致善,在亲亲、恤民、仁人、爱物这一利己利人的过程中体悟至诚至纯、至仁至韧与至乐至美的“万物一体”。
第二,现代西方文论的参考和借鉴。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在新著《我审美故我在——生命美学论纲》中的《巴黎手稿——生命美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作者揭示出深刻的思想逻辑:马克思的哲学思考是以“人的解放”为核心的,也是由“实践的唯物主义”与“实践的人道主义”两个维度组成,马克思的美学思考主要不是体现在“实践的唯物主义”之中,而是体现在“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维度。马克思的美学是“生命”的、“生成”的、“生产”的。它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集中体现,也是“完成的人道主义”的理论表达。在《巴黎手稿》中,真正给与我们以美学启迪的,不是马克思的关于人类解放的历史求解——“实践的唯物主义”,而是马克思的关于人类解放的价值省察——“实践的人道主义”,也就是对“实践”的“人道主义”的批判,以及从实践活动对于人的满足程度出发的对于实践活动的进步与否的省察。因此,马克思的美学直接与马克思关于人的思考有关,也就是直接与马克思关于“实践的人道主义”的思考有关,而间接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有关。
受到加缪无神论人道主义的影响。荒诞体现原因与结果的割裂、愿望与现实的对立、目的与手段的悖逆、个体与类的疏离,而荒诞是虚无的生命活动的虚无呈现,是丑对美的调侃,信仰的重要性、必要性、迫切性如影随形。他有句非常经典的名言:“我们可以拒绝宗教,但不能拒绝宗教精神;我们可以拒绝信教,但不能拒绝信仰;我们可以拒绝神,但不能拒绝神性;我们可以拒绝恨,但不能拒绝爱”。[2]
最后,潘知常对存在主义理论的阐释也独树一帜。萨特否认了上帝造就人类、“本质先于存在”的有神论,提出了生命本体第一法则——“存在先于本质”。潘知常把海德格尔的存在和中国美学的道的内涵、海德格尔的真理和中国美学的真在的关系做了详细比较。海德格尔认为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对世界的本质局限于某种确定的、既定的、固定的“存在者”,而忽略对“存在者”存在根源的求索。存在是客体化、对象化、概念化之前具有本真性、鲜活性、遍在性、超越性和本源性,这和中国老子的“有以为未始,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的源初世界;是禅宗的“万法明明无历事”“洪钟未击”的源初世界;是庄子“道可道,非常道。道恒无名”的源初世界。海德格尔认为“真理”不是知识体系中的是非价值判断,也不是认识论中知识与客体的符合,而是传统形而上学忽略的“去蔽”或“澄明”过程的“存在”的揭示中。这和中国美学推崇的先于主客体二分的关系的、从理性认知和逻辑认识的遮蔽中破土而出,使得生命的本真处于恬然澄明的状态之中的“真”有异曲同工之妙。潘知常这样做的总结:“海德格尔的存在学说和中国美学的道有深刻的融通,它们同样是一个在客体化、对象化、概念化的那个本真、活生生的世界,从遍在性看,是不离有;从超越性看,是不离于无;从本源性看,是不离有无,不落有无。永远在变的是遍在性;永远不变的是超越性;变而不变的,不变而变,是本源性。”[3]
三、多元互补融合式路径的意义
(一)审美意义:赎回纯真虔诚的生命
自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再到工业革命,哲学家尼采振聋发聩地呐喊“上帝已死”,将意味着传统价值体系完全崩溃,意味着一个人有限的生命能够在上帝保护下得到精神慰藉的存在方式完全崩溃,意味着以神为标准尺度对人的存在进行最高价值判断的标准完全崩溃,他认为传统美学把形而上观念视为所有问题的出发点,就无可避免的导致虚无主义。“上帝之死”是尼采思想中一个重大转折点,不仅标志着他对人生、人性和哲学本质的深刻思考,而且也提供了一种重新审视现代社会的视角。
潘知常用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理论进行传媒文化的批判,指出人们刚刚摆脱对自然经济的依赖,又陷入了对肆意膨胀物性依赖,同时出现在现代商品化、消费化的审美活动中,若任由其发展下去,我们的时代将会会成为一个灵魂虚无的时代、一个爱的匮乏的时代、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他对物欲横流和人伦丧失的社会现实进行启蒙哲学的美学批判,其审美意义就是用一种救赎美学,赎回“最为虔诚、最为忠实、最为仁慈的人类”为基本宗旨。[4]
(二)文化意义:生命的审美境界
人类文明是一部探索和探寻魅力社会的过程,无论是柏拉图构思的“理想国”,还是莫尔勾画的“乌托邦”,抑或是《圣经》中描述的“伊甸园”,魅力社会成为鼓舞、激励人们追求和实现美好愿景的精神期待,然而尼采的“上帝死了”、福柯的“主体死了”的时代使得“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叶芝语)韦伯打造现代世界光辉而伟大的“祛魅”工程,法国象征派诗歌的先驱波德莱尔发表了象征主义代表作《恶之花》,尼采发表了体现酒神精神、高扬生命意志的《悲剧的诞生》,被称为“维也纳第一精神分析学派”的弗洛伊德发表了标志精神分析心理学的正式成型的《梦的解析》,未来主义代表马里内蒂发表了《未来主义文学技巧宣言》等都不遗余力的在艺术王国反叛现实主义传统,在人的感性、生命、个体、生存与审美活动的关系上开辟出新的救赎世界。“艺术,乃是使生命成为可能的壮举,是生命的诱惑者,是生命的伟大兴奋剂。”[5]对于个人而言,艺术和审美就是心灵的拯救与超越,生命有限的战胜与超越、生活意义的创造和打造,对于社会而言,则是文化虚无主义的拯救良方和抵御技术文明的异化的法宝,这就是潘知常关注的根本原因,
潘知常认为当最高形态的审美活动中的自由生命一旦步入诗性境界,以追求自我自由存在、维护自由存在作为自身责任,以尊崇与捍卫个体的绝对意义为自身责任,追求终极价值、终极意义等形而上学的属性及最高形态的审美活动。抛弃世俗社会中一切是非善恶功名利禄对人性的掩盖和束缚,对艺术双重“解蔽”后的审美方式致力于生命的敞开、发展、涵养、提升,实现了人类精神世界与宇宙人格的拓展、解放与升华,达到自我建构的旁通统贯、生香活色、绵延不绝、一体俱化的生命境界,由此生命突然之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这是对人类与天地万物在最初本源性上的精神性还原与回归的状态;更能达到个人与天地万物结合成“大无我”的化境怡养的本真状态,达到超越是非、痛苦、生死而进入超越超拔、恬然澄明境域时生命的自在笃定、惬意欢愉的巅峰极乐的审美体验的至高境界,这和“生命美学教父”“爱的教父”潘教授受到古今中西方生命美学思想的启发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