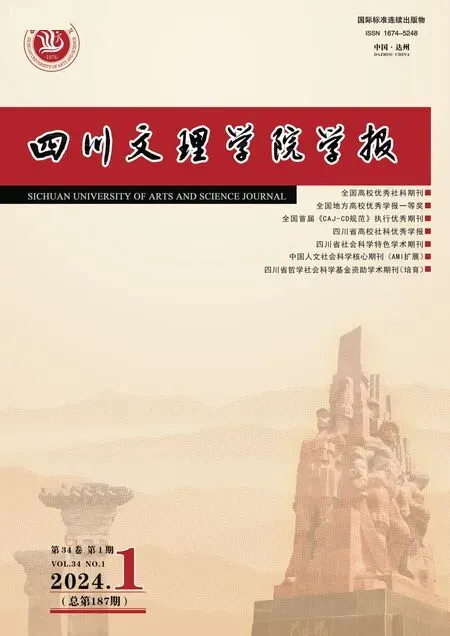生命美学理论对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建设的启发
——兼评潘知常新著《我审美故我在——生命美学论纲》
刘 燕
(浙江传媒学院 创业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思想解放一小步,文化服务提高一大步。
美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也是文化思想界的引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到2035年,实现“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那么,如何进一步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实现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的目标呢?
文化之美在精神,精神之美在审美活动。审美活动与生命活动息息相关,审美活动就是人类存在的本体。潘知常提出的生命美学,关注生命、情感和境界,又被称为情本境界论生命美学,或者情本境界生命论美学。在近四十年的美学生命中,他用整整200万字、三本巨著(美学三书)系统阐释了他的生命美学思想。从《信仰建构中的审美救赎》(2019 年出版)到《走向生命美学——后美学时代的美学建构)(2021 年出版),再到《我审美故我在——生命论纲》(2023 年出版),潘知常不仅回答了中国美学界“美学问题”与“美学的问题”两个重大学术命题,其生命美学理论的三个重要的美学支撑命题:“生命视界”“情感为本”“境界取向”与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在实现“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的目标上也具有内在一致性,对我国公共文化建设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启迪。
一、生命视界:“实践的人道主义”马克思美学的公共文化服务思想
潘知常的生命美学理论一直强调“生命视界”。“生命视界”的提出,是在1985 年。在《美学何处去》(《美与当代人》1985年第1期)一文中,潘知常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美学界重视实践美学,而忽视人的精神世界的非人本化的美学研究现状反思,他在文章中“呼唤着既能使人思、使人可信而又能使人爱的美学,呼唤着真正意义上的、面向整个人生的、同人的自由、生命密切联系的美学。”他认为“真正的美学应该是光明正大的人的美学、生命的美学”“美学应该爆发一场真正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应该进行一场彻底的‘人本学还原’”“美学有其自身深刻的思路和广阔的视野,它远远不是一个艺术文化的问题,而是一个审美文化的问题,一个‘生命的自由表现’的问题。”[1]176
潘知常的生命美学思想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一切为了人民”是中国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宗旨,公共文化服务的目的就是实现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4 个重点关键词“幸福”“美好”“基本”“均等”,无一不是围绕着人的基本需要展开的。从思想的发源地来看,潘知常生命美学理论也来自于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巴黎手稿)。在《我审美故我在——生命美学论纲》专著中,潘知常对生命美学的发源与马克思美学思想的关系做了阐释。他认为1985 年生命美学从《巴黎手稿》起步,来自一个基本的判断:马克思美学是以“人的解放”为核心的,亦即是同时兼顾了“实践的唯物主义”与“实践的人道主义”的。李泽厚的实践美学体现了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美学思想,生命美学则体现了“实践的人道主义”。马克思的美学思想是人本主义的,它并不是直接地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有关,即李泽厚所代表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美学有关,而是直接地与马克思的“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美学思想,即潘知常的生命美学思想有关,生命美学的思想基础就是人本主义。潘知常认为在这个意义上,美学不是向人类解放的历史求解——去践行“实践的唯物主义”,而是引领人类解放历史——去省察价值追求“实践的人道主义”。[1]85既然马克思美学思想的逻辑是人类价值判断标准——人的全面解放,而非唯物主义的历史科学标准——人的劳动实践;更何况前者生命美学将审美活动看作是生命活动的必然与必需,后者实践美学将审美活动看作是实践活动的附属品、奢侈品。那么,很显然,前者潘知常生命美学的理念就更契合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思想,更符合在共产主义社会中,马克思所期冀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这样的一种个人全面发展的美学理论,也更贴合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目标和宗旨,更值得推广和践行。
马克思的美学思想一直强调从人出发,它直面的必然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也必然是有意识的生命审美活动。“实践的人道主义”马克思美学即生命美学非常强调从“生命视界”出发,将审美活动向人的生命活动还原,向感性还原,从而赋予美学以人类学的意义。在公共文化服务的建设中,要践行“实践的人道主义”马克思美学思想,首先必然要满足的也即是人们对有意识的生命审美活动的需要。“幸福”“美好”明显地是人的生命审美活动需要满足之后产生的美感,而“基本”“均等”则是人的生命审美活动需要满足的前提条件。无论如何,这意味着,公共文化服务优先要做的是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的生命审美活动的权益,也即是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和基本文化需求,这也是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现代化的底线。
从美学的角度来看,人的基本的审美活动需要有神性、理性的、生命性的(感性)三种,分别形成了神性的、理性的、生命的三种视界。“神性”视界的审美活动的核心是宗教活动,至善目的是其理所当然的价值终点,审美与艺术服务于宗教的至善目的,道德神学和神学道德是“神性”视界的公共文化服务的价值所在。“理性”视界的审美活动崇尚科学美学,求真是其价值所在,在劳动实践、科学视界中发现美是公共文化服务的目标。“神性”视界是人的审美活动的道德觉醒,“理性”视界是人的审美活动的知识觉醒,这些在公共文化服务中都有重要的教育意义。但从人的全面解放和发展来说,“神性”和“理性”视界的审美活动都是外部驱动的审美活动觉察,是外驱力产生的道德和知识的伪救赎,而不是人的内部审美活动觉醒产生的真正的审美救赎。这样的公共文化服务,满足的是主办方的需要,而不是审美主体的需要,势必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需要。
具有生命美学的公共文化服务,应当是“生命”视界的公共文化服务,是以“美”的名义为人性启蒙开路,以“美”的名义为“热爱生命”“尊重生命”启蒙开路,从人的生命出发去唤醒人的内在的生命审美活动,透过审美与艺术通往人的世界,引发人们洞悉人性奥秘、澄清生命困惑、寻觅生命意义,将公共文化服务转型为对人的“生命”视界的服务,去启蒙人们的生命审美意识,将“道德的人”“知识的人”生成为“生命审美的人”。
生命美学的“生命”视界关注的“生命”,严格来说是人类的小生命,而不是宇宙的大生命,虽然生命美学也会涉及宇宙大生命,但与生态美学所奉为至宝的宇宙大生命不同,生命美学的“生命”是“万物一体仁爱”“生之谓仁爱”的人类的小生命,它的思想来自于朴素的马克思的“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基本立场,同时又是对中国美学的生命美学传统的继承,是“孔子+马克思”的美学思想在新时代的发展。这完全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现在提倡的“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生命”视界的公共文化服务要做的也就是在第二个结合的美学思想——生命美学的思想基础上,在审美与艺术的公共文化服务中实现习总书记提倡的第一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天地人生,审美为大。审美与艺术,就是生命的必然与必需。在审美与艺术中,人类享受了生命,也生成了生命。生命就是审美,审美就是生命。中国美学一直以来并不把审美活动作为一种工具方式,也不把审美对象作为一个对象化的物,而是将审美与人生直接打通,使审美活动成为人生证悟的一种方式,成为生命回归安身立命之地和最后归宿的安顿。因此,当代公共文化服务提供的审美活动,在道德和知识的层面之上,应当更关注生命的解蔽,不论形式和内容如何丰富,都不应限于对外在世界的丰富“呈现”,而应是一种丰富地“敞开”,对每一种生存方式、生命过程敞开,包容多元的生命形态,为生命的觉醒创造奇迹,为生命的升华作见证,引导艺术创作从“我思故我在”的“神性”审美视界、“我在故我思”的“理性”审美视界,走向“我审美故我在”的“生命”审美视界。
二、情感为本:公共文化服务要情感为本
人是情感的动物,情感优先于理智存在。情感的存在,是人之为人的终极性的存在,也是人的最为本真、最为原始的存在。所谓理性和思想,“都是从那些更为原始的生命活动(尤其是情感活动)中产生出来的”。[3]“情感为本”是潘知常生命美学的第二个命题,他主张审美活动要回到生命,就必然要优先回到人的情感中。我们对世界的知觉,是由情绪和感情揭开的,而不是概念和理性,情感自由比理性自由更为根本,对情感的需要也比对理性的需要来得更强烈。
潘知常认为,“情感机制是人类最为根本的价值器官”,在1995年出版的《反美学——在阐释中理解当代审美文化》一书,他指出:“人类对于情感需要的渴望,来源于人类的生命机制。当代心理学家已经证实:就人类生理层面而言,作为动力机制的因此也就最为重要的是情感机制,而不是理性机制。过去,为了论证人类理性的伟大,美学家曾经过分重视新皮质而忽视皮下情感机制。把大脑新皮质的功能看作是审美活动的复杂过程的唯一中心,现在看来,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就探讨审美活动的根源而言,真正的重点不是理性的机制而是情感的机制。其中,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是两大关键。”[1]186
情感的哲学化,是当代哲学和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审美情感的解放,也是审美生命向无限敞开的必经途径。对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来说,要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就是要提高人们审美活动中的情感自由和情感满足,释放人们与生俱来的充沛情感,让人民群众在审美与艺术中体验情感美。遗憾的是,传统美学一直过于强调审美活动的无功利性,而忽视了审美的情感价值功利。潘知常认为,对于功利性的忽视是“传统美学的一个从柏拉图开始的重大的美学失误,”审美活动既有无功利性又有功利性,“这所谓美学的功利性就是:对于人类的情感的满足。”[1]186他认为,审美活动不属于“理性-真理”系统,而是“情感—价值”系统。审美、情感与人的解放之间存在着一组对应关系,审美解放、情感就解放、情感解放,人就解放,人解放就能带来人的全面发展。然而,在传统美学,对于“情感-价值”系统的研究始终被视而不见,审美活动也被逼迫得从“情感-价值”系统中退了出去,委身于“理性-真理”系统,被当成了一种“以美启真、以美储善”的工具,[1]189为此,有必要让“情感-价值”从“理性-真理”的思考框架中解放出来,将人从“理性-真理”的桎梏中解救出来,因为没有绝对的真理和绝对的理性,人们所追求的审美活动寻求的是属于对象的真理,在感性中被直接给定的真理,在审美活动中唯一存在的世界就是属于审美对象的世界。
“情感为本”提示我们,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和形式建设的重点,就是要以“情感为本”,以“美”为名激发和满足群众潜在的情感需要,从而实现生命审美的价值,因为审美的感情会让人产生特殊的愉悦,“我们觉得美的地方正是能够提高人类祖先生存机会的地方”“我们通常会接近让人愉快的对象”“艺术让我们生活得更好”,[4]审美带来的情感愉悦会让我们生活的更美好更幸福。公共文化艺术的呈现要以人类情感的体验来建构,让情感回到文化和艺术审美的核心地位上来,去反映人的内在,从而实现人的自我的生命审美救赎。
维戈茨基说:“没有新艺术便没有新人”“艺术在重新铸造人的过程中”“将会说出很有分量的和决定性的话来”。[5]公共文化艺术的内容生产也就是让艺术工作者按其本意来生产艺术作品,推进新艺术的产生和新人的塑造。不过潘知常在《我审美故我在—生命美学论纲》中认为,有不少人以为美学的研究对象是艺术,这是因为大众最常所知的美学研究对象就是“情感的形式”+“形式的情感”“有意味的形式”+“有形式的意味”,这与艺术的研究对象是相似的,是“形式+情感”的创造。其实不然,所谓“美学”,其实也就是审美哲学,它直面的是进入情感关系的生命活动,是关于进入狭义的情感关系亦即审美关系的生命活动的哲学思考。它所研究的主要对象的确离不开“情感的形式”+“形式的情感”“有意味的形式”+“有形式的意味”,但却是情感化的生命活动的世界,是“世界的形式化”+“形式的世界化”。[1]191这样看来,公共文化艺术仅关注“情感+形式”的狭义的个体的“小美学”是不够的,还要关注“形式化的世界”与“世界的形式化”后的“大美学”,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去创造艺术。
诚如音乐创作,黑格尔说,“音乐的独特任务就在于它把任何内容提供心灵体会……按照它在主体内心世界里的那种活生生的样子”“音乐的基本任务不在于反映出客观事物而在于反映出最内在的自我。”[6]这“活生生的样子”“最内在的自我”便是人类最内在的生命情感。卡西尔指出,“我们在艺术中所感受到的不是那种单纯的或单一的情感特征,而是生命本身的动态过程”“在艺术家的作品中,情感本身的力量已经成为一种构形的力量”、在审美活动中,“我们所听到的是人类情感从最低的音调到最高的音调的全音阶;它是我们整个生命的运动和颤动”。[7]为此,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生产不应该走向“小美学”,而应该走向“大美学”,应当以“情感为本”,不止于关注文学艺术的审美创作,而是借助关注文学艺术的审美创作去进而关注人的解放,关注世界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命话题,在小与大之间见微知著,发现世界、发现人性、发现生命、发现意义,找到“情感与形式”的最佳载体。唯有此,公共文化服务上才能取得理想的“情感-价值”效果。
三、境界取向:公共文化服务要提升境界审美
阿格尔在上个世纪70年代写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的序言中写道:“因为异化存在,所以马克思主义存在,而且必然存在。”[8]因为,“正是异化构成了我们时代怨愤的基础”。[9]在现代社会,异化仍然是我们精神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公共文化服务现代化要解决的一大问题就是人的精神虚空问题。虚空是21 世纪最大的人类精神疾病的源头,这是一种吉登斯所言的“个体在联系到一个差异性和宽泛的社会世界时所体验到的那种无力的感受”,[10]在传统的社会中,个体还能够掌握生活的大部分,但是在现代世界中,人们已经无法掌控个人的生活,如一句歌词所唱“明天与意外哪个先来,永远不要去猜猜猜”。
潘知常在《我审美故我在——生命美学论纲》中的第三个命题是“境界取向”,“境界取向”其实就是价值世界的被发现。他从1985 年就指出,人不但是现实存在物,而且还是境界存在物;1988 年他提出:美在境界;1989 年,他正式提出:美是自由的境界,“美便似乎不是自由的形式,不是自由的和谐,不是自由的创造,也不是自由的象征,而是自由的境界”;1991 年,他又提出了“境界美学”,“中国美学学科的境界形态,所谓境界形态是相对于西方美学的实体形态而言的”,并且指出美学并“不是以认识论为依归,斤斤计较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而是以价值论为准则,孜孜追求着有限与无限的同一性”,美学“以意义为本体而不是以实存为本体”、“旨在感性生命如何进入诗意的栖居”“为宇宙人生确立生命意义,寻找永恒价值,挖掘无限诗情。”[1]195
生命美学“境界取向”的核心关键词是“价值转换”,潘知常认为“美学之为美学”,首先却必须被理解为对于“美学何为”的追问。这是一种本体论型的追问。在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不再是一种认识关系,而是一种意义关系。“境界取向”是对人的审美意义的问题的回答,也即为生命活动的价值意义给出审美的答案。宗教的、道德的、科学的答案,过去的一切价值追问已经难以适应当下的时代难题,美学之为美学就必须在新的时代语境中重估一切价值,重新对世界进行解释和思想重构。世界本来就没有唯一世界,也没有真实世界,唯有的就是对世界的解释与再解释,重构解构与再重构。人类对于世界的解释与重构并非一劳永逸,曾经被解释的还会被再解释,曾经重构的还需要再重构。
重估一切价值,就是要重估生命,从新的价值来认识生命,重构生命的意义感,使之超越人性的本性,达到新的生命境界。现代社会,每个个体的生命境界差异很大,物欲、现实、道德、审美时刻左右着我们生命的格局,潘知常认为,美学即人,人即美学,美学之为美学在于对一切价值的重估,就是要推动人的审美境界“连续不断地觉醒”,进而使人成为人,成为自我觉醒、自我生成的人。美学,是一门生命自我开掘、自我提升的境界提升之学,它是“为己”之学,而不是“为人”之学。[1]200
潘知常生命美学的“境界取向”一语击中当下人们精神世界虚空、生命境界沦落的现实,在物欲至上、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空虚麻木、抑郁盛行的现实中,生命价值确实需要重新被评估、被认识、被解释和被提升,首要的却是对现有价值的反思与再反思。这是因为美学是从省察生活开始的,而不是从认识生活开始的。反思生活,不是为了“装饰”生活,而是为了重估生命的意义,更好地追寻属于自己生命的美好生活,因为生命只有一次,不可辜负。
对于公共文化服务来说,重估一切价值,不仅仅是供给大众大量的富有生命反思性的文化艺术作品,更重要的是借助于审美艺术生产活动,让人民群众去追问、去思考,去对一切未经省察的生活,都去问的一个为什么,唤醒大众对当代价值与个人生命价值意义的反思,在连续不断地生命觉醒中拔擢生命的境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正是公共文化服务的价值所在。
那么,公共文化服务又如何才能拔擢大众的生命境界,促进人民群众过上真正地属于自己生命的美好生活呢?在《我审美故我在——生命美学论纲》中,潘知常为我们提供了生命美学的智慧答案:重构“中华梦”的主导价值、引导价值。潘知常认为,“中华梦”与“美国梦”“欧洲梦”的主导价值和引导价值是完全不同的。“美国梦”强调物质性,是以“经济人”“竞争”去重构主导价值、引导价值,是以自由换金钱的价值;“欧洲梦”强调精神性,是以“文化人”“平等”去重构主导价值、引导价值,是以闲适换生活的价值。“中华梦”不同,它追求的是“天下归美”“天下大同”“美美与共”,是以“审美人”“仁爱”去重构主导价值、引导价值,是向美而在、为美而生的审美价值。因此,以“中华梦”为主导价值、引导价值的文化生产,就要以“万物一体仁爱”之美的名义,重建中国人的自我,使人成为人,成为具有生命审美人格、生命审美境界的人。[1]720-721
潘知常提出的“中华梦”是一个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新中国的现代性审美价值,要实现这一审美价值,在公共文化服务中提升人的境界,离不开对大众生命审美人格的培育。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4 个重要关键词“幸福”“美好”“基本”“均等”,也无一不与生命审美人格的培育有关。不过,当下风行的“唯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唯科学主义”“唯经济主义”“唯享乐主义”“拜物教主义”“拜金主义”的文化环境,与生命审美人格的培育土壤却是相悖的。公共文化服务要重构“中华梦”的主导价值、引导价值,达到提升大众生命的境界,就要断然离弃诸此种种歧途,推动文化艺术工作者按照生命审美的价值规律生产。一言以蔽之,用生命美学的理论解题,仍是回归生命,以“人的发展为中心”去疏通生命的源泉,以生命为引线去诠释世界、创造生活,以“万物一体仁爱”的态度地看待、对待、善待人生,在“连续不断地审美觉醒中”,推动每个个体“因生命而审美”“因审美而生命”,最终达到个体生命境界的最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