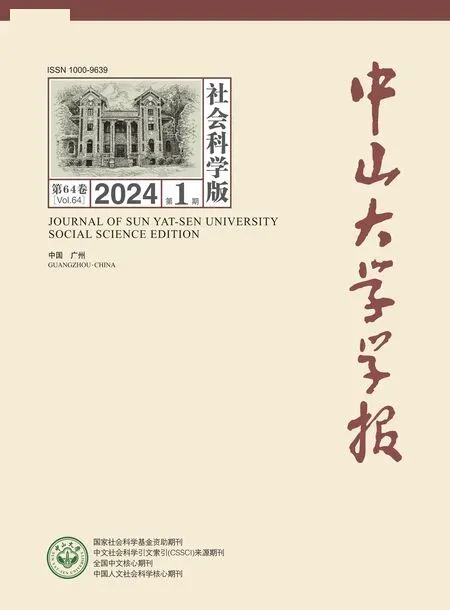事的突显与经学态度之弊:章学诚“六经皆史”说重估 *
刘梁剑
引 言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生活年代与康德相当,其“六经皆史”说自晚清以来便备受关注,中外解者众多①余英时论述“章实斋的‘六经皆史’说”,征引日文、英文文献甚夥。参见[美]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增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12 年。章益国近著也提供了丰富的参考书目,并主张从隐喻的角度把“六经皆史”解为“六经似史”,进而引向“四部皆通”的知识分类观和学术演变观。参见章益国:《道公学私:章学诚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11—212页。章著借鉴默会知识论等思想资源,中西互证互释,对章学诚思想作了别开生面的诠释。。从字面上看,“六经皆史”讨论经史关系,至于究竟是以史解经,还是以经尊史,抑或尊史抑经,则各家持说不同。再者,史又有书写的历史和发生的历史的区别(书写的历史至少又有史料与史意两个不同的层面)。如以书写的历史解史,则“六经皆史”关乎两种知识门类,所论限于知识内部;如以发生的历史解史,则“六经皆史”溢出知识的论域而走向现实,史与世、事发生关联,进而要求经与世、事发生关联,以经世的主张批判经学态度。
本文试图在后经学时代重估清代思想家章学诚“六经皆史”说对经学态度的箴砭。经学态度者何?其基本表现是尊经。秉持经学态度而尊经,不是泛泛意义上的尊重经典,而是在相当强的意义上主张若干部经典之中蕴藏了全部的绝对真理,人们的工作乃是如何正确理解这些经典。因此,经学态度必然还关联着一整套与之相匹配的理解言、事、道、圣、史等关系的观点与方法。重估章学诚对经学态度的箴砭,乃是对“六经皆史”之说进行一般性的义理阐发。“阐发”者,在所阐发对象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关切之间实现良性互动,打开其义理规模,抉发其当代意蕴。
一、言—事—道:六经载道
“六经皆史”的经学批判意义,钱穆已明言之,“实斋著《通义》,实为箴砭当时经学而发,此意则知者甚尠”;章学诚倡“六经皆史”之说,“盖所以救当时经学家以训诂考覈求道之流弊”①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416、426页。。章学诚的前辈学人戴震倡言:“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②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东原文集(增编)》,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240页。此可谓戴震理学的基本纲领③笔者曾将戴震理学称为“批判理学”,以彰显其从语言分析入手批判宋明理学的维度。参见刘梁剑:《戴震批判理学及其语言哲学之成立》,杨国荣主编:《思想与文化》第12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1—128页。。章学诚明确提出异议:“训诂章句,疏解义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也。”④章学诚:《原道下》,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03页。戴震理学也是一种经学,需要以“六经皆史”说批判之。批判总是蕴含了批判的根据(在此意义上,没有道理的批判之所以没有道理,不是因为缺乏根据,而是因为根据缺乏道理)。那么,“六经皆史”这个命题批判经学的根据在哪里?一言以蔽之,“六经皆史”,立“史”破“经”。
章学诚把经、史视为两种不同的著述方式。在他看来,真正的著述都是史:“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⑤章学诚:《报孙渊如书》,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21页。相形之下,经是一种蜕变的书写形式,是“近儒”不切人事而直言义理的写作方式:“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⑥章学诚:《浙东学术》,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21,121页。这样的经,其写作方式是“著书”:“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⑦章学诚:《易教上》,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1,2页。这里的“著书”当然不是指一切书写,而是指离事而言理的刻意著述。如《易》“非圣人一己之心思,离事物而特著一书,以谓明道也”⑧章学诚:《易教上》,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1,2页。。“六经”并非这种意义上的“经”,所谓“六经皆史”意味着,六经与其称之为近儒所理解的“经”,不如称之为史:“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⑨章学诚:《浙东学术》,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21,121页。
在以上对照中,章学诚实际上也交待了史的写作方式:即人事、事物、政事而言理载道。这便涉及言、事、道之间的微妙关系。首先,言事合一:“古人事见于言,言以为事,未尝分事言为二物也。”⑩章学诚:《书教上》,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21页。关于言、事的内涵,各家有不同的理解。如倪德卫认为,言与事为历史书写中两类对立的材料,言者,“著名人物的政令、奏章和文学篇章”,事者,“统治者或大人物的行为”。参见[美]倪德卫著,杨立华译:《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165 页。余英时解章学诚的言事合一观,与柯林武德相类比,把言解为内在的思想,把事解为外在的行动。参见[美]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增订本),第251—259页。在直接层面上,六经对事加以明述。六经皆史,六经皆事。“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⑪章学诚:《易教上》,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1,2页。其次,由事显道。六经对事加以明述,其根本目的却不是为了单纯记事,而是为了明道。但是,道是形而上者,不能离开形而下之器(也就是事)。就道与言的关系而论,这意味着道不能直接明述,只能“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通过“政教典章人伦日用”等形下之器显现。章学诚并非否定六经载道,而是否定“后世”儒者离开六经所言之“器”而直接把握道的错误理解方式:“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为是特载道之书耳。”⑫章学诚:《原道中》,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00、101页。不妨一提的是,余英时引此,认为章学诚“谓‘六经皆器’,非载道之书”。见[美]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增订本),第53页。此解似误。“六经皆器”说固然突显“器”,但并没有因此径直否定六经载道。以六经为“特载道之书”,则道离于器,理离于事,从而走向经学的态度。六经之言具有“言—事—道”三元二重结构:其一,言与事,六经之言明述事,故曰“六经皆器”;其二,事与道,事以显道。就言与道的关系而言,六经之言明道,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六经载道”。但是,如何理解这里的“载”字?六经之言并非通过明述的方式明道,而是通过明述事的方式显示道。六经之言乃事中涵理显道之言,而非明述道理之言①在此意义上,我们赞同岛田虔次的以下说法:我们应“从‘事’而不是从‘言’寻找经中的‘义’或‘道’的根源”。参见[日]岛田虔次:《六经皆史说》,刘厚琴主编:《日本韩国的儒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75页。。如“不知六经皆器”,则“言—事—道”三元二重结构中居间的“事”失落了,只剩下言与道,二者之间也被误解为明述关系。如此,言蜕变、异化为离事之“空言”。与此同时,按照经学的态度,道也变成了超越于事的永恒真理,所谓“恒久之至道”②刘勰:“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1《宗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21页。。
经学家以训诂考覈求道,所犯错误便是如此。“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③章学诚:《原道中》,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01页。经学的态度失落了经中之“事”。“学者但诵先圣遗言而不达时王之制度,是以文为鞶帨絺绣之玩而学为斗奇射覆之资,不复计其实用也。”④章学诚:《史释》,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271页。由此,六经之言变为离事之空言。经学复以离事之空言为意义之源,以理孳理,穷理盘道,难免落入空虚。何以解之?唯有事。“秦王遗玉连环,赵太后金椎一击而解;今日性理连环,全藉践履实用以为金椎之解。”⑤章学诚:《书孙渊如观察〈原性〉篇后》,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570页。
二、事变:道不备于六经
“六经皆史”箴砭经学态度,因为章句训诂因失落经中之“事”而不足以发明六经所载之道。“六经皆史”立“史”破“经”,恢复事之于言、之于道的源发地位。在此意义上,六经皆史,即六经皆事。事“凝而成‘史’”⑥杨国荣:《人与世界:以事观之》,北京:三联书店,2021年,第202页。,发生的历史凝为书写的历史。然而,事与史之间仍有其张力。事凝而成史,却是凝而不固。一方面,“凝而不固”意味着,我们需要从历史书写回归凝于其中的历史事实,进而把握显现于历史事实中的道。这是一个如何有效理解历史书写的问题。另一方面,“凝而不固”意味着,已发生的历史虽然可以凝为书写的历史,但历史本身并没有固化,现实中的事不断发生着,只要时间不打住,总是要超出已经凝为书写的史。事超乎史,道亦超乎史。“‘六经皆史’,则六经固不足以尽夫道也。”⑦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419页。因此,章学诚批评经学态度以为道备于六经的预设:“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⑧章学诚:《原道下》,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04,104页。这是说,倘若“道备于六经”,那么经学研究方法就足够发明道了;但是,世事不断变化,在六经完成书写之后,世事仍在发生,因此,六经不能言说这些后发生的事变,因此也就证明道不备于六经。这里省略了一个推理的前提:事变,道亦变;倘若道不随事变,六经书写之前的事变就足以穷尽道。道之所以不能封闭于六经,正是因为道随事而变、因时而生的历史性。历史需要不断书写(章学诚讲“随时撰述以究大道”⑨章学诚:《原道下》,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04,104页。),而任何历史书写相对于生生不息的事与道来说总是滞后的、不充分的。当然,历史书写本身也是事与道生生不息的一种方式,其中之一便是,历史事件之意义与价值总是处于未完成的状态。如赵汀阳所言:“历史中的每件事情,其意义和价值都不是自足的,都取决于它在后续历史中的延伸力。所谓‘内在价值’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幻觉。”⑩赵汀阳:《历史·山水·渔樵》,北京:三联书店,2019年,第42页。生生,不仅是历史的生生,也是历史书写的生生,又是历史书写参与历史的生生。除非时间打住,历史终结,否则一个历史事件总是处在意义不断更新的可能之中。
因此,经学态度之误,不仅在于不足以发明六经所载之道,而且还误在通过六经把握恒久之至道的雄心。章学诚标举董仲舒“道之大原出于天”①章学诚:《原道上》,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94,94,95,94页。,这是用“天”对显“人”在认知上的有限性。章学诚进而用“自然”解释“天”:道“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②章学诚:《原道上》,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94,94,95,94页。。道,生成于事,不是一成不变的超验性的绝对真理,而是内在于历史事件之中、随着历史事件的展开而不断展开的自然过程。倪德卫如此解读道的历史性:“章学诚的道似乎是人类本性中倾向于一种有秩序的、文明的生活的基本潜能,这一潜能在历史中逐渐将自己写出,在那些人们必将认为是正确的和真实的东西中实现自身。‘道之大原出于天’。但‘天’对章学诚而言实际上是令人敬畏的自然秩序……章学诚对人类的道德秩序有着本质上是宗教的敬畏,而与此同时他又将它完全视为自然的、逐渐展开的。”③[美]倪德卫著,杨立华译:《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第104页。不仅常人,就是圣人亦不能完全掌握道。与道之“自然”相对的,便是圣人的“不得不然”:“道有自然,圣人有不得不然……道无所为而自然,圣人有所见而不得不然也。”“不得不然者,圣人所以合乎道,非可即以为道也。”④章学诚:《原道上》,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94,94,95,94页。除了区分“自然”与“不得不然”,章学诚还在类似的意义上区分“所以然”与“当然”。“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人可得而见者,则其当然而已矣。”⑤章学诚:《原道上》,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94,94,95,94页。“自然”,就道自身的展开而言;“所以然”,就道与事物的关系而言;“当然”或“不得不然”,就事物与人的关系而言。“当然”之“当”,不是规范意义上的应该,而是描述意义上的得当。当然者,当其时会的时措之宜。如冯契解章学诚“六经皆史”:“六经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教典籍,这些典籍所记载的是‘器’,说明了当其‘时会’应采取的措施,这就是‘当然’。”⑥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冯契文集》(增订版)第7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1页。圣人于道有所见,但所见之道只能是道于一时一地所展开者(“当然”,“不得不然”),而不可能是道之全体(“所以然”,“自然”)。圣人于道有所见之道,固然是圣人的“过人”之处,但同时也彰显了圣人在道、在天面前的有限性。
在此,“六经皆史”之说展现出破除圣人神话的解放力量。章学诚甚至直接批评儒家过分尊孔的错误:“夫文章以六艺为归,人伦以孔子为极,三尺孺子能言之矣,然学术之未进于古,正坐儒者流误欲法六经而师孔子耳。”⑦章学诚:《与陈鉴亭论学》,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17,718页。章学诚固然高度肯定孔子“述六经以训后世”的伟大功绩,但他还是通过周孔之别、述作之异强调孔子的限度,其背后的理据则是历史撰述须即事明道的真义:“韩退之曰:‘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夫说长者道之所由明,而说长者亦即道之所由晦也。夫子尽周公之道而明其教于万世,夫子未尝自为说也。表章六籍,存周公之旧典,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非夫子推尊先王,意存谦牧而不自作也,夫子本无可作也。有德无位,即无制作之权。空言不可以教人,所谓‘无征不信’也。”⑧章学诚:《原道中》,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00页。孔子讲“述而不作”,并非谦词,而是道出了自己有德无位、本无可作的“不得已”窘境。不得已,没有机会像周公那样“得位行道,经纬世宙”,所以只能“表章六籍,存周公之旧典”。倘若一味尊孔,就会“虚尊道德文章,别为一物,大而经纬世宙,细而日用伦常,视为粗迹矣”⑨章学诚:《与陈鉴亭论学》,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17,718页。。这正是经学态度道器分离的理论错误。
三、历史撰述:以事观之
“六经皆史”说揭示“言—事—道”三元二重结构,经学态度忽略了事的居间地位与事变的源发地位。进一步看,作为历史撰述的言实际上也是事之一种。因此,从“事”的角度考察历史书写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六经皆史”说对经学态度之箴砭的意蕴。
事凝成史,凝而不固。凝而不固,源于事与史的张力,实际上也是发生的历史与书写历史之间的某种张力。这便涉及“历史”的二重义。如岛田虔次在讨论章学诚时也指出:“所谓历史一词包含两种意思,其一为事件,其二为事件的记录知识。”①[日]岛田虔次:《六经皆史说》,刘厚琴主编:《日本韩国的儒学研究》,第267,268页。然而,从发生的历史到书写的历史,居于其间的历史撰述者早已在场。《说文解字》考察“史”的本义:“史,记事者也。”由此可见,“史”一名而三义,即历史书写者(主体义)、事件(客观义)和历史记录(主观义)。岛田虔次指出:“同时包含这三种(客观的、主观的、主体的)意思,是中国所谓的‘史’的独特性。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这三种意思的统一,还必须看作只在外面的偶然性之上所包含的意思’。”②[日]岛田虔次:《六经皆史说》,刘厚琴主编:《日本韩国的儒学研究》,第267,268页。或许我们可以说,中国所谓的“史”相较于“历史”(history)的独特性,不仅在于它除了客观义和主观义之外尚有主体义,而且还在于,正是通过主体义,客观义和主观义建立了内在联系,从而使得三义的统一不是外在或偶然的。历史撰述者将发生的历史记下来,转化成书写的历史,而后来者则通过书写的历史认识发生的历史。
然则,历史撰述者记事,不纯是记事而已。六经皆史,章学诚所理解的史乃是即事明道。他区分了掌故与史义:“作史者贵知其义,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③章学诚:《言公上》,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202页。掌故是典章制度,史料是也;与之相别的史义则是掌故所承载的道,所谓作史者“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④章学诚:《史释》,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270页。。上文论及“六经皆史”说立史破经,批评离道于事。现在我们看到,“六经皆史”同样批评离事于道。离道于事,道事两橛;离事于道,亦是道事两橛。道事是两物,二者显然有别。但是,在分析二者之别的同时,还要有见于二者之合,否则就陷入道事两橛的形上思维。在章学诚之前,王阳明已提出“六经皆史”说,他与弟子徐爱关于经史关系的问答有助于我们理解“六经皆史”说的辩证思维特质。“爱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⑤王守仁:《传习录上》,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1页。徐爱将经与史分开、事与道分开。阳明指出,这是分析地说,分别“以事言”“以道言”。与此同时,还要综合地说,所谓“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这里的“即”“亦”,正是强调二者有相同相通之处(但非完全等同)。
作史者即事明道,这里的“明”固然首先是文字上的阐明,但文字上的阐明又会溢出文字而作用于现实生活,对历史产生实际影响。前面论及“事凝成史、凝而不固”的两个方面,在此我们看到了第三个方面:书写的历史“溢出”书写,进入发生的历史,构成后续发生的历史事件的一部分。历史撰述在双重意义上做事:首先是观念层面的“作”,然后是现实层面的“作”。杨国荣在讨论“事”与“史”的关系时指出:“意识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运用语言以凝结和传递思想,由此进一步影响历史,都属广义的人之所‘作’,它们同时构成了历史视域中‘心灵所做的事’的一般特点。”⑥杨国荣:《人与世界:以事观之》,第205页。历史视域中“心灵所做的事”,既包含观念层面的“作”,也包含现实层面的“作”。章学诚讲“史学所以经世”⑦章学诚:《浙东学术》,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22页。,这无疑是强调现实层面的“作”。仓修良解释说,“六经皆史”的“史”,既具有“史料”之史的内容,又具有“经世”之史的内容:“孔子删订《六经》,目的在于‘存道’‘明道’‘以训后世’,让后人从先王政典中得知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⑧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4页。史学经世,乃是即事明道资治。就过程而言,这是以书行事;就结果而言,这是以书取效。
历史撰述以书行事,不仅可以经世(成物),还可以对作史者自身产生影响(成己)。章学诚引“立德、立功、立言”分疏著述行事所取之效:“语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人生不朽之三,固该本末兼内外而言之也。鄙人则谓著述一途,亦有三者之别:主义理者,著述之立德者也;主考订者,著述之立功者也;主文辞者,著述之立言者也。”⑨章学诚:《答沈枫墀论学》,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14页。立德、立功、立言,是著述的成物之效;反诸己,则由此三种“效”实现人生之不朽和生存意义之安顿,此乃以著述行事的成己之效。进而言之,成己之效,意味着三种人性能力在著述这一做事过程中的自我成就,因为考订、词章、义理相应于人的才、学、识,有待于“积”“扩”“达”的努力:“由风尚之所成言之,则曰考订、词章、义理;由吾人之所具言之,则才、学、识也;由童蒙之初启言之,则记性、作性、悟性也。考订主于学,辞章主于才,义理主于识,人当自辨其所长矣;记性积而成学,作性扩而成才,悟性达而为识,虽童蒙可与入德,又知斯道之不远人矣。”①章学诚:《答沈枫墀论学》,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13页。
历史撰述在双重意义上做事:通过观念层面的“作”达到现实层面的“作”。那么,这是如何发生的?章学诚讲,“撰述欲来者之兴起”②章学诚:《书教下》,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36 页。章学诚将“撰述”与“记注”相对立:“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记注仅关注史料,已非完整意义上的史学著述。“六经皆史”所立之史,既与经学意义上的经(离事解道)相对,又与记注意义上的史(离道解事)相对。赵汀阳释“六经皆史”:“经为史提供了精神依据,史让经的精神获得生命。”见氏著《历史·山水·渔樵》,第2页。这里的“经”“史”可能正是经学意义上的经和记注意义上的史。。所谓“来者之兴起”,乃是后来者在读史的过程中得到激发,进而在现实世界中有所作为。诗可以兴,史亦可以兴。观念层面的“作”属于作史者,现实层面的“作”属于读史的来者,二者以兴发为中介。从事实与价值的关系来看,历史撰述即事明道,乃是通过价值赋义将客观史实转变为精神实在③赵汀阳探讨了历史真相与历史所创造的精神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历史去建构一个精神世界,虽然超越了知识论问题,但并不是说,历史无关真相,而是说,历史的真相以及想象一起共同创造了一个精神世界,共同建构了一个文明立身所需的形象、思想、经验、忠告、情感和记忆。”氏著《历史·山水·渔樵》,第39页。。作史者向来者传递精神实在,而来者的“兴起”,即是接受精神实在的价值规范与精神激发,获得经世致用、改变世界的命题性知识(knowing-that)、能力之知(knowing-how)与动力之知(knowing-to)。其中,命题性知识是关于理智的知识,比如道是什么;能力之知是关于能力的知识,比如如何行道;动力之知是激发行动的知识,比如要去行道。
四、神解与效法:在经典中即事明道
“六经皆史”说批评以训诂考覈求道的经学方法。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恰当地对待往圣先贤的著述?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作史者即事明道,也就是说,通过明述事的方式显示道;与之相应,读史者,亦须即事明道,也就是说,透过关于事的明述之言来把握显示其中的道。道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学术文章,有神妙之境焉。末学肤受,泥迹以求之;其真知者,以谓中有神妙,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者也。”④章学诚:《辨似》,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58页。《论语·公冶长》记子贡之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章学诚解释说:“盖夫子所言,无非性与天道,而未尝表而著之曰,此‘性’也,此‘天道’也。故不曰‘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而曰‘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也’。”⑤章学诚:《原道下》,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04页。“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也”,因为性与天道不可言传(表而著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性与天道”本身不可得闻,因为性与天道仍可意会。性与天道属于形上智慧,可意会不可言传。同样,属于实践智慧的经纬世宙与政教典章亦是可意会不可言传。从知识的分类来说,可言传的是明述知识(explicit knowledge),不可言传可意会的是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就人性能力而言,把握默会知识需要“神解”、技能、鉴别力、判断力、理解力等默会能力(tacit powers)⑥关于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的系统研究,可参见郁振华:《人类知识的默会维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自然,“神解”这种默会能力见于章学诚而不见于波兰尼等西方哲学家的讨论之中。。在此意义上,经学态度之所以不足以发明六经所载之道,在于误将关于道的默会知识当作明述知识,而对于神解等默会能力认识不足。
意会者,会意是也,所谓“善读古人之书,尤贵心知其意”⑦章学诚:《言公下》,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216页。。作史者即事明道,“道”乃是作史者意之所在,即所要传达的意图。作史者以道为意,后来者便须领会此“道意”。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分析,我们说出或写出一个句子,想表达一个意思,这构成了这个句子的话语意义(不妨称为“语意”,意者,想表达的意义,或者说带有意向性的意义)。这个句子首先要合乎文法,别人能听得懂。换言之,它要具有语句意义(不妨称为“语义”)。一个句子的语句意义由字词的意义和字词在语句中的组合所决定,但同一个句子可以表达不同的意思。话语意义固然基于语句意义,但又比后者多出一些东西。一个句子的话语意义,即说话者在说出或写出这句话时想表达的意思,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说话者的表达意图①参见[美]约翰·塞尔著,李步楼译:《心灵、语言和社会》,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33—148页。。从读者或听者的角度来看,理解一句话就需要在把握语义的基础上把握语意。如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依前引《文史通义·原道中》,这句话的语义是:“夫子尽周公之道而明其教于万世,夫子未尝自为说也。表章六籍,存周公之旧典。”但要理解它,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追问其语意:究竟是夫子“推尊先王,意存谦牧而不自作也”?还是孔子表达“不得位而行道,述六经以垂教于万世”的“不得已”窘境?通过“语意”和“语义”的区分可以看出,无论是经学家以训诂考覈求道的主张,还是戴震“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基本纲领,都误将“语意”(话语意义)化约为“语义”(语句意义)。
章学诚曾自述,二十岁是个人精神发展上的分水岭(“吾之廿岁后与廿岁前不类出于一人”②章学诚:《家书六》,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824页。),是年发生了一件关乎心智成长的大事,其中便蕴含了对语意和语义之分别的觉解。章学诚写道,二十岁时读到庾信“春水望桃花”,吴兆宣注引《月令章句》:“三月桃花下。”其父抹去吴注而评曰:“望桃花于春水之中,神思何其绵邈!”他当时“便觉有会”。章学诚所“会”者,父注与吴注之别,而二者之别,实乃吴注在语义上求解(春水中何以有桃花),而父注在语意上求解(诗人通过写春水中之桃花寄托绵邈之神思)。经此领会,章学诚对自身的才质特点(自身人性能力的过人之处)有了明确自觉,同时也明确了超越训诂考覈、以神解精识得古人撰述之意的经典阅读方法:“自后观书,遂能别出意见,不为训诂牢笼,虽时有卤莽之弊,而古人大体,乃实有所窥。”“吾读古人文字,高明有余,沉潜不足,故于训诂考质,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识,乃能窥及前人所未到处。”③章学诚:《家书三》,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819页。
把握“语意”需要“神解”这一默会能力。这种作为悟性的理智德性能够直觉意义整体,用章学诚的话说,具有“全”的特点。他说:“理之初见,毋论智愚与贤不肖不甚远也;再思之,则恍惚而不可恃矣;三思之,则眩惑而若夺之矣。非再三之力转不如初也。初见立乎其外,故神全;再三则入乎其中,而身已从其旋折也。必尽其旋折,而后复得初见之至境矣。故学问不可以惮烦也。然当身从旋折之际,神无初见之全,必时时忆其初见,以为恍惚眩惑之指南焉,庶几哉有以复其初也。”④章学诚:《辨似》,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58页。“初见”文本,凭神解得理之全,窥见古人大体。“再思”“三思”入乎其中,对于细节有更深入的理解,但与此同时也会失去对意义整体的把握,故而需要努力保持“初见”时得理之全的神解。章学诚此说无疑强调了对文本意义整体的理解先于对部分的理解,而且这里的“先于”既是时间在先又是逻辑在先。然而,此论也有不充分之处:在实际的诠释过程中,整体—部分之间存在循环,对部分的理解也会反作用于对整体的理解,其中包括修正甚至推翻对整体的理解的可能性⑤章益国将章学诚与戴震相比较:“戴震的‘字→词→道’,三者构成水平轴上的提喻关系,而章学诚的‘初见之全’和‘再思’‘三思’,三者保持了纵轴上的、‘相似’的等阶关系,相互比观、构成了诠释的循环。”章益国:《道公学私:章学诚思想研究》,第161 页。此说甚有启发。不过,按笔者之见,章学诚片面强调“初见之全”的先在性,“初见之全”和“再思”“三思”尚未构成整体—部分之间的诠释学循环。。对整体的理解也有可能出错,换言之,“神解”有时候也是靠不住的。实际上,章学诚讲自己不为训诂牢笼,于古人大体实有所窥的时候,也提到“时有卤莽之弊”。“卤莽”者,神解出错了,直觉有可能只是错觉。
分而言之,一方面,“神解”“精识”,一是作为悟性的默会能力,一是此默会能力发用而实现的精神成就,所谓“悟性达而为识”。另一方面,“达”的过程性也意味着,从神解到精识,仅有直觉是不充分的,还需要理智“再思”“三思”的艰苦劳作。其中最重要的类比思维,章学诚所谓“学者之要,贵乎知类”。他举例说,《易》之象,《诗》之兴,《礼》之官,《春秋》之例,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其理仍是一以贯之的通于类①章学诚:《易教下》,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6页。。知类为什么重要?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看,这是因为“类比思维或范例推论是有效地传递或获得默会能力的基本方式”②郁振华:《人类知识的默会维度》,第228页。。
然而,从神解到精识,直觉加上理智的“再思”“三思”依然是不够的,因为“精识”之为精神成就超出了纯粹的理智成就。如前所述,作史者向来者传递精神实在,而来者的“兴起”,即接受精神实在的价值规范与精神激发,获得经世致用、改变世界的命题性知识、能力之知与动力之知。如果说,命题性知识是理智之事,那么能力之知与动力之知乃是超乎理智的实践智慧。实践智慧的习得,最有效的办法乃是通过范例学习,所谓“学也者,效法之谓也”。所谓“效法”,首先指圣人“效法于成象”,使自己的行为从容中道,合乎“无过与不及”的标准(“准”):“盖天之生人,莫不赋之以仁义礼智之性,天德也;莫不纳之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伦,天位也。以天德而修天位,虽事物未交隐微之地,已有适当其可,而无过与不及之准焉,所谓成象也。平日体其象,事至物交,一如其准以赴之,所谓效法也。”进而士希贤、贤希圣,士与贤效法圣人,学习像圣人那样使自己的行为从容中道,合乎“无过与不及”的标准(“准”)。士与贤如何效法圣人?“必观于生民以来,备天德之纯而造天位之极者,求其前言往行,所以处夫穷变通久者而多识之,而后有以自得所谓成象者,而善其效法也。”③章学诚:《原学上》,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08页。效法圣人,以圣人的“前言往行”为范例,设身处地地体会圣人在“穷变通久”等不同的境地中如何自处,这样才能对于圣人之“效法于成象”有所“自得”,进而在自己碰到的“事至物交”的情形下,像圣人那样从容中道,“一如其准以赴之”。这正是以圣人为范例,通过其言行学会时中的实践智慧。
结 语
我们身处后经学时代。冯友兰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以董仲舒为界,将中国古代哲学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二期。作为时代标志的“经学”,主要是一种精神、态度或方法④杨国荣区分了经学的两重内容:其一属于广义的文献之学,与文献的研究相关;其二“与价值取向相联系,表现为具有某种意识形态功能的观念形态”(杨国荣:《经典、经学与经典之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作为时代标志的“经学”,侧重于杨国荣所讲的经学的第二重内容。他又认为:“经学既具有学术的意义,也表现为一种思想观念,经学的秩序关切与政治品格,主要与后者相关。”(杨国荣:《经学的历史形态与现代走向》,《光明日报》2023 年9 月23日第11版)依此分疏,作为时代标志的“经学”侧重于思想观念的意义。。经学时代的哲学家,其说无论新旧,总是依傍古人,尤其是依傍经学而证其真。中国现代为经学时代之后的“新时代”,此时哲学家可“撇开经学而自发表思想”⑤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43,343页。。就其主流而言,“新时代”乃是走出经学时代的“后经学时代”。
不过,“前时代之结束,与后时代之开始,常相交互错综”;表现出来的一个方面,已如冯友兰所说,“在前时代将结束之时,后时代之主流,即已发现”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43,343页。。冯友兰未言明的另一方面则是,在后时代开始之后,前时代之余流,仍残存其中。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可以注意的是,后经学时代虽已走出经学,但作为精神、态度或方法的经学仍残存其中,有时甚至出现由余流、潜流跃升为一时之主流的反常现象。比如,随着马克思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出现了以经学方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倾向;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儒家思想的复兴,也出现了某种以经学方法对待儒家思想的倾向。在一定意义上,时时反思经学方法,避免“以‘定于一尊’的态度来对待各家(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学派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派)”⑦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冯契文集》(增订版)第7卷,第652页。,乃是后经学时代保持“后经学”状态的必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