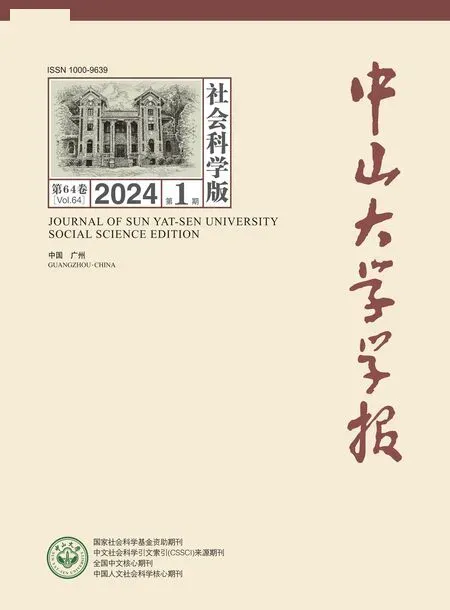极性与折叠:论谢林“同一哲学”的辩证结构 *
王 丁
尽管在谢林的晚期哲学中,他对黑格尔的批判及其所包含的关于存在概念的更深刻的辩证法已逐渐为人所知①详见王丁:《存在何以“不可预思”》,《哲学研究》2022年第6期。,但关于他早期哲学的辩证法仍然笼罩在黑格尔判词的阴影里。实际上公允地看,倘若一个哲学家要以“大全一体”的方式去构造一个体系,那很难设想他会为了这个目的竟不去设想与之相对应的“辩证法”。毕竟一般地看,“大全一体”就意味着一切在一之中存在,同时一也在一切之中存在,这就要求一和一切在其中绝不处在一种还原关系中。否则“体系”就会自身坍缩为一个黑洞,而非谢林一直强调的“宇宙”②这个词在谢林的语境中的意思就是一切在一中存在的整体。。有些学者沿着黑格尔对谢林的批判,以及谢林之后的语焉不详的回应出发,把谢林早期体系,也就是“同一哲学”体系中表面上看来阙如的“同一与差异”问题视为谢林中晚期哲学的核心推动要素③参见[德]菲利普·施瓦布(Philipp Schwab)著,王丁译:《从原则到无定者——从与黑格尔的争辩看谢林“世界时代”与“埃尔朗根讲座”中的体系概念》,《哲学评论》第22辑,长沙:岳麓书社,2018年,第75—95页。。但他们完全忽略了,谢林在《近代哲学史》中把黑格尔哲学视为通向一种真正“大全一体”哲学的“插曲”④[德]谢林著,先刚译:《近代哲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54页。。尽管谢林对黑格尔的如此评价有待商榷,但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有必要澄清谢林在“同一哲学”时期的辩证法结构,进而才可以看清,他与黑格尔的争论和分歧究竟在哪里。事实上可以认为,谢林与黑格尔之争实则是围绕关于“大全一体”体系建构的两种方案之争,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和《哲学史讲演录》中的批判,很容易让人以为谢林的“同一哲学”是一种缺乏思辨性内在结构的“神秘主义”或“浪漫主义”。但事实并非如此,黑格尔的这种误判实际上是来自一种源自费希特、对“理智直观”概念的惯性误解,只有澄清了这个概念在谢林哲学中的含义,谢林“同一哲学”的辩证法结构才会清晰呈现。而且从这一路径出发还能看到,谢林的早—晚期哲学并没有像通常认为的那样有一种仿佛断裂的转折关系,反倒一如既往地在贯彻他从早期就开始阐发、不同于黑格尔的“肯定辩证法”。而这一辩证法最大的特质就在于它的极性展开和折叠结构。
一、可疑的黑格尔的批判
综合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和《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对谢林的批判,可以得出黑格尔针对谢林的几个一以贯之的论点,首先是关于“理智直观”:
谢林哲学一方面从费希特哲学出发,另一方面像雅各比那样,以直接知识为原则……这种理智直观的内容或对象现在仍然是绝对、上帝、自在自为的存在者……谢林的哲学是从直接的知识,理智的直观开始。①[德]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等译:《哲学史讲演录》卷4,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386,397页。
如果说还有第三种情况,即思维把实体的存在与自己合并,并把直接性或直观活动理解为一种思维,那么我们还得看看,这种理智直观是不是重新堕落为一种僵化的单纯性。②[德]黑格尔著,先刚译:《精神现象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1页。
从黑格尔的判词来看,首先可以明确,在他看来谢林的“理智直观”概念是一种有内容的直接知识。一方面它类似于费希特那里的理智直观概念,即自我自身的行动就是对其存在的充实,反之亦然。因此这是一种对于体系开端及其第一原理的直接确知和确证。另一方面它也类似于雅各比强调的直接知识,即它是一种不可再行追溯的直接被给定的内容。但考虑到黑格尔这里所引用考察的乃是谢林的《先验唯心论体系》,所以不可以把这里的“从费希特出发”视为谢林早期哲学体系本身的一般性特质。实际上不仅谢林本人在《先验唯心论体系》中已经强调过,这里要考察的是已然作为“体系”进而完结了的“先验唯心论”,而不是要以之为整个体系的出发点或者模板③可参见王丁:《谢林的政治哲学期待》,《云南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在1801 年首次阐发自己的“同一哲学”之际,谢林就尤其强调:
在把自己多年来视为真正哲学的唯一一门哲学,试着从两个完全不同的方面阐述为自然哲学和先验哲学之后,我现在感到由于科学的当今状况所迫,不得不比我自己想得更早地把体系自身(它为我做出的许多不同阐述奠定了基础)公之于众。④[德]谢林著,王丁译:《对我的哲学体系的阐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3页。
所以从谢林自己的话来看,黑格尔对于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的评述,不能运用到对于以1801 年阐述为起点的“同一哲学”上。但如果继续追溯《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对“同一哲学”的评述,可以发现他仍然处在一种解读的“惯性”中:“正如费希特从自我=自我开始,谢林也同样从绝对直观出发,把它作为命题或定义来表述……在其中一切对立都完全消除了。”⑤[德]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等译:《哲学史讲演录》卷4,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386,397页。所以无论如何可以看到,不管是出于“故意”也好,还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哲学史叙事也必须把谢林哲学如此定位也好,黑格尔仍然是把《先验唯心论体系》与“同一哲学”做了连续化的处理。黑格尔在这里所批判和评述的着眼点除了把“绝对直观”或者“理智直观”与费希特的“自我=自我”等而视之,还有一点就是认为这是一个体系的内在“出发点”。从这一处理出发,才能把《哲学史讲演录》与《精神现象学》关联起来。正如黑格尔认为在费希特那里,自我=自我的三重体(知识学的三个基本命题)会“重复”在以之为出发点的整个体系展开过程里。他也同样认为在谢林那里,以A=A 为“起点”的潜能阶次公式并不是“同一个东西自行分化为众多相互有别的形态,毋宁说这是同一个东西的杂乱重复……(是)同一个公式的单调重复”①[德]黑格尔著,先刚译:《精神现象学》,第9,10,9,13页。。因此这就是一种“单调的形式主义”,这种形式主义“把差别和规定抛入空洞的深渊”,因此这种知识“与那种作出区分并得到充实的认识……相对立”,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才说出了那句名言“黑夜里的牛都是黑的”②[德]黑格尔著,先刚译:《精神现象学》,第9,10,9,13页。。
对于黑格尔的这一整个结论,必须仔细看待。首先可以明确,黑格尔认为谢林“同一哲学”的起点和费希特知识学的起点都是一个自明的、已然自身充实的开端。但正是这种已然完成了的开端的自身充实,导致体系的演进成了一种形式主义的重复:“如果发展意味着同一个公式的单调重复,那么那个原本真实的理念就将永远停留于开端了。”③[德]黑格尔著,先刚译:《精神现象学》,第9,10,9,13页。换句话说,开端的自身充实和自明,恰恰就让“发展”不可能了。众所周知,黑格尔所要求的恰恰是发展中的知识,以及作为全体的真理,而非从自明起点出发的“重复”的形式主义。其次也可以看到,这一点恰恰要求,为了防止“黑夜里的牛”,知识的开端既不能是自明和自身已然充实的,因而同时也必须是最贫乏的。在这种意义上黑格尔才可以说,“绝对者在本质上是一个结果……开端、本原或绝对者,最初直接说出来的时候,仅仅是一个普遍者”,这样的词语必须转变为“更丰富的东西”,也就是一个自否定的进而自身中介的命题展开系统④[德]黑格尔著,先刚译:《精神现象学》,第9,10,9,13页。。所以有待讨论的问题就是:1.谢林在“同一哲学”中是否采用了与费希特意义上等同的“理智直观”起点;2. 如果抛开黑格尔对于体系=发展的知识整体的基本意图不谈,那么在解决了问题1的情况下,我们或许还可以问:一种不以此理念为主导的体系在谢林那里是否可能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需要首先看看谢林本人在《近代哲学史》中对他与黑格尔之间这段公案的回顾,毕竟正是这一点导致了两人的决裂。在这个文本里,谢林首先就表示,自己在1801 年的那个“同一哲学的第一个原始文献里,‘理智直观’这个词语根本没有出现”⑤[德]谢林著,先刚译:《近代哲学史》,第177,178,178,180页。。从这一点出发至少可以推测,除了在1807 年的时候就已经阅读过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谢林在埃尔朗根大学和慕尼黑大学讲授这门“近代哲学史”的时候,至少也了解到了黑格尔的哲学史课程,毕竟黑格尔在其中也只参考了这个1801 年的“第一个原始文献”,而且也以为其开端是“理智直观”。谢林紧接着回应了我们上面总结的第1个问题:“(费希特)希望通过理智直观来确保自我是一个直接确定的东西,亦即一个无可置疑的存在者。‘理智直观’所表达的意思,恰恰就是伴随着一种直接的确定性而说出来的‘我存在’。”⑥[德]谢林著,先刚译:《近代哲学史》,第177,178,178,180页。所以他也很明确地意识到了,理智直观在费希特那里完全还是在沿着近代哲学的先验进路,描述某个自明且自身充实的开端的存在状态。谢林强调,在自己那里理智直观的意思则是一种“摆脱主体”的活动,也就是要通过理智直观“提炼出来的普遍、无规定的主体—客体”⑦[德]谢林著,先刚译:《近代哲学史》,第177,178,178,180页。。所以在费希特那里,理智直观之所以是理智直观,不外乎自我就其活动方式而言,与自身作为存在者并无任何中介活动,其存在的直接性就是其反思活动,故而偏向于“直观”的直接义。但在谢林这里,这个概念的目标并不在于有某种已然充实内容且具有自身规定性的确定“开端”,而是强调一种无处不在的“主体—客体”的存在形式,所以其侧重点在于“理智”。而且这里更关键的一点在于,这种存在形式自身就是极性的,或者说,自身就具有一种思辨性。如果说在黑格尔那里,重点是要强调一种开端空洞的知识发展整体,而且基本运动模式就是“主体即实体”,那么黑格尔的辩证法也需要一种内在于一切的极性存在模式。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谢林感到非常“冤枉”,认为自己与黑格尔并无不同:“黑格尔想要的不是一个单纯的绝对者,而是一个存在着的绝对者”⑧[德]谢林著,先刚译:《近代哲学史》,第177,178,178,180页。。倘若真如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里认为的,谢林“与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者有共同之处,把知识放在对永恒理念的内心直观里”⑨[德]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等译:《哲学史讲演录》卷4,第398页。,那谢林何必要强调自己对于黑格尔的这种“同情理解”呢?他对此同时也主动区分了他的三个常被混淆的术语:a. 绝对者乃是“最终的东西,纯粹的结果”;b.“贯穿于整体的东西……是‘绝对同一性’,以避免让人想到任何基体或实体”;c. 开端则是“无差别”,但这也意味着,它会凭着主体—客体的极性结构指向差别,因此“无差别”的真正概念乃是“平衡”,即能进行主体化和客体化的“能”①[德]谢林著,王丁译:《近代哲学史》,第180、175页。。
所以总体来看,且不论谢林在《近代哲学史》中的这番澄清是否真的“切合”他在确立“同一哲学”之初的意思,抑或是为了矫饰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在他心中种下的毒刺而作的一种自我修正。但无论如何可以看到,理智直观概念并不像黑格尔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已然充实的自明开端,它并不具有任何“内容”。但这种缺乏内容和规定也同样意味着这是一种极性的存在基本结构。从谢林本人的这番回顾中我们至少可以确认,“同一哲学”本身的结构是主体—客体的存在结构,它才是谢林意义上的“理智直观”的相关项。同一哲学的目的并非抽象的“绝对者”,而是“存在着的绝对者”——即经历了这整个极性结构的绝对者,而非“单纯的绝对者”——而它的开端则是“无差别”,而非费希特意义上作为自我的理智直观。所以现在需要讨论问题2,即倘若真如谢林所说,黑格尔以为他所缺乏的体系要素,他自己的体系都拥有,那这个体系是如何运作的?
二、隐匿的折叠结构
在1801年第一次阐述“同一哲学”之际,当时年轻气盛的谢林多少都有为了立刻与费希特划清界限而故意“戏仿”斯宾诺莎的意思,比如以挑衅的语气说“要以斯宾诺莎为楷模”②[德]谢林著,王丁译:《对我的哲学体系的阐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9,11页。,毕竟费希特曾经明确表示斯宾诺莎的体系完全超出了知识学的批判主义的界限③[德]费希特著,王玖兴译:《全部知识学的基础》,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7页。。所以仅凭1801 年的第一次阐述,我们很难得出与黑格尔同样的结论,即“谢林又把斯宾诺莎的实体、简单的绝对本质重新提出来。并且又重新给予了先验唯心主义以绝对唯心主义的意义”④[德]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等译:《哲学史讲演录》卷4,第396页。。通过前文现在已经可以知道,倘若斯宾诺莎意义上的实体被赋予了先验唯心主义的意义,那就会落入黑格尔所误解的费希特意义的理智直观概念中。而谢林在《近代哲学史》中的“自辩”也恰恰可以在1801年的这个文本开头处找到:
理性必须从思想者那里被抽离出来。对于进行这种抽离活动的人来说,理性会直接终止朝向某种主体性之物,而大多数人都以为,理性就是指向某种主体性之物的,在这种情况下,理性自身当然也不再可能被设想为某种客体性之物,因为某种客体性之物或者被思想的东西唯有在与思想者的对立中才是可能的,而在这里,理性全然从作为思想者的主体中被抽离出来了。⑤[德]谢林著,王丁译:《对我的哲学体系的阐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9,11页。
尽管谢林在此确实没有使用“理智直观”的概念,但这个概念在谢林哲学中与其说是一个体系建构意义上的概念,不如说一直有稳定的语义,是一个进入体系的预备性概念。在1821年的“埃尔朗根讲授录”中,谢林就对此进行了一番总结性的定论:“正因为‘理智直观’这个表述首先还需要解释,所以把它弃置不用是更明智的。其实不如把这种状态描述为‘绽出迷狂’(Ekstase)。它意味着我们的自我被设定在了自己之外。”⑥[德]谢林著,王丁译:《全部哲学的本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30—31页。所以根据谢林的“自辩”和对比这两处的语义可以看到,1801 年的“抽离”与1821 年的“绽出迷狂”实则是一个意思,即都是一种去自我化的活动,这种活动跟笛卡尔传统以来的任何自明性确证毫无关系。或许可以说黑格尔“蒙”对了,但对于这种抽离—理智直观的意思,黑格尔完全理解错了。此外,在1821 年对“理智直观”的说明中,谢林还尤其强调,若要获得真正的哲学态度,必须“离弃……一切尚还是一个‘存在者’的东西……甚至还要离弃那个恒在的存在者,也就是离弃神……即便神也不过是一个存在者而已”①[德]谢林著,王丁译:《全部哲学的本原》,第13页。。所以如果继续按谢林的自辩来看,倘若这个体系的基本结构和贯穿一切的法则是“绝对同一性”,那么它除了是一种普遍结构以外,不可能是任何一个具有自身性和自明性的存在者。反过来也可以说,任何一个在某种角度看来最具备绝对同一性的存在者,不管是费希特意义上的“自我”还是黑格尔所误会的“神”或者“绝对者”,都不过是对绝对同一性的某种聚集或者呈现,而绝不是它自身。因此完全可以认为,如果套用海德格尔的说法,谢林的“同一哲学”体系建构和黑格尔一样,都不是从存在者出发,而是从某个超出但同时也内在于一切存在者、并让存在者得以可能的法则出发的。
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继续沿着谢林的阐述,这个“绝对同一性”的体系建构作用又是如何呈现的?在1801 年的阐述中,谢林以模仿斯宾诺莎并“戏仿”费希特的方式对之进行了一种常常让人误解的说明:“既然理性之外无物存在,那么对理性存在而言的最高法则,进而对一切存在而言的最高法则(既然一切都是在理性中被把握的),乃是同一性法则,这一关联于一切存在的法则由A=A 来表达。”②[德]谢林著,王丁译:《对我的哲学体系的阐述》,第13,14,18,19页。正是由于这句话,“绝对同一性”不仅在黑格尔那里,而且常常也在后世学者那里被误解为“同一律”。但如果首先联系这里所谓的“理性”的语义——即不附着于任何一物但能够使某物成其自身者,那首先可以明确这种所谓的“一切存在的法则”是一种内在性的法则,而A=A 仅仅是它的表达。因此谢林紧接着就强调:“A=A 这个命题,普遍地来设想,说的既不是A 本身,也不是作为主体,或者作为谓词存在的A。相反,通过这个命题设定的唯一存在,就是同一性自身的存在。”③[德]谢林著,王丁译:《对我的哲学体系的阐述》,第13,14,18,19页。倘若这个命题强调的是某个主体或者谓词的A,那就会落入费希特那里的自我始终等同的——尽管这种等同是思辨的——层次上。而既然这里的重点是中间的“=”号,那么这个“=”号很明显就不是所谓的“黑夜里的牛”,而是一种普遍的内在性。紧接着谢林又补充了两个命题:1.“绝对同一性不能被设想为是通过命题A=A 被设定的,但它是通过这个命题被设定为存在着的”;2.“跟命题形式A=A 同时一道被设定的,也是跟绝对同一性自身的存在一道被直接设定的,但它并不属于绝对同一性的本质,而是只属于其存在的形式或者方式”④[德]谢林著,王丁译:《对我的哲学体系的阐述》,第13,14,18,19页。。从命题1可以看到,命题A=A 跟绝对同一性这个整体性的内在原则绝非同一回事,但如果这个内在性原则只有通过A=A 才是“存在着的”,那可以认为,A=A 属于“存在者”的层面。换句话说,绝对同一性是要通过A=A来“映现”或者说“指引”,尽管它超越于一切存在者乃至最高的存在者,但如果它不是一个抽象的黑夜和内在性原则,那它就必须在一切身上呈现。而从命题2 也可以看到,谢林也严格强调这一区分,即绝对同一性的“形式”或者说呈现就表达在这个命题里,但这个命题绝非绝对同一性自身。可以认为,谢林在这里始终保持着同一性和分有了同一性的同一者的区分,因而绝对同一性的构造仍可以套用于海德格尔的存在—存在者的区分与统一关系上。但更为重要的是第三和第四个命题:
在主体位置上和在谓词位置上被设定的,是相同的整全的A。
绝对同一性唯有在同一性的同一性这一形式下才存在。因为绝对同一性唯有在命题A=A 的形式下存在,而这一形式与其存在是同时被设定的。但在命题A=A 中,相同者跟自身是相同的,也就是说,被设定的乃是同一性的同一性。也就是说,绝对同一性唯有作为同一性的同一性而存在,这是绝对同一性不可与存在自身相分裂的存在形式。⑤[德]谢林著,王丁译:《对我的哲学体系的阐述》,第13,14,18,19页。
在这里,论说的对象发生了陡然的变化。如果说前面几个命题讨论的仍是“=”号,那么在这里,对主体—主词和谓词位置的设定就沿着关于“形式”—存在者的一端开始了讨论。倘若有某个存在者之一般A,在绝对同一性的整体结构中存在,并且这种存在是能够构造作为体系的一切即一的存在,那这里所讨论的A 就必定不是具体的某个东西,而只能说是一个X,或者说“某物”。而且如果它无论是在主体—主词还是在谓词的位置上都是相同者,那么不管这个X 是什么,都是在回应谢林在1801 年阐述的开头所说的基本目标,即所谓的“先验哲学”和“自然哲学”都是同一哲学的片面的方面。也就是说,倘若某个X是先验哲学中的对象,那它必定同时也是自然哲学中的对象。换句话说,即便是在存在者的层面来考察A=A,那依然可认为这中间的“=”号仍具有一种非还原的思辨结构。但这种“同时”关系也需要下一个命题的补充,这里的重点在于,绝对同一性作为贯穿于一切的整体内在性的“本质”,与在存在者一端的一并呈现的作为“形式”的同一性一道,才是“同一哲学”体系建构中的真正结构。倘若这里所谓的整体内在性和存在形式是分离的,那就会堕入一种高级的神秘主义中,仿佛万物尽管都在映现真理,但这种映现也只是扭曲,万物自身都不是它的真实映现而仅仅是倒影,万物的存在仿佛就是对真理的某种犯罪。尽管是真理让它们存在,但它们仿佛把真理剥夺为了自己存在的形式,因此唯有“抽离”于它们,才能返回作为本质的绝对同一性。这或许也是黑格尔把谢林的同一哲学误解为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变体的一个根源。
但这里的后一个命题,显然强调了本质和存在的同一性才是绝对同一性的真正概念,或者说存在和存在者的同一性才是真正的要讨论的东西。所以在命题A=A 中设定的其实是三个东西:a. 绝对同一性,即那个“=”号;b. 存在之一般A,它在绝对同一性中总是以一种非还原的、可以分化在先验哲学与自然哲学之中的方式与自身等同;c. 但这种等同方式并不在于绝对同一性和存在者之一般的等同,而是在于,存在者之一般的存在就是绝对同一性的同一性,绝对同一性自身“进入”了对于任一存在者的构造中,主词—主体一端的A和谓词一端的A的同一性本身也包含了绝对同一性。因此尽管可以说,作为本质的绝对同一性超越于一切、抽离于一切,但它必须在存在者的存在中才“存在着”,因此,存在者的存在尽管不是绝对同一性自身,但仍是“同一性的同一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看到同一性概念发生了两次折叠,并且只有经过了这两次折叠的同一性概念才是绝对同一性。换句话说,绝对同一性的“绝对性”尽管一方面体现在它超越于一切存在者,但也同时体现在它内在于一切存在者中,这就意味着,这种绝对性同时也关涉于一种与存在者的自身规定性相关的有限性,更关涉那个让谢林当时看来两种分立且对立的不同科学之间的同一性。
所以总体来看,如果说黑格尔体系的基本法则是通过开端自身的空洞,以及“主体即实体”的否定性思辨方式进行体系整体的演进。那么通过回顾谢林1801年体系的几个主要命题,仍能发现至少以下几点:1. 体系开端其实就是理性自身,“理智直观”无非是为了防御费希特式的自明方案进行的一种去主体化活动,并非体系自身的开端;2. 理性自身,也就是绝对同一性同时折叠为了作为“本质”、进而超越于一切的同一性,即“=”号和折叠在一切存在者自身中,与其形式同一的“同一性的同一性”;3. 所以所有以上命题所呈现的都是同一性自身的绝对性,或者说真正的“绝对同一性”概念乃是自身无限的同一性与折叠入有限者、并作为其存在法则的“存在着的”同一性的同一性;4.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谢林1801年体系阐述所表达出来的基本体系结构乃是超越与内在的同一,或者说作为超越者的同一性与作为内在法则的同一性的同一性①笔者之前也将之表达为“三阶的同一性”,但可以看到从谢林1801 年的阐述出发,这一表述仍然成立。详见王丁:《存在何以“不可预思”》,《哲学研究》2022年第6期。。所以正如后来他在《斯图加特私人讲授录》中总结的:“同一个同一性也是A=A(形式)里面的系词。”②[德]谢林著,先刚译:《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及相关对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16页。但此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如果说,绝对同一性A 和它的存在形式A=A 之间的这种超越—内在的同一性仍具有同一性,那么这个意义上的同一性就需要将自身极性化为两端,也就是作为超越者的同一性和作为形式的同一性必须以某种方式是作为它们之间系词的同一性的另一重呈现,这又该如何解决呢?
三、从折叠到极性:导向晚期哲学的问题
在这里仿佛陷入了一种无穷的倒退:如果我们认识的出发点是通过理智直观的抽离活动得出的那个作为“本质”的同一性,而它也不过是“绝对同一性”的超越性一端,且真正的“绝对同一性”概念是它与内在于存在者中、作为“形式”的同一性间的同一性,那就意味着,我们的理智永远不能达至一个确凿的科学的开端,我们的理智无论怎么逃逸有限者,最终仍会发现自身处在一个与有限者的构造相伴生、已然自身折叠了的同一性结构中。但这种倒退或者说循环仍然是积极的,这也正是谢林超越了先验哲学传统和费希特式先验唯心主义的地方,更是他有理由在黑格尔面前“叫屈”的地方。在1821 年的“埃尔朗根讲座”中,谢林最终对这种循环或者倒退直言不讳:“除了从永恒自由中走出(永恒自由即1821年语境中的“绝对理性”),为此而生的科学也没有其他道路;可倘若没有对永恒自由的知识,科学也不可能从它出发。”①[德]谢林著,王丁译:《全部哲学的本原》,第28页。所以无论如何可以看到,谢林与黑格尔一样,都认为科学体系自身并无一个确凿的“开端”。人类知识的开端乃是一个在体系中已然开端的开端,理智直观也好,绽出迷狂也好,都是为了让人类从“我知”回归体系自身的运动洪流中。而体系自身的运动也同样总是已经开端,人类知识的开端绝非体系自身的开端。
但这样就留下了两个问题:1. 同一性的折叠不仅是超出一切的它自身与内在于一切的它自身的同一性;2.“理智直观”的必要预设了,体系与人类知识活动本身也具有一种相对峙的关系。对于这种关系,谢林惯用的例子是“磁体”。在每一个磁体上,都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标出南极和北极,但这种极性是相对而非固定的,并且磁体作为磁体存在,必须存在于这种极性中。倘若没有极性,极性就不作为磁体而“存在着”了。在谢林看来,这就是绝对同一性的最初“图型”。这一图型的特点在于,绝对同一性=磁性不仅是磁体整体,而且也内在于每一个极点中,极点的极性和对立恰恰在于绝对同一性内在于它们之中。在这里,任何一个极性自身是有限的,一方面它自身不过是绝对同一性—磁性本身的一种片面呈现,另一方面它也只有在与另一重极性的对立中才成其自身。相比于任一极性,磁性本身仿佛是无限的。就如同相比于任何一个存在者自身,仿佛从它们那里抽离而得、作为理智直观相关项的绝对同一性才是无限的。但这种无限性就和作为“本质”的绝对同一性一样,缺乏使它能够“存在着的”形式。因此真正整全的磁体就如同真正的、作为“同一性的同一性”一样,乃是前两者的总体性。在这个意义上,谢林也就把一切存在者区分为了三个基本的“潜能阶次”:
既然绝对性的形式始终且必然与自身等同并且总是这个与自身等同的形式,那么哲学作为整体,其一切个别的建构就都表达在双重的统一性中,这个统一性既是有限者(殊异者)中的统一性,也是无限者(普遍者)中的统一性,因而这个统一性就是这两种统一性的无差别;进而据此而言,倘若我们把观念上的规定(在本质相同的内在统一性上的规定)刻画为潜能阶次,那么哲学的形式整体,以及一切在个别环节中的建构,都可以回溯为“有限者”,“无限者”和“凭着对这两个潜能阶次的绝对等同设定而产生的永恒者”这三个潜能阶次上。②[德]谢林著,王丁译:《对我的哲学体系的阐述》,第231页。
从这一段可以明显看到绝对同一性的极性—思辨性构造:1. 首先是“双重的统一性”概念。在谢林哲学的语境中,不同于作为法则的同一性,统一性(Einheit)总是一个在多和一的关系中出现、并表明在一与多的对立中任意一方能够作为并保持自身而与另一方对立的原则。正因为有限者—殊异者—极性与无限者—普遍者—磁性的对立的前提,乃是每一方都作为自身且不—是对方。因此让双方各自成为自身的法则必须是同一种统一性,即让某物成“一”的能力。2. 也正因为两种统一性实则又根据同一种统一性而得以对立,因此实则两者也处在一种更高的整体中。3. 因此这个更高的整体,就是所谓的“永恒者”,实则是对前两者的一种肯定,在这种肯定中,前两者也得到了自身的存在,以及与这一存在相伴随的对立与统一。所以无论如何可以看到,所谓的绝对同一性在折叠之际也呈现出自身的极性,而只要这一结构能被刻画为这种极性,并从极性出发来理解。那就意味着这是一种肯定性的结构,因为不仅极性的双方以及在极性中活生生存在的磁性本身,必须通过那个“第三潜能阶次”肯定之前的两个。所以一开始的问题也就通过对这一极性结构的揭示回答了:同一哲学的体系建构法则及其包含的思辨关系,乃是一种肯定性的思辨关系,而非一种否定性的思辨关系。两者的不同点首先体现在:1. 在黑格尔那里,体系的演进乃是通过开端的贫乏来保持,也就是通过否定这种贫乏而在命题中进行自身终结,最终实现整体。而在谢林这里,体系的预备是揭示自明性起点的贫乏,但这种贫乏马上又转为了理性构造洪流中的充实。2. 贫乏—否定性的体系演进在于线性前进,而肯定—极性的体系展开则很难说是一种“演进”,毋宁说是绝对同一性的一种自身的内在性“复调”。3. 这种复调意味着绝对同一性必须不断去构造自身中各个层次的极性,进而产生出一种折叠性的无限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谢林才在数学和力学兼有的意义上把自己体系构造的基本单元称为“潜能阶次”,这个词在数学的乘方意义上,恰恰在表明着相同者在自身折叠的内在关系中的变化与创造性的肯定,按照德勒兹的说法,这是一种在谢林体系中“与辩证法完全对应的微分学”①德勒兹将之称为“谢林哲学中最重要的部分”,参见[法]德勒兹著,安靖、张子岳译:《差异与重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325 页。此外,曼弗雷德·弗兰克针对黑格尔的“重复”断语,用了“复现的同一性”(Reduplikative Identität)来刻画谢林的这种“微分学”结构,正如在微积分运算中,无限性总是作为运算的整体前提参与任何一个具体的运算并且使之可能,谢林的“同一性”结构的重点并非要去古希腊哲学传统意义上“一与多”的关系,而是要构造某物一方面成其自身,在成其自身之际也能在整体中存在,并且这种自身=整体存在的结构也能让某物脱离整体存在的总体结构。所以唯有同一性自身是“复现”的,才能保证整体—某物的归属与疏离结构。因此A=A 可以被扩写为A作为A=B 作为B,即同一性本身也是某物“作为”某物而获得自身性的前提,“作为”结构就是绝对同一性的存在方式。详见Manfred Frank, Reduplikative Identität, Stuttgar: frommann-holzboog, 2018, S. 123。。
前文已经提过谢林1821年阐发的一种“循环”,而这种“循环”也可以在极性关系中来理解。在那个循环中,“永恒自由”和“人类知识”构成了另一重极性关系。这之所以是一种极性的关系,理由无非也在于倘若要在体系结构本身中避免“黑夜里的牛”,那也同样要在关涉人类知识的时候,避免陷入一种雅各比主义式的狂热,否则黑格尔的批判就坐实了。在1821年的这个文本里,人类知识被认为是“作为知识活动而存在”的永恒自由,而知识活动则是对于永恒自由—绝对理性的客观创造洪流的“观念性的摹像(Nachbild)”,在人类知识中,永恒自由—理性“被限制在了对进程的纯然观念性重演上”②[德]谢林著,王丁译:《全部哲学的本原》,第22、23,28,33页。。而人类知识活动的本性就是“自我性(Ichheit),就是意识”③[德]谢林著,王丁译:《全部哲学的本原》,第22、23,28,33页。,而意识作为自我性,其特质就在于将某个东西作为某个东西自身来进行意识,也就是将一切的意识相关项进行“属己化”,甚至对于永恒自由—理性也不例外:“人类意图把它作为自由来意识,然而恰恰在这种把自身当作中心而把自由吸引向自身的活动中,人类把自由虚无化了。”④[德]谢林著,王丁译:《全部哲学的本原》,第22、23,28,33页。尽管表面上看来,这些说法仿佛有一种“绝圣弃智”的意思,但如果考虑到前文已经提过的这个循环的前提,即这里的重点是放弃“自我性”以寻求“科学”。那仍然可以认为,人类意识构成了一个永恒自由的可能同时既被阻碍、但也可能复归的“开放点”:“只有在(真正的)知识活动中才存在一个开放点。”①[德]谢林著,王丁译:《全部哲学的本原》,第23,28页。尽管这里涉及的更复杂问题在此无法展开,但仍可以从极性关系出发来看待谢林体系直到晚期的一个更深层次的结构:1. 在早期“同一哲学”中,属人的、或者说由自我意识开启、由“自我性”支配的先验哲学属于体系本身的一个面向,即绝对同一性在—自我—之中存在时的情形。但是在通过理智直观—抽离而进入对体系自身的阐述之后,人类意识的位置消失了。即便摹仿斯宾诺莎的几何学模式来阐发这个所谓的体系本身,也仍然令人起疑:这种阐发的思想必然性从何而来?2. 所以在前文所引谢林1802 年对体系的进一步阐述里,他很明确地表示,所有那些极性的结构,都是“观念性的”,亦即对人类知识活动而言的。但这里的人类知识活动已然不再是一种自我—自明性意义上的知识活动,它始终是建立在复归理性洪流的前提上的。但我们仍然可以问,这种观念性的极性构造的合法性在哪里?3. 因此在谢林1821年的文本中,人类的真正知识活动本身也与永恒自由—绝对理性构成了一种极性关系。这之所以仍是一种极性关系,不仅在于倘若人类坚持自我性,那么人类意识以及先验哲学意义上以意识为基础的知识活动就会与永恒自由构成对立。但这一对立恰恰也是永恒自由自身类似于磁体那样极性关系的呈现,因为“人类就是已然到达自身的自由”②[德]谢林著,王丁译:《全部哲学的本原》,第23,28页。,因为唯有自由方可阻碍自由,唯有自由方可联系不同的自由。
结 语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可以看到,即便在某种视角下,可以认为谢林哲学从早期关于理性体系内在构造的“同一哲学”演进到了在1821 年已经充分展现的“自由哲学”,但极性结构仍保持不变。归根到底,这一结构的重点仍然是肯定性,而非黑格尔意义上的否定性。因此最后看来,谢林与黑格尔之争的核心或许最终落脚在下面这个问题上:一种大全一体的体系建构辩证法,是否不仅有黑格尔的否定性版本,而且还有谢林的肯定性版本。倘若这个说法成立,那么谢林的这种肯定辩证法在思想的源流中又来自哪里?它又在哪里觅得了自己的回声?只要这个问题仍未解决,那么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可能还言之尚早。或许可以说,大全一体体系建构的黑格尔版本终结了,但谢林的版本仍悬停在尚未进入历史的某个凝固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