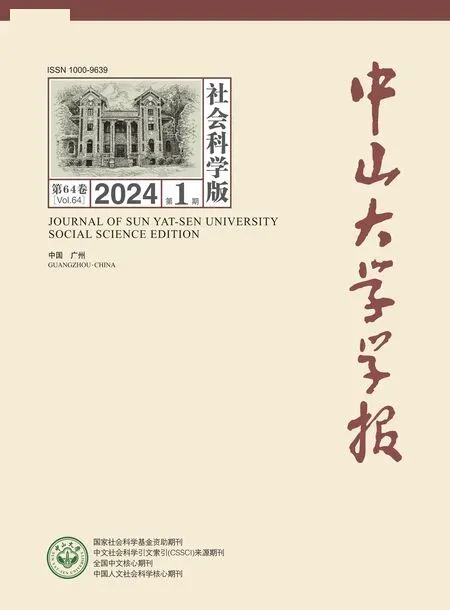编 后 记
本期刊文18 篇,覆盖文史哲、社会学与经济学等学术领域。
在当代研究思想史的学者群体中,复旦大学葛兆光以融通文史哲等领域而自出裁断,卓然名家。他笔下的思想史甄综种种传世与出土文献而别具眼光,让传统的似乎已经大致成型的思想史总能放出一种新的光芒。在一定程度上,他成就了这个时代思想史研究“深美闳约”的理想状态。兼之他对中国古代思想文明自觉的敬畏和戒惧之心,使得他的论著往往充满着冷静而富理性、刚健而有辉光的特色。大凡一种文化总有正面与背面两种样态,华夏文明史对“正面”的梳理与论析,已然自成一种明晰的传统,这种传统带给我们足够的自豪甚至无尽的想象。但文化之泉跋山涉水一路奔流,也必然经过山之北与水之南,如此文化史的背阴面,不仅需要我们付出足够的重视,也需要我们与正阳面的情形自觉形成一种互勘的思维,方能用理性的视野带出一等的识见。关于中古华夏主流是否已经文明,这看似是一个“无”中生“有”的问题,但深入而看,这问题不仅存在,而且具体到天师道“清整道教”之事,野蛮之习气竟然触目皆是,荒诞、残忍与放荡等不经行为显然偏离了传统的礼乐文明,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所以,如何看待周孔之后特别是中古时期文明与非文明的交叉与纠葛,就成为思想史上无法回避的问题。葛兆光从胡适与杨联陞关于中古中国宗教的通信说起,把一个十分严肃甚至严峻的问题竟然用娓娓道来的方式讲论出来,令人仿佛走出《世说新语》之前院,搁麈尾而步后院,意外得见另外一种风景。
《春秋》是一部兼有历史与政治等多重意义的著作,因其特殊“笔法”而呈现出文简而义丰的特点。《春秋》义出多方又隐约迷离,给读者带来的历史、政治与文学等的阅读障碍便所在都有,这客观上成就了《春秋》阐释学的源远流长。在《春秋》学史上,朱熹的地位隆盛,《朱子语类》中的《春秋纲领》在宋代及此后的学术史上,素受尊崇。但一人之学术殊难牢笼百代,即便作者思力称雄一时,也必有其思力或过甚、或不及、或偏离之处,学术之前修未密、后出转精者,类多如此。若清初张自超之《春秋宗朱辨义》,便在“宗朱”的基础上“辨义”,是以貌似释“朱”,而其实自“张”一军。台湾成功大学的张高评精研《春秋》有年,述作颇多,此次他对张自超此书直书示义之书法的探讨,在事、辞与义三者之间,寻得自家开悟之天地,亦足启人心智。
文学的审美意义总在虚实之间呈现出来,日记与书信虽偶与事实有违,而于一时之心境,则真实性也大体值得信任,这正是书信日记在文学研究取材时难以被取代之处。某研究王国维有日,而近十年之述作,率多取材《国家图书馆藏王国维往还书信集》《王国维书信日记》及友人萧文立编注之稿本《罗振玉书信集》(暂名)等,研读含玩其中,每有感悟,因悟成文,往往如此。北京大学张剑关注近现代稀见史料多年,主事相关丛书之编纂出版积成规模,影响日深。编纂之余,对日记书信之于情境文学史的构建,也多实证实悟之理论创获。本期刊发其《爱是一种创造吗——林庚白与张璧情感分析报告》一文,便是其对情境文学史建构的一次具体实践。林庚白视张璧为理想女性之范式,但结果事与愿违,现实的冷峻遂转换为文学创作中含有一定虚拟意义的自我形象重塑,于其事或有无征者,但于其情则或有可原者。文章颇多第一手之史料,读来当兴味不浅。
近来某因关注陈弢庵,而不期然关注到逊敏斋主人载泽。载泽在清季曾受命与端方等人赴东西洋考察政治体制,以为民情日趋汹涌的未来宪政提供借鉴,择善而从,其《考察政治日记》便是其当时行踪与思想的记录。但君主立宪与共和宪政还是有着明显的区别,这是清末虽渐开门户却终究收束脚步的原因所在。但从学术史角度来考量,这一段经历却是中国社会迈向宪政过程中的关键一步。光绪三十四年(1908)的国会请愿在当时影响广泛,而国会期成会在其中则扮演了领导和组织的作用,尽管请愿活动的效果甚微,但这种推进中国政治发展的努力还是有着一定的意义。本期刊发赵建民关于国会期成会与1908 年国会请愿关系一文,对此事的前因后果剖析颇为细致。
魏晋的魅力主要体现在思想与情感、行为恣肆与约束之间的大致平衡,这使得你只要仔细追寻,魏晋基本能满足当时或此后各种大大小小的想象。似乎找不到厌倦魏晋的绝对理由,当然也不大可能沉醉在魏晋而难以自拔,因为只要打开黄卷,魏晋留存的遗憾便常常扑面而来。这就是一个难以说尽说透的魏晋,是一个在远近与离合之间的魏晋。整体与个体、无限与有限,在魏晋思想的发展中,总是处于一种“交战”之中,和谐是短暂的,交锋却是常态。这意味着关于魏晋的思想,一切的重组与新构都有可能,胡海忠从魏晋玄学与宋明理学的关系中,发现无限与一体正可以为重构魏晋思想提供可能。世间一切的可能与可能之间,有的得以长久生存,有的则被瞬间淹没,但更有力量的可能,毕竟是值得期待的。本期同时刊发的葛兆光文章,同样可以为此增添一重佐证。
在这个多少有点漫不经心的时代,要讨论肉身的沉重与灵魂的轻盈,确实会令人张皇失措。这时候回味李金发的诗歌,就容易稍加安顿不安与跳荡之心。如其《弃妇》诗之第一、二节云:“长发披遍我两眼之前,遂割断了一切羞恶之疾视,与鲜血之急流,枯骨之沉睡。黑夜与蚊虫联步徐来,越此短墙之角,狂呼在我清白之耳后,如荒野狂风怒号:战栗了无数游牧。/ 靠一根草儿,与上帝之灵往返在空谷里。我的哀戚惟游蜂之脑能深印着;或与山泉长泻在悬崖,然后随红叶而俱去。”读来一切若有所悟,一切又好像在恍惚之间,这是因为象征虽有意义指向,但其本身就有着许多不稳定、不清晰的地方。这是诗歌必须面对的情况,哲学的情况似乎也同样如此。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就曾纠葛在思维与感性、范畴与直观等如何结合的问题上,而要把不同性质的东西达成彼此一致,“想象力”就是一种重要的弥合剂。这为“象征”提供了充足的理论空间,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谢林与黑格尔在艺术哲学中的“象征”之争,理论的窒碍就少了很多很多。先刚以此为题,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就是挑战与机遇并存。
本期刊出之时,离龙年春节就很近了。数日前一位京中友人从微信发来一幅画,嘱某题诗,画面是两只兔子躺在青草地上,各自享受着在天地自然中的躺平之乐,果然人间有味是清欢,因题曰:
他欢他卷任循环,我兔安眠若等闲。
流水无声青草地,繁星醉在月光间。
只是吾人与兔子毕竟不同,安躺在地,仰望星空,可以陪伴逍遥的,除了一杯清茶,还有《中山大学学报》开年第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