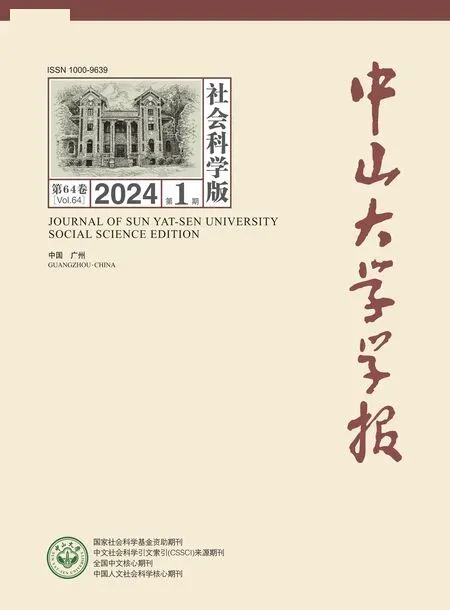论清初遗民僧的“至情”与“疑情” *
李 瑄
遗民僧,即表现出遗民立场的佛教僧侣①遗民僧之名虽然首见于陈垣《清初僧诤记》(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85页),但是清初文献中关注到他们和普通僧侣不同的“遗民为僧”“遗民逃禅”“有托而逃”“隐于浮屠”“浮屠逸民”“忠孝佛事”之类的记录和讨论却非常普遍。遗民僧事实上已经被区别于普通僧人和儒者遗民来看待,其群体意识也已经产生(参见李瑄:《遗民僧的概念辨析、身份界定与研究展望》,《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23年第3期)。,产生于王朝更迭的特殊时期,尤以明清之际人数众多、社会影响力大而令人瞩目②目前寻检遗民僧资料最为便利的工具书,是谢正光、范金民编撰《明遗民传记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该书也是目前搜集有传记可考的明遗民数量最多的索引,共收2000 余人;其中“僧”类收录159 人。邵廷采说“僧之中多遗民”,于此可见一斑。笔者又调查了一些谢著未收的文献,发现有传记存世的遗民僧至少在300人左右。。他们兼执儒、释伦理准则,活跃于宗教、哲学、公益、政治、文学、文化传播等诸多领域。其文学作品及文艺思想都极受清初文坛重视,遗憾的是相关研究成果却至今寥寥。
现有僧人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唐宋二代,僧诗创作的高峰期却在晚明清初。明清僧诗的数量远远超出前代。据李舜臣调查,见于公私书目的释家别集“东晋1种,唐代9种,宋代30种,元代19种,明代66种,清代348种”③李舜臣:《历代释家别集叙录》前言,北京:中华书局,2022年,第36页。,可以大致反映不同时代僧诗风气的涨跌。
明清两代的僧诗风习,又以明万历至清康熙时期为高潮。明代僧人别集,万历以后的占半数以上;清代僧人别集“主要集中在清前期,即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又以康熙朝为最多”④参见李舜臣:《明代释家别集考略》,《学术交流》2015年第9期。。清初僧人习诗见于文人记录非常频繁。宋琬云:“数十年来,诗教与禅宗并行,于是方袍之士,人人自以为握灵蛇之珠矣。”⑤宋琬:《题筠士上人诗》,《安雅堂未刻稿》卷6,《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05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第209页。万历以降,在憨山德清、雪浪洪恩等带动下,丛林诗风越来越盛。顾景星记录过一个痴迷于作诗的西湖僧人心函,其人“善近体诗,与士大夫辨论声韵切反,字栉句比,沾沾自喜”;外出游览之际,兀自“抱膝跽石,戛焉苦吟”①顾景星:《二上人遗诗序》,《白茅堂集》卷34,《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06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275页。。他痴迷的程度不仅违背了禅宗的“不立文字”,连登岸舍筏的“文字禅”也涵盖不了。心函这样好诗的僧人恐怕并非特例,佛门诗风之盛已招致士人侧目。魏禧说:“诸方动手成文,朝脱于纸,暮登于木。”②魏禧:《答石潮道人》,胡守仁等校点:《魏叔子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348页。可见当时僧人不仅热衷作诗,还热衷于出版诗集。
在这样的文学环境当中,清初遗民僧能诗是情理中之事。清初最著名的几个诗僧群体,如临济宗三峰派继起弘储(1605—1672)门下、晦山戒显(1610—1672)门下、临济宗天童派牧云通门(1599—1671)、木陈道忞(1596—1647)门下,曹洞宗寿昌派觉浪道盛(1592—1659)门下,曹洞宗天然函昰(1608—1685)门下的习诗子弟,均以遗民僧为中坚。明清僧诗总集中,《诗遯》《海云禅藻集》《珠林风雅》以遗民僧诗为主体。此外,清初最著名的诗僧,如贤首宗苍雪读彻(1588—1656)、临济宗雪峤圆信(1571—1647)、晦山戒显,曹洞宗祖心函可(1612—1660)、今释澹归(1614—1680),都是遗民僧。吴伟业评论读彻“当为诗中第一,不徒僧中第一”③吴伟业:《梅村诗话》,李学颖集评标校:《吴梅村全集》卷5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第1144、1145,1145页。,充分显示了遗民僧诗在清初诗坛的地位。遗民僧是清初佛门对时代剧变最为敏感的成员,他们的诗文也对以往佛教文学传统有明显突破。
一、“不可遏抑”的遗民僧诗
中国僧诗从东晋发源,至唐代成熟,在文学史上受到关注的主要有两派。一是初盛唐以王梵志、寒山、拾得为代表的白话诗僧,作品流传于民间④项楚:《寒山诗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6页。。二是中晚唐以皎然、灵一、贯休、齐己等为代表的文化诗僧。他们出现于唐代兴盛的诗歌风气中,把写诗作为专门事业来对待,留下不少诗集。这一批诗僧形成了区别于文人诗的“僧诗风格”,特征是“清寒”⑤据蒋寅统计,皎然共479 首诗中出现了125 个“清”字(蒋寅:《大历诗人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5 年,第363页)。李舜臣统计了灵一、法振、灵澈等人诗歌中的“清”字,亦得出相似比例的数据。故定论曰:“‘清’实在是中唐诗僧们所崇尚的审美趣味。”(李舜臣:《岭外别传:清初岭南诗僧群研究》,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7 年,第174 页)此一风格,覃召文称之为“清雅”;周裕锴则称这些诗僧为“清境派”。。清,因其离俗出世而意存深远;寒,则由其山林生活单调枯淡。宋人郑獬云:“浮屠师之善于诗,自唐以来,其遗篇传于世者班班可见。缚于其法,不能闳肆而演漾,故多幽独衰病枯槁之辞。”⑥郑獬:《文莹师诗集序》,文莹撰,郑世刚、杨立扬点校:《玉壶清话》“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10页。衡诸宋代九僧、元代中峰明本等诗僧,其说大致不差。覃召文谓中晚唐诗僧“奠定了中国僧诗的基调”⑦覃召文:《中国诗僧纵横谈》,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第68页。;周裕锴则认为,“清境派”诗僧“在中晚唐以后逐渐成为僧诗的主流”⑧周裕锴:《中国禅宗与诗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3,45—53页。。
僧诗的清寒特质,被宋代文人调侃为“蔬笋气”。这是一种超世俗、超功利的审美范型,弊病也如周裕锴所说:意境过于清寒,题材过于狭窄,语言拘谨少变化,篇幅短小少宏放⑨周裕锴:《中国禅宗与诗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3,45—53页。。这一概括虽然不能包含僧诗的全部作品,却抓住了由唐至明数百年间僧诗的基本取向。
清初遗民僧诗不乏清寒之作,然而远非“清寒”所能笼罩,他们打动世人也多非“枯淡”之诗。吴伟业记录苍雪读彻云:“师虽方外,于兴亡之际,感慨泣下,每见之诗歌。”⑩吴伟业:《梅村诗话》,李学颖集评标校:《吴梅村全集》卷5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第1144、1145,1145页。石璜记释中涌:“每当剧饮大醉,辄歌数阙,中涌必从而和之。感慨悲愤,泣数行下。”①石璜:《释中涌诗集序》,《匏庵先生遗集》卷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42册,第617页。 鄂州岩头全奯禅师语,释超永编:《五灯会元》卷7,《卍新纂大日本续藏经》第80册,第144页。在如此情感状态下写作,诗风不会枯寒。陈锡嘏云:“虽释氏主于寂灭,而性情之所流露,有不可得而遏抑者。”②陈锡嘏:《远庵上人诗序》,《兼山堂集》卷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47册,第501页。“不可遏抑”之情,正是遗民僧诗区别于一般僧诗最显著的特征。
遗民僧诗的情感力量令人震撼。他们多书写包含了家国关怀的伦理情感与济世热忱的宗教情感。如以下一些作品:
读彻《焚笔》:土冢不封毛尽秃,铁门断限字原无。欲来风雨千章扫,望去苍茫一管枯。③吴伟业:《梅村诗话》,李学颖集评标校:《吴梅村全集》卷58,第1145页。
弘储《答天宁恒侄禅师》:插身热恼海中央,八万波旬焰正狂。烧煮任他忘昼夜,心肝依旧烈于霜。④《答天宁恒侄禅师》,释弘储:《灵岩树泉集》卷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第21b页。
函昰《庚寅二月雷峰即事》:野寺疏钟接晚笳,蓟门残雪岭南花。十年征战江云断,二月风烟山日斜。古洞暮猿凄绝岸,荒原明月照谁家。越王台上西风急,夜夜哀魂到海涯。⑤天然函昰著,李福标、仇江点校:《瞎堂诗集》卷10,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4—105页。
函可《皇天》:皇天何苦我犹存,碎却袈裟拭泪痕。白鹤归来还有观,梅花斫尽不成村。人间早识空中电,塞上难招岭外魂。孤雁乍鸣心欲绝,西堂钟鼓又黄昏。⑥释函可:《千山诗集》卷10,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02页。
以上不厌其烦引用不同宗派⑦读彻属华严宗,弘储属禅宗临济宗,函昰、函可属禅宗曹洞宗。、不同地域、不同题材、不同情境的遗民僧诗,以展现其深沉而激烈的群体性情感表现。无论是读彻一笔扫荡苍茫风雨,还是弘储无畏烈火焚烧,抑或函昰从西湖反照看见荒原以及函可发出问天长啸,都映照出他们心境的悲怆与情绪的激烈。
这种心境是时代动荡与刚健人格撞击的回响。以弘储为例,《答天宁恒侄禅师》作于顺治九年,期间他被清廷逮系受“庭鞫大杖”。“烧煮任他忘昼夜”不是豪言壮语,而是迫在眉睫的死生旦夕。徐枋评弘储此诗为“朝闻道,夕死可矣”⑧《灵岩树泉集序》,徐枋撰,黄曙辉、印晓峰点校:《居易堂集》卷5,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9页。,强调其慷慨取义的遗民面貌,但“插身热恼海中央,八万波旬焰正狂”却分明不同于儒者遗民。“热恼海”是佛教名词:“热恼”是说苦痛使人身热心恼,《法华经》:“我等以三苦故,于生死中受诸热恼,迷惑无知。”“海”形容烦恼深广、无边无际,《华严经》曰:“众生没在烦恼海。”宋僧惠洪《临济宗旨》云:“有玄有要者,一切众生热恼海中清凉寂灭法幢也。此幢之建,譬如涂毒之鼓挝之,则闻者皆死。”⑨《临济宗旨》,《卍新纂大日本续藏经》第63册,东京:株式会社国书刊行会,1975—1989年,第168页。此外,“波旬”是佛教恶魔之名,译为杀者、恶者,“常欲断人慧命”⑩参见《丁福保佛学大词典》,DILA佛学术语字辞典,https://glossaries.dila.edu.tw/。。此诗设定群魔乱舞、众生迷狂的苦难世相为背景;“插身中央”以主动、尖锐的姿态进入苦海;“烈于霜”的“心肝”就是“清凉寂灭法幢”,为救度世人而先置之死地的“涂毒鼓”。“涂毒鼓”是禅宗语词,“击一声远近闻者皆丧”⑪,能令“所有贪欲瞋恚愚痴悉皆灭尽”⑫《大般涅盘经》卷9,《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2册,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第661页。。这样的声音不可能清寒枯淡而必然壮烈激昂。
遗民僧追求的诗歌风貌也与浓烈的情感互为表里。石濂大汕(1644—1702)说:“若夫峭拔处如波浪兼天涌;奔腾处如风云卷地来;幽韵处如兰谷竹溪,清香并至;惊人处如海立天崩,倾湫倒岳,霹雳火闪,电光交加而来:此皆不容一毫牵强揑捏。”①大汕著,余思黎点校:《海外纪事》卷3,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54页。要言之,遗民僧诗的群体特征,是由宗教精神、伦理信念和时代环境共同铸就的强烈感情力量;其区别于一般僧诗的不仅是风格差异,更是精神气力的强弱②此处借用大汕语:“纵能摹拟髣髴,断无其全副精神气力,却不知自我作古之为愈矣。”(《海外纪事》卷3)。
二、至情:即人情是佛法
遗民僧寄托于诗歌的情感能量与前代诗僧大不相同。他们抒写大动乱时代的慷慨悲怀,与通常僧诗离世绝俗的枯寒作风大异其趣。这种文学情感观的佛学依据是大乘佛教的入世精神:真谛与世谛合一,于人世间度脱众生。遗民僧将其宗教追求置于世缘流转当中,通众生忧戚而振济之,因此他们自觉投入与俗世相通的情感。觉浪道盛曰:
天地人物,只有一性情之灵为可传也……此心不死,则天地人物文章功业皆有神而可传,传而能通也,是又乌可已哉?③释道盛:《读方挺之传题辞》,《天界觉浪盛禅师全录》卷28,《嘉兴大藏经》第34 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7年,第759页。
天然函昰曰:
天下有至性,然后有至情。有至情,然后有至文。文所以达其情者也,情所以极乎性者也。④《伦宣明使君释骚序》,《庐山天然禅师语录》卷12,《嘉兴大藏经》第38册,第196,196页。
“性情之灵”和“至情”都强调情感的力度。它们既是自然情感,又是伦理情感。“至性”“性情”在理学流行后成为论诗常谈,然而在此处它并非像理学术语那样强调约束⑤从“诗言志”发端的性情诗论在“礼”的约束下压缩情感表达空间,参见王秀臣《“诗言志”与中国古典诗歌情感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2期。。檗庵正志(1600—1676)云:
文句从册子上来,文句而已矣。自胸襟流出,则啾如蚊蚋而充塞十虚,轰若雷霆而刻雕万有。能诠一切,一切不能诠。非成天下之亹亹者,其孰能与于斯?⑥释正志:《翼庵鄼禅师杂著跋语》,《檗庵别录》卷6,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第5a页。
“自胸襟流出”指作者情意与语言合二为一的状态,语源来自岩头全奯(828—887):“若欲播扬大教,一一从自己胸襟流出,将来与我盖天盖地去。”⑦《雪峰义存禅师语录》卷1,《卍新纂大日本续藏经》第69册,第72页。意即扫荡一切现成说教,唯有自身真实感悟,才能够无限广阔以至“盖天盖地”。“自胸襟流出”后来成为形容禅师们顿悟自性后与万物相通的成语,“啾如蚊蚋而充塞十虚,轰若雷霆而刻雕万有”,就是形容这种浩气充塞而又无微不至的状态。它是作者自身生命动能带动的天地万物共振,个人、万物、天地形成融通无间的共同体。对主体来说,只有与万物苍生休戚相通才能成就其广大,只有与现实世界接触、关联才能了悟自性。这样强烈的入世精神和离世观心的“蔬笋禅”显然是背道而驰的,故曰:“非成天下之亹亹者,其孰能与于斯。”
道盛、函昰等人言论中不难看到儒家诗论的影子。“性情”是儒家诗论习语,明清人言“性”通常不离忠孝伦理。函昰又云:“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皆惇然有至性行乎其间,故能善用其情发为文章,冠履天地,争光日月。”⑧《伦宣明使君释骚序》,《庐山天然禅师语录》卷12,《嘉兴大藏经》第38册,第196,196页。把至情的道德属性说得很明白⑨遗民僧文学情感观的价值论基础之一是儒家道德文学观,主要表现为强调“文道”关系或以“性情”论诗。这与儒者遗民是大体一致的,可参见李瑄:《天地之元气:明遗民的文学本质观》(《浙江学刊》2006 年第1 期),《明遗民的“性情”新义与明清之际的诗坛衍变》(卢盛江等编:《罗宗强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不过,除了儒家伦理,更值得注意的是至情论和大乘佛教入世精神的联系。
一般来说,“情”是佛教摒除的对象。佛教所称“六情”从“六根”触缘而生,又称“情识”。情识所依的因缘本来虚妄不实,故又称“妄情”。众生为之迷惑转倒,计虚妄为假有,沉溺于无常失却本性,故又称“迷情”“情障”。“性体圆明,本无生灭。情尘覆蔽,乃有圣凡”①见月读体:《传戒正范》卷1,《卍新纂大日本续藏经》第60册,第630页。,情是未能觉悟的凡俗众生的特性,是粘于物境的感性执着。传统僧诗的清寒、枯淡,从根本上说正是来自僧人断绝情根、超越世俗的宗教追求。然而,尽管情在佛学中被认为是妨碍觉悟的消极因素,晚明文学中却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文学主情论者,如徐渭、汤显祖、屠隆、冯梦龙,大多与佛门关系密切,有些还有精深的佛学修养②廖肇亨注意到:“晚明的主情论者往往也是坚定的佛教信众。”(廖肇亨:《晚明情爱观与佛教交涉刍议》,《中边·诗禅·梦戏:明末清初佛教文化论述的呈现与开展》,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第366页)。
这其中或有文人借助佛教来摆脱理学压制的原因,但佛教本身必须为之提供思想资源③已经有研究者试图作出过解释。如黄卓越《晚明情感论与佛学关系之研究》(《文艺研究》1997年第5期)指出以王畿为代表的心学家吸收洪州禅的“无所分别、随缘任运”思路,包容了日常生活的合理性,是一种巧妙的论辩方式,将日常生活及其情感的合理性肯定了下来。汤显祖的“深情”论则受心学、佛学思维影响,将“原始生命冲动”作为本体心性加以肯定,世俗之情因此被升华为超验之情。再如廖肇亨《晚明情爱观与佛教交涉刍议》(《中边·诗禅·梦戏:明末清初佛教文化论述的呈现与开展》,第366—390页)一文认为“佛教将爱欲当作一种体悟人生真谛的契机”。。佛教的修行目的,有自度、度人二种。汉传佛教以大乘为主,谓“以空观灭情入寂”求自度为小乘,“悯念安乐无量众生,利益天人,度脱一切”为大乘。晚明佛教复兴的代表人物紫柏真可、憨山德清、云栖祩宏等,都具有浓厚的入世性格。遗民僧兼执儒家伦理,入世倾向强烈,其领袖如道盛、弘储、明盂、函昰等人无不极具救世热忱。道盛云:“夫所谓佛法者,即世间法也。”④《人法必交相重说》,《天界觉浪盛禅师全录》卷24,《嘉兴大藏经》第34册,第729页。“所谓出世间法者,又岂舍此世别有所谓出世乎?”⑤《古今决不可一日无师友说》,《天界觉浪盛禅师全录》卷24,《嘉兴大藏经》第34册,第726页。完全把宗教价值的实现寄托于人间。
入世济众就需要理解众生的情感世界。石林道源(1586—1658)注释李商隐诗,曾受钱谦益质疑:“公真清净僧,何取乎尔(春女、秋士之悲)也?”他回答说:
佛言众生为有情。此世界,情世界也。欲火不烧然则不干,爱流不飘鼓则不息。诗至于义山,慧极而流,思深而荡。流旋荡复,尘影落谢,则情澜障而欲薪烬矣。春蚕到死,蜡炬成灰,香销梦断,霜降水涸,斯亦箧蛇树猴之善喻也。且夫萤火暮鸦,隋宫《水调》之余悲也;牵牛驻马,天宝《淋铃》之流恨也。筹笔储胥,感关、张之无命;昭陵石马,悼郭、李之不作。富贵空花,英雄阳焰。由是可以影视山河,长挹三界,疑神奏苦集之音,阿徙证那含之果。⑥钱谦益:《注李义山诗集序》,《有学集》卷15,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钱牧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703页。
道源将义山诗情纳入佛教华严法界观来看待。《华严经》云:“尔时世尊,处于此座,于一切法,成最正觉。智入三世悉皆平等,其身充满一切世间,其音普顺十方国土。譬如虚空具含众像,于诸境界无所分别;又如虚空普遍一切,于诸国土平等随入。”⑦实叉难陀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卷13,《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0册,第1—2页。“万法平等,均成正觉”是其核心:森罗万象皆具虚空之性,虚空又涵容一切事相;在这个意义上世出世间原无差别,佛与菩萨度化众生就在现世之中。澄观《华严经疏》云:“触境斯了,六根三业尽是文殊;实相体周,万象森罗无非般若。”⑧《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卷1,《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5册,第596页。佛法不离现世,离开森罗万象又到哪里去找寻佛性?根据这一思想方法,李诗所呈现的人间苦乐都在法界之中,都是证道之具。要度化众生,引导其勘破此世的虚幻,最好的办法是使之经历深刻的情感体验。《维摩诘经》“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①释僧肇等:《注维摩诘经》卷7,《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8册,第396页。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只有投入情感才可能超出思维知解、真切地体验透悟。道源说“欲火不烧然则不干,爱流不飘鼓则不息”,没有饱尝人间的爱恨悲欢,也就没有了悟无常的绝大力量。
佛教面向大众,如果只是道理说教功效有限。僧侣往往采取文学演绎如变文、小说、戏曲引导大众从情感激荡中领悟佛法。《联灯会要》曰:“如来举身相,为顺世间情。”②释悟明辑:《联灯会要》卷9,《卍新纂大日本续藏经》第79册,第85页。文艺通过情感达到宣教目的,诗歌也是达成情感互通的有效途径。佛教虽然追求最终的离智绝情,却并不废弃感通人情广传佛法,《贤愚经》甚至还有“世尊究人情”的说法③释慧觉等译:《贤愚经》卷8,《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册,第404页。。禅宗讲“随机设化”,也讲究顺乎人情,易解易入④李遵勖编:《天圣广灯录》卷29记庐山惠日院达禅师云:“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随机设化,应物施为。古人拣择一门,要人易解易入。”《卍新纂大日本续藏经》第78册,第569页。。世出世间、佛法人情打成一片,晚明以降,佛教的入世性格非常鲜明,紫柏真可曾宣称:“佛事人情,初非有二,顾其用心何如耳。”⑤释达观:《湖州府弁山圆证寺募四万八千弥陀缘起》,《紫柏尊者全集》卷13,《卍新纂大日本续藏经》第73 册,第255页。
遗民僧怀有济世悲愿,如果不通人情则无从知晓众生的困溺苦楚,救世未免成了一厢情愿。觉浪道盛云:“做善知识须是大通人情,而心亦敬之。”⑥《天界觉浪盛禅师全录》卷16,《嘉兴大藏经》第34册,第684页。从这个思路出发,僧侣自身的人情体验也必不可少。弘储云:“举身相为,顺世间情。”⑦《灵岩廿一录卷下》,《南岳继起和尚语录》卷8,《嘉兴大藏经》第34册,第317,319页。他多次公开宣称自己“不能忘情”⑧《复张孝廉冰庵》:“老秃师不能忘情于病维摩。”(释弘储:《灵岩树泉集》卷下,第9b页)“岂能恝然无情”⑨《复顾子克居士》,释弘储:《灵岩树泉集》卷下,第7a页。,在祭悼法侣、道友时从不避讳情感激荡的表现。这一行为的思想基础,是人情不异佛法:
道乎?情乎?情牵生死,道绝去来。道非尝(常)道,情岂尝(常)情。⑩释弘储:《住苏州灵岩崇报寺语》,《南岳继起和尚语录》卷2,《嘉兴大藏经》第34册,第288页。
这里的道包含了利益众生的济世之道,情也不仅仅是个人感情,而是宗教情感、伦理情感与个体自然情感的合一。弘储等人的言行超出了“为顺世间情”的方便法门,进入到“即人情是佛法”⑪《灵岩廿一录卷下》,《南岳继起和尚语录》卷8,《嘉兴大藏经》第34册,第317,319页。的层次,这是遗民僧至情文学观的思想根基。
三、诗之“怨怒”与禅之“疑情”
遗民僧的文学情感论以重情为主流,且有倡导极端情感体验——“怨怒”的一派,以曹洞宗觉浪道盛及其弟子为代表。道盛云:
予以怨之一字,尤为造化之玄枢,性命之秘藏。⑫《僧祥马培元近稿序》,《天界觉浪盛禅师全录》卷22,《嘉兴大藏经》第34册,第722页。
孔子言诗,虽兴、观、群、怨并发,其秘密藏而纯归于一怨字……此怨字,发人情后天之密。非到怨处,不足以兴,不足以观,不足以群。到群,又不能不怨。不怨则不能归根复命,于绝后重苏……予以庄生善怒字,屈原善怨字,孟子尤善怨怒二字。盖未有怨而不怒,怒而不怨也……凡此以正直之气发天地人物不平之气,以会归于天地中和者,皆怨怒功也。⑬《论怨》,《天界觉浪盛禅师全录》卷33,《嘉兴大藏经》第34册,第795页。
其弟子无可弘智(俗名方以智,1611—1672)云:
尼山以与天下属诗而极于怨,怨极而兴,犹春生之,必冬杀之,以郁发其气也。行吟怨叹,椎心刻骨,至于万不获已。有道之士相视而歌,声出金石,亦有大不获已者存。存此者天地之心也,天地无风霆则天地瘖矣。①方以智:《范汝受集引》,《浮山文集后编》卷1,黄德宽、诸伟奇主编:《方以智全书》第10 册,合肥:黄山书社,2019 年,第32页。
他们把“怨怒”作为其诗学的核心命题,内涵很丰富。已有研究者从易学、庄学讨论,但其主张中的宗教精神尚待发覆②参见[日]荒木见悟:《憂国烈火禅——禅僧覚浪道盛のftftfkい》第五章“怨の禅法”,东京:研文出版,2000 年;谢明阳:《明遗民的“怨”“群”诗学精神——从觉浪道到方以智、钱澄之》,台北:大安出版社,2004年。。道盛与弘智的“怨”论虽然源自孔门,却显然已经超出诗教“温柔敦厚”的控制范围。道盛说“未有怨而不怒,怒而不怨”,弘智说“无风霆则天地瘖”,“怨”“怒”并举,明确肯定个体被精神困境激发的极端情感。他们标举的诗学代表是《离骚》,道盛云:
善读《骚》者,举千古之自怨自艾,号泣旻天……孰以屈子之怨忧未能格君之心,遂谓不逮于大舜文王哉?③《三子会宗论》,《天界觉浪盛禅师全录》卷19,《嘉兴大藏经》第34册,第698页。
屈子怨而不怨,则怨即怒也。不见《离骚》皆不平之怨耶?④《论怨》,《天界觉浪盛禅师全录》卷33,《嘉兴大藏经》第34册,第795页。
弘智云:
(《离骚》)忠不见用,信而见疑,其心一,其声悲,不必以传,不能以不传。此其日月争光之文,文固已传天地之心矣。⑤方以智:《屈子论》,《岭外稿》中,《浮山文集前编》卷8,黄德宽、诸伟奇主编:《方以智全书》第9册,第533页。
《离骚》是中国愤激文学的典范。虽然后世学者力图将其涵容到儒家诗教中⑥典型代表如朱熹《楚辞集注》引刘安“《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朱熹:《楚辞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页)。,但多强调其伦理价值,对激烈悲愤却少有肯定。即使在遗民僧中,也有天然函昰评论屈原“情穷则中乱,中乱则无以自托于世”。他是“至情”的主张者,却要求“善用其情而不流乎激烈”⑦《伦宣明使君释骚序》,《庐山天然禅师语录》卷12,《嘉兴大藏经》第38册,第196页。。双方分歧的实质是对情感与理性关系认识的差异。函昰和大多数儒家诗教论者认为情感应该随时受到理性控制,否则就可能扰乱社会秩序,故此反对无限制的激情;道盛、弘智等人将情感视为精神的发动状态,认为情感强度越高能量越旺盛。他们把情看作生命的原动力、“传天地之心”的中介,怨怒之情就是天地生机的鼓荡⑧道盛、弘智等主张“怨怒”诗学,思想来源颇为复杂。《离骚》是其标举的诗歌典范,此外易学与庄学也是重要的思想资源。易学方面,以“生生不息”为精神内核,尊火为宗;庄学方面,以庄子为“愤疑”与“有情”者。因相关问题荒木见悟与谢明阳已有深入讨论,故本文从略。。
肯定怨怒之情在清初并不孤立,儒者遗民也多有发扬怨怒之情、突破诗教规范的主张,如申涵光云:
温柔敦厚,诗教也。然吾观古今为诗者,大抵愤世嫉俗,多慷慨不平之音。自屈原而后,或忧谗畏讥,或悲贫叹老,敦厚诚有之,所云温柔者,未数数见也。⑨申涵光:《贾黄公诗引》,《聪山集》卷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07册,第494页。
彭士望云:
世则有然,文从而变。而作文者之用心弥苦弥曲,弥曲弥厉,如天地之噫气,郁不获舒,激为震霆,凝为怪雹,动荡摧陷,为水溢山崩。夫岂不欲为卿云、旦日、甘雨、融风?势有所穷,不得已也。①彭士望:《与魏冰叔书》,《耻躬堂文钞》卷2,《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52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34页。 《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21,《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7册,第901—902页。
“怨怒”文学观是明清之际社会剧烈震荡的产物,是个体精神被现实摧折时的反抗,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遗民论证怨怒之情的合理性主要从两个方面:一是“求真”的文学观念。他们书写时代与个人的冲突,不肯限于“温柔敦厚”而去自我矫饰②清初出现对“温柔敦厚”的特殊阐释,参见夏秀《清初文论对“温柔敦厚”的拓展性阐释》,《江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二是对于自身情感的道德自信。他们以“天地元气”自命,坚信自己的价值坚持是世界秩序恢复的基础,“愤而不失其正”即可不朽③清初遗民的相关研究,参见李瑄《明遗民群体心态与文学思想研究》第五章第三节“怨怒之诗:‘温柔敦厚’的突破与诗教功能的实现”(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
道盛等所言“怨怒”也虽然包含儒家伦理信念④参见[日]荒木见悟《憂國烈火禪——禪僧覺浪道盛のftftfkい》第五章“怨の禅法”;谢明阳:《明遗民的“怨”“群”诗学精神——从觉浪道到方以智、钱澄之》第二章。,但更具宗教精神。他们强调激情体验的创造性能量,这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是极为罕见的。石溪大杲(1612—1692)云:
怒字是大炉鞲,不肯安在生死海中。有过人底愤懅,方能破此生死牢关,从自己立个太极,生生化化去也。⑤方以智:《药地炮庄》卷1引石溪语,黄德宽、诸伟奇主编:《方以智全书》第2册,第120页。
激情状态是不能安于现状的产物,它源自个体突围寻求生命价值的需求。犹如遭受烈火焚烧,饱受痛苦煎熬而后获得超越生死的绝大力量。这种力量打击昏沉的世界,重新启动天地创生化育。道盛云:
(怨字,怒字)皆是自心中创出造化来,变易天地人物。即此一字,为吹毛剑也可,为涂毒鼓也可,为狮子吼也可,为九转丹也可……千古人不能成大事者,只是不精一……须是大猛烈汉子始得。⑥《一字法门》,《天界觉浪盛禅师全录》卷33,《嘉兴大藏经》第34册,第792页。
这里用的吹毛剑、涂毒鼓、狮子吼、九转丹等禅宗比喻,都是使人死而后生的猛烈意象,以之形容怨怒即豁显其超出常人识量的创生之能。这种能量毫不留情地将人逼到生死关头,把人从日常安稳中打出。从中不难看到一种强烈的宗教精神,一种通过极致修行以自我成就、救赎众生的圣者情怀。
以禅宗“疑情”来阐释“怨”亦是遗民僧此种宗教精神的表现,道盛曰:
夫子称诗可以兴观群怨。此怨之一字,即吾禅门疑情也。⑦《胡洪胤盛高姚诸士云莲净修禅侣请茶话》,《天界觉浪盛禅师全录》卷9,《嘉兴大藏经》第34册,第648页。
儒门有一怨字,如大舜如怨如慕,太甲之自怨自艾,与诗之可以怨等,乃禅家所谓疑情——必欲求其故而不得也。⑧《天界觉浪盛禅师全录》卷32,《嘉兴大藏经》第34册,第782页。
参“疑情”是大慧宗杲(1089—1163)提倡的禅法。宗杲说:“疑‘生不知来处,死不知去处’底心未忘,则是生死交加。”⑨《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23,《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7册,第911页。疑情是生命找不到下落时精神极度痛苦的状态。宗杲的“看话禅”要求参禅者“只就疑情窟里举个话头”⑩《大慧普觉禅师普说》卷4,《卐正藏经》第59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0年,第962页。。话头是用来集中精神的短小禅宗公案,它本身的意义不重要,举此话头与彼话头也无分别,要紧的是牢牢把住,绝不放弃:“不用抟量,不用批注,不用要得分晓,不用向开口处承当,不用向举起处作道理,不用堕在空寂处,不用将心等悟,不用向宗师说处领略,不用掉在无事甲里,但行住坐卧时时提撕。”⑪诸多“不用”,实际上将可能的一切现成答案、祖师的一切已有经验、佛教的一切修行方法全都清除干净,使参禅者进入无路可去的绝境。“但向欲绝未绝处,与之厮崖,时节因缘到来,蓦然喷地一下”①《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23,《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7册,第911页。,情绪累积到爆发之时,冲破疑情即冲破精神极限。此一过程不可借助现成模式,不能通过知解达成,不能接受他人传递,只能从自身体验中绝处逢生②[日]荒木见悟著,廖肇亨译:《大慧宗杲论禅悟》,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15 卷,第4 期;有关大慧宗杲“疑情”的研究,可参见[韩]吴容锡《大慧宗杲看话禅之“疑情”研究》(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道盛以“疑情”释“怨”,即是将“怨”视为宗教修行中最紧要的环节。从“怨”所指极端痛苦愤懑的情感状态来看,它与“疑情”是同质的。这种宗教性的情感不同于自然情感,不会随着境遇迁转。它是主体所有迷闷的汇聚,因全部精神灌注而产生无穷能量,含藏着改写世界图景的可能。
“怨”是自我成就、即佛教所谓“自度”的必经之路。道盛云:
此怨之一字,即吾禅门疑情也。所谓臣不得君,子不得父,乃至不得于朋友百姓,皆此自怨之疑情。孟子善于形容大舜,谓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此正是自怨自艾,自起疑情。曰:“我何以不得于父母兄弟哉?”非有怨恨于顽父、嚚母与傲弟也。才有怨及父母兄弟,则此自怨自艾之心终无以自悟,亦终不能感格其父母使底豫也。参禅人不返求诸己,我如何不明我自己性命,如何却被妄想之所流转?毕竟我如何作得主,妄想生死又从何而有?只如此痛切参去,更无第二人,更无第二念。久久伎穷俩尽,一旦顿断命根,便是大事了明也。今人参究而不悟者,皆是为生死心不切,与不能久远痛愤耳。③《胡洪胤盛高姚诸士云莲净修禅侣请茶话》,《天界觉浪盛禅师全录》卷9,《嘉兴大藏经》第34册,第648页。
其所描述的参悟过程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不平→自怨(反求诸己)→疑情→不明自己性命(生死心切)→久远痛愤→顿断命根(大事了明)。其中有两点需要留心。其一,这是一个自我修炼过程。个体与世界撞击而引起种种“疑情”,疑情积聚而进入精神极度痛苦的激情状态,是为“怨”。怨不是对境遇不公的愤恨,它是自身性命尚未明彻的痛愤。其二,要进入这种状态,必须有极为顽强的求道意志。道盛所谓“生死心切”,大杲所云“过人底愤懅”,弘智说“古人拼定一生两生,只是一个痛切发愤”④《示众》,《青原愚者智禅师语录》卷2,《嘉兴大藏经》第34册,第826页。,都是说要有过人的勇气与执着。无力与现状决裂者不能发动疑情,不能忍受无路可走的痛苦者无法直面疑情,不能从废墟中重建自我者难以突破疑情。只有真正全力追问“从哪里来,到何处去”的人才能通过这种痛苦的试炼,所以“须是大猛烈汉子始得”。
“怨”也是“度人救世”的必要条件。前引道盛所云“以正直之气发天地人物不平之气,会归于天地中和”即此意。这是极其宏大的济世理想。其实现的主要思路是通过求道者(个人)的“正直之气”(怨怒)→激发众生(群体)的“不平之气”(疑情)→走向(始终在进行中)“天地中和”(理想)。众生本来具有的道心与人情就是世界由乱复治的根本,但它们需要激发。所以大杲说怨怒“生生化化”,弘智说怨怒“变易天地人物”,都是立足于个体至情激发群体生机的可能。
道盛说“吾人真心顿发,足以惊天地、感鬼神,曾无人物山河之能隔也”⑤《开示堂中人》,《天界觉浪盛禅师全录》卷7,《嘉兴大藏经》第34册,第634页。,至情是真心的发动,是个体活动能量的显现。佛教宗师的责任就是发动求道者的真心。道盛自诩云:“宋元已前,但能使人疑情起,不肯教人起疑情。山僧虽无实法与人,然亦不敢孤负来机。”⑥《戊寅圆通问答》,《天界觉浪盛禅师全录》卷11,《嘉兴大藏经》第34册,第655页。“来机”指参询者自身的求道热情,没有什么现成“实法”可以安顿它;只要培育它,使其壮大为生命体验聚焦的“疑情”,就能产生惊天地感鬼神的能量。道盛并不为人指点迷津,他看重的是人心本有的“热性”:
自予本来热性,一朝触发,直欲八面燎人……古人师资激扬,参证心法,是皆热性相摩,触发本有灵焰,而传此千圣不传之密旨也……参学之人,若非热心相激,真性洞明,又安能迸出胸襟、透出顶,使此灵光独耀,迥脱根尘,而光天照地、耀古腾今也哉……盖传灯者,传此热焰也。惟此热焰,乃能烧绝生死知见,透出真性灵明……其火所触之处,更不容他一物,而又能成一切物也……孰不有此热性?设使不遇师友真火触发,又安能透此灵焰,与佛祖争光,而照彻天地哉?①《五灯热序》,《天界觉浪盛禅师全录》卷21,《嘉兴大藏经》第34册,第713—714页。
“热性”蕴涵“八面燎人”的能量,它通过人与人“相摩”“相激”而“触发”“迸出”,成为具有破坏力与再生力的“热焰”。此“热焰”与“疑情”“怨怒”同体而异名,都是个体精神极为旺盛、活跃、富有能量的状态。道盛一派有自我燃烧似的求道激情。他们设想的“即怒怨而致中”,即求道者之“真火”激发无数火种,世界成为大冶烘炉,“人心行处灭绝后重苏”②《天界觉浪盛禅师语录》卷7,《嘉兴大藏经》第25册,第719页。,最终通向“光天照地、耀古腾今”的理想过程。
文学为这种孤绝的人生状态、极端的情感体验赋形,因而成为带动天地生机流转的枢纽。道盛举《史记》所传项羽《垓下歌》,谓之“首二句轰轰烈烈,感愤千状,是造物之逼杀英雄。直使风云失色而天地无光”。因此,作品呈现的情感“似与道德性命无甚关系,然而往往有为乾坤吐气”,“若无此一笔,便不能使千古英雄一段精光永永流传于天地之间”③《天界觉浪盛禅师全录》卷32,《嘉兴大藏经》第34册,第782页。。弘智云:“诗不从死心得者,其诗必不能伤人之心,下人之泣者也。”④方以智:《范汝受集引》,黄德宽、诸伟奇主编:《方以智全书》第10册,第32页。从“热性”传递的角度来看,只有展现创作者激情状态的文学作品,方堪为火种传递的中介、激发读者潜藏的精神热力。
重视激情的文学观虽然由道盛一派刻意阐发,在遗民僧中却有共同的思想基础。首先,不少遗民僧都有重视“疑情”或亲身“起疑”的经历。岭南曹洞宗宗宝道独云:“疑之一字,切之别名耳。总是生死心切,便自起疑。”⑤释道独:《宗宝道独禅师语录》卷2,《卍新纂大日本续藏经》第72册,第119页。函可云:“要学此道,必须发个狠毒,将无始来一点习气千难割、万难割处痛下一刀……思量、计较尽时,平生伎俩一点也用不着,莫生退怯,莫求功效,正好拼命与之厮捱。”⑥释函可:《千山剩人禅师语录》卷5,《嘉兴大藏经》第38册,第240页。其次,不少遗民僧都有以文艺作品惊醒世人、起疑发悟的意识。弘储自称:“惯自将四大海为一枚砚,须弥山作一管笔,向太虚空里横写竖写,忽然写出个地狱变相,直令人与非人,顿生无限怕怖。”⑦《与金刚庵卧云梵月二禅师》,释弘储:《灵岩树泉集》卷下,第49a页。戒显云:“一字一句,如入万山深处。荒寒幽悄,使人毛发俱慄。”⑧释戒显:《和天台三圣诗序》,兴慈编:《合订天台三圣二和诗集》,《大藏经补编》第14 册,台北:华宇出版社,1985 年,第732页。这都是将参禅经验与文学经验合而为一,从宗教功能上理解文学的价值。由此观之,遗民僧的“怨怒”文学观除了动荡时代的情感回响之外,还包含了超凡入圣的宗教情怀,是佛教济世悲愿的文学折射。
结 论
遗民僧是依据政治立场及伦理取向而归类的佛教僧侣群体。他们有重大的社会和文化影响,在清初文学与中国佛教文学史上也非常重要。其代表人物如苍雪读彻、无可弘智、晦山戒显早已受当时执诗坛牛耳者如钱谦益、吴伟业、王士禛等推崇;清初刊刻的各类总集中随时可见他们的作品。相同的政治立场选择背后是相似的价值选择、文化认同与宗教信念,它们造就了遗民僧作品与文学思想的群体特征。
一些遗民诗僧如读彻、函可、澹归已受到学界关注,覃召文云:“这些爱国诗僧的作品由于内有道德之蕴,故其为辞有歌有怀,其为声亦悲亦壮。”①覃召文:《中国诗僧纵横谈》,第222页。李舜臣亦云,一些岭南诗僧具有“深沉的天下意识”,“诗情郁勃,汪洋恣肆”②参见李舜臣:《岭外别传:清初岭南诗僧群研究》,第183—186、202—217页。。这些评价都触及遗民僧诗的群体风格。不过,风格所从何来从未被深入讨论,也几乎无人对遗民僧进行群体性诗学研究。
如果将遗民僧与清初儒者遗民横向对比,二者重感情、求至情乃至尚怨怒的主张都一致。他们同受易代冲击、有同样的政治立场和振济天下的自我意识;他们声气互通,文学思想也交互影响。二者的差异也是显著的。儒者遗民的重情论以“真”为基底,以特殊时代个体的真实情感体验冲破统治秩序规范;强调“真”与“正”的统一,自信伦理情感的正当性。遗民僧的重情论有明显的宗教色彩。“情”是万法众生之俗情,也是世界关联的纽带和生命能量的显现;它常常将人推入精神绝境,必须经其磨炼方能进入宗教圣境。遗民僧都是富于现世关怀的入世僧,无论为了自度还是度人,他们都肯定俗世的情感。
如果将遗民僧放在文学史纵向坐标上,其独特性更为突出。在中国僧诗史上,他们不同于主流诗风的清寒枯淡。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诗言志”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情感至上论非常罕见;谈到情感强度问题,很少有人突破“温柔敦厚”规范:即使怀有大悲大恸,在诗文中也要力求委婉表现;以极端激烈的情感体验为诗心,是一般人不敢想更不敢说的。乱亡时代的危机感与济世热忱使遗民僧表现出热烈、刚健的精神气质,在中国诗学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观察,“怨怒”情感要求是一次由下而上的文化突围。儒家诗教要求“温柔敦厚”,中国古代诗歌讲究含蓄深沉,出于自上而下的情感规范需求。古典政权注重维持社会平稳,希望臣民克制、安分、忍耐,要求文艺发挥平衡情绪的作用;士大夫文人是这一文艺观的维护者,其精英意识又使他们态度矜重,不肯喜怒行之于色,自我驯化为限制情感的实践者。塑造情感为适度的、平衡的、令人愉悦的(包括悲情的审美化),既无害于秩序稳定,又典雅端庄:情感驯化实际上要求个体由内而外地服从固定的群体秩序结构。
遗民与遗民僧推崇极端情感体验,底色是民间文化人在社会秩序动荡时期迸发的文化领导权要求。易代之后,他们没有政权认可的政治与文化权力,却拒绝承认新朝的合法性,以续绝存亡者自居。其领导权只能通过惊醒一般民众,唤起其文化自觉来行使。他们倡导令人不安的、刺激性的、逼迫式的情感,就是要发动社会能量去改变现状。这种意识与晚明以来下层士人话语权的扩大有关。晚明下层文人群体如复社,通过出版、集群、交际等渠道放大文化话语权,甚至有效干预过政事。明亡之后此种权力意识在汉族士人中延续,也折射于文艺思想。不过,遗民与遗民僧仍然有实质性的差异。儒者遗民的权力意识主要体现为保存文化的内敛方式,遗民僧却显现为带动世界恢复运转的外放热力。再追究下去,遗民尚握有承继先朝的文化权,僧侣却一直处于权力系统边缘,又何敢自命为“会归天地中和”?这只能归因于宗教入世精神的释放。它是易代之际民众对抗新朝权力意志的集结,也反映了晚明以来佛教的进取精神。概言之,遗民僧试图打开一条通过释放个体能量以激活群体生机的绝地求生之路,将之称为中国文学思想史上重情论之巅峰,当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