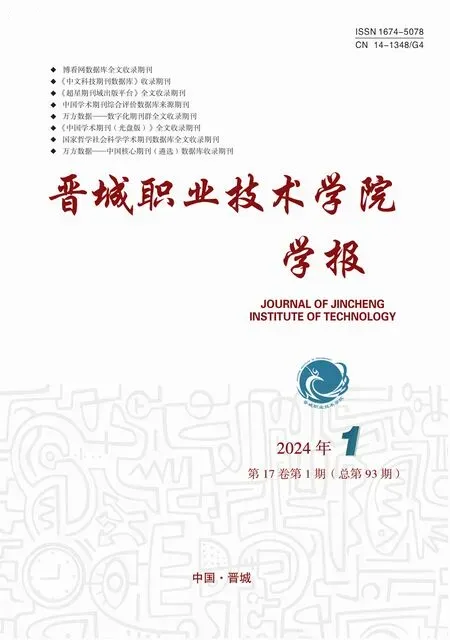由沈从文“寄食者”群体生存状态看其文学创作的生命观
何 欢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昆明 650000)
沈从文曾明确表达过自己的创作动机:“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的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1]。这座小神庙在沈从文笔下宛如一个人性的试验场,每时每刻都有不经意的偶然发生,每时每刻都上演着不同人物的悲欢离合。在沈从文所创造的湘西世界里有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强健的水手、博爱的老妇人、大自然的女儿翠翠,也有凶恶的土匪、神秘的巫婆和水边摇曳的妓女。而这其中就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作者往往称她们为“寄食者”,她们是出卖肉体换取生存的妓女群体,却也是这座神庙里最为重要的一类人物。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涉及到妓女群体的作品主要是《丈夫》和《柏子》,两部作品都在极力塑造着这一群体因身份的独特性而导致的生活独特性。这样一种为世人所不齿的身份,在沈从文笔下却有着独特的魅力,她们如翠翠,在环山伴水的湘西世界里养成了敢爱敢恨的自然之美,却又如潇潇,被困在这无尽的山水时空之间。她们的矛盾正是作者的矛盾,这种矛盾是作者基于自己所建人性之庙所展现的一种辩证的生命观。本文的生命观主要定义为:沈从文笔下的“寄食者”群体在面对变化万千的世界时的生存形态以及她们所展现出的特有人性。
一、自然孕育下的真挚生命观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如同与世隔绝的桃花源,在这里即使是“吃四方饭”的妓女,也有着未经雕刻的天真和自然。而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有情爱,有亲情,也有乡民之间和谐的邻里之情,正是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与自然让这些“寄食者”们的特殊情感得以安放。在沈从文的笔下,妓女这一群体展现着生命的朴实一面,即用着自己的方式来对生命进行不懈的追求。
(一)《丈夫》中生存压迫下的人性抉择
沈从文在塑造“寄食者”的情感时,主要是以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来进行描写,从而体现了城市与湘西乡下的区别,这一对立在《丈夫》中表现得较为明显,老七迫于生存压迫,选择从乡下到了城市,最后又从城市的泥淖中回归乡土。《丈夫》主要讲述的是在家种田的丈夫过节来到城市花船上看望妻子,在这过程中受到屈辱,最后携妻子一同返回故乡的故事。在沈从文的描述中,丈夫看到老七无论穿着打扮还是言语对话都沾染了城里人的习性,生存本能欲望的满足使她无意识间失去了人性中那份淳朴与神性,现实生活的泥沼蒙蔽了她的双眼,让她无意堕落却又不得不堕落。丈夫的到来唤醒她本已沉沦的内心,于是她选择离开花船同丈夫一起回到乡下。
老七的丈夫,从开始见到妻子的高兴、乐观、没有羞辱感,到与水保交谈后拘谨而感到羞辱,最后士兵闹船与妻子一同返乡,整个过程是一个神化至美人性变为人化人性最后又回归至美人性的过程。而老七这一角色的人性变化就更为明显,从最初做活补贴家用的单纯愿望到不自觉沾染上城里的“恶习”再到最后被丈夫唤醒回归家园,做到了完全意义上的人性回归。人化人性是现实生存中人面对生存压力而呈现的一种生存状态,而神化人性则是沈从文湘西世界中人物的基本特征,是“在深层次上抵制着城市文明的拓展,为逐渐落魄的古老宗法农村社会人的生存状态注入了一股强心剂”[2]。通过沈从文笔下的两个人物可以看出,沈从文对湘西淳朴的神化人性的赞美往往带有对城市人化人性的批判。
在沈从文的笔下城市永远是黑暗、肮脏的,那里四处都散发着灵魂的腐臭,而湘西乡下却是一个完全干净、自然的庙宇,所以沈从文对“寄食者”们总是带有合乎自然的包容。老七从乡下来到城市,在沾染一些“恶习”后又回到乡下的整个过程,正是沈从文建造湘西世界时,面对外来文化入侵的一种态度,也是一份最纯真的理想——至美的人性将唤醒被人类文明所侵蚀的恶习。在《丈夫》中,在乡村与城市,即美与丑的强烈对比下,“寄食者”们原始单纯的情感和自然健康的生命欲望得到了沈从文的肯定。
(二)《柏子》中自由情爱下的生命本质
在沈从文的“湘西式”生活里,有青年男女的纯真悸动、乡民之间的笙磬同音,也有看似不合伦理的事情轮番上演。小说《柏子》中妓女与水手通过大胆而自由的爱情来暂时逃脱自己生活的困顿;小说《丈夫》中丈夫与船妓妻子通过自己的方式经营着他们的爱情。虽是屈辱地顺从生活,可正是这些行常人所不能行、见常人所不能见的另类人物,才使得这座小神庙富有且真实。
1.原始情感的袒露
在这片没有被现代文明入侵的地域上,湘西的一切都宛如自然神灵亲自捏造,即使是“寄食者”们也有其独特的灵气所在,这种灵气主要表现在“寄食者”们对自我情感的真诚以及尊重上。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是充满旺盛生命力的,是粗蛮与纯真交织的,特别是在小说《柏子》中,这份真挚而肆意大胆的感情便更为明显。
《柏子》主要讲述的是水手柏子与妓女用他们独特的方式经营着他们自己生活的故事。如果说《边城》中的翠翠是湘西世界自然孕育的女儿,拥有清明如水晶的眸子和山雨一般清澈的情感,那《柏子》中的水手便是湘西世界风雨泥沙里幻化的男儿,是绿树浑水里生长的山大王,可以爬上桅杆肆意歌唱,可以在生存之余尽情笑骂,无论是欢笑还是困苦,他们都那般豪爽而畅快。正因如此,他们所爱上的女人也同他们一样豪爽而纯真,“性格弱一点儿的,接着就在梦里投河吞鸦片烟,强一点的便手持菜刀,直向那水手奔去”[3],她们将自己生命最深处的真实融入那些真切的爱恨情仇中。辰河的发达使岸边的妓女得以生存,同时也养育了她们如水流般倔强而柔韧的性子,吊脚楼锁住的仅仅是身体而非灵魂,在来往过客里寻找那份真情并用心经营是她们与艰难生存对抗的方式之一。如柏子的情人,会在吊脚楼等待情郎归来,会担心柏子的安危,会为柏子的到来抹上香油与脂粉,嘴上骂着心里却也为柏子的归来泛起小小涟漪。
虽做着最不被世人所接受的职业,但沈从文依然从中挖掘到那份尚未被城市文明所侵蚀的人性之光。沈从文通过描写二人重逢来着重表现柏子与妓女之间那份超出生理需要和本能满足的情感,有妓女因思念常伴的细微动作,有久别重逢后短暂的欢愉,有离别之际的叮嘱眷恋与山盟海誓。文中提到青浪滩那边的女子“更标”,但柏子依然选择跟着船回来与自己的情人相会,明知对方是个以出卖肉体为生的妓女,但在柏子眼里她不比任何人逊色。而柏子的情人也如此,在来来往往的商客里选择坚守那份与柏子独一无二的真情,会担心他到常德府找“乐子”,会埋怨他与自己数月的分离,这份爱是超越身份职业、不带有任何偏见的,是原始生命交织而迸发出的情感的一种自然流露,读者能在这些只言片语里感受到二人那份超脱肉欲的情感,实现“灵”与“灵”的融合。
相较老舍笔下的作品《月牙儿》和《骆驼祥子》,沈从文通过淡化故事发生的社会背景和人物所真实经历的人生来突出那份湘西世界特有的至美人性,同为妓女,月牙儿与柏子的情人几乎是两种相反的色调,“沈从文侧重于表现下层妓女卑微却不失人性美好的精神”[4]。同被生活所困,祥子与柏子的结局却完全不同,将三部作品结合来看,更加能体现沈从文创作的独特浪漫,即在平凡人的生活里找寻那份淳朴的诗意人生。
在《柏子》里,妓女在生命的压抑与生命的本能之间倔强而自在地活着,她们所表现的这种本真而自在的生命形式,也正是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所独有的。面对鱼肉欢愉,“寄食者”依然留存的纯真情感使我们更加清晰地感受到沈从文高度审美化后的湘西世界,是过滤愚昧与畸形后留于平凡人生命中的那份真性情和真古朴。在对她们抱以怜悯的同时也真真切切感受着她们本真的生活和那份简单而真挚的欢乐。
2.原始生命力的绽放
同样是写乡土世界,鲁迅笔下的乡土萧条而荒凉,充满了对国民性的批判,而沈从文的乡土却洋溢着生命的活力与爱欲的张扬。在沈从文的湘西世界里,很少见到自我压抑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寄食者”群体,她们要比任何人都能直视自己的内心,“寄食者”们坦然接受自己的命运,直面生活的重击,不被命运完全左右,深陷泥潭依然平视于泥沼中挣扎的自己。她们身上简单质朴、自信以及敢爱敢恨的精神特质都是生命之花自由绽放的养分。
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提到“文化不仅压制了人的社会存在,还压制了人的生物存在”[5]。在沈从文眼中,性爱是人存在的一种方式,是“生命意识的一种符号”,因此他不断用那些寄食者与水手合乎自然的相处方式来抵御文化的入侵。在爱欲与道德的天平上无条件倾向生命欲望的释放。这种放在现代不合乎伦理的情感,在这座小神庙里也找到一个相对自洽的存在方式。
在湘西世界里水手与妓女好像有着天然的关联,他们之间的爱并不那么轰烈和璀璨,更不会像一些历史人物一样值得歌颂,但这两个群体的结合往往又能散发一种独特的美感,这种美感使人忘却所谓的伦理道德只着眼于那份“灵”与“灵”之间的交流,水手能在“寄食者”身上获得心灵的慰藉,而“寄食者”们也能在水手身上感受到超出困苦生存状态难能可贵的爱。吊脚楼的妓女对水手一片痴情,而水手也对她们用情专一,这种人人平等的理想化生命秩序正是现代都市没有的。那份真挚纯洁的心灵将肉欲横流的肮脏与纸醉金迷的丑恶一并洗刷干净,留下的只是生命最为本真的坦诚相见,是自然而淳朴的两性关系。
神性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无处不在,不仅有翠翠的灵气,又或是三三的健康,还有《柏子》吊脚楼上等待情郎的“寄食者”们,她们是湘西下层人民中独有的一种生命形式的典型。她们在屈辱生活中保存着纯洁而真挚的情感,在与情郎相会时尽情释放自己的生命欲望,在她们身上没有因为职业而暗淡干涸的人性,更多的是面对生命“非常态”形式时的游刃有余和坦荡。沈从文笔下的“神”存在于芸芸众生之间,是不同生存状态下最本真而自在的生命形式。
面对生命本能的欲望,《柏子》中的妓女是大方、自然的,她们有着山水雕饰后的野性,即使能在字里行间感受到她们悲凉凄苦的宿命,但依然会对她们的所言所行钦佩。在现代文明的压抑下,无论男女都被规训得那么统一,面对情爱时的难以言表又或是面对自身欲望时的错愕压制,在这山水相隔的湘西世界里这份“文明”便不复存在,她们率性泼辣,在粗鄙的言语里饱含着对情郎的关怀。这种自然的两性关系是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批判,更是对女性这一群体所拥有的独特价值的尊重。
二、环山里的悲剧宿命观
沈从文一直想要用古希腊式的健康质朴的生命形态以及田园牧歌式的创作笔调构造出那个自己所想象的湘西乌托邦,以此来完成他想要“重塑”民族精神的愿望。绵绵流淌的沅水陪伴了沈从文的整个童年,也使他对水的喜爱异于常人,而水这一意象正与其生命观密不可分,在沈从文的大部分作品中,水是一种生命力的呈现,湘西生活的人与事都和水不可分割。青年从军的生活经历也是推动沈从文生命观形成的一大原因,在《从文自传》中沈从文提到自己在这一时期看到大量血腥的画面,死亡意识也在这一时期萌发,军旅生涯使沈从文真切体验到了人世间的黑暗与残酷,对生命的思考不断加深。
在现代文学作品中,妓女往往是肮脏社会的代名词,她们往往是社会环境异化的符号,但沈从文作品中的“寄食者”群体却并非如此,她们是“食”与“性”冲突下产生的悲剧,艰难生存环境下依然保存的纯真灵魂成为她们的遮羞布。虽然艰难的生存环境没有消弥她们对自己生命的负责和对爱的向往,却也让她们在追寻自我生命的过程中饱受摧残。
(一)爱欲分离的悲剧宿命
沈从文笔下的男子大多雄健强壮,而女性则大多有着柔和之美,这种柔和并不是一戳而破的绵,而是像水一般有着自己的韧劲,对生活有一套自己的活法,对自己的生命更是给予高度的尊重与负责,这种尊重往往是以更为迂回的形式表现出来。就如沈从文自己所说,“天下的女子没有一个是坏人,没有一个长得体面的人不懂得爱情。一个娼妓,一个船上的摇船娘,也是一样的能够为男子牺牲、为情欲奋斗。比起所谓大家闺秀一样贞静可爱的,倘若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心,女人的心是在好机会下永远向善倾向的。女人的坏处全是男子的责任、男子的自私,以及不称职才是女子成为社会上诅咒的东西。”[6]与此同时,这些“寄食者”的哀乐也常常伴随着历史的隐痛。
作为沈从文理想的产物,湘西世界并非都是完美的,“寄食者”们在自由释放自己生命力的同时也摆脱不了小人物的悲剧宿命。沈从文的“寄食者”群体像是一个矛盾的共同体,作者既希望她们野蛮肆意、没有边界地生长,同时也对她们透露着或多或少的怜悯,这一怜悯主要来自这些“寄食者”们悲剧的人生结局。当这些“寄食者”们年老后或许流落街头,或许因为感染疾病而死,或许一代一代在成为“寄食者”这条路上反反复复,昙花一现的悲剧结局是沈从文不想看到的,他渴望这些“寄食者”拥有冲破封建牢笼的新思想,拥有独立的意识,继续坚强生存下去,但又不愿放弃在现代文明冲击下“寄食者”们消退的自然生命力和健康纯洁的心灵。
《丈夫》中老七虽爱自己的丈夫也不得不因生活困顿去做船妓,老七的离家表面看只是离开丈夫,实际上是将丈夫与她的爱与欲一并带走。迫于生计,老七与丈夫同许多村民一样将做船妓看作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若非丈夫的到来老七不会意识到二人早已被剥夺的爱与性的权力。在沈从文的小说里,湘西的男子往往身强有力而女子往往逍遥自在,但在《丈夫》中丈夫的形象是懦弱的、卑微的,老七的形象是隐忍的、柔弱的,面对权力被剥夺他们无法反抗只能逃回乡下去。老七在回与不回间毫不犹豫选择了前者,这一抉择背后隐匿了多少她对丈夫的爱,以及因为生活困顿当初不得不爱欲分离的苦楚。
相较于《丈夫》,《柏子》中的柏子与情人则很符合他对小说人物形象的一贯塑造,柏子无拘无束地简单生活着,最大的愿望便是登船上岸去寻那固定的妓女,柏子的情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在一个个日夜里思念着情郎的归来。欲望的蓄积那样充沛,欲望的满足又那样痛快,二人在极端的压抑与释放之间很容易产生幻灭感。作为妓女本身,她的生命里充满了悖论,为了想要的生活不得不与另一种生活做交换,靠肉体的交易来解决谋生及爱情的需求。妓女潇洒自在,同柏子嬉笑怒骂的背后隐藏着清醒的头脑,时刻提醒着自己将爱与欲分离,这种撕裂感与欢愉过后的幻灭感正是平凡人生活常态里最难以诉说的悲痛。
沈从文以“贴着生活写”的原理构造着梦中的湘西世界,用同时期文坛上“非主流”的视角书写着另一种真实的人生,他将触角伸及普罗大众非正常的常态生活中,同时也将那些难以言说的隐忧和悲苦埋藏于字里行间。生命的绽放不仅仅源于欲望与无畏的灌溉,更有着风吹日晒时深深扎根的困苦,而这在狂风暴雨里高歌的勇气更是证明了生命坚韧的存在。
审美性与悲剧性共存是沈从文创作的常态,也是他看待湘西世界的一种态度,因此也造就了他质朴而有些落寞的笔调,用最温淡的笔调书写着湘西世界里这些“寄食者”们最为真切而悲苦的一生,也用审美化的叙事方式讲述着她们苦中作乐的坚韧生命观。
(二)永远无解的宿命镣铐
尽管沈从文极尽笔力来美化湘西世界,许多读者依然能够从《丈夫》中感受到沈从文在打造这座“希腊小神庙”时的徘徊,即环境的闭塞使得这些妇女无法从现状中抽身,但文明的侵蚀又何尝不是另一副明晃晃的金镣铐。在这个文明与原始的拉力游戏里,沈从文最终还是选择了原始而真实的人性,选择用一种浪漫的理想式描写作为结局。比起文明的侵蚀,选择最小化那些人身上的困苦,就如老七虽拥有与外界沟通的机会却依然选择回归那个贫困而简单的生活,这一充满希望的结局也是作者对他们生活的美好祝愿。我们都知道“希腊小神庙”只是作者构建的一个梦境,既然是梦就总归要有醒来的时候。老七与丈夫回乡后是否能支撑他们的生活,老七是否还会因为生活的困顿而重蹈覆辙,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但至少在这一次的选择中我们看到了苦难下的人性光辉。
在“名分不失,利益存在”[7]的不正常观念影响下,老七也渐渐习得城市里的恶德,是丈夫看望时首先关心钱财的言语,又或是醉鬼闹事时她的“急中生智”。丈夫的到来将她从麻木漠然中唤醒,最终在贫穷而困苦的生活压力与人性尊严面前,老七选择了人的尊严。与《丈夫》类似的柳暗花明式结局还有《萧萧》,变成城中女学生的梦虽未实现但总归算得上善终。沈从文对生命最为淳朴的人性的笃定,造就了他作品中女性的结局,在同情她们的同时也坚信着那份来自山水馈赠的纯良天性不可磨灭,老七的结局正是一种宣告:并非每一个人都会被“文明”侵蚀。
比起老七和柏子情人的真情与潇洒,沈从文在《一个多情水手和一个多情妇人》中对夭夭的情感要表现得更为复杂。男权社会下生存的她,十九岁便被卖给五十岁烟鬼,“只要谁有土有财就让床让位”,而年轻的夭夭“对于钱毫无用处,却似乎想的很远很远”。夭夭同老七和柏子情人一样,有着所想所爱却要被禁锢在这片滞后而闭塞的牢笼里,她们将水手看作自我与外界沟通的唯一使者,期待着获得一份心灵上的慰藉。从夭夭身上可以看出,她所拥有的人性之美不仅仅是那份真诚的渴望,更是即便手铐枷锁也依然想要望向远方的决心。夭夭是独特的“原人”,除了有老七和柏子情人的纯真,更有那双憧憬未来而放光的眼睛和鲜活的生命力,体现着湘西世界里女性身上最为明显的标志:面对悲惨命运时永不退缩的精神和向往未来的坚定,这份坚定无关他人仅仅只是作为生存在世界上的个体——她们自己。
面对夭夭的职业,沈从文没有看轻她;面对夭夭的悲惨经历,沈从文也无法帮助她。他能做的只是将自己的怜悯与关怀沾上墨汁洒向纸间。沈从文曾说过:“我的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都欣赏我的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够欣赏我的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8]在展现和歌颂人性真善美的同时,沈从文也无可避免地将故事染上一层宿命的悲剧感。自然真挚的背后是无法挣脱的死循环,就如同夭夭最后的歌声,虽明亮悠长却也只是缠绕在那一层层山峦之间,无法真正与外界得到沟通。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的时间如同那缓缓沅水,看似流动日新月异,实则如同一滩死水仅泛起的一点点涟漪也将被那些“不变”的人或事抚平。这使得沈从文作为一个返乡人,在面对夭夭命运的沉重时也只能是“我觉得他们的欲望同悲哀都十分神圣,我不配用钱或别的方法渗进他们的命运里去,扰乱他们生活上那一份应有的哀乐”。
桃花源的背后是与社会相脱节的生存环境,或许在外人眼中它是“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又或是“黄发垂髫,怡然自乐”,但作为生存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并非心甘情愿地在那里生活。面对畸形丑恶的现代文明,极致的人性之美无法得以合理安放,二者的碰撞也必然变成物极必反。在文明进步的现今,“希腊小神庙”里那些纯净的灵魂该不该留、如何留都是沈从文思考的问题,当生命存在的两种极端碰撞在一起时如何将它们进行合理安放,正是丰富沈从文生命观的一大养分。沈从文“希腊小神庙”的自然与风土人情之美总是让人遗忘那些生活在潮湿泥土上的小蝼蚁,她们就像蝴蝶翅膀上的一粒灰尘,被裹挟在历史的微风里,晕头转向。而恰巧是这些尘埃让湘西这一看似干净的世界也蒙上点点灰尘,使得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及其生命观更加完整和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