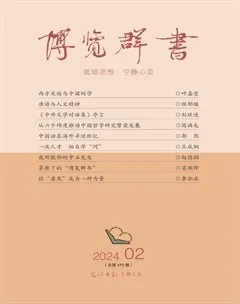“土于盆”还是“上于盆”
孟昭连
《促织》以一只小虫写人生故事,其情节的曲折跌宕,主人公命运的沉浮变化,深深吸引着读者,表现出特有的艺术魅力。但因为作者运用的材料是促织,而促织之戏又是我国古代早已有之、颇有成规的民间娱乐活动,具有很强的“专业性”,这就使《促织》故事也具备了某种特殊性。《促织》写主人公捉到青麻头促织后,持虫回家,“土于盆而养之,蟹白、栗黄,备极护爱”。但在蒲松龄的几种抄本中,有的“土”误为“上”。自此引起了究竟是“土于盆”还是“上于盆”的争论,持续时间数十年,直到现在还是各说各话,无法统一。由于《促织》很早就编入了大中学校的语文教材,涉及的读者面极广,所以这个争论的影响所及,也非常广泛与深入。
“土于盆养之”
首先应该明确,《促织》虽属小说,但故事非凭空虚构,创作素材是有所本的。明末刘侗、于正奕的《帝京景物略》是《促织》取材来源之一。该书卷三“城南内外”中有“胡家村”条,记永定门外胡家村“禾黍嶷嶷然被野”“禾黍中荒寺数出,坟兆万接”“所产促织,矜鸣善斗,殊胜他产”。下面就详细记述了当时京师人玩斗促织的盛况,并介绍了捕捉、畜养、格斗、繁殖的方法,及促织的著名品种。《促织》的很多文字就来自这里。
《帝京景物略》上原本就是“土于盆养之”,蒲松龄乃借用现成说法。“土于盆”之语在《帝京景物略》中属于促织的“留”(即留种繁殖)部分,原文是:
促织感秋而生,其音商,其性胜,秋尽则尽。今都人能种之,留其鸣深冬。其法:土于盆养之,虫生子土中。入冬,以其土置暖炕,日水洒,绵覆之。伏五六日,土蠕蠕动。又伏七八日,子出,白如蛆然。置子蔬叶,仍洒覆之。足翅成,渐以黑。匝月则鸣,鸣细于秋,入春反僵也。
在现有促织史料中,这一段是最早谈到促织人工繁殖方法的记载。在此之前,玩赏促织均是捕捉自然界的野生虫再加以驯养。不过用此法繁殖的促织野性不足,一般不能用来搏斗,只能作为鸣虫畜养,听其鸣声,所谓“留其鸣深冬”(拙著《中国鸣虫》曾详考过这个问题)。繁殖的方法是将交配过的雌性促织养在盆中,盆底铺有细土,让雌虫在土中产卵。这种土很松软,利于雌虫尾后的产卵管插入。“土于盆养之”的真正含义正在于此。刘侗在叙述这个过程时,共出现了四个“土”字:
土于盆养之,虫生子土中。入冬,以其土置暖炕,日水洒,绵覆之。伏五六日,土蠕蠕动。
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从先到后,都是围绕着“土”字在叙述,非常严谨。第一步,把(雌雄)蟋蟀用放入松土的盆养起来。第二步,雌雄蟋蟀交配后,雌蟋蟀将产卵管插入土中产卵。(注意,这两步是在秋天蟋蟀正值盛龄期进行的,然后将卵放到常温下保存。)第三步,到了冬天,将产卵的土移到热炕上,每天用喷壶往土中洒水,并用棉被盖起来保温。第四步,过了五六天,土中开始有动静,好像有小虫子要爬出来。再过七八天,大小如蚂蚁的白色小蟋蟀就出来了。足翅渐成,小蟋蟀由白变黑,一个月之后就能鸣叫了。刘侗记录的这个完整过程,仍然是现代京津一带鸣虫爱好者人工繁殖冬虫的基本方法。这四个步骤,每一步都离不开土,离开土整个过程就被破坏了,也就不存在了。正因为第一句是“土于盆”,才有了第二句的“生子土中”以及下面的“以其土置暖炕”“土蠕蠕动”,小蟋蟀正是在土中孕育了新的生命。倘若把“土于盆”改成“上于盆”,下面三句中的“土”从何而来?
值得一提的是,在《帝京景物略》里,这部分内容是讲蟋蟀的繁殖方法,但蒲松龄不明此理,把这句话用在雄性促织的畜养上,所谓“土于盆而养之,蟹白栗黄,备极护爱”,这就不对了。畜养雄虫的盆中虽需砸“泥底”,但那是用粘土、细沙、陈石灰再加水混合而成的,干后硬如铁石,严格地说只能算“泥”而不是土。这不能不说是蒲松龄的一个小小失误。
《帝京景物略》“胡家村”条记载的上述内容,后来又被多种文献收入,考察相关文字的内容,也可证明“土于盆”在这些文献中都是一致的,没有“上于盆”的说法。
《古今图书集成》是康熙到雍正年间历时二十八年编辑的一部大型类书,被称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此书博物汇编禽虫典“蟋蟀部汇考”就收入了“胡家村”条全文,但改题为“刘侗《促织志》”,并将内容细分为“产、捕、辨、材、斗、名、留、俗、别”等几部分,“土于盆养之”就在“留”的小题下。由截图可以看出,“土于盆”非常清晰。
刊刻于乾隆四十一年的著名蟋蟀谱《蚟孙鉴·原序》有云:
余平生于游戏三昧之事,靡不为之,惟促织未之讲也。每见秋来醉心于此者,心窃笑之。及读麻城刘同人先生所著《帝京景物略》,中载胡家村一则,乃知一物之微,其足动人爱护也如此,其足费人精详也如此,不禁油然有动于中也。
之后便照录《帝京景物略》“胡家村”大部分内容,人工繁殖蟋蟀的方法恰在其中,“土于盆养之”清晰可见,毋庸怀疑。
《钦定日下旧闻考》是乾隆年间于敏中、英廉奉敕编撰的北京史志文献书,全书共分星土、世纪、形胜、城市、官署、苑囿、风俗、物产等共18门,内容浩繁。在此书的“物产”部分,有“臣等谨按:胡家村在永定门外,今尙产促织”字样,下面即照录“胡家村”条人工繁殖蟋蟀的文字:
促织感秋而生,其音商,其性胜,秋尽则尽。今都人能种之,留其鸣深冬。其法:实土于盆养之,虫生子土中。
有意思的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人工繁殖蟋蟀的方法,到了清代还传入宫中,以致冬日的紫禁城里响起蟋蟀、蝈蝈的鸣叫声。《日下旧闻考》就在录下“胡家村”条的文字后,紧接着还有乾隆十三年御制《咏络纬》诗一首,诗后有编者按语:
臣等谨按:《络纬御制诗》是为首见之篇,恭载卷内。
诗云:
群知络纬到秋吟,耳畔何来唧唧音。
却共温花荣此日,将嗤冷菊背而今。
夏虫乍可同冰语,朝槿原堪入朔寻。
生物机缄缘格物,一斑犹见圣人心。
乾隆這首诗写的是冬日的宫中,鲜花盛开,蝈蝈鸣叫,一派夏秋时的欢快景象,完全改变了大自然规律,此景此情,让他想起了皇祖康熙帝的“圣人心”。诗前有序说明作此诗的原委:
皇祖时,命奉宸苑使取络纬种,育于暖室,盖如温花之能开腊底也。每设宴则置绣笼中,唧唧之声不绝,遂以为例云。
这里说的是康熙曾命宫中花匠,将蝈蝈卵置于暖房繁殖新蝈蝈,每当宫中宴饮时就以蝈蝈不绝的鸣声陪伴着大家,并且形成惯例一直流传到乾隆朝。诗中的“格物”“圣人心”就是指的康熙培育蝈蝈之事。当然,这并非康熙皇帝的发明,而是借鉴了明代民间已经出现的人工繁殖蟋蟀的方法。
以上多幅截图无可辩驳地说明,不但最早出现在崇祯本《帝京景物略》中的是“土于盆”,而且陆续收录在《古今图书集成》的刘侗《促织志》、乾隆刻本的蟋蟀谱《蚟孙鉴》及四库全书本《钦定日下旧闻》中的相关内容,同样都是“土于盆”而非“上于盆”。
“上盆”与“上于盆”
民间玩蟋蟀的术语中确实有“上盆”的说法,古谱上也有,意指从野外捉来的蟋蟀,正式放入养盆中饲养。也称“下盆”或“落盆”。如下面几例:
1.早秋得蛩上盆,不宜频频观看,更不可向日色觑之。亦不得用芡,恐牙根嫩,開闭损伤。如此耐惜,则蛩无老态,深秋必健斗而常胜。([清]赠怡馆增订《王孙鉴》“养蛩不老法”)
2.生虫初上盆时,见光奔驰不定。如三数日后尚复如此,则贮水净器中,以手搅之,使水旋转,置虫水中,任其矫跳不起。浴后入盆,停光亮处,俟体干燥,再盖盆盖。(石孙外子《蟋蟀谱》“浴虫诀”)
3.早秋得虫上盆,宜耐心养之,于中秋后定斗,必多枭将健战。最忌频频开盆看之,尤不可向日中观看。(石孙外子《蟋蟀谱》“养虫要言”)
4.早秋蟋蟀譬如人已长成,喂食不宜疏忽。加以天气炎热,所食尤易于消化。从上盆起,大码蛩每日须喂鲜粥粒半;中小码蛩照减。三日后大码蛩每日须喂饭一大粒,中小码蛩照减。喂食之时,最宜注意。(胡耀祖《蟋蟀试验录》“早秋养法”)
5.盆须用古,器必要精。如遇天炎,常把窝儿水浴;若交秋冷,速将盆底泥填。下盆须食白花草,则泥泻出;然后必飧黄米饭,可长精神。([明]周履靖续增本《促织经》“蟋蟀论”)
6.蛩初出土,勿使落盆,最好用陈闷筒养之。陈黄米饭浸二三日,淘净喂之。初出草者,可喂四五粒,数日后以次递减。筒须间日揩拭,或更换干净之筒,勿使其中有烂饭龌龊,致伤须爪。旬日后蛩性驯熟,方可落盆。([清]秦子惠《王孙经补遗》“三秋养蛩法”)
前四例均为“上盆”,第五例是“下盆”,第六例是“落盆”,含义都相同。值得一说的是,“落盆”除了指将新蟋蟀放进养罐中饲养,更多的时候是指蟋蟀格斗时,双方将斗虫放到斗盆中。
除了养蟋蟀,“上盆”一词在花卉行业用得也较多。如:
立夏之后,菊苗盛矣,可五六寸许,是为上盆之期。将上盆也,数日不可以浇灌,使苗受劳而坚老,则在盆可以耐日。([清]陆廷灿《艺菊志》)
凡植花,三四月间方可上盆,则根不长而花多,若根多则花少矣。([清]陈淏子《花镜》)
花卉上盆,是指将花苗从田野或大棚移到盆中养护。
综上可知,《促织》某个抄本中出现的“上于盆”,是抄写讹误所致,并非蒲松龄的本意。其实,这个错误在以前的研究中已有不少人指出了,并强烈呼吁出版部门改正过来。但很遗憾,在现有的出版物中,错误的“上于盆”不但依然故我,而且出版物数量还大大高于正确的“土于盆”。
“上”与“上于”
事实上,比这更糟糕的是,传播了错误的语言知识,“上于盆”文理不通,文言中罕见“上于”这种表达形式。
《说文》:“丄,高也。此古文上,指事也。凡丄之屬皆从丄。上,篆文丄。時掌切。”这是个指事字,丄为小篆字形,古文作二,下面的“一”表示位置的界线,线上一短横表示在上面的意思。“上”本义为名词,指高处。如“宛丘之上兮”“施于松上”等。“上”作动词用,后面直接加宾语,如现代汉语的“上楼”“上车”“上班”等,中间不能加介词。在文言中同样如此,如“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上堂拜阿母,阿母怒不止”“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其他如“上本”“上仙”“上冢”,也是直接带宾语,中间不需加“于”。《国语辞典》只有一例“上于”,例句正是《促织》中的“上于盆而养之,蟹白栗黄,备极护爱”,如果能找到第二例,相信词典编辑不会用这个有争议的例句。事实正是如此,我在浩若烟海的古代文言作品中再三搜寻,几无所得。《周易·需》:“云上于天。”但此处的“上”是用名词的本义高处之义,非动词用法,故三国王肃注本此句作“云在天上”,非常口语化,与现代口语无异。换言之,“云上于天”的意思是“云比天高”“云在天的上面”之义。唐孔颖达《左传正义》:“言云在天上,须散而为雨。”亦是此义。宋人李心传《丙子学易编》:“不言天上有云,而言云上于天,见其气之上升也。”也是这样理解的。与“上于盆”比较相似的倒有一例,出自《礼记·曲礼上》:
主人就东阶,客就西阶。客若降等,则就主人之阶。主人固辞,然后客复就西阶。主人与客让登,主人先登,客从之。拾级聚足,连歩以上。上于东阶,则先右足;上于西阶,则先左足。
这一段文字非常繁琐,讲的是古代宾主相见时的礼仪,连如何举足上台阶都有一套严格规定。“上于东阶,则先右足”是说上东面的台阶,就先抬右脚;上西面的台阶,则先抬左脚。这里的“上于”其实口语中只说“上”就行了,但为了构成四字句,读起来有节奏感,故加了“于”。先秦文言中的虚词,很多时候是充当衬字用的,并无实义,只对诵读有形式上的作用。再如与此相类的动词“入”字,既可以直接带地点名词作宾语,如“入齐”“入陈”“入曹”等,也可以“入”后加“于”再带地名宾语,如“入于齐”“入于陈”“入于曹”,两者都通,前者是口语,后者加“于”的则是文言书面语。这两种用法在《春秋》中的数量差不多。朱熹认为“上于”的用法太少见,干脆在注《礼记》时就把上面两句改成了“上东阶先右足,上西阶先左足”,两个“于”和两个“则”都被删掉了,句子显得更简洁,也更易于理解。朱熹的语言观与一般文人不同,更倾向于口语化表达,他跟学生谈话如叙家常,令人倍感亲切,对古代白话书面语的产生发展,朱子语言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作为文言大家的蒲松龄,饱读诗书,对文言中“上于”的用法十分罕见,应该是清楚的,所以他在借鉴《帝京景物略》时,不可能将原来的“土于盆”改为“上于盆”。在此笔者也呼吁编辑出版部门,不要让错误的“上于盆”延续下去了,要勇于承认并改正错误,免得贻误更多的后生,这才是研究《聊斋》应有的态度。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