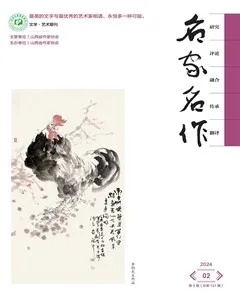植物影像的怪异生态学与录像艺术实践
张承昊
[摘要] 当代艺术家制作的录像艺术以及其他影像中的植物,标志着人与植物以及自然之间新的情感关系得以生成。通过怪异生态学以及情动的去主体性、差异与生成的力量的视角,将讨论建立于一种比电影生产更具自由性的影像生产模式,重新考虑录像艺术或影像中被再现的植物,以及这些植物影像所体现的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触碰,影像中的植物、人与自然之间的新联系将被重新审视。
[关 键 词] 植物影像;怪异生态学;非人再现;情动;差异与生成
我们如何看待以DV或移动设备为介质的植物影像的再现?我们何以感受它们,无论它们是在城市、公园、都市绿地或近郊,乃至荒野之中?我们如何讨论以“恐树症”为主题的影像与视频,以及与之相关的那种奇怪的亲密感?很明显,聚焦于植物的视频与录像艺术,并不是以叙事操控单纯的情感关系,也不属于那些早已被批判过多次的凝视机制。由此,它们揭示了录像艺术所能提供的不同的解读可能性。在这些录像的世界中流动着的,是纯粹的非人(non-human)影像实验所生产的强度。将怪异理论[1]加于生态学之上,以此评估这类录像作品,甚至以此来重新考虑电影中的植物以及它们的再现、它们与人类的联系,一种视角以及一种邀请或许能够显现,它将推动我们重新思考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触碰。
一、反向恋物、植物与性别
在各类影像中,植物仿佛有了人一样的生命,在历史范畴里的各种各样的文本,拟人都能作为一种赋予物质具有灵魂般的生命的方式。无论是郑波所制作的录像艺术,还是我们自行拍摄的视频,人与植物之间的关系与其隐喻的能指,可能会使观影者对植物的类人生命感到恐怖或敬畏。在它们被影像化的过程中,一种拟人的幻觉产生,而那些在植物之间的人(男性主体),在影像的机制下自然而然地被物化了。这里存在着双重的物化:首先,电影媒介将人类进行影像化而产生的物化机制,以及与它紧密相连的,通常被加诸女性角色及人物的物化——包括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提到的切分身体的恋物(fetish)模式以及观众认同的窥淫癖(scopophilia)模式,配合俄狄浦斯轨迹(Oedipus trajectory)的叙事,将女性永恒地置于被看的客体位置[2];其次,通过场面调度,人类中心主义的空间关系被重新导向、重新影像化并置。
反向恋物反对基于依赖母亲身体的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合写的电影工业所依靠的系统,即穆尔维所宣称的对女性的恋物的经济剥削。[3]“最早的物恋只是关于巫术,以及对于女性的控制”[4],这一巫术般的时刻使得郑波镜头中的非人與人类再现被重新物化、组合。实际上,无性别的自然一直以来都被话语视作是女性的,或者说,它被指派为一个古老的、阴性的性别;由此,这野性的、暴力的以及混乱的女性“自然”,成为男性的科学所要驾驭的客体[5]。文学与哲学的历史都显示着资源/女性在夺取行为之间的共通性。而那些蕨类植物与非蕨类植物是无性别的吗?我们无法像指定人类的性别那样定义蕨类植物的孢子生产,但无性别可能是人为制造的假象,一种巴特勒(Judith Butler)式的二元性别结构的原型可能广泛存在,并可能被复制、粘贴,成为一种从古典文学到控制论社会的计算机模型中都能找到的阳性主体—阴性客体的父权等级摹本。但是,即使发现了它的不真实,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这种实际上是被建构起来的本质就一定能够被成功挑战——它有可能通过颠覆的行为而再次强化自身。[6]
巴特勒做出了回应:物质至关紧要。[7]而人类生产物质与附属产物,利用各种工具介入自然,进行着新陈代谢,人生产着非人。物质也生产着人:肌肉纤维的无休止的断裂,通过碳水化合物、脂肪与蛋白质得以重新建构,甚至增殖——这是肌肉生长的辩证运动,通过无生命的非人的物质,人的身体获得更大的体积。这是一个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式的身体,又一直处于性别的权力关系在历史的延续中,不断被类似于表演性(performativity)铭写社会性别的机制形塑。巴特勒认为,异性性存在矩阵(heterosexual matrix)也在生产生理性别;那些看似是用来形容身体的语言,实际上却塑造了这一身体。[8]麻省理工学院的主控基因研究为巴特勒的论述提供了科学话语,他们关于TDF决定因子与性征转化的研究,其部分所依据的推测是,多达百分之十的人有染色体的变异,不符合XX-以及XY-的归类。[9]既然如此多的人在主控基因而非染色体的语境中,不能契合于二元生理性别的矩阵内,那么它究竟该怎么再去定义?而郑波的影像则反映了,泛灵论般的植物所再现的性别体系如同埃舍尔和瓦胥本尔所指出的,文化偏见事实上是一系列关于“什么才能构成一项有价值的探究”的定见,而整个胚胎学领域也因为过于偏重细胞核在细胞分化中的中心角色而受到批评。[10]当亲密超越既定的主体,进入一个人与植物、自然或生态之间的关系网络。那么何为自然?“自然而然”之物如何被建构?这也与影像制作的批评与实践有关。
二、朝向一种怪异生态学
具有独特繁殖模式的蕨类植物所给予艺术家的,更多的是一种联通:从作为他者的植物映射作为他者的其他物质,以重新揭示非人存在的能动性。而这一切都借由录像与视频艺术更进一步的形式自由而实现,这种自由标示了超越古典叙事模式与主流的电影制作体系的影像生产模式。此处对植物的再现,是将镜头重新对准非人物质的一次尝试。怪异理论的介入使得知识生产经历跨学科化以及对科学既定话语的解构。[11]
变动,即“怪异”。透过影像中的植物,对于它们叶片或枝蔓舒展或摆动的调度,暗示了怪异生态学的一种文本现实。城市可以被一种主流男性知识分子的空间吞噬,牧场、乡村或荒野也能被建构为一种男性征服自然以确证自身的神话。具有语言优势的主流系统却自如地征引、遮蔽着其他的经验;同样地,电影作为一种再现系统,仍然复制着相同的生产模式。
如前所述,在一个将女性、动物、自然与性存在去价值化的文化中,某些主体被阴性化、动物化以及自然化。[12]因而,不只是伊丽莎白·格罗兹(Elizabeth Grosz)倡议一个与非人存在共在的理想的世界;不同的空间分配伴随着主体的建构,非人的性、它的多元性,以及生态问题的解决,也许都可以寄希望于怪异理论——不仅是类比于怪异动物的多元取向[13]所体现的。另外,德勒玆(Gille Deleuze)装配(assemblages)的怪异生态学具有跨学科、块状统筹的特性,启示着一个“多于人”的复数的肉身(more-than-human corporealities)[14]:这将提供另外一种打破围绕着菲勒斯霸权的等级化的剥削体制的工具,这种体制广泛地存在于世界各地对古典好莱坞的挪用之中。由此,怪异生态学还提供了更多的影像可能性,正如郑波的录像艺术挑战着影像再现的陈规与非人物质的从属地位。这与罗安清试图改变人类中心主义的方式类同,使一种朝向人的知识的物质回归其自身的互相呼应,运用一种工具去直观物质与世界之间的参与,使物质获得其本身的生命[15]。看似中立的科学、技术与存在实践(practices of being)也难以改变人类中心主义,非人(nonhumans)将保持着消极、非能动的状态。[16]
三、人与非人之间:非人再现与怪异情动
郑波偏爱的蕨类植物的叶子像是四肢,延伸于层层叠叠的绿墙、绿雾间。人的身体在仿佛没有边界的绿墙的裂缝里移动,在被我们称之为植物的物质及其质地(texture)[17]之间游移;而镜头则可以不断地重构或置换空间关系。所有这一切身体与植物之间的亲密,并非任何一个地区的主流电影工业模式所能尽数体现。此时此刻,人的有机体与植物的有机体之间不但相互连接,更仿佛已经失去了能动性上的差别:郑波4K画质录像作品的影像特质给我们一个例证,它契合劳拉·穆尔维在20世纪70年代所呼吁的对主流电影快感的抵抗[18],使不同的恋物模式得以体现。那么,它的作用机制可能是什么样的?它何以触动观影者的情感,又如何借此来模糊主体的边界,从而促成新的生成(becoming)以及人类与非人物质之间的新关系?新泛灵论(the new animism)[19]开启了新思考模式,然而,泛灵论也将其禁锢于一种人类意向性中,如果物的“灵”按照泛灵论成为人类情感的延伸存在,那么物与物之间的交互就不再那样明朗;回归一种重新思考的装置,可能需要迈克尔·马德(Michael Marder)的“植物思考”(plant-thinking)——“让我们进入一种多物种关系,在那里意识与意向(intention)也许不是起点。”[20]
由此,这种多物种关系显现于录像艺术、视频与电影中的植物——这些非人的存在的再现之间。在德勒玆看来,艺术创作的目的在于“从知觉及其主体状态中提取感知物,从各种状态转换的情状中提取情动”[21],与此同时得以强调的正是“差异”的潜力:“如果哲学是将语言从对概念和问题的简单定义和定见的固化之中解放出来,那么艺术则是创造感受和感知。”[22]而艺术在这里所创造的包含着情动的聚块并不来自人们固化了的定见,在柏格森的意义上,这些定见漠视了情感的状态。因此,在差异的力量之下,艺术家应当将各种感受与感知不断地增添到这个世界,当创作完成之后,作为观众的我们还会被拽进感觉复合体,我们便与情动一同生成。[23]由于情动是非个体的、流动的,它承诺了一种混淆主客体的开放性质:“我在感觉中生成……同一个身体既给予它也接受它,而这个身体就既是客体又是主体。”[24]同样地,德勒兹引述塞尚,论述了去主体式的思想[25],并且塞尚对模糊轮廓的思考、回归物本身与主客体的取消也已被梅洛-庞蒂论述过[26],德勒兹似乎往前更进一步,思考如何生成为非人。
“被体验的知觉上升到感知物,从被体验的情感上升到感受(情动)。”[27]由此,在这种消弭主体边界的思潮下,现象学与德勒兹理论似乎相交错,反应并生成关于肉身的论述;从梅洛-庞蒂的肉身观念出发,德勒兹认为“世界和身体作为对应物彼此交流”,而电影实现了这种交流[28],从肉身的混沌之中被诉诸框架结构的形成,再由此产生新的情动[29]。换句话说,在电影与影像艺术中,正是这种“差异”促成了新的转化与生成:“我感觉,我生成为女人……生成为通灵者,生成为纯粹物质”——科勒布鲁克等诸位学者由此探讨了有关德勒兹与巴特勒的主体间性以及德勒兹理论的怪异性。奈基亚尼(Chrysanthi Nigianni)在序言中引用德勒兹与加塔利(Félix Guattari)并进行论述,认为巴特勒理论中的操演性(performativity)与德勒兹与加塔利的思考相似,他们使得怪异远离通过再现与指认而实现的再生产[30]。德勒兹以精神分裂分析(Schizoanalysis)取代精神分析,试图询问中产阶级家庭模式对欲望的压抑,询问为何我们应该接受惯例、标准和价值,又是什么阻止了我们去创造未来的新欲望或新形象;换句话说,通过反对合理化,创造和转变的权力被推进了:“不存在原初的心灵,而只有原初的部件,是‘精神分裂或非人的、可移动的碎片。”[31]因而,影像中非人生命的再现使主体的情感得到另类的触发,人类的主体性边界被许诺以瓦解的可能,响应着关于差异与非人的论述:“存在着多样化的人类绵延和非人的绵延,我们要超出被空间化了的和秩序化了的视角,才能思考其他的绵延。”[32]
四、结束语
录像艺术中的怪异生态学与跨物种的非人物质再现,将重新锚定跨物种的情感与情动生产以及相关的扰动的力量。离开主流电影生产模式的凝视与恋物机制以及叙事生产的束缚,将更自由的影像形式与数字制作纳入考量的范围,那么这种力量恰好可以通过以下方面得以显现:首先,植物影像的怪异生态学标定了新物质主义的转变,强调植物以及非人物质,从泛灵论的介入情动理论的搅扰,我们能够看到一种开放的潜力,这将使人与物质之间的层级重构成为可能;其次,人与非人之间的影像再现背后的情动生产机制保障了使这种可能性得以实现的潜力,由差异而生成,这使植物影像的实践能够对稳定主体边界的消解与新的情感关系的生成之间的联动作出承诺。
参考文献:
[1]王逢振. “怪异”理论[M].陈俊,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2][18][英]劳拉·穆尔维. 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M]//杨远婴主编. 电影理论读本.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
[3][英]勞拉·穆尔维. 恋物与好奇[M].钟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4][美]威廉·皮埃兹. 物恋问题[M]//孟悦,罗钢.物质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61.
[5][美]卡洛琳·麦茜特. 自然之死:妇女、生态与科学革命[M].吴国盛,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2.
[6][8][美]朱迪斯·巴特勒. 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M].宋素凤,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7][9][10][美]朱迪斯·巴特勒. 身体之重:论“性别”的话语界限[M].李钧鹏,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139-142.
[11]Valentine,D. Imagining Transgender:An Ethnography of a Category[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140.
[12]Mortimer-Sandilands,C. and Erickson,B. “Introduction:A Genealogy of Queer Ecologies”[M]// Mortimer-Sandilands,C. and Erickson,B. eds. Queer Ecologies:Sex,Nature,Politics,Desire.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10:1-47.
[13][14]Sandilands,C.“Queer Ecology”[M]// Adamson,J.,Gleason,W. A. and Pellow,D. N. eds. Keywords for Environmental Studies.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16:169-171.
[15][16][19][20] Tsing,A.“When the Things We Study Respond to Each Other: Tools for Unpacking ‘The Material”[M]//Harvey,P.,Krohn-Hansen,C. and Nustad,K. G. eds. Anthropos and the Material.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19:222-243.
[17]Donaldson, L. F. Texture in Film [M].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2014.
[21][23][25][27][29][法]吉爾·德勒兹,菲利克斯·加塔利:什么是哲学?[M].张祖建,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439-440,456,413-445,439-440,473-476.
[22][31][英]克莱尔·科勒布鲁克.导读德勒兹[M].廖飞鸿,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26-27,6.
[24] [法]吉尔·德勒兹.哲学的客体:德勒兹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1..
[26][法]莫里斯·梅洛-庞蒂.意义与无意义[M].张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28][澳]雷克斯·巴特勒. 导读德勒兹与加塔利《什么是哲学?》[M].郑旭东,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9.
[30][32] Nigianni,C. and Storr,M. “Introduction” [M]// Nigianni,C. and Storr,M. eds. Deleuze and Queer Theor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9:1-10.
作者单位: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