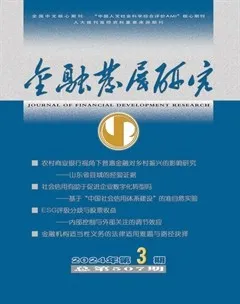财政金融融合支持耕地保护的国际经验与借鉴
任旭峰 李晓平
摘 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耕地保护既需要耕地制度本身的改革创新,也离不开国家财政金融系统的支持。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形成了与耕地产权和保护制度持续创新相配合的比较有效的耕地保护财政金融融合支持体系。借鉴其经验,我国需在深化耕地产权和保护制度改革的基础上,构建相互协调、共同发力的财政金融融合支持耕地保护新格局,加快发展多层次专業化农业金融服务体系,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实现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耕地保护。
关键词:财政金融融合;耕地保护;国际经验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24)03-0083-08
DOI:10.19647/j.cnki.37-1462/f.2024.03.009
一、引言
粮食安全是战略问题。2020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要像保护大熊猫那样保护耕地,严防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迅速推进,城市化率从1980年的19.40%飙升至2022年的65.22%,预计到21世纪中叶将达到81.63%(李善同等,2017)[1]。与此同时,我国耕地面积却持续下降,根据《关于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主要数据成果的公报》《关于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主要数据成果的公报》,2009—2021年,我国耕地面积由20.30亿亩减少至19.17亿亩。早在21世纪初,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就指出,在全球范围内,除高科技领域外,中国的城市化是21世纪初期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于春,2002)[2]。而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国耕地保护面临来自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挤占压力。
从全球范围看,自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导致大量优质耕地资源转用,对土地市场、生态环境甚至对全球粮食市场产生了冲击,引起各国政府对耕地产权、保护制度以及财政金融支持体系建设等问题的高度关注(Himiyama,1999;Duke等,2012)[3,4]。绝大多数农业经济学家一致认为,从一国长期社会福利角度出发,制定耕地保护政策并实施财政金融支持措施是非常必要的(Mille和Silvrc,2007;Yang,2010)[5,6]。在这一背景下,发达国家逐步建立了相对完善的耕地产权和保护政策,配套建立了财政金融支持体系(Mcdonal,1997;Lynch,2009;清水彻朗,2016)[7-9]。美国和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阶段,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提升对耕地的挤占,引致人地关系紧张以及粮食短缺和资源环境问题,与我国目前发展实际具有相似之处。尽管两国面临着不同的土地利用条件,但均采取了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并构建了相应的财政金融支持体系(Duncan,2001;瞿振元和大多和严,2007)[10,11]。研究这两个国家的经验,可以为我国耕地产权和保护制度的调整完善以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金融融合支持体系提供借鉴。
二、美国的耕地保护和财政金融支持制度
美国耕地资源丰富,但随着人口规模持续增加和城市化带来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挤占,耕地面积呈现出持续下降趋势(Szlanfucht,1999)[12]。1967—1975年美国损失了大约2300万英亩耕地,下降规模超过了总面积的20%(Coughlin和Keene,1981)[13]。从各州损失土地所占比例看,9个州超过30%,4个州超过40%,2个州超过50%(Ueruergensmeyer,1981)[14]。为协调工业化、城市化与耕地保护的关系,保持稳定健康的农产品长期生产能力,美国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相对完善的耕地产权与保护制度,并建立了与之配套的财政金融支持体系。
(一)美国耕地产权制度
美国是一个实行耕地私有制的国家。尽管其建国宪法并未明文规定土地私有制,但1791年《权利法案》在修订过程中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度,将全国土地划分为公地和私地两种类型,规定在未得到充分补偿的条件下,公民私有财产不能因公益目的而被国家征收。这一修订不仅确认了土地私有制度,还明确规定了政府征用私有土地的目的和条件。从美国建国初期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通过公地拍卖和向垦荒者无偿赠送两种方式建立了以家庭农场经营为基本形式的耕地私有制度。各州政府通常会建立完善的土地产权登记制度,以证明土地的权属。目前美国土地利用状况显示,大约42%的土地为公地,分别归联邦、州和城市政府所有,而剩余的58%为私有土地,其中大部分是耕地(孙利,2021)[15]。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美国的耕地所有者通常享有与耕地相关的经营开发、销售、租赁、抵押、继承、馈赠等权利,但国家保留了征用、征税和用途规控等限制性约束。在这一法律规定的权利框架内,美国建立和实施了各种耕地保护制度和财政金融支持措施。
(二)美国耕地保护制度
1916年,纽约州率先在全美范围内采用用途区划办法,对区域内耕地实施保护措施。随后,1926年,美国最高法院正式批准土地规控制度,而1935年《水土保持和国内生产配给法》则在法律层面上为耕地保护提供了支持。到20世纪40年代,全美大多数州已经实施了区划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初,一些州开始探讨将耕地保护与区划办法结合,发展出了新型政策工具,如耕地征用权区划等。1976年,美国首次提出基本农田概念,授权各级政府有权制定基本农田规划措施,划定行政区域内的基本农田保护区,要求耕地所有者必须保证规划区域内的基本农田用于农业生产。1981年《农地保护法》和2000年《农业风险保护法》进一步对基本农田转用行为作出了更为严格的限制。尽管农地区划是一项成本较低的政策工具,但受耕地所有权人发展意愿和政府规划等因素影响,面临短期调整压力,不一定是长期有效的政策(吴正红和叶剑平,2009)[16]。为提升耕地保护政策的长期效果,美国引入了土地发展权购买(PDR)和土地发展权转让(TDR)两种新型市场化工具(Johnston和Duke,2007)[17]。PDR指的是政府非经营性组织从耕地所有者手中购买耕地的非农开发权利,购买后,耕地所有者只能将耕地用于农业生产。截至2006年,全美约有1200万亩土地通过实施PDR得到了保护,政府为此投入了大约15亿美元(丁成日,2008)[18]。当政府难以承受PDR保护的成本压力时,降低政府耕地保护支付压力的TDR政策开始实施。在实施程序上,TDR与PDR类似,但在受让主体方面,TDR允许营利性组织参与土地发展权流转,赋予购买主体在发送区获得土地发展权后在接受区建设更大密度建筑的权利。除上述政策外,美国还通过积极的政策对耕地征收和整理行为进行了规范。
(三)美国耕地保护财政支持制度
美国耕地保护财政支持政策主要体现在农产品价格补贴、耕地休耕计划补贴、税收减免和保险补贴方面(Sumner,2000)[19]。
一是农产品价格补贴。1933年《农业调整法》采用无追索权贷款方式为农产品制定了财政支持的最低价格保护政策,信贷公司在政府支持下向农业经营者提供为期10个月的短期贷款。贷款到期时,如果农产品销售收入高于贷款额,农业经营者可以出售农产品偿还贷款;如果低于贷款额,可以将农产品直接转让给信贷公司偿还贷款,财政补贴贷款损失。1996年《农业改善与改革法》为减轻政府财政压力,规定在农产品销售收入低于贷款时,农业经营者可以在市场上继续销售农产品获得收入,信贷公司则按销售收入与贷款之间的差额获得政府财政补贴。2002年新《农业法》继续实施了营销援助贷款和贷款差价补贴办法,实质上仍是无追索贷款政策的延续。此外,为遵守WTO规定,1996年《农业改善与改革法》还制定了直接补贴制度,对与政府签订生产灵活性合同的耕地所有者提供一定数量的固定补贴,该制度在2002年《农业法》中得以维持。
二是耕地休耕计划补贴。美国耕地休耕计划在演化过程中逐步与耕地保护政策融合,成为美国耕地保护的重要政策措施(Claassen等,2008)[20]。早在1956年,美国就提出了短期和长期耕地休耕计划。短期政策旨在控制农产品产量,而长期政策则着眼于耕地自然条件保护。1961年,政府规定农业经营者耕地休耕比例应达到所拥有耕地总面积的20%。对于休耕耕地,政府给予相当于正常年份收入50%比例的现金或实物补贴,并规定将超过规定比例休耕土地的补贴比例提高至60%。1965 年改革办法根据政府计划将休耕土地分为无偿休耕和有偿休耕两种类型,执行无偿休耕政策的农业经营者有权享受无追索权贷款和税收优惠政策,政府不再进行休耕政策补贴,但政策规定数量的休耕土地仍可继续享受政府财政补贴。1985 年,美国推出了土壤储备保护计划,向农业经营者提供土壤保护成本 50%比例的财政补贴。
三是税收减免。美国政府在耕地保護中注重税收调控,对于将耕地和农业保持权捐赠给政府非营利性组织的耕地所有者,给予一定数量的税收减免,同时在税收激励措施中规定,对于维持耕地农业用途的耕地所有者实施个人所得税减免。2006年,美国国会批准了大幅提高联邦税收减免额度支持耕地保护的提案,体现了政府在耕地保护中加大税收调控手段作用的倾向。
四是保险补贴。政府按照50%~80%的比例对农业经营者的保费支出进行补贴,并实施农业灾害援助计划,对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引起的损失,给予相应的灾害补贴(Glauber,2013)[21]。2020年,美国农业保险总保费收入为100.60亿美元,其中财政补贴63.10亿美元,补贴率高达62.77%(谭啸威和陈新建,2021)[22]。
(四)美国耕地保护金融支持制度
美国农业金融制度经过长期发展,已形成了包括政策金融、合作金融、商业金融和农业保险在内的复合金融支持系统(Jensen,2000)[23]。
农业政策金融体系由农民家计局、农村电气化管理局、商品信贷公司和小企业管理局等子系统组成。其中,农民家计局的主要任务是协助无法获得其他金融机构支持的贫困和低收入农业经营者获取发展所需资金;农村电气化管理局为农业经营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必要的贷款和担保服务;商品信贷公司主要为农业经营者提供农产品抵押、农产品生产设备购置的短期贷款服务;小企业管理局则为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小企业提供贷款和担保等金融服务。
合作金融方面,政府支持和出资设立的农业贷款专业银行和基层管理机构逐步演变为农业经营者所有、国家农业信用管理局管理的金融机构。该体系包括联邦中期信用银行、农业合作银行和土地银行3个核心组织。联邦中期信用银行是最核心的机构,1934年《联邦信用社法》将全国划分为12个信用区,每个信用区均设立联邦中期信用银行,负责向生产合作社成员发放1~7年期的中期贷款。农业合作银行系统由设立于华盛顿特区的中央合作银行和分设于12个信用区的合作银行组成。中央合作银行和分设合作银行之间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各自独立运作,主要业务是为各个信用区的专业合作社购买设备、生产资料以及补充营运资金提供贷款支持。分设于12个信用区的土地银行及所属合作社组成了美国联邦土地银行系统,该系统主要为农业经营者提供期限为5~14年的长期不动产抵押贷款服务。
农业保险方面,自1938年《联邦农作物保险法》颁布实施以来,美国逐步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农业保险系统。该系统包括联邦农产品保险公司、私营商业保险公司和保险经纪人等三个层次的机构。第一层次是联邦农产品保险公司,该公司在历史上曾直接经营农业保险业务,从1996年开始,在转型负责农业保险再保险业务的同时,开始履行行业管理职能。第二层次由具备农业保险业务资格的私营商业保险公司组成,其在开展农业保险业务时通常会得到政府的支持。第三层次则由保险经纪人和查勘核损人等机构和人员组成。2022年,作为美国政策性农业保险最大险种的农业收入保险实现保费收入150.97亿美元,保障金额1429.52亿美元,所涉及的耕地面积约2.1亿英亩。
三、日本的耕地保护和财政金融支持制度
人口密度大、土地资源有限一直是困扰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耕地面积一直呈下降趋势,总面积从1961年的608.6万hm2减少到2003年的476.2万hm2,年均减少3.15万hm2。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是日本工业化和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期,也是耕地面积减少最快的时期,其中,1973年耕地面积减少6.80万hm2,达到峰值(于伯华,2007)[24]。然而,通过持续的制度创新,日本维持了38%左右的粮食自给率,特别是大米作为国民主食,基本上能够自给自足且有一定剩余(姚毓春和夏宇,2021)[25]。这一成就得益于日本的耕地产权与保护制度以及相关财政金融政策的支持。
(一)日本耕地产权制度
日本在二战后实施《自耕农创设特别措施法》,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土地改革。具体做法是,国家在两年内强制收购封建地主耕地,然后将其出售给农户,逐步实现以农户自主经营为特征的自耕农制度。这一改革在1952年《农地法》中得以明确,从而在法律层次上确立了耕地私权制度。21世纪初,日本全部土地中,国家公地约占35%,法人社团占地约为8%,剩余57%为私人所有且以耕地为主(唐顺彦和杨忠学,2001)[26]。为了应对经济高速发展导致的耕地面积减少以及兼业经营和人口老龄化引起的耕地荒废问题,日本政府积极进行了自耕农制度改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政府曾通过给予农户优惠贷款的方式刺激农户提高耕地经营规模,但该政策未达预期,促使政府将目标调整为耕地使用权流转。1961年《农业基本法》在坚持自耕农制度的条件下,允许小规模农业合作社接受离地农户委托,實施耕地代耕。1970年《农地法》修订不仅承认脱农者的耕地出租权利,还放宽了《农业基本法》中的耕地租赁限制。1975年《农业振兴区域整备法》进一步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出租耕地农户的权利。 1980年《农用地利用增进法》以耕地租赁为中心,鼓励建立区域性耕地利用改善组织。在政府支持下,农村地区农协组织协调大户和生产合作组织接受离地农户的耕地经营委托和作业委托,促进耕地经营规模集中扩大。1993年《农业经营基础强化促进法》实施认定农业人①制度,进一步支持引导耕地利用规模集中。
(二)日本耕地保护制度
日本自1919年开始施行土地用途管制,《城市规划法》和《市街道建筑物法》为该制度确立了法律基础。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政府陆续制订的4次全国性国土综合开发计划都提出了耕地保护目标。1969年新《城市规划法》和1970年《建筑规划法》对土地用途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规划,将全国土地划分为农业、都市、森林、自然公园和自然环境保护五大地域,并对每一个地域的土地用途进行了更加详细的二级规划。实践中,日本以《农地法》为基础,逐步形成了相互联系、层次清晰的耕地保护制度体系。农业经营基础强化主要体现在1980年《农地利用增进法》和1993年《农业经营基础强化促进法》中,特别是《农业经营基础强化促进法》中实施的认定农业人制度,对具有资格的农业经营者提出了明确的耕地保护要求。此外,土地改良也是耕地保护的一部分,其包括耕地生产条件改良和新耕地开垦两个主要内容,要求不同层次的参与主体实施符合实际的耕地改良计划。为防止城市化和工业化引起的耕地过度占用,1975年《农业振兴区域整备法》对划定在农业振兴区域内的耕地实施了更为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另外,日本政府严格限制耕地转用,并按照生产能力将全国耕地分为农业振兴整备区域、甲种和乙种三类,每类耕地转用设有不同限制条件。在耕地转用规制基础上,政府根据土地所在区域位置和城市规划范围,将耕地进一步区分为市街化区域(该区域是已形成或未来要优先实现城市化的区域)耕地和市街化调整区耕地,对于这两种类型的耕地转用,政府分别实施了不同限制措施和批准程序。
(三)日本耕地保护财政支持制度
日本耕地保护财政支持制度主要通过政府财政对农业政策金融的支持来实现。农业政策金融是指政府或地方公共团体通过发放低息贷款或对民间金融机构贷款进行财政补贴等方式,支持耕地保护和农业发展。其中,农林渔业金融公司(政策公库)是农业政策金融的主要执行机构,负责提供农业政策性金融贷款,贷款资金来源于中央和地方财政。此外,为配合耕地使用权流转改革,日本实施了耕地保有合理化法人制度②和认定农业人制度。农林渔业金融公司(农林中金)不仅是耕地保有合理化法人的发起人,还负担该类法人租入耕地所发生的金融借款利息、日常管理开支和工作人员工资等费用。通过认定农业人制度,法定程序认定的农业经营者有资格获得国家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近年来,为促进市街化区域耕地转用,日本税收制度对于该区域内的耕地持有人征收与宅基地类相同税率的税收。然而,对于市街化区域外 (包括市街化调整区)的耕地转用,则对所涉及的利益主体执行较高税率,这种税收政策旨在调节土地合理利用并鼓励市街化区域内的耕地转为其他用途。
(四)日本耕地保护金融支持制度
伴随耕地产权与保护制度以及财政支持制度演进,日本形成了包括政策金融、合作金融、商业金融和信用保证在内,分工明确、相互协调的耕地保护复合型金融支持体系,政策金融和合作金融在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2018年日本农业经营者贷款来源机构中,政策公库、农协金融系统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占比分别为44%、40%和16%。政策金融由政策公库主导,致力于通过提供低息或优惠利率的中长期贷款服务,支持农业经营者进行耕地保护和农业经营。合作金融则以农协系统为基础,通过基层农协、信农联和农林中金三级机构,为农业经营者提供短期流动资金融通服务。同时,该金融支持体系中设有信用保证制度,由中央和地方两级农业信用基金协会提供信用担保服务,以降低金融机构的运营风险。这一复合型金融支持体系的建立旨在确保农业经营者获得必要的金融支持,同时通过协调不同层级的金融机构促进农业经济稳定发展,进而实现对耕地的保护。政策金融和合作金融在这一体系中作用关键,为日本耕地保护提供了相对充足的金融支持。
四、美国与日本财政金融融合支持耕地保护的主要经验
耕地资源作为土地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不仅承载着人类基本的生存需求,同时作为价值承载者,也是人类劳动创造和积累的历史性舞台。全球范围内人口增加、现代化进程加速等因素导致耕地人口承载力下降,引发了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失衡,耕地保护日益成为影响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关键问题。在此背景下,美国和日本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代表,对耕地产权和保护制度进行了调整,构建了财政金融政策融合体系,以支持耕地保护和农业发展。这一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全球范围内对于耕地保护的共识和努力。
(一)持续进行耕地产权和保护制度调整
良好的耕地产权和保护制度是构建耕地保护财政金融支持体系的基础。美国和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针对土地产权和保护制度进行的调整,确保了其财政金融支持体系的有序构建和可持续发展。两国均实行耕地私有制度,美国实施家庭农场制度,而日本则实施自耕农制度。为防止现代化和城市化对耕地资源的过度挤占,两国均通过土地用途规划政策限制不合理的耕地转用。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美国尊重耕地私有产权,重视引入市场化手段,如PDR和TDR等,引导积极的市场化制度创新。与此同时,美国实施了内容广泛的土地整理制度,通过协商和产权调整,使区域内耕地利用达到最优,保障了优质耕地的最佳生产功能。在日本,国土综合开发计划为全国耕地保护提供了宏观制度基础,地域规划和二级规划在国土管理中占据核心地位。在坚持私有制的前提下,日本通过耕地使用权流转促进了耕地保护制度创新。耕地保有合理化法人和认定农业人制度为日本近年来的耕地保护制度创新提供了微观基础。总体而言,两国通过不断的制度调整,建立了既有顶层设计又有微观规定的耕地产权和保护制度体系,形成了一个具有较强操作性和较理想运行效果的政策有机体。
(二)注重财政金融政策支持体系融合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主要通过间接调控来实施宏观调控行为,而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则是政府对市场主体进行间接调控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在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起到关键作用,财政政策主要关注国民收入的分配,而金融政策则侧重于对已获国民收入的周期性调剂流通。根据协同演化理论,财政金融融合形成的复合体系能够有效克服两者的局限性,相互协同、相互影响,实现优势互补,形成良性内在发展机制。美国和日本的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在支持耕地保护中呈现出融合发展的趋势。两国通过不断调整演化,建立了成熟完整的法律法规体系,为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实施和融合发展提供了清晰明确的制度基础。实践中,美国通过农业法案的调整或制定,将财政金融政策纳入法律体系,制定明晰的法律条款规范各涉农利益主体行为,为实现政策目标提供了保障。相对而言,日本采取了基本法和普通法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基本法的修订和普通法的调整,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为促进两者融合发展,特别是为应对WTO相关规定,美国和日本在实践中采取了多样性的政策工具,如直接补贴、休耕补贴、土壤保护成本补贴、保险补贴、无追索权贷款、政策性贷款、再保险等。在法律规定框架内,两国通过多样化的政策工具组合,持续进行方式方法创新,注重引导社会资本和市场力量支持耕地保护。
(三)积极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
农业生产的弱质性特点是困扰各国耕地保护财政金融支持体系,尤其是金融支持体系发展的重要因素。耕地资源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更具备社会保障和生态功能。按照经济学外部性理论,耕地资源的社会保障和生态功能显然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征,对耕地资源的保护实际上也是对其外部性的保护,同样具有外部性特征。由于农业生产的特点和外部性的存在,市场失灵在耕地保护中普遍存在,需要政府的外部干预。美国和日本在耕地保护中积极实施了财政税收调控政策,但由于资源禀赋和制度环境不同,两国的财政政策体现出不同的特点。美国主要侧重于实施面向农业经营者和耕地所有者的直接财政支持政策,包括农产品价格补贴、耕地休耕计划补贴、土壤储备计划补贴和保费补贴等,充分体现了对农业生产主体的关注。相反,日本更注重财政政策对中介组织的培育,通过中介组织实施间接财政支持政策。这主要体现在政府独资或主导出资设立政策公库、农林中金、信农联、基层农协、耕地保有合理化法人以及两级农业信用协会等机构,并为这些机构提供财政性资金支持等方面。另外,两国都为农业经营者提供了税收优惠政策,且对不同类型的耕地转用行为实施了激励和惩罚性税收政策。总体上,尽管两国财政政策实施路径存在差异,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彌补了耕地保护中的市场失灵,促进了耕地保护外部性内化,通过减轻农业经营者财务负担的方式促进耕地保护目标的实现,同时对引导社会资本和市场力量支持耕地保护产生了积极作用。
(四)推动构建复合金融支持系统
在积极财政政策引导下,美国和日本在长期发展中都形成了包括政策金融、合作金融、商业金融、农业保险和信用体系在内的复合金融支持体系,以适应耕地产权和保护制度调整。实践中,美国和日本的政策金融和合作金融均成为支持耕地保护的主渠道,商业金融则起到辅助作用。两国政策金融和合作金融的组建和运行方式存在一些差异。两国的政策金融机构虽然都是由政府出资设立和控制,但美国的政策金融包括四个子机构,而日本的政策金融中仅有政策公库这一机构。合作金融方面,两国都注重协调各方利益,积极引导各级各类主体参与体系的设立和运营,以实现共容利益。美国合作金融系统由3个核心子组织和分设于12个信用区的土地银行系统组成,而日本的合作金融系统主要体现为农协系统的三级金融机构。从两国政策金融和合作金融所涉机构的资金来源看,两国均采取了控制性措施,将财政资金和农业经营者存款作为金融支持的主要资金来源,并注重积极引入外部资金。总体上,两国的农业金融所涉机构共同构成了相互协调、相互补充、互不交叉、高效运转的系统,为耕地保护政策的实施提供了良好支持。在农业保险和信用体系方面,美国注重发展农业保险,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农业保险体系,在保障农业经营效益和提高农业经营者耕地保护积极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之不同,日本注重发展农业信用体系,其构建的双层信用基金协会为各类贷款提供了有效的信用保证,极大提高了各级各类金融机构为耕地保护提供金融支持的积极性。
五、美国和日本经验借鉴与启示
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明确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发展目标。国家近期陆续出台了系列改革政策,在推进乡村振兴中积极构建耕地保护新格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2024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前,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不懈夯实农业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强调“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美国和日本财政金融融合支持耕地保护的经验可为我国耕地保护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一)调整耕地产权和保护制度,夯实财政金融融合支持体系发展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和合作化运动,我国土地产权从私有制转为公有制。1954年《宪法》规定国家可以征购征收集体土地为国家所有。1975年《宪法》明确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我国土地所有制的两种主要形式,这为农村土地特别是耕地集体所有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按此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地方政府在耕地保护中承担主要责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实践中创建完善了集体土地征收、城市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制度。从1986年开始,耕地保护成为我国基本国策,并在同年颁布的《土地管理法》中予以明确。1997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推动建立了土地用途管制和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制度。2005年《省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法》明确省级人民政府在耕地保护中负有主要责任。2017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要求加快构建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的耕地保护新格局,并提出“进出平衡”新政策。2021年新《土地管理法》对加强耕地保护、改进占补平衡、制止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等内容进行了规定。2022年对耕地保护方面的地方政府党政责任作了明确规定。总体而言,从用途管制到“三区三线”区划改革,从“占补平衡”到“进出平衡”,从农户负有耕地保护责任到地方政府党政同责,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三权分置改革”,都是我国土地产权和耕地保护制度不断创新的方面。为构建和发展财政金融融合支持体系,我国仍需在尊重市场经济原则的前提下,持续改革创新,为财政金融融合支持耕地保护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
(二)创新涉农财政政策,引导构建耕地保护财政金融融合支持体系
财政金融政策作为两大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近年来,我国在财政金融改革方面取得了不少新进展,进行了一系列创新性制度安排,如财政出资设立担保机构、PPP模式、绿色金融以及结构化货币政策等。这些措施对我国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然而,与美国和日本相比,我国在财政金融相互协调融合发展支持耕地保护方面仍处于探索阶段,政策工具仍以各类财政补贴和支持发放贷款为主,存在改进空间。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耕地保护财政金融融合支持体系,我国应充分运用财政税收手段,发挥“看得见的手”的引导作用。同时,可借鉴美国和日本经验,通過协调政府、金融机构、监管机构和市场主体等各利益主体,探索财政金融融合发展创新模式,包括建立健全我国涉农资金管理、调动社会资本和市场力量的相关制度,设立类似日本政策公库的机构,以统筹协调涉农财政资金的监管,确保其有效使用。此外,通过实施税费优惠、建立财政风险补偿机制、成立国有信用担保和保险机构等措施,创新财政金融融合政策工具和组合使用方法,综合降低支农社会资本的经营风险和成本,调动社会资本和市场力量支持耕地保护的积极性,进而逐步优化财政金融融合发展的制度、机制和措施,推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涉农财政金融融合支持体系。
(三)多措并举,建设耕地保护多层次专业化金融支持体系
我国已构建了以商业金融为主导,包括政策金融、合作金融、商业金融、村镇银行、互联网金融、担保公司和保险机构等金融机构在内的多层次耕地保护金融支持体系,但受制于安全、利率和机会成本等因素,该体系难以满足我国耕地保护金融需求。对照美国和日本经验,我国农业金融服务体系存在政策金融支持不足、合作金融发展迟缓、涉农金融服务体系不完善、支农产品结构单一、风险补偿机制发育缓慢等问题。面对高风险低收益现实,外部政府干预和内部管理效率优化是实现农业金融供需平衡的可行途径。为改变目前状况,金融体系建设应着力从农业金融机构调整、服务完善、产品创新和风险补偿机制等方面进行创新,在国家层面可以考虑设立类似美国国家农业信用管理局的专门机构,统筹协调全国农业金融体系的发展。农业金融机构调整方面,首先,需要明确三大政策性银行的定位,形成分工明确、协作高效的涉农政策金融体系;其次,大力发展农业合作金融体系,以省级农信社为基础,整合各级各类农业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互联网金融公司等机构,建设涉农利益主体广泛参与的高效运转体系;最后,引导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发挥商业金融主渠道作用,设立专门事业部,支持涉农业务发展。在服务完善和产品丰富方面,需综合运用政策工具对各级各类农业金融机构进行支持,激励其进行服务和产品创新。风险补偿机制方面,创建政府主导的农业信用保证和保险体系,引导鼓励农业经营者参与,提高各级各类涉农金融机构的积极性,促进农业金融服务体系健康发展。
注:
①认定农业人是经由市町村政府选择和认定,在扩大耕地规模和农业经营效率方面有积极性的农业经营者。
②耕地保有合理化法人是政府培育和扶持,各县、市町村政府及农协共同建立,服务于耕地流转的专业中介组织
参考文献:
[1]李善同,吴三忙,高春亮.中国城市化速度预测分析 [J].发展研究,2017,(09).
[2]于春.新时期的都市圈建设为郊区城市化带来新动力 [J].南京社会科学,2002,(05).
[3]Himiyama Y. 1999. Historical Information Bases for Land Use Planning in Japan [J].Land Use Policy,(16).
[4]J M Duke,A M Borchers,R Johnston,S Absetz. 2012.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Contracts:Using Choice Experiment to Estimate the Benefits of Land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J].Ecological Economics,(74).
[5]R C Mille,D Silvrc. 2007. Value Chain Financing In agriculture [J].Enterprise Development and Microfinace,18(1).
[6]Sisi Yang.2010. A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Banks and the Relief of Rural Financial Difficulties [J].Internationa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5(5).
[7]M G Mcdonal. 1997. Agricultural Landholding in Japan:Fifty Years After Land Reform [J].Geoforum,28( 1).
[8]L Lynch.2009. Land Preservation Program Achieve High Levels of Effiency [J].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e Economics,(05).
[9]清水彻朗(日).日本农业政策与农协改革相关动向及日本农业的未来展望 [J].世界农业,2016,(08).
[10]M Duncan. 2001. An Evaluation of Proposed New Tools for Rural Financial Markes:RURPI Rural Financial Task Force [J].Rural Policy Brief,1(5).
[11]瞿振元,大多和严(日).中日农村金融发展研究[M].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
[12]DL Szlanfucht.1999. How to Save America's Depleting Supply of Farmland [J].Drak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Law,(4).
[13]R E Coughlin,J C Keene. 1981. The Protection of Farmland:An Analysis of Various State and Local Approaches [J].Land Use Law&Zoning Digest,33(6).
[14]JC Juergensmeyer.1981. Farmland Preservation:A Vital Agricultural Lawissue for The 1980's [J].Washburn Law Journal,(21).
[15]孙利.美国土地管理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借鉴与启示 [J].资源导刊,2021,(04).
[16]吴正红,叶剑平.美国农地保护政策及对我国耕地保护的启示:以密歇根州为例 [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48(04).
[17]RJ Johnston,JM Duke. 2007. Willingness to Pay for Agricultural Land Perservation and Policy Process Attributes: Does the Method Matter? [J].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04).
[18]丁成日.美国土地开发权转让制度及其对中国耕地保护的启示 [J].中国土地科学,2008,(03).
[19]D A Sumner. 2000. Domestic Support and the WTO Negoriations [J].Austral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44(3).
[20]Roger Claassen,Andrea Cattaneo,Robert Johansson. 2008. Cost-Effective Design of Agri-Environmental Payment Programs:U. S.Experie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J]. Ecological Economics,65(4).
[21]J W Glauber. 2013. The Growth of the Federal Crop Insurance Program 1990—2011 [J].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95(2).
[22]譚啸威,陈新建.美国农业收入保险的发展历程、运行机制与启示 [J].区域金融研究,2021,(10).
[23]E Jensen. 2000. The Farm Credit System as a Government-Sponsored Enterprise [J].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22).
[24]于伯华.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耕地面积变化及其启示 [J].资源科学,2007,(05).
[25]姚毓春,夏宇.日本、韩国粮食安全现状、政策及其启示 [J].东北亚论坛,2021,30(05).
[26]唐顺彦,杨忠学.英国和日本的土地管制制度比较 [J].世界农业,20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