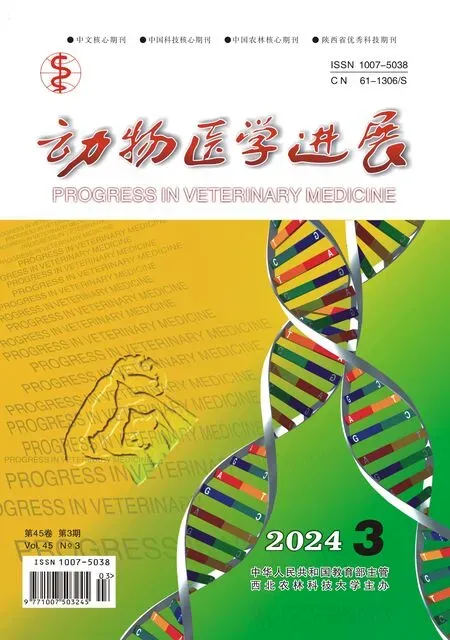猪肝羧酸酯酶研究进展
付岳林,周琼琼,朱慧文,肖启玲,陈 琦,石德时
(华中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农业微生物国家重点实验室,湖北武汉 430070)
猪肝羧酸酯酶又称猪肝酯酶(pig liver esterase,PLE),是由多种同工酶组成的酶家族。PLE独特的手性水解特性使其在有机化学合成领域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近1个世纪以来对PLE的研究主要围绕其在有机化学合成应用方面开展[1-4]。PLE家族作为哺乳动物中复杂的羧酸酯酶家族,成员多且理化特性相似,用物理、化学方法很难分离纯化获得单一成分的同工酶。早期研究发现,PLE具有羧酸酯酶的基本特性,可水解丁酰胆碱、芳香胺等内外源性酯类、酰胺类化合物。早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就尝试从猪肝脏中提取天然的PLE,发现PLE对丁酸甲酯的水解动力学不符合米氏方程,从而发现从猪肝脏中提取的PLE是多种同工酶的混合物,且同工酶的水解特性各不相同,再加上不同批次的提取物成分不完全一致,这些因素严重阻碍了对PLE的研究应用。随着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对PLE编码区序列、蛋白空间构型及水解活性等有了深入了解,PLE家族成员的全基因序列、基因表达调控机制、表达谱及品种差异、在猪常用药物代谢及猪体内炎症反应中作用及机制不断被揭示和阐明。
1 PLE的基因与同工酶分类
PLE同工酶的基因序列及氨基酸差异是研究其功能和水解特性的基础。PLE家族成员中,γ-PLE是报道最早且研究最多的一种。γ-PLE完整cDNA序列长1 698 bp,编码566个氨基酸,N-末端有18个氨基酸的信号肽序列,信号肽剪切后得到长548个氨基酸的成熟多肽,活性中心是Ser 204-Glu 336-His 449(去掉信号肽后的位置),周围环绕着共有结构域Gly-Glu-Ser-Ala-Gly。在C末端有His-Ala-Glu-Leu的4肽结构,与已知羧酸酯酶内质网潴留信号同源,表明该酶定位于内质网腔,但PLE成员之一的APLE(alternative pig liver esterase)在毕赤酵母中表达却定位在细胞周质间隙,说明内质网潴留信号对PLE的细胞定位不是绝对的。
由于在GenBank中PLE基因序列不完整,导致PLE家族基因表达的遗传结构和调控机制研究存在困难。结合荣昌猪BAC文库和第3代PacBio基因测序,筛选出PLE家族的完整基因序列并进行分析,获得4个PLE基因的完整序列,即PLE1、PLE-B9、PLE-C4和PLE-G2(accession number:kx577727,kx5777728,kx577729,kx577730),初步揭示了PLE基因结构和家族基因组结构规律,还阐明了PLE家族基因在染色体上以基因簇的形式存在[5-6]。每个PLE亚型由单个基因编码,且基因间序列同源性高,表明PLE家族是从单个祖先基因进化而来[5]。PLE的启动子特征则与其他哺乳动物CES启动子类似,不含有典型的TATA盒但是含有GC盒,有 2个转录起始位点分别位于翻译起始密码子ATG上游-39 bp和-37 bp处,潜在的转录因子结合位点有 C/ EBP、 Sp1、 USF、 CdxA等[6]。
根据γ-PLE的cDNA序列(GenBank:X63323)设计引物,得到包含γ-PLE在内的6种同工酶,并将γ-PLE更名为PLE1,其他5种同工酶分别命名为PLE2~PLE6,上述各种亚型PLE的cDNA序列高度同源,以PLE1为参照,各亚型分别与之有3~24个氨基酸的差异,这些差异氨基酸分布在5个固定的区段[7]。对猪肝组织PLE的ORF序列进行克隆,根据25个可变位点按氨基酸类型,对PLE亚型进行分类,在猪肝中发现108种PLE同工酶,除去已经报道的5种同工酶外,有103种同工酶是新发现的同工酶,显示出了PLE家族的复杂性;同时发现PLE的表达水平存在年龄、品种以及组织差异[8]。这些差异的存在,对猪在物质代谢、疾病发生等生理的影响还无相关报道,需进一步研究。
2 PLE的空间结构
生理状态下猪肝羧酸酯酶多以三聚体的形式存在,分子质量约175 ku。通过二维等电聚焦电泳得出组成三聚体的亚单位有3种,根据亚单位的分子质量和等电点差异分别命名为α、β、γ,通过十二烷基硫酸钠电泳分离,结果显示α、γ亚基丰度高,β亚基丰度低。以免疫球蛋白重链(H)和牛血清白蛋白(BSA)分子质量为参照,α、β、γ亚基的分子质量分别为58.2、59.7、61.4 ku,等电点分别为5.8、5.2、4.7,通过氨基酸比对分析,显示α比γ亚单位含有较多的天冬氨酸和精氨酸,研究表明PLE主要以γγγ、αγγ、ααγ、ααα三聚体形式存在[5]。
PLE成熟多肽有5个半胱氨酸残基,分别处于70、71、99、256和267位,可以形成二硫键用来维持催化中心的空间结构;一个潜在的糖基化位点(Asn-Xxx-Ser/Thr)在62-64位,其糖基化程度可能与酶的活性有一定相关。催化部位肽段为“-X-Cys-Pro-Thr-Ser-Asn-X”,可以帮助PLE酶活性中心形成稳定的空间结构。参照人羧酸酯酶晶体结构,通过同源建模对PLE1的空间结构进行分析,绘制PLE 1三聚体和单体的结构模型,发现PLE1的空间结构由α、β、γ亚单位组成,相邻单体残基通过范德瓦尔斯力结合[9]。关于PLE理化性质与空间结构研究可关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进一步探究 PLE 蛋白空间结构,分析 PLE-药物分子复合物模型,从而在 PLE 的活性位点或入口通道引入靶向突变,或可将其转化为一种更具选择性、催化效率更高的同工酶,进一步提高临床使用效率;二是详细探究 PLE 空间结构中每个结构域的功能,以期为阐明PLE 在生物体内药物代谢等生理生化过程中的作用机制提供更多信息。
3 PLE的催化水解特性
酶的水解活性及底物特异性由酶的一级结构和蛋白空间结构决定,不同亚型PLE的水解特异性取决于两个关键结构:一是Ser 204、Glu 336、His 449组成的催化三联体,二是72-87位氨基酸组成的底物通过的螺旋通道。不同PLE亚型的螺旋通道结构存在差异。水解过程中,底物需经过螺旋通道,才能进入催化三联体而被水解。现在认为PLE同工酶之间的底物特异性差异,可能由螺旋通道结构不同所致,并不是由催化三联体决定[10]。另外,PLE 1对三丁酸甘油酯、辛酸乙酯和乙酸甲酯的水解活性依次下降,提示PLE的水解活性与底物的某特定基团(如醇基或酰基的大小)有密切关联。
PLE各亚型之间的氨基酸对同一底物的水解活力差异不同。如APLE与PLE1有21个氨基酸的差异,但是对苯甲酰甘氨酰法尼基半胱氨酸甲酯(benzoyl-glycyl-farnesyl-cysteine methyl ester,BzGFCM)的水解活力几乎相同,而PLE3与PLE4、PLE1有20个氨基酸的差异,对BzGFCM的水解活力却分别提高了7倍和9倍,说明了不同位置氨基酸对PLE水解活力的影响大小不等,通过比较发现PLE第285位氨基酸对PLE水解BzGFCM的活力影响较大[9]。通过对已报道的PLE亚型研究发现,所有的亚型均存在相同的活性中心(Ser 204-Glu 336-His 449),但即便是氨基酸序列差异极小的PLE同工酶对同一底物(如p-NPA、2-AG)的水解活力也会相差甚远[10-11],表明酶活力的高低并不完全由活性中心决定,关键位点的氨基酸类型可能也是影响PLE酶活力的重要因素。此外,PLE水解底物有高度的立体选择性,PLE水解立体选择性的差异可能与酶的螺旋通道结构密切相关,研究PLE各亚型的对映选择性,可以为其作为生物催化剂在有机化学合成领域的应用提供理论指导。
4 PLE的功能
4.1 PLE与药物代谢
PLE可高效水解多种酯类和酰胺类化合物释放出相应的自由酸,在药物的水解代谢中也发挥重要作用,如PLE催化1-甲基-1-环丙烷基甲基(CM)水解,产物可作为组蛋白脱乙酰酶(HDACs)抑制剂,并作为治疗癌症和神经退行性疾病等疾病的候选药物,PLE也可以催化消旋 l,2-双甲氧羰基-4-氧环戊烷水解生成 R,R-二酯,产物可以用于抑制HIV[12-13]。由于 PLE 具有高效水解活性,结合人羧酸酯酶可以通过水解功能调控药物在体内的疗效及毒副作用的启发,有理由推测,与其他CES 同工酶一样,PLE 的表达水平及水解活性与兽药在体内的疗效和代谢密切相关。如PLE能够有效的水解β-内酰胺类抗生素药物阿莫西林(AMO)和氨苄西林(AMP),水解发生在β-内酰胺键处,明显降低甚至消除了其抗菌活性[14]。根据研究可以推测,耐药性的产生可能也与宿主体内药物代谢酶的表达水平、组织分布及水解活性密切相关,即耐药性的产生是由细菌和宿主双方共同决定的。以上研究结果提示 PLE 在机体各组织的表达水平及水解活性可能是影响药物治疗效果和代谢过程的重要因素,故在制定某些药物的用药方案时,应充分考虑PLE在体内的表达丰度与活性。
PLE对许多人类临床常用药物也具有显著的水解作用。有研究比较了BNPP对人CES1、 PLE和其他哺乳动物羧酸酯酶对氯吡格雷的水解影响,发现BNPP可以有效抑制包括PLE在内的羧酸酯酶对氯吡格雷的水解[15];PLE可以显著加速阿昔洛韦及其三环衍生物(6(4-MeOPh)-TACV及其酯)的水解[16];PLE可高效催化外消旋叠氮乙酸酯,产物可为治疗牙龈疾病提供独特的疗法[17];用PLE探究新型镇痛药瑞芬太尼的降解动力学,发现PLE可加速瑞芬太尼的降解,并且当PLE存在时,瑞芬太尼的体外半衰期随温度的升高而缩短[18]。PLE具有强大水解功能,可运用到人类临床中药物的设计与研发中,如瑞芬太尼是重症监护病房常用的镇痛药,危重病人体温波动较大,因此在日常工作中应特别注意温度对药代动力学的影响。同时在选择动物模型进行药物代谢研究时,应充分考虑到动物体内羧酸酯酶对药物代谢的影响,以便提供更加科学准确的临床数据。
通过研究PLE和RLE对UTL-5g(一种TNF-α的小分子抑制剂)的水解发现,PLE对肽键也具有水解功能[19],关于PLE是否能水解肽类物质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4.2 PLE与炎症反应
炎症是机体组织对损伤性刺激的一种防御性反应,炎症反应的程度取决于促炎介质和抗炎介质是否均衡,对大多数的病原或刺激引发的炎症反应,机体自身可以通过炎症产物的负反馈作用完成炎症平复[20]。CES与机体炎症反应有密切关系,可作为大麻素降解酶介入内源性大麻素实现对机体炎症的调控,PLE作为CES家族成员之一同样具有调控机体炎症的作用。
内源性大麻素参与炎症、疼痛、认知等一系列生理活动[21],主要包括花生四烯酸乙醇胺(anandamide,AEA)、2-花生四烯酸甘油(2-arachidonoylglycerol,2-AG),大麻素与受体CB2等结合启动的抑炎连锁反应,是机体实现炎症稳态的主要机制之一[22]。经典大麻素降解酶——酰基甘油酯酶(monoacylglycerol lipase,MAGL)和脂肪酸酰胺水解酶(fatty acid amide hydrolase,FAAH),可以水解大麻素而上调炎症水平[20],而Brittany 等发现小鼠羧酸酯酶可降解2-AG,其活性甚至超过了经典大麻素降解酶[23];人羧酸酯酶水解 2-AG 的活性与经典大麻素酶的活性相当[24];PLE可高活力水解2-AG、AEA[25]。PLE通过水解内源性大麻素及其氧化代谢产物前列腺素脂类,生成促炎介质花生四烯酸和前列腺素类,从而发挥显著促炎作用[26],且不同亚型PLE水解2-AG的活力存在巨大差异[10],提示不同的PLE亚型在炎症反应中的贡献存在差异;而通过降低PLE的表达或抑制其活性可以降低机体的炎症反应;同时研究发现PLE在猪原代肺泡巨噬细胞对2-AG的水解比例显著高于经典大麻素降解酶MAGL,表明PLE是2-AG水解的限速酶,在体内炎症反应中可能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PLE可成为治疗猪炎症性疾病的新靶标,PLE作为大麻素降解酶调节机体炎症的机制,为研究并解决炎症相关疾病提供新的角度与视野,为治疗人类炎症性疾病的药物开发提供参考。LPS诱导的炎症反应可降低组织中PLE的表达水平及对p-NPA和2-AG的水解活性[25,27],提示 PLE很可能是机体炎症负反馈的关键靶标,PLE的调控很可能是机体维持炎症稳态的重要机制之一。
4.3 PLE与癌症
PLE可对异戊烯基蛋白去甲基化,该蛋白的去甲基化对其将某些重要功能蛋白锚定在质膜上是必不可少的,PLE通过这种方式,影响细胞的增殖、分化、信号传导及凋亡[9]。聚异戊二烯基甲基化蛋白甲基酯酶(PMPMEase)也具有与PLE一样的去甲基化功能,后经蛋白组学比对和Mascot数据库检索证实,猪肝中的PMPMEase和PLE是同一种物质。
PMPMEase可靶向聚异戊二烯化途径可逆步骤中水解PPMTase(一种聚异戊二烯化依赖性酯酶)的酯产物,具有选择性水解聚异戊二烯化底物的独特能力[28]。PMPMEase活性对于聚异戊二烯化蛋白的代谢、活性和功能是重要的,最近已经在PMPMEase siRNA对RhoA甲基化状态、激活及其对F-肌动蛋白和细胞形态学的影响的研究中得到证实[29]。此外PMPMEase在癌症和退行性疾病的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用多不饱和脂肪酸(PUFAs)抑制PMPMEase会导致癌细胞死亡[28],提示PMPMEase活性在癌症中可能增加;PMPMEase在胰腺癌、结直肠癌、肺癌细胞中的酶活性和蛋白表达升高,抑制PMPMEase活性可诱导癌细胞凋亡,并且抑制后也改变了癌症相关基因的表达[30];PMPMEase作为雄激素不敏感性前列腺癌的新药物靶点的潜在作用已被确定[31]。使PMPMEase成为一种合适的生物标志物,可用于部分癌症的早期/伴随诊断。开发出有效和特异性的PMPMEase抑制剂,并且靶向该酶进行特异性抑制或可成为临床治疗癌症的有效且新颖的策略。
5 结语
国内外对PLE家族的研究重点主要是围绕PLE的基因克隆、结构分析、功能性表达和手性水解特性展开,对PLE在体内药物代谢、营养物质代谢、信号转导等药理生理功能方面相应的研究报道还是相对较少。但对于还有哪些PLE同工酶存在,同工酶各自的基因序列及表达产物的水解特点,对内外源性物质特别是药物的水解机制和代谢贡献、不同品种猪同工酶丰度及酶活性的差异、表达调控机制、表达谱等,正在被逐渐揭示或阐明。基于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进化原则,PLE庞大的家族被保留于动物体内,并且在组织器官内广泛分布,提示其在机体中必定具有重要的生物学作用及意义,目前研究所展示出的其在内外源性化合物的水解、调控机体炎症水平等方面的作用仍只是冰山一角,其强大功能与巨大潜力,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索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