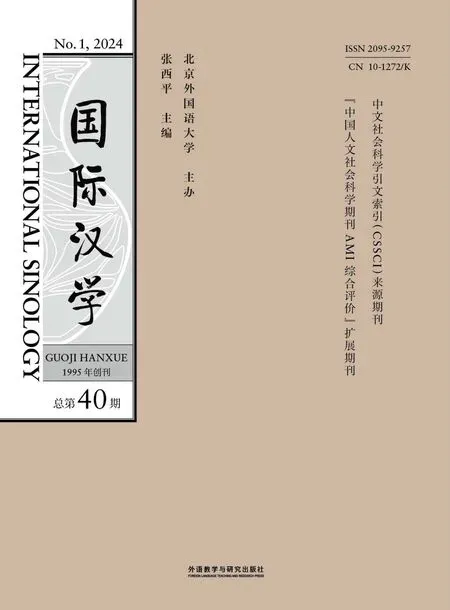德国巴陵会传教手册的中国书写与话语范式*
□ 陈 悦 张 帆
一、巴陵会早期对华传教与刊物出版
萌蘖于17 世纪的德国虔敬主义(Pietism)追求“基督再临”和“神圣的新秩序”,在动荡的19 世纪德国催生出一批大大小小的传教差会,其空前盛况被德国著名神学家古斯塔夫·瓦内克(Gustav Warneck,1834—1910)称为“传教世纪”①Gustav Warneck, Warum ist das 19. Jahrhundert ein Missionsjahrhundert.Halle: Fricke, 1880, S.16.。柏林巴陵会②巴陵会(习称信义会),由柏林法学教授莫里茨·奥古斯特·冯·霍尔维克(Moritz August von Hollweg,1795—1877)1824 年牵头十位基督徒创立。成立初期名为“Die Gesellschaft zur Beförderung der evangelischen Missionen unter den Heiden”(“促进在非基督徒间开展新教传教的协会”),1908 年更名为Berliner Missionsgesellschaft(BMG),1992 年再次易名为Berliner Missionswerk(BMW),沿用至今。便是在此传教浪潮下创立的德国新教传教差会的佼佼者,其创建之初积极垦拓海外势力,陆续向非洲和东亚地区发展教务,受到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的鼓励支持。1850 年,郭实猎(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所作《中国国门已开》的著名煽动性演讲令威廉四世对中国这个遥远的文明古国产生了极大兴趣,③Karl Rennstich, Die zwei Symbole des Kreuzes. Handel und Mission in China und Südostasien.Stuttgart: Quell Verlag, 1988, S.143.也得到德国新教传教差会的积极响应。巴色会、巴勉会、小巴陵会、巴陵女书会等传教差会陆续派遣传教士来华,④孙立新:《从中西文化关系角度看19 世纪德国新教的中国传教》,载《文史哲》2003 年第5 期,第41—42 页。而第二次鸦片战争也为在华传教提供了更多保障与便利。1882年,原本持观望态度的巴陵会首次派遣传教士韩士伯(August Hanspach,1826—1893)和何必力(Friedrich Hubrig,1840—1892)来华,在广东客家地区发展教务,同巴勉会明确划分教区,全面接手小巴陵会在中国南部的传教工作。
1898 年,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二世扬言要夺取“阳光下的地盘”,出兵占领胶州湾,同年4 月,巴陵会华南传教区总牧郭宜坚(August Kollecker,1857—1943)和 昆 祚(Adolf Kunze,1862—1922)教士来到青岛考察,由昆祚留青岛负责实行“实验性传教”。同年,传教经验丰富的巴陵会传教士和士谦(Carl Johannes Voskamp,1859—1937) 和 卢 威 廉(Wilhelm Lutschewitz,1872—1945)从广东传教区驰援青岛,协同昆祚在即墨和胶州等地建立传教站。截至“一战”前夕,巴陵会的传教工作已从青岛逐渐推行至胶州湾全境。“一战”战败后,德国不再拥有胶州租界区的管辖权,巴陵会山东教区的传教工作随之终止。1952 年,外国传教士被禁止在华宣教,巴陵会华南教区的传教士亦陆续离开中国,其在华传教史至此画上了句号。
巴陵会自成立起便定期发行出版物,记录差会内部工作进展,宣传外派传教士的教务成果,海外各教区定期寄回家乡的书面报告成为巴陵会出版物中最具吸引力的内容。根据巴陵会1882年颁布的《传教规章》,“传教士有义务认真撰写日志,每一季度经由教区总负责人寄回总部委员会,详细汇报传教工作、传教活动的进展和困境,以及传教地境况。”①Missionsordnung der Gesellschaft zur Beförderung der evangelischen Missionen unter den Heiden zu Berlin.Berlin: Im Selbst-Verlage der Gesellschaft, 1882, S.66.“亲历者在报告中所呈现的鲜活事迹比国内精心改编的故事具有更大的影响力”。②Ibid.传教文章不仅有助于圈内人士了解巴陵会的传教活动和进展,而且也是激发教徒读者积极关注巴陵会教务发展、资助乃至参与传教事业的首要且最自然的途径。③Roswitha Bodenstein, Die Schriftenreihe der Berliner Missionsgesellschaft.Berlin: Berliner Missionswerk, 1996, S.3.
随着巴陵会海外传教事业的迅猛发展,1866年,《巴陵会宣传册·新系列》(Traktate der Berliner Missionsgesellschaft.Neue Folge, 1866—
1867)作为第一套新版传教宣传手册,在两年间共出版三期,因当时巴陵会尚未在中国开展教务,未刊发来自中国传教区的文章。第二套传教手册《巴陵会传教宣传册·新系列》(Berliner Missionstraktate.Neue Folge,1871—1886)共 印行28 期,当时巴陵会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尚处草创阶段,故仅有一期中国教区作品,即传教士何必力撰写的信徒故事《李宗音——中国传教忠实的见证人》(Li-tshyung-yin,ein treuer Zeuge in der chinesischen Mission,1885)。该故事讲述了广州传教区身世凄苦的阿勤(音译,浸礼后更名为李宗音),经历磨难入读巴陵会传教学校,毕业后投身传教事业,力疾从公,成为教区的典范,被巴陵会柏林总部授予执事职位。该文堪称在华传教士作品的范本,后收录于《新传教文集》(Neue Missionsschriften)。1889 年,巴陵会为更好地记录和宣传海外传教活动,成立“柏林新教传教协会书店出版社”(后文简称“书店出版社”),为出版和传播新版传教刊物提供了重要阵地和保障。
二、新版传教系列手册与来华传教士的中国书写
书店出版社成立后近五十年间,巴陵会陆续出版《新传教文集》、《儿童传教文集》(Missionsschriften für Kinder,1890—1906)、《新传教文集(新系列)》(Neue Missionsschriften〈Neue Folge〉)、《儿 童 传 教 文 集(新 系 列)》(Missionsschriften für Kinder〈Neue Folge〉)、《儿童传教文集·新系列》和《小开本儿童传教文集》(Kleine Kindermissionsschriften)等系列传教手册,每种发行规模5 期到91 期不等,但制式基本统一,以单行本的形式每期刊发一部作品,体裁包括游记、演讲、小说、日记等,其中来自中国传教区的作品近60 期④这些传教系列手册中也有来自其他传教区的作品,如南非、乌干达、马达加斯加、印度、日本等,本文仅论述来自中国传教区的作品。,作者包括近二十位德国来华传教士和三位中国基督徒,内容涵盖中国语言、民间信仰、文化礼俗、妇女儿童、中国传教工作境况、中国信徒传记等。传教手册出版后深受德国读者欢迎,部分作品多次再版,被译成波兰语、索布语和立陶宛语等,仅《新传教文集》和《儿童传教文集》在发行的前五年就分别售出11 多万册和近15 万册,⑤Bodenstein, op.cit., p.7.可见其传播之广、影响之大。
《新传教文集》创刊于1890 年,截至1907年停刊时,共印发86 期,其中中国教区作品15 期,占比逾六分之一。巴陵会在《年度报告》(Jahresbericht,1891)中特别推介该刊:“朋友们,我们恳请您将目光转向《新传教文集》,我们将在所有传教节日公开展示这一刊物,请给予特别关注。”①“Jahresbericht,” Missions-Berichte der Gesellschaft zur Beförderung der evangelischen Missionen unter den Heiden zu Berlin für das Jahr 1891.Berlin: Verlag des Missionshauses, S.198.杂志统一采用蓝色封面和封底,关涉中国教区的杂志封面以中国人物为主,封底多配有传教士拍摄的中国家庭全家福、中国妇女或中国寺庙的照片。每期篇幅一般为16 页或32 页,题材主要包括:中国信徒故事,如《新教教徒宋恩福》(Der Evangelist Sung-en-phui,1890, 第15期)、《学者李尊朝的报告》(Mitteilungen aus dem Gelehrten Li-syn-tshoi,1890,第25 期)、《李 宗音——中国传教忠实的见证人》(第57 期)、《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Das Wichtigste aus den Tagen meines Lebens,1901,第65 期)等;在华传教工作与生活概览,如《德国殖民地传教区的办学情况》(Allerlei Schulbilder aus der Mission in den deutschen Kolonien,1906,第81 期)、《胶 州 地区即墨市的传教工作》(Aus der Missionsarbeit der Stadt Tsimo im Gebiet von Kiautschou,1906,第82期)、《由康庄大道转向独木小桥:传教区生活图景一览》(Vom breiten zum schmalen Wege:ein Lebensbild aus der Mission,1902,第70 期)等;关于中国人的生活百态,如《中国的形形色色》(Allerlei aus China,1901,第63 期)、《中国那些有关生命与死亡的画面》(Bilder des Todes und Bilder des Lebens aus China,1901, 第64 期)、《中国女人》(Die Frauen Chinas,1902,第73期)等。②《新传教文集》中国教区作者包括巴陵会传教区总牧来施那(Friedrich Wilhelm Leuschner, 1862—1922)、卢威廉、和士谦,以及何必力、黎威廉(Wilhelm Rhein, 1864—1941)等传教士;值得一提的是,第25、65 期首次收录两篇分别由中国基督徒李尊才(Li-Syn-Tshoi,音译)和陈奋斗(Tsen-Fen-Thau,音译)撰写、后由德国传教士和士谦与来施那翻译整理的中国信徒故事。
作为巴陵会在华传教士首次大规模集中书写的“中国故事”,各文类采取不同的叙事策略。首先,讲述“信徒故事”惯用对比叙事的策略,凸显信徒在“归信基督教”前后思想与行为上的显著变化。如通过读书人陈奋斗自述曾因“异教的邪恶”沦为鸦片瘾者,饱受煎熬与折磨;但基督教“上帝的恩典”将他从黑暗带入光明与“平安的港湾”,成为广东始兴传教站一名中国同工,坚守信仰,虔信至终(《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其次,在华“传教日志”与工作生活概览相对客观平实,多记叙传教士在华建立传教站,乐善好施,吸纳教民,发展教务,彰扬传教的功德绩业。如《胶州地区即墨市的传教工作》详细记叙了传教士在即墨地区考察和建立传教站的所见所闻,利用热闹集市售卖基督教宣传册,通过办学、看诊等方式与当地乡民拉近距离,招收信徒,传播教义。最后,描述中国人生活百态与民族特性的文章,惯于将中国信徒置于异教徒的对立面,强调传教给中国人带来的福音与恩赐,激发德国基督徒对中国异教民众的同情怜悯之心。如《中国女人》从家庭地位、婚嫁、生育等角度描述女人遭遇的不公与苦难,突出中国女性亟待接受福音的必要与迫切。总之,《新传教文集》作为德国巴陵会在华传教的早期重要的差会宣传刊物,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及近代“中国形象”在德国的建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05 年,巴陵会对传教手册实施了彻底而有效的变革,力图以更低的价格出版更精美的作品,实现更广泛的传播效果。③Martin Wilde, “Für die Winterzeit,” Mission und Pfarramt 2 (1909), S.135.改版后的《新传教文集(新系列)》至1937 年停刊,累计发行91 期,其中来自中国传教区的作品21 期,占比近四分之一。新刊手册除了沿袭旧刊的“传教士在华工作概述”“信徒传记”等突出传教士在华传教成果以外,有所创新。首先,形式上比旧版更加精美,采用质地优良的内页纸张与彩绘封面,设计力求与时俱进,正文添加了与作品相关的插图,如人物、风景照、中国传教站或教区地图,以及中国茶舍、寺庙佛像、中国信徒的手写信件、祖先祠堂等。每期作品篇幅有所扩容,增至16 页至40页。其次,作品题材更加“中国化”,描述中国民间信仰与礼俗,如第27 期《中国的偶像崇拜》(Bilder aus dem chinesischen Götzendienst,1910)、第54 期《龙王》(Liung wong,der Drachenkönig,1922)、第55 期《在中国南部的经历与听闻》(Erlebtes und Erlauschtes aus Süd-China,1925)等;撰写中国信徒传记,如第30 期《基督教旗帜下的忠诚斗士》(Ein treuer Streiter unter Christi Fahne,1910)、第37 期《水牛石的基督徒》(Die Christen vom Büffelstein,1912)、第38 期《穿过黑暗,迎来光 明》(Durch Nacht zum Licht,1913)、第45 期《两位中国人如何寻得救主》(Wie zwei Chinesen den Heiland fanden,1914)等;探究中国语言文化,如第79 期《中文难吗?》(Ist die chinesische Sprache schwer?,1935)等。最后,传教士作者阵容扩大,视野和立场多元拓展,除老作者来施那、和士谦及卢威廉以外,还有昆祚、戈特弗里德·恩德曼(Gottfried Endemann,1874—1914)、 米 伦 贝 克· 古 尔(Mühlenbeck Gurr,1892—1923)、赫 尔 曼·米 勒(Hermann Müller,1884—1923)、弗里德里希·施米特(Friedrich Schmitt,1896—? )、 玛 丽· 肖 尔 茨(Marie Scholz,生卒年不详)等新人涌现。总之,尽管来自中国教区的《新传教文集(新系列)》几乎每期作品均有关涉中国民间信仰与祭祀礼俗的记叙,但传教士作品的初衷必定不是弘扬中国文化,而是为了开阔本国视听、增益国民见闻、累积民族智识。因此,中国文化的传播难免受到他国意识形态的宰制,而着力显化中国作为“异教国家”的蒙昧与顽腐,夸大传播福音、帮助中国人摆脱“撒旦的魔爪”的宗教意涵。
此外,巴陵会陆续推出四套儿童传教手册,亦颇具影响力。与《新传教文集》同年创刊的《儿童传教文集》,收录“由传教士撰写的通俗小说”和有关“传教区的记录”①“Jahresbericht,” Missions-Berichte der Gesellschaft zur Beförderung der evangelischen Missionen unter den Heiden zu Berlin für das Jahr 1890.Berlin: Buchhandlung der Berliner evangelischen Missionsgesellschaft, S.412.,发行16年,出版55 期,②《儿童传教文集》1890 年创刊,是年发行18 期,1892—1894 年出版中断,之后每年印发1 期到6 期不等,直至1906 年停刊。收录德国传教士撰写的“中国故事”七篇③该系列手册有三期作品作者不详,分别为《一座中国大城市》(Beschreibungen einer chinesischen Großstadt, 1890)、《中国传教图景》(Bilder aus der Mission in China,1889)、《一位被贩卖和拯救的中国人的故事》(Geschichte eines verkauften und erretteten Chinesen,1889)。,例如和士谦的《一位中国基督徒奇怪的生活方式》(Merkwürdige Lebensführung eines chinesischen Christen, 1903)记述“皈依”基督教,临终感受到“神赐平安”的信徒故事;伊丽莎白·弗兰克(Elisabeth Franke,生卒年不详)的《李村》(Lizun, 1906)描述了传教士在李村招收中国信徒,并以基督徒的方式共同庆祝中德节日,呼吁德国儿童读者助力福音传播,为异教国度敲响“教堂的钟声”;昆祚的《中国的黑暗力量》(Die Macht der Finsternis in China, 1906)则将尚未福音化的中国与民众比作魔鬼撒旦代表的“黑暗”,而将基督教渲染成拯救中国的“光明力量”。需要指出的是,昆祚“过于相信上帝的力量”,对“《圣经》里的话深信不疑”④Lotti Kohls, Von Engeln geleitet. Teil I. Tsingtaumädels Jugendweg.Metzingen: Brunnquell-Verlag der Bibel-und Missions-Stiftung, 1979, S.8.,过度的信仰内化使其文字欠缺文学审美性与艺术真实性,“他的报告既不具有和士谦作品的戏剧性,亦缺乏卢威廉文字的可信性与确切性”⑤Lydia Gerber, Von Voskamps “heidnischem Treiben” und Wilhelms “höherem China”. Die Berichterstattung deutscher protestantischer Missionare aus dem deutschen Pachtgebiet Kiautschou 1898—1914.Gossenberg: Ostasien Verlag, 2008, S.141.,这也是昆祚虽在华传教多年,但其作品较少受到关注的原因。七部作品就形式而言,篇幅均不超过17 页,手册封面与封底为中国传教区照片或手绘的教堂、传教士或中国官员肖像、中国敬拜仪式;故事内容亦缺乏典型的“儿童性”,故冠名“儿童传教文集”显得有些名不副实。
《儿童传教文集》停刊三年后,巴陵会继而推出《儿童传教文集(新系列)》,总计发行17 期,涉及中国传教区作品共7 期,每期篇幅为15 页至32 页不等,内容包括:传教士“工作日志”和“信徒传记”,如戈特弗里德·恩德曼《如何从魔鬼的奴隶变成上帝的仆人》(Wie aus einem Knecht des Teufels ein Gottesknecht wurde,1913,第11期)和玛丽·肖尔茨《效仿慈悲的撒玛利亚人的中国姑娘》(Chinesische Mädchen in der Nachfolgedes barmherzigen Samariters,1914, 第16 期);中国民间故事,如来施那《假神明招致嘲笑》(Die falschen Götzen macht zu Spott,1909, 第6期)和戈特弗里德·恩德曼《中国故事若干则》(Geschichten aus China,1913,第13 期)。这些故事多用窠臼化的俗套叙事显示基督教信仰的“优越性”,贬斥中国神灵崇拜滋生“迷信”、落后、愚昧与荒谬。就形式而言,《儿童传教文集(新系列)》的内页纸张质地优良,彩色封面印有中国主题手绘,如第6 期封面为中国巨龙与德国传教士的对峙,喻指两种文化、宗教信仰之间的对抗与角力;有的封面则采用圣经主题,所绘图案为一本摊开的《圣经》,具体为马太福音第28章19—20 节内容,以彰扬福音传播的合规性与神圣性。概而观之,《儿童传教文集(新系列)》与旧版相较,内容同样过于成人化,栏目设计与同时刊行的主流刊物《新传教文集(新系列)》并无二致。“一战”爆发后,德国无暇顾及东方传教事务,《儿童传教文集(新系列)》随即停刊,而“一战”战败更让巴陵会险些退出在华传教的舞台。
1926 年,巴陵会逐渐恢复元气,重启儿童传教手册的刊印工作,改革刊行《儿童传教文集·新系列》(Kindermissionsschriften.Neue Folge),至1936 年停刊,出版15 期,中国传教区作品共9 期,均由传教士古斯塔夫·肖尔茨(Gustav Scholz, 1871—1965)的妻子玛丽·肖尔茨和昆祚之女洛蒂·科尔斯(Lotti Kohls,1902—1989)创作,篇幅介于13 页至32 页。该手册形式设计更加精美,彩色封面绘有独具艺术观赏性的画作,内页配有多幅黑白简笔插画或照片,如中国的神像敬拜、花轿、学堂、家庭合影等,语言风格更加简单质朴和口语化;尤为值得称许的是,该系列手册首次凸显“儿童性”的办刊宗旨,“宗教教育的必要前提是赢得儿童的兴趣”①Walter Freytag, “Vom Bildungswert der Missionserzählung,” Vom Dienst an Theologie und Kirche: Festgabe für Adolf Schlatter zum 75. Geburtstag, 16. August 1927.Berlin: Furche-Verlag, 1927, S.238.,封面多选用儿童主题,故事内容增添了儿童阅读的趣味性和针对性,主要描写逆境中的中国儿童凭借信念和坚持,虔信基督教而获得救赎的故事。如《阿妮——一个盲女的故事》(A Ngi,die Geschichte einer Blinden,1927,第6 期)和《雪婴 与 福 弟》(Schneewaise und Glücksbrüderchen,1925,第15 期)讲述了中国女盲童在传教士创办的寄宿学校重获新生的故事。《忠泰:一个中国女孩的故事》(Dschong tai:die Geschichte eines chinesischen Mädchens,1926,第1 期)、《中 国儿 童》(Chinesenkinder,1930,第10 期)、《可以喜爱中国孩子吗?》(Kann man Chinesenkinder liebhaben?,1930,第11 期)和《永恒的光线照进来》(Das ewige Licht geht da herein,1932,第13 期)均记述了中国儿童在传教士的照顾与训导下成长,最终领洗入教的经历。这些作品倡导博爱与救赎,女传教士的文字格外显豁出母性的柔美和人性的光辉,实现了传教小说“不容忽视的价值”,即让儿童读者对“被赋予的一切抱有感恩之心”②Ibid., p.242.。
1937 年,书店出版社推出全新的儿童传教手册《小开本儿童传教文集》,取代《儿童传教文集·新系列》。《小开本儿童传教文集》共出版五期,其中三期是“中国故事”,均出自中国南部教区传教士弗朗茨·胡恩(Franz Huhn,1881—1960)之手,篇幅均为16 页。《无头偶像》(Der Götze ohne Kopf,1937)描绘了中国宗庙祠堂的祭祀仪式,民众敬慎虔诚地祈愿、赛龙舟的热烈场面,为德国儿童读者传达异域陌生的宗教图景,“祈愿失败”的故事结局增强了离奇曲折的文学效果,增添了作品的趣味性与吸引力。《茶舍》(In der Teehütte,1937)则描述一位传教士在中国茶室歇脚攀谈,他将孩童比附为上帝“走失的儿子”,以此安慰“走失了儿子”的中国父亲,以实现文本的宣教目的。《盘古庙》(Im Tempel des Panggu,1937)借中国“盘古创世”神话引出“上帝创世说”,呼吁中国儿童参加教会的周日主日学,聆听耶稣的故事。总体而言,在后期儿童传教手册系列中,多见传教士将中国故事与圣经教义相结合的论道方式,描绘出孤苦无助的中国儿童领洗入教的具象过程,既实现训喻功能,亦不失趣味与可读性,从而将儿童救赎与基督教传播融为一体。
三、传教士中国书写的东方主义话语范式
柏林巴陵会传教士的中国文本拘囿于欧洲中心主义立场与基督教文化逻辑,遮蔽了对中国礼俗文化与宗教思想的探发抉微,导致中国知识生产与传播的错位与倒置。
其一,传教士对中国神话传说的执意误读和对民间信仰的盲目贬斥。中国既是“信仰他者”,也是“文化他者”与“文明他者”。在文化中心主义的视角下,传教士以自身的历史立场与文化逻辑构筑“他者”文化的诠释规则,将“他者”视域下的中国和中国文化置于“福音化”与“文明化”的西方社会的对立面。正如奈杰尔·拉波特(Nigel Rapport)所言:“自身的历史偶然性和本土观念、事实和时间往往被提升成绝对的原则,而那些非常态的则被武断、被拆散,甚至被忽略。”①奈杰尔·拉波特(Nigel Rapport)、乔安娜·奥弗林(Joanna Overing)著,鲍雯妍、张亚辉译:《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The Key Concept),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年,第10 页。传教士弗朗茨·胡恩的《盘古庙》,采用第三人称的记叙视角,以对话形式,借中国村民之口道出“盘古开天辟地”的民间神话传说,由此引出基督教“上帝创世”的典故。作者将中国传说与基督教的两种“创世论”并置,向儿童读者抛出“人类起源说”的审美考问:“由盘古的虱子幻化而成,或依照基督上帝的形貌而创,你们认为哪种更加美好?”盘古神话彰显的人本主义思想显然被弱化,盘古“神于天,圣于地”所显豁的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精髓被漠视和芟荑。正如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 1935—2003)所言:“客观的结构(东方之实际所指)和直观的再结构(东方主义者对东方的表述)被混为一谈。东方主义者的理性被强加于东方之上,其原则也摇身变为东方自身的原则。”②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Orientalis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年,第173 页。
其二,尽管巴陵会在华传教后期,部分开明传教士意识到“德国时常对中国产生误解”③Franz Huhn, Im Tempel des Panggu.Berlin: Buchhandlung der Berliner evangelischen Missionsgesellschaft, 1937, S.4.,故而摒弃对中国故事的选择性解读与刻意歧化。然而他们自身的学识素养、道德理性与宗教情怀不可规避地影响着对中国异质文化的接受与体认,过度的信仰内化削弱了其理性、客观地审视中国“他者”文化的可能性与意愿。事实上,巴陵会传教士大多出身手工业阶层,通常“未接受完整的国民教育”④Gerber, op.cit., p.32.,学养尚浅,对“中国故事”基本停留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层面,阻碍了他们对中国文化思想内核的感知与传达,故只能在“喻道功能”层面对“中国故事”进行表面加工和机械的“叙事搬运”,诸如“盘古创世”这类寓意丰富的中国神话传说在实现“异化”与“西传”的同时,也成为传教文学训喻功能下的“牺牲品”。
其三,为探寻中国人的信仰根基,巴陵会传教士试图在中国神话故事中“解码”中国“这一泱泱大国的宗教想象”,进而考察“中国人对神明与鬼神的思考”⑤Johann Adolf Kunze, “Vorwort,” Liung wong, der Drachenkönig.Berlin: Buchhandlung der Berliner evangelischen Missionsgesellschaft, 1922, S.2.。昆祚的《龙王》讲述了流行于山东民间的五个“龙王”故事:龙王施法降冰雹、黑龙王传说(两则)、泾河龙王被斩首、青龙王与药王孙思邈,以此展示中国道教对中国神话想象的渗透与规约。这些神话传说蕴含道家的鬼神观,是“从人类世界向神明世界的直接过渡,犹如两个世界之间不存有界限……神明的世界呈现出完全的人类关系。”⑥Ibid.人世“天子”在道家思想中位列道家师祖之下,但在其他普通神明之上,“人与神彼此转换,人与神明本质上共同存在于同一个世界”⑦Ibid.,由此生成传教士话语体系下的“中国式”鬼神观:中国人对于神明的追寻与崇信并非“跨越现世”,而是“在现世中寻索”。
显然,德国传教士对“龙王”传说的阐发绕不开中国的“龙”与道家风水文化。“龙”是中国的象征,是中国古人用以供奉和祈福的神。但“龙”之于基督教而言是“邪恶的集合体”①Johann Adolf Kunze, “Vorwort,” Liung wong, der Drachenkönig.Berlin: Buchhandlung der Berliner evangelischen Missionsgesellschaft, 1922, p.4.,是将整个世界诱向歧路的原罪之蛇,故而在传教士撰述的诸多作品中惯于将中国人对“龙”的尊崇敬畏贬斥为迷信崇拜。在中国道家风水文化中,“龙”代表着山川地脉的起伏与走向,但在传教士的相关阐释中,中国“龙”化育为一个任由轻率批驳的恐怖意象,道家风水文化更沦为“幻象和异端邪说,是精神生活和健康文化发展的桎梏”②Helle Jörgensen, “Zum wechselvollen Verhältnis von Mission und Politik: Die Berliner Missionsgesellschaft in Guangdong,” Deutschchinesische Beziehungen im 19. Jahrhundert. Mission und Wirtschaft in interkultureller Perspektive.Münster: Lit, 2001, S.191.,讥讽中国民间信仰只是对现实与自然界“最表面的”“幼稚的观察”③Kunze, op.cit., p.4.。由此可见,传教士在以中国为“他者”的书写中采用“污名化”手段,集体对中国施以定型化的观念复制,“相斥性的意识形态把自我置于他者之上”,以此实现“虚化他者”的目的。④奈杰尔·拉波特、乔安娜·奥弗林:《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第11 页。
其四,奉行虔敬主义的巴陵会秉持保守的传教原则,即“将所谓民众的‘落后’表述为真正的‘基督教的缺席’,并将传教视为昏暗(异教)与光明(基督教)之间的斗争”⑤Jörgensen, op.cit., p.191.。因而在巴陵会传教士对中国神话传说和异质宗教文化的诠释与解读中,极易寻得泾渭分明的互斥与对立,如赞誉希腊神话是“文化世界共有的精神财富”,以其“美好的艺术形式”流传于世,并影响了歌德、席勒等文学大家的创作。而中国神话故事“出自二三流作家”,中国的民间宗教虽“衍生出神话故事”,但其宗教思想“没有为宗教想象留下真正的创作余地”⑥Kunze, op.cit., p.2.,这显然是在西方文化本位主义的视域下评价中国文化遗产的优劣,力图形塑僵化落后的中国,显现出一种“隐伏的”东方主义书写范式,即“否认东方和东方人有发展、转化、运动的可能性。作为一种已知并且一成不变或没有创造性的存在,东方逐渐被赋予一种消极的永恒性。”⑦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第274 页。
此外,巴陵会在华传教重镇大多设在中国乡村,传教士作品中亦不难看出中国故事的陈述者多为淳朴乡民,对于中国故事的转述与诠释大多拘囿于与其生存息息相关的农业生产和农耕文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传教士的叙事格局与准确度。
事实上,巴陵会传教士刻板俗套的“中国书写”是当时基督教的神圣性向世俗性坠落的精神危机的表征,他们在书写“中国故事”时守持“基督教等同于文明,异教等同于野蛮”的结构观,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西方没落”的矫饰与逃遁,以期获得“一种无法从福音中得到确证的优越意识”⑧Erling von Mende, “Einige Ansichten über die deutsche protestantische Mission in China bis zum Ersten Weltkrieg,” Von der Kolonialpolitik zur Kooperation.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München: Minerva Publikation,1986, S.394.,由此在德国本土引发争议和批评。新教传教士常被视作“心胸狭隘的道德主义者的缩影”⑨Gerber, op.cit., p.20.,著名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抨击巴陵会传教士的部分中国叙事是“将一些无法歪曲的东西歪曲化”,是脱离事实的“自由创想”和“近乎病态的嗜好”。⑩Ibid., p.124.德国汉学系首位教授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呼吁以“科学的”方式探赜中国“陌生的思想世界”⑪Otto Franke, Beschreibung des Jehol-Gebietes in der Provinz Chihli. Detail-Studien in Chinesischer Landes-und Volkskunde.Leipzig: Dieterich, 1902, S.VII.,而非一味流布众所周知的、谬误的中国知识。
概言之,至19 世纪中叶,早期耶稣会士营构的理想而神秘的“中国神话”逐渐祛魅。在用坚船利炮撞开中国国门之后,处于工业文明阶段的西方与衰落中的前现代农业文明阶段的中国相遇,旧有的东西方平衡被打破,“东方被描述为一种供人评判的东西,一种供人研究和描写的东西,一种起惩戒作用的东西,一种起图式作用的东西”①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第52 页。,中国被西方视作可供掠夺的对象和自我发展的警示。这种普遍偏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19 世纪德国新教来华传教士的中国想象,奠定了他们对中国这一异国他乡的“第一印象与感知模式”②Doris Kaufmann, Frauen zwischen Aufbruch und Reaktion. Protestantische Frauenbewegung in der ersten Hälfte des 20.Jahrhunderts.München, 1988, S.158.。19 世纪末至20 世纪初,“传教出版物作为大众文学……对同时代教徒的中国形象认知产生了深远影响”③Gerber, op.cit., p.20.,传教士书写的“中国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构筑了当时德国人眼中的中国“他者”雏形。德国巴陵会来华传教士的中国书写是承载着政治权力、知识权力、文化权力、道德权力的东方主义话语产物,其叙事话语充斥着中德文明二元对立的教条式印记。巴陵会传教士时刻不忘基督教君临天下的“救世姿态”,④叶隽:《主题的迁变——从德国传教士到留德人群》,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年,第55 页。他们在虔敬派保守的宗教底色之下,单向度地将中国视为亟待拯救的“异教国度”,对中国文化习俗肆意曲解和歧化,表现出片面的排他性与对立性,为基督教福音传道提供便利与庇护,充当为母国“谋求政治利益、承载政治影响力”⑤Wolfgang Franke, China und das Abendland.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62, S.72.的角色,而被歪曲或异化的“中国故事”亦是19 世纪至20 世纪上半叶中德权力关系的映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