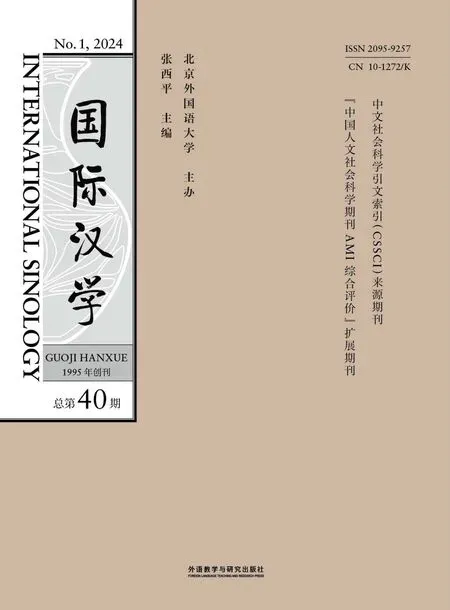19 世纪朝鲜半岛汉语会话书俗字变异解析*
□ 张 黎 敏春芳
一、引 言
汉语俗字的研究,历来以碑刻文献、敦煌写本为主要研究对象。近年来,不少学者认识到,在古代朝鲜半岛、越南、日本以及琉球等地,由非汉语母语者用汉字创作的各类文本中,“既存在大量来自中国以及本国创造的汉语俗字,更有自身创造的反映本民族独特文化的‘国字’或‘固有汉字’,甚至偶尔夹杂与汉字形体迥异的本民族文字。”①王晓平:《朝鲜李朝汉文小说写本俗字研究》,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2 期,第66 页。尤其是接受中国汉字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朝鲜半岛,保留了大量以汉字为载体,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的典籍文献,对其语言、文字、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
学界对朝鲜半岛的俗字研究已初具规模,先后以官刻本《樊川文集夹注》、《训世评话》,坊刊本《九云梦》、写本《漂海录》等朝鲜半岛地区相关的汉籍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汉文小说或早期汉语教科书中的异体俗字用例。②参见张成、姚永铭:《〈朝鲜刻本樊川文集夹注〉文字研究》,载《古汉语研究》2007 年第1 期,第92—96 页;何茂活:《〈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异文处理谫论》,载《古汉语研究》2008 年第2 期,第95—96 页;刘春兰:《〈训世评话〉语法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文学院,2010 年,第11—34 页;王晓平:《朝鲜李朝汉文小说写本俗字研究》,第66—75 页;何华珍:《俗字在韩国的传播研究》,载《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3 年第5 期,第51—57 页。何华珍将俗字研究从朝鲜半岛逐渐扩展至日本、越南等汉字文化圈,③何华珍:《俗字在域外的传播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年。近期专门探究了草书符号“ ”在东亚各国的源流发展。④何华珍:《草书符号“ ”与东亚俗字传播》,载《古汉语研究》2022 年第2 期,第110—128 页。金永寿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对朝鲜汉字资源文献的整理等,⑤金永寿:《朝鲜汉字资源文献整理与研究述评》,载《东疆学刊》2021 年第2 期,第16—28 页。均为汉字在朝鲜半岛的传播研究奠定了基础。随着域外汉字研究视野的不断拓展,朝鲜半岛的俗字研究还需要加强不同书写形式的专题调查和断代研究。
21 世纪初,一批流行于朝鲜王朝(1392—1910)后期的汉语会话类教科书(下文简称“会话书”)见于韩日一些国立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及私人收藏处。经汪维辉、朴在渊等中韩学者考证,除了《华音启蒙谚解》是由当时的朝鲜译官李应宪编纂外,《骑着一匹》《中华正音》等其他会话书均由朝鲜民间私人所作。①参见汪维辉、远藤光晓、朴在渊、竹越孝:《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续编》(上),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朴在渊、金瑛:《骑着匹(六堂文库)·中华正音(华峰文库)》,首尔:学古房,2011 年。韩国学者朴彻庠在《骑着匹(六堂文库)·中华正音(华峰文库)》的序文评价道:“此次校勘、影印的《骑着匹》和《中华正音》并非司译院编撰,而是19 世纪由个人制作的抄本贸易汉语会话书,故不存在刊印本。”②朴在渊、金瑛:《骑着匹(六堂文库)·中华正音(华峰文库)》,第1 页。这些来自朝鲜民间的汉语会话书抄本,由于编写者的汉语水平有限,有的书写随意、潦草,俗字异体更是比比皆是,真实地反映了朝鲜民间的书写习惯,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深入研究汉字在朝鲜半岛传播、接受与流变的丰富宝库。
二、会话书抄本的俗字类型
正如张涌泉所言“朝鲜人在使用汉字的过程中,也采用或创制过一些俗体字,……其中有些字与中国的俗字相同或相近,有些则是朝鲜民族的创造。”③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増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42—43 页。在19 世纪朝鲜汉语会话书抄本中,既有传承自中国的正体字和俗字,也有朝鲜民间自创的变异汉字。本文在自建俗字语料库的基础上,以传统“六书”理论、汉字构形学理论为指导,全面考察朝鲜半岛19 世纪中晚期的汉语会话书(6种12个文本④朝鲜王朝后期汉语会话类教科书“6 种12 个文本”分别是: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藏《你呢贵姓》、韩国鲜文大学校朴在渊教授藏《学清》、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小仓文库藏《华音撮要》、日本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阿川文库藏《中华正音》、韩国顺天大学图书馆藏《中华正音》、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书阁藏《骑着一匹》、日本驹泽大学图书馆濯足文库藏《中华正音》、韩国高丽大学六堂文库藏《骑着匹》、韩国华峰文库藏《中华正音》、韩国藏书阁藏《华音启蒙谚解》、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书阁藏《中华正音》和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小仓文库藏《关话略抄》。)中的俗字与正字⑤本文的“俗字”是指这批会话书文献中所见的区别于正字的不规范“异体字”,“正字”是指中国现代汉语通用字中的繁体字。在笔画、构件和整字三个层级的变异类型及相关特征。这不仅是朝鲜半岛汉籍文献整理与相关研究的前提,也是加深理解汉字在朝鲜半岛的传承和变异的基础。
(一)笔画变异
“从书写的角度讲,笔画是最小的书写单位,又是汉字构形系统中最小的、最底层的构形单位。”⑥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年,第235 页。书写过程中某一笔画的笔形改变,对汉字的构件样式和整字结构都有较大影响。根据各类笔画变异的方式和原因,会话书抄本中俗字的笔画变异可归纳为简省、增繁、同化、异化、易位五种类型。
1.笔画简省
笔画不仅是汉字最小的书写单位,也是字形简化的基础。在这批会话书抄本文献中,有些正体字在基本轮廓不变的情况下,常有单笔画和复笔画的简省现象,从而形成正俗两体的差别。在汉字形体演变过程中,两个以上的点画多简省为一点,而这批抄本中仅有一个点画的字也会被简省,如(臭)⑦文中所用字例,均出自于《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续编》和《骑着匹(六堂文库)·中华正音(华峰文库)》。为了准确反映古籍俗字原貌,文中部分字例保留了繁体字,有些生僻字例来自超大字符集,或者以拍照抓图等形式呈现。括号前是俗字体,括号内是正体简化字,下仿此。、(厂)、㐲(伏)、減(减)、(准)等;多个横画或竖画的字,也易省去一个相同的笔画,如(德)、(值)、(槽)、(要)等。有时仅存的一个撇画也被简省,只保留字形的轮廓,如(鬼)、(候)、畨(番)。有些没有独立构意的复笔画也会被简省,如蔵(藏)、卓(桌)。
笔画本身虽然不能独立构意,但笔画简省对上一层级的构件简省起了最基础的构形作用。会话书抄本中单笔画或复笔画的简省,直接改变了原正体字构件的部分表意或示音功能,影响了原有的构字理据,同时也增加了朝鲜学习者对构件及整字的辨识难度。
2.笔画增繁
在这批会话书抄本中,除了具有装饰性“羡余”笔画外,某些增笔可能也受到了前后字形的相互影响。如“規[规]”②方括号前是正体繁体字,方括号内是正体简化字。在《学清》《华音撮要》《关话略抄》等抄本中,均增加一撇画作“”,可能受相邻字“矩”的影响,造成构件“夫”增加撇画类化为构件“矢”。也有些笔画通过增繁方式,来避免因笔画或构件简单而导致的形近字讹混,如藏书阁本《骑着一匹》的“丈”和濯足本《中华正音》“五”,分别作“”“”或“”,两字增加的点画和竖画,分别与抄本中“大”“王”两字形成一定的区别特征。故抄本俗字在便于书写而简省笔画的同时,也为字形的识别而添加笔画,从而导致抄本俗字也有繁化的趋势。
3.笔画同化
有些本不相同的笔画,在这批会话书抄本中趋于相同或相近。如两点、四点和多点的笔画,均写作一横,使本来有区别特征的笔画趋同。如藏书阁本《中华正音》“會[会]”作“”,六堂本《骑着匹》“黑”作“”,其表意构件“曾”“”中间两点均改换为一横。《华音撮要》“鳳[凤]”作“”,“盡[尽]”作“”,“寫[写]”作“”,“壞[坏]”作“”,其表意构件“鸟”的基础构件“灬”,示音构件“㶳”“舄”“褱”的基础构件“火”“灬”和“眔”的中间四点均同化为一横。
笔画同化现象使比较繁复的笔画趋于简单,多样的笔画趋于统一,对于书写确实提供了方便。不过,笔画同化也会造成形体的相混,如两点、四点和多点同化后的横画,与本来的横画就会出现混淆,反而会影响学习者对不同笔画性质的理解和辨认。
4.笔画异化
有些笔画不仅可变换为别的笔画,还可异化为不同的构件。如一点画可变异为短撇画,如“亡”的构件“亠”,恢复为小篆形体“入”,以“亡”为构件的“忙”“忘”,分别作“”“”。四点画不仅可变异为一横,如(凤)、(尽)、(写),还可变异为几个意义毫不相干的“从”“大”“火”等不同构件,如(点)、(遮)、(鲜)、煑(煮)。带点的复笔画变异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某个复笔画变异为两点画,如“走”“足”表意构件“止”的复笔画变异为两点,分别作“”和“”;另一种是某个复笔画变异为三点画,如“哥”“看”表意构件“可”“手”的部分复笔画均变异为三点画,分别作“”“”。这些复笔画的变异可能与朝鲜书写者求简心理和快速书写产生的连笔有关。
笔画异化现象多将复杂笔画异化为简单笔画,但有时也会异化为更复杂的笔画或无理据关系的构件。因此,笔画异化对构件和整字形体的变异都有较大影响。
5.笔画位移
当某一笔画所处的平面位置有所改变,也会形成一些俗体字形。如《你呢贵姓》、六堂本《骑着匹》和华峰本《中华正音》均将“本”写作“”,笔画“一”从“木”的竖笔中间移至最底部。又如“就”在《骑着一匹》系列各本,有“”“”“”等多个形体微殊的俗体,除了一些字形的表意构件“京”作“亰”外,主要差异就是构件“尤”上一点画被移位至“乚”的不同位置。
一般而言,笔画的位置发生变化时,很难改变字形构意,但会影响字形的区别特征,这也是抄本俗字呈现形体多样化的原因之一。
(二)构件变异
“构件是由笔画组成的具有组配汉字功能的构字单位。”①《信息处理用GB13000.1 字符集汉字部件规范》,北京:语文出版社,1998 年,第2 页。因此,构件是汉字基本构造单位和构形表意的基本要素。根据汉字构形学理论,不仅要关注汉字的表形构件、表意构件与示音构件,还要重视字形的记号类等特殊构件,强调它们在具体俗字中的构形功能和区别字形的作用。根据构件异化的方式和原因,会话书抄本中的构件异化俗字大致可分为:简省、增繁、同化、异化、换用、易位、记号化七种类型。
1.构件简省
构件是汉字构形系统的核心,也是反映汉字书写简化的构形单位。抄本俗字的构件简省主要集中于直接构件或基础构件,各类简省形式既有规律性,又有灵活性。
直接构件简省类俗字多省表意构件,如“蹬”作“登”,“湖”作“胡”,“怠”作“台”等。有些保留下来的示音构件也具有表意功能,如“登”“胡”既表字音外,还表示“上车也”“颔肉”等义。有些形体复杂的直接构件多被替换为简省构件,如包围结构的“麽[么]”、“開[开]”,其示音构件“麻”和表意构件“門[门]”,改换为相对易写的构件“广”“门”,分别作“”“庅”。有些俗字则简省了复合构件的基础构件,如六堂本《骑着匹》“幫[帮]”、“價[价]”,简省了表意构件“帛”和示音构件“贾”的基础构件“白”“贝”,分别作“”“価”。有些还简省了相同的基础构件,如藏书阁本《骑着一匹》“勞[劳]”,其示音构件“熒[荧]”省音,基础构件的两个“火”被简省为一个,作“”。
通过笔画和构件不同层次的简省,会话书抄本俗字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形体简单、书写方便的目的。不过,有些构件简省后破坏了原字的基本构形信息,如藏书阁藏《中华正音》“快”作“夬”等,直接构件失去了主要的表意功能,反映了朝鲜民间书写者在汉字书写便利和汉字构件理据识别两方面的矛盾。
2.构件增繁
除了添加笔画使部分俗字构件增繁外,大量俗字还在正字已有的构件上直接添加别的表意构件。张涌泉认为这类俗字是“床上迭床,屋上架屋”的用字现象。②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増订本)》,第47 页。
会话书抄本在象形字“包”“胃”“瓜”“州”、指事字“四”、会意字“票”“套”“麻”、形声字“背”“房”“暂”“账”“张”等造字方法的基础上,又添加了一些突出字形示意功能的表意构件,分别作“”“”“苽”“洲”“泗”“標”“”“蔴”“揹”“”“”“”“”。这些额外添加的表意构件多属于意义范畴的类推,如“背”“套”增加“扌”表示人的行为动作,“胃”增加“肉”表示身体部位,“瓜”“麻”增加“艹”表示草木类,“州”“四”增加“氵”表示与河水有关的地形义。
追求书写的简化实用本是俗字变异的主流,但别异同也是书写者的内在要求,故字形增繁也伴随其间。抄本中的构件增繁俗字,既有笔画的繁化,又有新构件的添加,凸显了汉字因隶变或楷化而减弱的字义信息,却违背了原构件的构形原则和实际功能,也造成了字体冗余和记忆负担。
3.构件同化
某些构件与其他构件在形、音、义方面本无关联,在这批会话书抄本中却出现形体趋同现象,从而形成了正俗两体的差别。
同化虽然使多样的构件趋于统一,但也忽视了构件本身的形义联系。朝鲜书写者把汉字构件看作可随意改造的符号,虽然表面上减轻了学习者对汉字的记忆负担,本质上却背离了汉字以形表意、因义构形的基本性质。
4.构件异化
“异化是指文字的书写者忽视构件或字形固有的形义联系,将一个形体改造为构意迥别的其他形体的现象,其本质为变异求别。”①何山:《魏晋南北朝碑刻文字构件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304 页。不论是成字构件还是非成字构件,会话书抄本的书写者对同一个构件的改造方式不一,形变结果也不一。
“口”本是独体象形字,是言说与饮食的器官。当“口”作为成字构件时,字形会异化为“工”“厶”等不同构件,同时模糊了整字构字理据。以“口”为构件的字族,也类推发生了字形变异,如“沿”作“”,“狗”作“”。有时构件“口”还会简省为“丶”“丿”等笔画,如“单”作“”,“雖[虽]”作“”。敦煌俗字的“口”俗写多作“厶”,如“句”作“勾”,“员”作“”等。②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増订本)》,第123 页。显然,当“口”作为成字构件时,朝鲜会话书的异化字形比敦煌俗字更多样。
会话书抄本的构件异化类俗字,多以笔画简省、笔画替换构件、简单构件替换复杂构件,呈现了构件异化形体的“一对多”特征。
5.构件改换
当正体字中的一个构件替换为另一个构件,也会形成正俗两体的差别。考察构件的改换,可以发现抄本的俗字字形随音义变化而在不断调整和适应。
在会话书抄本中,构件改换多以形、音、义相近为取向。如《华音撮要》“冒”作“”。据《说文·冃部》,“冒”是从冃从目的会意字,“”下部的构件形似“肉”部,小篆“肉”楷化写“月”,该字形与“目”仅一横之别。藏书阁本《骑着一匹》“鴛[鸳]”“碗”分别作“䲶”“”,示音构件“夗”改换为“元”“完”,两个构件不仅音同或音近,且构件“元”“完”的形体比“夗”简易,故形近或音近的构件易发生改换。藏书阁本《骑着一匹》“躱[躲]”作“”,华峰本《中华正音》“體[体]”作“軆[体]”,构件“身”改换“肉”,“骨”改换“身”,三个构件均与身体义相关,故义近构件也易发生改换。
构件改换也以书写求简、求易为取向,如像箭之形的“矢”,其小篆字形隶变后,曲笔拉直写作“夫”,“矢”“夫”两构件形体相近,且“夫”比“矢”书写简易,故抄本中大量的“候”字构件“矢”均改换为“夫”,作“”“”等;个别构件也以繁化来反向改换,如“規”字的构件“夫”又换用为“矢”,写作“[规]”。又如构件“”笔画较繁复,会话书抄本将其基础构件“囟”,均换作形体简单的构件“田”,故以“”为示音构件的“惱[恼]”,可写作形体相对简易的“”“”等俗字。
从会话书抄本构件改换的特点、效果和规律看,多数改换的前后构件在读音或意义上有一定联系,且换用后仍能体现原字形的构造理据。不过,有些俗字的构件换用仅据易写或形近,如藏书阁本《中华正音》“爽”作“”“”,构件“㸚”换作“”;藏书阁本《骑着一匹》和濯足本《中华正音》“缸”作“”“”,构件“缶”换作“ ”。这类构件换用也会造成形近构件的混用。
6.构件位移
变换某一构件所处的空间位置,也会形成正俗字的差异。抄本俗字的构件位移方式大致有以下五种:有左右构件位移,如“峰”作“峯”,“朗”作“朖”,“蘇[苏]”作“蘓”等;有上下构件位移,且表意构件改换,如“鬆[松]”作“”等;有左右构件位移至上下构件,如“概”作“㮣”,“略”作“畧”,“胸”作“”等;还有上下构件移位至左右构件,如“節[节]”作“”等。
构件组合的空间位移,也是区别汉字形体的重要特征之一。当抄本正体字的内部构件相互发生空间位移,就会改变构件的布局图式,从而形成了众多异体俗字。
7.构件记号化
“符号替代是简省笔画的一种有效方法,因而在俗文字中应用极广。”①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増订本)》,第47 页。会话书抄本有不少正字的某一构件被记号构件所替代,改变了原本汉字的音义构字理据,从而形成了正俗两体的区别。抄本中常见的记号构件有点号、横号、曲折号、“口”号、“厶”号、“”号、“ ”号、“ ”号、“文”号、“入”号、“尺”号、“ ”号和“”号等。如点号构件,可替换不同构件的左右或上下重文结构,如“纔[才]”作“”,“哥”作“”,“樂[乐]”作“”,“麤[才]”作“”等。
会话书抄本还有大量的儿化词,其写法一般都是在儿化前字下写一个“儿”字。如《华音撮要》有三种“儿”的写法,除了前一种情况外,“”号也表儿化功能。不过,有“”号的儿化词写法有差异,即“”号与前一字体编排有一定区别。一种是儿化前字与“”号有一定间距,如“些兒[儿]”作“”,《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续编》(下文简称“《续编》”)校录为“乙”;另一种是“”号紧贴儿化前字,形成合文,如“今兒[儿]”作“”,“候兒[儿]”作“”。故这批会话书抄本的儿化词不仅形体多样,类型与功能也比前期会话书有所增加。
与表意构件和示音构件相比,记号构件的形体相对比较简单,且具有明显的构形或区别特征,易于学习者的认读与书写,但也让学习者减少了理解汉字原有构件的表意功能和构造理据的途径。
(三)整字变异
整字是汉字系统中形、音、义统一的记词单位,也是字形最直接的呈现单位。会话书抄本中的笔画和构件,以承用汉语古文字或古隶书字形、改变造字思路或以重文符号替代等变异方式,进入上一层级组装并推动了抄本中的整字变异。
1.整字承用
抄本中不少俗字直接承袭了形体较简单的古文字或古隶书的形体,后世使用的正体字却是为这些古字记录的词而另造的新字形。如“貌”在《华音撮要》作“皃”,甲骨文字形像人之容貌。据《说文》,小篆“”,加形符“豸”为籀文“貌”,今皆用籀文“貌”为正体,抄本却以古文字形“皃”为“貌”的俗体。“皃”“貌”均见于敦煌文献,如S.800《论语》:“动容貌,斯远暴慢矣。”S.610《启颜录》:“乃密令侯白改变形皃,着故弊衣裳。”②黄征:《敦煌俗字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268 页。朝鲜时代《高丽太师壮节申公忠烈之碑》(1607)和《物名考·卷四》(1802)等汉文献也多见“貌”的各种变体。①吕浩:《韩国古文献异形字研究》,第310 页。这批会话书抄本却继承了中国字书和文献中“貌”的本字“皃”。
2.整字改换
整字改换是根据造字法创造出与正体音义相同,构件完全不同的俗体字。如形声字“笨”在濯足本《中华正音》作“倴”,在藏书阁本《骑着一匹》作“”,形旁“竹”改为“亻”,声旁“本”改为“奔”“ ”,俗字“倴”“”与正字“笨”的表意构件和示音构件均不同。又如在藏书阁本《中华正音》中,从糸辡声的形声字“辮”(辫)和从肉旁声的形声字“膀”,分别改换为从髟偏声的形声字“”和从羽房声的形声字“”。从囗从或的会意字“國[国]”,在六堂本《骑着匹》改换为从口从玉的会意字“”。
这类整字改换的俗字仍然遵循了汉字的造字思路和方法,只是与正体字选用的构件和结构方式有别,反映了汉字形体在朝鲜半岛呈现的动态发展过程。
3.重字替代符号
能够替代相重文字的简单符号被称为重字符号。在会话书抄本中,某些文字之后常以“”“”“”等形体表示相重文字,其两点或分离或连笔,但形体大致相似。在《你呢贵姓》和《学清》中,原文相重的后一个文字写作“”,《续编》校录时直接还原前一字,如“”均校录为“筭筭”;《续编》校《华音撮要》、濯足本《中华正音》、藏书阁本《骑着一匹》等会话书时,在前一字后录“々”表示重文符号;《六骑·华正》校六堂本《骑着匹》和华峰本《中华正音》时,在前一字后录“゛”以表示重文符号。
会话书抄本中的重字替代符号不同于符号构件,是有音有义的构件,但不具备可释性。该用字现象仍反映了抄本对书写简省的心理需求。
三、会话书抄本的俗字特征
19 世纪中晚期朝鲜半岛汉语会话书抄本俗字在笔画、构件和整字三个层级的变异,真实记录了朝鲜王朝后期民间书写者对汉字系统的调整和取舍,同时也反映了朝鲜半岛俗字对汉字形体的传承与变异特征。
(一)三个层级的“简化变异”
简化是汉字发展的主旋律,也是会话书抄本俗字变异的主要方式。当汉字在朝鲜半岛传播与使用时,汉语会话书的编写者在承继汉字传统书写符号系统时,也尽可能从笔画、构件和整字三个层级,以简省、同化、改换和记号化等方式,不断追求文字的简便易写和有效认读。其中,笔画和构件的简化是抄本俗字变异中最基础、最直接的表现形式。
抄本俗字的简化路径多途,手段多样。在尽量保留汉字字形区别特征的前提下,汉字的三个层级都发生了“简化变异”。首先是笔画层级,有相同笔画、不明显或不重要的笔画易简省;或因相近、相同形成的共笔,或因相邻而形成的连笔均减少了笔画;或几个较复杂的笔画同化为一个简单笔画。故在笔画与构件两个层级中,主要以简单笔画替代多笔画组成的某个构件等。其次是构件层级,有直接构件或基础构件易简省;或笔画复杂的构件改换为笔画简单的构件;或形体简单的记号性构件改换形体复杂的构件等。最后是整字层级,有承袭了古文字或古隶书相对简易的形体,或选用形体简单构件重新造字等。
总之,这批汉语会话书抄本中的俗字,通过笔画、构件和整字三个层次相互协调、相互影响,有层次、有系统地对源于中国的汉字形体和结构进行了简化和变异,从而形成了大量形体趋简的俗字,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从事边贸活动的朝鲜民间学习者对汉字的书写和记忆负担。当然,为了区别字形,抄本中也有一些俗字的繁化倾向,不过所占比例不大,复现率较低。
(二)构件形体的“类推性”
这批会话书抄本的俗字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形体各异,但是从整个系统来看,构件层级的变异具有一定的规律。尤其是构件形体的类推性,是维持会话书抄本文字系统的有效手段。在会话书抄本中,主要是通过表形和示音构件的形体变异实现这一类推规律,具体表现为:当某个构件在不同构字环境中形体发生变异后,通过类推作用使含有该构件的字族都具有同样的变异形式。
当表形构件发生形体变异时,在新字中承担表意功能的构件也会类推发生形体变化,如“虎”“能”变异为“”“”后,成为抄本文字系统中的新质要素,当“”“”为表意构件时,含有构件“”“”的字族会类推变异,故“號[号]”“琥”“唬”和“罷[罢]”、“擺[摆]”分别写作“”“”“”和“”“”。当示音构件发生形体变异时,不仅表示新字的读音,也会类推出具有相同变异形体结构的一系列字族,如“詹”“巠”“廉”为示音构件时,“擔[担]”“簷[檐]”、“經[经]”“輕[轻]”“簾”“賺[赚]”,分别类推作“”“”“”“”“”“”。
因此,在简化与类推的共同作用下,抄本的俗字系统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始终处于平衡状态,如“卑”简省撇画变异为“”,以“”为示音构件的字族中,“稗”“粺”“脾”“牌”分别类推为“”“”“”“”。构件“垚”形体比较复杂,俗字以两点为记号构件替代了重复构件“土”,含有“堯”的简省构件字族“繞[绕]”“燒[烧]”分别类推为“”“”。
(三)传承变异中的“创新性”
这批汉语会话书中的大量俗字,是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汉语俗字字形。如前文例字“国”在六堂本《骑着匹》作“”“国”,分别见于《中华字海·口部》和《汇音宝鉴·卷二公·公上入声》,今“国”为规范汉字的简化字。在其他会话书中还有“”“”等字形。如“国”在《关话略抄》作“”,从王从囗,该字形见于《偏类碑别字·囗部》所引北齐天保八年《宋敬业造象记》和《碑别字新编·十一画》所引的《贾思业造象记》,以及《龙龛手镜·囗部》《四声篇海·囗部》《字汇·囗部》《正字通·囗部》《宋元以来俗字谱·囗部》等字书和宋元小说等;《正名要录》的“国”之下脚注“”,说明“”是“国”的俗字。敦煌文献中也有该字形,如《双恩记》:“吾唯有汝偏怜惜,满黄金未为值。”①黄征:《敦煌俗字典》,第145 页。“”字也见于朝鲜高丽时代文献,如《净兜寺五层石塔造成形止记》(1031)、《长谷寺药师如来坐像腹藏发愿文》(1346)②吕浩:《韩国古文献异形字研究》,第250 页。。在藏书阁本《骑着一匹》《中华正音》《华音撮要》中,“国”还作“”,该字形简省了“国”的构件“或”的一点画,朝鲜前期会话书《老乞大》的清本《老乞大新释》《重刊老乞大》作正体“国”,元明本《原本老乞大》和《老乞大谚解》却作“”;该字形也见于《长谷寺药师如来坐像腹藏发愿文》(1346)、《古文书集成·碑铭1-13》(1725)、《古文书集成·教文1-1》(1765)和《古文书集成·陈情·请愿8-1》(1923)等朝鲜时代的汉文文献。③同上,第250 页。
1.新造六书俗字
抄本中有些俗字继承了正体字的意义和用法,却改变了字体的结构方式。如六堂本《骑着匹》和藏书阁本《骑着一匹》“夢[梦]”原本作“㒱”,形声字“夢[梦]”的示音构件“瞢”被记号构件“入”所代替,作会意字“㒱”。朝鲜文献《九云梦》中“夢[梦]”也作“㒱”,“暮”作“㒲”;《漂海录》中“幕”作“ ”①何华珍:《俗字在域外的传播研究》,第176 页。;《韩国俗字谱》也收有“慕”之俗体“ ”字。②金荣华:《韩国俗字谱》,汉城:亚细亚文化社,1986 年,第77 页。《老乞大》诸版本无该字例,后期会话书既有形声字“梦”,也有新造会意字“㒱”。
2.新造记号俗字
有些俗字构件变异为符号,突破了原正体字的构造理据。如大部分抄本中“盡[尽]”的示音构件为“㶳”,其基础构件“灬”简省为一横画,作“”,而六堂本《中华正音》“盡[尽]”原作“”,其表意构件仍保留了表示器物的形旁“皿”,示音构件为现行通用汉字“尽”的记号构件“尺”。朝鲜时代文献《古文书集成·上言3-1》(1721)、《物名考·物谱序》(1802)、《古文书集成·记3-1》(1848)、《古文书集成·条约10-2》(1887)和《古文书集成·祝辞2-1》(1922)等均作“”。⑤同上,第156 页。《老乞大》诸版本有“”“盡[尽]”两个字形,而这批会话书抄本则使用了更简省的“”“”,其中“”是“盡[尽]”在会话书抄本中的新造记号俗字。
3.新增音义俗字
有些俗字虽继承了正体字的形体,却改变了原字的音义和用法。如《华音撮要》“罷”原本作“罣”,《集韵·去声·霁韵》:“罣,也。”⑦(宋)丁度等:《集韵(述古堂影宋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第509 页。表悬挂义,《玉篇·网部》:“挂,挂碍也。”⑧(南朝梁)顾野王:《大广益会玉篇》,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第299 页。也表内心的牵绊和阻碍。在会话书抄本中,“罣”同“罷”,仅表示句末语气。“罣”在结构上以意符“圭”换用了意符“能”,且义项增补为表语气“罷”(罢)的俗字。
四、结 语
19 世纪中晚期流行于朝鲜半岛的《骑着一匹》《中华正音》等汉语会话类教科书,是一批反映中朝边境贸易往来的民间手抄本文献。会话书抄本用字猥杂,俗体丛生,既有通行于现代汉字的简化字、由假借同音或近音的记音字、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异体俗字,还有朝鲜民间自创的汉文变异字。其丰富多样的用字形态,不仅真实体现了朝鲜民间的书写习惯,也是研究汉字在朝鲜半岛传承与变异的珍贵宝库。
本文在自建俗字语料库的基础上,以传统“六书”与汉字构形学为理论指导,全面考察了这批会话书抄本的俗字与正体字的形体变异面貌。我们发现,这批民间会话书抄本中的大量俗字,主要承袭了中国历代典籍和字书等文献中的字形,与中国本土文献的汉字字形相近。同时也在汉字原有的轮廓基础上,在笔画、构件和整字三个层级上发生了一些形体变异。其中,笔画与构件的类别、置向、位置、结合方式、组合关系等的改变,是抄本俗字变异的重要特征。通过笔画和构件的简省、同化、异化、改换和符号化等方式而变异的俗字,的确减轻了朝鲜学习者对汉字的认读负担,却或多或少地改变了汉字原有的表意或示音功能,影响了构字理据和形义联系。另外,以增繁或位移等变异方式形成的俗字,多有字形的冗赘或一字多形现象,反而给识读和理据识别带来了负面影响,凸显了域外汉语学习者对汉字书写和辨认的矛盾。
会话书抄本俗字灵活而多样的形体变异方式,体现了朝鲜王朝后期民间私人对汉字书写的调整和取舍。会话书抄本在承继汉字传统符号系统时,笔画和构件的简化是最基础、最直接的形体变异表现形式,构件形体的类推性,是维持会话书抄本文字系统的有效手段。在简化与类推的共同作用下,会话书抄本俗字不断调整和变异汉字形体的局部要素,新造了六书俗字、记号俗字和新音义俗字。朝鲜编写者在追求汉字的易写和有效认读的过程中,努力保持抄本俗字系统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始终处于平衡与和谐的状态。然而,朝鲜半岛汉语会话书的俗字无论如何变异,都基本没有摆脱中国汉字字形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