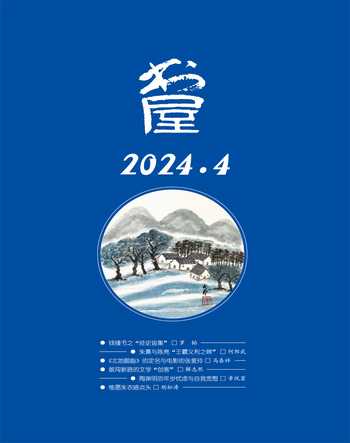陶渊明的年岁忧虑与自我宽慰
章悦茗
《游斜川》(并序)是陶渊明隐居时期的作品。
斜川之游是一次与邻人同行的山水游宴。南朝宋永初二年(421)正月五日,年约五十七岁的陶渊明有感于年岁流逝,人生过半,忧虑之情难以排解。于是,他趁着初春的美丽光景,当即邀请二三邻人同去斜川游览。在斜川,他们傍水闲坐,近观夕阳下游曳的鲂鲤鳞片闪闪,静听和风里翻飞的水鸥鸣声阵阵;远望清丽的曾城山独秀中皋,别有风姿。在仙境般的大自然里,心中感慨顿增,“欣对不足,率尔赋诗”。乡里邻人饮酒作诗,于酒酣之时更是放下一切俗世忧伤,畅聊家乡、生平。这些上了年纪的人们有着各自不同的人生经历,但他们都很珍惜这难得畅意的当下。全诗在“且极今朝乐”的高亢情绪中升华,最后想必是“家家扶得醉人归”。
在陶渊明所处的晋宋时代,佛、道思想盛行。佛教鼓吹形尽神不灭的因果报应说,道教则追求成神成仙、长生不老。佛、道信徒通过相信生命的可延续性,缓解年岁短促的焦虑;通过积攒功德或是修仙炼丹,来追求生命意义的延续。然而,陶渊明对于人生更多的是持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他认为天地合而万物生,生死皆为自然之常态,而非人格神作为主宰,更没有所谓的前世今生。“咨大块之受气,何斯人之独灵!禀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垂名”“茫茫大块,悠悠高旻,是生万物,余得为人”。在写给儿子们的《与子俨等疏》中,陶渊明开头便道:“天地赋命,生必有死,自古贤圣,谁能独免?”因而,在陶渊明的观念里,生死也是偶然的、荒诞的,是外在的,它们为人类构建出一种被限制的处境,年岁忧虑因之而生。
陶渊明在《形赠影》诗中区分出三种生命体的长短。“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天地山川永恒存在;“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草木顺应自然“常理”,随时序而荣枯;“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最智慧的人类却不公平地有着最短暂的生命,“彭祖寿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这种观点虽然不免粗糙朴素,但揭示了陶渊明对生命的理解方式——既然自然规律如此,那么“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观其一生,他的确做到了“委运”;但是,缺少佛、道那样自我疏导、麻痹的途径,对人生的眷恋与“甚念”,常常以年岁忧虑的形式流露出来。
陶渊明身处这样一个时代,想必内心也会被生命短促所压迫,有感于“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尤其当他追忆过去,“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曾经血气方刚的少年,如今“开岁倏五十”了,依然过着贫病交加的生活,“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早已成为空言。自身抱负没有实现,儿子们各个也“总不好纸笔”。虽然这是陶渊明顺应本心的选择,但如果他以早年受过的儒家教育稍加自我审视,他的前半生在功利意义上可谓一事无成;若再联想到人生苦短,就更令人忧虑悲伤了!这种“知天命”之年的焦虑同样也是一种普遍现象,根据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石崇在元康六年(296)金谷集会时是四十八岁,王羲之在永和九年(353)兰亭集会时是五十一岁。《金谷诗序》中的“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兰亭集序》中的“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都是他们面对恒常自然界生发出的生命之叹。前半生人生意义的迷惘,后半生春秋有限的悲伤,共同构成了处于这一人生节点的人们对生命自然的特殊感知。
作为隐士的陶渊明,在初隐阶段常常是独来独往,诗歌中也充斥着“孤云”“孤鸟”等意象。而当他从柴桑里移居南村后,与当地村社的人们交往频繁起来。南村居民因为“素心”被陶渊明欣赏,“邻曲时时来”“过门更相呼”逐渐成为新的生活方式,“登高赋新诗”也是一项常见活动。南村一带或许居住着许多外来人,所以同游斜川的雖是邻居,还需要“各疏年纪乡里”。正如“浔阳三隐”中的周续之来自雁门,刘遗民来自彭城,南村可谓一个下层文人士子聚居地。身处其中的陶渊明虽然隐居,但内心并不封闭,而是融入社群之中,甚至对仕、隐身份之别都淡化处置。正如他在《感士不遇赋》中所言,“或击壤以自欢,或大济于苍生。靡潜跃之非分,常傲然以称情”,仕隐皆出于各自本心,并非阻挡人与人的障碍,他与颜延之的友情就是明证。
饮酒是陶渊明的一大嗜好,酒在不同情境下的作用也不尽相同。斜川之游的饮酒,一是极尽游乐,以求获得更好的游宴体验;一是借酒消愁,以求短暂逃离当下。清醒时的陶渊明即便再随性,也要受到日常生活的诸多限制,其内在世界也被约束在外在的“壳”中。只有酒到“中觞”,“一切近俗之怀,杳然丧矣”,此刻内在精神才能以磅礴之势冲破而出,使主体达到形神相融、浑然一体的境界。
像许多魏晋士人一样,陶渊明热爱自然山水;但不同于将自然视作观照对象的人们,陶渊明做到了融入自然,物我合一,“在中国文化史上,他是第一位心境与物境冥一的人”。他在自然中开阔心胸,也从山水田园里汲取智慧。既然人类随自然规律而生灭,那么当渺小的人类回归自然,将个体生命进程融入更广大的宇宙循环中,人生短暂的忧虑便从更高层面得以疏解。
斜川的景色美不胜收,“曾丘”便是多次出现的一个重要物象。根据袁行霈先生的考证,陶渊明一行游观的曾城山,与传说中昆仑山最高峰“增城”同名。《天问》中有“昆仑悬圃,其凥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几里?”,《淮南子·地形训》中有“昆仑中有增城九重”的相关记载,因而陶渊明会说“遥想灵山,有爱嘉名”。然而,现实中的曾城山却没有九重之高耸。逯钦立先生认为曾城山可能是鄣山,也就是“庐山之一隅”。联系陶渊明在《游斜川》序中所言“彼南阜者,名实旧矣,不复乃为嗟叹”,曾城山很可能是庐山旁一座不起眼的小山峰。
这样一座小山却牵动了陶渊明的思绪。他对曾城山的描述是:“若夫曾城,傍无依接,独秀中皋”“虽微九重秀,顾瞻无匹俦”,它虽然远没有传说中的仙山高耸,也不如“名实旧矣”的庐山被人频繁称赞,但它不依傍别的山峰,在平地中挺拔而起,风姿俊秀。对着曾城山,陶渊明是“欣对不足,率尔赋诗”,是“缅然”凝视,长久思考。
附:
《游斜川》(并序)
辛丑正月五日,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临长流,望曾城,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彼南阜者,名实旧矣,不复乃为嗟叹。若夫曾城,傍无依接,独秀中皋,遥想灵山,有爱嘉名。欣对不足,率尔赋诗。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
开岁倏五十,吾生行归休。
念之动中怀,及辰为兹游。
气和天惟澄,班坐依远流。
弱湍驰文鲂,闲谷矫鸣鸥。
迥泽散游目,缅然睇曾丘。
虽微九重秀,顾瞻无匹俦。
提壶接宾侣,引满更献酬。
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不?
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
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