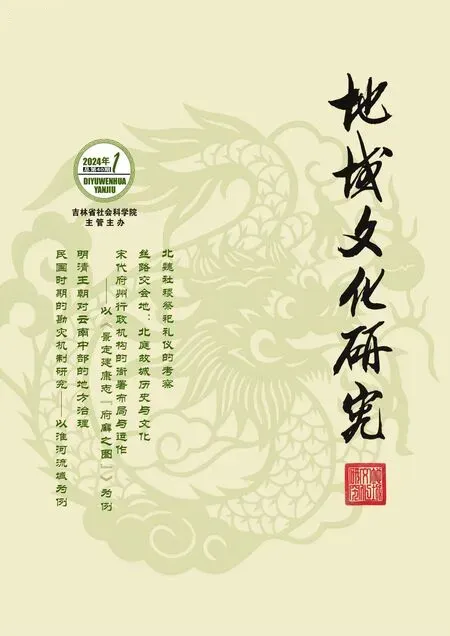北魏社稷祭祀礼仪的考察
张鹤泉
北魏的社稷祭祀是王朝重要的礼仪,因而,王朝对社稷的设置和祭祀仪式的举行都有明确的规定。因为北魏社稷祭祀礼仪的实行受到晋制的影响,所以,这一礼仪是仿照传统汉族礼仪制定的。而且,北魏王朝还将这一礼仪作为王朝政治统治的象征,因此,阐释北魏社稷礼仪的实行情况,有益于认识拓跋鲜卑人所建王朝统治的特点。然而,由于相关史料的缺乏,限制了对北魏社稷祭祀礼仪问题的考察,因而,相关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北魏社稷的设置、社稷祭祀礼仪的规定及社稷祭祀礼仪与皇帝统治的关系等诸多问题做一些探讨,进而透视北魏社稷祭祀所具有的中原汉族王朝礼仪。
一、社稷的设置
北魏社稷祭祀是重要礼仪。可以说,社稷祭祀在北魏建朝不久就开始实行。天兴元年(398),道武帝“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①魏收:《魏书》卷2《道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3页。也就是说,道武帝定都平城后,为实行社稷祭祀礼仪而设置了社稷坛。《魏书·礼志一》:“天兴元年,定都平城,即皇帝位,……冬十月,平文、昭成、献明庙成。岁五祭,用二至、二分、腊,牲用太牢,常遣宗正兼太尉率祀官侍祀。置太社、太稷、帝社于宗庙之右,为方坛四陛。”由这一记载可以看出:道武帝是将王朝的宗庙与社稷并置,并将社稷置于宗庙之右。而且,所设社稷坛分为社坛和稷坛。可是,社坛不只有一坛,而是有太社、帝社两坛;稷坛则只有太稷坛。
道武帝将社稷坛设于宗庙之右的做法,应该是有渊源的。《礼记·祭义》:“建国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庙。”《周礼·冬官·小宗伯》:“小宗伯之职,掌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据礼书的记载,显然,自周代以来,就将社稷的设置纳入礼制的规定中,确定了“右社稷,左宗庙”的模式。由此可见,道武帝在平城设置社稷,正是仿照中原汉族王朝的传统做法。
道武帝在平城设置太社、帝社和太稷,则是受到晋代礼制规定的影响。《晋书·礼志上》:“前汉但置官社而无官稷,王莽置官稷,后复省。故汉至魏,但太社有稷祠,而官社无稷,故常二社一稷也。……至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立二社一稷。”可见,两晋王朝是将王朝社稷的设置分为太社、官(帝)社和太稷。并且,只使太社与太稷相结合,而帝社则与太稷没有联系。晋代的这种设置社稷的规定,被视为“二社一稷”模式。
应该说,将王朝设置的社分为二社,是源自儒家的传统理念。正如《礼记·祭统》:“王为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而成书于东汉的《白虎通义》对礼书中规定太社和王社区分的意义做了阐释。其中《社稷篇》称:“王者、诸侯俱两社何?俱有土之君,《礼记·三正记》曰:‘王者二社,为天下立礼曰太社,自为立社曰王社,……太社为天下报功,王社为京师报功,太社尊于王社。’”依据汉儒的看法,设立太社是为天下报功;设立王社则是为京师报功。而且,太社要尊于王社。可见《白虎通义》是以今文经的看法阐述周制。这些对设置太社、王社意义的阐释只是儒家学派的意见,然而这种看法却对晋代设置社稷有很大的影响。西晋人傅咸上表称:“《祭法》:王社、太社,各有其义。天子尊事宗庙,故冕而躬耕。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亲耕故自报,自为立社者,为籍田而报者也。国以人为本,人以谷为命,故又为百姓立社而祈报焉。事异报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②房玄龄等:《晋书》卷19《礼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91页。傅咸的意见成为西晋王朝设置太社、帝社的依据。傅咸的观念明显吸收了《白虎通义》阐释的设立两社的意义。
不过,傅咸还阐释了设置太稷的依据。他认为:“人以谷为命,故又为百姓立社而祈报焉”。③房玄龄等:《晋书》卷19《礼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91页。而太社正是为天下所立社,也就是为民所立社,因而,也就具有为天下祈谷的目的,所以,就需要使太社与太稷相结合。因此,可以说晋代王朝设置“二社一稷”,正是受到汉代儒家观念的影响,也就是采取了汉儒所阐发的周代古制的规定。
道武帝定都平城采取“二社一稷”的设置,实际采取了他任用的汉族官员对社稷的认识观念。《魏书·道武帝纪》:天兴元年,道武帝使“仪曹郎中董谧撰郊庙、社稷、朝觐、飨宴之仪。”可见,北魏初年,王朝礼仪的制定,都是由汉官董谧主持完成的。而在平城设置“二社一稷”,应该是董谧以晋代的社稷设置为依据而实行的。很明显,道武帝在平城设置太社、帝社、太稷,实行“二社一稷”模式,应该是以晋制为基础,并加以仿照而成的。
自道武帝开始,至献文帝时,北魏王朝一直保持“二社一稷”的设置。但是,太和十五年(491),孝文帝在建成明堂、太庙之后,“十有二月壬辰,迁社于内城之西。”①魏收:《魏书》卷7下《孝文帝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8页。尽管孝文帝在平城改动了社坛的设置,但这种变动,只是社坛位置的迁移,并没有改变道武帝“二社一稷”的设置模式。
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使“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②魏收:《魏书》卷7下《孝文帝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8页。由于孝文帝迁都洛阳,所以,就要在新都重新设置社稷。《魏书·孝文帝纪下》:“(太和二十三年)诏前将军元英讨之。乙酉,车驾发邺。戊戌,至自邺。庚子,告于庙社。”《洛阳伽蓝记·城北》:“京师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户十万九千余。庙社宫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为一里,里开四门;门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门士八人,合有二百二十里。”这两条记载中提到的“庙社”,应该是在洛阳设置的宗庙与社稷的省称。这说明,孝文帝在新都洛阳继续采取宗庙与社稷并置的做法。
从孝文帝在洛阳设置的社稷来看,应该是以道武帝确定的“二社一稷”为基础的。《魏书·释老志》:“肃宗熙平中,于城内太社西,起永宁寺。”《洛阳伽蓝记·城南》:“御道西有右卫府,府南有太尉府,府南有将作曹,曹南有九级府,府南有太社,社南有凌阴里,即四朝时藏冰处也。”这两条记载说明,在洛阳城中,有太社的设置。既然在洛阳有太社的设置,自然应该有帝社的设置。《魏书·刘芳传》:“(刘)芳以社稷无树。……今者植松,不虑失礼。惟稷无成证,乃社之细,盖亦不离松也。”据刘芳所言,在洛阳城中,应该设有稷坛,所以才会提及为稷坛植树的问题。这些情况透露出孝文帝在新都洛阳设置社稷,仍然延续“二社一稷”的模式。《隋书·礼仪志二》:“后齐立太社、帝社、太稷三坛于国方。每仲春秋月之元辰及腊,各以一太牢祭焉。”很显然,北齐王朝实行的是“二社一稷”的设置。然而,北齐的制度大多数是延续孝文帝改革后的规定,因此,北齐实行的社稷设置,应该与孝文帝的做法有承袭关系,所以,也就是从北魏在洛阳以“二社一稷”为模式的设置延续而来的。
北魏在洛阳设置的社稷坛,有更完善的构建。景明三年(502),宣武帝诏提到:“今庙社乃建,宫极斯崇,便当以来月中旬,蠲吉徙御。”③魏收:《魏书》卷8《宣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5页。诏书中提到的“宫”,当为社宫。显然,洛阳社宫的建筑十分壮观。而且,太常卿刘芳上疏建议:设社稷“宜植以松。……今者植松,不虑失礼。”④魏收:《魏书》卷55《刘芳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226页。刘芳的建议为宣武帝采纳,又在洛阳社稷坛外种植了社树。可以说为社稷坛植树,是遵循汉族传统的礼仪规定。《周礼·地官·大司徒》:“设其社稷之壝而树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与其野。”正表明为社稷植树的意义。然而,社树还是对社稷神祇信仰的展示。正如《白虎通义·社稷篇》称:“社稷所以有树何?尊而识之,使民人望见师敬之,又所以表功也。”因此,在宣武帝时,王朝依据汉儒的阐释而种植了社树,从而使社稷的设置更为完善,并展现出神秘的色彩。
孝文帝还使社稷设置与王朝的封爵制度结合在一起。太和十六年(492),孝文帝进行爵位改革,采取虚封爵与实封爵并行的做法。北魏的实封爵包括王爵、开国郡公、县侯、县伯、县子、县男等级。这些受封实封爵者有他们的封地。这些封地,或为行政郡,或为行政县。治理封地的官员与行政郡、县的官称不同。治理王国者被称为内史;治理开国爵封地者被称为相。例如,李肃“出为章武内史。”①魏收:《魏书》卷36《李顺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44页。房伯祖“为从事中郎、平原相。”②魏收:《魏书》卷43《房法寿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71页。然而,受封实封爵的封地,只是他们的食邑所在地,因而,也就是划定收取租赋的行政区域。例如,奚绪“开建五等,封弘农郡开国侯,食邑三百户。”③魏收:《魏书》卷29《奚斤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01页。邓羡“以义阳军司之勋,封安阳县开国子,邑三百户。”④魏收:《魏书》卷24《邓渊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37页。因此《魏书·地形志上》称:“魏自明、庄,寇难纷纠,攻伐既广,启土逾众,王公锡社,一地累封,不可备举,故总以为郡。”也就是说,北魏封授实封爵,实际是一种特殊的分封制。正因如此,北魏王朝将封授实封爵与社稷的设置相结合。《魏书·源贺传》载源怀上表称:“至(太和)二十一年,车驾幸雍,臣复陈闻,时蒙敕旨,征还当授。自宫车晏驾,遂尔不白。窃惟先臣远则援立高宗,宝历不坠;近则陈力显祖,神器有归。如斯之勋,超世之事。丽以父功而获河山之赏,臣有家勋,不沾茅社之赐。得否相悬,请垂裁处。”《元袭墓志》:“(元袭)恭宗景穆皇帝之曾孙,京兆康王之孙,洛州刺史武公之子。……匪唯泽洽一邦,固亦润兼京邑。以茂绩克宣,勋庸有著,遂割裂山河,开建茅社。”⑤《元熙墓志》,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96页。由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北魏王朝使受封实封爵者,都要在他们的封地上设置社稷。《隋书·礼仪志四》载北齐册封:“诸王、五等开国及乡男恭拜,以其封国所在方,取社坛方面土,包以白茅,内青箱中。函方五寸,以青涂饰,封授之,以为社。”北齐使受封实封爵者在封地设置社稷的做法,应该是沿袭孝文帝爵制改革后的规定。因此,可以明确,北魏在受封爵者的封地上,都要“以其封国所在方,取社坛方面土”。所谓方面土,也就是五色土。这种以五色土为受封者设置社稷的做法,在周代已经实行。《逸周书·作雒》:“封人社壝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国中,其壝东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骊土,中央衅以黄土,将建诸侯,凿取其方一面之土,焘以黄土,苴以白茅。”《周礼·地官·封人》:“封人,掌诏王之社壝,为畿封而树之。……凡封国,设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贾公彦疏引孔注云:“王者封五色土为社,建诸侯则各割其方色土与之,使立社。焘以黄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洁,黄取王者覆四方。是封乎诸侯立社稷之法也。”很显然,儒家观念中的这种分封制度,是五行说盛行后才出现的,所以,才确定要依据受封诸侯的方位决定获得社土的颜色。也就是“天子有太社焉,东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⑥班固:《白虎通德论(汉魏丛书本)》卷之上《社稷篇》,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54页。可见,以天子社稷的“方面土”作为受封者的社稷设置,不过是将五行观念与分封结合起来,以此象征受封爵者的社稷不过是天子社稷的分支,进而体现受封者与皇帝所具有隶属关系。很明显,北魏王朝使受封实封爵者在封地设置社稷,实际承袭了中原汉族王朝的传统做法,并以这种做法体现出受封实封爵者与皇帝之间建立了牢固的臣从关系。
综上而言,天兴元年(398),道武帝就在首都平城设置社稷,并仿照晋制设置了太社、帝社、太稷。也就是采取了“二社一稷”的设置模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依然按照“二社一稷”模式设置新社稷,并使社宫的构建更为壮观,并且还依据传统礼制规定种植社树,因而更增加了社稷的神秘色彩。而且孝文帝又将社稷的设置与实封爵的封授相结合,使受封实封爵者以王朝社稷的“方面土”在封地设置社稷,进而体现受封者与皇帝的臣从关系。因此,可以说北魏王朝社稷是仿照中原汉族王朝的礼仪设置的,并使其成为拓跋鲜卑皇帝实行统治的一种象征。
二、社稷祭祀礼仪的规定
道武帝在王朝社稷设置上,实行了“二社一稷”的做法,并且,还确定了社稷祭祀礼仪。如前所述,道武帝实行的社稷祭祀,实际是由仪曹郎中董谧“撰朝觐飨宴郊庙社稷之仪。”①魏收:《魏书》卷24《崔玄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34页。而董谧是精通传统礼学的汉族士人,所以,道武帝确定的社稷祭祀,实际仿照了中原汉族王朝的礼仪。关于道武帝实行的社稷祭祀礼仪,在《魏书·礼志一》有明确记载。其中提到:“(天兴元年)冬十月,平文、昭成、献明庙成。岁五祭,用二至、二分、腊,牲用太牢,常遣宗正兼太尉率祀官侍祀。置太社、太稷、帝社于宗庙之右,为方坛四陛。祀以二月、八月,用戊,皆太牢。句龙配社,周弃配稷,皆有司侍祀。”依据这一记载,可以明确,天兴元年(398),道武帝实行的社稷祭祀礼仪包括对祭祀神祇、日期、用牲及祭祀的主祭者的规定。这些规定,应该是北魏社稷祭祀礼仪的主要内容。
(一)社稷祭祀确定的神祇规定
北魏王朝社稷祭祀的神祇,是以社神、稷神为主神,为社神、稷神设“方坛四陛”,而且,社稷祭祀的神祇,除了要祭祀主神之外,还规定了配祭神,即以“句龙配社,周弃配稷”。这种以句龙、周弃配祭社稷的做法有其渊源。《晋书·天文志上》:“弧南六星为天社,查共工氏之子句龙,能平水土,故祀以配社,其精为星。”可见,晋代是以句龙为社的配祭神。既然以句龙配社神,也就要以周弃配稷神。因为在汉族传统的神祇观念中,句龙和周弃是不分离的。《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左传》所记这一传说,正透露了句龙与周弃并存,社神、稷神配祭神的情况。句龙与周弃作为社神、稷神配祭神的传说,后为礼书吸纳。《宋书·礼志四》:“《礼》云:‘共工氏之霸九州,其子句龙曰后土,能平九土,故土以为社。’”显然,由于礼书记载了这一传说,所以,对晋代的神祇观念产生很大影响。应该说,这种神祇观念,实际决定了晋代规定社稷祭祀还要供奉配祭神祇。由此可以明确,北魏祭祀社稷以句龙和周弃为配祭神的做法,显然是承袭了晋代社稷祭祀礼仪中的神祇规定,因而,也就是以汉族传统神祇的传说作为确定神祇的依据。
(二)祭祀社稷礼仪有明确的时间规定
天兴元年(398),道武帝确定“以二月、八月”,②魏收:《魏书》卷108之一《礼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735页。为祭祀社稷的日期。《宋书·礼志一》载晋制:“祠大社、帝、太稷,常以岁二月、八月二社日祠之。”很显然,晋代社稷祭祀日期为二月、八月。也就是说,北魏祭祀社稷的日期参照了晋代的礼俗,与晋代的规定是相同的。
从北魏举行社稷祭祀仪式的时间来看,也有确定的依据。《通典·礼五》:“北齐立太社、帝社、太稷三坛于国右。每仲春仲秋元辰及腊,各以一太牢祭焉。”北齐祭祀社稷日期,应该是延续北魏孝文帝改革后的做法。据此可见,北魏祭祀社稷的时间,应该是选择仲春、仲秋的元辰日举行。汉儒阐释其中意义。“岁再祭何?春求谷之义也。故《月令》,‘仲春之月,择元日命人社。’《援神契》曰:‘仲春获禾,报社祭稷。’”仲秋祭社稷,与仲春相同,也具有“报社”的意义。
不过,选择元辰日祭祀社稷,却有更深意的规定。顾炎武考证,“《月令》:‘择元日,命民社。’注:‘祀社日用甲。’据《郊特性》文,日用甲,用日之始也。”①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影印本)》卷6“社日用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据顾炎武所说,礼书确定祭祀社稷,应该在用甲之日,是以天干定日。然而,祭祀社稷,汉用午,魏用未,晋用酉,各因其行运。②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影印本)》卷6“社日用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即以地支定日。可是,北魏祭社之日,则确定“用戊”,③魏收:《魏书》卷108之一《礼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735页。即以天干确定元辰。这不同于晋制“用酉”,即以地支确定祭日。所出现的变化与北魏以土德为统治象征相关。《魏书·道武帝纪》:“(天兴元年),尚书崔玄伯等奏从土德,服色尚黄,数用五,未祖辰腊,牺牲用白,五郊立气,宣赞时令,敬授民时,行夏之正。”在金、木、水、火、土五行中,戊与土结合。也就是祭祀社稷用戊日,正是要与北魏的土德相配。由此可见,北魏祭社稷的用日,并没有选择晋制,而是采用了《礼记·郊特牲》中的天干定日的做法。很显然,北魏祭祀社稷“用戊”定日,是为了将戊日与北魏的土德相结合,所以,摒弃晋制以地支定日的规定,而采取《礼记》中以天干定日的做法。然而,太和十五年(491),孝文帝将北魏的土德改为水德,表明北魏对晋代的承袭。这种改变也就要使以天干定日改为晋代的以地支定日,也就是说,孝文帝改革后,王朝社稷祭祀定日又延续了晋制的规定。
(三)祭祀社稷礼仪的用牲规定
天兴元年(398),道武帝确定祭祀社稷“皆太牢”。④魏收:《魏书》卷108之一《礼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735页。道武帝采取以太牢祭祀社稷的规定,是仿照传统汉族中原王朝的礼仪规定。《礼记·郊特牲》:“郊特牲而社稷大牢。”《礼记·王制》:“天子社稷皆大牢。”可见,按礼书的阐释,祭祀社稷用牲,只有以太牢祭祀,才能够突显天子的至尊地位。正因如此,道武帝确定的这种用牲规定,一直为后世皇帝所遵守。延兴元年(471),孝文帝为减少节省祭祀所用牲畜,“其命有司,非郊天地、宗庙、社稷之祀,皆无用牲。”⑤魏收:《魏书》卷108之一《礼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740页。显然,北魏祭祀社稷与郊祀、宗庙之祭一样,没有废除用牲的规定。直到北齐时期,祭祀社稷“每仲春秋月之元辰及腊,各以一太牢祭焉。”⑥魏征等:《隋书》卷7《礼仪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42页。汉儒对皇帝用太牢祭社稷做了阐释。《白虎通义·社稷篇》称:“以三牲何?重功故也。《尚书》曰:‘乃社于新邑,羊一、牛一、豕一。’《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大牢,诸侯社稷皆少牢。’”也就是说,祭祀社稷用牲规定与显示皇帝的最高地位具有一致性。
北魏祭祀社稷所用牲畜与其他祭祀一样,都要由廪牺令掌管。祭祀社稷仪式开始时,“廪牺令掌牲,陈于坛前。”①魏收:《魏书》卷108之一《礼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736页。而且廪牺令还要“掌养牺牲,供祭群祀等事。”②魏征等:《隋书》卷27《百官志中》,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755页。北魏王朝的廪牺令,先为专门设置的职官。前《职员令》规定,廪牺令,为从五品下,③魏收:《魏书》卷113《官氏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986页。可为明证。但太和二十三年(499)制定的后《职员令》已经不见有廪牺令的设置,《隋书·百官志中》载北齐太常属官有廪牺令,说明这一职官已经纳入太常属官之列。
(四)祭祀社稷礼仪的乐舞规定
天兴元年(398),道武帝“诏尚书吏部郎中邓渊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吕,协音乐”。从北魏郊祀天、地的礼仪来看,“冬至祭天于南郊圆丘,乐用《皇矣》,奏《云和》之舞,事讫,奏《维皇》,将燎;夏至祭地祇于北郊方泽,乐用《天祚》,奏《大武》之舞。”④魏收:《魏书》卷109《乐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827页。据此可见,北魏王朝祭祀天、地都有专门的乐舞。
《魏书·乐志》:“初,高祖讨淮、汉,世宗定寿春,收其声伎。江左所传中原旧曲,《明君》《圣主》《公莫》《白鸠》之属,及江南吴歌、荆楚四声,总谓《清商》。至于殿庭飨宴,兼奏之。其圆丘、方泽、上辛、地祇、五郊、四时拜庙、三元、冬至、社稷、马射、籍四、乐人之数,各有差等焉。”《魏书·乐志》:“永熙二年春,稚、莹表曰:……案今后宫飨会及五郊之祭,皆用两悬之乐,详揽先诰,大为纰缪。……令六悬既成,臣等思钟磬各四,釽鐏相从,十六格宫悬已足,今请更营二悬,通前为八,宫悬而具矣。一具备于太极,一具列于显阳。若圆丘、方泽、上辛、四时五郊、社稷诸祀,虽时日相六,用之无阙。”由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在社稷祭祀礼仪中的乐舞是与王朝祭礼规定的诸种祭祀一并共用的,并没有专门的乐舞,此举应该是受到晋代礼仪的影响。《晋书·乐志上》:“泰始二年,诏郊祀明堂礼乐权用魏仪,遵周室肇称殷礼之义,但改乐章而已”。这里提到西晋专门为郊祀、明堂祭祀规定了用乐。而且,还由散骑常侍傅玄编订歌词。这些用于祭祀的乐歌有:《祠天地五郊夕牲歌》《天地郊明堂夕牲歌》《天郊飨神歌》《地郊飨神歌》《明堂飨神歌》《祠庙夕牲歌》《祠庙迎送神歌》。⑤房玄龄等:《晋书》卷22《乐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80-682页。也就是郊祀天地、明堂祭祀、宗庙祭祀都要有专门的乐歌。可是,却没有为社稷祭祀编订专门的乐歌。《宋书·礼志一》:“祠大社、帝、太稷,常以岁二月、八月二社日祠之。太祝令夕牲进孰,如郊庙仪。”这表明,西晋王朝规定祭祀“二社一稷”采用了郊庙礼仪。由此来看,晋代祭祀“二社一稷”,应该采用郊祀乐舞。因此,可以明确,北魏不为社稷祭祀规定专门的乐舞,显然是仿效晋代对祭祀乐舞的规定。不过,与晋制不同的是,北魏社稷祭祀所用乐舞,不只在郊祀、宗庙之祭时使用,在举行五郊、三元、冬至、马射、籍田礼仪时也都采用。因此,北魏祭祀社稷所用乐舞,也就表现出独有的特点。
(五)祭祀社稷仪式的三献仪式
北魏祭祀社稷礼仪中的三献仪式,应该说承袭了晋代礼仪的做法。《晋书·礼志一》:“司空、太常、大司农三献也。官有其注。周礼王亲祭,汉以来有司行事。”可见,晋代祭祀社稷三献,是由司空、太常、大司农完成的,而皇帝并不亲祭,所以被称为“有司行事”。道武帝制定的祭祀社稷三献仪式,仿照晋制规定,“皆有司侍祀”。①魏收:《魏书》卷108之一《礼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735页。可见皇帝不亲祭的规定逐渐出现了变化。《隋书·礼仪志二》:“后齐立太社、帝社、太稷三坛于国方。每仲春秋月之元辰及腊,各以一太牢祭焉。皇帝亲祭,则司农卿省牲进熟,司空亚献,司农终献。”《隋书·礼仪志二》:“后周社稷,皇帝亲祀,则冢宰亚献,宗伯终献。”这些记载说明,在北齐、北周祭祀社稷的三献中,都由皇帝行首献。在北齐,为司空行亚献,司农行终献;在北周,则为冢宰行亚献,宗伯行终献。很显然,北齐、北周祭祀社稷的三献仪式,仿效了周天子亲祭社稷的做法,并实行由皇帝行首献的规定。《白虎通义·社稷篇》:“王者自亲祭社稷何?社者,土地之神也。土生万物,天下之所主也,尊重之,故自祭也。”可见,在汉儒看来,由天子亲祭社稷,正是掌控国土的象征,所以,出于加强皇权的需要,也就要采取皇帝亲祭的仪式。可以说,北齐、北周实行由皇帝亲祭社稷的做法,是延续了儒家的传统理念。但北齐、北周的做法,应该与北魏有联系。因为北魏孝文帝改革后,大力吸收儒家的观念,因而,也就需要在祭祀社稷仪式上有所体现。因此,北齐、北周实行由皇帝亲祭社稷的做法,应该与北魏后期社稷祭祀仪式的变化有承袭关系。
此外,北魏还实行告祭社稷的仪式。这些告祭都与王朝重要事务有关。例如国都的迁移。《魏书·献文六王上·广陵王羽传》:孝文帝迁都洛阳,便“诏(元)羽兼太尉,告于庙社。”②魏收:《魏书》卷21上《献文六王上·广陵王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46页。还有皇帝的亲征。太和二十三年(499),孝文帝“车驾发邺。戊戌,至自邺。庚子,告于庙社。”③魏收:《魏书》卷7下《孝文帝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4页。皇帝亲征的祭社,称为宜社。《隋书·礼仪志三》载北齐皇帝亲征“次宜于社,有司以毛血衅军鼓,载帝社石主于车,以俟行。”北齐的宜社,应该是从北魏延续而来的。然而,皇帝亲征宜社,却是仿照晋制。在晋代王朝规定,“礼有事告祖祢宜社之文”。④房玄龄等:《晋书》卷19《礼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86页。这种宜社,实际是因事祭社的一种传统仪式。《周礼·春官·大祝》:“大师,宜于社。”《礼记·王制》:“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这些记载都反映周代以来所行“宜社”的重要性。正因如此,也就成为北魏实行宜社仪式的依据。
由上述可见,道武帝任用董谧制定的祭祀社稷礼仪,大都参照了晋代的规定。可以说北魏是依据中原汉族王朝的规定,制定了祭祀社稷的礼仪,因而,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拓跋鲜卑皇帝对传统的汉族社稷祭祀礼仪的高度认同。
三、社稷祭祀礼仪与皇帝的统治
如前所述,天兴元年(398),道武帝于平城设置了“二社一稷”,并使仪曹郎董谥制定“郊庙、社稷之仪。”⑤魏收:《魏书》卷108之一《礼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817页。在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依然设置“二社一稷”,进一步完善了社稷祭祀礼仪。可以说北魏历朝皇帝都重视社稷祭祀礼仪的实行。《魏书·礼志四》载延兴三年(473)孝文帝诏令:“其命有司,非郊天地、宗庙、社稷之祀,皆无用牲。”这一诏令是北魏皇帝使社稷祭祀在王朝祭典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反映。也就是说,社稷祭祀与郊祀天地、宗庙祭祀一样,都是王朝不能缺少的礼仪活动。北魏王朝之所以重视社稷祭祀礼仪的实行,是因为这种祭祀不仅是对社神、稷神崇拜的礼仪活动,而且也是北魏皇帝实行政治统治的象征。
从北魏统治特点来看,在道武帝率拓跋鲜卑部入主中原后,实行了以皇帝为最高统治者的官僚制。《魏书·道武帝纪》:“(皇始元年)初建台省,置百官,封公侯、将军、刺史、太守。”使王朝的官僚机构初步建立起来。实际上,道武帝为了统治的需要,不仅设置了拓跋鲜卑职官,还仿照晋制,设置了汉官。因此,北魏王朝的官僚体系表现出“胡汉杂糅”的特点。而且,北魏担任职官者,不仅有拓跋鲜卑贵族,还有归顺的汉族士人。由于北魏采取鲜卑与汉人同组官僚机构的做法,也就需要使这些官员都要尊奉皇帝为最高统治者,并要凸显拓跋鲜卑皇帝的至尊地位。而要实现这种政治局面,不仅要采取政治控制的措施,还要通过王朝礼仪活动加以认同,因而,也就需要皇帝确定对王朝仪礼的选择。当然,祭祀礼仪的确定也就与皇帝的统治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正因如此,天兴元年(398),道武帝“定都平城,……立坛兆告祭天地。……二年正月,帝亲祀上帝于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①魏收:《魏书》卷108之一《礼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734页。也就是将他称代王时的“西向设祭,告天成礼”②魏收:《魏书》卷108之一《礼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734页。的拓跋鲜卑礼仪改为南郊祭天的汉族礼仪。同年十月,道武帝在平城建“平文、昭成、献明庙成。……置太社、太稷、帝社于宗庙之右,为方坛四陛。”③魏收:《魏书》卷108之一《礼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735页。道武帝的这些做法表明,他要以实行中原汉族王朝的郊祀、宗庙与社稷祭祀礼仪来显示他统治中原地区的合理性。应该说,道武帝在祭祀礼仪上的这种选择,表明他对汉族祭祀礼仪的认同。由于这种认同的理念,当然也就昭示实行这些祭祀所包含的政治意义。《礼记·礼运》:“故礼行于郊,而百神受职焉。礼行于社,而百货可极焉。礼行于祖庙,而孝慈服焉。”正道破郊祀与宗庙、社稷祭祀在维护天子统治上都起到重要的作用。并且,在儒家理念中,王朝最高统治者要“明乎郊社之义,尝禘之礼,治国其如指诸掌而已乎。”④《礼记正义·仲尼燕居》(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1613页。而且这些礼仪是要显示“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尝禘郊社,尊无二上”⑤《礼记正义·曾子问》(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388页。的意义。由此可见,道武帝实行郊祀天地、宗庙祭祀、社稷祭祀,不仅要表明他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具有合理性,而且要通过这些祭祀礼仪显示他作为拓跋鲜卑皇帝所具有的最高统治地位。由于道武帝将郊祀天地、祭祀宗庙、祭祀社稷礼仪作为皇帝最高统治的象征,所以,也就成为北魏后世皇帝必须奉行的旨意。
然而,就社稷祭祀礼仪的实行而言,其对凸显拓跋鲜卑皇帝的至尊地位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因为汉族中原王朝长期实行社稷祭祀,所以,也就将社稷祭祀的神祇作为王朝的代称。诸如《礼记·曲礼》:“国君去其国,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礼记·少仪》:“问国君之子长幼,长,则曰:能从社稷之事矣。”很显然,这种以社稷指代王朝,在汉族各阶层中,已经成为牢固的观念。可以说这种观念中的社稷,实际就是最高统治者所拥有的王朝。应该说,在拓跋鲜卑皇帝的统治下,汉族人依然保留对社稷的这种认识。例如,明元帝时,清河大族崔浩献策便称:“请陈瞽言。自圣化龙兴,不崇储贰,是以永兴之始,社稷几危。”⑥魏收:《魏书》卷35《崔浩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13页。孝文帝时,汉臣程骏上表称:“夫为社稷之计者,莫不先于守本。臣愚以为,不观兵江浒,振曜皇威,宜特加抚慰。”①魏收:《魏书》卷60《程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347页。这些事例说明,汉族官员视拓跋鲜卑皇帝的统治与汉族皇帝的统治一样,都能够以社稷作为王朝的象征。然而,对拓跋鲜卑人而言,随着社稷祭祀的实行,也就吸纳了社稷神祇代表王朝的理念,因而,在北魏皇帝的诏令中,多见以社稷指代王朝的事例。例如,《魏书·献文帝纪》载皇兴五年(471)诏:“今稽协灵运,考会群心,爰命储宫,践升大位。朕方优游恭己,栖心浩然,社稷刈安,克广其业,不亦善乎?”在拓跋鲜卑官员中,也都将王朝称为社稷。例如,鲜卑勋贵刘尼议政称:“今不能奉戴皇孙,以顺民望,社稷危矣。将欲如何?”②魏收:《魏书》卷30《刘尼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21页。而且,在拓跋鲜卑官员的奏章中,也常见这种事例。例如,元雍上表称:“皇居寝食,所在不知;社稷安危,又亦不预,出入柏堂,尸立而已。”③魏收:《魏书》卷21上《献文六王上·高阳王雍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55页。于忠上表也称:“自大明利见之始,百官总已之初,臣复得猥摄禁戒,缉宁内外,斯诚社稷之灵,兆民之福,臣何力之有焉。”④魏收:《魏书》卷31《于栗磾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45页。这说明,在拓跋鲜卑族群中,已经接受汉人的观念,也就是社稷是皇帝统治的国土。正因如此,北魏定期举行社稷祭祀礼仪,就为其统治覆盖上对社稷神祇崇拜的色彩,也就能够在礼仪活动的信仰上,强化拓跋鲜卑人和汉人对皇帝统治的认同意识,进而也就使社稷祭祀礼仪成为皇帝掌控全体臣民必须服从其统治的象征。
北魏通过社稷祭祀还能够体现王朝官员对皇帝的臣从意识。因为拓跋鲜卑和汉族官员都对社稷神祇有共同的信仰,因而,也就将其与服从皇帝号令的行动联系在一起。因此,在《魏书》《北史》中,多见“社稷之臣”的记载。例如,太武帝称古弼“可谓社稷之臣。”⑤魏收:《魏书》卷28《古弼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92页。但是,北魏皇帝将王朝官员视为“社稷之臣”,是有明确标准的。《魏书·景穆十二王中·任城王云传》载元澄向孝文帝进言:“社稷诚知陛下之社稷,然臣是社稷之臣子,豫参顾问,敢尽愚衷。”宣武帝召见于烈称:“卿父忠允贞固,社稷之臣。”⑥魏收:《魏书》卷31《于栗磾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64页。由这两条记载可以看出,北魏皇帝将一些官员看作“社稷之臣”,是对他们忠实服从皇帝意志的褒奖。而这种褒奖,则是与北魏皇帝已经被王朝官员视为“社稷主”⑦李百药:《北齐书》卷23《崔棱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333页。的观念相联系的。因此,北魏王朝以“社稷之臣”褒奖官员,正是要将他们对社稷信仰的理念转变为效忠于皇帝统治的行为。由此可见,北魏王朝实行社稷祭祀礼仪,应该对王朝官员尽忠皇帝的行为产生重大的影响。
北魏王朝社稷祭祀对从事生产活动的社会下层群体也产生重要的影响。实际上,北魏王朝实行社稷祭祀仪礼与拓跋鲜卑人的生产活动的转变有很大的关系。从早期拓跋鲜人的生产活动来看,是以游牧为主。然而,随着拓跋鲜卑人的南下,生产活动和社会组织也发生变化。登国初年,拓跋珪就开始采取“散诸部落”⑧魏收:《魏书》卷113《官氏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014页。的措施。所谓“散诸部落”,正如《魏书·外戚上·贺讷传》所言:“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也就是将拓跋鲜卑人流动的居住方式,改变为定居的方式,并且,将以“君长大人”为首的残存部落民编入王朝户籍,并由王朝直接控制。拓跋珪采取的这种措施,为拓跋鲜卑人由游牧生产转向农耕生产创造了条件。而在拓跋珪称帝后,不断向中原地区发展势力,在汉族人农耕生产活动的影响下,使拓跋鲜卑人的生产方式出现变化。《魏书·食货志》载,道武帝平定中山地区后,使拓跋鲜卑人与迁移的汉人都在平城京畿内“各给耕牛,计口授田”。并且,还在京畿“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劝课农耕,量校收入,以为殿最”。①魏收:《魏书》卷110《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850页。八部帅,也就八部大人,其主要职责是管理八部拓跋鲜卑人从事农耕生产。可见,在京畿内、外的大部分拓跋鲜卑人都要从事农耕活动。天兴三年(400),道武帝又“始耕籍田。”②魏收:《魏书》卷2《道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6页。并举行籍田礼“祭先农,用羊一。”③魏收:《魏书》卷108之一《礼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735页。这说明道武帝对拓跋鲜卑人从事农耕持积极鼓励的态度。这些情况表明拓跋鲜卑人的生产活动已经转变为以农耕为主业。对拓跋鲜卑人而言,这是一个飞跃。④陈连庆:《〈晋书·食货志〉校注〈魏书·食货志〉校注》,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4页。
中原汉族王朝的社稷祭祀与农耕活动密切相关。《周礼·春官·肆师》“社之日,莅卜来岁之稼。”《白虎通义·五祀篇》:“王者所以有社稷何?为天下求福报功。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广博,不可遍敬也;五谷众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谷之长,故封稷而祭之也。”都反映了这种情况。因此,拓跋鲜卑人转为以农耕为主业,也成为王朝实行社稷祭祀礼仪的基础。反之,社稷祭祀礼仪的实行,也成为北魏以发展农业为重要举措的象征,并且也促进拓跋鲜卑人与汉族人对农业神祇信仰的趋同。正因如此,北魏王朝实行的农业政策,也就使拓跋鲜卑人与汉族人的区分逐渐模糊。
从北魏王朝的户籍政策来看,在北魏前期,王朝除了将一些拓跋鲜卑人编制为特殊的兵户之外,凡是王朝能够控制的人口都有统一的户籍。《魏书·食货志》:“先是,天下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库,以供调外之费。至是,户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后增调外帛满二匹,所调各随其土所出。”可见,北魏王朝一直采取“九品混通”法征收赋税,赋税的征收以“户”为单位。凡是纳入王朝户籍编制的,无论是拓跋鲜卑人,还是汉族人,都成为王朝编户民,并未做区分。只是在北魏前期,一些拓跋鲜卑人还保留部落民的残迹;而汉族人则在宗主督护制下,实行大户制。然而,在孝文帝改革后,大部分拓跋鲜卑人与汉族人都向编户化方向发展。也就是北魏王朝摈弃了胡、汉分治的做法,而采取了胡、汉共治的措施。
从北魏王朝实行的土地政策来看,也没有将拓跋鲜卑人与汉族人明确区分。表现最明显的是,太和九年(485),孝文帝实行的均田制。孝文帝“下诏均给天下民田”。⑤魏收:《魏书》卷110《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853页。北魏实行均田制,明确将土地分为“露田”“桑田”,将受田民分为“男夫”“妇人”“奴婢”。还将特殊的受田者分为“诸民有新居者”、“诸远流配谪、无子孙及户绝者”、“诸宰民之官”。⑥魏收:《魏书》卷110《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854-2855页。很明显,孝文帝采取的均田制,只将受田者区分为不同的阶层,并没有以民族加以区别。可见,北魏均田制的土地分配,实际正是要使拓跋鲜卑人与汉人都能获得相同的权益。
由此可见,北魏王朝在赋税征收和土地分配上没有实行民族区分的做法。而北魏能够采取这种做法,自然是与拓跋鲜卑人转为以农耕为主业,并实现了与汉民族在生产活动趋于一致的演变特点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因为北魏王朝实行的社稷祭祀礼仪包含“为百姓立社而祈报焉”①房玄龄等:《晋书》卷19《礼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91页。的意义,所以,也就有益于北魏王朝发展农业的政策推行。从这一方面来看,北魏实行社稷祭祀礼,在促进汉人与拓跋鲜卑人在生产活动的逐渐交融上,起到了不能忽视的作用。
结 语
北魏在建立政权初期,就开始实行社稷祭祀礼仪,并使这一礼仪在王朝祭典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北魏王朝为了显示对社稷祭祀礼仪的重视,便在首都平城设置社稷。孝文帝迁都后,又在新都洛阳设置了社稷。可以说,北魏王朝仿照晋制,设置了太社、帝社和太稷,也就是采取了“二社一稷”模式。北魏王朝以这种模式设置社稷,表明中原汉族王朝的社稷设置对拓跋鲜卑的王朝礼仪有重大的影响。
北魏实行的社稷祭祀礼仪的规定,也参照了晋代的规定,因而,祭祀的神祇、日期、用牲、三献仪式都承袭了传统汉族礼仪规定,并没有太多的变动。所以,拓跋鲜卑统治者实行社稷祭祀礼仪,显示了他们对传统汉族祭祀礼仪的高度认同。
北魏实行社稷祭祀礼仪,还具有以这一礼仪作为其政治统治的象征作用。实际上,北魏将社稷祭祀与郊祀天地、宗庙祭祀一并置于重要的地位,正是要利用这一祭祀来显示皇帝统治的至高无上,并且作为被统治者臣从皇帝的表现。而且北魏社稷祭祀礼的实行,也是王朝推行有利于农业生产措施的体现。因为拓跋鲜卑人入主中原后,迅速向农耕生产转化,因而就使他们能够接受社稷神祇的信仰。以与汉人的这种共同信仰为基础,可以进行农耕活动,进而促进拓跋鲜卑人与汉人在生产上的密切联系。由此来看,北魏社稷祭祀礼仪的实行,也就成为影响拓跋鲜卑人与汉人交往、交流、交融的不能忽视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