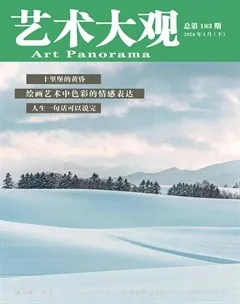十里堡的黄昏
迟子建
十里堡是都市里的乡村。
黄昏降临时,印染厂门前那条本不清澈的河流便被夕阳的余晖给涂抹得一片灿然。这时,简朴陈旧的桥两侧就已经被郊区的菜农给占据了。
这些菜农面若枣色,穿布衣,有的妇女在冬季时还包着土里土气的头巾,他们提秤的手和他们的吆喝声一样粗糙。有时他们还赶着马车或驴车来,车上载着水灵灵的蔬菜。
他们有板有眼地走在黄昏里,没有比这种情景更感人的了。
听完了这种来自乡间的声音,你沿着十里堡那条庸碌、闭塞的长街再走上一刻吧。
卖白鲢鱼的人将期望的目光投在你身上,一些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胡同口的矮板凳上沐浴夕阳。
如果你走路稍不留神,会被四处支起的小摊撞着。卖驴打滚的人戴着鲜亮的白帽子;卖煎饼果子的摊前总是那么热气腾腾;炸饼在油锅里发出知了一般的叫声;卖各种腌菜的老婆婆,将那一盆盆五颜六色的腌菜陈列在玻璃柜里,玻璃锃亮锃亮的,里面的每样腌菜都是老婆婆的一个通话。
走在这样的街上,你会感觉到生活的气息阵阵拂来,给人的精神以一种慰藉。
秋天尽了,苍白混沌的冬天来了。十里堡桥下的流水在傍晚时常常升腾起一团团乳白色的雾气。
站在桥头卖菜的农人如临仙境,但他们绝不会因雾气的影响而缺斤短两,他们在浓雾中拼命睁大眼睛去看秤星,他们的布底棉鞋踩着坚实的路面,远来的马蹄声越发响亮了。
那时我们会更加怀念春季在桥头卖鲜红草莓和樱桃的小姑娘,怀念秋季挑着沙果担子的健壮汉子。
他们不是京城人,他们居住在农村,种菜,种粮,也种花。农人们在城市的边缘生活着,他们不时给京城挟来新鲜的田野气息,送来最不可缺少的生命养料,送来稻谷、玉米、水果、蔬菜,也送来朴实、忠厚与善良。因为有了他们,京城就像被一股活水围绕着,富庶美丽,生生不息。
我忘不了离开北京的那年冬天,那是圣诞节前夕的阴沉的黄昏,还是在十里堡那条幽僻的长街上,我拿着一沓刚买到的散发着廉价香水气味和美丽谎言的贺卡往回走,忽然在桥头遇见一个卖竹编小摆设的乡下人。
他年纪很大了,穿一件黑棉袄,目光有些迟钝,身前的篮子里放着形形色色的竹编:黑嘴巴短尾巴的狗,胖乎乎的小鸡,姿态娴雅的鸭子,有些鲜红眼珠的小兔子。
我问他每件卖多少钱,他说一元。他并不看着我说话,我蓦然察覺这是个盲人。我问他这些小动物是不是他编的,他点点头。
我突然觉得羞愧难当,我花许多钱买来一堆印刷精美却难掩矫情的贺卡,而对这些充满自然气息的竹编却熟视无睹。
是城市要消灭一个有着故乡的人的心中那最后一缕乡愁吗?那一刻我的眼睛发潮了。
天台的参天古木、颐和园的亭台楼阁、王府井的繁华街市,并没有给我留下太多的回忆。能让我想起北京的,总是东郊那个叫十里堡的地方,那个我生活了三年的地方,我忘不了那儿的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