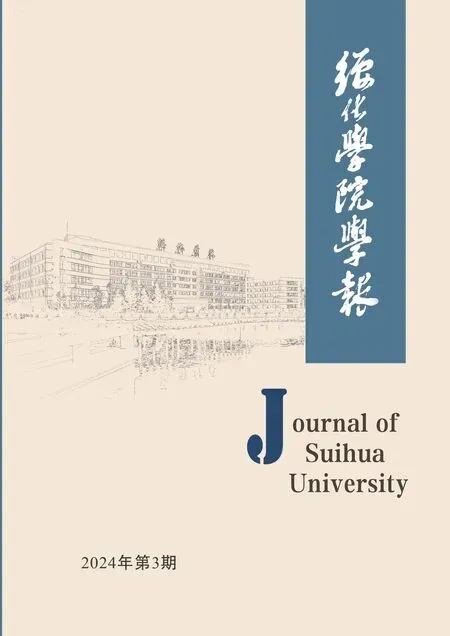自我身份认同的丧失与构建
——《红字》中的创伤叙事研究
付岳梅 应世潮
(大连海洋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辽宁大连 116300)
《红字》中,霍桑对人物刻画就像是一位医生在剖析海丝特·白兰、亚瑟·丁梅斯代尔和罗杰·奇灵渥斯三位主人公的情绪,发掘他们各自内心创伤,展现了三人面对创伤不同的应对,激发人们的思考,倡导人们以善行洗刷罪恶,净化心灵。本文拟从创伤理论视角研究《红字》中的创伤叙事,探讨创伤救赎之道。
一、创伤性体验:丧失自我确定感
(一)丑行揭示的屈辱创伤。对海丝特·白兰而言,因通奸而遭受的示众惩罚,让她需要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屈辱,忍受着人性所能承担的一切。此外,在她的胸前佩带着一个鲜红的A字,宣示着她是一位罪人,一位不知廉耻的女人,让她由高贵的贵妇沦落至“荡妇”,耀眼的红字是那么明显,致使白兰在任何时候都将遭受别人的非议和鄙视的目光,让她在生活中无所遁形。耀眼的红字使白兰与其他人之间划上了明显的分割线,她成了一位“社会弃儿”,只能是为了照顾孩子,顶着别人的鄙夷,尽可能在较小的活动范围谋生存,此外还要承受外界的欺辱,却不能反抗,担心在反抗中被别人再一次揭开她的“通奸”罪行,让她又要承受一次不堪忍受的凌辱,因此她选择以“禁闭畏缩”自我麻木,尽可能将生活的重心投射至女儿身上,从而减轻对自身的轻视。甚至海丝特时常出现幻觉或幻想,出现“记忆侵扰”的症状:有时候产生了注视着她胸前的红字“A”的村民身上同样藏着罪孽,和她一样都与魔鬼签了约的幻想;有时候会怀疑珠儿是否真实存在,产生珠儿是魔鬼、精灵还是她的女儿的奇怪念头。在极大羞辱感的影响下,海丝特同样有过死亡的念头:“不时有一种可怕的疑虑极力要占据她的灵魂,怀疑是否该把珠儿马上送上天国,自己走向‘永恒的裁判’所断定的未来世界去,才会更好些呢。”[1]
(二)罪恶隐藏的自责创伤。对亚瑟·丁梅斯代尔来说,他内心承受着极致煎熬。在大众眼里,他是一位“年轻俊美,学识渊博,善于辞令,有着极高的秉赋和极深的造诣,在教民中有着极高的威望”的牧师[2],但是当白兰站在绞刑台接受审判的时候,他是一位为了自身前途而“明哲保身”的懦夫,他“忧心忡忡、惊慌失措”,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把自己封闭起来”获得“安然”。丁梅斯代尔在圣职上越是大放异彩,取得的成就越辉煌,他就越会陷入对自身“伪善、懦弱”的在意,懦夫和伪善者的身份与他之前才华横溢、前途光明的年轻牧师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巨大的落差感和对自我确定感的缺失,对其心理造成了极大的创伤。他的内心无时无刻不受到愧疚感和耻辱感的侵蚀和折磨,出现了“过度警觉”和“禁闭畏缩”的创伤症状:一方面丁梅斯代尔担心“奸夫”身份的暴露,警惕医生奇灵渥斯对其心理状况的询问,另一方面他经常独处一室、独自散步,极力避免与外界的接触。他的身体日益孱弱无力、满脸愁容倦态、彻夜难眠,而且经常用鞭子抽打自己以期通过肉体的虐待来获得内心的安宁。虽然海丝特戴上红字“A”,但是丁梅斯代尔时常用手捂着自己的胸口,感觉自己的胸口烙上了滚烫的红字“A”。这些病态的行为,正是心理创伤的表征。
(三)因爱成恨的背叛创伤。对罗杰·奇灵渥斯来说,海丝特和丁梅斯代尔的通奸行为是其创伤的根源。奇灵渥斯原本是一位有名望的、学识渊博、医术高明的医生,即使在被印第安人俘虏消失的两年间,他内心依然怀揣对家庭的期望,努力学习印第安人医术以此充实自己,并且凭借自身高超的医术,在美洲殖民地获得无尚的荣耀和成就。然而妻子海丝特的出轨,让奇灵渥斯内心的期待都化成泡影,特别是在经历重重困境,以为要迎接美好生活之际,在绞刑台上看到妻子因为通奸而接受审判,这样残酷的现实与自己的幻想之间的强大落差,造成了奇灵渥斯内心的极度痛苦与恐惧,“一种令人极度痛苦的恐惧布满了他的面容,像一条蛇一样在上面迅速地蜿蜒缠绕……他的脸色因强烈的情绪而变得阴暗”,显现出了奇灵渥斯内心世界的状态。因此他不仅威胁妻子隐藏身份,还将自身视为荣耀的“白兰先生”称呼改为罗杰·奇灵渥斯,以表明自己将会把挖掘与折磨海丝特情人的目标作为自身后续生活的全部。在创伤记忆的侵扰下,奇灵渥斯失去了自己的身份,也抛弃了原来的生活轨道,从一个胸怀理想的医生变成了一个隐秘的、邪恶的、虚伪的复仇者,高超的医术无形中也成了他复仇的邪恶工具。仇恨心理使他的外形日益畸形,神情充满邪气,他不再是一个正常的医生,“从前那种勤学睿智的品格,那种平和安详的风度”已经被“一副急切搜索、近乎疯狂,而又小心翼翼、高度戒备的神情”所取代。
三位主人公是创伤的受害者又是加害者,海丝特与丁梅斯代尔的通奸行为是奇灵渥斯创伤的根源,同时奇灵渥斯后续的种种报复行为,也加重了对海丝特与丁梅斯代尔的伤害。
二、创伤沉溺:徒增个人伤悲与愤懑
(一)自责情绪笼罩身心,找不到排解出口。丁梅斯代尔在创伤体验下,选择了躲避,“拒绝恢复与外在现实正常的认同关系,长时间陷入自责、沮丧、冷漠等心理情感”[3],这导致丁梅斯代尔整天背负着巨大的压力在前行,特别是随着自身事业的不断提升,个人内心的担忧以及对自身伪善与懦弱的批判就会更加来势汹汹。长期的人前伟岸,人后阴暗的精神折磨,让丁梅斯代尔沉溺其中,无法自拔。他无法从教众身上寻找到自我身份的认同,将自身的创伤转化成引渡他人脱离困苦的精神力量,而是常常产生自我怀疑,觉得“我看起来做的那些好事,我对之毫无信心,它只是一种幻觉而已。像我这样一个灵魂已经毁灭的人,怎能对拯救他人的灵魂有所裨益呢?——或者说,一个亵渎的灵魂能够净化别人的灵魂吗?至于人们的尊敬,我宁肯它变成轻蔑与憎恨!”[4]由于没有站出来承认自己是海丝特的情人、珠儿的父亲,丁梅斯代尔极其厌恶自己的懦弱和虚伪,通过一系列的行为来惩罚自己。他时常鞭打自己的肩膀直到血丝渗出,将斋戒视为自我惩罚的方式并一直坚持到双膝颤抖为止,他还彻夜不眠地做祈祷以折磨自己。丁梅斯代尔在饱受长达7 年的内心负罪感及良心的谴责下,在绞刑台坦白了自身为通奸者的秘密,但是随着内心情绪的释放,丁梅斯代尔“在众人的惊惧之声中,这个受尽蹂躏的灵魂辞世了”。
(二)因爱生恨,复仇至上丧失人生乐趣。奇灵渥斯,其将自身的创伤体验全部转化成了“憎恨”,包括对海丝特的憎恨,更有对丁梅斯代尔的憎恨。他每天想着的都是隐藏起自身,去寻找让自身家庭失去温暖的情夫。对海丝特,他威胁对方不要揭穿自身的改头换面,他要做隐藏在黑暗中吐着信子的毒蛇,他原本“平和安详的风度,如今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急切窥测的神色”。当他发现丁梅斯代尔胸口上有与海丝特一样的红色标记时,他“将两臂伸向天花板,一只脚使劲跺着地面,以这种非同寻常的姿态放纵地表现他的狂喜”[5],他此时完全将创伤受到的伤害转化成了对丁梅斯代尔寻求报复的快感。他不断运用自身本可以救助他人的医术,对丁梅斯代尔施以“肉体上的疾病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摧残”,甚至他运用自身高超的医术积极治疗丁梅斯代尔因长久处于愧疚与自虐而早已“破烂不堪”的身体,从而能够拥有更长的时间来折磨丁梅斯代尔。这种病态的复仇心理,成了奇灵渥斯生存的“能量”,然而随着丁梅斯代尔的离世,奇灵渥斯因“扭曲的心灵再也找不到依托”而“快速枯萎”。
三、创伤救赎:构建自我身份认同
(一)慰藉给予了直面创伤的勇气。在通奸审判的羞辱示众中,海丝特虽然被迫直面村民的议论和审视,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生活压力,但是女儿珠儿的存在,让海丝特不得不面对即将到来的生活,“为母则刚”的天性,使海丝特在面对任何非议甚至歧视时都有了勇敢生活的动力,同时女儿的乖巧懂事,使海丝特获得了难得的精神慰藉。可以说,女儿在赋予海丝特责任的同时也给予了她极大的精神慰藉,致使她在最初面对创伤时,有了面对创伤的勇气。
(二)联系扭转了创伤环境。养育女儿的重担,迫使海丝特需要通过做针线活挣钱维持生计,通过“针线”这一媒介,她与周边人重新获得联系,为了获得他人更多的订单,海丝特需要拥有更为高超的针线技艺来提升自身竞争力,在不断地与周边村民的联系过程中,通过技艺使自身逐渐获得了别人的认同,周边人员对海丝特的形象认同从通奸者变成“巧妇”,而胸口醒目的红色A字在此过程中,被赋予了“能干”的含义。
(三)重铸展现了人格魅力。在与周边逐渐熟络之后,海丝特原本善良的品德也有了得以施展之地。不在意他人对自己的冷嘲热讽,她经常对穷人与病人伸出援助之手,使自己逐渐获得了人们的尊重与认同,其胸口醒目的A 字此时就犹如修女胸口的十字架一般,有了神性,人们越来越觉得“她胸前绣着的字母在闪闪发光,那超凡脱俗的光芒带来了温馨和安慰”,海丝特变成了周边穷困人员的“天使”。
(四)成长找到突破创伤的路径。因为敢于面对现实,海丝特促进了自身与周边人员的融合。在一次次给予对他人的付出与帮助中,海丝特重新找到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她不再满足物质的救济,她在自我救赎过程中,精神状态也变得越来越好,从异国他乡返回新英格兰的海丝特成为了当地村民尤其是女性的精神导师,他们带着“种种忧伤和困惑,来寻找她的忠告”,海丝特则“尽其所能安慰她们,为她们指点迷津”,而且“用一个人生活中最真实的考验向人们显示神圣的爱心如何使我们获得幸福”。
三人中,只有海丝特完成了最终自我创伤的救赎,只有她最终走出了创伤的边界,没有因为通奸事件造成的伤害与他人的鄙夷而自怨自艾,而是选择勇敢地面对,在与他人相处过程中,重新找到了个人的施展空间,用自己的勤劳、善良、博爱改变了周围人对她的看法,将周边原本创伤的环境塑造成了一个展现自我的平台;而丁梅斯代尔与奇灵渥斯两人,一位受困于愧疚与悔恨之中,将自己的内心与他人隔离开来;另一位沉溺于复仇的欲望之中,把自己的生活拖入到狭隘的报复私念里,把自己置身于创伤环境里,从而不断沉沦与迷失,失去了与外界的交流,丧失了自我价值的认同获取,最终走向了人生的“凋零”[6]。
结语
从创伤叙事角度解读《红字》中的悲剧,发现海丝特、丁梅斯代尔和奇灵渥斯都是创伤患者,对“通奸事件”的主观感受是造成他们创伤性体验的事件。这一事件使海丝特成为一个人人避而远之的“社会弃儿”,致使海丝特丧失了原有的自我确定感。但是通过以针线活为媒介,海丝特把耻辱的红字“A”变成“能干”和“天使”的象征,重新在社区生活中构建积极身份,实现自我认同,走出创伤的阴影。而丁梅斯代尔和奇灵渥斯则在该事件后迷失自我,失去了自我价值感,他们分别在“肮脏的骗子”和“复仇的恶魔”的自我评价中生活,在心理创伤的纠缠和侵扰中走向了死亡。归根结底,造成海丝特、丁梅斯代尔和齐林沃斯的心理创伤的根源是保守的清教思想,尤其是婚姻观念对人性的压抑和束缚。对于17世纪的民众或者清教徒而言,“婚姻恋爱应服从于对上帝的爱”,清教牧师约翰·科顿(John Cotton)更是“鼓励人们看待配偶‘不要出于他们自己的目的,而要为了更好地侍奉上帝,使他们更亲近上帝’”。在这种婚姻爱情观念为主导的社会中,尽管奇灵渥斯与海丝特的婚姻并非以情感为纽带,他们之间的婚姻仍然是神圣的,理应为了遵照上帝的训令繁衍生育,为上帝增添荣耀。正是这种压抑人性的婚姻观从根本上导致了海丝特、丁梅斯代尔和齐林沃斯之间的悲剧。而且这种压抑人性的婚姻观念与19世纪追求个性解放的浪漫主义思想格格不入,正是通过书写个性独立、勇于追求幸福与自由的海丝特的最终胜利,霍桑痛斥保守的清教思想,歌颂人性的自由与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