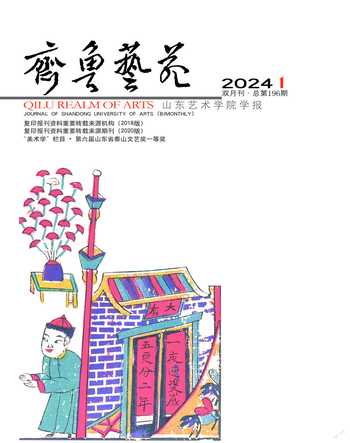生态艺术助力生态公民塑造路径探析
刘心恬
摘 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生态公民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生态公民塑造的路径主要依靠生态美育。生态美育的基本任务是塑造生态公民。艺术场馆在开展生态美育、塑造生态公民、构筑生态社群等层面应发挥更为显著的作用。生态艺术助力生态公民塑造的基本路径包括当代艺术展与生态文明主题的有机融合,走入田野与社区的社群艺术与生态审美化生活方式的有机融合等。“共生世界”2022济南国际双年展的策展理念彰显了生态人文关怀,为生态艺术塑造生态公民的路径提供了有益启示。
关键词:生态艺术;生态美育;生态公民;生态审美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J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236(2024)01-0066-05
法国艺术史学家保罗·阿登纳(Paul Ardenne)在《生态艺术:人类世与造型的创作》中指出:“二十世纪下半叶之初,艺术的生态转向是不可否认的。……生态艺术家的形象是从颇为晚近的2000年才开始成形,以一种普遍的方式发展起来。”[1](P13)随着相关创作、策展及批评等艺术史文献的累积,生态艺术及其美育价值成为近三年学界的研究热点。2021年8月,“生生之介——后疫情时代生态美学发展国际研讨会暨生态艺术展”在济南举办。2022年12月举办的“生态美学与当代艺术”国际研讨会将“生态艺术与环境艺术”列入议题。2023年4月举办的“生态文明视域下的艺术学学科体系建设”高峰论坛专设“生态美学与生态艺术”“生态美育与艺术人文教育”分论坛。在此学术语境下,第二届济南国际双年展举办。展览以“共生世界”为主题,包含“人与自然共生”“地域与世界共生”等五个维度,凝聚生态文明、文化惠民、新文科建设、生态美育等多学科领域热点。2023年3月,“试说新域——2022济南国际双年展生态美学研讨会”举办。生态艺术的社会美育价值成为与会学者讨论的焦点之一。
一、生态公民塑造问题的时代语境与学理阐释
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等一同列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的重要内容。这一论断是反思西方现代化道路所造成的生态危机弊端,并在新时代语境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出的深刻再阐释。在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征程中,不仅要坚持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也要努力促进思维方式的绿色转型。所谓思维方式的绿色转型是指以朴门永续(permaculture)为原则的系统思维方式,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坚持生态整体主义,体现生态人文关怀。
当代艺术审美活动是生态公民塑造的主要途径。习总书记提出:“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 [2](P116)这要求我们将生态公民塑造纳入精神文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视域中,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坚持走生态友好发展道路,引导公民践行绿色生活方式。生态艺术有助于全体公民树立生态审美意识,对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关系进行自觉的审美观照,在主体层面防微杜渐地避免生态危机的进一步蔓延与加剧。因此,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加强文化艺术元素的精神引领,充满生态人文关怀的生态艺术实践及生态美学理论便可通过社会美育渠道使生态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
在此时代语境下,围绕生态艺术开展的美育实践取得一定进展。自2018年以来,全国各地众多颇具代表性的生态艺术展览及项目问世,于其中可见当代艺术家、策展人、艺术机构已有塑造生态公民的使命自觉。 [3]2022年7月,山东美术馆举办“观此青绿——山东美术馆馆藏生态文明主题绘画作品展”并举办学术研讨会。这些文化惠民活动在公众内心植入了生态理念的种子,充分履行了公共艺术服务与审美教育的职能。而今,“共生世界”济南国际双年展的举行又使生态文明主题艺术系列活动成为山东美术馆的美育品牌。
近年来涌现出如此密集的生态艺术活动,究其原因,与后疫情时代艺术创作群体对全球生态危机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有关,同时也得益于学术研究对艺术创作的反哺。自党的十七大至二十大,在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指引下,生态美学自主性知识体系日益成熟。2020年后,关注生态艺术的研究论著及评论文章显著增加。目前,理论界正积极跟进生态艺术的发展,充分进行个案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生态艺术学建构路径。这些都为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生态公民的塑造奠定了理论基础。
进入21世纪,公共管理、审美教育等多领域皆有关于“生态公民”的若干阐释,如沈莉的《生态公民养成的重要性及对策研究》、李娜的《生态公民的意蕴及其养成路径探析》等。李娜指出,生态公民应具备系统思维、和谐理念,其首要责任是“确保自身的生态足迹不会损害和阻碍他人及后代追寻有意义的生活选择的能力” [4]。在美学与艺术学领域,也有学者从培养目标的角度反思了“环境教育”与“生态美育”在公民生态意识塑造中的区别。丁永祥认为,单凭传统环境教育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生态意识的培养须走一條从物质上升到精神的路径,因而“未来的环境教育应该与生态美育相结合,充分发挥生态美育的优势” [5]。从精神层面开展生态美育,即要培养具有生态审美意识的“生态人”,“培养大量的‘生态人,是未来生态美育的主要任务” [6]。龚丽娟进一步指出:“生态美育从传统的生态教育发展而来,既有对传统生态教育的突破,转而注重人的生态审美化生存,将生态人培养成生态审美人。” [7]
上述研究为艺术学理论界重新界定生态公民的概念内涵提供了前期准备。基于此,赵奎英在探讨后疫情时代语境下生态艺术与生态公民塑造之关系时指出:“作为生态文明主体基础的生态公民具有以下显著特征:生态公民是具有环境人权意识的公民;生态公民是具有良好美德和责任意识的公民;生态公民是具有世界主义理念的公民。” [8]“生态人”“生态审美人”与“生态公民”是相近的概念。但后者的提出意味着更加深入地思考了人类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责任和义务应该如何表达,首先强调的是其作为“地球公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程相占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最终必须落实在每一个公民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只有当绝大部分公民都转变为生态公民之后,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才有可能成功。” [9]
二、生态艺术助力生态公民塑造的基本路径
20世纪60年代,在生态环保运动思潮的影响下,当代艺术家聚焦环境破坏、生态失衡及永续发展路径探索等问题而创作了大量生态艺术作品。时至今日,当代艺术早已成为反映生态问题、引导受众塑造生态意识的重要途径。生态艺术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全球各地的艺术家“用艺术的方式关怀生态危机,借助不同的媒介表达生态意识或生态思想观念,创造了多种多样的生态艺术作品,包括生态诗歌、生态小说、生态绘画、生态音乐、生态建筑、生态舞蹈、生态摄影等” [10]。郝凝辉认为,狭义的生态艺术指的是“以生态为主题的绘画、雕塑、装置等多种造型艺术作品” [11]。约翰·博伊斯的《土电话》、汉斯·哈克的《莱茵净水工厂》、丹尼尔·麦克考米克的《分水岭雕塑》、海恩里克·哈坎森的《倒下的森林》、阿米·沙罗克斯的《水的博物馆》、徐冰的《凤凰》《背后的故事》、陈强的《黄河水体纪念碑》以及姚璐的《新景观》等,都是生态艺术领域的代表作品。但就塑造生态公民的效果观之,社会参与艺术(socially engaged arts)也是生态艺术的典型形态。包括约翰·博伊斯的《7000棵橡树》《清洗埃尔博河活动》、尹秀珍的《洗河》《南极》《种植2018》、徐冰的《木林森计划》、靳立鹏的《愈园计划》等在内的许多社会参与艺术在生态公民塑造层面收效更佳。
由此可见,生态公民塑造的基本路径包含两个维度。其一是在艺术场馆中借助生态主题艺术作品欣赏树立公众的生态审美意识的生态美育方式;其二是走入乡村田野与城市社区的借助自然行走、生态修复、耕读手作、宜居生活、景观改造、审美疗愈等生态艺术项目培育公众生态共同体意识的方式。前者在传统社会美育实践中汲取已臻成熟的宝贵经验,而后者更强调在地性、参与性、融合性的新路径。二维度又分别包含若干不断生成并持续创新的案例类型,为生态公民塑造路径探索提供了有益启示。
首先来看公众进入美术馆欣赏生态艺术作品的路径。就策展理念而言,由“共生世界”2022济南国际双年展观之,生态艺术教育的开展有赖于艺术策展的生态转向。若策展人一方面意识到生态危机的严重性,另一方面相信生态艺术在公众美育效果层面的突出贡献,同时有意识地致力于生态公民的塑造,当代艺术策展的生态转向便可达成。2022年底至2023年初,与济南国际双年展近乎同时启幕的还有“和美共生:第三届新疆国际艺术双年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美丽中国·广东生态文明艺术双年展”“大地之歌:2023美丽中国纪事”“合成生态:北京艺术与科技双年展”“美丽中国——生态环境书画展”“千岛万物:生态艺术展”“涌现:气候危机下的生态艺术行动”“可持续的博物馆,可持续的艺术”等展览及项目,皆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主题。后疫情时代,在全国范围内如此大规模、高频率地密集举办生态艺术展是符合时代语境的,而策展主题对公众观展思路的引领是塑造生态公民的有效路径。
就技术创新而言,数字媒体艺术与生态文明主题实现了充分融合。据悉,本届济南国际双年展的互动性作品比上届增加了30%,以包含AR、VR、人机交互、3D打印等科技元素的数字公共艺术助力生态公民塑造。“数字公共艺术不仅催生了公共艺术的电子科技和三维模拟技术的不断创新,更重要的是将生态理念介入到公共艺术的主题和创作中,激发了大众的生态审美意识。” [12](P128)比如,《飞越黄河》《金声玉振》《未被证伪》《元·五岳》《19赫兹》《鹊华十二时》等作品,都以艺术家独特的视角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并通过艺术化的手段邀请参观者融入其中。与传统造型艺术相比,装置艺术、数字艺术本就令人感到新奇,而生态文明主题的介入,又令作品多了一分魅力。许多作品的最终呈现有赖于受众的参与,多维度调动视觉、触觉、听觉等诸多感官。当欣赏者置身黄河美景、五岳之巅、蔚蓝深海、杏坛飞花甚至宇宙太空,虚拟性地感知到自然人文之美,深刻感受到人与自然之间的亲缘关系,再也不会置身于生态环境之外。数字艺术的呈现方式对展馆环境及观展群体是生态友好的,使其更适合表现与生态相关的内容。生态文明主题的数字公共艺术的价值在于使生态审美意识“渗透到跨媒介的艺术互动中,呼吁大众关注生态问题,激发大众增强生态意识,启发大众生态审美教育”[13](P138)。
艺术场馆在生态社群构筑与生态公民塑造中应发挥更为显著的作用。“共生世界”2022济南国际双年展便是典范,其所打造的都市桃花源与生态乌托邦向世人展示了艺术的公共文化服务功能。此类生态艺术活动品牌将带动城市生态社群的发展,助力生态公民的塑造,是未来生态艺术策展的重要趋势。
其次来看公众走入田野与社区参与社群艺术的路径。这一路径的特色鲜明地体现于社群艺术与生态审美化生活方式的有机融合。靳立鹏的《愈园计划》是自2021年启动至今的生态艺术项目。通过效法自然生态智慧,他以四川美术学院及周边环境作为作品实施空间,秉持朴门永续系统思维,使愈园成为一个“融合生态食物生产、能源与雨水收集、社区堆肥、养蜂、种子图书馆、生态美育与生态艺术疗愈等主题,以及链接校园内外与城乡社区的长期修复项目” [14]。从靳立鹏的川美愈园堆肥计划、吴玛悧的树梅坑溪生态社群活动等典型案例可知,生态公民的塑造不能单纯依靠环境教育,更要依靠审美教育,尤其是以生态社群活动与生态艺术创作欣赏为主要途径的生态审美教育。曾繁仁先生指出,生态艺术家的创作应“提升生態社群的重构,帮助界定社群概念本身,并且弘扬一种生态责任感”[15](P207)。靳立鹏认为:“生态系统思维告诉我们,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是自循环、零废弃与可持续的;……因此人类社会也应效法自然的可持续性去营造可持续的未来社区。” [16]将生态社群、未来社区及生态责任感等关键词聚集一处,便勾勒出生态公民塑造工作在美术场馆之外的第二条有效路径。
除此之外,这一路径的特色还体现于艺术乡建项目与可持续发展的有机融合。21世纪初,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与逐步推进,艺术乡建项目在许村、青田、乌镇、石节子等乡村区域落地。坚持生态友好原则的艺术乡建项目一方面使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深入人心,另一方面也借此契机实现了当代艺术的生态转型、绿色村居可持续发展、文创产业带动经济文化发展等多重效益。以2018年广安双年展为例,当代艺术家在考察当地自然生态环境及人文风俗后,创作了具有鲜明在地性的生态艺术作品。走入田野的生态艺术展凸显了在地性与公共性,突破了美术馆空间的局限性。生态主题艺术乡建项目策划的目的在于,将聚焦生态问题的装置、行为及跨媒介艺术置于绿水青山环绕的乡野之中,反差性的视角有利于启发公众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更直观地引导其树立生态审美观及生态家园意识。
公众进入美术馆欣赏生态艺术作品或走入田野与社区参与生态社群艺术是生态公民塑造的主要路径。阿登纳提出,“艺术是生态之战的核心”,“促进、支持觉醒才是有益、可敬的目标”。 [17](P9)因此,塑造生态公民是生态艺术履行社会美育使命的重要任务。生态公民的塑造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之义,主要实现途径在于生态审美教育。而生态美育的形式是多样化的,艺术场馆须创设生态艺术活动品牌,吸引更多的受众群体,更高效地服务于生态社群的构筑。
三、生态艺术助力生态公民塑造路径的基本特征
生态艺术在塑造生态公民的过程中呈现出多方面的基本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美育效果上看,因关系到人类生存的最根本问题,生态艺术往往具有亲民性。以垃圾制作的装置作品、描绘自然环境破坏的画面、拍摄动植物因污染而畸形生长的摄影和纪录片,以及倡导人与自然共生的各种社会参与艺术等等,较为直观地传递了艺术家想让欣赏者了解的信息。而受众在欣赏此类作品时,也能较为深刻到位地把握作品理念。因此,生态艺术助力生态公民塑造路径具有社会性、无门槛性、多层次性,尽可能地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引发公众对生态危机问题的关注与反思。
其次,从实施手段上看,助力生态公民塑造的生态艺术往往具有公共性的基本特征。艺术家常采取交互参与、在地融合的方式增加艺术作品审美接受环节中受众的互动程度,如前述济南国际双年展中的数字媒体艺术作品。在社群艺术及艺术乡建项目中,受众参与作品互动游戏甚至与艺术家合作完成作品的案例更是不在少数。在地性使生态艺术作品提升了与特定空间地域的黏合度;参与性使作品意义的生产过程变为受众获得审美体验的同步环节;交互性使艺术创作与欣赏成为不断生成而具有可持续性的新形态。尤其是社群艺术及行为艺术,可作为生态艺术项目在多地范围内面对不同受众群体多次实施,如尹秀珍的《洗河》等便是典型案例。
再者,从舆论引导上看,生态艺术往往具有鲜明的指向性、批判性、警示性、反思性与启迪性。在本届双年展上,陈坚的《呼吸》以口罩为主体意象的30幅组图放大了公众眼中习以为常的日常物件,引发人们关于疫情的思考;徐国峰的《母子》以体量巨大、色彩醒目的一大一小两只红鹈鹕引导受众的视觉观看,当五颜六色的现代生活垃圾从母亲口中倾倒入孩子口中时,观者内心无不震撼;V^小组作品《19赫兹》将鲸群生存所需自然生态环境条件及受人类干扰的数据以可视化图像呈现,并以沉浸式体验布局空间,将作品的共情效果发挥到极致,被参展观众评选为最受关注的20件作品之一。
生态艺术所具有的上述特征与之诞生于生態危机的时代语境有关,也与其塑造生态公民的使命相联。值得注意的是,为了突显艺术批判的力量,达成警世的舆论效果,艺术家不再拘泥于传统艺术的造型手段或单一感官的审美接受方式,而是尽可能广泛挑选最适合表现主题的媒介元素进行创作。因而,生态艺术通常是跨媒介性的、交叉学科性的,其塑造生态公民的路径也必然是多样化的。
结语
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到生命共同体再到生态审美共同体,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及生态审美研究的中国话语体系逐渐完备。生态主题艺术作品及项目以艺术化的呈现形式反映生态问题、表达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反思。艺术场馆为生态美育与生态公民塑造搭建了平台,在生态危机时代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双重语境下,助力审美教育走上新高度。这标志着中国当代艺术叙事的生态转向趋势愈发鲜明自觉,也意味着当代艺术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必将实现更大的价值。
参考文献:
[1][17][法]保罗·阿登纳.生态艺术:人类世与造型的创作[M].詹育杰译.台北:典藏艺术家庭股份有限公司,2021.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3]刘心恬.论中国当代艺术生态审美表达的基本特征[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3(02).
[4]李娜.生态公民的意蕴及其养成路径探析[J].理论导刊,2014,(10).
[5]丁永祥.生态审美与环境教育[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1).
[6][7]龚丽娟.从生态教育到生态美育——生态审美者的培养路径[J].社会科学家,2011,(7).
[8]赵奎英.艺术参与和生态公民的重塑——后/疫情时代的艺术功能思考[J].学术研究,2022,(3).
[9]程相占.生态文科:从文科的生态转向看新文科的生态维度[J].新文科理论与实践,2022,(3).
[10]程相占.生态艺术学的建构思路与整体框架探析[J].艺术评论,2022,(12).
[11]郝凝辉.超越先验:生态艺术和设计的社会雕塑意义[J].美术研究,2022,(1).
[12][13]张嫣格.介入性观看:视觉艺术的生态维度[M].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22.
[14][16]靳立鹏.诗意建构与修复——以愈园生态艺术行动为例[J].美术观察,2022,(1).
[15]曾繁仁.生态美学基本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刘德卿)
收稿日期:2023-09-01
作者简介:刘心恬,女,博士,山东艺术学院艺术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生态美学与生态艺术学。
项目来源: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生态艺术学建构研究”(23AA001)的阶段性成果。
doi:10.3969/j.issn.1002-2236.2024.0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