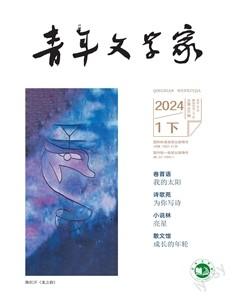景生情,情生景
胡国民
在意境美学发展史上,王夫之是一位重要的人物。他从情与景的关系问题入手,从审美活动中去观察,将其上升到哲学本体的高度。一般认为“天人合一”是其哲学思想的出发点,亦是其美学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他接受了张载的“气”一元论,认为“皇哉!盈天地之间,清乎!虚乎!一乎!大乎!莫之御而自生者乎!”(《诗广传》)他指出,天地及天地间万物都本于阴阳二气,人亦由阴阳二气的交感变化而来:“男女构精而生,所以生者诚有自来;形气离叛而死,所以死者诚有自在。”(《周易外传》)由于有“天人合一”的思想作指导,在王夫之的意境美学思想中,情与景的关系就非常重要。本文仅就情景交融、情景互生,进而达到情景合一而构成审美意象尝试进行探讨。
一、“情以景合,景以情生”—情景的生发模式
王夫之的“情景”说在继承前人学说的同时,并没有拘泥于前人的传统思维定式,具有自己创造性的发展。他认为“人情者,君子与小人同有之情也”,与一般时人先贤所论无二,但他又讲“实则天理、人情,原无二致”(《读四书大全说》),克服了传统天理人欲的矛盾,强调情与理的内在统一。他认为文艺的抒情性质是其根本性质:“诗以道性情,道性之情。”在此,“性之情”则强调情之理化,因为“诗源情,理源性,斯二者岂分辕反驾者哉?”(《古诗评选》)而且,他将道性之“情”与孔子所说的“兴观群怨”联系起来,称之为“四情”:“出于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游于四情之中,情无所窒。”(《姜斋诗话》)情在这里,不仅理化了,而且还具有雅化的趋势。此时,王夫之将情感进行生活的和审美的区别,强调审美的情感由生活的情感而来,诗“惟能静斯以入化”,“沈醉而入,洗涤而出”(《古诗评选》),即通过审美的方式,悲郁惆怅之情也能化为闲旷和怡之情,这种情感的净化、雅化的过程,较之前人则显得深刻而系统,更富于美学意味。
与情一样,王夫之在谈景也别具一格。一般认为“景”主要是指与主体构成审美关系的自然之景。但在王夫之看来,与情构成审美意象之景既包含自然属性的一般景物,也包括带有社会属性的人等。而后者则诉诸主体的审美想象能力,是艺术化了的“真实之景”。正如他评谢朓《江上曲》为“空中如响,曲折如真”,评潘岳《内顾诗》为“想象空灵”(《明诗评选》)。为此,他指出“景”有三种:
有大景,有小景,有大景中小景。“柳叶开时任好风”“花覆千官淑景移”,及“风正一帆悬”“青霭入看无”,皆以小景传大景之神。
在他看来,写景的最终目的是要“以小景传大景之神”。以“风正一帆悬”为例,这句诗出自唐代诗人王湾的诗《次北固山下》:“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由于潮水渐涨,江面越发显得宽广,江面因一叶小小的风帆而显得更加宽阔。因潮生而上涨的江水与恰到好处的正风相会,才有这“风正一帆悬”的景观,勾勒出壮美的大江行船图。如若在弯曲的小河里就不会“风正一帆悬”了。这里写的是大景中的小景,表现的是小景的画面,却使人联想出另一大景的意象。这就要求我们要善于取景,即通过主体的审美体验,使毫无生机的景物得以转变为饱含主体生命的艺术化的形象。正如他评《诗经·小雅·出车》:
“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蘩祁祁。执讯获丑,薄言还归。赫赫南仲,猃狁于夷。”其妙正在此,训诂家不能领悟,谓妇方采蘩而见归师,旨趣索然矣。……而南仲之功,震于闺阁,家室之欣幸,遥想其然,而征人之意得可知矣。乃以此而称南仲,又影中取影,曲尽人情之极至也。
可谓诗中有景,景中又有景,能领略其景中之景,则正体现主体的审美想象力的妙用之处。仿佛景中之景尽在眼前,历历在目,这看似写景,实则“曲尽人情之极也”。在此,景中景非一般现实之景,而是饱含主体情感因素的审美意象,也就是大景。正是由于这种写景则传情,写情则生景,使得主体能够从容地进入审美领域,创作出的作品才能生机无限,意趣盎然。
二、“景非滞景,景总含情”—情景的构成逻辑
在谈到情景相生的问题时,王夫之多处提及“景生情”“情生景”之类的命题,在他看来,情景是互生的。首先来看“景生情”。景中生情历来是中国古典诗歌创作的传统方式之一。“六艺”之中的“兴”正是托物言志、触景生情,而后来的“物感”说也基本上是即景生情。
王夫之也认为情景结合的最高境界是妙合无限,即情中有景、景中有情。一般对于景物的描述,首先是对当下之景的感触。由于客观外在的景与主体内心的情感体验和经历有某种契合,如睹物思人、长亭折柳等都能唤起主体内心深处某种稳定持久的感情,于是睹景生情,寓情于景,“自然感慨,尽从景得,斯所谓景中藏情”(《唐诗评选》)。在景与情的熔铸过程中,融合后的景不再是先前的自然之景,而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之景,即“景中有人”,也就是經过审美感情浇灌后的艺术新胚胎—审美意象,如他在《姜斋诗话》中指出:
景中情者,如“长安一片月”,自然是孤栖忆远之情;“影静千官里”,自然是喜达行在之情。
“长安一片月”的后一句是“万户捣衣声”,诗中描绘的正是这样一个场景:明月当空,万籁俱寂,诗中主人公触景生情,感怀亲人,辗转无眠,而捣衣之声传遍万户,恰好加重了这种思念的情绪,于是后文便有“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之叹。后一句“影静千官里”,关于杜甫的这句诗,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曾多次提及:“‘影静千官里,心苏七校前,得主矣,尚有痕迹。”他指出,杜诗仍是有主有宾,只是主宾尚未达到妙合无垠的境界。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的身影静静立于满朝文武的身影之中,历经战火之乱而重新回到皇帝身边,诗人的喜悦之情油然而生。从这几句例证可看出“情生景”大约指诗人在不期而遇的某种外在激发下睹物生情,或者诗人的情感活动伴随着外在的景物的形象感知而生发或展开。虽不直接写情,却句句皆情。
“景生情”的审美发生次序是由景而情,由实而虚,即客观之景注入主体的心灵,与主体的心灵相契。对主体而言,“景生情”是外在的景奔注主体心灵的“入”的过程。根据这一审美流程,“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姜斋诗话笺注》),是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景)唤起了读者相似的情感经历和人生感悟(情),经历了由景生情的审美过程。
三、“情不虚情,情皆可景”—情景的相互升华
写“景生情”如此,写“情生景”亦如此。在其看来,“诗中之情,也并非溟然空洞之心,它已为客体之景所弥漫”(刘洁、张晶《论王夫之诗学理论中的审美主客体论》)。“景生情”可以看作是一个由物及我的过程,“情生景”则与之互逆,是情感的外化。在这一意象的生成范式里,情是第一位的,是主旨。主体外向性的情,使客观之景皆着“我”之色彩,即所谓:“皆心先注于目;而后目交于彼不然,则锦绮之炫煌,施嫱之冶丽,亦物自物而己自己,未尝不待吾审而遽入吾中者也。”(《尚书引义·大禹谟》)“心先注于目,而后目交于彼”描述的即是情生景的心理过程,“心”是主体的模糊意念,它发出使自在之物成为审美对象的审美注意、知觉选择和表象摄取等心理活动;“目”指审美认识对视知觉的依附性,首先情生于心,心注于目,而后目觸外界物象,并将情感与外物融合为审美对象。
在此,“情生景”大约有三种生成范式:其一,诗人由情造景,或者景被情所灌注,使之成为“情之景”,使得外在景物明显带有主体主观情感的印记,如他评曹植《当来日大难》中“今日同堂,出门异乡”,称之为“情之景”。他认为诗中短短八字,却显示出强烈的情感色调的对比,勾勒出两幅迥然不同的画面:一是同堂欢聚之乐,一是相隔一方之苦。诗中寥寥八字,并未直接写情而情自溢出,情中含景而诗人遐想无限,倍增诗人的忧怀之情。其二,诗人先情生于心,心然后注于目,依据自身的审美情感来选择、再造外在之景,从而产生新的审美意象。正如郑板桥的“胸中之竹”源于眼前之竹而非眼前之竹。王夫之正是如此,在评曹学佺《皖口阻风》中有“客恨不如风里树,一枝吹落向南天”,认为是“与情中写景”,诗中归客之情难于言表,只恨一腔思乡之情能化为南向飞落之枝,以解思乡之苦,表现出诗中主人公急于回乡却阻于半路的焦虑不安的情绪。在此,情中之景表现出一种被主观之情对象化的“人迹”,客观之景为主观之情所包围笼罩,表现出扎眼的“有我之境”。可见,“情生景”是一个情感客观化、对象化,由虚而实的过程,使客观自在之景获得主体性地位。从情感运动导向看,它是一个“出”的过程,是以审美意象作为论诗旨归的。王夫之认为,主体心中郁结的自然情感(喜怒哀乐)只有对象化到合适的“客观关联物”上,才能使情成形,化生出意象,主体原生之情才能升华。其三,随意会状,景以情显,即通过具体的现象的描绘,激发出主体的创作之情,再以情生出新的审美意象,也就是说“情中景”乃是主体在进行审美活动对审美对象的再发现与重新建构,所谓“诗成珠玉在挥毫”(杜甫《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似乎是主体灵感在瞬时间地迸发,实则“写出才人翰墨淋漓,自心欣赏之景”(《姜斋诗话》),名为写情,实则景因情生,使人循其情而进其景。在诗作中,诗人灵感迸发时精神的昂扬和创造力的活跃,让诗人信笔挥洒、文如泉涌,无不构成一幅极富情趣的妙景。又如,王夫之在评杜甫《登岳阳楼》中的“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时,认为“尝试设身作杜陵,凭轩远望观,则心目中二语居然出现,此亦情中景也”(《姜斋诗话》),诗中通过一叶孤舟与病容憔悴的老者形成强烈的情感的落差,仿佛杜甫晚年孤独漂泊、穷困潦倒的窘况历历在目。
由此可知,情景相生的命题表明:第一,情和景是在双方的相互关系中生成的。客观世界并没有现成的作为艺术内容的景,主观心灵世界也没有现成的直接作为艺术内容的情。从客观的物到艺术的景,从日常的情到艺术的情,是一个复杂的转换过程,一个质的生成过程。这个过程,绝非照镜子式的再现或者直线式的表现。第二,情与景是共生的。在艺术创作中,作家不是先有了情,再去找景,也不是先发现了景,再去找情;不是先对情来一番提炼,再去转换景,也不是对景先来一番改造,再去注入情。情与景相互建构,相互激活,一同生长,一同发育。第三,情与景的生成就是审美意象的本体生成。情缘景而生,伴景而成,在生成过程中始终结合着景的感性形象,因而能超越内在封闭状态而升华为审美意象的主观因素。另一方面,景因情而生,缘情而成,在生成中始终包含着情的精神活力,因而能超越自然状态升华为审美意象的客观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