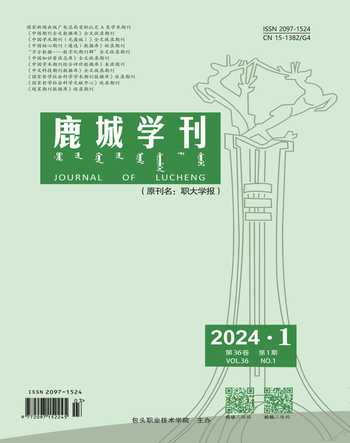“志”与“史”:《片警宝音》的现代性叙事与文化记忆
袁雨欣
摘 要:电影《片警宝音》以民族志式的、新历史主义的现代性叙事视角作为阐释工具,将当代中国时代风貌的影像民族志式书写酝酿其中,既保存了当代中国的文化记忆,又附和和补全了历史话语,对本土民俗和文化的保护和推广投入了关注。
关键词:《片警宝音》;民族志叙事;新历史主义;文化记忆
“Aspiration” and “History”:The modern narrationand cultural memory of the film “Patrolman Baoyin”
Yuan Yuxin
(Shandong University of Arts,Jinan 250307)
Abstract:In 2018,the film Patrolman Baoyin,jointly produced and produced by the Propaganda Department of the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Public Security Department of the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won the 18th China Film Huabei Award for Outstanding Ethnic Minority Films after five years.The film brews the image ethnographic writing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times,returns to the left place of national history,and makes up for the omissions,producing unique cultural memory.From the ethnographic and neo-historicist perspective of the modern narration of the film,and from the cultural memory of Asman back to the emotional reference of people in the film,the epic meaning of “ancient and modern drama” of Chinese national images can be analyzed.
Key words:Patrolman Baoyin;Ethnographic narration;New historicism;Cultural memory
位于中國西北部地区内蒙古乌拉特后旗的戈壁滩上,有一位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人民警察宝音德力格尔,管辖着1672平方公里的区域长达二十余年。守护边疆安全、几十余年扎根基层的宝音被评为一级英模,他的故事在2018年被改编为电影《片警宝音》。2023年5月,《片警宝音》获得第十八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奖。《片警宝音》静观丝路边境戈壁英雄的平凡事迹,采用一种显示当代中国时代风貌的影像民族志式书写方式,这种审视视野讲究对传统话语和历史的解构和颠覆,同新世纪以来打破文本局囿、重建物质与话语阐释的新历史主义不谋而合。民族志和新历史主义两种文学叙事的手段延用至影像不免使之获得了更新颖的阐释。如此重返历史遗落之处又补苴罅漏,生产着独到的文化记忆。因此,从电影《片警宝音》的现代性叙事——以民族志式的、新历史主义的视角作为阐释工具,中国民族影像“古今同戏”史诗之义得以剖析。
一、“志”——民族志叙事的影像策略
作为影视人类学的一种方法,民族志扮演的叙事功能更具科学性、整体性,从电影本体与影像历史双重溯源,中国民族影像和影视人类学并非一致却也相互调适,具有一定亲缘性。《片警宝音》之所以具有影像“民族志”式叙事的特征,首先因为这是一部非虚构性的反映民族地区事物的文本,能够展现民族地区的制度和风貌、仪式与文化;其次电影承载超越文字以外的阐释功能——“在视觉思维的基础上,对传统人类学较少涉猎的空间、情绪、感情、记忆、梦境、信仰等领域,进行更为细致、深入的探索与实践。”[1]《片警宝音》的故事被重建,产生时间和空间双重的修辞学,具有艺术的诗性和民族志“厚描”表现手法的文化深度。
(一)自然主义客观叙事
民族志的撰写过程在方法论上历经三个阶段,即“客观事实、文化事实及社会事实。”[2]非同于民族影视侧重艺术表达与民族仪式,影像民族志作为“文化反思与批评的手段,不直接涉及对电影工作者的创作历程的民族志考察,而是直接把完成后的电影作品视为文本,对其展开文本和表征分析”,[3]导演作为外来之人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即在文化相对主义中重组宝音的事迹完成影像书写,并为影像提供“存而不论”的原始视角。作为一部描写当代中国边疆公安干警工作实录的民族电影,《片警宝音》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下,以自然主义的客观视野只写“真”,不竭力渲染美和善的部分。尽管宝音本人是具有良好品格的、朴实的、至真至善至美的公安模范,但影片也未见着力刻画其品质的大写设计。
客观的看,宝音作为当地旗派出所的一名片警,工作所及事关民族地区群体的“现实”,故影像得以从宝音的第一人称出发进行阐述,揭示一段日常的、也饱含族群记忆的、地理和经济的状况与现实。例如乌拉特后旗这一地带水井数目众多却干涸缺水,北邻蒙古边境、位于内蒙西部的巴彦淖尔常年祈雨,在寻亲女孩和汉人媳妇李红来到后旗后天降大雨,以致本地牧民都欣喜地认为她们是带来幸运的人。学者范华提出影像的“性灵”,其“本质是‘真,‘真意味着尊重、相信异文化前提下达成的跨文化理解”,[4]宝音作为影像叙述中心,被电影制作者隐去“他者”视角、采用回归草原生存者的策略,是非阐释性的整体主义的民族志叙事手段。同时,导演杨瑾作为山西人,抱有对待异文化的能动的文化立场,持有开放的、学习的态度,并通过电影以还“真”的文化视角观照乌拉特后旗这片土地的生存机制,进而呈现出属于宝音家乡的、真实的文化整体。
(二)阐释意味文化叙事
格尔茨说:“我所追寻的是析解(explication),即分析解释表面上神秘莫测的社会表达。”[5]客观事实被遮蔽了,继而转向从社会生活中捕捉人的主体思考、阐述和意志。电影影像着力刻画的主体自始至终是人,并将表述的民族志经验生产于导演和真人宝音在影像之外的对话中,因为导演欲重塑和阅读的文化符号,本身来自于宝音这一亲历者的阐释和经验。同时,影片内部用汉族的媳妇,异乡女孩的寻亲两种情节作为潜文本,表述着对待异文化的书写,让不同文化主体站在既有的书写视角上注重多区间内文化类型的流动关联,以获得“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
电影描绘民族英模宝音德力格尔的事迹带有人本主义的倾向。文化一方面决定了人的思想意图,而被指导的文化意识也同样影响着既有文化和结构。因此参考人的行径、情感、行为也是侧面理解文化行为的途径。电影反映群像的不同忧虑及透过群像体现经济实况。镇上的牧民一边修车为生,一边还期冀拾到珍贵玛瑙以换个好价钱,工厂陆续来了新工人却仍然人力资源短缺,两位干警设路障查控的空暇都不舍得吸完一整支烟。出于一种书写者的研究视角,这些情节并非被成系统地、序列化地罗列出来,而是经过宝音抹去话语的叙述,完成了一种“‘非语言交流领域中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的捕捉与文化符号的主体性阐释”,[6]这是以一种实践的、人文的、经验主义的操演来呈现的,我们可以看到导演在自身和宝音之间构建起一个互通的、开放的阐释空间,这个空间搭建起宝音本人(文化持有者)绝对的话语能动性与主体自由。
此外,电影文本内几种人物主体互动关系得以民族志叙事化处理:汉族女孩李红和卓拉的到来使得宝音增加了新的工作对象,她们作为乌拉特草原的外来者同宝音在相同时空中构建出新的对话机制,并滋养出文化持有者与文化接受者之间“人化”的情感认知。卓拉入驻乌拉特后旗以后同宝音同吃同住,适应新环境并与继弟打成一片,李红作为汉族女人打井水吃蒙餐,换上蒙族服饰目送野生黄羊放生。卓拉在宝音和其母的追问中得以不断确认自己的身份——森格是自己的亲生父亲;李红也在丈夫追问“你看这里的树有什么感想?”和宝音“你是谁?”的哲学拷问中移情,肯定自己真正走进乌拉特后旗,在无垠和辽阔的疆域里成为了乌拉特的女人。
(三)书写事实社会叙事
社会民族志叙事被认为是知识社会学的“事实”,即进入一定社会关系中受意识形态和制度挟持的社会性事实。社会事实被蒙上更为浓烈的反思意味,即透过民族志书写,厘清文本肌理,以实现民族志的“自觉性和正当性”。[7]
当代民族志叙事尊重“真”,并将已经稳定的、得以传播的事实继续传承下去。但走到今天的知识社会学的事实,需要采取民族志修辞去再次整合一个独特的叙事系统,并对一切日常进行美学改写。在民族志的“写文化”中,后现代的民族志书写模式探索出隐喻的、超现实主义的文学化道路来。《片警宝音》中有这样一个情节,羊倌故意杀害了汉族女人,宝音从草垛中发现女人的尸体。从电影的叙事排列来看,羊倌一开始就作为草原上被追逐的人成为悬疑性的线索,而掉落的牙、对不上脸的假身份证,最终将矛头指向了“李红惨死——逃跑的羊倌”看似无关的两条线索上,这是小说型的文学叙事手法,一场谋杀案看似戏剧化但也是草原上真实发生的故事。宝音发现现场后,燃起篝火等待刑侦部门到来,电影中突然出现一幕灵异景观:死去多日的李红从草垛上站起来欲要离开,宝音大声喊道:“你不能走!”此时红蓝交辉的光闪起,大部队来了。电影从始至终采用的真实、旁观的拍摄在此转化为鬼魅神秘的诗性修辞。
电影隐晦地将蒙古族民俗穿插进叙事情节中,摒弃宏大的表达方式。宝音曾问萨满师傅:寺庙何时修缮好?师傅回应:该修好时便好了。蒙古族的偏方吃狼胃能治胃病,月牙形狼油是有福之人的独享。说蒙语的牧民们家家户户摆着成吉思汗像,镜头不做直摄和奇观处理却仍见痕迹。卓拉和斯钦结婚时的蒙族婚礼,长辈要用酒轻点新人印堂以表祝福。斯钦从那达慕比赛归来、森格的女儿摔跤夺冠后的意外……这些属于草原上独有的念词和仪式,这些独特的社会事件,为描述、总结、分析、解码影像提供资源,影像民族志再构蒙古民族生活,实现影像民族志对文学、社会等的互动。
二、“史”——新历史主义叙事的影像视角
新历史主义所提供的新视野,一方面为影像诠释历史记录的不足提供更多机遇,另一方面跳出历史以外的领地以诗学的修辞构筑人类行为的新支点——以对个体命运的关怀书写历史。
(一)写人的史学
《片警宝音》在叙事的脉络中遵循一个原则:扎根群众的工作必须要写“人”的故事。电影叙写是以宝音和草原群像为代表的“人”的叙事,新历史主义视野下的影视创作“把整齐划一的宏大历史撕裂,以喧嚣浮躁、日常世俗的动机和欲望贯穿始终,颠覆和消解了以往革命历史电影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本质的演绎”。[8]《片警宝音》如是塑造了片警宝音的工作日常,登记入户、巡逻、办低保、分羊羔、打水井、慰問老兵等,日常堆砌出的历史,其叙述源动力来自主动书写的个体“人”,并嵌入与“真实”并存的情感之史、内心之史。退伍的老兵独居守住土房,拒绝再盖,草原建设的见证者在时间洪流中失语,而历史的必然和个体的欲望成为重塑历史的新观。
(二)写地的史学
新历史主义者采用“厚描” 手法,将多个“小故事”组成“微观叙事”的新型文本。安德鲁·西格森阐释民族和电影的想象性关联时提出一种内向的路径,“把本土的电影与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或传统联系起来,赋予其独特的性质。”[9]一方面电影以宝音作为地区管理者的警察身份描绘了乌拉特后旗的地理状貌、经济问题、风土人情和民俗仪式,诸如电影开始的西部风土地貌全景俯瞰,全片叙述的西北干旱缺水但劳动力短缺的困境。另一方面,电影刻画乌拉特后旗友爱互助的民风、勤劳的牧民,记录独特的蒙古族婚礼仪式、萨满超度和放还野生羊的注目礼等桥段。这种民族影像的新历史主义叙事,具体体现为在宝音的主体视角下,边境守卫者将个人生命融入国家历史谱写的家国情感叙事。
三、结语
《片警宝音》通过影视“民族志”式书写,透过新历史主义的全景视角,既保存了当代中国的文化记忆,又附和和补全了历史话语,对本土民俗和文化的保护和推广投入了关注。民族影像的现代性叙事,不仅来自于叙事方式和分析视角的探幽索秘,更要关注电影核心文化、价值主义等内容在接受美学上能否起到人类学研究的终极作用——“求真”,能否通过“大人物小日常”的主题及新影像叙写方式,传达非理性历史的审判思维供大众面对艺术和历史的深度思考。
参考文献:
[1]朱靖江.田野灵光——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的历时性考察与理论研究[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4:25.
[2]李银兵,曹以达.民族志的三重叙事与实践反思[J].云南社会科学,2019,227(1):139-146.
[3]郑少雄.表征再造现实:四部藏地影片的人类学分析[J].电影艺术,2018(3):33-39.
[4]王新宇.赋权·深描·整合:影像民族志对异文化的阐释模型——以“鄂温克三部曲”为例[J].四川省干部函授学院学报,2022,94(4):84-89.
[5](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5.
[6]王新宇.赋权·深描·整合:影像民族志对异文化的阐释模型——以“鄂温克三部曲”为例[J].四川省干部函授学院学报,2022,94(4):84-89.
[7](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M].高丙中,吴晓黎,李霞等译.北京:商务印刷馆,2006:13.
[8]储双月.论中国电影的新历史主义叙事[J].内蒙古艺术学院学报,2022,71(1):74-79.
[9]张英进.民族、国家与跨地性:反思中国电影研究中的理论架构[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2 (3).
(责任编辑 吴乌英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