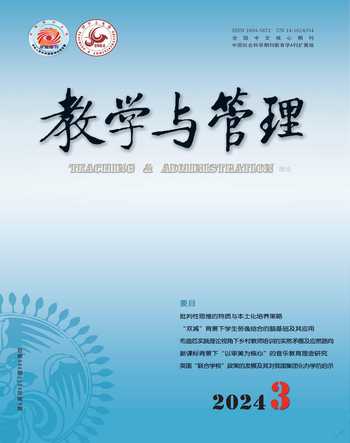多学科视角下中小学生学业负担的成因及治理
焦彦平 王娟

摘 要 双减”政策颁布,为学生过重学业负担的热现象进行了降温;中小学生学业负担,不仅仅是教育问题,也是社会其他方面的问题,解决这个复杂问题,仅依靠“双减”政策是不充分的。欲要“减负”,先知“重负”之故。影响中小学生学业负担的形成因素是复杂的,决定了不能单纯地依靠单一的或某一种理论审视其成因,而是需要将其置于文化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和教育学等多学科视角下理解,并提出针对性的纾解之策,实现对学业负担精准化治理。
关 键 词 双减”政策;中小学生;学业负担;精准化治理
引用格式 焦彦平,王娟.多学科视角下中小学生学业负担的成因及治理[J].教学与管理,2024(09):40-44.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为中小学生学业负担的热现象进行了降温。中小学生学业负担,不仅仅是教育问题,也是社会性问题,解决这个复杂问题,仅依靠“双减”政策是不充分的,需要弄清楚影响中小学生学业负担有哪些复杂的因素并针对性提出治理的策略。
一、中小学生学业负担成因的多学科审视
欲要“减负”,先知“重负”之故。影响中小学生学业负担形成因素的复杂性决定了不能依靠单一的或某一种理论审视其成因,而是需要将其置于文化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和教育学等多学科视角下理解。
1.文化学视角下“学而优则仕”与千年科举考试文化的濡化
中国古代教育,一直都是先有学,后有教。自孔子提倡“学而优则仕”开始,学习就成为了平民通向做官的途径,而学习成绩优良是做官的重要条件,所以“以学做官”成为仕进的一条重要途径,凸显了学的重要性。隋炀帝大业二年,始建进士科,标志着科举制度的正式确立。科举制是个人自愿报考,按科命题,以文艺才能为标准评定成绩,限量择优录取,以这种方式为国家选拔官员[1]。所以,科举制的确立强化了“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与此同时,学校作为培养人才的场域,为科举不断输送人才。随着科举制越来越受重视,成为“国家抡才之大典”;而学校教育受轻视,逐渐沦为科举的附庸,且学校培养目标、教育内容和试策方法亦迎合科举的需要。因而,科举考试文化经由学校场域濡化广大士子。那么科举是如何加重士子的学业负担?一方面,科举是一种高风险、高竞争性选拔考试[2]。科举的应考人数很多,而名额有限,通常进士科百人取一,明经也只有十人取一,竞争十分激烈[3]。据《唐代进士科举年表》统计,自622年至907年近300年间,进士科共开考262次,录取6656人,平均每榜不到26人[4]。为了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中获胜,广大士子只能选择夙兴夜寐的勤学和苦读,学习儒家经典,应试科举。另一方面,古代士子需经过科举的层层选拔,才可真正地登科及第,步入仕途,成为上层统治精英。如在明代,士子要历经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的层层考试和选拔,一环扣一环,一环也不能脱钩。想要在这么多环节中脱颖而出,平民中的士子只能给自己学业上压重担,故有“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的诗句。由此观之,科举制强化了“学而优则仕”,并使之逐步深入到古代士子的意识当中,而士子要想步入仕途之道,則需要参加科举考试,要想在科举中胜出,则需勤学和苦读经书。是故形成“勤学—读书—科举—做官”功利主义逻辑,且一直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并在人们的意识中继续发挥着作用。
2.社会学视角下文化资本获得及其代际传承和再生产的需要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中国社会分层越来越呈现出金字塔式的结构,一批文化和经济的中上层群体成长起来,并逐渐意识到无法定量化操作的文化资本及其“再生产”的重要性。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既包括语言表达能力和总体文化意识,也涵盖学校系统的知识以及教育文凭等资源。并指出文化资本分配的不平等使社会阶层在教育成就与文化消费模式上差异很大[5]。因而,上层精英凭借固有的文化资本和雄厚的经济资本,依靠家庭良好文化氛围潜移默化浸润子女,并投入大量金钱用于子女教育,以“继承”和“再生产”的方式将文化资本传递给子女。中间阶层为了使下一代能够向上层流动,对其来说,最值得信赖的投资是教育,为此,凭借已有经济资本,并在文化资本思想驱动下,给孩子报大量的补习班或请家教,提升孩子的学业水平,使其考取高水平的大学,以“再生产”的方式将文化遗产传递给子女,形成一条“教育投资——将经济资本转化成文化资本——得到更高水平的教育机会”隐蔽的再生产链条[6]。但布迪厄的文化资本及其“再生产”理论适用于中上阶层,对普通群体适用性不大。中国社会中普通群体占大多数,那么他们的子女遵循怎样的上升逻辑?有学者指出,由先赋性动力、道德化思维模式及学校化的心性品质所构成的底层文化资本,是底层子弟向上流动特有的文化资本,也是其学业取得高成就的密码[7]。概言之,无论是中上阶层还是普遍群体,都意识到文化资本成为子女向上流动的强大动力,而教育成为文化资本获得的最可靠方式。所以,家长将对教育的重视转化为有效的行动,即给孩子报大量的课外补习班,加重了孩子的学业负担。
3.经济学视角下人力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凸显与人力市场选才标准的改变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各种要素成为资本,尤其是人力资本成为最重要的要素之一。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的形成主要由个人在保健投资、教育投资、人力迁移投资和信息投资等方面的投资活动而实现[8]。在他看来,经济取得进步的根本原因是对人和知识进行投资[9]。而学校教育是培养人力资源和积累人力资本最重要的因素。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学校教育不是一种纯消费行为,而是一项质量投资。社会和个人接受教育所付出的各项成本,都是为了获得一种可提供未来收益的生产性成本。这些收益包括未来的工资收入、未来的自我雇用和家务活动能力以及未来在消费方面的满足感。加之,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到来,高学历的劳动者也愈来愈多,使雇主更多地将文凭作为筛选求职者的过滤器。这种选才和用人标准,助长了人们对获取高学历的期望与需求。所以在市场经济以及人力资本思想强势影响下,人们也愈来愈意识到教育以及教育投资的重要性。为了使孩子能在社会中脱颖而出,取得较高的社会地位,一方面,家长加大教育投资力度,借助“影子教育”,让孩子获得更多的知识,取得更高的学业成就。另一方面,剥夺孩子课堂外的自由时间,延长孩子学习时间,给孩子的学业增负。
4.管理学视角下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平衡与区域内优质教育竞争内卷化程度增加
我国在不断推进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义务教育也进入了“后普及化”阶段,“拥有公平的优质教育资源成为人们的新追求”[10]。但现阶段我国的优质教育资源呈现分布不平衡及区域内教育内卷化的趋势,优质教育资源的短缺与人们对优质教育需求越来越高的矛盾成为突出的教育问题和社会问题。从历史的向度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受国家总体经济水平较低的国情制约,国家将有限的教育经费投入到对国民经济起直接作用的高等教育,形成“高中心”教育发展逻辑[11],忽视了对基础教育的投入,造成基础教育在经费、师资和设施等方面先天性不足。此外,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是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受工具理性主义的裹挟,为了使有限的教育资源得到最大化利用,在区域内设置重点中小学校,服务经济社会的发展。之后,随着公民教育权利意识的增强,发现重点学校加剧了教育的不公平。继而,国家用示范学校取代重点学校,实质还是重点学校的翻版。加之,由于东部地区和城市经济水平高于中西部和乡村,经济越好对教育的反哺作用越大,所以东部地区和城市聚集了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上述这些因素,使我国的基础教育阶段的优质教育资源呈现出区域、城乡和校际间的不平衡。虽然区域、城乡和校际间都存在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平衡的现象,但人们更加关注区域内校际间的优质教育资源。与薄弱学校相比,重点学校在财力、人力和文化资源都占有绝对的优势。为了孩子获得更优质的教育,家长不惜血本瞄准本区域内的重点学校,付出更多时间及金钱等成本,争取这些优质教育资源,造成区域内优质教育资源竞争的内卷化。所以,在内卷化裹挟下,父母将这种期望投射到孩子的身上,为了使孩子能上重点学校,让孩子淹没在做海量作业的题海战术之中,增加了学生的学业负担。
5.教育学视角下确定性知识对学生规训与“唯分数”评价加强
受工具理性主义的裹挟,大部分学校从“升学”“锦标”工具性目的出发,在知识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将中小学生当作“小大人”,将其视为“是其所是”的存在者,以预设的成人为标准,不考虑其最近发展区,将其视为知识的接收容器,用确定性知识规训学生,注重“是”的教育——侧重事实和知识获得,忽视“应该”的教育——漠视价值和道德培养。这是一种僵化的记忆性知识传授,仅是为了帮助学生获取高分数,加重了在智育方面的负担,扼杀了学生的创造性和超越性向度,使其成为“单向度的人”,放逐了“成人”作为教育之终极目的。加之,在学校“唯分数”评价观念驱动下,教师总是以超前或超纲形式对学生进行培训,一定程度上与循序渐进的教授方式相脱轨[12],致使学生的学业负担日益加重。黑格尔指出,精神一旦为空疏浅薄的意见所占据,理性便不能追寻它自身的目的,因而没有活动的余地[13]。这些繁重学业负担,挤压甚至侵占学生兴趣和特长的发展空间,忽视学生的情感以及其他各育,阻碍了学生德性、理性和情感的具身和全面发展,致使学生的精神世界没有活动的余地。
二、多学科视角下中小学生学业负担的治理之策
从上述以多学科视角分析中小学生学业负担成因来看,影响中小学生学业负担形成因素是复杂的,不能依靠单一策略对其进行治理,而需要將家庭、学校、企业、政府作为治理的主体,并在多学科关照下提出针对性的治理之策,实现学业负担精准化治理。
在中小学生学业负担治理过程中,对不同治理主体采取的治理方式及其承担责任是不同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历经“教改式”和“清单式”减负[14]之实际效果不太理想,原因在于各治理主体缺少主动承担治理减负责任的自觉性,存在着各治理主体责任不明确,主体间各自为政且互动性较弱的封闭局面。为了实现学业负担精准治理,关键在于各治理主体要有一种责任自觉,明确应承担的责任,加强各治理主体间相互协作,形成家庭、学校、社会和政府四方主体协同治理的合力。各治理主体的责任明确之后,还应注意不同学科视角隐喻着各治理主体所承担责任和采取治理方式也不尽相同。具体治理学业负担的机制如图1。
1.文化学视域下破除“学而优则仕”观念影响,树立新的家庭教育观和孩子成长观
与古代社会相比,虽然现代社会文明程度已相当高,对人与教育的认识以及教育理念也更理性化,但由于我国几千年考试文化观念逐渐积淀成了一种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对现在的社会生活仍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是造成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重要因素之一。
破除这种影响的关键,在于家长要树立新的家庭教育观和孩子成长观。首先,家长要弄清家庭教育不同于学校教育。与专门进行知识、方法和技能传授的学校相比,家庭教育将生活和养成教育作为主要内容。生活教育侧重于让孩子置身于日常生活的场域中,接触和观察所处的环境,建构日常生活经验及其图式,形成初步的生活图景。养成教育重点在于家长的亲自示范或言传身教,并给孩子设立家风须知,让孩子知道应该或不应该做什么,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达到积浸而养成之效果。其次,家长要主动和自觉地扭转教育“剧场效应”,避免家庭教育盲从性。在教育“剧场效应”的影响下,为了让孩子实现赶超甚至领跑,大部分家长出现盲目从众的现象,导致教育领域出现严重的内卷,孩子的学业负担亦被无限加重。面对这种不利影响,家长要跳出“剧场效应”的辐射范围圈,认识教育“剧场效应”的危害,主动地形成一种公共自觉,不做教育“剧场效应”的制造者和从众者,关注孩子成长的阶段性和关键期,注重孩子在学习上的循序渐进,让孩子的身心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最后,家长要注重孩子的具身发展。家长不仅要关注孩子的身心发展,更要注重其精神发展,关照其精神世界。家长给孩子学业增负,虽可能暂时使孩子学习上取得高成就,但从长远看,这既损害了孩子的身心健康,更可能造成其精神世界的不完满。
虽然家庭在破除传统教育观念对学生学业负担影响上发挥着主力作用,但也不可忽视政府和学校的辅助作用。政府应借助“互联网+”和新兴自媒体在全社会营造一种新教育观念氛围,以润物细无声方式助推家长形成新的家庭教育观;政府还应将那些以新家庭教育观为指导帮助孩子成才的家庭作为典型榜样,发挥榜样示范带动作用。学校亦应该与家庭建立一种家校合作模式,助推家长转变根深蒂固的旧家庭教育观念,使家长能够更科学、更高效营造一种利于孩子全面和谐发展的家庭氛围。
2.社会学视域下普通群体依靠自身和外部力量,弥补文化资本的不足
在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方面,普通群体与上层精英和中间阶层存在巨大的鸿沟,导致普通群体子女学业负担更重。那么,普通群体应如何弥合上述出现的鸿沟?一方面,普通群体依靠自身力量,积累“具体化”家庭文化资本。在普通群体家庭中,由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低,所以在短时间内很难提高“体制化”家庭文化资本,但可以借助由家庭文化习惯和家庭文化期待构成的“具体化”的家庭文化资本,助力孩子的发展。具言之,在孩子成长的早期,普通群体父母应提供和营造好的家庭文化习惯、合理的教育期待、高质量的亲子互动;既要关注孩子的智力发展,也要培养孩子意志、兴趣等非智力因素。另一方面,普通群体借助外在的力量,弥补文化资本不足。各中小学校作为实施教育的主要场域,也要关注那些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相对较弱的学生,在人格上尊重他们、在情感上关爱他们,弥补其家庭文化资本不足,并在学业上帮助他们,减轻他們过重学业负担。同时,国家和社会在教育政策和教育资源方面,应更多地向普通群体孩子倾斜,尽量解决普通群体因经济资本不足导致教育资源短缺的问题。
3.经济学视域下社会应改变选才和用人标准,实现学生在就业上相对公平
鉴于市场经济以及人力资本思想强势影响,企业愈来愈重视人才,将唯文凭和唯名校作为选才首要标准。如何超越根深蒂固的传统选才标准,实现学生在就业上的相对公平,成为现代企业服务社会的重要使命。企业要适应经济供给侧改革的需求,注重提升创新水平能力,实现产品从量向质的跃迁。基于此,企业要变唯文凭和唯名校为唯能力和唯综合素质的选才与用人标准。具言之,在选人和用人时,企业应处理好分数与能力、显性知识与默会知识、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这三对关系。首先,企业要破除“分数=能力”这种根深蒂固的选人思维模式。不可否认,分数高意味着学习能力强,但学习能力仅仅是能力的一种,而非全部。所以,企业以分数或文凭选才是一种片面的、单一的选人标准,忽视了被选人的社会交往、工作进取心、事业忠诚度等能力。其次,在选才时,企业还应识别被选人的显性知识与默会知识。显性知识是完全能够用语言表达的知识,具有普遍性、传递性和可交流性;默会知识作为一种个人知识,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具有很强的情境性和实践操作性[15]。默会知识之于企业是很重要的,在面对市场中各种复杂的因素时,拥有缄默知识的人,可以克服信息不充分缺陷而迅速作出正确地判断,为企业发展带来效益。最后,在选人时,企业还应关注被选人的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人的智力因素主要包括感知、记忆、想象和思维等;非智力因素主要包括注意、兴趣、动机、性格、意志等[16]。人的非智力因素之于企业是不可或缺的。在工作中,员工的坚韧性和对工作浓厚的兴趣等非智力因素,对企业发展有着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因此,在选才时,企业应处理好以上三对关系,实现唯能力和唯综合素质的选才和用人标准,实现学生就业的相对公平。这种新选才观念作为一条传导链改变家长和学生就业理念,进而减轻家长和孩子因企业将学历和文凭作为筛选求职者的过滤器所造成的学业焦虑。
与此同时,政府应稳健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引导企业更多地吸纳接收职业教育的学生,并对该类企业提供更多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助推企业进一步打破根深蒂固唯文凭和唯名校的传统选才标准,从根本上扭转企业对职业教育的刻板和偏见认识,使得职业院校毕业学生也能获得社会、市场认可与青睐,缓解学生因高考竞争而不得不被过重学业负担所役使之问题。
4.管理学视域下政府应发挥教育政策工具效用,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发展
鉴于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平衡及其导致的教育竞争内卷化,政府应主动担当起对教育负宏观管理的责任,依据英格拉姆与施耐德的政策工具分类原理[17],充分发挥教育政策工具效用,促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均衡发展。第一,无论是省域还是县域政府相关部门,运用行政手段调整“越好的中小学校,集聚更多优质资源”的市场行为,对民办中小学实施严格的准入标准,健全“名校”校长和教师的轮岗机制,发挥权威工具在改变优质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衡的局面中的作用。第二,各级政府对那些主动从东部和城市地区到中西部和农村地区的中小学校的领导以及老师,给予更高的物质待遇和相应社会荣誉,对其中有突出贡献的,给予专门的奖励,运用激励工具促进薄弱中小学校发展。第三,各级政府将政策文本提出的提高义务教育质量和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发展的目的,通过引导、整合和认同策略,让“名校”增强承担更多责任的意识,利用集团化办学或与薄弱学校联合办学,扩散和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发挥符号和规劝工具的效用。第四,各级政府加强对薄弱中小学校在基础设施、专项资金、师资培训和教育信息化服务公共供给上的投入、扶持,发挥能力工具在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发展上的作用。第五,各级政府要下放权力,扩大薄弱中小学校办学自主权,并让其参与到教育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决策过程中,彰显学习工具的价值。
5教育学视域下学校要加强自身的内修,助推学生全面发展
学校作为培养学生的主要场域,在落实“双减”政策和减轻学生过重学业负担上,要加强自身的内修,发挥排头兵和主渠道的作用。一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做到应教尽教,实现学生的具身发展。教师应走出“时间+汗水”的教学路径依赖,充分利用课堂给定的时间,向课堂教学要质量。教师既要将知识体系中关键知识点和关键环节作为应教的范围,也要将学生在掌握知识同时并培养其核心素养作为尽教之则,并潜移默化地浸润学生的品德,使课堂不再聚焦于记忆性知识传授,把学生从确定性知识的规训中解放出来。二是加强作业的精选和设计,科学认识作业的价值定位。学生做的每一道作业,既是基于课程标准关于学科教育教学目标要求而设计的,也是嵌入学生的学科知识结构与学生学科前置知识的巩固和学科后续知识的发展相关联的。好的作业设计要以能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更能完善学生学科知识结构、情感结构和社会经验结构为标准,设计出有思维性、探索空间的好作业。三是全面改革学生评价。教育评价的本质是鼓励学生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提高自己学业水平并实现超越自我。由于每个学生的学习与发展速度是有差异的,不能要求所有的同学在同一时间达到同样的水平。为了让学生不掉队,教育评价应尊重学生个性差异,坚持分类的原则,用多个标准和多次评价对学生进行综合性评价,让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实现增值。由于以上措施,学生的课外时间就不会被侵占,学业负担自然就减轻了,也就不必求助于校外机构补不足。
总之,在推进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针对中小学校过重学业负担,“双减”政策颁布,无疑是一剂猛药,但其有一定的限度。为了深入推进“减负”,需从多学科的角度思考过重学业负担的成因并提出纾解之策,实现对学业负担的精准化治理。
参考文献
[1][3]孙培青,杜成宪.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76,180.
[2] 刘海峰.科举停废110年祭[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5):83-91.
[4] 刘海峰,李兵.中国科举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432-444.
[5] 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M].陶东凤,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228.
[6] 朱伟珏.“资本”的一种非经济学解读——布迪厄“文化资本”概念[J].社会科学,2005(06):117-123.
[7] 程猛,康永久.“物或損之而益”——关于底层文化资本的另一种言说[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6,37(04):83-91.
[8] SCHULTZ,T W.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J]. American Econ-omicReview,1961(01):1-17.
[9] 西奥多·舒尔茨.对人进行投资:人口质量经济学[M].吴珠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1.
[10] 郑石明,邬智.迈向有质量的公平:中国教育公平政策变迁与转型逻辑[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8(05):29-37.
[11] 张旸.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减负背后的供需困境与化解[J].中国教育学刊,2021(09):27-32.
[12] 余晖.“双减”时代基础教育的公共性回归与公平性隐忧[J].南京社会科学,2021(12):145-153.
[13] 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32.
[14] 龙宝新.中小学学业负担的增生机理与根治之道——兼论“双减”政策的限度与增能[J]. 南京社会科学,2021(10):146-155.
[15] 郝文武.教育哲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125.
[16] 李洪玉,阴国恩.中小学生学业成就与非智力因素的相关研究[J].心理科学,1997,20(05):423-427+480.
[17] SCHNEIDER A,INGRAM H. Behavioural assumptions of policy tools[J].The Journal of Politics,1990(02):510-529.
[作者:焦彦平(1993-),男,山西朔州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王娟(1996-),女,山西太原人,山西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助理研究员,硕士。]
【责任编辑 杨 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