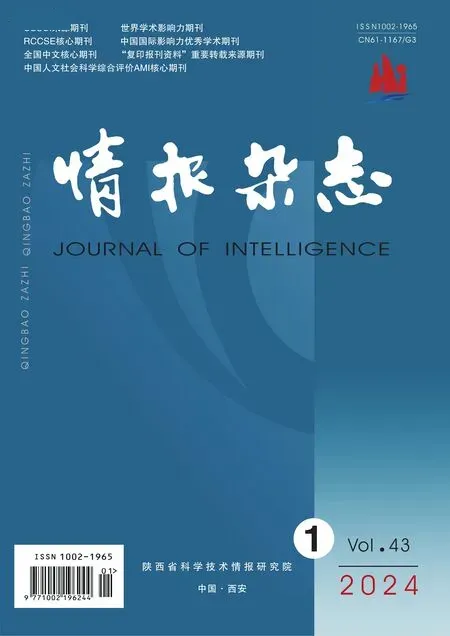情报公开的决策动机、潜在矛盾与战略启示
刘文龙 李 兵
(1.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100029;2.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北京 100007)
0 引 言
当前,伴随着全球进入数字信息时代,信息的快速传播正在打破传统情报秘密化的形态,情报公开成为各国战略竞争的新方式。2022年2月11日,美国突然向媒体公布,俄罗斯将于2月16日向乌克兰出兵。消息一出,立刻震惊全球,不仅使各国安全部门神经紧绷、媒体界一片哗然,同时也使各国民众躁动不安、恐慌情绪与日俱增。
事实上,情报公开早已不是鲜有之事。早在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向美国媒体公布了“齐默尔曼电报(Zimmermann Telegram)”。这份电报是当时德国外交部长齐默尔曼(Zimmermann)向德国驻墨西哥大使发的一份绝密电报,其目的是试图联合墨西哥向美国发起战争。然而,该电报被英国截获并转交美国,最终促使美国放弃中立、选择参战[1]。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爆发,美国得知情报后经过审慎考虑,决定通过广播的形式向全美民众宣布苏联在古巴建立导弹发射场的事实,之后以围守古巴的方式与苏联达成协定,最终解除了危机。再如,近几年以色列持续向媒体公布秘密情报,如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部署地图、伊朗德黑兰的秘密原子弹仓库照片、伊朗核档案材料等[2]。随着各国竞争和冲突加剧,国家将秘密情报公开的现象逐渐增多;尤其在当前数字信息环境下,情报已经不再局限于秘密决策这种最基本的情报目的,各国情报公开逐渐成为一种趋势。
然而,国家为什么会选择公开秘密情报?为什么在当前数字信息时代情报公开会愈加频繁?自有情报工作以来,情报一直都是以保密为主。情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做出精准的决策、部署有效的行动以及给敌人最致命的打击;一旦情报公开,对方已经知道我方获取的信息,或许会改变行动方针,反而会使我方陷入被动。但是,现实是秘密情报却在被反方向使用,情报公开成为了情报发展和应用的新方向。那么,情报公开的目的是什么?将带来哪些战略收益?产生哪些矛盾?寻求从情报秘密化向情报公开化的转变原因,将对我国的情报发展产生一定的启示。
1 情报公开的决策动机
所谓情报公开,又称“官方公共情报披露(Official Public intelligence disclosure, OPID)”[3],主要是指以政府官方为主体的情报公开行为。其与信息公开(Information discourse)既有一定的联系也有相应的区别。一方面,信息公开和情报公开都是将部分选中的信息对外界进行公开或者重点强调,试图对外界环境和民众认知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信息公开是将部分未经加工、未公开的信息在特定情形下进行对外公布。而情报公开则是将所获取的有价值的情报知识,经过多种因素的综合考量之后所进行的对外公开。相比于情报而言,信息的范围较广[4],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信息公开包含情报公开。同时,情报公开的内容并非全部情报,而只是适合公开的情报信息,只占全部情报的一部分。简言之,情报公开是专有信息的公开,是决策部门进行情报分析和严密决策之后,将部分情报作为一种对外工具,甚至将情报武器化的行为。
1.1 利益竞取之中的主动公开
1.1.1情报公开是一国实施战略威慑的手段
有学者指出,情报公开既有威慑策略也有威逼策略,威慑策略即告知对方我方已经获取相关行动信息,并可能采取对应行动,迫使对方审慎决策行动计划;威逼策略是指对手已经通过行动造成了一定的行动事实,通过非战争的手段迫使对方放弃所取得的行动成果,并退回到行动前的状态[5]。在国际政治领域,战略威慑既有单个国家发出的个体威慑,也存在多个国家共同组成的集体威慑,而情报公开则是战略威慑的一种,既产生个体威慑效果,也具有集体威慑效应。一方面,当单个国家进行相应的情报公开时,该国家的实力以及接下来可能采取的行动将会对对手产生一定的威慑作用,对手将不得不仔细考虑接下来的行动后果以避免利益损失[6]。另一方面,情报公开也会唤起多个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关注,形成集体威慑。尤其在当前数字信息环境中,情报公开具有轰动效应和聚焦能力,在各路媒体助力下,情报公开不仅会使对手面临行动暴露的风险,同时也会迅速引起各国的协同响应,迫使对手面临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7]。例如,在2022年俄乌冲突之前,美国、英国以及欧盟国家持续关注乌克兰局势,这些国家先后向媒体透露相关秘密情报,多国情报协同公开引发了全球民众对乌克兰危机的关注,同时也推动西方各国后续的合作进程[8-9]。
1.1.2情报公开有助于增强本国的战略叙事
所谓战略叙事,实质上是指,国家为动员民众、调动资源以及获取支持而采取的有利于本国利益的“话语武器”[10]。战略叙事可分为合作性叙事和竞争性叙事,合作性叙事是指在特定时期为促进国家间合作而构建的友好型叙事方式,而竞争性叙事则是国家间在竞争或冲突的环境下为维护本国利益、打击竞争对手而构建的身份、情感两方面都对立的行为手段[11]。显然,情报公开主要是一种竞争性叙事手段。在国际竞争环境下,国家往往以“公平、正义、和平、安全”等国际社会最根本的发展秩序为旗帜,通过情报公开的方式揭露他者违反国际秩序的“种种恶行”,丑化他国形象,为本国的对外行动提供合法性支持。例如,2018年,美国、英国、法国认为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一个科研中心藏有大规模杀伤性化学武器,此消息一出立即引来民众的大量关注。随后,美、英、法对叙利亚展开大规模空袭行动[12]。再如,在俄乌冲突中,西方国家采用竞争性战略叙事将俄罗斯塑造成损害国际秩序、破坏和平的“入侵者”形象。随之美国联合西方国家决定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支持[13]。
1.1.3情报公开有助于获取政治支持和推动政策通过
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国家政治发展的基石,无论何时,民众的声音和支持率都会对政治决策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当一国政府进行决策时,寻求民众支持是获取政治行为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尤其在关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等重大战略行动面前,将关键情报公之于众能提供相应证据和论点,不仅能够力排众议、解决党派斗争、为政治立场辩护,同时也能够提高政府行为透明度、增加民意支持率、增强决策信心。例如,在美苏冷战期间,伴随着苏联导弹战略威慑能力的提升,尼克松政府想采取与之相匹敌的战略武器发展计划,但国会内部各种声音难以调和、政策难以推行;为此,尼克松政府有选择地披露关于苏联SS-9导弹的最新遥感数据,同时还命令其国防部长公布苏联相关战略武器的部署进程,最终在相关情报披露下,美国国会迅速通过战略防御行动计划[14]。
红土镍矿主要分为褐铁矿型和硅镁镍矿型两种。褐铁矿类型红土镍矿组成特点是:含Fe较高,一般40%~50%,MgO 0~5% , SiO2 10%~30%;硅镁镍矿型红土镍矿组成特点是:含Fe较低,一般15%~30%,含MgO 15%~35%,SiO2 10%~30%。采用还原熔炼工艺后,由于该法属于熔池熔炼,可通过改变炉内的还原氛围实现镍铁的选择性还原性。由于金属镍熔点为1 450 ℃,冶炼熔渣温度必须在该温度以上。
1.1.4情报公开成为竞夺舆论话语权的有效工具
纵观历史,任何一场国际冲突爆发之前都会弥漫着难辨真伪的信息,冲突各方会通过各种方式散布信息来混淆民众视听。尤其在当前数字信息时代,大数据的高速化、海量性等特征更是为各类信息传播提供了生存空间,冲突各方能够采用数字水军、社交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如ChatGPT)等方式在贯通全球的社交网络中散布虚假信息。当网络中充斥着大量各种样式的信息时,国际舆论场也成为了国家间战略竞争的一部分。在此背景下,情报主体可以选择采取情报公开的方式攻击他国的舆论势力、打乱他国的舆论计划、制造舆论混乱,以便掌控舆论高地[15]。在传统认知中,情报往往被民众认为是用于机密决策的重要信息,因此,情报的秘密性和权威性能够引起民众的信任。面对嘈杂混乱的信息环境,以政府为代表的权威机构进行情报公开成为拨开舆论迷雾、获取舆论话语权的关键手段。例如,在俄乌冲突中,美国为取得舆论场的竞争优势,试图通过情报公开的方式攻击俄罗斯的行为;拜登曾对此指出:“我们对世界保持透明,我们已经分享了俄罗斯的行动计划和网络攻击的解密证据,这样就能将真相大白于世界”[16]。
1.1.5情报公开是一种战略敲诈的手段
由于各国都关注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力,因此,国际社会成为一种遏制他国非法行为、维护国际秩序的有效力量。在当前数字网络环境下,个体民众能够在数字空间中自由发声,大幅增加了国际社会对国家行为的制约能力。为实现国家利益和推动国际社会对他国行为施加压力,情报主体也会将情报作为战略敲诈的手段,通过情报公开来主导国际社会,不仅会影响民众的认知和国际社会的压力走向,同时也会损害对手的国际形象,使其疲于应付。例如,2020年9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在联合国公开展示黎巴嫩首都的地图,指出黎巴嫩真主党在贝鲁特国际机场附近的一个工厂是秘密武器库,并强调这将在黎巴嫩首都引发一场灾难性爆炸;随后以色列国防军又公布了两个位于贝鲁特的由黎巴嫩真主党用来制造精准制导导弹零件的地点[17]。此事一出,引来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谴责,真主党为了应对以色列公开的情报舆论,被迫宣称将立刻邀请国际记者前来调查,而调查结果却是该工厂仅仅是一个拥有重型机械的小工厂,并没有武器装备生产和储备[18]。
1.2 压力传导之下的被迫公开
1.2.1情报公开是政府部门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
情报生产、情报监管及情报使用在一般情况下分属三个部门。情报生产部门负责客观情报的收集和生产,为政府决策部门提供及时有效的情报支持服务;情报监管部门负责情报的统筹管理,防止情报泄密,维持国家情报的安全;而情报使用部门主要是决策部门,利用情报进行战略制定等行为。在常态下,情报生产、监管和使用是一个贯通的流程,但情报使用部门却能有意推动情报公开、迫使情报政治化[19]。例如,2002年12月美国小布什总统看到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约翰·麦克劳克林(John E. McLaughlin)提交的关于伊拉克相对客观的情报时,心生不满;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尼特(George Tenet)为了迎合政府的需要而承诺将解密一部分情报使政府的政策更具说服力[14]。而根据后来解密的资料来看,美国和英国早在2002年就已基本达成出兵伊拉克的共识,最关键的是需要寻找一个合适的出兵理由[20]。也就是说,情报生产、情报监管和情报使用之间存在各政府部门的相互博弈,当支持情报公开的利益团体取得优势,要求将部分情报进行公开,那么情报公开将成为国家对外利益竞取的一项工具。
1.2.2情报公开是媒体问责和信息快速流动的压力所致
信息秘密化是情报工作的基本要求,然而,伴随着信息的快速传播,媒体问责助推着部分秘密情报走向公开。例如,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事件发生时,世界各国的信息传输还都以固定电话、广播、电报为主要的传播形式;从美国发现古巴正在建设导弹发射场,到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通过广播向全美发表讲话,通告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事实,再到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中间历经了13天的时间。2001年美国“9·11”事件,当时全球互联网和移动电话正在大规模建设中,电视广播已经普及;从美国遭遇袭击,到美国总统小布什审查遇袭相关情报并向公众做出回应,中间用了十几个小时的时间[21]。而如今,全球深度交融,在各种官方媒体、自媒体等主体的作用下,任何一个地方发生危机事态,几秒钟之内就会人尽皆知。正如当前俄乌冲突,在全球媒体注视下,世界几乎在实时关注着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一举一动。媒体为揭露事态真相、迎合公众对关键信息的需求,将不断向政府部门和情报机构施压,最终将迫使官方部门解密部分情报来应对媒体问责。
1.2.3情报公开是社会民众和利益集团的安全需求所致
国家情报收集和应用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同时也是为了维护社会利益。伴随着民众认知水平提高,危机信息在数字技术的作用下,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社会民众对危机更加敏感,对安全信息的需求逐步增加。与此同时,国家安全与公司发展、资本投资、科技创新、社会民众等各种利益集团的交集逐步加深,当网络上某一突发事件兴起,舆论的广泛传播不仅会影响公司的产品销售、股价波动、战略决策,同时也会引起社会民众的恐慌情绪,最终可能导致公司撤资、公民逃离、跨国旅游下降、投资锐减、经营决策失误等一系列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充分且及时的情报公开成为稳定社会情绪的主要方式,有助于应对社会民众和各种利益集团的问责压力、维持政府合法性,同时也能够建立政府和民众以及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信任关系,维持社会稳定。
总而言之,情报公开既是情报主体的主动利益竞取行为,也是社会各种压力传导、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结果。官方情报关系到国家安全、政治利益和情报的可持续发展,公开披露情报并非轻举之事,任何一项官方情报公开都是情报主体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相互权衡之后才做出的决定。
2 情报公开的潜在矛盾
事实上,情报公开的潜在矛盾也不容忽视,尤其在数字网络的放大效应下,情报公开的负面影响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2.1 情报公开与威慑失败之间的矛盾
情报公开是情报主体试图采用较低的成本威慑对手、迫使对手改变行动的方式,但也存在威慑失败的问题。事实上,情报公开相比于军事威慑、经济制裁等强威慑,是一种弱威慑形式,而弱威慑存在失败的可能性会更高。国际社会具有无政府性,虽然当前已经存在各种国际制度规制着各国行为,但国家间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仍然遵循着丛林法则,当情报主体无法威慑到对手,情报公开的意义也将大打折扣。尤其在对手下定决心的情况下,情报公开这种弱威慑形式将无法遏制对手的行为。另外,情报公开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被视为一种默认行为,表明情报主体不愿意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威慑对手,而只是采用情报公开的方式表明态度;否则,如果情报主体决心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其在情报使用上则会更加隐秘且谨慎[22]。
2.2 情报内容失误和情报权威受损之间的矛盾
如今,网络开源信息成为各国情报获取的重要来源,然而,网络数据的海量性和多样化也参杂着大量人为捏造的虚假信息,使数据的可靠性降低。一方面,在匿名的网络环境中,没有标注出处的信息远远大于具有可靠来源的信息,尤其在深度伪造、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作用下,通过对音频、、视频、图片的深度合成,被捏造的数据足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在此背景下,情报信息收集就面临着真假难辨的困境;再加上网络信息传播速度加快、情报分析时间缩短,因虚假信息而造成情报失误的可能性将会极大增加。另一方面,伴随着情报政治化发展,在政府决策部门自上而下的压力和情报部门自下而上的迎合下,捏造事实、篡改数据等失去客观性和真实性的虚假情报生产一直甚嚣尘上。例如,美国历史上曾经发起的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战争,其在战争之前都会通过加工符合军事行动目的的情报来寻求对外行动的合法性和正义性[23]。在此背景下,当情报内容失误,情报部门往往成为首要问责对象,情报权威性将会极大受损[24]。
2.3 情报公开的轰动性和情报网络被破坏之间的矛盾
众所周知,情报获取具有多种形式,除了当前较为流行的开源情报获取之外,内部渗透、实地探查、秘密监听等传统情报获取方式依然发挥作用。开源情报模式和传统情报模式共同构成了当前各国的情报网络,而一旦将情报公开,对手将会迅速排查信息泄漏的节点。如果是技术漏洞或者技术落后而导致的情报泄漏,对手将会加快弥补技术缺陷、提高技术能力,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情报主体和对手之间的情报技术差距;而如果是参与决策的人员泄密,那么渗透到内部的情报人员将会面临生命危险[24]。也就是说,无论是何种方式的情报公开,其都有可能破坏经过长期构建和维护的情报网络,影响情报的持续获取。例如,“棱镜计划(PRISM)”是美国国家安全局自2007年开始面向世界,监听全球个人数据、文件传输、通讯交流、网络日志等内容的绝密窃听计划,2013年被美国前中情局职员斯诺登(Edward Snowden)揭露曝光。这虽然不是官方主动的情报公开,但也使美国部分情报网络和运营方式暴露于公众。该事件不仅引起了各国的极大反对,同时各国也逐步加强了反情报、反监听的能力。
最后,情报公开的社会需求与情报公开引起恐慌之间的矛盾。众所周知,社会具有多层次性,不同人群的认知水平、安全承受阈值、危机感知能力都存在较大差异,而当一份情报获取之后,决定是否公开应该以国家战略需求为中心,还是应当以民众需求和社会稳定为中心?应当以高知群体为中心还是应当以普通民众为中心?这些在情报公开之前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如前文所述,情报公开的其中一个外在原因是民众的社会需求,尤其在信息快速传播的数字时代,情报公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民众的恐慌情绪,维护社会稳定,但是当情报公开后,虽然缓和了一部分人的安全焦虑,是否会引起另外层次人群的恐慌情绪?情报公开本身是否会成为挑起舆论争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换句话说,由于目标群体的接受程度存在差异,情报公开的内容和表述方式都将对社会稳定产生影响,情报公开可能会引起社会的次生恐慌[24]。
3 情报公开的战略启示
在当前数字信息时代,面对情报工作的新变局,将情报公开作为国家维护安全、保持稳定、对外竞争的一种方式,逐渐受到各国的青睐。为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推进我国情报事业的发展,我国应当从以下方面合理考虑情报公开的行为。
第一,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情报公开进行系统顶层设计和规范操作流程。秘密情报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维护国家安全,离不开情报的支撑[25]。在进行情报公开之前,需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思想框架下考虑情报安全、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应当做到情报公开与国家利益、国家安全之间的协调统一,至少情报公开不能威胁到国家安全。当然,伴随着时代的发展,情报公开逐渐成为一种趋势,不能因固守国家安全而失去将情报公开作为获取国家利益工具的机会。因此,国家可以积极考虑情报公开的效用,制定相应的情报审查流程和规范,以及在特殊情况下的情报审批和决策应急模式,在维护国家安全的情况下,推动部分情报走向公开化。
第二,全盘统筹战略行动计划,推动情报威慑效用最大化。如前文所述,相比于军事威慑和经济制裁,情报威慑是一项低成本的信息威慑行为。在全球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双边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较小,情报威慑可能因无法触及对方核心利益而面临威慑失败的窘境。然而,在当前“混合战争”时代,国家间的竞争与冲突早已超越了军事、经济等硬实力的冲突,不能将情报公开作为单一的方式来施行威慑行为,而应当将其作为对外战略竞争中的一个方面,全盘统筹考虑行动计划。在情报公开之前,要将其与其他行动协调起来,明确情报公开的威慑目标和威慑效果,确定对手的行动决心和核心利益,将情报公开与军事威慑、经济制裁、舆论控制等方面综合起来,增强情报威慑的效用。
第三,利用先进技术提高情报分析的精准性、避免情报内容的政治化,维护情报机构的权威性。推行情报公开不能以牺牲情报权威性为代价,在实质上,情报部门和政府部门应当是协调统一的整体,维护情报机构的权威性也是在维护国家安全、推动情报的可持续发展。在当前虚假信息盛行、网络数据无序流转的环境下,情报内容失误和情报权威受损之间的矛盾使情报部门面临极大的压力。面对此问题,一方面,应当加强对先进技术的使用,增强情报收集和分析的准确性,无论是及时将先进技术嵌入到情报收集工作之中,还是与先进数据公司合作[26],都必不可少且至关重要。另一方面,避免情报内容政治化,应当加强情报审查和监管力度,降低政治部门胁迫情报部门或者情报部门迎合政治部门的倾向,提高情报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以便维护情报机构的权威性。
第四,增强情报来源的保密性,保障情报网络的可持续发展。越是精确且机密的情报越容易暴露情报网络节点的位置,而对手也越容易获知情报泄露的出口,破坏我方的情报网络。因此,要维持情报公开和情报网络安全之间的平衡,其一,谨慎公开由情报人员实地获取的秘密数据,避免因秘密情报公开而遭到反侦查的问题。其二,谨慎公开由先进技术获取的实时情报,避免因情报公开而使相应技术泄漏,成为对手弥补情报短板、遏制我方情报获取的工具。其三,在特殊情况下推行情报公开,可与民间情报机构进行合作。与国家情报机构相比,民间情报机构的重要性相对较低,但社会影响力却在逐步增强。尤其在开源数据对于情报越来越重要的时代,民间情报机构同样也能获取较为机密的情报内容。因此,与民间情报机构合作来公开相应情报,不仅可以提高情报来源的多样性,同时也可以避免暴露官方情报网络,实现秘密情报的可持续发展。
第五,具体考虑情报内容的影响性,避免受众差异而引发次生恐慌。情报公开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稳定民众情绪、维护社会稳定,但同时也可能会引发次生恐慌、扰乱社会稳定。为此,在情报公开之前,一方面,应当考虑情报公开的方式方法,避免采取过于激进的表述方式,应根据具体的情报内容、危急程度来调整情报公开的方式。另一方面,应当考虑情报的影响范围以及受众接受程度。情报与部分民众利益相关还是与整体民众利益相关,这个问题在情报公开之前需要仔细考虑,当情报与部分民众利益相关,将容易引发其他民众的恐慌,而当情报与整体利益相关,情报公开将有利于凝聚民族力量、获取民众支持以及推动政策通过。简言之,有选择地公开情报将有利于避免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而导致更大的社会不稳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