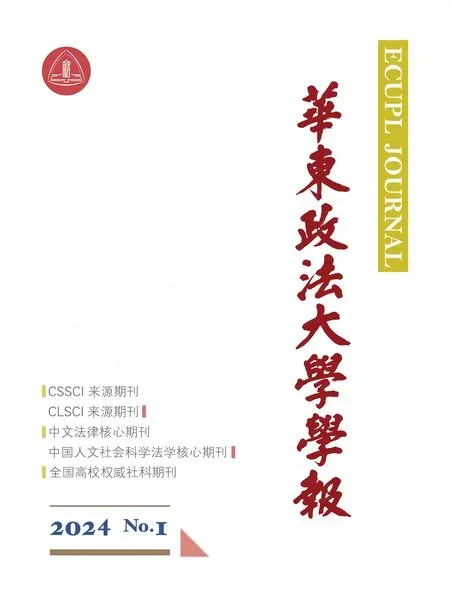最后的律学家
——徐象先、蒋楷的清律讲义及其生平志趣
苏亦工
目 次
一、楔子
二、徐象先氏讲义及其民初国会提案
三、蒋楷生平及著述
四、《律服疏证》
五、“礼”与“唐礼”之辨
六、结语
一、楔子
笔者近年整理了清季徐象先的《大清律讲义》、吉同钧的《大清律例讲义》和蒋楷的《大清律讲义前编》等三部著作。徐氏讲义刊行于“丁未仲冬”,即光绪三十三年,亦即西元1907 年年底或1908 年年初之际。吉氏讲义大抵刊行于光绪三十四年至宣统元年冬春之际,即1908 年年底或1909 年年初。蒋氏讲义刊行于宣统二年三月,即1910 年四五月间。这个时期,正是清廷变法修律的关键阶段,也是西方法律和法学知识涌入中国的第一波高潮。
受此时代背景影响,三部讲义存在着一些共同特点:均为撰著于清末变法修律之际的新式讲义体著作,〔1〕讲义体著作至迟在宋代已经出现。(宋)邢昺:《〈孝经〉注疏序》:“会合归趣,一依讲说,次第解释,号之为讲义也。”参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 年影印本,第2538 页。均以清末法律改革或刚刚出台的大清新刑律草案为参照,同时又均保持了比较鲜明的传统律学色彩。换言之,这三部讲义皆出自具备一定西学知识,甚至对新输入的西方法学有相当了解和认知的旧式士大夫之手。上述这些共同特点使得这三部讲义既不同于20 世纪以后出生的、以西学知识为主导的新式法学家的著述,又不同于传统的律学著述,譬如沈之奇的《大清律辑注》、吴坛的《大清律例通考》,与清末律学大家若薛允升之《读例存疑》《唐明律合编》、沈家本之《历代刑法考》《律例偶笺》《律例校勘记》等书也多有不同,甚至与其后程树德的《九朝律考》亦复差别不小。可以说,这三部讲义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兼具新旧、中西的双重属性:一方面,在基本价值观上仍坚持中国文化的传统,咸以“中学”和“旧学”为体;而另一方面,在著作体裁、形式和术语上,也适当融入了一些清季新输入的外来文化元素,即以“西学”或“新学”为用,堪称是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在“律学”或“法学”〔2〕注意:此处所说之“律学”,非谓其与西方法学有任何实质性差别,仅指受中国传统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影响而形成之中国传统法学;此处所说之“法学”,乃广义之法学,不限于外来输入之西方法学或受西方法学思想影响而衍生之法学。领域的代表性著作。用陈寅恪先生的说法,即“新瓶旧酒”。〔3〕参见苏亦工:《文化与法——也谈贺麟先生的文化体用观》,载《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 年第3 期。
笔者以为,正是这种“中体西用”“新瓶旧酒”的特点,使得这三部讲义具有了鲜明的末代律学色彩。相应地,这三部讲义的作者都可被视为中国最后的律学家。
三部讲义中,以吉氏讲义影响最大、流传最广,蒋楷在其讲义中即曾参考引证。〔4〕《大清律讲义前编一》(宣统二年石印本,下同),“德宗景皇帝上谕”条下提及“京师法律馆《讲义》”。“京师法律馆”即“修订法律馆”,当指吉氏讲义“廿卷本”。参见苏亦工:《吉同钧清律讲义的版本、成书过程及其价值》,载《法律科学》2023 年第5 期。该书效法薛允升《读例存疑》的体例,以《大清律例》中的《名例》和《刑律·贼盗》两篇律文为纲,逐门讲解,兼及条例。如能结合氏著《大清现行刑律讲义》讲解其他各篇各门律例的内容一体阅读,则该讲义不啻为《读例存疑》之更新版。相对来说,吉氏讲义最重中外刑法实体规则的比较,殊多精辟见解,至今读来,仍能发人警醒。譬如在讲解《刑律·贼盗·二罪俱发以重论》门律例时,吉氏批评《日本改正刑法草案》说:
谓从一处断之规是犯一罪与犯数罪受刑相同,自犯人计之,犯一罪不若犯数罪之利益矣。刑法之目的本为预防犯罪,而此法却有奖励犯罪之趋向,是与刑法之本旨相背矣。复采《德意志刑法》并科主义,除死罪及无期惩役、禁锢不科他刑外,余俱於并合罪中加其刑期之半,盖其改正之法虽较现中律从严,实与《唐律》用意吻合,且切中近今情弊,附记於此,以备参考。即此可见,外国立法不惮再四推勘,精益求精,其所长人者在此,其可取法者亦在此。独怪新学之家仅於文法名词之间袭其皮毛,讵非买椟还珠乎?〔5〕《大清律例讲义》卷二,《名例下》。
又如他在讲解《刑律·贼盗·强盗》门律例时说:
外国强盗均无死罪,《俄律》凡强劫住宅村落者,罚作十年以上苦工……《日本刑法》惟强盗杀人处死,强盗伤人及强奸妇女处无期徒刑;若无以上重情,虽结伙持械、用药迷人,俱分别处以惩役云云。互相比较,彼法轻而盗风日减,我法重而盗案日增。以外国比中国,更可见严刑重法仅治盗之标,非弥盗之本也。现在修例,拟将强盗罪名略为轻减,而议者群相诟病,皆未尝统古今中外刑法源流而合参之也!〔6〕《大清律例讲义》卷三。
吉氏还对清初修律改变中国历代律典窃盗罪无死刑的传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明律》,一百二十贯罪止流三千里,顺治四年改“一百二十两流”罪为“绞监候”,康熙年间改为“一百二十两以上绞监候”,又添“三犯不论赃数,绞监候”一语,从此为窃盗始拟死罪矣……惟自古迄今,治盗之法多矣,曾未闻畏法而人不敢为盗。法不足胜奸,汉之武帝、明之太祖,其明验与?!老子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孔丛子》述孔子之言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敎民,民匮其生,饥寒切於身而不为非者,寡矣。故古之於盗,恶之而不杀也。”观此二说,可得弭盗之道焉。今不必空言清心寡欲,潜移默化也,第采东西各国之法,广兴工艺、农桑、森林、牧畜各实业,使民衣食有资,然後遍设警察以稽查其出入,使之无所潜藏窝顿,庶几盗少息焉。而其要尤在能得良吏,茍无良吏,则以上二者皆具文也。〔7〕《大清律例讲义》卷三,《贼盗·窃盗》。
近代以来,吉氏常因观念守旧而饱受讥贬。观其上述言论,可知进步保守实与公平正义无关。评判法律制度和思想观念善恶是非的标准,应以其是否尊重人性、提升人格及有益民生为断。诚如有学者所言:“人有义务服从公正的法律但不服从非正义的法律。正义的法律是提升人格的法律;反之,非正义的法律是贬损人格的法律。”〔8〕[美]戴维·鲁本:《法律现代主义》,苏亦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304 页。
关于吉同钧的生平著述,近年来研究成果较多,笔者亦已另文专论,〔9〕参见苏亦工:《吉同钧清律讲义的版本、成书过程及其价值》,载《法律科学》2023 年第5 期。故不复赘言。本文拟着重谈谈迄今鲜有人关注的徐象先的生平志趣和蒋楷极富特色的律服研究。
二、徐象先氏讲义及其民初国会提案
徐象先,字暮初,浙江温州永嘉县人,系温州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同时也是知名中医徐定超先生(1845—1917 年)的第三子。关于象先之生卒年,记载不同。《永嘉县志》谓其生于清光绪三年(1877 年),卒于1950 年。〔10〕参见永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永嘉县志》,方志出版社2003 年版,第1357 页。《永嘉县志》谓其生于公元1877 年。此处关于徐象先生平而未另注明出处者,皆据此书。《民国人物大辞典》及《浙江民国人物大辞典》则谓其生于西元1880 年(光绪六年),卒年不详。〔11〕参见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720 页;林吕建主编:《浙江民国人物大辞典》,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529 页。未知孰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冬,象先考入是年刚刚开始招生的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成为该校招收的首届学生,初学数学,后转学法律。〔12〕参见《温籍数学家群体传略·徐贤仪》,载胡毓达:《数学家之乡》,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 年版,第166 页。京师大学堂档案中收录的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十月分两馆员生月考应得各奖清单内就有徐象先获得三元奖励的记录。〔13〕参见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年版,第217 页。《浙江民国人物大辞典》称其“早年就读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春毕业后〔14〕参见永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永嘉县志》,方志出版社2003 年版,第1357 页。历任京师警务学堂(后更名为“民政部高等巡警学堂”)〔15〕《永嘉县志》作“北京巡警学堂”,不确。参见韩延龙、苏亦工等:《中国近代警察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版,第239 页。教员、顺天法政学堂教务长及邮船部主事等职,〔16〕参见戴岩梁:《徐定超行略及家世序》,载陈继达主编:《监察御史徐定超》,学林出版社1997 年版,第410 页。《大清律讲义》应该就是他任教于民政部高等巡警学堂时期撰写的讲义,其时他也不过三十岁左右。宣统三年(1911 年)武昌首义,浙江宣布脱离清廷“光复”,徐定超就任温州军政分府都督,象先出任军政分府秘书处处长。〔17〕参见梅冷生:《徐定超组织温州军政分府经过》,载陈继达主编:《监察御史徐定超》,学林出版社1997 年版,第335 页。民国二年(1913 年)春,象先当选中华民国首届国会众议院议员。但袁世凯为追求独裁集权,自始即极力干扰国会的正常运作,先于同年11 月4 日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籍国会议员,〔18〕参见朱宗震、杨光辉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稿: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819-821 页。翌年一月又下令停止其余议员职务,国会遂遭解散。〔19〕参见蒋碧昆编著:《中国近代宪政宪法史略》,法律出版社1988 年版,第156 页;陈茹玄编著:《中国宪法史》,世界书局1933年版,第46、65 页。迨民国五年(1916 年)六月袁氏殂落,8 月1 日黎元洪恢复国会,继续制宪。象先仍为议员,在民国六年一月召开的宪法会议上,象先独立提出了《宪法草案第十二条修正案》,并与众议院议员魏肇文和唐宝锷共同提出了《宪法草案第十一条修正案》,〔20〕参见《宪法会议公报》第24 册,第12-14 页、28-29 页。陈茹玄编著的《中国宪法史》第93-94 页有关于此修正案背景之议论。他还联署了由众议院议员何雯提出的宪法第五章《国会委员会之修正案》。〔21〕参见《宪法会议公报》第37 册,第95-97 页。同年六月,张勋复辟,国会再遭解散。民国十一年(1922 年)重开国会,象先三任议员,〔22〕参见《民国议宪人名表》,载吴宗慈:《中华民国宪法史》,于明、王捷、孔晶点校,法律出版社2013 年版,第99 页。与吕复等联名提出了《宪法教育章草案》。〔23〕参见《宪法会议公报》第57 册,第24-27 页。此外,他还参与了《六法全书》的编纂。民国十七年(1928 年),象先举家返回温州故乡,以律师为业。抗战爆发时,象先已年逾花甲,仍出任浙江省赈济署总干事长,积极救济渔民。民国三十年(1941 年),永嘉县城沦陷,象先携眷避难至江心屿,汉奸逼令岛上居民悬挂太阳旗,象先因拒不服从而遭到汉奸殴打,事后象先仍强调“做人要有骨气”。至于象先的结局,史料失载。
清末咸同光宣之际(19 世纪50 年代至80 年代)应该是中国最后一代〔24〕参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 年影印本,第2507 页。《论衡·宣汉》:“且孔子所谓一世,三十年也。”参见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818 页。律学家生成的年代,其中同治末叶迄光绪初元(1870 年代)的出生者,可能身兼传统律学家和现代西式法学家的双重角色,徐象先和程树德堪为代表。这以后则只能产生新派的西式法学家,而不再可能出现传统的律学家了。
相较另两部讲义,徐氏讲义在体例上更接近现代著述,更具概括性、系统性,也更便于今人理解。这一点我们观其目录便可了然。该讲义分编、章、节三级结构。绪论编分为“律例”“律目”“律附”三章。首章介绍律典结构和律例关系。次章叙述律典篇目的历代沿革。末章内容最为丰富,但略显驳杂。作者分为“总说”“律母律眼”“诸图”“服制”“各部则例及《中枢政考》《会典》”“注释”“比引律条”“检尸图格”“《督捕则例》”“五军道里表”“三流道里表”“秋审期限定例”“秋审实缓比较”等十三节,俱为理解《大清律例》乃至整体把握清代法制的津梁。总论编分为“法例”“刑名”“处决期限”“矜疑缓决”“减轻、原免、赎罪”“宥赦”“数罪俱发”“再犯”“共犯”“加减罪例”等十章,略似当今刑法学讲义的总论部分。惜乎作者未能完成讲义“总目”〔25〕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有“总目”,他本或阙。中原计划撰写的后两编,“各论”和“余论”。
由于新刑律草案总分则分别发布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八月和十一月,其时象先的讲义已先期完成,故不能像另两部讲义那样作详细且有针对性的直接比较。但因象先少吉、蒋两人二十三四岁,故其西学底蕴更为深厚,对西方法学和西方文化的理解也更为透辟。从象先讲义中引证的许多修订法律馆奏折及若干光绪新章来看,他对清末新输入之西学持相当开放和欢迎的态度,赞成参酌西方法律修订大清律。《大清律讲义》在讨论清律中的“天文生”条时,作者即明确表示:“若今则科学大明,此律殊属可废。”在谈到《尚书·吕刑》中记载的“金作赎刑”时,他说:“然自新法理言之,实有大不然者,盖财产本权利之一,定罪无容疑之理者也。”〔26〕徐象先:《大清律讲义·绪论》,第三章第三款。
与吉、蒋两人不同,进入民国以后,象先在政治上依然相当活跃。从民初象先以国会议员身份参与的几道宪法提案中,不难看出他后来对西学,尤其是西方法学乃至西方文化的认识和求索仍在持续深化之中。更应强调指出的是,这几道提案也是我们研究象先志趣和民初宪法史的重要资料。
民国六年(1917 年),象先独立提出了《宪法草案第十二条修正案》(关于人民财产不受侵犯条),认为宪法草案第十二条原案规定的“人民之财产所有权不受侵犯,但公益上必要之处分依法律之所定”不够严谨,保护范围也过于狭隘,人民财产很容易受到侵害。该条修正案理由书指出:
本条为保护人民私有财产之规定。夫所谓私有财产者,除人类外,凡一切事物皆包含在内。原案“人民之财产所有权”一语范围未免过狭,且政府干涉人民权利之手段,财产为其最要部分,如租税、公用征收及搜查、扣押等事,皆与人民财产有直接关系。然此诸端,将来必定有各种法律,故仅用非依法律不受侵犯,已可概括原案;“但公益上必要之处分依法律之所定”二语洵属赘旒,且词意冗钝,尽可删除。盖一切法律,无一非为公益起见,即无一非公益上必要之处分也。是否有当,敬乞公决。〔27〕《宪法会议公报》第24 册,《修正案十九》,第28-29 页。
象先的这一提案,极富远见。他说:“私有财产者,除人类外,凡一切事物皆包含在内”,“且政府干涉人民权利之手段,财产为其最要部分”。这种对私有财产广泛性的强调及对政府以“公益”为借口剥夺私人财产权的警惕防范之心,绝非杞人忧天,无的放矢。试观中国近世民生饱受摧残之历史,无一不与私有财产权的丧失有关。
象先对私有财产的重视,符合儒家一贯倡导的“富民”主张。《论语·子路》云:“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孟子·梁惠王上》说得更透彻:“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必须使民众“有恒产”,而后“有恒心”。《孟子·滕文公上》谓:“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
在昔传统时代,居于政治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要求“为人君,止于仁”,主张君官要“为民父母”,要让民众“有恒产”,反对官府“与民争利”;而“使民以时”“养民也惠”“使民也义”“使民如承大祭”“使民养生丧死无憾”,至少在理论上皆为身膺民牧者时时都要牢记的箴言炯诫。凡属劳民伤财、横征暴敛的行为,无论是出自地方官府还是中央朝廷,均非理直气壮之事。但自清季舶来西方法律及学说以后,形势骤变。官府动辄以“公益”为正当借口,假借宪法法律授权许可的“暴力行为”,随心所欲地剥夺人民的私有财产及其他一切权利,而“宪法”和“法律”正是政府得以理直气壮为所欲为和胡作非为的保护伞和遮羞布。民贼独夫们一旦掌握了法治或法制这块冠冕堂皇的金字招牌,人民非但不敢言,甚至已经不敢怒、不能怒了!设若民众当年能对象先的这一提案诚心接受并坚守不移,则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可能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可见,国人在学习和引介西方文化时,多只片面地关注和炫耀其民主、法治和科学等积极的一面,忽视抑或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三者也存在着严重副作用的另一面。
同在1917 年,象先还与另两位众议员共同提出了针对宪法草案第十一条的修正案,即关于自由信仰孔子之道的修正案。宪法草案第十一条原案规定:“中华民国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制限。”修正后改为:“中华民国人民有信仰孔子之道及其他宗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制限;其尊孔典礼别以法律定之。”其理由书写道:
本员以为,孔子之道并非强迫的,乃系自由的……本员用本此旨,提出十一条修正案,使人民得自由信仰,不犹愈於强迫者之感化尤深耶?!此修正之理由一。孔子是否宗教家,学者聚讼纷纭……以此种种证之,孔子之为宗教家,殆无疑义,唯孔子不仅宗教家而已也。查各宗教家均以改良社会人心为务,而孔子则兼有国家政治之观念,世界大同之眼光,此不同之点一。各宗教家均有入主出奴,唯我独尊之成见,孔子之道则大无不包,通而无碍,故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此不同之点二。各宗教家或主张一神说或主张多神说,均属迷信。孔子则破除迷信,注重人道……此不同之点三。有此三点,故本员以为,与其谓孔子之教不若谓为孔子之道。孟子曰:“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故规定孔子之道对于“教”字之义较为通博且有本原。此修正之理由二。总之,孔子之道非片面的,乃集大成的。孔子之道以德化人者,非以力制人者……故本员以为,定孔教为国教,而滋各教之烦言,何如使人民自由信仰之为得耶?!如此,则人民将奉为宗教家也,可奉为教育家、政治家、道德家、哲学家也亦可。至尊孔典礼为数千年来历史相沿之成例,值兹民国初建,允宜由法律规定以定人心。〔28〕《宪法会议公报》第24 册,《修正案二》,第12 页。
象先主张“自由信仰孔子之道”,无论在当时还是今日,都可能会被视为“保守”“落后”,甚至“倒退”。民初以来,围绕孔教入宪问题争讼不断,反对的声浪始终占据压倒性优势。这里笔者强调两点:
其一,象先等人之所以推尊“孔子之道”,在于“孔子之道以德化人,非以力制人”。检讨清季以来引入之西学、西政、西法以及西方文化,多为“以力服人”者,鲜有“以德服人”者。纵有之,亦往往与西人之实际行为不符,可谓口是心非、名实相背。
其二,象先等人的修正案并非要将孔教或孔子之道定为国教,强加于人,而只是要求保证中国人民享有自由信仰孔子之道的宪法权利。尽管这项权利具有的只是消极的、否定性自由(negative liberty)的性质,即不受干扰和不受侵犯的性质,而非积极的、要求或强制他人必须信仰的性质。〔29〕关于“消极自由”及“积极自由”等概念,可参见[英]以赛亚·柏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11 年版,第170-182 页;Maria Dimova-Cookson, Rethinking Positive and Negative Liberty, London, Routledge, 2020, p.3.但是,回首其后数十年的中国历史,象先等人提出的这条修正案不啻一言成谶。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之后,中国人民果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丧失了自由信仰孔孟之道的权利,如今这项权利是否真的得以恢复也仍成疑问。虽然自辛亥革命以来的一个多世纪里,我国历届政府均将西方“信教自由”或“宗教信仰自由”概念纳入历次制定的宪法性文件和相关法律条文之中,〔30〕譬如1912 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6 条,1923 年的《中华民国宪法》(即“曹锟宪法”)第12 条,1947 年的《中华民国宪法》第13 条,1949 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5 条、第53 条,1954 年《宪法》第88 条,1975 年《宪法》第28 条,1978 年《宪法》第46 条和现行《宪法》第36 条。但中国人民信仰自己文化传统中的孔子之道却是一种奢望,甚至一度成为莫大的罪恶。为此,我们不得不承认象先等人的先见之明。如此说来,象先等人当年提出的宪法修正案岂不仍有其紧迫的现实意义?!
从理由书中还可看出,象先虽然熟稔近代西方法学,但依然是孔孟之道的传承者和传统文化的捍卫者。高恒先生认为,中国传统律学兴起于秦汉之际,最初研究律学者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儒者,“他们提倡以儒家经义作为研究律学和审理案件的理论依据”;“另一类是律学家,多出身文吏。他们解释法律,着重於阐明条文本义,探讨名词、术语的含义。这类律学,滥觞於西汉中期,至东汉後期已非常盛行”。而这两类人研究的律学,从西汉起逐渐合流,到东汉曹魏时期有重大发展,至两晋时代“已成为独立学科的中国古代律学”。这种律学的基本特征是“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31〕高恒:《沈家本与中国古代律学终结》,载高恒:《中国古代法制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380-382 页。可见象先的《大清律讲义》仍属于典型的传统律学,与纯西式法学著作在价值观和方法论上皆有实质的不同。笔者以为,象先和与其同庚的程树德〔32〕关于程树德氏生平思想,可参见钟赓言、程树德:《宪法讲义大纲·比较宪法》,苏亦工、何悦敏点校,收李秀清、陈颐主编:《朝阳法科讲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整理弁言。一样,既是一位精通西学的法学家,同时又是坚守传统的律学家!
三、蒋楷生平及著述
蒋楷,字则先,一字仲则,湖北荆门州(今荆门市)人,清咸丰二年(1853 年)生,民国二年(1913 年)卒。光绪十一年(1885 年),楷以荆门直隶州州学优廪生资格中乡试第二十六名,选为光绪乙酉科拔贡,时年三十二岁。光绪十六年(1890 年)代理山东莒州知州。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黄河利津段决口,楷奉命参与河工,撰成《河上语》一卷。楷去世后多年,该书获得了民国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先生的赞赏,谓之“其文佳,其注详,而苦无图”,因嘱人附之以图,更名为《河上语图解》,收入“黄河水利委员会丛刊第二种”,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 年)刊行,至今犹为研究我国水工名词之重要参考资料。〔33〕参见(清)蒋楷撰,(民国)陈汝珍、刘秉鐄附图:《河上语图解·序》,黄河水利委员会民国二十三年编印,第1 页。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楷补授莒州知州。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调署山东平原县知县。时山东各地民教关系紧张,教众多恃洋人势力横行乡里,乡民亦不甘屈辱,群起抗争。于是教案迭兴,民教势同水火。楷身为地方长官,主张安抚教民,平息冲突,以避免贻外人以干涉之口实,与时任山东巡抚毓贤意见相左,动辄得咎,竟被其“奏准革职,永不叙用”,“驱逐回籍”。翌年,楷据其亲历撰成了《平原拳匪纪事》一卷,本意在为自己辩冤,不期日后竟被中国史学会作为记录义和团暴动初起的第一手重要史料全文收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九种”——《义和团》。〔34〕参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义和团》(第1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第351-362 页。
楷罢官回鄂后,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深悉其冤而又颇重其才,乃“致之幕下”,委以“稽查武备学堂”差事。经张之洞奏请,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六月楷得以开复原官。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冬十一月,楷获授山东濮州知州,次年十二月以记名御史调任张之洞主政的学部,为候补员外郎。宣统元年(1909 年)六月二十九日,楷奉旨派充山东青岛特别高等学堂总稽察。《大清律讲义前编》即其在此任上撰成的讲义。〔35〕参见王健泉:《蒋楷年表》,载陈广珍、张国梁主编:《蒋楷文集》,香港银河出版社2002 年版,第224-227 页。
蒋楷一生仕途坎坷,但才华横溢、撰述甚丰,影响亦不可谓小。除前述各书外,氏尚著有《经义亭疑》《那处诗钞》等数种。民国二年腊月三十日(1913 年2 月5 日),楷以郁闷成疾,病逝于任上。
蒋楷的讲义题作《大清律讲义前编》。所谓“前编”,从内容看,约略相当于徐氏讲义的绪论和总论。全书分为四编,即《圣训》《经义》《历代律目沿革表》《律服疏证》,体例颇为奇特。前三编简明扼要,合计篇幅仅及第四编之半强。前编一为《圣训》,辑录有清历朝皇帝颁发律典条例之御制序言及上谕共八道,并加案语,以揭示当朝立法之要领。前编二为《经义》,汇集《尚书》《周礼》等儒家经典中关涉刑罚治法之文字,以阐明中国固有法制之价值基础。前编三为《历代律目沿革表》,清晰地梳理了历代律典篇目之沿革。前编四篇幅最重,最能体现该讲义之风格,也最见功力,其内又分为四个部分:前三部分以五服为序,尽展作者研究律服之收获;第四部分则可区分为补遗和答问两方面,抒发作者之心得。蒋楷博学多识,经学功底深厚,其讲义《圣训》《经义》《律服疏证》三编,皆围绕经学阐发义理,显现了作者对法律内在机理的深刻洞见,也说明人类文化在终极价值层面无分西东,殊多共通之处。
譬如,在疏证《尚书·康诰》中“用其义刑义杀,勿庸以次汝封”一句时,楷加案语:
日本论国际法之性质,曰:凡判事之性质,惟在确守既定之权利、义务而非剏设变更其权利义务。申言之,即固有之权利不能夺,夙所未有之权利不能与,固有之义务不能免,夙所未有之义务不能加。判事某尝谓余曰:“诉讼之胜败不因裁判而决,当胜者胜,当败者败,故判事无权使之一胜而一败也。”与此合。〔36〕《大清律讲义前编二》。
西方素有法律是人类的发现而非创制之说,〔37〕参见[美]爱德华·考文:《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强世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年版,第1 页。蒋氏所言正合此意。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修律大臣沈家本等上奏提出删除旧律中的“比附”,〔38〕参见高汉成主编:《〈大清新刑律〉立法资料汇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版,第21 页。蒋楷指出:
今修律大臣疏请删除比附而引《周礼》县刑象布刑禁各条,以为法者与民共信之物,故不惮反复申告,务使椎鲁互相警戒,实律无正条不处罚之证。又引汉制“附所当比”为比附之始。窃谓律无正条不处罚最为驳议口实。据法学之理,有当声明者三:法律所无,而可诉讼、可裁判者,民法;不能诉讼、不能裁判者,刑法。刑事变幻不如民事之多,当声明者一也。法律既定,许引伸,如原禁钓鱼,投网甚於垂钓,可以钓鱼之罪罪之。不许附会,如原禁童子吃烟,遇童子饮酒,不得以吃烟之罪罪之。当声明者二也。欧洲用成文法之国亦不废习惯法,和朗曰:习惯法之有法律效力不始於判事据以裁判之时,故判事适用习惯法与成文法初无分别。〔39〕《大清律讲义前编二》。
这段文字真可谓言简意赅,画龙点睛。在论及财产继承问题时,蒋氏又云:
窃谓民法者,刑律之母也。《法兰西法典》以亲族居首,《日本旧民法》因之,《新民法》四曰《亲族》、五曰《相续》。近来所主法典,《总则》之次即曰《亲族》,次曰《财产》,而以《相续》为闗於亲族、闗於财产,为之殿焉。窃愿当事者与民政部、礼部速定民法以立其基也。又愿迟回审顾,於数千年相沿之礼教,数万里习惯之人情,不蹈习故常,不改错规矩,考诸三王而不谬,质诸百世而无疑也。若但点纂他国之民法为编纂我国之民法,其能行与否,非所敢知已!〔40〕《大清律讲义前编一》。
蒋氏出语未久便不幸言中了!中国日后的民事立法一依日本之先例,以法德民法典为圣经,东施效颦而至今未悟。可哀可叹!
四、《律服疏证》
蒋氏《律服疏证》以《大清律例》正文前的“服制”〔41〕《大清律例》卷3 为服制;《大清律例会通新纂》卷2 诸图之后。为诠释对象,以朱熹“丧礼须当以《仪礼》为正”〔42〕(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89,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6 年版,第2283 页。为价值基准,评点律服及其所依从之现行礼制——古礼迭经修改后之当朝礼制,重在指摘此二者之内在逻辑混乱,譬如:
此节有不解者五:父母为长子斩、齐各三年,礼也。今父母同不杖期,不解一;既降长子矣,而適孙不降,不解二;长子之妻反由大功加而为期,不解三;长子与长子之妻既无别矣,而众子与众子妇又不同,不解四;众子及女在室之期,与子为人後之期,服例各别,混而同之,不解五也。〔43〕《律服疏证二》。
明清两代,律学繁盛,律学家蜂起,官私注律之书若雨后春笋般层见叠出。然而在众多律学著述之中,专门针对律典服制的作品却极罕见,蒋氏此书或为清代律服研究的仅存硕果。据沈家本《薛大司寇遗稿序》〔44〕参见(清)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中华书局1985 年版,第2213 页。知薛允升生前撰有《服制备考》一书稿本,惜乎未曾刊刻传世。著名古籍版本学家顾廷龙在1935 年6 月撰写的一篇文章中,称其当年在北京某市肆上购得过该书稿:
日前休沐,蹀躞小市,在某肆瞥见尘封之敝架,有丛残一束,标签曰“汉律稿本”。取而视之,零乱无次,无序无跋,不署作者姓氏。粗检一过,未见题及汉律者。及重阅之,则三册考服制,而余为论唐明律。因思考汉唐明律与服制者,非薛允升莫能为,必为其稿本无疑。……考服制者,必为《服制备考》,计三册不分卷,其字迹全如唐明律稿之改笔,则全为手稿矣。得之偶然,不亦幸哉!後晤李祖荫先生麋寿,告以薛氏久失之《服制备考》,今归寒斋……《服制备考》幸系原稿,涂改满幅,不题书名撰者,贾者遂不辨而弃置一隅。〔45〕顾廷龙:《薛允升服制备考稿本之发见》,载《顾廷龙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 年版,第405 页。文字、标点似有讹误,此处据文意酌改——笔者注。
顾廷龙先生一生整理出版过无数古籍,但却始终未将薛氏的《服制备考》公诸于世,未知何故。幸好顾氏在该文中抄录了《服制备考》卷首的“代叙”。薛氏的这篇“代叙”也很奇特,除了首尾两段,几乎全文转引了清代学者吴嘉宾《丧服改制说》开篇的小序。吴氏认为,周礼传至后世者只有丧服。丧服制度的大义有三,即“父”“君”“宗”。但是两周以后,丧服制度发生了三次重大变化:一为“汉文帝诏吏民短丧,而服君之义微”;二为“唐以後加异姓服,有大功、袒免,而服宗之义微”;三为“明制加子为母、妇为舅姑皆斩衰,子为庶母期、父为长子期、众子皆期,而服父之义微”。丧服制度存在的目的就在于为人道设定权衡,一旦变更,势必造成严重的价值淆乱。
道者,尊亲而已。以尊易亲则废仁,以亲易尊则废义。以其不尊不亲者易其至尊至亲者,则等杀无辨,而废礼。礼废而刑益烦,民日不知其所适矣。〔46〕(清)吴嘉宾:《丧服会通说》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影印版,第391 页。
薛允升赞成吴嘉宾的观点,并进而指出,服制之等差详载于《仪礼》:
不特别亲疏也,亦分贵贱;而君父之服,列为第一,盖所谓尊无二上也。今律则合大夫士庶而为一,并不载为君之服,而於後来增添之服多於《仪礼》者大半,此古今之所以大不相同也……夫为君之服,律内既未载入,又何敢另生他议。而王侯公卿与庶人同一服制,将礼所谓诸侯绝、大夫降者,亦俱废而不用矣。谨就律文所载各条,详其原委,并备录群儒论说,而参以末议。其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显然,薛氏撰作该书之目的,是要梳理《大清律例·服制》各条之原委并评点后世服制变化背离《仪礼》的得失。顾廷龙先生亦指出:
读此文,始知所据为前清律文,乃取各条校之,尚无缺失,采摭前说,可称极备;所抒己见,衷於一是,可谓言五服之集成矣。曩定刑律,本於宗法,尊卑亲疏,以服制为纲维。唐之改制,详於《开元礼》,明之改制,详於《孝慈录》。明於唐制既皆更改,而律亦多所重定。薛氏既为《唐明律合编》,以显明律之谬,服制尤为核心,遂别著《备考》若干卷(或谓四卷)明其渊源之所自。方今古制垂废之日,此书似无所用,然於研究刑法史及宗法制度者,乃一重要之本。薛氏生当国体将变之时,则此书实为丧服之一总结也。〔47〕前引薛允升语及此处引顾廷龙语皆见顾廷龙:《薛允升服制备考稿本之发见》,载《顾廷龙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 年版,第405 页。
薛氏原稿今已无从得见,故难以将薛氏《服制备考》与蒋氏《律服疏证》加以比较。但从前引薛氏“代叙”及顾氏的描述看,两书的主旨似颇为接近。若然,多少可补薛稿遗失之憾。
薛氏谓“为君之服,律内既未载入”,故“不敢另生他议”;则其书之重点当在指出“王侯公卿与庶人同一服制”之失而不敢议及“为君之礼”,以谨守“非天子,不议礼”之传统。蒋氏则似乎走得更远。盖薛氏虽“生当国体将变之时”,但毕竟未变;而蒋氏适逢其变,故已无多顾忌。他在解答“父为长子三年”之义时说:
重其嫡者,尊其祖也。明太祖责子之不孝,而先自处於不慈,乌乎可?尝谓明太祖之变礼甚於唐太宗。自父为长子不三年,而正体之义亡。祖为嫡孙与父为长子同,而定亲疏之义亡。父为长子与舅为嫡妇同,而别内外之义亡。长子众子同,而严嫡庶之义亡。父在为母斩衰三年,而家无二尊之义亡。妇为舅姑斩衰三年,而妇人不贰斩之义亡。庶子为慈母、为所生母皆斩衰三年,而尊厌之义亡。长子众子皆为庶母期,而父所不服子不敢服之义亡。内宠竝后嬖子匹嫡,太子其危矣!建文之亡虽曰天乎,亦诒谋之不善耳。〔48〕《律服疏证四·答问》。
蒋氏《律服疏证》第四章正是为补正律服乖谬阙失而作。该章开篇即言:“古礼简简而赅,今制繁繁而乱。疏律服既讫,因条其阙遗,分列於左,而以答诸生之问附之。”他所补正的服制,包括四方面:
一为与清朝《钦定三礼义疏》相背者四条,即“补礼之所有者三条,律之报服所有、本服所无者一条”。
二为补“尊尊之服”,即薛氏所谓不敢另生他议的“为君之服”。蒋氏曰:“《大传》:‘服术有六:一曰亲亲,二曰尊尊。’《小记》:‘亲亲,尊尊……人道之大者也。’《丧服经》首曰父,亲亲也。次曰诸侯为天子,尊尊也。今律载九族五服之图,只及家族可也。《服制总类》於家族以外概不之及,有父子无君臣矣。凌氏廷堪乃以《丧服》尊尊之礼为封建而设。其然?岂其然乎?”
三为补“殇服”。蒋氏特言其故:“《大传》:‘服术有六〔……〕五曰长幼。’郑注:‘长幼,成人及殇也。’齐衰之殇九月、七月也,而在大功前。大功之殇五月也,而在小功前。虽其文不缛乎,而情之所不容已,即礼之所不可阙也。三殇之制,汉、晋至元莫之敢易。明初《集礼》及令亦仍之。《孝慈录》出,始一切削去。礼何不幸,一厄於唐太宗,再厄於明太祖也。”
四为补“降服”。蒋氏曰:“惟尊降、厌降为今所不讲,乃彚而录之。而以不降先焉。”
除上述四方面的补阙外,蒋氏还补作了“心丧之礼”。他解释说:
古之降非降也,三年之丧降而期,降而小功缌麻,而其饮食居处犹三年也。今之不降亦非不降也,其饮食自若也,居处自若也。贺循《丧服要记》:“凡降服,既降,心丧如常月。”刘智谓:“小功以下,不税〔服〕乃无心丧。”自元以来不行久矣。今辑心丧之典与心丧之说为一篇。〔49〕以上几处引文未注明出处者皆据《律服疏证四》。
所谓“心丧”,是与“五服”相对而言的。礼制定丧服为斩衰等五种,是“其文也;不饮酒、不食肉、不处内者,其实也。中有其实,而外饰之以文,是为情文之称。徒服其服而无其实,则与不服等(尔)〔耳〕。虽不服其服而有其实者,谓之心丧”〔50〕(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92,陈金生、梁运华点校,中华书局1986 年版,第3045 页。。蒋氏说:
愚尝谓服制当一以周公之礼为正,後世有所增改者,皆溺乎其文,昧乎其实,而不究古人制礼之意者也。〔51〕《律服疏证四》。
细读《律服疏证》,可以看出蒋氏礼学功底深湛,故常能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在回答诸生提问时他说,“言律而言礼”是因为“礼,律之所由生也”。清人孙星衍即谓“律出於礼”〔52〕孙星衍:《重刻故唐律疏议序》,载(唐)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667 页。;近人陈寅恪先生亦一再言“礼律关系至密”,“古代礼律关系密切”,〔53〕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63 年版,第16、100 页。都是在强调礼对律的重要影响。笔者昔年曾撰文讨论唐律与礼之关系,以为“唐律所据以为准的‘礼’是唐礼,亦即秦汉以来繁衍变异了的礼”〔54〕苏亦工:《唐律“一准乎礼”辨正》,载《政法论坛》2006 年第3 期,第116 页。。其实不独唐律如此,后世若明清两代制定律典亦同样以本朝之礼为准。清代学者如吴嘉宾、薛允升和蒋楷等人看来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以《仪礼》中保留的丧服古礼为著例与经汉、唐、明等朝变更了的当朝礼制作了详尽的比较。而作为律学家的薛、蒋二人则更措意于指出以当朝礼——清礼——为准制定的律典服制的阙谬。可谓先得我心!
言礼何以特重视服制?蒋氏答曰:“罪多而刑五,丧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此言出自《礼记·服问》,注谓:“列,等比也……列,徐音例,注同,本亦作例。”〔55〕(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 年影印本,第1659 页。“上附下附”大抵即如《尚书·吕刑》的“上下比罪”“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之意。此句大意即以五种刑罚和五种服装作为判断犯罪轻重和亲疏远近的标准,上下比较,举一反三,一以例万。吴嘉宾说:
权,所以知轻重;度,所以知短长。先王之道犹权、度也。传曰:“辠多而刑五,丧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後世治丧服者多矣,未有能观其会通者。夫先王之道固有时而易,人道则无易。丧服者,人道也。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别自古及今,未之有改也。不观其会通,则安知先王之所以为权度者?苟观其会通以行之,则先王之道至於今日,虽欲稍为之损益,其於吾之心将必有惄然不安。〔56〕(清)吴嘉宾:《丧服会通说·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影印版,第345 页。
蒋氏引此句作答,应是认同吴氏观点,以为丧服制度代表了人道的亲疏远近,不可以随意变更,法律改革同样不能背弃人道。有学生问其:“律载五服始於何时?”蒋氏首先否定了宋王应麟的后唐说,认为隋唐时期的法律已引入了五服制度:
《开元礼》五服附於令,非令自是始有五服也。显庆二年,长孙无忌等奏称:“修律疏人不知礼意,舅报甥服,尚止缌麻,〔於例不通,礼须改正,〕今请修改律疏,舅(为)〔报〕甥亦小功。”则唐律有五服矣。《隋志》有《丧服假宁制》,有《齐五服制》。《通典》引魏《丧葬令》、晋《丧葬令》又在唐前。〔57〕《律服疏证四·答问》。
如前所言,蒋氏撰著《律服疏证》之目的似与薛允升相近,旨在指出《大清律例·服制》不遵古礼而以后世叠次修改之礼为准的差失,并试图纠谬补阙,恢复古礼之本意,重振中国文化之精神。
五、“礼”与“唐礼”之辨
高明士教授认为,唐律所依据的“礼”并非当时的“唐礼”:
所谓“唐礼”,通常指《贞观礼》《显庆礼》,乃至《开元礼》,今日传存为《大唐开元礼》,也是其後历朝制礼的蓝本。这些礼典,基本上是规定当时(指唐朝)的礼之仪、礼之制,关於礼之义极少。唐律所见的唐礼,在礼之仪、礼之制方面,相关条文并不多,反而多见於唐令,如《祠令》《衣服令》《卤簿令》《仪制令》《假宁令》,乃至《丧葬令》等;相对的,礼之义方面则有较多规定,尤其是关於亲疏、尊卑、贵贱、长幼、男女等之伦理等差秩序。唐律根据礼所规定的这种伦理等差秩序,基本上是源自儒家经典及其後的历史发展而来的,并非基於当时的“唐礼”。〔58〕高明士:《中国中古礼律综论:文化的定型》,商务印书馆2017 年版,第75-76 页。
此说与吴嘉宾、薛允升和蒋楷的看法皆不同,何者为确呢?笔者以为,“唐礼”也是“源自儒家经典及其后的历史发展而来的”,而“孔孟的思想借助‘唐礼’这个载体渗透到唐代法律之中在一定意义上确是事实”〔59〕苏亦工:《唐律“一准乎礼”辨正》,载《政法论坛》2006 年第3 期,第121 页;又见张中秋、潘萍:《传统中国的司法理念及其实践》,载《法学》2018 年第1 期,第69 页脚注13。。刘俊文先生说:
唐代以“三礼”为经,故唐代行用之礼的主体仍是“三礼”。所谓“主体”,就是说唐代仍然遵循“三礼”所阐述的礼的基本思想和原则。但是,唐代统治者出於政治需要,又据“俗情”对古礼有所变通,制定了唐礼,包括《贞观礼》《显庆礼》和《开元礼》。这些变通,主要表现在有关吉、凶、军、宾、嘉五礼的一些具体规定和仪节上。以丧服礼为例,其变通大端有三:一是姨舅服制……二是叔嫂服制……三是父在为母服制……这三处改动,特别是第三处改动,曾引起不少人的非议……因此可以说,所谓唐代行用之礼,就是“三礼”所阐述的礼的基本思想和原则加上唐代制定的有关吉、凶、军、宾、嘉五礼的具体规定和仪节。〔60〕刘俊文:《唐律与礼的密切关系例述》,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 年第5 期,第68-69 页。
今存本《唐律》虽不像《大清律例》那样集中开列“丧服图”和“服制”,但细加考察,仍能发现《唐律》中的服制也是“唐代统治者出於政治需要,又据‘俗情’对古礼有所变通”后的“唐礼”,而非直接和完全依据古礼——《仪礼》。《旧唐书·礼仪七》载:
上元元年,天后上表曰:“至如父在为母服止一期,虽心丧三年,服由尊降。窃谓子之於母,慈爱特深,非母不生,非母不育。推燥居湿,咽苦吐甘,生养劳瘁,恩斯极矣!所以禽兽之情,犹知其母,三年在怀,理宜崇报。若父在为母服止一期,尊父之敬虽周,报母之慈有阙。且齐斩之制,足为差减,更令周以一期,恐伤人子之志。今请父在为母终三年之服。”高宗下诏,依议行焉。〔61〕(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27,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1023 页。
考之《大唐开元礼》“齐衰三年·正服·子为母”条,其小注曰:“旧礼父卒为母周,今改与父服同。”〔62〕(唐)萧嵩等:《大唐开元礼》卷132,民族出版社2001 年影印本,第621 页。这里所说的旧礼似应指《显庆礼》或《贞观礼》。蒋楷说:“上元中武太后上表,初亦未有行用,垂拱初,始编入格之疏矣。後萧嵩等改修五礼,请依〔开〕元敕,遂为成典。”〔63〕《律服疏证一·斩衰三年》。核之《唐律疏议·户婚律》“诸居父母及夫丧”条疏议:
父母之丧,终身忧戚,三年从吉,自为达礼……若居父母及夫之丧,谓在二十七月内,若男身自娶妻,各徒三年。〔64〕(唐)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257 页。
这里说“父母之丧”“三年从吉”,可知服母丧亦三年,非服期或周,与前引《大唐开元礼》的规定正相吻合,而与先秦“儒家经典”有出入,此《唐律》“基於当时的‘唐礼’”之一证。
大唐贞观年中,八座议奏:“令舅服同姨小功五月,而律疏舅报於甥服犹三月。谨按旁尊之服,礼无不报,己非正尊,不敢降也。故甥为从母五月,从母报甥小功;甥为舅缌麻,舅亦报甥三月:是其义矣。今甥为舅使同从母之丧,则舅宜进甥以同从母之报。修律疏人不知礼意,舅报甥服,尚指缌麻,於例不通,理须改正。今请修改律疏,舅报甥亦小功。”制可。具开元礼。〔65〕(唐)杜佑:《通典》卷92,王文锦等点校,中华书局1985 年版,第2515 页。
此处之“律疏”,即指《唐律疏议》。〔66〕参见(唐)杜佑:《通典》卷165,《刑法三》,王文锦等点校,中华书局1984 年版,第4244 页。“高宗永徽……四年,有司又撰《律疏》三十卷,颁天下。”查《唐律疏议·名例》“十恶·不睦”条疏议:
小功尊属者,谓从祖父母、姑,从祖伯叔父母、姑,外祖父母,舅、姨之类。
又“内乱”条注曰:“谓奸小功以上亲、父祖妾及与和者。”疏议说:
奸小功以上亲者,谓据礼,男子为妇人著小功服而奸者。若妇人为男夫虽有小功之服,男子为报服缌麻者,非。谓外孙女於外祖父及外甥於舅之类。〔67〕(唐)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15、16 页。
据《唐律疏议》可知,“舅”“姨”同为小功尊属。而《仪礼》甥舅之服皆在缌麻章;〔68〕参见(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卷33,彭林整理、王文锦审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629-630 页。则此处之“据礼”,非据古礼者甚明。查《大唐开元礼》,“为舅及从母丈夫妇人报”列于“小功·成人·正服”条下,不同于《仪礼》。〔69〕参见(唐)萧嵩等:《大唐开元礼》卷132,民族出版社2001 年影印本,第625 页。是知唐礼改订甥舅服制后,《唐律疏议》亦作相应改订,不再沿袭古礼。此《唐律》“基於当时的‘唐礼’”之再证。
刘俊文认为:“唐律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唐律,是唐代法令的总称,包括律、令、格、式四种法典。”若依此说,则唐礼对唐律的影响又不限于《唐律疏议》,复及于令、格、式等,可谓既深且广,学界已有不少研究,兹不具论。〔70〕参见陈戍国:《从〈唐律疏议〉看唐礼及相关问题》,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1 期;陈戍国:《从〈唐律疏议〉看唐礼及相关问题(续)》,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2 期;霍存福:《论礼令关系与唐令的复原——〈唐令拾遗〉编译墨余录》,载《法学研究》1990 年第4 期。
蒋氏之重视《仪礼》丧服经传,可能与吴嘉宾一样,是将之视作“周公之礼”的硕果仅存了。为此,他在讲义中对秦汉以来的历次改订旧礼之举多持批评态度,对清季舶来的“西学”或“新学”也时加驳斥,从中不难看出其基本价值观和文化立场。但蒋楷并非一味保守而不知变通的冥顽不化之徒。
在女性再嫁的问题上,他的态度就比较开明:“夫死不嫁,礼也。然禁之使不再嫁,亦未能尽合乎人情。”他还批评“宋以後之儒好责人以难,而不顾其势之能否自存,其人之能否自守。新学家遂欲一切破坏,隳万世男女之防矣”〔71〕《律服疏证四·答问》。。在他看来:
礼有其可变者,改正朔、易服色是也,故曰三代不相袭。礼有其不可变者,父子之亲、男女之别是也,故曰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律可变也,礼不可变。列朝之《服制令》可变也,而先王之所以定亲疏决嫌疑者不可变。今律学馆方订律,礼学馆方议礼,将以此说质之。〔72〕《律服疏证四·答问》。
这段话的立场很鲜明,基于儒家经典《礼记·大传》,〔73〕原文作:“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显示蒋楷仍是传统文化的捍卫者,亦即清末法律改革过程中站在沈家本等变法派或法理派对立面的“礼教派”〔74〕参见张国华:《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372 页。阵营的一员。不过,“礼教派”未必即可斥之为“顽固派”。与张之洞、劳乃宣等人一样,他对清季法律变革的态度是折中的,而非不加分辨地反对和拒绝:
今既毖於时势,奉旨修订法律,则律亦不能不变矣。若谓修订之後永永不变,则虽圣者不能。
对于新刑律草案,他也是有褒有贬,并非全盘否定:
法律至今日,不惟修律大臣以为当变,即各部各省之力诋《刑律草案》者亦未尝以为不当变也。窃谓当变者法,不当变者道!新订《刑律草案》有四善焉……而有必不可行者二:如父子之亲、男女之别不甚分晰,经学部奏驳之类;如日本名词可改而不改,经两广总督奏驳之类。一戾乎相沿之礼教,一戾乎习惯之人情,度当事诸公改订之时,必有以处。此楷讲《大清律》首述圣训,非敢执祖制以关变法者之口,而快官吏、刑幕不便变法者之心。
在修律的一些技术细节取舍上,蒋氏也常能提出自己的见解:
与其用最新学说,固不如删存中律,参用德日之为愈矣。〔75〕以上三处引文皆见《大清律讲义前编一》。
这里不难看出蒋氏与吉同钧、徐象先等人的一致之处,即主张在变法改制的过程中,尊重和保留相沿数千年的国粹——中国传统的人伦道德。近代著名礼学家曹元弼阐发其所撰写《礼经学》一书的目的时明言:
俾学者知礼之所尊尊其义。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天经、地义、民行,得之者生,失之者死;为之者人,舍之者禽兽。知者知此,仁者体此,勇者强此,政者正此,刑者型此,乐者乐此,圣人之所以作君作师,生民之所以相生相养,皆由此道出也。〔76〕(清)曹元弼:《礼经学》,周洪校点,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1 页。
蒋楷等末代律学家编撰清律讲义的目的,应与曹元弼相同,就是要努力捍卫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守护中华民族的生命之源。
六、结语
本文讨论的三部清律讲义,既有共性又各具特色。一方面,三者均以《大清律例》为讲解对象,且因处于同一时代大潮之下,书中都采用了不少受外来法律和法学影响而新生的且至今依然广泛使用的名词和术语,如“主权”“时效”“管辖范围”“名誉”“自由”“权利”“义务”等。不过,三位作者均未停留在简单地套用几个浅显的名词术语阶段。基于各自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学术造诣,三人均能以当时东西各国的法律和文化为参照背景,展开横向比较、评骘中国固有法律并对正在进行中的法律改革提出自己的意见或建议,这就使得三部讲义形成了许多共同的时代特点。
另一方面,由于年龄、阅历和学术背景等方面的差异,三部讲义在体例、内容和着重点上绝不雷同,皆有各自的鲜明特色。可以说,三位作者均是从自己的视野出发,向我们展示了《大清律例》,甚至中国固有法律的多重面貌。其中既有宏观的、价值深层的阐发,又有微观的、特定规范的剖析。尽管三位作者各有侧重,但并非盲人摸象、以偏概全、自说自话,令读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是同中见异,异中有同。三位作者共同的出发点应该都是传统学人在中国固有法律面对外来文化和法律的致命挑战时所表现出的强烈忧患意识,而最令三位作者关切的则是传承数千年的中华道德伦理的兴衰和中国文化的命运。在固有法律断灭百多年后的今天,难道我们不该反思吗?!
——宁稼雨《〈世说新语〉与魏晋风流》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