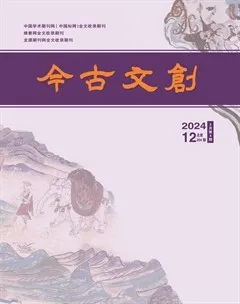捷克导演维拉 · 希蒂洛娃的女性言说与当下社会思考
【摘要】女性导演维拉·希蒂洛娃作为捷克电影史乃至世界电影史上的一座高峰,其独树一帜的美学风格与对社会时势的针砭时弊为电影文化贡献了更加多样的可能性。因着导演的女性身份,其作品常常充满了女性关怀,并有意识地促就了时代宣言的写成,尽管希蒂洛娃自身拒绝承认这一点。作为东欧社会变革的亲历者,她将视角对准了阳光背后的黑暗,时而一针见血地批判丧失道德的社会,却又常常将主题打碎,复杂到难以言明核心思想。捷克从早期的社会主义社会到20世纪90年代步入资本主义社会,女性群体在家庭与社会上始终处于不内不外、不远不近的尴尬境地,是前进还是维持原样的自由犹如手中沙,难以自我定夺。对于这一问题,希蒂洛娃导演在不同时代下给出了不同回答,虽然从未正面言明态度,但对于女性电影作者、理论与创作依旧起到了极大的激励作用,进一步丰富了女性表达,延续了时代发声。
【关键词】捷克新浪潮;东欧电影;两性关系;女性主义与个人主义之争
【中图分类号】J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12-0094-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12.029
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精进,即使是再渺小的个体也拥有了自我发声的空间与权利。不论是文字还是画面,都是时代性话语的构成。而对于大多数东欧国家而言,漫长的政治变革与经济发展使得社会问题颇多,本土孕育的民族文化与人民特性便成了创作者的主要素材来源,电影由此成了一道彩虹,寄托着希望与诉求。以女性电影为例,领头人维拉·希蒂洛娃(Vera Chytilova)以女性为镜,折射出了许多社会问题,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莫过于《雏菊》(Sedmikrasky,1966)、《陷阱,陷阱,小陷阱》(Pasti,pasti,pasticky,1998)与《不同的事》(O necem jinem,1963)等,其将严肃与趣味相结合的手法也影响了大批后来者。当前较具话题性的有克里斯蒂安·蒙吉(Cristian Mungju)的《四月三周两天》(4 lunis,3 saptamani si,2 zile,2007)、朱拉·亚库比斯克(Juraj Jakubisko)的《吸血女伯爵》(Bathory,2008)、巴林·纳吉(Balint Nagy)的《据我所知》(Legjobb tudomasom szerint,2020)与阿丽娜·格里高尔(Alina Grigore)的《蓝月亮》(Blue Moon,2021)等,虽然故事内容不同,但都将女性主体与时代背景相结合,要么美学风格突出,要么时代价值深远。由此看来,维拉·希蒂洛娃对于推动东欧电影艺术风格与女性电影书写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摄影机与两性关系
(一)物像与成像
影史长河中,女性导演的数量增减与社会文明的开放程度有着密切联系,因电影自诞生起便是掌握在男性手中的技术。早前在很多男导演的电影作品中,女性角色常被设定为天使与恶魔,对男主行为和情节推动起到助攻作用,站立的位置被划定在男性身后,因此成了时有时无的背景板,真实的生活样貌无法得到确切展现。而后在文明发展趋势与现实主义文化思潮的推动下,众多男女导演站到了同一战线,将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拉进了镜头里。而在其中,女性导演自身的性别身份与生活经历常常促就其别具一格的观察视点,在人物创作上更偏向于现实中的女性什么样,电影里的女性就是什么样,她们的外在形象、生活方式、内心想法与抗争话语会更趋向于摆脱来自第三视角的怜悯悲叹,从而更具独特的自我意识。虽然也有很多女性导演难逃窠臼,性别差异也并非那么明显,但至少女性电影自由书写的大跨步都是由女性群体彼此扶持完成的。
(二)维拉·希蒂洛娃的镜头与叙事关怀
二战结束后,捷克斯洛伐克步入社会主义阶段,文艺界一并实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路线,然而20世纪60年代期间经济危机的出现与反斯大林模式的兴起,难以平復的社会情绪和维持虚假和平的文艺创作促使了一批先锋导演的诞生。作为新浪潮中的唯一一位女性导演,希蒂洛娃在进入布拉格电影学院前曾学习哲学与建筑学,也从事过纺织、模特、场记等工作,或许正是因为积攒了丰富的人生经历,才能从创作伊始便闪耀出别具一格的梦幻色彩。在她的镜头下,有奋力反抗的女学生,有举止疯癫的神秘女子,也有疲劳崩溃的家庭主妇和经济独立的体操运动员。这些人物有着不同的人生轨迹,生活在不同的阶层社会,逆来顺受和奋起反抗的选择也只是时代洪流中被记录下来的剪影。希蒂洛娃并没有擅自给她们画下既定的结局,而是留下了未来一切可能的希望之种,从女性导演的职责出发,在叙事和书写上提供了最大化的关怀和体贴,并借她们之口表达出自身向往。
希蒂洛娃自早期创作开始便将目光对准不同职业的女性,例如《天花板》(Strop,1962)和《许多跳蚤》(Pytel blech,1962)这两部毕业时期的作品,前部讲述了一位时装模特在他人的注视与摆弄下渐渐变得内心空虚,因而出走去重新寻找自我的故事;后部则讲述了一位女子因不满学校评价劳动模范的僵化制度而进行反抗,并在潜移默化之下影响了其他女学生的故事。这两部的拍摄手法十分新颖,环境描写和音乐叙事相互交映,尤其是《许多跳蚤》还利用了第一人称的摄影视角搭配旁白来与其他人物进行对话,这种屡次打破第四堵墙的做法和影片女主反抗学校制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到了新浪潮时期,希蒂洛娃于1966年拍摄的《雏菊》更是在捷克电影史上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助其成为“东欧最前卫女导演”,极具个人特色和神秘感的剪辑手法令人目不暇接,而混乱背后同样暗藏了两位少女在权力和金钱的强迫推动下,“主动”成为飘摇在资本主义荒漠中的恶之花,精神世界一片荒芜。
在《不同的事》中,则是通过一位家庭主妇和一位体操运动员生活画面的交替剪辑,以不同的身份对比来展现时代倾轧下的殊途命运。快乐来源于自我精神上的满足,所以操劳重复且无意义家务的Vera是不快乐的,《天堂禁果》(Ovoce stromu rajskych jime,1970)里的夏娃也是不快乐的,开头色彩鲜艳的树林花叶幻灯片式的闪现,与夏娃赤裸的身体叠加,混沌之感犹如被刻意引誘的欲望,直至结尾处,人物定格与不断失焦的红花首尾呼应地完成一首悲伤的爱情之诗。彼时的希蒂洛娃,无论是在技术还是内容创作上都已达到高峰,激进辛辣的同时也表达了强烈的女性身份诉求。
1968年初布拉格之春的昙花一现换来的是更加窒闷的创作环境,此时的希蒂洛娃因《雏菊》内容不当而被禁止创作6年,再次出现在大家视野的作品是《禁果游戏》 (Hra o jablko,1977)和《预制板的故事》 (Panelstory aneb Jak se rodi sidliste,1980),希蒂洛娃的目光由女性扩至全体人民,主题上也趋于平淡日常。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天鹅绒革命爆发,捷克共和国独立成立并于20世纪90年代步入资本主义社会,希蒂洛娃以最后两部作品《陷阱》和《愉快的时刻》 (Hezke chvilky bez zaruky,2006)对当时人民道德感的缺失与麻木表达了强烈批判。前者讲述了一位女性被两位陌生男性联合性侵后进行复仇,但因话语权的丧失,所有反抗都似一拳打在棉花上,这也是希蒂洛娃第一次将男权社会的权力倾斜与女性发声受阻的矛盾明晰地摆在台面上进行书写;《愉快的时刻》则讲述了一位女心理医生除了面对每天来自不同病人的叨扰之外,自身也饱受心理摧残的故事,快速晃动的镜头和结尾定格的狂笑,希蒂洛娃以最集中的笔触描写了女性内心在强压之下的变异过程。
不难看出,希蒂洛娃对女性群体的关注从一而终,小到家庭工作的方方面面,大到阶级权力的内在异变,女性似乎被钉在了被动位置,从来都是承受方。而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动,来自多方的复杂因素宛若紧紧缠绕的藤蔓,男女两性皆困斗于其中。
二、自由界限的流动
(一)解放的洪流与凝视的胶着
在希蒂洛娃的电影中,大多数女性都拥有选择的自由,譬如“一间自己的房间” ——生存空间的构建、自由恋爱与结婚对象的抉择、性解放等,这些缺口由社会所有个体齐力撕扯而成,手边流动的风传递了新的希望。但问题是,长久抗争的果实实现了人人共享吗?
《不同的事》里的Vera,作为家庭主妇承担着内外琐事与子女教育的重担,不用外出工作的结果便是依附在丈夫的阴影之下,让渡权利的同时消化吸收一切负面情绪;《天花板》里的女模特,虽然经济独立不用依附于他人,但依旧无法自由掌控身体的主动权,顺应成为摆放在玻璃柜中的洋娃娃,承受着他人的审视打量与欲望发泄。同样的故事还发生在《天堂禁果》《禁果游戏》《天堂禁恋》(Vyhnani z raje,2001)和《陷阱》之中。20世纪60年代的性解放运动给予了女性身体反抗与欲望表达的权力,性开放似乎成了一种不受控的潮流,但在希蒂洛娃的作品中男性的虚伪不负责与女性的单纯易沉溺却是常见表述对象。正处于冷战时期的捷克人民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采取拒绝态度,在彼此同一化的进程中,女性的性别特征被掩盖,性开放似乎成为一种身体宣言,加之“去共产主义政治运动”的影响,女性再度沦为他者,因此男性凝视成为主要威胁;而步入资本主义社会后,女性本身易被商业化,加之传统性别规范对女性贞洁的要求,故女性的身体被撕扯为两半,一半是《天堂禁恋》和《陷阱》中的凝视承载体与欲望发泄对象;另一半则是《预制板的故事》中被当众羞辱的未婚先孕女学生和精神崩溃声嘶力竭的家庭主妇。无法忍受却又无力反抗的下场便是被归纳于社会秩序下的“非正常人”,这种离轨模式最终只会带来劫难。
拥有选择自由的同时,也要承受着来自权力阶级的目光凝视,这类隐形阻力也许会促使你靠近《雏菊》中两位女性的情感立场—— “世界在堕落,所以我们也要变坏”,以身体寻找精神自由的结果便是将自己变成“木乃伊”,但或许也会反其道成为动力,推动改变当前情势,成为《许多跳蚤》中的那具能够翩翩起舞、摆脱束缚的自由之身。
(二)社会变革与内外秩序的东鸣西应
玛丽亚·马尔库什(Maria Markush)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和布达佩斯学派的成员,在此学派的论文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 (Socialist Humanism)一书中收录了玛丽亚的《妇女和工作:走入死胡同的解放》(Women and work:liberation into a dead end)。她指出东欧各国步入社会主义阶段后的新经济政治结构,一方面将女性推离家庭外出工作;另一方面又顺承生理性别的传统偏见,将女性锁在家中伺候丈夫和育儿,就算请服务业帮助也难以支付薪资①。同理,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公有制转为私有制,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鲜明区分再次浮出表面,因此,妇女所面临的家庭压力只会更大,传统社会角色的分工再度来袭。马克思主义认为妇女解放的关键在于经济独立,从希蒂洛娃的《不同的事》和《雏菊》中也可以看出,没有收入来源的女性要么困于家庭丧失自由,要么招摇撞骗心灵异化,都是需要依附于男性才得以生存;而在《禁果游戏》和《愉快的时刻》中,有稳定工作和独立自强的女性在生活支出与精神徜徉上相对而言会更加自由,也会更易于拥有拒绝的底气。
(三)正常人与歇斯底里的“神经质”女性
法国哲学家露西·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在《他者女人的窥镜》(Speculum:De lautre femme)中提到,“歇斯底里(hysteria)”这个词早在1980年就成了临床上弃用的医学术语,而在此前一直是用以指代女性的特有疾病,其中一大症状便是“神经质”。在希蒂洛娃的电影作品中,常常可以看见这样的“神经质”女性,她们的情绪总是忽上忽下,比别人更加容易焦虑、愤怒、痛苦和绝望,例如《不同的事》中被丈夫坦白出轨要求离婚的Vera、《天堂禁果》中手捧红花情绪大变的Eve、《预制板的故事》中的“Dying mom”,以及《愉快的时刻》中面对镜头崩溃狂笑的Hana。一般来讲,任何人都可能发生神经质症状,但需要处于特定条件下,而在希蒂洛娃的笔下,这些女性通常只有两个起因:一是无爱难续的家庭与情感纽带;二是离轨混乱的心灵与当代社会。行动自由的世界里布满了伸缩紧扣的网,也许上一秒即将发生质变,但在下一秒就因为内心的崩溃而选择了退缩。《陷阱》中的女性为了复仇做出了许多出格的事情,理智、判断与自爱是其勇气的构成,但当权力以玩笑形式进行堂而皇之地撒谎与包庇时,一切努力便都化作了推动隐喻男性生殖器官的广告牌完成的工具,当受害者成为被特权阶级戏弄的对象,再歇斯底里的呐喊也无人应答。
三、个人主义与女性主义的融合再思考
(一)东欧土壤孕育下的个人主义与女性主义之争
Antonín J · Liehm是出生于布拉格的一位电影批评家,其发表于1974年的《近看電影》(Closely Watched Films)中收录了一篇希蒂洛娃的采访稿,文中希蒂洛娃强调表明“与其说我是女性主义者,还不如说我是个人主义者” ②。此番言论的背景位于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浪潮期间,彼时的西方女性正竭力强调参政、就业等多方面自由,并提出了“个人的就是政治的”等权力主张。而这番偏颇言论的出现即代表着东欧历史车轮的印记引导人民对西方思想采取抵制态度,导致本土女性十分抗拒“社会性别”这个词,社会主义时期内男女携手奋斗,而诞生于资本主义的女性主义只会造成不必要的性别分裂③,因而需要加上特有的阶级因素,去重建本土的女性宣言,希蒂洛娃的言论无疑是最好的证明。但从电影记录来看,这并非是个体女性/男性所遭遇的特殊问题,也并非是存在于单个家庭内部的罕见裂变,而是同处于性别秩序被严格划分的社会下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换言之,不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只要社会性别的本质没有改变,那么女性主义者和自由个人主义者的目标就都是寻求实现真正的两性平等与众生平等。
(二)希蒂洛娃创作观念的当下性思考
如今的电影舞台上,女性导演的身影总是随处可见,女性角色的形象设计也在逐渐变得丰富,话语权的趋向平衡无疑代表着社会文明与包容程度的不断提升。希蒂洛娃以女性视角与镜头叙事的关怀,以各类边缘女性角色的书写,以用肉身碰撞陈规旧序的决心摆脱了时代束缚,将话语溶于画面,影响了一代代执镜作笔的新人。
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Chizuko Ueno)曾说过:“女性主义即追求一种所有弱者都能够受到尊重的社会。”希蒂洛娃虽不同意被贴上女性主义的标签,但其作品无疑为女性形象与话语权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丰富了两性政治的表达,对当代社会问题提出了批判与思考。因此,借由希蒂洛娃的创作经验与女性言说的珍贵价值,应在鼓励个人创作与主旨表达的同时,将目光放到全社会与众生平等的高度上,以追求男女两性的真正平等去进行性别政治相关的艺术创作,去找寻女性身心解放的正确途径;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和思考改正的态度去看待当代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注释:
①朱禹洁:《玛丽亚·马尔库什的社会学思想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②Liehm、Antonín J:《Closely Watched Films:The Czechoslovak Experience》,纽约白原市国际艺术与科学出版社1974年版。
③汪琦、陈密:《视线向东:接纳东欧女性主义》,《妇女研究论丛》2016年第1期,第97-106页。
参考文献:
[1]汪琦,陈密.视线向东:接纳东欧女性主义[J].妇女研究论丛,2016,(01):97-106.
[2]张颖.微拉·齐蒂洛娃的电影道德笔记——访谈录[J].当代电影,2019,(03):99-101.
[3]郭燕平.性别政治、反讽叙事与现代性焦虑——薇拉·齐蒂洛娃创作通论[J].当代电影,2019,(03):82-87.
[4]朱进进.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历程、理论界定及其发展前景[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9,(01):13-18.
作者简介:
郑齐铮,武汉大学,戏剧与影视学专业,研究方向: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