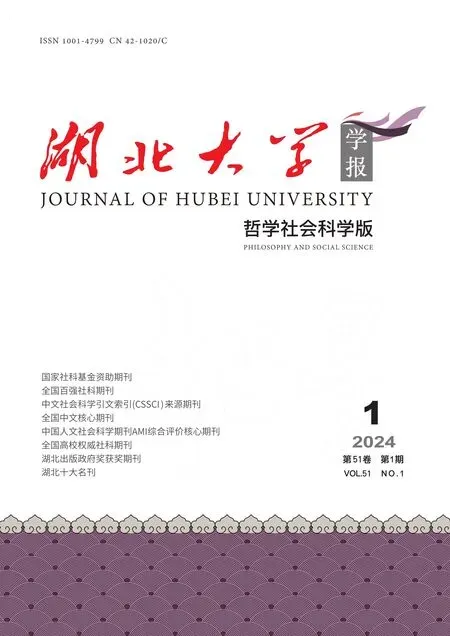从FORM到FORMALISM:形式自律简史
冯黎明
(湖北民族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 湖北 恩施 445000)
形式主义与审美伦理是艺术自律论的两根支柱。形式主义为艺术自律论提供了艺术独立于日常生活习性状态的“异质性”文本结构维度上的合法化依据,审美伦理则给予艺术自律论以“人性解放”的终极性价值约定。形式主义用艺术文本的新异性结构为审美伦理拟订“诗意栖居”的“营造法式”,而审美伦理则将形式主义提升成为一种逃离现代性大洪水的救赎之道。从西方审美文化的历史来看,“形式”由“载体”转型为“本体”直至升级为“主体”甚至“主义”,乃是艺术自律论生成的核心机制,这一转型是由康德美学开启继而由形式主义完成的。“形式”一旦被提升为“主义”,则艺术和艺术家便因为握有制造形式的独门秘笈而跃出了沉沦的世俗生活世界,成为不受日常生活秩序约束并摆脱了功利主义伦理牢笼的自律性存在。
一、质料/形式:知识学的二元论
从知识论角度来看,古典时代的中国和西方都曾经形成过一种二元论的认知模式,在中国古典思想中这种二元论最早的表现大概是《易经》中“象”和“形”的对应分解,后来则演化为“形”与“神”的二元论、“道”与“器”的二元论或者“言”与“意”的二元论等等;而在西方的形而上学思想谱系中,这种二元论的最典型形态则是所谓“本质”与“表象”的二元论、“内容”与“形式”的二元论或者“理性”与“感性”的二元论等等。就像“形/神”二元论、“言/意”二元论深刻地影响到了中国古典艺术哲学一样,在西方思想文化史上,由古希腊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演绎出来的“内容/形式”二元论直接建构了一种普适性的艺术阐释模型。古典知识学的这种二元论通过将认知对象切分为相互关联的两个部分并且让这“二元”相互说明,由此构成了关于普遍真理的因果关系的诠释。其中,最为著名者莫过于柏拉图借“洞穴比喻”区分可知的世界与可感的世界,从这一二元论出发,柏拉图得以确定了eidos/idea的真理性。无论是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宇宙论知识学还是中国思想的伦理本体论知识学,古典哲学的二元论都呈现为二元等级秩序的构型,比如“本质”高于“表象”、“内容”先于“形式”、“道”优于“器”、“意”重于“言”;比如在老子那里,“大象”甚至可以“无形”。因此当古代智者们把二元论知识学模型用于解释艺术问题的时候,艺术哲学也被赋予了一种二元等级的理论结构,比如西方的内容决定形式、中国的神似高于形似的艺术观念。
在柏拉图的二元论中,eidos概念是由idein(观看)延伸而来的,因此这个词也跟morphe(形状)的意义相关。柏拉图赋予eidos以普遍、绝对和神性的含义,于是“形状”便超越个别的可见之物成为了形而上的“理想”或曰“理式”,而个别的可见之物的外形则被视为与真理隔膜的表象。柏拉图以此二元论解释诗学问题,认为模仿个别可见之物的诗人除非进入迷狂状态,否则是没有可能哪怕迷蒙地靠近真理的。柏拉图的eidos概念虽然在词源上跟“形式”相关,但是却被他改造成了后来西方艺术哲学传统中高于形式的“内容”,类似于黑格尔美学中被“感性显现”所表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不认同柏拉图将实体和理式分离,但是他仍然从二元论的知识学层面解释存在,只不过亚里士多德的“质料/形式”二元论的“形式”并未脱离实体而已。亚里士多德先是在《物理学》中将物理世界的存在区分为质料、动力、形式、目的四因,后来又在《形而上学》中区分为质料和形式二因。亚里士多德的质料表现为事物的无规定性的个别状态,与之对应的“形式”则具有着普遍规定性的逻各斯功能。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因为诗依照“可然律”而非“必然律”描述可能发生的行动,“可然律”跟形式化的逻各斯相关,所以诗是能够表达普遍真理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二元论知识学开创了西方艺术哲学的一种审美形而上学传统,即:艺术通过描述个别事物的可见外观而间接地表达普遍性的形而上真理。这里应该辨明的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在理式、逻各斯等形而上的真理论意义上使用“形式”概念的,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开创了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形式本体论。当古希腊智者们将这种知识学的二元论用以解释诗学问题的时候,便引生出后来以“内容/形式”二元等级秩序为学理主轴的艺术哲学和诗学。古希腊之后的西方艺术哲学和诗学中的“内容/形式”二元等级秩序逐渐将“形式”概念跟真理的内涵分离,多数学者都只是在表现论或者技艺论意义上使用其form的含义,即事物的外观表象而非本体或真理,这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智者们以形式为本体的认识有明显的差异。经过后来普罗提诺、奥古斯丁以及文艺复兴时代的学者们的解释,古希腊的二元论艺术哲学逐渐演变成为了内容形式二分、内容决定形式、形式表达内容这样一套美学信念。在这一美学信念中,被古希腊智者们认定为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普遍形式却被降低为服从所谓“内容”的感性外观。这一信念在古希腊之后的西方思想文化历史中的形成跟神学的普及不无关系,因为神学思维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超验真理和经验世界构成二元等级秩序,它让我们在艺术哲学和宇宙哲学之间看见了一种知识学维度上的同构关系。“内容/形式”二元等级秩序的信念到黑格尔美学发展至顶峰,形成了完整的艺术哲学理论系统。当然,古希腊之后的西方形而上学历史上,“形式”概念有过多种意义上的使用,但是“内容/形式”二元等级秩序的基本框架一直持续到19世纪,直至形式主义的艺术理论以康德哲学为据重新论证形式本体论。
符·塔达基维奇在《西方美学概念史》中解释了西方美学史上“形式”概念的诸种内涵和用法,他将其归纳为五种基本类型:第一种是形式A,即“各部分的排列”,这主要指结构;第二种是形式B,即“被直接感觉到的东西”,这主要指外观;第三种是形式C,即“对象的范围或轮廓”,这主要指造型(其实形式A、形式B和形式C三种形式近似,可归为一类);第四种是形式D,即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隐德莱希”,“表示对象的概念本质”;第五种是形式E,即康德哲学意义上的“心灵对感性对象的作用”,这可以看作是先验理性的“内在形式”(1)符·塔达基维奇:《西方美学概念史》,褚朔维译,北京:学苑出版社,1990年,第297-298页。。塔达基维奇的A、B、C三种形式指的都是艺术作品的感性表象,属于传统的“内容/形式”二元等级秩序中的“形式”。在描述了这五种形式概念的历史演变之后,塔达基维奇还对康德之后的形式概念作了一些解释,其中主要涉及斯比格尼乌·普洛纳斯科、阿道夫·希尔德布兰德以及艾柯等人的形式观。
塔达基维奇对形式概念的分类其实可以归纳为三种形态的形式理论:第一种形式观视形式为艺术作品的外观、表象,跟作为内容的思想、真理相对应,包括艺术作品中各部分的排列、造型轮廓、感性外观等等,这是传统艺术哲学的主流观念;第二种形式观其实应该称为“形式化思维”,这种所谓“形式”更像柏拉图的eidos或者亚里士多德的“逻各斯”,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的认知方式;第三种形式观是康德美学关于形式的自由游戏的论说,即艺术的本质在于先验的、内在的、主观的形式的游戏性外化。在康德的先验哲学中,物自体是无形式因而也是“不可知”的,形式属于先验理性的范畴,是想象力自由游戏的表象,因此形式乃是艺术之“本体”。
就“形式”概念而言,康德之前长期主宰西方审美文化历史的主要是“形式化思维”和“感性外观”这两种形态。作为形而上学的起源,形式化思维用抽象的概念或者逻辑模型祛除存在的个别表象,以形而上的“一”解释形而下的“多”,从而达成一种宇宙论意义上的普遍真理。古希腊之后,“形式化思维”决定了西方思想的形而上学路向,也为西方文明走向现代性提供了知识学的动力装置(2)关于“形式化思维”,参见冯黎明:《形式研究与形式化方法》,《文艺研究》2012年第1期。。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批评的那种“形式主义”学术,就是这种形式化思维的表现。卡尔·曼海姆论述知识社会学的时候则把“形式有效性”跟“实证主义”并列为两种具备了合法性的知识生产方式(3)参见卡尔·曼海姆:《卡尔·曼海姆精粹》,徐彬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19页。。在艺术哲学领域,“形式化思维”更多地是在方法论意义上形成了范式美学的理论路径,比如著名的“三一律”就是形式化思维的典型案例。从对艺术品的属性和结构的理解来看,西方美学传统中占据主流位置的是视形式为对应于内容的感性表象的观点。当然,这种载体论的形式观跟形式化思维在知识学上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因为作为“感性外观”的形式得以出场的原因恰恰在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认知范式让作为本质的逻各斯失去了“身体”,感性的表象于是就演变成了显现逻各斯的“载体”。在西方形而上学的知识学二元论传统中,作为跟本体(理性、真理等等)相对应的载体(表象、结构等等),形式被认为是低于内容的二级元素。内容和形式的二项分离形成了一个等级秩序,内容主宰着形式,形式服从于内容。
因为形式是为表现内容而存在的载体,所以形式又跟“技艺”发生着密切的关系。历史上艺术家长期被视作“能工巧匠”,人们认为艺术家的工作跟领悟真理没有实质性的关系,艺术家只是一群制作精美的外观形式的物品以显示真理的装潢工匠。这种技艺论跟“内容/形式”二元等级秩序一起阻断了艺术的自律性念想,因为居于从属地位的形式必须接受作为主体的内容的统治,而且作为工匠的艺术家又只具有制作形式的能力,“内容”是由神或者领悟了神的意志的王者们订立的。文艺复兴之后,西方艺术理论开始在“美”的维度上构想艺术的属性,制作美的外观形式的艺术家们的地位很快得到提升。当“美”取代“真理”成为艺术的独立内涵时,以技艺创造美的形式的艺术逐渐获得了自立门户的观念条件。既然艺术之本性在于美,而由技艺创造出来的形式美恰恰就是美之存在性的表达,那么美的形式就可以视作艺术的独立属性的显现。发端于文艺复兴的“美的艺术”观念演进至启蒙时代,已经得到了知识精英们的基本认可。至康德美学诞生,“内容/形式”二元等级秩序终于被“形式本体论”取代,艺术也借助于自身特有的先验属性而跟合概念性的知识活动、合目的性的伦理活动划清了界限。康德用形式的自由游戏来界定艺术的本质,这一全新的艺术本体论意味着艺术在人类社会实践中的独立性存在,因此可以说形式的本体论是通向艺术自律论的起点。形式主义者罗杰·弗莱在后期印象派中发现了绘画艺术的现代变化:“长期形成的习惯产生了根深蒂固的信条,这种信条便造成了异议:绘画的目的就是对自然形体的描绘摹仿。如今,这些艺术家并不追求其实只是真实外形的平淡无奇的复制,而是想方设法激发人们对崭新明确的现实的信念。他们企求的不是摹仿形体,而是创造形体,不是摹绘生活,而是寻找生活的等价替代物。”(4)罗杰·弗赖伊:《法国后印象派画家》,弗兰西斯·弗兰契娜、查尔斯·哈里森编:《现代艺术和现代主义》,张坚、王晓文译,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第139页。这就是说,现代艺术要创造一种不依附于实存事物的“人造”形体。可见,随着艺术自律论的蔓延,艺术形式启动了跳出二元等级秩序、寻求独立自主的程序。
二、从形式载体论到形式本体论
尽管阿尔贝蒂、齐美尔曼等人认可古典艺术的“形式美”特性,但是因为古典时代艺术的最高价值在于“表达真理”,所以被视为“载体”的形式即使具备了“审美特性”也不足以升级为“本体”。二元论知识学的艺术哲学设定了艺术作品的“内容/形式”二项分离式存在、内容涉及普遍真理而形式涉及个别表象、内容决定形式而形式表达内容,这种古典主义艺术观念在黑格尔美学中演绎为完整严谨的理论体系。对于黑格尔来说,绝对精神在感性实在的表象中完成了其现实性,此乃艺术的历史性存在的依据,因此作为表象的“形式”不可能脱离作为理念的“内容”而独立存在。黑格尔写道:“艺术的内容就是理念,艺术的形式就是诉诸感官的形象。艺术要把这两方面调和成为一种自由的统一的整体。”(5)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87页。这在艺术中具体表现为“理念的感性显现”,只是黑格尔特别强调内容和形式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就像他把绝对精神和实在之间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视为世界历史的主题一样。在《小逻辑》第二篇“本质论”中讨论“内容与形式”(Inhalt und Form)时黑格尔明确地说:“内容非他,即形式之转化为内容;形式非他,即内容之转化为形式。”(6)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78页。这种辩证式关系固然强调了形式的不可或缺,但是其作为载体而非本体的属性并未发生变化。黑格尔并不认可由康德先验哲学开创的自律论美学,因为“理念的感性显现”这一规定性在本质上就排除了形式自由的可能性。绝对精神跃出感性实在走向自由这一终极性的价值归宿决定了作为理念的感性显现的艺术只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当绝对精神不再需要借助于感性形式获得现实性的时候——黑格尔认定这是浪漫主义之后艺术的宿命——艺术也就“历史性”地终结了。
如果说黑格尔美学体现了古典主义艺术的审美理想,那么康德美学更多地体现了审美现代性的历史趋势。康德美学对于审美现代性的启示性意义主要来自于《判断力批判》有关艺术自律的论说,这一论说是康德先验哲学的自然结果,它在理论上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是审美伦理的自主性,其二是形式本体论。
文艺复兴时代建立起来的西方经典艺术范式的基础是写实主义,写实主义艺术观念把对存在之物的还原当成艺术的本质属性,它强调“形式”服从“质料”。但是文艺复兴晚期在意大利出现的样式主义(Maniera)艺术也曾经表现出一种追求形式独立性的倾向,比如彭托尔莫《十字架》中色彩与人体自然特征的背离,还有丁托列托、布隆齐诺等人画作中光和色的独立性,都显示出写实主义和焦点透视的艺术体制规定了形式(光影、色彩、线条、形体等等)服从物象的范式之后艺术家的一种挑战秩序的冲动。样式主义艺术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无视古典文化的整一性宇宙论,试图让外观形式脱离世界的内质而自由呈现,这打破了自然事物的同一性,让人联想到启蒙现代性把“应当”和“存在”分开破坏了神创宇宙的同一性。样式主义艺术后来受到人们多方诟病,西方艺术的主流仍然是写实,人们仍然坚信形式只是表现事物的“载体”,直到启蒙时代的浪漫主义审美文化开始重启当初样式主义艺术的形式独立性实验。到康德的时代,夏尔·巴托依据阿尔贝蒂以来关于“美的艺术”的认识把“美”设定为艺术的本质,于是属于美的范畴的形式在艺术中的依从地位得到改善。让-菲利普·拉莫的《和声学基本原则》认为音乐只是一种规则化的声音,后来施莱格尔意欲构建的“绝对音乐”指的也是这种完全形式化的音乐艺术。康德美学对启蒙精英们关于形式化艺术的想象予以先验哲学的论证,在“自律性”的维度上使得自主性和自洽性的形式游戏成为艺术的本质属性。
古典思想是从形式论层面上理解美的,比如托马斯·阿奎那关于美的描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启蒙时代。英国经验主义思想家们将美从物的形式特性转移至人的行为特性,这启发康德在先验理性维度上思考美之属性,以至于将美提升到伦理立法机制的高度。文艺复兴以后,美逐渐被视为艺术的存在性,因此随着美由物的形式特性转变为跟人类自由相关的伦理立法机制,艺术在人类社会实践中也获得了一个自主性的相位。这里的关键之处在于作为形式特性的美转型为人类行为的一种特性,这一转型使得“美的艺术”不再是“载道”的光鲜外表,而上升成特定价值或者真理的“策源地”。启蒙时代发生的这场“形式”的革命是由旗手康德最后完成的。关于康德美学对审美伦理的论说,学界已经有详细的阐述,本文不再展开叙述。就康德有关形式问题的论说而言,其中最为关键之处在于康德把西方美学传统中的形式载体论转变为形式本体论。康德说:“美是一个对象的合目的性形式,如果这形式是没有一个目的的表象而在对象身上被知觉到的话。”(7)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2页。尽管康德没有完全排除作为实存者的外观、轮廓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形式”,但是他只是从“依附美”而非“自由美”的意义上给予此类对象的概念性形式以美学意义的。从《判断力批判》第11、12两节讨论“合目的性的形式”与鉴赏判断的关系的内涵上来看,康德的“形式”指的是内在的、主观的、先验的心灵的形式。这一点也可以从《纯粹理性批判》讨论“纯粹知性概念的图型法”的内涵中见出来,康德写道:“理念为了实现出来,就需要一个图型,即需要一个从目的原则中先天得到规定的本质性的杂多和各部分的秩序。”(8)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29-630页。很显然,这里的“图型”属于先验性和目的性的范畴,因此它作为形式类似于柏拉图的“理式”。康德就这样把形式从物象中赎回交还给了判断力活动的主体,而主体则由此获得了通过想象力游戏创造形式的自由。正是借助于形式的自主性显现这种本体论,康德美学将形式的自由游戏推进至艺术的自律性存在的境界。康德美学论证形式本体论的一道关键程序在于他把“形式”从“事物的显现方式”这一传统信念中解放出来,将其置于先验理性的范畴之中论证其对无形式的“物自体”形式化的作用。康德的先验哲学否定了物自体本身具有结构性形式的认识,在康德看来,理性对于世界的认知不是因为事物的表象形式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其本质的载体,而是主体将先验性的概念或者目的投向物自体从而赋予了物自体以可理解的形式,因此“形式”不是事物的表象而是理性的对象化,形式源自于先验理性的主体而非实然性的“物”。
进入19世纪后,康德美学的艺术自律论朝向两个方向推进,其一是唯美主义的审美伦理实践,其二是形式本体论的艺术学理论体系。如果说唯美主义者们以康德的审美伦理为生存哲学演绎了艺术自律论的生活实践进而启发了20世纪的审美解放论的话,那么从19世纪中期的汉斯立克到20世纪前期的罗杰·弗莱的形式本体论美学则以康德美学的形式游戏论为理论基石,构建出“纯形式”的艺术哲学体系进而引导了先锋艺术的形式革命。审美伦理和形式本体论是康德美学艺术自律论的两道核心程序,它们分别构成了艺术自律的价值论支点和存在论支点,同时它们又从价值论和存在论两个方面构筑起审美现代性的观念大厦。
自从康德把形式由载体提升为本体,形式游戏就很快进化成为了艺术的自主性存在的本质规定性。在审美现代性被艺术自律论孕育成型并迅速成长的19世纪,唯美主义和形式美学相互呼应,掀起了审美现代性的第一次浪潮。到19世纪晚期,欧洲审美文化界已经普遍认可了艺术自律论。随着艺术自律论在知识精英群里蔓延,艺术理论(包括各门类艺术理论和一般艺术理论)也以形式本体论为思想资源构建形式主义的阐释体系。形式主义阐释体系的理论内核在于否弃艺术的指涉性意义,将形式从对实存世界的依附中解放出来,凸显其自律、自主和自洽的特性,以形式的创造和理解、形式的构成和运作、形式的意义生产机能等为艺术理论的学理基质。形式主义艺术理论力图把康德美学关于形式的自由游戏的论说植入对具体的艺术现象的解释之中,这种解释在两个基本层面上得到展示,其一是门类艺术理论,其二是一般艺术学理论。
跟数学是最为形式化的知识活动相类似,音乐艺术先天的形式化特性使它最早被当作形式本体论的典范。继拉莫和声学之后,汉斯立克在《论音乐的美》中认为音乐艺术的审美特性不依附于外在的内容,它仅仅“存在于乐音、以及乐音的艺术组合中”(9)爱杜阿德·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音乐美学的修改新议》,杨业治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78年,第38页。。汉斯立克此论的实质在于为音乐艺术的独立性设立合法化原则,跟后期印象派用二维性来寻求绘画艺术不可复制的独立属性一样。对于一直由物象统治的绘画艺术来说,让点线面摆脱物象的纠缠表达造型的自由,这几乎就是印象派到表现主义的绘画艺术的历史主题。哈罗德·奥斯本总结20世纪初期之后的艺术发展时认为,现代艺术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把强调的重点放到符号信息而不是语义信息上,放到一件作品的形式和结构上,而不是放到它所再现和描述的事物上”(10)哈罗德·奥斯本:《20世纪艺术中的抽象和技巧》,阎嘉、黄欢译,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1988年,第11页。。到表现主义的“无物象绘画”和立体主义的“纯粹造型”,艺术形式已经上升为意义产业中的“第一生产力”,因此在比如罗杰·弗莱等艺术批评家眼中,“构图”才是绘画艺术最重要的工作内容。跟绘画、音乐艺术领域里的形式本体论思潮一样,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诗人们也极力主张诗的纯粹性。王尔德说:对于艺术家,“只有一个时间,即艺术的时刻;只有一条法则,就是形式的法则;只有一块土地,就是美的土地”(11)赵灃、徐京安主编:《唯美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90页。。在20世纪的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家们看来,诗(文学性)仅仅只是一种特定方式的“句法结构”而已。
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的百年历史中,随着各门类艺术将自有形式特性本体化以及思想文化日益趋向结构主义的“形式化”知识学,所谓“一般艺术理论”意义上的、以形式本体论为基础概念的艺术哲学也逐渐成型。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一批德国艺术理论家在康德美学的引导下致力于建立形式本体论的艺术学理论,这些学者包括阿洛伊斯·里格尔、海因里希·沃尔夫林、罗伯特·齐美尔曼、康拉德·费德勒、阿道夫·希尔德勃兰德等等。其中希尔德勃兰德在1893年出版的《造型艺术中的形式问题》一书,典型地表达了形式本体论的艺术观念。希尔德勃兰德讨论的主题是造型艺术的形式问题,但是他在书中表述的关于艺术的普遍属性的认识却完全可以纳入新康德主义哲学体系。希尔德勃兰德将形式区分为“实际形式”和“知觉形式”,实际形式属于概念而知觉形式属于判断力活动,所以艺术是知觉形式的表现,“知觉形式在内容上比实际形式更为丰富,因为在其诸因素之间存在着主观性的关系”,“事实上当一个艺术家在心里把他单纯的表现转变成富有表现力的空间价值时,他的这种表现是对整个形式世界的表现”(12)阿道夫·希尔德勃兰特:《造型艺术中的形式问题》,潘耀昌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19页。。沃尔夫林选用五对概念(线描与图绘、平面与纵深、封闭与开放、多样性与同一性、清晰性与模糊性)描述文艺复兴以来的艺术史,这五对概念的内涵全部涉及形式(13)参见海因里希·沃尔夫林:《艺术风格学——美术史的基本概念》,潘耀昌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21页。。进入20世纪后,现代主义艺术大都认可形式主义的一般艺术学理论,因为这一理论将形式本体化的做法意味着艺术与实在世界的脱离,意味着艺术可能凭借着形式的自主性将自身从外部世界的“内容”统治下解放出来。所以罗杰·弗莱、克莱夫·贝尔、阿波利奈尔等人都不再关注造型跟物象的表现性关系问题,而是热心于讨论造型本身的意义生产机制,因为他们意识到,造型(形式)才是艺术的存在本体。
形式本体论的艺术哲学通过论证形式的“先验性”而赋予形式以实在世界中的独立位置,此一逻辑继而在先锋艺术中演化出一种新的形式观,那就是形式的自由。
三、从形式自由到形式主义
进入20世纪后,先锋艺术高举艺术自律论的大旗征服了审美文化世界。先锋艺术在形式本体论的基础上继续前行,把形式的自主推向形式的自由,用形式的自由游戏异化甚至消弭质料意义上的物。就像结构语言学认定非指涉性的句法结构这一形式特性是意义的创生机制一样,先锋艺术的“新异性”形式也被认定为通往自由和解放的必由之路,也像福柯论及20世纪的知识型一样,“词”与“物”分离了,“词”不再依附于对“物”的相似性而自由了。借助于形式的自由和审美伦理,先锋艺术释放出艺术自律论的激进美学锋芒。
形式本体论终结了传统的“内容/形式”二元等级秩序并且让形式不再受到内容的限制而独立地从事意义生产,但是形式本体论并未抛弃内容,只是反过来把内容视作形式的载体,犹如备受罗杰·弗莱青睐的塞尚借助于物象表达出一种原始的单纯或者一种“造型的色彩”。就此意义而言,形式本体论尚未允许形式完全自由,形式仍然不能脱离内容这块“大地”。到立体主义和表现主义登台,形式自由论开始取代形式本体论成为艺术自律的主题。立体主义主张的“纯粹造型”和表现主义奉行的“无物象绘画”都意在让形式彻底摆脱内容的纠缠而自由游戏。康定斯基这样表述他对于绘画艺术“原则性的东西”的理解:
1、“在抽象内容上”,即从物质表面的物质形式的真实环境中脱离出来,以及
2、在物质的画面上,即通过这一画面最基本的特点产生作用。(14)瓦西里·康定斯基:《点·线·面——抽象艺术的基础》,罗世平译,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第10页。
就是说,绘画艺术的原则在于脱离物质以及物质的形式让画面本身作为物质得以显现,因此作为画面的形式跟物质无关,只跟心灵发生关系。哈罗德·奥斯本引述沃纳·哈夫曼的话评论说:“康定斯基抹去了物质的世界,否定对立,转移了他的目光。对他说来,绘画不再是人与其环境的一种对话;它是人与自己内心世界的对话,它现在可以不用求助于外部世界的已成型的象征就能交流。”(15)哈罗德·奥斯本:《20世纪艺术中的抽象和技巧》,第142页。这种跟物质世界无关的形式只能是一种康德意义上的先验形式,先验形式是自由的,因为它只涉及主体的先验理性和自由意志。康定斯基的无物象绘画诉求中蕴含着现代主体性的自我建构机制,昭示着先验人性跃出大地意义上的自由,这一自由在表现主义艺术中体现为点线面逃离物象的规约转型为绝对精神的表现。相比较而言,毕加索、乔治·布拉克等人的立体主义虽然对心灵、意志等不感兴趣,但是立体主义以造型的纯粹性为艺术的终极价值,在推崇形式的绝对自由这一意义上跟表现主义相通。瓦尔特·赫斯评价立体派说:“造型,象(像)在塞尚那里,被了解为一个与自然平行的进程,不是仿自自然。”(16)瓦尔特·赫斯编著:《欧洲现代画派画论选》,宗白华译,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第72页。立体派要把造型当成一个独立于自然的真实的存在,它具有超越自然法则的自由。
表现主义和立体主义推崇形式自由的结果就是抽象的体制化。马列维奇这样谈论他的至上主义绘画:“人们必须直接面向着色彩群自身,在它们里面寻找决定性的形式。红、绿、蓝的群的运动是不能用表述的素描反映出来的。这个动力主义正是绘画群的反叛行动,以便从物象里独立出来,解放出那些不表述何物的各形式;这就是说:纯绘画性各形式要成为主体超越理智的形式,即成为绝对主义,绘画中的新的现实主义。”(17)瓦尔特·赫斯编著:《欧洲现代画派画论选》,第150-151页。这也是蒙德里安的新造型主义的主旨,在蒙德里安看来,“抽象艺术是具体的,并且通过它的特殊表现手段,甚至于比自然主义的艺术更具体些。在造型手段的界限内,人们能够创造一新的实在”(18)瓦尔特·赫斯编著:《欧洲现代画派画论选》,第157页。。马列维奇的至上主义和蒙德里安的新造型主义将印象派以来现代艺术解放形式的实验推进到极致,在这些典型的抽象艺术中,形式不仅具有自主性,不仅可以脱离实在世界的物象,进而更是先于物象的绝对精神或者超越物象的自由意志,艺术家的形式感创造了世间从未有过的新现实。抽象艺术将形式册封为创世之神,认定艺术就是用形式进行的“创世”活动。此前的形式本体论者们还只是给予形式以自主地位,而到抽象艺术这里,形式的自主性升级为形式的自由。立体主义的纯粹造型和表现主义的无物象绘画,这两面大旗引领着现代艺术在审美现代性轨道上向前疾驰,借助于形式的自主性而获得自律性地位的现代艺术皈依了“形式拜神教”,作为创世之神的形式就像不食人间烟火的唯美主义艺术家一样飞离了大地自由翱翔,甚至向人们昭告末日救赎的神谕,被康德解放的形式现在要来解放人类了。
正是看到了形式的自由中蕴含着带领人们走出沉沦的世俗世界获得救赎的可能,所以先锋艺术登上审美文化舞台以来的艺术哲学大都高举审美解放的旗帜,坚信艺术的本质就在于一种“新异性”或者“震惊性”的形式游戏,这方面的论述绝大部分来自批判理论。对于坚持审美救世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来说,形式的自主和自由建造了与世俗世界相抗衡的审美之维,而审美对世俗世界的“否定”则让身处现代奴役之中的人类获得救赎。马尔库塞写道:“艺术的批判功能,艺术为自由而奋争所作出的奉献,存留于审美形式中”,审美形式当然不是依附在实在事物上的认知载体,它是一种“异样性”的绝对精神,“审美形式给那些习以为常的内容和经验以一种异在的力量,由此导致新的意识和新的知觉的诞生”(19)马尔库塞:《审美之维——马尔库塞美学论著集》,李小兵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212、235页。。马尔库塞这样定义他以之为艺术定性的“审美形式”,即:“所谓‘审美形式’是指把一种给定的内容(即现实的或历史的、个体的或社会的事实)变形为一种自足整体(如诗歌、戏剧、小说等)所得到的结果。有了审美形式,艺术作品就摆脱了现实的无尽的过程,获得了它本己的意味和真理。这种审美变形的实现,是通过语言、感知和理解的重组,以致于它们能使现实的本质在其现象中被揭示出来:人和自然被压抑了的潜能。”(20)马尔库塞:《审美之维——马尔库塞美学论著集》,第211页。这里的“审美形式”先于并高于实存世界的既定秩序,它体现着先验理性的主体性自由,因此它才具有改变实存世界并重新赋予实存世界以秩序的功能。马尔库塞的“审美形式”是自由游戏的形式,它否定且打破了被规定的世界的规定性,然后神创性地将一个全新的秩序赋予世界。阿多诺也认为,艺术形式的特性就在于它对现实世界的否定性,即,艺术在形式的领域里成为现实世界的对立面。事实上,用“异样事物”(das andere)这个概念解释艺术形式的特性就是阿多诺首创的。在阿多诺看来,形式创造了一种“否定性的表象”,它可以带领我们走出同一性思维从而超越现代异化,因此他认可抽象绘画、认可勋伯格的无调性音乐,甚至认可“反艺术”的艺术,因为他在这些艺术中见出了自由形式这种异样事物的社会功能——审美解放。此外,本雅明关于现代艺术“震惊性”的描述、格林伯格关于现代艺术“自我反思”的描述,都可以见出批判理论家们对先锋艺术登上历史舞台后艺术形式的“自由化”倾向的解释。在文学领域里,尽管文学很难完全脱离“指涉性”,但是仍然有一些激进的形式主义者主张文学性的本质就在于一种自由的形式,比如什克洛夫斯基给诗歌艺术的感觉下的定义:“艺术感觉使我们在其中感觉到形式(可能不仅是形式,但至少是形式)的一种感觉。”(21)维·什克洛夫斯基:《词的复活》,转引自鲍·艾亨鲍姆:《“形式方法”的理论》,茨维坦·托多罗夫编选:《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蔡鸿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9页。纯粹的声音或者纯粹的造型或许具有艺术性,但是纯粹的“词语游戏”能够产生文学性,这也许只是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幻想。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的形式本体论那里,形式虽然有了自主性,但是还不能像先锋艺术那样任由形式随心所欲,如克莱夫·贝尔就用“意味”(significant)来限制形式的活动范围或者活动规则。但是在纯粹造型和无物象绘画蔓延开来后,人们似乎意识到,形式原来可以为所欲为地塑造一个美丽新世界。
从文艺复兴到印象派的欧洲艺术传统中,“内容/形式”二元等级秩序维系着艺术的统一性,跟前现代性时代由神学信仰维系着世界的整体性一样,形式在这个统一性的艺术世界里被规定了表述内容的载体的地位。从印象派到野兽派这段时间,形式开始寻求独立,光影、线条、色调、造型等等开始脱离物象自我表达,立体主义和表现主义则干脆扔掉内容让形式彻底地独往独来,此后的先锋艺术宣布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来临,这个时代的主题就是自由游戏的形式作为造物主统治艺术世界。审美救世主义者们面对着一地鸡毛的社会现代性指望用自律性的艺术来拯救沉沦的世界,因此支撑着自律性艺术大厦的自由形式便被赋予了单凭一己之力再造同一性世界的重任。自由游戏的形式在灭掉了内容之后便成为了救世的希望,这正应了存在主义哲学的名言:自由是一种责任。
在先锋艺术以形式的自由演绎审美创世的神话的时候,不可承受的救世重负让形式开始尝试逃避自由,于是在先锋艺术潮流中出现了一种“无形式”的实验。所谓“无形式”的先锋艺术,跟阿多诺论及的“反艺术”有几分类似,其特点都体现为对造型秩序等“形式性”的逃逸或者反抗,如涂鸦艺术致力于躲避“几何学理性主义”的现代形式、行动绘画致力于消解艺术形式的可见性和实体性、超级写实主义则让事物在为之赋形的主体缺席的状态中自我显现。这些先锋艺术对既有艺术体制的冲击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被先锋艺术所崇尚的自由形式本身也被它们视为累赘。法国学者蒂埃里·德·迪夫用“当形式变成态度”这一短语来描述“无形式”的艺术。在迪夫看来,现代艺术观念相信“原生态”的人类天性本身包含着一种创造力,所以原始形态的人性的自然表达就成其为艺术了,无须后天学习那些被认为是创造了优美形式的技艺。这一观念带来的结果就是一种抛弃形式、回到混沌的“无形式”的艺术,所以“从兰波(Rimbaud)到博伊斯(Beuys)贯穿整个现代史,始终以时钟般有条不紊的规律来重复自己的口号:‘人人都是艺术家’”(22)蒂埃里·德·迪夫:《当形式变成态度——及其他》,佐亚·科库尔、梁硕恩编:《1985年以来的当代艺术理论(增订本)》,王春辰等译,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第22页。。美国学者罗莎琳德·克劳斯从巴塔耶的“背离”(deviations)一词入手将“无形式”解释为一种降低到原始状态的过程,比如克劳斯以之为例的辛迪·舍曼作品中的那些意象——“作为混沌无序的零散之物、或碎屑或恶心的物质”(23)罗莎琳德·克劳斯:《没有结论的无形式》,佐亚·科库尔、梁硕恩编:《1985年以来的当代艺术理论(增订本)》,第118页。。审美现代性希望借助于形式的独立和自由而建立起自律性的艺术体制,但同时又给予形式以“自反性”的权力,于是形式愈自由愈走向“自反”,最后就是形式获得自由的同时也注定了它走向虚无的宿命。
余论:形式成为“主义”之后
一般说来,形式在造型艺术中意味着视觉形象的光影、线条、比例、色调、形状,在语言艺术中意味着话语的句法、节奏、音韵,在音乐艺术中意味着音响的轻重缓急、抑扬顿挫……这一切被称作形式的艺术元素,在古典的整一性世界中的功能定位于表现真理、理念、思想、本质等等的载体,是低于艺术品主题的次一级元素,所以形式必须受到内容的制约,它本身不能有独立性。但是古典时代的思想文化同时又将“美”交付于形式,认为美存在于形式之中。从奥古斯丁把美视为各部分的比例以及悦目的颜色,到托马斯·阿奎那的美的三要素(完整、和谐、鲜明),再到黑格尔的“感性显现”,美在形式的观念一直是西方美学的主流观念。文艺复兴时代出现了“美的艺术”即以“美”为艺术之本体的思想,继而“美的艺术”从“美在形式”中借取来一种艺术自主性的合法性力量,艺术自律论在这里得到了一种思想史的支持。到启蒙时代,“分解式理性”要求所有社会实践都必须在理性面前重新证明自我存在的合法性,艺术则以“美”和“形式”的同一性为依据诠释自身存在的独立性,于是产生了康德美学关于艺术在“形式游戏”层面上的自律性的论说。由康德美学诞生之后审美文化的历史走向观之,形式的自主以至于自由构成了艺术自律论的两要件之一——另一要件是审美伦理。
启蒙运动以来,艺术哲学在形式问题上掀起了两次浪潮:第一次是形式的本体论,这次浪潮由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前期的各种形式主义艺术理论以及各门类艺术对自主性的阐释构成;第二次是形式的自由,这次浪潮由先锋艺术的形式革命和批判理论的审美救世主义观念构成。经历了这两次浪潮,“艺术形式”由古典时期的“内容/形式”二元等级秩序中的表象元素进化为一种具有合法化效应的“主义”。形式一旦变成“主义”,它就不再是古典时代依附在“质料”上的载体,甚至也不是近代形式本体论认定的那种借助于“意味”得以表现的自洽性结构体,作为“主义”的形式在先锋艺术中成了不受到任何限定的自由之物,它是想象力的自由游戏,是先验人性的自由表演。启蒙思想家们让审美形式主宰艺术是想要为现代性工程的项目之一——自律性的艺术——设定合法化的依据,他们认为形式自主性是艺术王国独立的基本条件。只是在“现代性之隐忧”日渐蔓延的时候,生活世界被技术理性殖民引发了审美现代性对世俗世界的否定,也引发了审美现代性的救世情结。于是通过形式本体论而获得自主地位的形式更是以一种激进的形态对抗世俗世界,它要让自己跟一切实存之物彻底斩断关联从而获得真正的自由。由此可见,先锋艺术的那种形式自由的诉求中隐含着审美救世的激情,也隐含着形式主义和审美主义在艺术自律论基础之上形成的“一体两面”的关系。格林伯格认为,现代艺术最为重要的秉性在于摆脱透视画法而趋向“平面性”,“平面性”这一形式特性意味着绘画艺术从物象的统治下逃离出来获得了真正的自主和自由,进而更是意味着“艺术作为独立的行业、门类和技能,绝对的自治,具有尊重自身的权利,而不仅仅是作为传达的载体”(24)Clement Greenberg:《走向更新的拉奥孔》,易英译,《世界美术》1991年第4期。。这就是说,形式超越质料变成“本体”彰显了现代艺术的自律性。
通过形式的自主和自由,主体走出实在世界的有限性进入先验人性自由实现的境界,这一境界以人类天性的彻底解放展现了启蒙思想的“天国”愿景。依照启蒙旗手康德的规划,审美伦理是自由王国的普遍伦理,因此形式主义在审美现代性的观念体系中以其对物的超越为审美伦理安装了启动程序。康德说“美是一对象的合目的性的形式”(25)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74页。,同时康德坚信人是目的,因此合目的性就自然跟道德在内涵上同一,“道德律乃是我们使用自由的形式上的理性条件”(26)康德:《判断力批判》下卷,韦卓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18页。,“合目的性的形式”于是就演化为一种道德行动,所以康德认为“建立鉴赏的真正的入门是道义的诸观念的演进和道德情感的培养”(27)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第205页。。很显然,康德这里谈及的道德只能是审美伦理意义上的道德,康德美学的真实内容在于通过对艺术自律的论证来设计道德在先验性维度上的审美生成机制。席勒说“只有形式才能作用到人的整体,而相反地内容只能作用于个别的功能”(28)席勒:《美育书简》,徐恒醇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第114页。,因此席勒要用形式游戏来解决现代人的人格分裂问题。唯美主义者们之所以一方面推崇形式美另一方面强调艺术家的审美化伦理生活,就是因为他们相信形式的自由游戏开启了通往审美化生存的路径。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批判理论同样看到了形式的自由游戏跟人性解放之间的关联,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都非常肯定先锋艺术在形式上的“异样性”,他们认为这种“异样性”的形式能将审美伦理赋予沉沦于功利主义伦理中的现代人,使之获得救赎和解放。形式主义和审美伦理就这样构成了艺术自律论的“一体两面”。如果说形式的自主和自由是艺术自律论的启动程序的话,那么审美伦理则带来了艺术自律论的功能扩展。艺术自律论以审美伦理引导形式游戏,为表象性质的形式注入人性自由的伦理内涵,从而将自律性的形式创造和形式展示的活动提升至人类解放的高度。
形式一旦自主以至于自由,则艺术在文本的构成形态层面上就获得了一种“否定性”的美学属性,这一属性使艺术超凡脱俗地跃出日常生活成为“孤立”的存在。形式的“孤立”使得艺术在存在论意义上摆脱了日常生活的纠缠,释放出一种自我立法的伦理想象,这就把形式的自由推进到了人性的自由的境界。艺术自律论的阐释视野中的形式游戏是一种“否定性”或者“叛逆性”的形式游戏,这种形式游戏是绝对自主性质的,它不承担表现任何先在的或外在的内容的职能。艺术自律论者们大都主张艺术形式的独特性而且以独特的形式对抗世俗世界的秩序。结构主义叙事学家热奈特写道:“自马拉美起直到俄罗斯形式主义止,尤其突出与散文体语言或日常语言相区别的‘诗之语言’的思想,诗之语言的形式特征表面上与使用格律诗句相联系,然而更深层却与改变语言的用途相联系——语言不再被作为透明的交际工具,而被视为敏感的、独立的、不可置换的材料,某种神秘的形式上的‘炼丹术’……”(29)热拉尔·热奈特:《虚构与行文》,《热奈特论文集》,史忠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94页。这种对迥异于习性的独特形式的追求使艺术摆脱了世俗生活世界,以自律性的姿态宣示审美伦理的终极性的意义旨归。先锋艺术家们在形式问题上表现出一种激进自由主义的态度,他们热衷于搞出一些让人感到“陌生”或“震惊”的视觉形态来挑战世人的观看之道,此一做法意在宣示自律性的艺术高举着形式游戏的大旗召唤人类走向自由。
形式的自主和自由意味着以创造“新异性”形式为职业生活内涵的艺术家在社会实践中的非凡地位,而艺术家与世俗性的社会实践的分离则意味着艺术自律体制的合法化。审美主义的伦理规划是从福柯谈及的那种“艺术家生活”(30)1984年2月29日,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演讲中谈到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出现了一种现代观念,即所谓“艺术家生活”,这一观念认为艺术家以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构建了艺术的真实性。参见米歇尔·福柯:《说真话的勇气:治理自我与治理他者Ⅱ》,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55页。中孕育出来的,现代社会实践中艺术家的生活方式本身就以形式游戏为其特性,因此形式的自主以至于自由便成为了艺术家职业生活独立性的有效依据。古典时代艺术家被视为工匠,他们以出色的技艺为艺术品装饰以美的形式,而艺术品的内容则已经由天神或者“哲学王”们制定。启蒙之后艺术家得益于“美的艺术”这种形式本体论思想逐渐获得自主性的社会地位,这一自主性的社会地位又形成了艺术家独特的职业内涵和职业伦理,因此艺术的自主性为艺术家创造形式美的职业内涵和审美化的职业伦理提供了合法化的依据。自浪漫主义起,形式的自主性就逐渐被认定为艺术家职业、生活和人格独立的基本原则;到唯美主义,这种形式独创性基础之上的艺术家生活就完全成型了,比如所谓“波西米亚式生活”就被人们当作艺术家生活的标志。先锋艺术占据现代审美文化舞台之后,形式本体论又上升为形式的自由,艺术家们享有着自由创造形式以至于“非理性”地创造形式的权力,这一权力更是加强了艺术家在社会实践中的独立地位。
艺术自律论激励下的形式主义艺术哲学是审美现代性生成和运作的思想动力,它把浪漫主义的主体性和独创性情结推进到唯美主义运动的“艺术家生活”方式,再继而推进到先锋艺术特立独行的形式的自由游戏。甚至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后现代文化中,我们也看到,无物象绘画诞生以来现代艺术创造的那些“震惊性”的形式元素被融入到生活世界的物品之中,散发出生存美学的色调。不过,让审美形式回归生活世界的做法并非当年艺术自律论哲学的初衷,高举艺术自律论大旗的审美主义者们推崇的是先验人性意义上形式的自由游戏,是超越了一切实存之物约束的绝对心灵的自由显现。但是在后现代文化中,自由形式似乎意识到自己正在走向失去了“大地”的虚无主义泥潭,审美救世之梦已然破灭,所以它最终还是得要降落在大地上,跟世俗世界一起经营日常生活。
早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形式主义的知识论就受到过批判。进入20世纪以后,现代性批判理论中不少思想家对现代世界的形式化以至于虚无化提出过警示,比如马克斯·韦伯、利奥·斯特劳斯、海德格尔等人。审美文化领域里最早指出形式主义有可能导致文学陷于虚无主义境地的是巴赫金,他在《文艺学中的形式方法》一书第二编中专门讨论了“形式主义的虚无主义倾向”(31)巴赫金:《文艺学中的形式方法》,李辉凡、张捷译,《巴赫金全集》第2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81-184页。。事实上先锋艺术纵情于自由形式的热情到二战以后就露出了减退之势,这体现在战后现代艺术中出现的两种形态中:其一是所谓“无形式”,这里最典型者就是行动绘画对“作品”的抛弃,还有概念艺术主张的“人人都是艺术家”,这些“无形式”的艺术潮流以原始的生命本能消解艺术自律论的审美形式;其二则是回归“质料”,让“物自体”自我呈现,这里最典型者是所谓超级写实主义绘画以及现成品艺术,它们不再坚持形式的主体性自由,而是让凭借着艺术自律论摆脱质料纠缠的形式无奈地隐匿起来,任凭质料以“原生态”显山露水。作为审美现代性之重要内涵的形式主义同样受制于现代性的“自反性”,由形式的自主到形式的自由,最后放荡不羁的自由形式终于“自反”地解构了形式本身。
“无形式”(Formlessness)的艺术出现于1950年代的欧洲,这一艺术潮流以法国艺术家让·杜布菲、意大利艺术家阿尔贝托·布里等人为代表。“无形式艺术”(Art Informel)这一术语出自法国批评家米切尔·塔皮耶的UnArtAutre(《另类艺术》,1952)一书。“无形式艺术”常常用原生态的质料拼合成为一种凌乱、粗粝的图案,以此反抗立体派以来的抽象几何形式的造型。这种对于所谓“造型形式”的挑战,我们在抽象表现主义、行动绘画以及各种“现场性”艺术、情境主义艺术中都见到过。“无形式”在从形式本体论到形式自由以至于形式意识形态的历史上难以定位,此类艺术似乎更应该由一种现代性批判理论加以解释。在海德格尔那里,“物之物性”被主体性形而上学遮蔽乃是现代世界走向虚无主义的根本原因,而作为存在者的“物”的自我显现则意味着真理被置入作品,这就是人之“诗意地栖居”的本真意义。现象学的“回到物自身”要解决的真问题是形式本体论对于物的“装置化”,现代世界的装置化用几何学的理性主义把本真之物变成了无质料的形式,于是生活世界步入虚无主义。海德格尔把艺术作品看作物性的自我“跃出”,在此“跃出”中世界的贫乏得以克服,所以在艺术中存在者进入真理。跟现象学的“回到物自身”一样,“无形式艺术”也是将“形式”看作几何学理性主义对于存在之物的遮蔽,看作存在者之存在性的虚无化。几乎所有的无形式艺术家都试图颠覆立体主义等“纯粹造型”艺术的几何化造型形式,他们希望用原初之物的“无形式性”抵抗理性主义文化对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在“无形式艺术”看来,原初的混沌之物被主体性形而上学用康德的先验形式祛除了其本真的物性,这种“现代性之隐忧”唯有让“前形式化”的原初之物自我显现才能得以解除。由此观之,无形式艺术似乎是形式意识形态生成史上的一个“非历史性”的现象,它更多地应当被放在“现代性批判”的思想维度上予以阐释。
从无形式艺术家意图挑战的“形式”来看,他们所理解的那种几何学理性主义的“形式”——比如立体主义或者至上主义的简约形式——跟后来发展出来的具有意义生产功能的“形式”似乎不太相同。就像海德格尔时代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家们一样,无形式主义者想象中的意义世界是原初之物的世界,此世界的意义性的存在被几何学造型形式隐匿了,于是他们要为这个原初的意义世界祛除形式之蔽。对于沉沦于绝对理性化的技术主义世界中的现代人来说,还原到前形式的物性世界乃是现代性批判理论设计的一条救赎之路。但是这些理论——包括无形式艺术、现场性艺术、情境主义艺术等等——没有意识到的是形式本身所具有的意义生成功能,就像纯粹声音形式的音乐艺术能够生产出某种激情一样。在结构语言学提出形式化的语义论之后,以福柯为代表的话语理论视形式(特定的谈论或者陈述的方式)为意义的生成机制;进而在话语理论的作用下,作为形式的“句法结构”成为了意义世界的创造者。此一观念延伸至艺术领域,利用自律论获得了超然独立的社会身份的艺术家们便通过创造“新异性”的形式而升级为“造物者”。“造物”是当代艺术的主体功能,当代艺术家凭借着此功能将自身提升至“造物者”的地位,于是当代艺术不再把向本真之物还原视为艺术在现代世界中的主要任务,而是把创造世间未有之物当成艺术的本性。
艺术自律论之所以能够为审美现代性提供合法性与合理性,其原因就在于形式主义和审美伦理的统一。在现代艺术的自律性体制系统中,形式的自由游戏生产出审美伦理,审美伦理的救赎功能就表现在形式游戏之中。形式的本体化以至于主体化的浪潮,不仅仅只是发生在现代艺术领域,进而在结构语言学出现之后的现代思想文化领域,同样也出现了视形式为意义生成机制的学理态势。福柯认为,文艺复兴时代的知识范式是“相似性”,近代的知识范式是“表象分析”,而19世纪后形成了一种词独立于物的“当代体验”(32)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502页。。这个“当代体验”使得结构语言学的形式分析被认定为一种有效的阐释技术,因为当代知识学认定“意义”是“结构”的产物。对于福柯来说,权力是被某种特定的话语形式生产出来的;受福柯思想的影响,新历史主义者海登·怀特在他的论文集《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中认为历史的意义来自于叙事形式;结构主义社会学用“结构模型”——比如列维·斯特劳斯的“二项对立”——分析社会体制也体现了这种形式主体论的学理路径。循此逻辑推进,“理论”和“后理论”就把资本主义批判的视角对准了资本主义的“形式”,比如伊格尔顿就认为艺术中的形式主义乃是构建和稳定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一种重要机制(33)参见特里·伊格尔顿:《资本主义与形式》,张永清、马元龙主编:《后马克思主义读本·文学批评》,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34-135页。。对于“后理论”而言,形式的革命通向解放与救赎,因此政治革命其实就是城市空间结构方式的革命、就是“可感性分配”方式的革命、就是话语结构方式的革命……于是作为“主义”的形式又被提升成为社会批判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