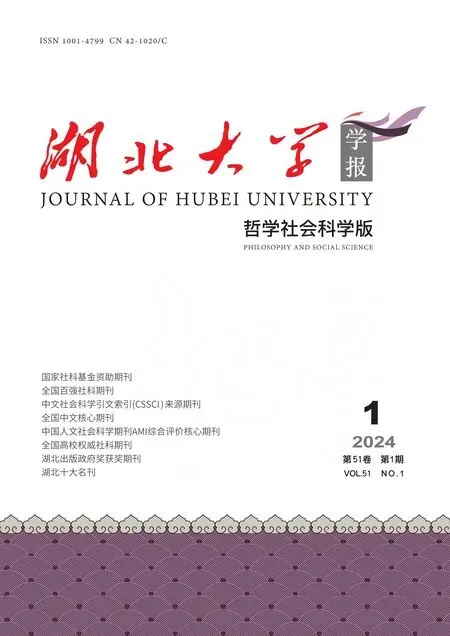重返感性:当代美学进入艺术的方式
——基于斯蒂格勒艺术观念的考察
王大桥, 冯乐群
(兰州大学 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1746年巴托以“美的艺术”(Fine Art)开启艺术的“美学化”进程,美学赋予艺术以合法性地位,使之与“技艺”层面的实用技术领域相分离(1)夏尔·巴托:《归结为同一原理的美的艺术》,高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13页。。以康德为代表的现代美学体系划定了“纯粹艺术”的范围,此后的黑格尔、谢林、阿多诺等理论家将美学发展为艺术哲学,艺术定义及其普遍法则成为审美理论的核心。艺术规定了美学研究的范围与边界,美学则演变为解读艺术的哲学学科。随着20世纪的概念艺术、现成品艺术、数字艺术等新的艺术样态不断扩展艺术概念的范围,个体的感性经验难以被形而上学美学中普遍化的审美属性所捕获,由此出现了一系列艺术“去美学化”的断言:阿瑟·丹托拒绝传统形而上学美学对“美的滥用”及其对作品的抽象审美界分,艺术自身的发展则构成了“极端的美学的反审美化”(2)阿瑟·丹托:《美的滥用:美学与艺术的概念》,王春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9页。;巴迪欧以“非美学”描绘艺术与哲学的关系,艺术作品以独立存在的真理性标识自身(3)Alain Badiou,Handbook of Inaesthetics,Alberto Toscano,tran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9-10.。美学所建构的艺术概念在面对新的艺术问题时丧失效度,当代美学需要更新理论话语,重新介入当代艺术现实。斯蒂格勒等当代美学家把重返感性作为“美学复兴”的独特进路,对艺术的考察不再局限于美的划分、审美属性与审美判断等本质问题,而是越过哲学美学坚硬的理论话语,重审艺术与感性间的双向构成关系,在对艺术之“技艺”意涵的回返中探察感性的重构方式,为实现美学与艺术的再次结盟提供了一条可行路径。
一、从审美判断到艺术的秘传性
艺术与美学的结缘使得艺术拥有了自身的评判标准,离散的艺术现象进入一个可普遍的识别体系之中。美学学科为艺术提供了身份与合法性地位,划定了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界限。康德美学以审美判断规定艺术的体验模式,建构起自律的艺术与无利害的审美愉悦。“美的艺术”不以感官感觉的愉快为准绳,而是以反思判断力为基础,引发可普遍、可传达的美的愉悦情感。不掺杂任何欲望与实用目的“审美无功利”从其他属性中孤立出来,构成艺术的核心原则,纯粹艺术于是成为美学理论的经典范例。以审美判断为核心的美学话语赋予了艺术以自主性,艺术经验不再是只属于个人的具体体验,而是拥有了主观的普遍性,并发展为一个真正独立的领域。不过,康德的审美判断以先验形式对艺术进行非历史化的处理,也造成了艺术与其他人类经验的分离。康德式艺术解读以先验主体组织知觉器官和经验材料,共通感统合了个体化的审美过程,“我”被置于“我们”的类的意义上。这使得审美经验的同一性预设主宰了具体的艺术经验,鉴赏活动的主体成为一个“无限性的投射者”,将一切艺术品接受为具有一致性的审美对象。康德之后的美学试图以不同方式统合纷繁复杂的艺术现象,旨在从特殊的经验过程中抽离出普遍性的审美标准与法则。艺术经验超越了现实而成为纯粹的审美问题,共享的艺术体系及其体验模式在不同审美理论中得以建构。
自康德以降的哲学美学以探求艺术本质为基本信念,将美学的目的转向了普世性的、恒久的艺术概念,艺术活动成为美学研究的核心范畴。美学家们对艺术的重视建构起美学与艺术间的等式关系,美学一度发展为“艺术哲学”,这几乎成为康德之后黑格尔、阿多诺等美学家的主导性认识。当代美学所面对的现实语境已不同于哲学美学,艺术自身以不断流动变化的实践抵抗审美判断的限定与规约,越来越背离了“美的艺术”理想以及引起愉悦享受的审美经验。斯蒂格勒敏锐地捕捉到美学中的艺术概念遭遇困境,杜尚的工业现成品艺术直接对美学发起挑战,标志着美学与艺术的极端分裂。在斯蒂格勒看来,哲学美学立场掩盖了艺术品不可化约的差异性与特殊性,遮蔽了处于所有艺术法则之源头的“无法还原的不规则性”,艺术哲学未能穷尽艺术品的内涵,难以涵纳当代艺术所激发的特殊审美感受。面对当代艺术创作与实践的急剧变化,美学定义艺术的方式面临危机,与艺术学之间的传统等式关系走向断裂。
无论是“基于艺术发展的现实对美学的挑战,还是美学自身的阈限”(4)王大桥、刘洋:《杜尚之后的康德疑难与迪弗的美学重构》,《中国图书评论》2023年第6期。,美学必须扩展自身的理论边界与视野以适应艺术的变革。与此同时,今天的艺术也亟需美学为之提供深刻的理论洞见,呼唤一种新的艺术识别机制。如果只讨论单数形式的艺术,艺术将成为可以随意对待的对象,其内涵将迷失在众多版本的阐释之中。美学为区别不同的艺术实践形式提供有用的概念和理论,其中“哪一种审美理论——哪种艺术哲学将能够对(或者已经对)已产生的、已展现的但却至今仍缺乏充分理论展开的当代艺术进行理论反思呢?回答这个问题显然需要我们复兴美学及审美理论的意义”(5)阿莱西·艾尔雅维茨:《美学:从20到21世纪的发展历程》,张睿靖译,阿莱西·艾尔雅维茨、高建平主编:《美学的复兴》,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5页。。当代美学以多种研究路径重新进入艺术,杜威和舒斯特曼的实用主义进路将艺术经验置于人类生活的经验之中,从美的艺术扩展至生活艺术,从而促进美学的复兴;贝林特则将包括艺术经验在内的审美经验整合到感知场域,以“审美介入”重申艺术体验与艺术世界之外“人的经验”之间的联系。当下的美学不再以审美判断这一普遍问题思考艺术,而是质疑艺术概念的独一无二性,否定艺术的同一性关系和普遍性在场方式,转向具体的艺术与感性经验等问题。美学从不同路径超越艺术哲学的范畴,向着更为具体和特殊的个体经验回撤,让感觉的身体成为技能与生活艺术的承载者,艺术作品回归流动生成的感性现场与日常生活语境。
在“美学复兴”的诸多理论进路中,以朗西埃和斯蒂格勒为代表的当代美学从关于艺术或者美的哲学和科学中解放出来,突破了辨识艺术的“艺术体制”范畴,转向流动生成的感性经验领域。朗西埃将美学定义为“可感性经验的重构”(6)雅克·朗西埃:《美学异托邦》,蒋洪生译,汪民安、郭晓彦主编:《生产》第8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6页。,美学既不是一般的艺术理论,也不是将艺术作为其全部研究对象的学科,而是“可感性、可说性和可想性的布局”(7)雅克·朗西埃:《美学异托邦》,第212页。。艺术被视为一种专属于其产品的可感的存在物,属于某种可感元素的存在模式,“艺术作品得以生产,是靠一种塑造了感性体验的肌理。这种肌理,关联着一些实际状况,比如表演和展览的空间,流传和复制的形式,同时,它也关系到认识所处的模式、情感所受的制约、作品所属的分类、作品的评价和阐释所用的思考图式”(8)雅克·朗西埃:《美感论:艺术审美体制的世纪场景》,赵子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页。。由于艺术不断重构感性,艺术史来自于感性肌理的一系列历史性变换,因此朗西埃将塑造可感肌理与认知形式的艺术纳入其美学研究视野。艺术之所以被称为“美学的”,在于它指定了可感性分配的模式,美学由此成为艺术的识别机制,即“艺术的审美体制”。朗西埃的审美体制与可感性分配在深层次上紧密相连,受“感性的分配”理论的深刻影响,斯蒂格勒同样对美学进行超艺术的理解。美学问题即普遍意义上的感觉(sensation)问题,即一种运行着个体的情感与感性的学科。在朗西埃的基础上,斯蒂格勒的美学(aesthetics)既是感觉(aesthesis)的一个扩展概念,也包含了感性在世界中的体外化形式,作为人工制品的艺术则构成感性的典型外化方式。面对思辨美学对艺术多样性的贬损,斯蒂格勒发掘了感觉在创造艺术时的重要作用,并以感性体验的多元性质疑传统美学中艺术的在场方式,引导了当代美学重新介入艺术的独特进路。
从艺术体验的独特性角度出发,斯蒂格勒阐发了美学对于辨识艺术之特殊性的独特方式,具体的感性活动挑战了既有的艺术概念,在此基础上美学让艺术获得了崭新的定位。不同于试图将艺术品归于特定艺术谱系之下的分析契机,斯蒂格勒以感性(sensible)概念批判康德的先验美学(9)Serge Trottein,“Technics,or the Fading Away of Aesthetics:The Sensible and the Question of Kant”,Christina Howells,Gerald Moore,eds.,Stiegler and Technics,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3,p.90.。不同个体在面对同一艺术作品时的体验千差万别,这种争议性既先天地被排除在康德的审美判断之外,又为审美判断的先验定义确立了基础。斯蒂格勒从康德美学中发掘了个体经验的独特性向度,鉴赏判断永远不能得到所有人的同意,甚至不能作出这样的要求,潜在的普遍化信念恰恰基于感性的特殊性。正是“在保持这种总是未实现,有待到来的状态中”(10)贝尔纳·斯蒂格勒:《人类纪里的艺术:斯蒂格勒中国美院讲座》,陆兴华、许煜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5页。,艺术体验才得以存在。为了捍卫艺术现象的独特性,巴迪欧主张艺术本身就是真理的生产程序之一,因此以“非美学”描绘艺术作品独立存在的真理性。而在斯蒂格勒对美学的界定中,艺术作为可感元素的存在模式与特殊经验的对象,其“独特性就是感觉性”(11)贝尔纳·斯蒂格勒:《象征的贫困2:感性的灾难》,张新木、刘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28页。。艺术即感性的经历,艺术之间的争论性与不确定性就是感性的独特性,其不可通约之处指向了情感与体验的惊奇。艺术中的差异性感觉构筑了集体个体化结构,主体导入了一种基于共同领会的综合,而非康德先验的“共通感”与知性的综合。对于斯蒂格勒而言,艺术成为承载感觉经验的特殊领域,充当独特物的感性为美学与艺术之关系的重建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区别于康德对鉴赏判断之主观普遍性的解读,斯蒂格勒将个体感性的特殊性进一步阐明为无法化约的神秘与错失,艺术在这个意义上从可普遍的审美愉悦转变为内在的秘传性。在斯蒂格勒看来,传统美学或形而上学美学遭遇谴责之处正在于以论证取代了演示,以知解力、沉思与公理代替了神秘的感性,悬置了艺术活动中人的身体行为和全部感受力。而独特的个体感性表现为一种神秘与意外属性,斯蒂格勒将之阐释为艺术的特殊属性,它超越了可再现性的分析与认识契机,指向作品的开放、不确定与未完成的特性。一件艺术品之所以称之为艺术,原因并不在于它是否符合任何一种普遍化的艺术准则,而在于它能否引发神秘性的感觉瞬间。“一件作品只有当它在感性上影响我们时,才发生作用,好像它突然使我们一下子注意到它。只有当它将我们拖入一种神秘,这一突然的呈现才能将我们深深吸引住,才能在感性上影响我们”(12)贝尔纳·斯蒂格勒:《人类纪里的艺术:斯蒂格勒中国美院讲座》,第43页。。受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启发,斯蒂格勒摒弃了认识论美学在主客二分的知识框架中考察艺术的方式,后者脱离了艺术作品的具体语境,对之进行对象性分析和认知。而在斯蒂格勒的艺术观念中,艺术连同它的世界关系一起呈现,我们与艺术的相遇成为偶然性的体验事件。当艺术激发了我们的惊奇,或是我们经验了作品的某种神秘之后,艺术才向我们显现出来。作品秘授的展演性承载了艺术“必须的意外”,揭示了此时此刻的感觉经验,又通向了现实之外的经验平面,蕴含着流动不居的人类感性及其不可化约的独特面向。
二、艺术的感性学谱系与感性的技艺性
朗西埃以“艺术的审美体制”重置艺术与美学的关联,将艺术视为可感力量的不可化约和异质性的在场。艺术是一个关于可感物的政治分配领域,艺术中新的跨个体化则是感性之物的重新配置,这指向了美学的政治维度。斯蒂格勒借用朗西埃“感性的分配”指认艺术的在场方式,在政治美学的视域之外建立艺术与技术现实间的关系,发掘朗西埃所忽略的工业技术对感觉性的独特作用(13)贝尔纳·斯蒂格勒:《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张新木、庞茂森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5页。。丹尼尔·罗斯指出朗西埃与斯蒂格勒对“感性的分配”这一概念的指涉不同,认为前者更多地指向艺术作为感性分配方式的政治意涵,后者则侧重于不同技术配置下感性之物的转变,“朗西埃没有想到的是,美学,即感性和感觉,已经成为一种对生活的诸方面进行计算与控制的特殊手段,它通过发明审美与情感技术来配置同步化的经验、欲望以及行为”(14)Daniel Ross,“Politics and Aesthetics,or,Transformations of Aristotle in Bernard Stiegler”,Transformations Journal of Media &Culture,No.17,2009.。朗西埃所指涉的艺术既不是美术也不是技艺,而是表现感觉自身差异性的审美体制。而对于斯蒂格勒而言,这种对艺术之感性肌理的考察,忽略了控制感觉的技术,以及技术所建构的感官的去功能化、再功能化和符号化过程。感性载入了艺术这一人造物的配置之中,并显现为神秘性、未完成性与意外属性。在感性与艺术之相互构成关系基础上,斯蒂格勒将感受力理解为一种“技艺”的建构,旨在思考技术与艺术的叠合。作为技术的最高形式,艺术的发展蕴含了人类感受方式的变化,因此艺术问题重新成为一个美学问题。
“感性的分配”无疑为艺术研究打开了新的进路,斯蒂格勒在此基础上将技艺作为感知的外化形式与语法化装置,思考感性问题的技艺性。继承海德格尔对艺术的理解,斯蒂格勒重返艺术的技艺性,将工艺、手艺、技巧与技术等要素包含在艺术范围之内(15)A.J.Pierce,“Aesthetic Medi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Technology:(re)New (ed) Strategies for a Critical Social Theory”,Critical Horizons,Vol.15,No.1,2014.。经由海德格尔对古希腊的艺术概念——技艺(tekhnē)一词的词源学考辨,斯蒂格勒认为人的存在可以通过反思这一词语的概念来理解,技艺同时也是包含感性的原始技术性的艺术(ars)。古希腊人优先将技术与艺术作品称为技艺,是因为艺术是最直接地标识存在的东西(16)Bernard Stiegler,The Neganthropocene,Daniel Ross,trans.,London:Open Humanities Press,2018,p.263.。艺术在作品中以其自身的表象进入了存在,存在的显现正是由存在本身的技艺构成的。当代艺术已截然不同于海德格尔所指涉的“技艺”,不再像它在古希腊时期那样,以技术与艺术的浑然不分状态给予我们存在的归属感。与此同时,艺术同样突破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美的艺术”与技术的长期分裂。艺术不再是“美”的产物,“美的艺术”亦不再作为艺术的最高评价体系,曾被划入非艺术范畴的工艺以新的方式回归艺术作品。今天的艺术既改造了“作为技艺的艺术”,也突破了“作为美的艺术”,而是与工业、设计和技术相互整合,在功能主义与知觉之间搭建联系,走向了工业生产方式与美学的新的结合。
在艺术与技术的关系问题上,早期批判理论持守艺术与工业产品的严格区分,技术及其工业产品作为艺术的对立面而存在,技术理性往往构成感性解放的阻碍因素。马尔库塞批判工业社会发展中个体感性的一体化与总体性趋向,技术压抑了个人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向度,从而使生活于社会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阿多诺激进地反对技术对个体经验的异化,文化工业消除了个体经验的差异性与拒不妥协的特征。现代工具理性及其技术形式以“伪个性”的商品化形式取代自主的主体性,使之符合于同一套虚假程式。不同于早期批判理论对技术理性的尖锐批判,工艺美术运动、工艺联盟、包豪斯等艺术运动的出现则大大削弱了艺术与技术之间的分歧。斯蒂格勒从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出发分析人类和技术的纠缠,返回技艺概念,从而看到了技术/艺术救赎的可能(17)Néill O’Dwyer,From Avant-Garde to Negentropy:An Aesthetic Deployment of Bernard Stiegler’s Genealogy of the Sensible,PhD diss.,Trinity College Dublin,2016,p.76.。在艺术与技术的再度结合中,斯蒂格勒改造了海德格尔的技艺概念,重审技术对感性的重构。美学唯有直面如今不断技术化的艺术实践,才能对急剧变化的艺术现实作出有效回应。
无论是艺术的技术问题,还是技术的艺术问题,都是记忆与义肢的结合,构成了感性的器官学。斯蒂格勒以作为“普通器官学”的美学来描绘艺术,感性从内在的身体器官走向自身存在之外的神秘和不确定性,非认知的感性维度在艺术中获得体外化的展现。感性不再仅仅由人类自身的器官来进行特定的生产,而是具有象征和技艺的特征,通过手工作品、艺术作品、书写作品、技术等等延异式的再生产来完成。“艺术是不大可能者、出乎意料者,它每次都是新的,是体内器官(一个或多个,尤其是视觉、听觉和触觉)与体外器官(一个或多个)之间不同步的(独特的、不匹配的)调节。这些调节的历史,就包含在广义器官学的领域中”(18)贝尔纳·斯蒂格勒:《雕塑、培育负人类世》,丹尼尔·罗斯、卢睿洋译,《新美术》2018年第5期。。作为体外化的存在者,人是由技术的、人造的物品,有时也是艺术品组成的。感性不只是一种主体的内在感受(feelings),而是需要载入象征和意指的视野,指向一种生产和接受的能意行动,即生产感官的技能。斯蒂格勒对艺术的器官学研究重新将艺术判断抛入未确定的感觉中,而不再将给定的作品归于某个特定的艺术谱系。“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关怀的时代,我们需要做的是器官学式地研究审美领域中判断力这一官能的种种历史”(19)贝尔纳·斯蒂格勒:《人类纪里的艺术:斯蒂格勒中国美院讲座》,第67页。,美学的思想或艺术的思想应该去描述普通器官学的关系演变,并将艺术放入感性的器官学谱系中进行考察。
耕地质量定级因素权重的确定主要有特尔斐法、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和回归分析等多种方法[18],金安区耕地质量定级因素权重的确定采用较为普遍的特尔斐法。
唯有让艺术复归技艺的含义,才能介入当代艺术中的感性问题,美学由此得以重新评估构成人类感觉性的维度。换言之,“正因为感觉首先就是一种技艺,所以感性(sensible)才是艺术的客体”(20)贝尔纳·斯蒂格勒:《象征的贫困2:感性的灾难》,第48页。。技艺构成人类对其感觉性的外化与扩展,“首先得从艺术问题出发,以便弄清感性的问题,而且不缩减为动物感官的器官”(21)贝尔纳·斯蒂格勒:《象征的贫困2:感性的灾难》,第188页。。作为象征与感性的表达形式,艺术构成了独特的美学场域,参与了感性谱系的外化过程。艺术或技能是感性生活的产物,即象征物,正如斯蒂格勒对艺术的重新界定:“至于艺术,它是这种感性独特性的经验和支撑,邀请人们参与象征活动,在集体时间中生产踪迹,与踪迹相遇。”(22)贝尔纳·斯蒂格勒:《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第11页。技艺是感性的表达与象征形式,如果不经由技艺,对感觉性的分析则会陷入虚无主义与形而上学的平庸之中。艺术开启或生成了一种存在模式,既关涉艺术和技术的交叉,也构成器官解放与感性的体外化。也就是说,技艺是感性的中介者,感性的组织依靠技艺来完成。技艺的对象则是人类流动生成的感性,也是由个体和集体记忆的义肢组成的“后生系统记忆”。
在重返感性的当代美学视域下,艺术史转变为以不同方式去感觉的历史,感知装置在迥异的技术语境中不断转化,催生了人类感觉方式的诸多变化,由此开启了一系列新的美学问题。斯蒂格勒经由艺术的技艺性重审从工业时代到超工业时代的美学问题,关注与技术连接起来的、普遍意义上的感觉性,转向一种“普遍美学”。正如音乐与技术体系之间的复杂交缠关系,自第一次工业革命至自动化社会的变革始终透视出感性的重塑过程,艺术的器官逻辑变异也构成了观测美学的独特视角。以乐器学这一第三持存的艺术为例,斯蒂格勒说明了艺术的技术化转变对美学的冲击,个体的感性经受在这种轰动中不断发生改写。于斯蒂格勒而言,艺术发展标识了感性的象征活动与器官学的变异过程。当艺术沦为社会建构的一种无差别的多样性,构成技术抽象装置的一部分,或是沉浸于商品世界,则会带来象征的贫困与感性的无产阶级化等一系列美学问题。在杜尚之后的“感性的机械转向”中,艺术以一种“工业美学”或“艺术工业主义”(ars industrialis)的面向展开。
“技术合成艺术”导致感性的去功能化与再功能化,为美学学科注入了新的思考。艺术的去功能化意味着感性之个体参与成分的丧失,个体从艺术的参与者与体验者变成消费者,美学的研究范式与议题随之发生转变。在容纳感性之多样性变化的美学话语中,工业技术对个体化的捕获以及感性的去个体化与无产阶级化进入其理论视野。由机械短记忆材料编织而成的艺术表现为一种美学参与的丧失,个体被剥夺了参与美学事件的可能性,失去其感觉性,欲望被工业化开发而退回到内驱力的水平,带来脱个体化与自我迷失现象。现代艺术的技术性变革向我们指出了感性的谱系,其中美学的经济功能造成了受众的无产阶级化,文化工业制造了均质的审美品位。当艺术成为力比多经济的幻觉技术,潜在的艺术家被去技能化,个体参与的感性维度消失,艺术死亡的预言则演变为真实。面对正在变化与扩张的艺术现实,感性经验的现实困境对美学的各个维度发起挑战,艺术实践的转变过程为感性问题提供了历时性的研究视角,美学的思想或艺术的思想则描述了这一普通器官学的关系演变。
时至今日,感知的体外化已转向了网络化的数字工业,感性的塑造由机械复制时代的模拟式变为数字式,超工业社会的道路开启了全新的器官阶段。斯蒂格勒将数字技术系统作为当代艺术的基础,它决定了艺术世界的创造活动,任何艺术都直接或间接地成为数字技术体系的一部分(23)Stephen Barker,“Unwork and the Duchampian Contemporary”,Boundary 2: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e,Vol.44,No.1,2017.。我们生活在一个失去神秘性的力比多经济时代,工业美学将人类不可化约的独特性去除,进行去个体化处理,而转化成可化约的特殊性。进入数字技术主导的超工业时代,感觉的外化形式——技艺以感性的消费替代了体验,自动化的技术体系对个体经验进行前所未有的全方位算法统治。斯蒂格勒悲观地指出,当代美学演变的产物是象征的贫困,生理组织的身体、人造器官以及由前二者相互协调而构成新的社会组织(24)贝尔纳·斯蒂格勒:《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第9页。。数字化带来工业的超可复制性问题,知觉装置被重新排布并深刻地改变了一般器官学的活动,在此基础上重塑了技术生命形式的器官式生成。去象征的、去想象的、去个体化的文化消费主义的霸权造成感知的短路,艺术中的感性自主参与维度则走向消亡。感知与记忆转移到具有自动化能力的单元,从而扩展了人的统觉能力。通过感觉的技术控制或控制感觉的技术,数字化时代的感觉性对个体与集体的独特性造成冲击并发展为一种大规模的象征的贫困。
三、艺术对感性的重构及其药性特征
当代艺术的诸种变化承载了当代人感性的重构过程,斯蒂格勒由此批判了数字技术主导下艺术的消费主义倾向,以及个体集体化、象征的贫困等一系列美学问题。但与此同时,他也明确地将与数字技术结合的当代艺术作为我们当下感性的载体,试图以数字艺术中的个体性参与抵抗文化工业与消费主义造成的美学灾难,在批判的同时显现出建构性的意味。技术系统的进化既去除了感受力的功能,同时也建立了新的感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知性、想象力与理性,从而建构起生命的新规则、日常生活的新形式,由此构造了一个新时代。面对彻底的物化和抽象的世界,即统计学意义上的、被工业产品所浸透的世界,斯蒂格勒看到技艺在变革人类感知方式方面的潜能,艺术创造了让生命值得一过的力量。
当代艺术成为制秘术,斯蒂格勒将其隐喻为“药罐使用术”,经由对感性经验的重塑赋予其药性特征。技术与科技带来的无限可能中蕴含着新的理论,这种理论也同样隐藏在饱受符号贫困之苦的情感之中,技能能够让我们回到生活的艺术,参与到当下的艺术制作中来。“在感性的第二次机械转向的时代中,艺术打开了一个去无产阶级化的视角以及反象征贫困化的策略,即一个新的治疗术,在美学领域从器官学上研究判断能力的历史将变得至关重要”(25)Bernard Stiegler,“Kant,Art,and Time”,Boundary 2:An Internature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e,Vol.44,No.1,2017.。艺术对于感觉的异质性发现具有特殊作用,对市场营销构成的美学制约条件进行反抗。“在超工业阶段,所要做的就是发明一种感性的新型组织,要从对超工业的批判(不仅仅是对它进行谴责)开始”(26)贝尔纳·斯蒂格勒:《象征的贫困2:感性的灾难》,第177页。。感性的艺术性表达成为这种新型组织,蕴藏着重组感性经验的潜能,新艺术的创造对于感性的重新建构产生作用。
美学作为感性的共享是无法计算或测量之物,艺术则代表了不可计算的感性独特性。面对技术逻辑所渗透的艺术以及分化的主体性,阿多诺、霍克海默、利奥塔都不同程度地指认了文化产业对审美的损害,经验与情感的差异难以在技术理性中获得统一。阿多诺对文化工业的谴责忽视了新的艺术形式对统觉能力的扩展,与阿多诺对电影艺术和流行音乐的极度排斥相异,斯蒂格勒认为与技术融合的艺术建构起新的美学,能够在感性共同体的基础上容纳感觉的差异性。艺术品在个体化过程中产生了内部的共鸣,个体随着这个震颤生成了独特性。斯蒂格勒将这种关系定义为一个触动或张力,个体化的触动是未完成的也是无限的。艺术触动感受力并造成特殊的情感,这一情感无法被还原为体内器官的“感官-运动回路”,而是在外化的技术与艺术中交互生成。艺术以这种方式对抗着可计算性的技术理性,并开启了负人类纪的审美经验,提供了超越人类世之疯狂景象的潜在未来图景。
当代艺术提供了一个批判性的反思空间,邀请观众不断参与不稳定的、流动的感受过程。经由对数字时代特有的新工具的吸纳,艺术承载了超工业时代的主体间性与程序工业的药理学面向,激发了对人与技术共同参与的重新思考。在超控制的艺术中蕴藏着颠覆并解体自动化情境的潜能,象征着一种去自动化的新理想。数字技术作为无所不在的工具,以第三持存的方式再度构成了记忆的痕迹。在《艺术工业主义宣言》中,斯蒂格勒提出工业社会中艺术的独特存在形态,通过技术的实践,可以重建欲望的对象和奇点的体验。“艺术工业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疗法重新投入药理学的实践”(29)Bernard Stiegler,What Makes Life Worth Living:On Pharmacology,Daniel Ross,trans.,Cambridge:Polity Press,2013,p.76.,其转换的中介是跨个体化,以创造一种新的工业模式,融合个性化的参与与技术,从而应对个体间感觉关系的断裂。在我们身处的时代中,机械与感知交融的当代艺术触发了聆听、观看、感知、体验的过程,“我们正在经历工具的‘非专业化’(de-professicnalisation),各种工具、设备和手段正在摆脱专业技术人员的垄断,流向非专业人员的手中,公众和业余爱好者手中再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工具”(30)贝尔纳·斯蒂格勒:《反精神贫困的时代:后消费主义文化中的艺术与艺术教育》,杨建国译,周宪主编:《艺术理论基本文献·西方当代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364-365页。。触手可及的网络技术重新组织了艺术的生产过程,业余爱好者不止是受众,更是艺术内容的提供者和参与者。
美学通过与技术相结合的业余爱好者来重新进入艺术,在艺术重组感知的过程中,对艺术作品的非审美判断意义上的“爱”发挥了独特的药理学作用。对做事技能的热爱锻造了更为广阔的生活艺术,杜尚对艺术品的质疑通向业余爱好者的可能性,斯蒂格勒由此阐发了艺术的技巧性与热爱间的不可分割,爱在象征的贫困时代是药理学意义上的,能够将奴役个体的技术、第三持存颠倒为自主的技艺,“从而必然使个体化即知识的新阶段成为可能”(31)贝尔纳·斯蒂格勒:《南京课程:在人类纪时代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自然辩证法〉》,张福公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78页。。斯蒂格勒通过业余爱好者的热爱来带动这一情境,达到感知的去自动化理想,通往新的共感的可能性。目光、听觉、感官和肉体的新的共在重启了感性的独特性,充当集体与个体的生活方式,以抵抗感性经验在今日技术语境中遭遇的一系列灾难。作为感性独特性的艺术经验邀请人们参与象征活动,也在集体时间中生产踪迹。技术装置的药性为一个去无产阶级化的新自动社会打开出口,开启了新型的感性分享的可能性。斯蒂格勒据此重思文化工业的药性,呼唤我们出发去冒险和经历这种感知与统觉的扩大,去体验这种超工业时代的感性经验。技术自身能够承载感觉的经验以构成一种抵制,人与技术共在的感性学谱系回应了如何在负人类纪恢复去自动化能力的问题,感知身体器官与技术器官之间的生产,建构了新的个体化过程。
基于艺术对感性经验的重构与解放潜能,斯蒂格勒的艺术观念为“数码研究”(digital studies)带来了启发。技术参与下的审美接受作为个性化的体验,而非网络中封闭的被动体验,这一观点在阐释数字艺术、后网络艺术以及技术合成艺术时极具有效性。在这些数字艺术家看来,与技术融合的艺术能够修改与一切事物的偶然性关系,尤其是与技术的关系,艺术由此开启了负熵的问题(32)Bernard Stiegler,Noel Fitzpatrick,“Digital Studies and Aesthetics:Neganthropology”,Noel Fitzpatrick,et al.,eds.,Aesthetics,Digital Studies and Bernard Stiegler,New York:Bloomsbury Publishing,2021,p.xxvi.。“体外化并不是简单地将一些东西转化入已经存在的媒体中;而是通过认知与情感的内在化来创造我们的内在性过程”(33)Jeanette Doyle,“Thirty Years:An Analysis of the Exhibition Art Post-Internet through the Work of Bernard Stiegler with Reference to Jean-François Lyotard’s Exhibition Les Immatériaux Jeanette Doyle”,Noel Fitzpatrick,et al.,eds.,Aesthetics,Digital Studies and Bernard Stiegler,p.96.。经由数字艺术对感性的重组,技术不再外在于我们,而是支撑着我们一切存在的方式。后互联网艺术不再是艺术家的独创,而是与大量业余爱好者的热爱相关,数字技术让艺术生产工具掌握在爱好者的手中,因此他们既是生产者、消费者,也是爱好艺术者。斯蒂格勒强调数字技术主导下艺术的自动化生成必须与业余爱好者的“非自动化”生产过程相结合,才能释放出身体体验的重塑潜能。如自拍照借助技术来模仿“自爱”,数字技术以更加亲密的方式帮助我们了解自我的独特性,自我价值感通过看到自我、通过在技术中外化了的自己来完成。
个体化是非静态的、难以描述的,并非一个已结束的阶段,艺术能够神秘地触动个体化与跨个体化。艺术生成一个不断搅拌着新个体的动态过程,通过集体式个体在艺术中的象征交流,实现感性之物的动态跨个体化过程。“艺术就是那个‘我们’所作的承诺(独特性)——它超出了存在于此时此地(作为身份)的、事实的、有限的‘我们’的边界”(34)陆兴华、张生主编:《法国理论》第8卷,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22年,第42页。。第三持存负载着想象与情感,同时也在编织着社会的个体化,艺术既向自我打开,也向一个广阔的非我打开。在朗西埃看来,艺术家就是组织感性和分配感性的人。斯蒂格勒则将艺术家作为个体化的样板形象,是可供支配的前个体的跨个体化操作者。艺术家对被感觉物进行外化和表达,创造了感性的共时化工业装置所无法清除的独特性,扮演了个体化推动者的角色。“艺术家更能为我们提供一种关于个性与差异、自由与多元伦理形式的表达”(35)金惠敏、陈晓彤:《当代美学伦理转向中的英美进路——以伯纳德·威廉斯和玛莎·努斯鲍姆为中心的考察》,《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业余爱好者的热爱与艺术家一样,都是跨个体化的动因,他们在个体化的“相位差的经验”中去重新理解艺术——一种更加开放的、不确定的、未完成的感性的体外化形式。由友爱建立起的“同在”打开了既是公共的又是个体化的时间和空间,将经验转变为无限,通过个体间可共享但不可通约的“神秘的激情”开启了共同体的可能性。
进入数字时代,艺术的药学特性瓦解了由过往时代的持存系统所生产出来的规则,艺术必须再次成为技术,在一般器官学中发挥鲜明作用。药——也就是每一种第三持存的新形式——既短路了感性的跨个体化循环,又让个体基于这些感性记忆的踪迹而形成集体性个体,从药学中产生集体预存。艺术允许我和我们之间通过感知的体外化也就是艺术作品,让一种跨个体化发生。“他打开事物,他自己也因此而打开:他的眼睛,他的耳朵,他的五官向感官大幅度打开”(36)贝尔纳·斯蒂格勒:《象征的贫困2:感性的灾难》,第20页。。感性的共同体诞生于主观的偶然之中,其中我和我们之间的张力与不可调和性始终处于动态与偶然之中,“作为美学意义上的共同体,从不同个体深层的感性基底形成审美认同和情感共鸣”(37)王大桥、何琪萱:《视觉共同体与欧洲中国风中的“女托邦”》,《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经由第三持存的跨个体化艺术,被共享的感觉及其意义才能形成,也由此才能构成社会性的集体化个体,换言之,才能形成向着这一时代的期待。新治疗法既是毒性的也是新时代的处方,技术的药性不断重启感性的独特性与差异性,数字第三持存的出现及其所带来的技术震惊往往激发了新的治疗与救治,连接起新的人群与共同体,网络效用创造的人为群体蕴含着感性共同体的潜能。
余论:重建美学与艺术的亲缘关系
美学与艺术的亲缘关系在今天的美学与艺术理论中被不断阐发,二者间的分合是其共同宿命。在哲学美学关于“美的艺术”的研究中,艺术不再是与实用知识和日常经验紧密相连的技艺,而是摆脱了宗教、科学与手工艺的从属地位,获得自身的合法性与清晰边界。传统美学将自身圈定于审美经验、审美价值与审美属性等特定范畴之内,美的艺术及其审美判断构成美学研究的中心,美学逐渐窄化为一种艺术哲学。艺术品屈从于“纯艺术”的幻象,美学一度遭遇艺术的驱逐。对美学不满的声音倾向于将美学思辨与艺术实践彻底区分开来,美学的罪责被指认为对艺术观念的歪曲。虽然美学在20世纪遭遇反美学与非美学的诘难,但无论艺术批评家与理论家如何坚称艺术实践应当摆脱美学的附庸地位,以获得自身的独立性,美学依然对识别艺术发挥着重要作用。诚如朗西埃所言,艺术问题的解决需要美学提供理论支撑,美学“能让我们识别艺术的对象、艺术的体验模式及思考形式,即我们为指责美学而试图分离的东西”(38)雅克·朗西埃:《美学中的不满》,蓝江、李三达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4页。。在艺术的去美学化观点之外,美学从未停止对艺术问题的探索,当代美学如何重新进入艺术,这一宏大问题域包含了不同的理论进路。约翰·杜威的实用主义美学从人类生活经验出发,复原艺术与生活之间的联系;鲁道夫·阿恩海姆“从感觉经验开始”定位美学,阐发艺术在创造和阐释知觉时的重要作用;纳尔逊·古德曼鉴别不同种类艺术中的多种形式符号,将美学理论带入博物馆、艺术教育、表演等艺术的应用领域(39)柯蒂斯·卡特:《跨界:美学进入艺术》,安静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4页。。这些理论基于不同的理论视角挑战艺术概念的独一无二性,打开了美学进入艺术的多重可能性途径。
当代社会的美学危机与艺术困境共同呼唤着美学的复兴与重建,美学如果能够与艺术继续保持亲缘关系,进入艺术的具体场域,就要改变美学的话语方式与提问方式。超越艺术哲学延伸至感性的整个领域,重审感性被塑造与改写的方式,是当代美学进入艺术的切入口。以斯蒂格勒为代表的当代美学建构了一种超越艺术的美学话语,思考感觉与意义问题,以宽泛意义上的感性学重新定义美学。美学的目的不再是建立普世性的艺术概念,抑或是关于审美判断与审美距离的陈词滥调,而是溢出艺术哲学的范围,关注艺术经验之外丰富而多元的感知形式,渗透于日常生活的各个感知领域。艺术成为当代美学诸多感觉方式中的特殊环节,而并不构成美学的全部研究对象。接续朗西埃对美学感知问题的思考路线,斯蒂格勒聚焦于艺术与感性的相互构成关系,回归丰富的感性领域以重新介入艺术,激活美学对艺术的解释力,推动了美学话语在艺术领域的复兴。
当代美学以重返感性的方式介入艺术,实现美学与艺术的双向改造。艺术的发展离不开美学话语的推动,同理,美学走向各种艺术的实践与批评,关注不同艺术中感性的独特性面向,艺术构成了独特的美学场域。在重返感性的当代美学视域下,美学从流动生成的经验世界中看待艺术与审美活动,重建艺术品与现实环境、技术语境的联系,回归丰富的感性领域以重新思考艺术。艺术逐渐走出了与生活相互隔绝的境地,不再被理解为去语境化、去历史化、中性化的陈列物,而是作为感觉的先驱,对周围世界的审美状况率先作出反应。艺术史是以不同方式去感觉的历史,艺术的发展催生了感觉方式的不断变化,开启了新的美学问题。如韦尔施所言,“人们以感知艺术的方式来感知现实。审美经验的基本原则不是将艺术看作某种封闭的东西,而是将其看作能够打开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去拓展世界那令人陌生的面向”(40)沃尔夫冈·韦尔施:《美学与对世界的当代思考》,熊腾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6页。。作为象征与感性的表达形式,艺术携带着强烈的感知力,辐射到我们对现实世界的感知之中。艺术重构了感性,换言之,我们的感性也正是艺术经验的沉积物。
面对多元化艺术实践对美学话语的更新,技术与艺术的关系问题成为当代艺术的核心议题之一。作为影响当代美学和艺术发展的主导性因素,技术的变化透视出不同时代中个体与集体感性经验的变化,“技术合成艺术”成为当代艺术发展的新方向,斯蒂格勒的“工业美学”在阐发新的艺术现实时极具有效性。随着中国当代艺术实践与科学、工业产品、工艺等元素的相互整合,其技术形式由早期的录像、有线电视、光学媒介转向了数字化的技术媒介。自动化、虚拟现实、计算机图像、全息影像等数字技术不断参与并推动着当代艺术的变迁,催生了网络艺术、VR艺术、数字装置等新型艺术样态。数字化时代的艺术既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和困境,遭遇空前的“象征贫困化”,又为建立新的感觉方式打开了通道。斯蒂格勒以批判美学视角反思艺术的“超可复制性”问题,道出了数字工业时代个体感性的均质化与匮乏性。他近乎预言式地指出,感性如今整个地被某种技术的东西所编织,这成为美学与艺术共同面临的危机。与此同时,斯蒂格勒将艺术的解放潜能诉诸公众的感性参与,认为艺术代表了不可计算的感性独特性,从而形成“反象征贫困化”的美学策略。作为一种技艺的建构,感受力在不同技术语境中发生转变,而与技术相融合的艺术品构成“感知的外置化”形式,成为观测人类感性活动的载体。艺术打破了惯常的感知模式与感觉形态,回归“美的艺术”诞生之前艺术的“技艺性”,在与技术相互融合的过程中重塑并改写着感性的谱系。多元化的艺术实践更新了美学学科的理论话语,通过对艺术品与技术之间关系的重建,斯蒂格勒的艺术观念为思考新的艺术现实带来了诸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