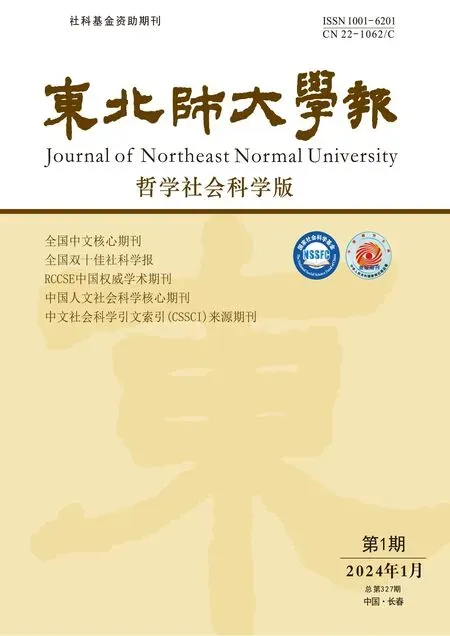李贽平等宽容思想探赜
于 溟 跃
(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 100029)
晚明思想家李贽是一位大器晚成者,这不仅因其个人思想成熟于生命后半期,而且他的影响也是在后世不断被阐扬和推举,称他为“生在死后”的思想家似乎也不为过。历史上,李贽的个体形象一向以狂、怪著称,他一生性情孤傲、狂放不羁、率性而行,敢于“背叛孔孟”,曾被视为“名教之罪人”而饱受争议。由于他言辞犀利、口无遮拦而被世俗误认为“性太窄,常自见过,亦时时见他人过”(1)李贽:《焚书 续焚书》,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86页。。而实际上,在他的思想中,平等宽容是一种主流底蕴。本文即围绕聚焦李贽的平等宽容思想,探究其理论渊源、形成发展及核心要义。
李贽平等宽容思想传世的几百年间,因其超越时代的开阔与锋芒而常常被学人论及,这是在传承赓续先贤,主要是汲取阳明心学,加之对儒释道思想博览慎思的整合,同时在独立思考、析疑匡谬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进而形成自己学说的。根据这样的线索进行探析,能够更好地对李贽思想形成语境化、体系化的观照,领悟其敢于怀疑批判的抗争精神及思想解放的启蒙品质,并定位李贽在思想史中更为真切的历史坐标。
一、对旧知的扬弃的承续
一个在思想史上留下深刻足迹的人,不可能不有所承续,李贽亦如是。一般来看,王阳明心学是其思想的理论渊源所在,这一点有李贽自己对王阳明思想的赞同和称扬为证(尽管这一意绪多集中于其人生前期,但也正印证了李贽对世界、对人生的认知是从王阳明那里起步的(2)李贽最早接触的当然也有儒家经典,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余自幼倔僵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阳明先生年谱卷下》)“稍长,复愦愦,读传注不省,不能契朱夫子深心。”(《焚书》卷三《卓吾论略》)),王氏心学中重视主观、漠视权威、傲视群伦的特质,给了李贽以深刻、长期的影响。这种思想接受过程在性格、性情上的塑造对于李贽而言,既有因异代认同而滋生的狷介愈烈,也有因知音太少而产生的孤苦渐浓,又有因特立独行而横生的寂寞日盛,故李贽在《名臣传》中借由“直节名臣”朱晖、朱穆的事迹,继李太白的“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送蔡山人》)之后,唱出了更为惨淡凄凉的“绝交歌”:“不须绝交,交自绝我。交已绝我,无交可绝。”(3)张建业主编:《李贽文集》第二卷《藏书》(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546页。种种情愫集聚在李贽的内心,促使他更为强烈紧迫地向外寻求思想慰藉;王阳明及其后学王艮,以及泰州学派诸君,都对李贽产生影响,成为他思想形成过程中重要的理性支撑与情感依靠。事物发展通常是内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李贽身处的文化背景使他在阳明心学中耳濡目染,所被动生成的狷介、孤寂的气质催生下的急迫的“内因”又构成了他主动接纳王学的决定性根基。这种历史和心理层面循环往复的认识与接受,也是以往和当今的李贽研究中似被轻视而略显苍白之所在。而在此基础上,能建立起怎样的理论主张和认知体系,是一位学者真正转变为思想家的关键和要害。
在人类的思想史、观念史中,平等是一个重要的范畴。华夏大地上的平等意识自古以来更多地集中于道德论视域,反映为圣人和民众在天性、品德上的相近乃至相同。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周公的政治理想与辅政职责有关。正如有学者指出,“周公还重新定义了‘德’的概念。在周公这里,‘德’已不再是《尚书·盘庚》里商人的那种无原则的恩惠,而是所有人生活在世间的客观道德律,如孝悌长幼、中正恭逊、宽宏温直等……他对‘德’的阐释,只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美好愿望……渴望生活在一位圣明君王统治下的安定中。而他的兄长周发却必须成为那位有‘德’君王”(4)李硕:《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484、485页。;《荀子·性恶》篇也屡有提及:“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等等。这些在主观上本是重视教化之举,是形而上的至德要道,以期提升民众忠孝的道德自觉,弥合社会矛盾;但在客观上又显得拉低了圣人君子的“品位”,从而在德行层面填平了圣人与民众、君子与小人之间的鸿沟,渐渐衍生出圣凡之间的差距原本很小的结论,这便氤氲出某种原始的平等意识。随着后来佛教“如来善修,如是平等”(《涅槃经》)教义的逐步本土化,平等思想开始了广泛深入的传播。
在封建礼教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等级社会里,平等意识的萌生和滋长异常艰难,这不仅如同空谷足音,也成了万古长夜里的一缕微光,吸引着“异端”的人们的天然向往和主动追寻,正所谓“在黑暗的长夜里已经发现黑暗世界的不可救药”(5)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18页。。在此种历史文化背景下,李贽道德论上的平等思想与发声呐喊便既有对前史的承续,又有对这一宝贵意识的发扬与坚守,同时更包含对旧有的反叛或痛斥。比如,他在《答周西岩》中因激愤而略显绝对地说道:“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无一物不生知,亦无一刻不生知者。”(6)李贽:《焚书 续焚书》,第1页。这种人人平等、物物平等的观念(值得注意的是,“天下”的概念本可追溯至远古王权的历史阶段,属于先秦诸子用以评说华夏治乱兴衰的政治论述范畴,而后成为皇帝制度下的支配理念之一,但李贽却拿来评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实为“天下”赋予了一定的人文关怀色彩)实乃不满于儒家学统中的“上智下愚”论。又如《答耿司寇》中理性沉静地娓娓道来——“圣人不责人之必能,是以人人皆可以为圣。故阳明先生曰:‘满街皆圣人’”(7)李贽:《焚书 续焚书》,第31页。,这里一方面指出圣人“不责”的宽容,另一方面既引王氏之言,鼓励民众追逐圣人、成为圣人,又实则谐谑地反向扩张着王氏的观点,实际上放大了民众与封建特权阶级之间的矛盾,深藏着一种众生实为平等的启蒙品质,而与孟子津津乐道的“君子之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孟子·离娄下》)判然有别。
受晚明时代风气影响,加之个人的价值取向所致,李贽对已僵化的理学流弊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反对权威,反对理学对人的禁锢,痛斥理学家们唯尊孔是瞻,丧失思考批判的能力,讥讽他们为“依门傍户,真同仆妾”(8)李贽:《焚书 续焚书》,第227页。。同时,李贽对人们在理学统治下失去个性、盲目顺从的奴性心态也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剖析,并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不愿做无识无见“贤否不分”的“黑漆漆之人”(9)李贽:《焚书 续焚书》,第227页。。李贽所处的时代受阳明及其后学影响,流布着崇尚良知、“凡圣如一”的平等思潮,即认为人无论高低贵贱皆有善良本心,良知面前人人皆平等。尤其是他所推崇的以王畿、王艮为代表的阳明后学,其领袖和骨干不乏底层出身,在士农工商各阶层都有接受者和拥趸。李贽也大力主张“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10)张建业主编:《李贽文集》第七卷《道古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61页。,倡导不要过高抬举圣人,也不要无端小视凡人,要求自由彰显人的“自然之性”——“各从所好,各骋所长”(11)李贽:《焚书 续焚书》,第17页。。中晚明的士人学说不再像以往那样多在达官贵人、社会精英中流转与发展,而有了一条途径走入民间、切近庶民,于世俗社会普通百姓之间产生广泛的感召效应,带动儒释平等观念的世俗化传播。这也使得平等思想不再独居于“庙堂之上”,而亦有了“江湖之远”。从而,李贽的平等思想已不仅仅局限在认识论层面,而是增添了一定的伦理实践性内涵。
与平等理念相表里的是宽容,无平等无以致宽容,非宽容无以见平等。李贽对于宽容也进行了许多论说。《藏书》是李贽的书系中写作用时最长的,也倾注了他最多的精力和心血,一如张舜徽所赞赏的那样,“卓吾史识极高,议论有绝佳处”,“‘藏书’是他一生最得意最用力的作品”(12)张舜徽:《中国史论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92页。。在《吕夷简》篇末,李贽有这样几句感慨:“夷简若过得朱文公眼目,殆亦可矣。何者?道学先生责人至纤细也。”(13)张建业主编:《李贽文集》第二卷《藏书》(上),第498页。李贽将对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家待人求全责备乃至琐碎纤细的不满扼要地和盘托出,一个“至”字,一个“纤细”,便使道学家的苛刻与不宽厚尽寓其中。这里既有李贽往日被道学所困厄而心生怨怼的合理发泄,也有他对道学伪士名不副实、表里不一等种种丑态的憎恶。我们不妨再将这条议论与《谢安》篇参照起来看:“然而晋祚卒延者何?王、谢之力也。伟焉哉!二公之于晋也。无求备,无取必,无敢侥幸。”(14)张建业主编:《李贽文集》第二卷《藏书》(上),第182页。如果说李贽批判朱熹之流是从反面立论,那么他标举王谢二人则是从正面立说,“无求备”三个字,一方面承续了儒家思想中“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的待人宽宥,反映了李贽于遨游史籍中所陶冶出的人格襟怀;另一方面,这三个字是从王谢家族的历史教训中总结而来,这样的顺序便使结论自然拥有了厚重的历史感与可信性,属于典型的“论从史出”。李贽没有带有主观色彩地去以单一的范式和视角解读历史,从而其思想的方法也并非史家们所待见的“以论带史”。
颇有意味的是,李贽对朱子的这番评价似在其身后产生了“回响”。清代王鸣盛在《蛾术编》中曾说:“朱子论三代以下人物,几无一免于讥贬者,而于七十子及孟子,亦皆有所贬。”(15)王鸣盛著,顾美华标校:《蛾术编》(下),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第1186页。在李贽对历史的承续中,我们得以见证他敏锐的洞察力,同时又为后世留下了关于平等宽容的思考的火种,他也因此而站在了时代的前沿。“李贽是在历史进程的正途上迈进”(16)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册,第418页。,“尽管李贽的社会思想和道德伦理学说并没有、也不可能越出唯心主义的藩篱,但其中所包含着的反封建的战斗精神,想摆脱中世纪神学的倾向,从历史演进角度来看,是有价值的”(17)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册,第434页。。
二、对已知的批判性的整合
在对先贤、旧知进行扬弃的传承与汲取的同时,李贽十分注重对于历史流传的知识的整合,他没有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而是用批判性的眼光做出取舍与消化,实现了具有超越意义的思考和创造。
(一)“圣上”与田舍翁:解构等级与意识解放
在《藏书》“贤将”类李责力传的篇末,李贽有一段信息量很大的评语:“李责力一言丧邦,何谓哉?‘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乎?’此探本之说也。然此本于人性,而彼合于名教,固宜其不相入耳。然又安知夫专事名教者,平生果无三房五室与帷薄之私乎?吾又恐其不免于责主之明,而恕己之暗也。甚矣!”(18)张建业主编:《李贽文集》第三卷《藏书》(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078页。这段话中至少有两层意蕴引人深思。首先,李贽把“圣上”与田舍翁相提并论,若经济条件好转,二者皆可能产生富贵易妻的观念。李贽将平日里高高在上、威风俨然的天子拉到像田舍翁一般的尘俗层面。在这里,封建社会中历经几千年形成的“君君臣臣”,圣君在上、臣民赞之颂之犹不及的诚惶诚恐似乎在李贽的几句轻描淡写下旋即黯然无光了。李贽换了一个视角,不是从政治,而是从人性的日常情欲和市民生活层面来审视君王,这既与他自觉地承袭阳明心学、泰州学派一系,以百姓日常生计为思考问题的立足点相一致,也与他本人异常敢想敢言、爽直自负的个性相生相济。
其次,这段话中蕴含着鲜明的使人情与名教相对立的因素。在中国思想史中,从礼教到名教再到理学,名义不同但本质相近,都是以倡导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为旨归,来维护、巩固社会秩序。而李贽却自觉地在上述三者之外批判性地标举人性、人情,为他身后小他23岁的汤显祖和小他47岁的冯梦龙开辟了一条任情的通衢。汤、冯二人不仅十分仰慕李贽,他们的文学创作也深受李贽思想的滋养和浸染。冯梦龙更是格外竖立起“情教”的大旗,让人情得以高扬和彰显,与“理”公然对垒。所谓“盖踵其事而增华”(《文选序》),李贽的筚路蓝缕之功是不可没的。一如许建平所说:“李贽的思想中反封建的东西、启蒙的东西又是如此之多,影响之深远,晚明思想史上鲜有与之匹敌者。”(19)许建平:《李贽思想演变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68页。
(二)从“君子”到“至人”:“异端”的超越性
李贽在《论政篇》里运用整合性思维谈及一个理想的政治观念:“且夫君子之治,本诸身者也;至人之治,因乎人者也。本诸身者取必于己,因乎人者恒顺于民,其治效固已异矣。”(20)李贽:《焚书 续焚书》,第87页。这番话有如下几层蕴涵。第一层是对“君子”“至人”的辨析。这里的“君子”是很为儒家津津乐道的,因其寄寓了儒家近乎道德上完美的价值认知;而“至人”则一般是受道家礼赞的,被认为是超凡脱俗,达到了与自然合一的无我境界。李贽将二者并举,仿佛形成了一种别样的况味:衬托出君子治国之术的略显平庸,而至人治国则高明不凡。这种笔法的效果与李贽生前身后一向奉儒学为正统的主流意识,既泾渭分明,又南辕北辙。于此可以看出,李贽因以“异端”自居——“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21)李贽:《焚书 续焚书》,第53页。,也便更为敏感无蔽地,似在潜意识中就自觉地对正统思想做出批判性的审视。他是一位有胆有识、自立自强的战士,更是一位拥有主体性、自主性的斗士。
第二层,李贽承认了儒家的“君子之治”存在于世间为既定事实,但又紧接着增加“至人之治”于其上,并褒扬推崇之,让君子之治相形见绌,这似乎是李贽在现实残酷的思想斗争中磨砺出的一个高明的抗争方法,类似于“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的民间说法,有一种气定神闲的自得之感。这与他一贯的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特色有所不同,而与苏轼《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所论四事一处行下状》的风格有异曲同工之妙——“今二圣临御,八年于兹,仁孝慈俭,可谓至矣。而帑廪日益困,农民日益贫,商贾不行,水旱相继,以上圣之资,而无善人之效,臣窃痛之”。这大概也缘于李贽对苏文的烂熟于心,以及对苏轼自由洒脱风格的心仪向往所致。苏、李二人都只是娓娓道来,让事实说话,平和话语中的“皮里阳秋”却别有耐人寻味的底蕴;他们的态度是赞是讽,或二者参半,则一概交给读者判定。再向前看,这种感觉也类似于杜甫诗的艺术手法。杜诗多用表面看起来客观平静的叙述,这对作者来说是其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日臻化境,而在李贽这里,则代表思想、文笔上的日渐老练成熟。
第三层,也是更为重要的,李贽在此处凸显了道家之境的高妙,但并没有停留于传统道家大多只为一己之旷达的范畴,而是将观照的重心放在“民”,突出强调顺应民心、民意的重要性,显示出质的跨越,以及胸襟境界的崭新提升。结合李贽的平等观特别是重视人情的方面来看,“恒顺于民”蕴含着从理性上的看重转向情感上的践行的新高度;再由王夫之“为善则非情不为功”(22)王夫之:《船山思问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5页。的论断出发进行思考,我们便更能洞察李贽在“顺”字前加上“恒”字的良苦用心和大有深意,即他认为:顺应民心民意不仅是历史上由来已久的问题,更应该是绵延到永恒的问题。这也是李贽爱民思想的重要体现。朱维铮曾评价李贽为“著名的史论作者”(23)朱维铮:《壶里春秋》,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225页。。李贽的“恒顺于民”在君本位的历史背景下诞生、发展,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不易的事情,充分展现了李贽具有超越性的批判能力,他是一位独立思想者。
另外,在这段论述中,李贽用了“因乎人”的说法,“因”本身就是古代哲学史、思想史乃至教育史上的一个具有生命力的范畴。自孔子与儒家的“因材施教”问世,贾谊的“因利乘便”(《过秦论》)、司马迁的“因势利导”(《史记·孙膑传》)、赵晔的“因地制宜”(《吴越春秋》),以及“因时制宜”(《淮南子》)等便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些言辞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所“因”内容大都聚焦于外在世界、客观事物。独独到了李贽这里,他将目光对准的是人,“因乎人”就是重视人、基于人。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李贽将“因材施教”理念从教育领域向政治、社会领域的一种移植,也是对孟子“民为贵”思想的发扬光大。要之,这是一次对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成功整合。
沿着这一思路,在“因乎人”和“顺于民”之间,可以发现潜藏着李贽的一个前卫的逻辑脉络:“顺于民”要以“因乎人”为基础,“因乎人”是“顺于民”的归宿和应遵循的标准。“民”所带有的一般是社会的、群体的属性,而“人”的属性是独立的、个性的。李贽的深刻就在这里:他的平等宽容理念是以个性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最终要落实到每一个独立的个体,强调了人的主体性。李贽既看到了社会层面民心向背的重要性,也看清了人的层面个性独立的关键性。前者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弘扬,后者则为民本思想赋予了一定的现代性张力,开辟了一条向近现代特质迈进的可行之路。
据此,李贽的“恒顺于民”堪称一座思想史上的丰碑。在明代这个穷通成败的特殊时代,李贽站在承前启后的历史交汇点上,出色地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这正如卢兴基所评价的那样:“明代的启蒙思潮由李贽推向高峰。”(24)卢兴基:《失落的“文艺复兴”——中国近代文明的曙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85页。也像蔡尚思所说:“李贽反对礼教的言论,很有独特之处。他自称的识、胆、才,都很突出。能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终于以七旬老翁而殉真理。这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中,实无人可与他一比。”(25)蔡尚思:《中国礼教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2页。
三、李贽的新胆新识及对后世的启迪
如果说李贽对旧知的承续是以“接着讲”(冯友兰语)的姿态,显示了薪火相传的学术史价值,那么他对已知的整合则是以“集大成”的范式,展示了博采众家的思想史品格。同时,李贽又以夺人耳目的真知灼见滋养了当世和后来的人,给当时的学界和社会增添了新气象。他关于平等宽容的思想理念所昭示和彰显的实际上是其怀疑批判的抗争精神及解放思想的启蒙品质,这种珍贵的新胆新识时至今日仍然具有生命力,有着常读常新的启示价值。笔者以为,“疑”和“胆”应是李贽创新创造的核心力量与旨归所在。
(一)“疑”的批判性与启蒙性
怀疑是进行学术批判、思想批判的首要锋利武器和先导基础,没有怀疑,其后的解构、否定乃至解放、重建都无从谈起。李贽在《观音问》中写道:“杨慈湖先生谓大悟一十八遍,小悟不计其数,故慈湖于宋儒中独为第一了手好汉,以屡疑而屡悟也。学人不疑,是谓大病。”(26)李贽:《焚书 续焚书》,第169页。李贽将不敢怀疑、不善怀疑看作学者的“大病”,着实有醒人心智、醍醐灌顶的作用。
要怀疑,首先要有胆,要敢于怀疑。圣贤在前,经典在上,如果不具备打破旧有禁锢、推动时代与文明进步的雄心壮胆,是无以实现的。在这方面,民间文化因远离礼教森严的朝堂宫廷而更好地孕育了怀疑精神,如皮锡瑞在《郑志疏证自序》中所言:“夫自汉至唐,郑学极盛,其时谚云:‘宁道孔、孟误,讳言郑、服非。’”(27)吴仰湘编:《皮锡瑞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80页。自汉至唐的几百年间,民间宁可不恭于孔孟两大圣人,也不去说郑玄、服虔所注之非,这便彻底颠覆了经典与经学之间的本末关系,在看似荒唐的同时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俗民谚所折射出的大胆和怀疑精神以及有学人不肯为经典所困、不愿为圣人所绊的情况。反过来讲,民间文化中叛离正统的部分是一种客观存在,若学人一味为雅俗观念所困,漠视甚至鄙视民俗民谚,那么有时便会不免陷入一种“片面的深刻”,难以得到全面公允的学术滋养。
而一贯以思想敏锐、言语大胆著称的李贽,曾把怀疑的种子直接种在了孔子身上——“这是挖老根,显老底,擒贼先擒王的手法”(28)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册,第435页。。李贽曾言:“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29)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册,第440页。在《答周柳塘》中,他也说:“大抵我一世俗庸众人心肠耳,虽孔夫子亦庸众人类也。”“夫子无不可者,而何不可见之有?若曰礼,若曰禅机,皆子路等伦,可无辩也。”(30)李贽:《焚书 续焚书》,第263页。李贽宣称“大成至圣文宣王”也是平庸的普通人,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之语。
《红楼梦》中出自贾宝玉之口的几大叛逆名言为人们所熟知,其一便是对“文死谏、武死战”的抨击。这句话却是发端于李贽在《答耿司寇》中的一句大胆揭发:“死而博死谏之名,则志士亦愿为之,况未必死而遂有巨福耶?”(31)李贽:《焚书 续焚书》,第29页。李贽将历代诸公假死谏之名换取“巨福”的虚伪丑恶的嘴脸揭露得原形毕露、辛辣至极。自史上树立起比干这样死谏的模范之后,死谏几乎成了后世大臣,尤其是文官道德自律的样板,于历来的臣子之道而言都具有不容亵渎之感。李贽敢于顶着历史步履的沉重和思想前行的艰辛,讲出自己对封建道德的怀疑,这让他身上不由得闪耀着启蒙思想家的光芒。
(二)“胆”的范畴的传承与启示
若非李贽兼集“识、胆、才”于一身,便难以使其知世论世的直言快语和珍贵风采流传于世。李贽自己亦有对此三字的创造性论述。他在《二十分识》中讲道:“有二十分见识,便能成就得十分才,盖有此见识,则虽只有五六分才料,便成十分矣。有二十分见识,便能使发得十分胆,盖识见既大,虽只有四五分胆,亦成十分去矣。是才与胆皆因识见而后充者也。空有其才而无其胆,则有所怯而不敢;空有其胆而无其才,则不过冥行妄作之人耳。盖才胆实由识而济,故天下唯识为难。有其识,则虽四五分才与胆,皆可建立而成事也。然天下又有因才而生胆者,有因胆而发才者,又未可以一概也。”(32)李贽:《焚书 续焚书》,第155页。自唐代刘知己在《史通》中提出人人皆知的“才、学、识”的认知理论后,它便在学界具有了普遍而长远的影响力和统治性。李贽弃“学”字而代之以“胆”,无疑更具有挑战性和创新性。在李贽身后一百年,诗论大擘叶燮又在《原诗》里对此命题增加了一个“力”字,这一论说同样影响深远。在此,对李贽、叶燮二说的异同加以比较,具有思想史脉络层面的探索价值。
李贽的“才、胆、识”主要集中在哲学、思想领域,叶燮的理论则主要针对诗歌创作、评价领域,但他们都认识到置“胆”字于“才”“识”之间的必要性,从而使人们更深层次地认识到,随着封建社会的行将就木,用以反抗黑暗的“胆”恰逢其时地显示出它的重要以及紧迫。李贽关于“胆”的认知得到了叶燮的认同,虽然相隔百年,这一观点还是得到了延伸;同时,李贽、叶燮一类先知先觉的思想家、理论家在反封建礼教、主张文学思想进化的道路上已表现出更加主动自觉的特点。
叶燮的“才、胆、识、力”说虽以李贽观点为本,但他追加了一个“力”字。何谓“力”?据《中国文学批评史》讲,“‘力’指概括各种事物与独自成家的笔力”(33)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94页。。“胆”既可以与“识”组合而成“胆识”,如李、叶都认为“识”居于主要地位;又可以与“力”组合成“胆力”,如此叶燮便在李贽的基础上,为“胆”的范畴增加了一定的理论深度与厚度。二人都强调“识”的重要,原因在于他们都认识到“识”能张“胆”,正如李贽所言“才胆实由识而济”,叶燮也说:“因无识,故无胆,使笔墨不能自由。”(34)叶燮:《原诗》卷二,王夫之等撰,丁福保辑《清诗话(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595页。有趣的是,李贽看到了“才、胆、识”三者之间有一种相生相济的关系,这实际上要比叶燮所强调的“识”与“胆”“力”之间的因果关系更具思想上的厚重。
不论是李贽所创新标举的“胆”的范畴,还是叶燮添加的“力”字,归根结底都是让文学思想能够创新进化。李贽生于1527年,叶燮生于1627年,而又过了一百年,在1727年,清代诗人、文学家赵翼出生,他的诗歌理论便是以强调创新为突出特质,这或许正是一种历史的巧合。换句话说,李贽以“胆”开辟出一条新路,叶燮则拓宽之,到了赵翼这里就变得更加鲜明。此外,在“胆”的这条线索中,也有近代王闿运的遥相呼应。他曾言:“看船山诗话,甚诋子建,可云有胆。”(35)周柳燕编著:《王闿运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6年,第299页。联系起来看,仿佛可见李贽、叶燮、王闿运三人跨越时空的莫逆于心和同频共振,“胆”在中华诗论中也不再寂寞、冷清。
在李贽身上,“疑”增添了“胆”的光彩,“胆”又壮大了“疑”的力度,“胆”为体,“疑”为用,“疑”“胆”相济。二者都是李贽为后人留下的宝贵治学财富与启发所在,同时,它们也正是李贽所创造的新知本身。
结 语
在封建社会的漫漫长夜和君王至尊、经学独尊的主流传统中,李贽坚守、发扬了平等、宽容的精神理念,倡导了“恒顺于民”的政治方法,拿起了“疑”和“胆”的思想武器去进行批判、抗争和启蒙。他的学说中既有旧思想的颠覆,也有新思想的建设;既有“入乎其内”的方法,也有“出乎其外”的超越。相比于明末清初三大儒,李贽显得毫不逊色。然而,任何人都有自己难以超越的历史局限性,李贽也不例外,他的平等宽容思想终究没能越出时代和唯心主义的藩篱。“李贽虽重视作为人类的人,无分凡圣,他还没有完全达到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则或人类学原则。”(36)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册,第434页。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中间过客,只是有的人会流痕甚至流芳。李贽身处中晚明转型期,其思想中的反封建、反传统也显示了承上启下的地位和意义。他向前承续王学,向后启发袁宏道、汤显祖等文人名士,其思想的启蒙价值更使得他备受现代学术史关注。
作为“异端”的先行人,李贽思想最主要的魅力在于其所显现的对既有之理的反叛性和超越性追求。他为学著说的前卫与新锐、艰难与辛苦,放在当时的历史文化环境中看实在是弥足珍贵。他对儒学道统的质疑反思呈现出令人赞叹的犀利和自觉,更是显现了冲击旧有秩序的批判性启蒙的积极意义,可谓思想史中一处不容忽视的历史坐标。筚路蓝缕者理应获得人们更加充分的关注和尊重。
——以黄麻士绅纠葛为中心的讨论
——《李贽学谱(附焦竑学谱)》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