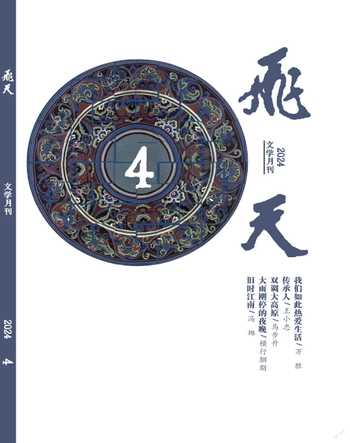人山人海
王倩茜
一
那年春天,我的大学同学延波到十堰出差,暂居几个月。
我回十堰探亲时,和他约见在汉江边。那是一个温暖的傍晚,整面汉江都弥漫着水汽散发出来的清爽气味。
延波租住在市中心的一个居民楼里,半新不旧,地板会发出嘎嘎吱吱的声音。他的房东住在隔壁,是个退休的高中数学老师,每次延波在墙壁上看投影电影的时候,一墙之隔的房东就开始弹钢琴。有时是《卡农》,有时是《小步舞曲》,还有时是《友谊地久天长》。房东也许是单身,一脸寡淡,职业习惯让她说话字正腔圆,延波从来没见她房里走出过第二个人。尽管延波和房东两人各自都背负着孤单,难以忍受的,但是他们的关系就维持在见面时礼貌地点头示意的范围。
暮色将沉,我和延波沿着汉江边行走。
五六十年前,我的爷爷也在这条江边行走,长江的最大支流,江水溶溶漾漾,往上游走是陕西,往下游走是江汉平原。
后来,爷爷患了癌症,前面几次化疗并没有击垮他,他始终头脑清醒,脾气暴躁。最后一次化疗顷刻把他变成了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那时候我只有九岁,他穿着中山袄子,老态龙钟,卧在沙发上一言不发,那个漫漫的傍晚,《新闻联播》正在播放春晚的彩排,我偷偷看着他沉重的面容。死亡到底有多沉重,我也不知道。最后两个月,他彻底放弃了治疗,一顿一顿喝着郧县黄酒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一直到闭上了眼睛。1995年,爷爷的骨灰装进了盒子里,埋在了市郊的墓地,和其他的亲人一起。
我不知道他在半山坡想不想念汉江,还能不能记起绿松石、女娲、七夕、郧阳人头骨文化,还有武当山,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在这里串联,那些小时候他讲给我的江边神话故事。他带我去老郧县人开的面馆吃面,酸浆面。手擀面打底,里面有豆芽、酸包菜,我没有什么胃口,他说独门秘籍是浆汤,腊菜白菜芹菜包菜嫩豇豆在锅里煮开捞起,再用八角桂皮封存,经过神秘的时间隧道。我以为酸浆的咸香可以驱散掉什么,可我的鼻腔里一直停留着特殊的气味,那是野菊的清香。
现在他就那么走了,我们也成年了,接着离开了鄂西北。老三线工业汽车城是在慢慢清冷,他像一个空巢老人被永远困在了这里,无聊,沉闷,满脸皱纹。
乡愁不能让伤口愈合,乡愁也许就是伤口。
爷爷去世的前几天,家里人已经在准备后事的方方面面了。大家拿来几张照片让爷爷挑选,选中了哪一张就点点头。我没有见到爷爷临终的模样,甚至逝去的面孔。那场追悼会我没有参加,除了全家人戴了一个月的黑纱袖章之外,我的记忆一片空白。
只是,当看到那张黑白大照片的时候,我忽然涌出了种种感触,最令人敬畏的莫过于孤独,比如阳台还堆着那么多酿黄酒的坛子罐子,凄凄凉凉的,最后都成了垃圾杂物的一部分,他是那么挚爱黄酒,最后还是败给了癌症。他只有61岁,尽管那时我觉得他已经很老了。
爷爷去世后将近三十年的时光,奶奶一直保持独居,从前我只是认为自己失去了爷爷,而最近我才频频意识到,奶奶失去的是生命中的唯一。爱情并非可以充饥的三餐,而婚姻则为他们提供了稳定精神的保障。他们结婚时有没有发誓“相濡以沫,坚守一生”?
走了一个环线,我和延波又回到了起点。继续往大桥的方向走,几股风刮来,我们俩各自裹紧了大衣,沿途的车灯快要闪瞎我们的眼睛,像是走在电影的长镜头里。不,这不是拍电影,只是我尽量想触动一点什么情绪,应景式的。
我们趴在大桥中间的栏杆上,江水的上面,像是在极远处俯瞰这个世界。2007年虽然成为了历史,但并没有那么遥远。我跟延波说起大学时影视鉴赏课上播放的电影,侯孝贤导演的,我忘了片名,讲的是三生三世情缘未了,静水深潭式的笃信相伴一生的一男一女。我至今记得镜头里的女人在絮絮叨叨地说话,那是一出哑剧,观众听不见她在说什么,整个世界都是“她”,“她”的“他”,女人的悲喜生死,都与整个世界无关。
我借机问延波到底追过多少个女生,延波笑了起来。他当年宣称不吃窝边草,把追逐的眼光投放在了哲学系的女生群里,后来借选修课的机会,又在历史系声名鹊起。我们说他不是在池塘里撒网,就是在池塘里钓鱼,钓到一条是一条。他认为没有什么不妥,因为他最后一条也没有钓上,他是双鱼座,不知道谁到底才是鱼。总之,到最后,他和女生们一一建立了革命般深厚的钢铁友谊。
大学毕业后,我和延波再也没有见过。尽管我们陆陆续续都有对方的消息。我长久定居在长江边的特大城市武汉,在那里,汉江最终汇入了长江。延波四处漂泊了好多年,接受强有力的人生撞击,慢慢变得理智。隆冬的时候,内蒙古的积雪折射出光芒,他决定回到陕西老家,汉江边的城市,秦岭山脉的一片云雾中。像是世间隐喻的安排,恋爱也好,结婚也好,都开始了最好的时光。眼神清澈,一闭眼世界就黑了,一睁眼世界就亮了。他开始研究手相,掌心的手纹慢慢清晰,财纹天纹地纹人纹,有一天手掌心突然出现了一个大元宝,模棱两可,是事业线和生命线在交接了。不过,他后来并没有成为人中龙凤,而是有了两个孩子,终于驱散了失落的阴影,甚是卓绝。
远山蜿蜒漫长,我们在灯烛点点里步行,延波问我:“三江面是什么?”他看见房东经常从外面买一碗端回家,用方言告诉他这是当地特色。
“三江面?是酸浆面。”
我纠正了他。
我不太愿意吃酸浆面,它是我的伤口,尽管我是嗜酸爱好者。可今天,我们还是决定去一中校门口吃酸浆面。
二
千禧年,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又开始了。我如愿考上了市一中,住在了外婆家。
三年后,我考上了外地的大學,我坐上绿皮火车,穿过一整座城市,穿过城郊和大山的隧道。后来的很多年,大城市的灯红酒绿已经司空见惯了,我常常会回到十堰探望外婆。
她还住在一中,三十多年了,她一直住在那里。半坡上的老房子,往下坡延伸就能走到市中心最繁华的五堰街。我敲门,马上就听到里面兴高采烈的东北话。
我在外婆家看出了寒酸和敷衍,是那种富足而无能为力的寒酸和敷衍。她有优厚的退休金,丰衣足食。双开门的大冰箱装满了蔬菜瓜果,怏怏的,几乎是灰黑色的了。她说是楼下邻居自己种的。黄瓜、丝瓜、苦瓜、茄子、玉米、毛豆、白豇豆、空心菜、木耳菜。即使换着花样吃,一个人无论如何也吃不完。还有第二个冰箱在厨房里,那个老旧的冰箱嗡嗡作响,里面塞满了购物袋,只能辨别出鸡蛋格子里堆着没拆封的面条和榨菜。
煤气炉子下面全是矿泉水瓶子,混合着淡黄色的油垢,里面装满各色五谷杂粮,绿豆、红豆,、黑米、红米。炒锅里还有没有清洗干净的食物痕迹,溢出来的米糊还黏在灶台上。整个厨房是个蒸笼,要拿电风扇往里面使劲吹风,才可以抵御西晒的窗户、灶台旁的蒸汽。
我们面对面坐在沙发上聊天,外婆眉飞色舞,说楼上楼下和隔壁的退休老师们的故事,她在说,我在听,但我听得心不在焉。她告诉我,楼上的邢会计走了。“邢会计是谁?”我问。“是晏老师的老伴。”她回答我。我记起来了,就是每天黄昏时一起搭伴坐在操场上聊天的老同事。他们和外婆一样,都是当年从东北来这里支援三线建设的。秋天依旧是忧郁的季节,外婆继续忧郁地说:“我也老了。”我偷笑,说:“都八十多岁了呢。”她不再说话,沉浸在自己的绝望中。她那么爱美,依旧那么爱美。既不能容忍自己将来卧床不起,也不能容忍床头柜边上摆着一个大号坐便器。无可逃脱的宿命的沉重。她说:“更老了我就进养老院。”
她进厨房给我泡红茶,去储藏室找瓜子和核桃。我们坐在暖气烧热的房间里看电视。她不爱看新闻频道,每晚都在看爱情家庭剧。剧情在戏中人的哭泣中进入高潮,她停止介绍剧情和吃瓜子,全神贯注地看。等哭泣气氛回落,情绪顺利转化,她继续把刚刚的剧情重述给我听,剖析那個男生到底爱不爱那个女生,她曾经是班主任,在人物的描述上一向比较强,事无巨细。
有几次,外婆又停滞下来,认真地看,用手势示意我不要说话,电视剧里那个男生又开始告白,款款深情。那个女生开始落泪,她的眼眶也开始发红。
——荒诞的是,她的青春仍被好好地保护着,年轻人的情感又一次具象化。我明明是沉迷于告白的那一代人,又忽然被她的情绪抽离了出来。
还有另一种精神食粮,是专门供给孤单的灵魂的。
她去外面参加各种各样的养生保健培训班,认识了很多陌生人。陌生人拿鸡蛋、奶粉、长生不老的药丸诱惑她,教她从利益的角度审视我们的关系。“我们”,指的是她所有的直系亲属。陌生人想尽办法让自己融入她生活的情境,混淆视听制造了掩饰性的身份,让她精神愉悦,她们撒娇喊她韦老师,挽着她的胳膊去市场买蔬菜,一起坐在沙发上朗诵诗歌,还把一筐筐鸡蛋和牛奶搬进她的冰箱。
重温过去一个人无法体验的生活,作为女儿,作为外孙女,这些是直系亲属没有精力做到的。
她的储藏室慢慢塞满了,连挪脚的地方都没有,好像空虚感也被填满了。作为感恩,她回馈给陌生人若干笔不菲的钱,谁也不知道她斥资多少万元,去购买延年益寿的保健品。陌生人亲自登门,把包装盒捧给她,有药丸,有饮品,毕恭毕敬,永生的愿望强烈到无法忍受。她看不清包装盒上的字,密密麻麻的至理名言,总之是高丽参人参西洋参野山参灵芝粉。
她是掏钱的那一位,主动权是在她的手里,若干桩合理的买卖之后,她笃信情绪和长生不老都有了。
有那么十多年,外婆会把两间闲置的卧室租给高中生住。80岁之后,她嫌太麻烦,便不再对外出租了。
她经常搬家,事实上,只是从一间卧室搬到另一间卧室。抱着枕头和被子,把床头柜重新整理了一遍,就完成了搬家仪式。春天到冬天,她每年都要搬家几次。
一天清晨,她睁开眼,听见卧室柜床里的海浪声。黎明的清静气氛里,海浪拍打着床板,涨潮,又在涌动中退潮。她从床上爬下来,慢慢靠近柜床,那个三十年前的多功能老家具,外公托人打造的,不用时便翻上去和穿衣柜融为一体,变成一扇柜门,需要时就可以翻下来,变成一张床。
她侧耳细听,海浪轻轻拍打沙滩,有细细的沙粒坍塌的声响,泡沫在远远地破碎,生出几丝伤感熟悉的情绪,唰啦唰啦。她敲了敲柜门,海潮慢慢退了,声音消失在海平线。她转身离开,再一次听见涨潮声。
从那一天起,柜床里就一直回荡着海水涨潮退潮的声音,整个卧室充满了海潮的咸腥味。她的耳膜有低鸣的声响,轻微的胀痛,半睡半醒中,一场酣畅淋漓的大暴雨即将来临,很奇怪,整个房间变成了一艘船,她独自睡在海水的暴风雨中,入眠格外踏实。她去北面的阳台浇花,校园里还亮着灯光,高中生们还在安静地上晚自习。站在教室灯光的阴影里,入迷聆听,没有海浪声,一轮上弦月在往天台移动,那晚最亮的两颗星星也不见了,大概是她老眼昏花,再也找寻不到。
过了七八天后,外婆忍不住找住在楼下的青年教师帮忙,拉下柜床,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三十年的老家具依旧散发着淡淡的木头味,只是坚持和时光殊死的对抗,已经染上了一层薄膜,它以机动战士的姿态,严防死守,无论青年教师怎么用力都打不开。
涨潮了。她让青年老师仔细听,里面正是在远处涌动的浪声。柔和的夕阳倾斜在屋里,海浪上是一片片金色的黄昏。她用手指触摸着柜门,天鹅绒的质地。那个声音很熟悉,潮水轻轻拍打时,就觉得心里像电击一样酸楚,刺激到了哪种感官,很忧伤,不知道在哪里听过。人到了80多岁,会开始感知到不可理解的东西,这种变化第一次出现,她担心自己生病了。
青年教师摘下眼镜,把耳朵贴在柜门上,仔细聆听,什么也没有听到。他下楼又找来另一个青年教师,试图一起打开柜门。
柜门终于打开了,里面当然没有大海,只是出乎意料地找到一片绸缎手帕,淡蓝色的,上面绣着“大连1954”,还有一句俄语,大概是她在北大荒当俄语翻译时留下的。大连,那是外婆的故乡,里面包裹着一个干净的海螺。
三
我和延波去一中吃酸浆面,半坡上的一家苍蝇面馆。
我告诉他,我外婆曾经住在一中。每一次我回来看她,她都会做很多我爱吃的菜,北方菜她基本不太会做了,只会做韭菜盒子。带馅烙熟的都叫盒子。五个鸡蛋加半勺盐打散翻炒,韭菜洗净切成小段,加两勺油锁水。她喜欢把面皮擀得厚一点,这样煎出来的外皮很酥脆。韭菜鸡蛋里她会加一勺盐和十三香,还有大连小虾皮,绝配。有时候,我回来和老同学频繁聚会,胡吃海喝加上睡眠不足,胃里翻江倒海什么也吃不了了。最后她只好做了一碗炸酱面,面里拌上萝卜丝和黄瓜丝,我就那样囫囵吞枣地吃了。
这些年,我有个很特殊的习惯——我回来看外婆或者奶奶时,总会先通个电话。挂电话前,就抓紧在屏幕上截了一张图。就是几十秒的通话记录。这是他们还在人世间的证据。说不上是残忍还是长情,衰老和死亡面前,既然无能为力,那就试着慢慢地告别他们,这是最朴素的意义。慢慢慢慢,提前哀悼这是最后一次通话。
那都是曾经的事。
“为什么是曾经?”延波好奇地问。
“因为房子卖了。”
我还记得那个分水岭事件。外婆88岁的那个冬天,学校决定将旧家属楼拆掉,因为它们年久失修,已经到了修修补补都无济于事的地步。当然,就连作为老字号的高中校园大门都将不复存在。那个冬天,学校用木板将家属院和校园严格地隔离开,也将她枯寂败落的晚年生活和喧嚣滚滚的前尘往事永远划出了分界线。
听母亲说,外婆已经有些阿尔兹海默症迹象了。我去看望她,临别时,她忽然拥抱了我。一种莫名其妙的离别感。在那个凝固的时间里,我用力记忆着她衣服上的药丸气味,明明无法接受,却又反反复复逼问自己,这会不会是最后一次见到外婆了?
拥抱完毕,她双手抚了抚我的脑袋,说了一句俄语。我问她什么意思,她似乎没有听清楚。临出门时,她忽然用大连话问我,你叫什么,你多大了,结婚了没有?
我一路大哭着回家。一夜无眠,后来又持续几天失眠。第一次吃下了褪黑素,第一次经历睁眼到天亮,哀乐随时都要奏响,一次次地说服自己接受,却又在接受后马上经历记忆的摧残。
后来我听说,外婆决定卖掉房子,带着养老金住进武汉的养老院,和母亲小姨团聚在一个城市。她不听任何人的劝说,很快卖掉了房子,只拿了一个旅行袋就离开了十堰。行李袋里也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几件换洗的衣服,牙膏牙刷,一点护肤品。她生活了半个世纪的十堰城,就像房子的附属品,变成了化石。“房子已经卖掉了。你们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那么酷,又那么残酷。
时间未必是治愈一切的解药,也许是毒药。后来我们又去武汉的养老院探望她,她已经年过九十了,护工说,她已经混淆了季节,总是神情恍惚地在衣柜里翻动,把衣服全都拿出來,一件接着一件地套着,最后把自己穿成俄罗斯套娃。
我们把她接出来吃饭,她依旧被打扮得珠光宝气,黄金首饰和挂坠一样不少,衣服上没有污渍和破绽。但是,她已经不认识我们了。她在哭的时候,我们被逗得直笑。她在高兴地笑的时候,我又觉得眼眶红了。我们在一旁说话,她不作声,只是一颗一颗地剥开基围虾,认真地吃。她还记得她是海边长大的人。
我们没法再多说什么。其实我们的人生似乎发生了巨大的偏差。回不去从前的故乡,又无法定居在真正的故乡。感同身受从来就是一个伪命题。就像延波没有追问我,为什么吃酸浆面会吃出忧伤的味道,我也不会强迫他回答,那些年在城市间漂泊时,有没有感到绝望。
四
社会福利院的大楼在汉口火车站的附近。悬浮在半空中的露台上,只能听见大马路轻微混沌的噪音,也许视野里全是林林总总的高楼大厦。
逐年老去的人,只能坐在椅子上看波澜壮阔的天空,好似海市蜃楼。不远处就是长江,也许可以看见更远的汉江,他们会艳羡吗?
我们不知道的是,折叠半开的窗户里,风是湿润的还是干爽的,遇见太阳的日子,能不能闻到夏天的汽水味。尽管距离火车站还有一段距离,但也许还能听到汽笛的声响。老人们有没有还想见面的人?
生命一站又一站的旅程,相互确认和告别,他们的面孔每天都在发生变化,身体越来越轻柔。在人山人海中。
责任编辑 维 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