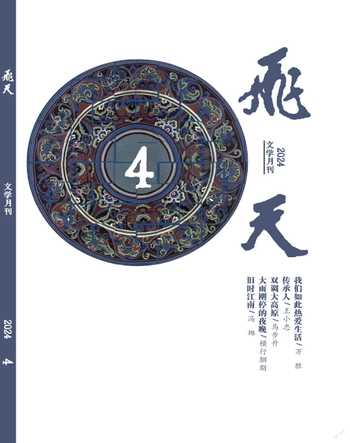租客
周荣池
1
我做过几年房东,但并非要靠“吃瓦片”生活。我们那个地方,相信人是房屋的胆。一个人胆破了恐要殒命,所以房子没有胆是要破落的,这并非完全是虚念。一些物器是要使用的,且可能越用越有气力和气质——这有点农民的禀性,他们越是劳作越有信念。
初见租客的时候,心中不免吃虚。我到底是乡下来的,做不出那种傲慢精明的脸色。中介带来的人,好像是媒婆介绍对象,把屋子和周围的形势一番夸赞,我听了都脸上发红。那年轻人脸色也纯朴,不多计较就应了条件。他似乎并不十分买账中介的话术,对一边话语不多的我倒有几分谦和。我以自己的判断——他和我一樣是乡村走出来的孩子,一问果然是某乡外出读书返乡就业的青年。中介并不因为年轻或者实诚就松自己的口风,她要靠租金的比例抽头,她也知道这是“一锤子”买卖。以后续租,就和她无关了。她几乎像是强迫一样,把那固定格式合同拿出来大致读了一下——其间读错了好几个字也浑然不知,这些和她手上的合同一样,都是形式,到手的佣金才是她关心的。她按着我的肩膀坐在了有灰尘的凳子上说:“你看这房客也算是老实,年轻人好说话!”待我签了字,她复又将那年轻人的肩膀按着坐下来:“你看,这老板也是体面人,这屋子住得放心!你信我,小伙子。”就这样,我因一纸租房协议成了这位中介嘴里的“老板”,成了一个陌生人的房东。我看出这个年轻人面色中的朴素,他确实没有什么精明的经验。我把钥匙交给了他,心里的窘迫轻松了。好像我才是一个租客,除了纸上的内容我实在也不知道有什么好交待,在中介收了双方的介绍费后立刻下楼。在楼道里,她自然安慰我:“这租客素质不错的,你信我!”我相信,她体现出的好感在于我们对她的费用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下楼的时候,我又多了一种羞愧感:我只是因为这几两散碎的银子,成了一种精明的城里人。房东就像是一个有着权柄的角色,是东家,是主家,是钥匙上的傲慢,但我并不愿意有这些。
此后我就几乎忘了这件事情。每年的房租那年轻人是主动给我的。我有一次在街头遇见他,生怕他客套地叫我是房东,故意装着没看见擦肩而过了。我想,他如果真是个和我一样的农村孩子,也不会喜欢那种客套的场景。城里人的热闹,多是一种虚浮的修辞,是乡下人说的“果子茶没有,果子话一大堆”。但这也不是全部的情形,农村人实在的冷漠也可怕。后来,他因为水电的事情电话给我,我不知道这是自己的义务,电话中就告知自己处理,费用在租金里自行扣去则是。此后他大概也觉得我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也就不问我的意见了。我不愿意自己租房的事情被提起,是有一种不劳而获的感觉,尤其是不乐意让别人觉得我是一个收租的城里人。后来退租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见面。他约定好了把钥匙放在屋内就走了。我手上有钥匙,但从来没有开过那门,我觉得那房子应该暂时不属于我了。
当我再次进入这处房子的时候,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期待。三年之后我才意识到,当初并没有问那年轻人租房做什么。心里想的是租房子除了居住,能有什么其他目的?他的具体目的是未可知的,他可以隐瞒或者改变,这并不是完全可控的。期间我也有过想象和担心,比如某天收到一个电话,说房子着火了,或者房子里的租客和人争执起来要拼命,甚至有更离奇的事情。这些消息网络上是常见的,所幸我并未接到这样的电话。
他退租之后并没将屋子打扫一下,留下的东西还留着一些过去生活的蛛丝马迹。可以看出来,这房子不是他一个人住的。从墙上贴的一张表格看来,他们在此组建了一个网络公司,内容好像是玩某款游戏。我上学的时候听说过这种营生,但想不到在自己的屋子里也会有这样的遭际。这处本来是我作为书房的一处小小的屋子,不过六十几平方米,这三年它可能的场景是这样的:厚厚的窗帘将朝阳挡在时间之外,夜以继日的年轻人刚刚睡去。电脑屏幕依旧闪亮着,机器不知疲倦地运转。它们的亮光才是这些年轻人的朝阳。它们不畏惧任何辛苦,键盘鼠标边上,是空的碳酸饮料瓶。烟缸里熄灭的烟蒂,说明着通宵夜战的坚持。那些外卖的包装,是他们与现实世界为数不多的联系。他们沉睡到午后醒来,或许会下楼看看熟食店里的食物,也会聚起来喝点小酒,商量着下一步的打算。这就是一种生活,是一种值得被记得的辛勤。他们之中有天才,有担当,有对生活的热情,网络就是他们的田野。他们并不比自己在农村的父母软弱或无能。他们有自己的办法,并没有因此失去任何的志气。他们走在街上的时候,脸上也照耀着明媚的阳光。
他们大概不十分会打理生活。他们何曾不是自己父母娇惯的孩子。也许只是当初没有太过认真读书,因此选择这样的生活。他的手上同样有父母一样苦痛的老茧。我后来看过许多视频是他们制作的,他们也是其中努力的主角。他们就是这样进城的——租借城里的房间和生存空间,同样走出了一种光亮的道路。我仿佛看到自己身后走下去的脚印,一路那么清晰,那么问心无愧。
我请了一位清洁工把屋子扫了,答应将他们留下的一应物品也都给了他去变卖。他打扫的时候不时地抱怨这些年轻人暴殄天物。有些东西在他看来是值些钱的。他和我一样都有来自农村惜物的心结。也许他也有这样的儿女,在更大的城市,租住着房子,为奔波的生活找到可以停脚休息的一隅。我后来把屋子修葺了一下,粉刷之后那几年积聚的气息就被隐藏了。只有如我农村来的古怪房东,在意一种莫须有的陌生气息。后来我再也没有遇见过这样的租客。也有一些令我感到满意的人家来住过。他们多是陪孩子来读书的。孩子升学或考学外出之后,他们就回到自己的乡间。没有人愿意永远做一个租客。
他们也没有我那么些古怪的想法。那六十几平方对他们而言只不过是一个房子。而我只是一位陌生的城市房东,没有人愿意去打听那些多余的念想。
2
我也是做过租客的,最早是在盐城读书的时候。
那时候,我和几位困难的同学都不愿回家,放假了便留在城市里指望勤工俭学。房子是我一个人去租的,我不想别人看见我为了讨价还价,而斤斤计较的样子。有意思的是,困难的人却总喜欢表现出大度的样子。我为此付出了许多虚荣的代价,但它又像是一种宿命。我见到那个精瘦男人的时候,就立即意识到他的精明尖酸。我有一种自以为是的识人态度,这当然也是穷人的敏感。我不记得和他具体说了什么,现在想来,以我的脾性是不愿意和他多啰嗦的。他把楼下东北角的房子钥匙给了我。那里面只有一床破旧的铺板。但想到独居的自由,还是十分的喜悦。
他站在去二楼的楼梯上,背对着光环顾院落,就像王者看他的城堡。
这处房子是座二层的四合院。门是朝西开的,门牌是老虎桥41号。门对着的巷子是南北向,巷子口有一个卖薄饼的摊子。一个中年妇女支应着早晚市。她做的薄饼极有我老家粘饭饼的味道。想想他们这个地方本是和家乡连着一条大河的,味道流传得相仿也是正常。老虎桥的桥已经不见了,只留下古旧的名字。这里还有一家东台鱼汤面和德州扒鸡味道极好。我不能说它们正宗,我不知道正宗的味道究竟如何。我因为经常来这里,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说到底这里是处城中村,但让人感觉十分亲切。不像干净的社区,热闹得让人觉得失真。你早上才睡醒走出来,满街的煎饼摊传来一种声音:宝宝吃蛋饼哇?真感觉是自家大姨在唤你,心里无比亲切。我以为老虎桥的煎饼是天下一绝的。
院子里住的第一户,便是那做薄饼的女人。这间房子最宽绰,便于放下她家乱糟糟的物什。她的男人倒很精致,一闲下来就坐着擦皮鞋。他的皮鞋是锃亮而体面的,其他装束也一丝不苟。他在单位给领导开车。平时待人很客气,笑起来也很斯文。他们有一个四五岁的女儿叫“管小雨”。他们用方言叫她的时候和我老家话一样,将雨读成“舞”的声音。小女孩平时在巷子里和一个小男孩玩,玩那种掀起衣服露出肚皮的游戏。我来时,她就朝我招招手。我走过去,她用手套着我的耳朵说:“叔叔,你假装用手打我嘴巴!”我如其指挥而行,他们突然对巷子口大声叫起来:“叔叔打我嘴巴子!阿妈!叔叔打我嘴巴子!”
接着就是一串银铃般明亮的笑声,穿过巷子直抵云端。我在心里也明媚地笑着。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孩子。有时候,她的父母也拌嘴。我觉得多是那女人的不对,她叉着腰有些悍。管小雨就不作声,走到二楼的台阶上坐着,或者站到我的书桌前望着。我后来搬到二楼来,她来得比以前多。她喜欢爬楼梯,穿着那蓝碎花的小旗袍。
楼上对面住着一个女医生,很少说话,嘴巴就像她的房门一样常闭着。有一次她好像电脑有问题叫住了我,我实在是个无能的文科生,以后就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楼上朝南的正屋里住着几个同村进城打工的年轻人,他们说一样难懂的滨海方言,每天晚上很晚才下工,回来之后又喝啤酒闹腾。我只知道其中有一个叫陶大,后来知道他们是进城来学厨师的,经常讨论老虎桥下卤菜的味道。这里的卤菜,和我家乡比起来实在是少一些水平的,或者说人们的认识不一样。女医生大概认为陶大他们太闹腾了,就带着电脑搬走了。租房子的人都是自愿的,就像一片树叶飘到哪里,有各自的心意,谁也不好多过问。
就像小袁从无锡跑到盐城来做生意,实在让人难以理解。他住在我的隔壁,是有一些抱负的文艺青年。那时候兴起一种“大头贴”生意,但盐城街上还不多见。他闲了的时候就弹吉他,或者走到我的屋子来,问我哪里会有那么多写不完的故事?我和他讨论方便面的不同做法。他是南方人,到底细腻一点。他常穿一件牛仔褂,对陶大他们的热闹有些不以为然,只跟我说说生意上的艰难。他推着眼镜说:“也是奇怪,为什么这里的大学生不愿意拍照呢?”我就是“这里的”大学生,但解答不了他的问题。他也解答不了自己为什么一定要来盐城的问题。那年的梅雨季节下了很多天的雨。他索性不再去做生意,就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弹吉他。院子里的人听不懂,也没有人敢埋怨。他的母亲从无锡来这里看他,上了楼之后,满脸的嫌弃之意,看得出她年轻的时候条件也不差。他就是不愿意跟着自己的母亲回去。他拍照片的地方是转租一处文具店的,连那老板都为他着急。梅雨停了又是三伏的溽热。那时候只有电风扇,但总算比集体宿舍自在。小袁实在挺不住就不辞而别——我疑心这座城市里是不是有他爱过的女子?
很奇怪的是,他走之后转让给店主的机器生意火爆。
我在老虎桥住过几年,都没有换地方。一个地方住得时间长了,会有一种令人怀念的气息。就连你看不上眼的人事,时间长了也会达成一种谅解。大家都是萍水相逢的,并不会有什么太多的瓜葛。即便是日子长了,有了些感情,终究也只是日后散了,才会在心里想起来的。再见到未必能说出什么像样的话,尤其是我们这些农村来的孩子,只是租一段屋檐遮风挡雨度日,哪里能在此生根呢?但以后回到村庄,想起来讲给子孙听,一定也是有些意味的。我有一年写篇有关“老虎桥41号”的小说,但后来没有写完。我本觉得自己对这个院子是有些深情的,可文章哪里会有生活本身更有滋有味呢。所以最终我没有能把这段真实的租客生活写成虚假的故事,我舍不得那么干。
3
我离开临泽古镇进城之后,又做过几年租客。
那是一个巷道纵横交错的城中村,房子都是当初进城者买地自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房主也是城市的租住者,他们虽然在时间上有某种“占地为王”的自豪,然而土地的集体性质,仍然决定其是无法改写籍贯的外来者。这在城市规划空间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意蕴,他们既是忘乡者,也更是失乡者。这里是城乡之间相互妥协与安慰的角落。从形式上看,这里的屋舍并非像城中村那样破败不堪,踞守城市的人有些是继承了贫困的,这种穷根难以拔除。倒是当初那些靠着勤劳致富的殷实人家,在城里买了地安身的,有些朴素的底气——甚至有点后发先至的傲气。我起初住进这个村落的时候,总是找不到回家的路口。不知道为什么,人们将屋舍与巷口的格局弄得整齐划一。这就是他们理解的城市,所有的事情都是“一刷齐”的。房东高爹爹告诉我一个办法:让我看着巷口的一口倒置的水缸,那是有别于其他人家的标识。水缸是从乡下带进城里来的,这在城里是一种丢了可惜,但留着又实在没有用处的物件。高爹爹就把它倒放在巷子口,用来阻挡偶尔绕路经过的汽车。这是在许多的道口都有的风景,大多数是奇形怪状的石头,只有这口水缸是唯一的存在。在那个时候,它暂时标记了我回家的路。
高爹爹的屋子也是二层的院落。除了堂屋和自己的房间之外,其他都租给了外人。他甚至把一块不大的晒台也用一种蓝色的彩钢瓦包裹成一间屋子出租。我在那屋子里住过,进门几步就是床边,没有任何陈设可言。它唯一体现出善意的地方就是租金低廉。夏天夜里雷阵雨来的时候,我常常想象这屋子会被风卷走——那样我坐在床上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窘态?乡下人进城最怕的并不是吃苦,是怕露出窘迫的神态,所以他们说话都是小心翼翼的。高爹爹的老太婆是个碎嘴子,每天不知道嘴里说的什么,就像是嘴边挂着瓜子皮,总没有清爽的时候。前一位租客走的时候,在墙上留了一幅观音画像,这成了她的心病,几乎每天都要来检查一下,更要警告我:请来的菩萨不能随便送走。说得时间长了,我甚至真起过恶念,但我不敢那么做,我知道这会要了她的命。我后来从小屋子搬进了正屋的二楼。这间房子要宽绰得多,她每天都要来叮嘱一番听不清的言语,并且用眼神暗示我东边夫妻俩又吵架了。住在东面的夫妻是跑班车的,每天固定的时间往返于两个城市之间,丈夫开车,妻子收票。他的妻子似乎并不十分有姿色,他总是怀疑妻子学坏了,有时候无端地就摔了杯碗。
他是真的下狠手打人,但第二天又求饶认罪。这让人觉得有一种令人心疼的喜感。他有时候会喊我们去吃酒,但是并没有人去。有一次下大雨,他们又争吵起来,把电视机扔到了楼下面。第二天一早,他们又发车讨生活去了。他们起得很早,这逼着我有了早起的习惯。早起了也并不读书,就坐在楼上的过道里看院子里的忙碌和來去,这比读书要有趣。我后来离开这里,还听说高爹爹去世的消息,不知道后来他们过得怎么样了。作为一个租客,我觉得那些房子对我是有恩的。对于进城者而言,我们某种意义上都是飘零的租客。即便是后来有了房子,或者把户口本上的住地也改了,但依旧是城市的外来者。我们依然说自己的方言,心里记着那些旧事情,在繁忙的城市中风里来雨里去。
责任编辑 赵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