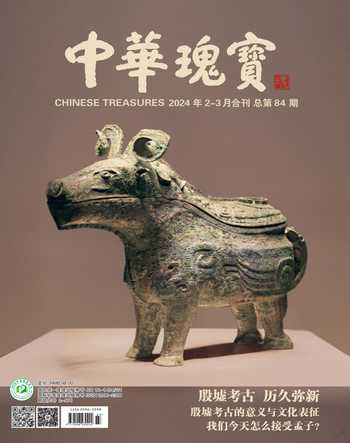庆龙年 赏龙纹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龙纹装饰传统由来已久,历久弥新。它时而粗犷威武,时而精细纤巧,时而朴素简洁,时而色彩斑斓……
2024年是甲辰龙年,作为中华民族古老图腾的典型标志,龙的意象形体自诞生起,便被赋予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指向。龙的民族性和社会价值的指涉性,突出表现在中华儿女是“龙之传人”的叙事范式。数千年来,中国社会在龙文化理念的加持下,以抽象演绎和具象呈现为蓝本,通过艺术加工、美学创造等多维形式,将虚拟化的“龙”形思想嵌入到生活视觉领域,不仅可观可感,而且若隐若现。尤其是在历朝历代传承至今的实体器物中,能工巧匠极尽创新之能事,将龙的文化意识体现得淋漓尽致,彰显出极强的艺术转化力。
龙袍上的皇家气象
封建社会历来推崇君臣有别、长幼有序,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体现在服饰上则是龙袍的符号化标识对皇权至上的渲染。由于龙是威严与权力的象征,贵为天子的皇帝以龙纹为装饰,将其刻画在各类生活器具上。龙袍作为帝王外在形象的呈现载体,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底蕴,着龙袍以正其身在整个封建王朝更是屡见不鲜。现藏于沈阳故宫博物院的清太宗皇太极御用黄色团龙纹常服袍就是众多帝王龙袍里的典范。相比于清代皇帝留存下来的各类朝袍,皇太极的这件御用龙袍可谓大道至简。袍身纵长130厘米,面料为明黄色织锦缎,整体造型为圆领、大襟、马蹄袖,云纹、团龙共嵌其上,袍领、袖间皆以蓝地云龙纹缎镶边,是目前皇太极遗存文物里难得一见的传世珍品。
袍服通体以传统的香黄色为底衬,仅在领口和袖口处施以龙纹,其余部分不着一墨,不仅精致淡雅,而且朴素简约。其虽无其他龙袍满纹绣制展现出的雍容华贵,却能引人注目,映入眼帘尽是“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庄重。倘若仔细观瞻可以发现,袍服上的织金云龙纹刻绘得细致入微,龙的形体苍劲有力、栩栩如生,意在诠释“宛若在天,却又遥不可见”的美学设想。
这件常服袍作为清初皇帝御用服饰里的一枝独秀,无论是形制用料的选取,还是纹饰色彩的设计,均与入关后的宫廷服饰有着较大不同。嘉道时期的龙袍多以满绣龙纹为主导,礼服和吉服上绣制的无一不是五彩龙纹图,色泽艳丽,富丽堂皇,前后胸部与左右两肩处均是一条正龙,典型代表是清月白地缂丝五彩金龙单朝袍。如道光帝御用的夏季朝服通身由38条形体不同、造型各异的彩龙组成,其中有9条正龙,18条团龙,11条行龙,分布于披领、肩袖、腰帷等处,并将山水、日月、星辰、鸟兽附着其上,与素净干练的皇太极朝袍相比,呈现出强烈的视觉反差。这反映出清代不同时期的社会发展源流和文化流变趋势。
龙纹作为黄袍上的构筑元素,一直以来寄予着统治阶级江山永固的美好期许。由于龙的通灵寓意,其被广泛视为驱邪避凶、降灾赐福的神兽。而且,龙是十二生肖中唯一不具备客观实在性的虛拟构想物,因此有着与众不同的天然神秘性。也正是基于这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文化意识,古人偏好以龙为艺术塑造范本,秉承“不似似之”或者“不似之似”的表现手法入诗入画,通过在服饰上绘制龙纹以展现皇家气象也便是顺其自然的事。
瓷上游龙若惊鸿
从史料来看,龙的图腾文化最早可追溯至三皇五帝时期。《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皇帝大败炎帝和蚩尤,先巡阅四方,后合符釜山,并创造龙图腾。其后,龙的形象渐渐生活化,大到楼台殿舍、门宇广厦,小到配饰装帧、文玩摆件,龙以无所不包的影响力渗透至社会民生之中。尤其是在瓷文化盛行的宋元时期,龙的实用功能得到延续,并发挥着信息传递、文化传播、历史传承等多重作用。
元代是瓷文化革故鼎新的转折期。其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科学技术的极大进步,瓷器的制作工艺日渐精良,纹饰的艺术张力呈现出多点扩散的特征。龙纹因大气厚重的审美风格,以及不拘一格的表现形式,成为元代宫廷画师竞相描摹的主要素材。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元蓝釉白龙纹盘即是元代蓝釉瓷器中的上乘之作。圆盘以简约见长,胎体并无烦琐的工艺设计,平底、折沿、浅壁,与随处可见的普通瓷盘几无差异。不同之处是,盘体通身施以蓝釉,釉面光滑匀称,沁色圆润,入眼可见如蓝宝石一样柔和的光泽。尤其是盘体蓝釉上以白色泥料塑贴而成的白龙,采用大写意的绘制笔触勾勒而出,粗犷奔放,形神兼备,尽广大而至精微,颇有出神入化的韵味。
元蓝釉白龙纹盘的点睛之处在于盘内刻画的龙形,细颈修长,三爪昂首,形如水上游龙,翩若惊鸿,投射出高贵典雅之美,堪称景德镇瓷器中蓝釉金彩的代表。而且,元青花是青花瓷的集大成者,颜色搭配强调对比性,作为流行色的白色与钴蓝,视觉呈现给人以清新脱俗之感。
元代龙纹的绘制讲求虚中见实、实中有虚,是本真与虚幻的复杂聚合。龙形的匠心十足,落实到瓷器上更加飘逸洒脱、大气磅礴。龙爪往往偏于锐利,极具锋芒却又不失矫健,既有“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的逶迤气概,又具备“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的皇家风度,留给历代藏家无尽的想象和渺远的遐思。
元代龙纹张弛有度的个性化展示,在青釉为主的瓷器中较为常见。一方面,受前朝审美影响和文化渗透,蒙古族对龙图腾的信仰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元代文人画在着墨方式上讲究笔意与涵养的融合,即层次感分明又不过分夸张。元代龙纹虽然有较大的留白空间,构图则沉稳有力,因此成为后人在艺术加工中竞相模仿的重要借鉴。
龙纹装饰与漆器之美
何为漆器?在汉文化的语言表达中并无统合性定义。一般来说,漆器是经过制胎式脱胎,再髹底漆、打磨、推光、装饰等工序制作而成的一种工艺美术品。《韩非子·十过》一章中说:“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之,削锯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西汉文学家扬雄在《蜀都赋》中也对漆器的华丽外表进行过形象描述,说其是“雕镂器,百伎千工,东西鳞集,南北并凑”。可见,漆器作为一类食具,不仅拥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制作工艺烦琐复杂,广受大众青睐。
无独有偶,龙纹的典雅以及富有的装饰性价值在漆器制作中亦是层见迭出。从考古出土的具体实物看,古代漆器上的龙纹变化多端,并无统一定式。如西周时期的漆器龙纹以浅雕为主,汉代的龙纹则倾向于写实。南北朝受佛教文化的影响,龙纹表现得更具动态感。但无论是哪一种表现手法,将龙纹与漆器相结合,以此传递美美与共的思想情趣,是古人在艺术创作过程中追求万千华丽集于一身的自我阐释。特别是明代漆器上的龙纹装饰,融百家之长,创独家之新,具有很强的致用观和富贵之象。
陈列于故宫博物院里的明嘉靖剔彩双龙捧寿纹委角方盘,是龙纹漆器里的大雅之作。这件方形漆盘横纵口径均为21厘米,盘心开光处雕有两条海水江崖捧寿龙,盘边以花卉纹作衬托,委角处的六角花锦上压雕翔鹤纹饰。盘上龙口喷张,龙须上扬,眉宇清晰可辨,龙鳞呈现火焰状,给人以居高临下的威严气势。
明世宗嘉靖是明朝第11位皇帝,在位时间长达45年,谥号肃皇帝。治国期间,嘉靖帝严以驭官,宽以治民,整顿朝纲,抗击倭寇,一度开创了“嘉靖中兴”的繁盛局面。这种严苛的为政方式使得明代的文化氛围趋于谨慎之风,形如上述的龙纹漆盘,做工精致规整,方圆有序,浅淡处简明扼要,关键处鞭辟入里,龙爪和龙鳞分外突出,镂雕和浮雕形成明显的差异,散发出独有的珠光宝气,在明代漆器中格外显色。
嘉靖时期的龙纹錾刻风格对后世统治者影响至深。例如,明万历黑漆描金嵌银螺钿龙纹箱,沿袭嘉靖时代的龙纹装饰工艺,龙身上有鳞,背部有鳍,鳍又分组而立,姿态威猛,威风凛凛,是粉彩类龙纹漆器实物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闻一多先生曾指出,与其说龙是多个图腾糅合而成具有象征意义的虚拟形象,不如说是龙的精神文化在文明社会里的多向度衍射。龙的形象塑造广泛沉淀于民族信仰、家国情怀和知识演化中,进而发展为具象的图案,并在文学创作、诗画演绎、民俗探赜的道路上交替更迭,历经千年而不衰。在历代统治者看来,这是文化基因作用于现世伦理,继而引发社会共情的必然逻辑遵循。
文化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软价值特质,当这样的文化与具象的实物弥合在一起,便会产生出其不意的美感。形如龙的意象指涉,恰恰是把中华传统美学精神与当代审美追求渐进式结合的行动规范。龙纹融于生活,并被人类加以利用,古今同理,概莫能外,这也其是艺术魅力之所在。
刘中才,中国散文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