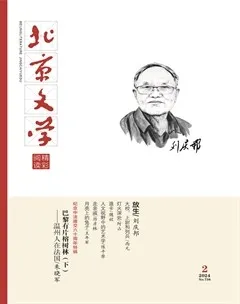刘庆邦的虚与实
王干
《放生》是我近年来读到的刘庆邦最好的短篇小说。擅短篇的刘庆邦,虽然写过长篇小说,但其成就主要在短篇领域。刘庆邦的小说创作是有传承的,他受到过林斤澜的影响,也有汪曾祺的影子,或者说刘庆邦秉承他们两个人的小说衣钵。林斤澜喜欢虚中见实,他的一些小说之所以被人认为看不懂,认为写得云毡雾罩似的,就在于林氏的密码式的写法,林斤澜总是将一些直面现实、直面人生的描写虚化,有时甚至玄化,小说表面的信息没有藏到后面的信息多,让读者有雾里看花的“隔”。《十年十癔》就是虚中见实的有益尝试,也是藏比显多的小说,就是海明威说的那种“只露八分之一”的冰山理论。汪曾祺年轻时才华横溢,绚丽多彩,中年以后的小说,一反年轻时的绚丽和修饰,变得平白淡泊,有时连形容词也懒得用,但汪曾祺写得越实,却透出很多虚的意味来。《受戒》《大淖记事》《岁寒三友》等都是近乎直白的记叙文,但意蕴却很耐人咀嚼。多年之后,汪曾祺仍受追捧,在于他的意味丰富,虚实相生,处处写实,却处处透虚。
刘庆邦的《放生》能够看出受这两个人的影响,在结构上,有林斤澜“矮凳桥”的方式,在语言上,有汪曾祺的明白与简洁。《放生》写的是一对河南夫妇从乡村来到北京谋生开菜店的遭遇,小说描写的时间截点是小菜店即将关闭的最后一个星期。丈夫牛国亮,被人称为老板,妻子马长平,被人称为老板娘,小说写他们每天傍晚吃饭,吃晚饭前,牛老板都要在菜店里喝上两杯小酒。菜店里放有一张折叠式的小饭桌。小说写牛国亮:不喝别的酒,只喝简称为“牛二”的牛栏山二锅头。他姓牛,“牛二”也姓牛,天天喝“牛二”。但牛儿的店一点也不牛,他们经营的菜店虽然发不了财,但也是自得其乐,这样本来惬意的小业主生活,却因为店面是违建,要关店,要拆掉菜店。小说便在这样的时刻,写他们的“自救”和挣扎。
这样的故事在北京发生并不意外,外地农民在北京的谋生,确实是“居大不易”,他们没有北京本地人的诸多优势,确实是一有风吹草动,便“惊慌失措”。牛国亮和马长平两口子对于菜店行将关闭拆掉的“拯救”方式确实是非常的无奈,也是非常的符合他們的性格。在茫茫的大北京,两个外乡来的打工夫妇,面对新政的到来,自然没有反抗和改变的可能,最多也只能是自虐。小说最后写到执法队员来到他们菜店拆迁,悲愤的牛国亮舍不得经营多年的店毁于一旦,但也无力去对抗,他只能将一只西瓜扔在地上来发泄自己的不满和对菜店的眷念,和我们在视频里见到那些暴力抗拒的镜头相比,确实是软弱而笨拙。当然,即使这样的自虐也要冒着违反破坏公共卫生的罪责。
他们一开始相信冥冥之中有神灵来保佑他们,能够保佑店面不被拆走幸存下来,于是牛国亮就买鱼放生,祈求厄运会被无形的力量消除。牛国亮的放生过程也是一波三折,起初是鱼不合适,因为妻子以为丈夫要吃鱼,并没有买活鱼,没有活鱼怎能放生?第二次购得活鱼,马长平像小偷一样放鱼的过程写得真切生动,小说写牛国亮“翻过那座树木掩映的假山,来到一处有野生芦苇的水边,趁前后无人注意,装作到水边玩水,赶快把三条鲫鱼放进水里。还好,三条鲫鱼都还活着,它们一入水,像是重新回到广阔天地,向远水游去。它们没有感谢马长平,也没有跟马长平说再见,摇摇尾巴就游走了。”
三条鱼满载着牛国亮夫妇的希望放生了,但牛国亮的店铺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放生,他们的菜铺子依然要拆除、迁走,愤怒而无奈的牛国亮只能砸一只西瓜来泄愤,“无可奈何花落去”,胳膊拧不过大腿,经营多年的菜铺子也瞬间消失。牛国亮夫妇菜铺子的悲剧也是这些进城者难以避免的隐痛。小说最后给了牛国亮菜铺子一条生路,这次不是固定的阵地,而是游动的铺子,牛国亮开着一辆车在原来的地方继续经营他们的小本营生,总算有了一条生路。
刘庆邦的进城系列小说写外地人和北京人的交往和纠葛,写了他家乡河南人民的朴实和忠厚,也写了北京人的热情和“局气”,写出了浓郁的京味文化,在一些片段中甚至能够传达出老舍小说的韵味来。尤其这篇小说中的两位北京人,足见其写人物的功力。一位是热心肠拄拐棍的罗阿姨,她是北京原住民,回迁户,对牛国亮、马长平夫妇关照有加,视作自己的晚辈。而另一位黄主任,则是作为外地人的对应物存在的,黄主任垂涎马长平,“黄主任没想到,农村还有长得这么好看的女人。他甚至想,作为一个农村的女人,长得差不多就行了,长这么好看干什么!他知道,小牛不愿意看到他常去菜店,不愿意让他看自己的老婆。小牛对他怀有警惕,目光里甚至怀有敌意。黄主任认为,小牛是一个缺乏教养的、粗鲁的人,有些看不起小牛,他觉得小马这么好的一个女人,真是瞎搭给小牛了。”
这里写出了黄主任的好色,对马长平的赞美,更写出他内心深处对牛国亮的“歧视”,一个“城里人”对“乡下人”莫名的优越感。这是刘庆邦藏在小说深处的“文眼”,和那些拆掉夫妻菜店的城管们相比,黄主任更可恶,如果有机会,他会拆掉牛国亮、马长平的家庭。
刘庆邦在处处写实的语境,藏着这么惊天的“虚”!
责任编辑 张 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