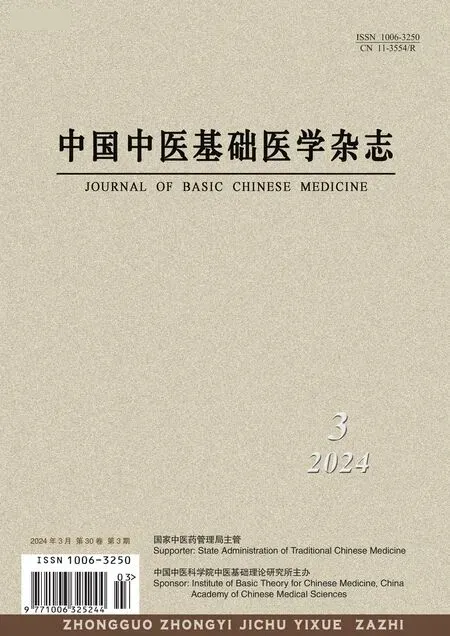基于针药结合理论的“纳米药针”研发的实践与思考❋
徐雯洁,孟 幻,肖 彧 ,王 鹏△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北京 100010;2.中国科学院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北京 100190)
针灸、中药同为中医药体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同根同源,历代医家在临床上将二者结合使用,发挥出协同增效的作用。“针药结合”理论由来已久,其核心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将针灸和药物两种治疗措施结合起来同时使用,达到疗疾治病的诊疗目的。近年来,针灸与药物(包括中药和西药)结合治疗临床各种疾病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研究者一方面积极探讨针药结合疗效机理,一方面利用新型的材料和工艺,研发药械组合新型工具。随着纳米材料的发展,以此技术平台为支撑,针灸与“纳米-中医药”结合,不断拓展针药结合的研究领域,为创新针灸新技术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和实现的可能。
1 “针药结合”理论溯源
1.1 针灸与药物内治相结合
“针药结合”理论早在《黄帝内经》中已经出现,“今世治病,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故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1]34。秦汉时期著名医家扁鹊用针药结合的疗法医治虢太子“尸厥”,先砺针石而针三阳五会之百会穴回阳,继用五分之熨,熨两胁肋以调气机,最后再用八减之剂调理脏腑,该医案为针药并用第一案[2]。汉代医家张仲景亦倡导针药并用,他编著的《伤寒论》中有大量的针药并用条文。宋代名医王执中也提倡针药并用,其所著《针灸资生经》中专列“针灸须药”章,记录针药并用之感悟以示后人。
1.2 针灸与药物外治相结合

清末浙江钱塘医家吴师机,一生致力于膏药敷贴外治法的研究,他认为贴药与针灸相合相通,诊疗手段中既有用药物贴敷经穴治病,也非常重视贴药和针灸的配合使用,拓宽了给药途径和临床思路[4]。其将几十年外治经验撰成《外治医说》一书,刊成后易名为《理瀹骈文》。书中指出,药物外治同针灸“虽治在外,无殊治在内也”[5]425,两者的作用机制都在于通调经络气血,调和脏腑阴阳;提出“膏中用药味,必得通经走络”“一归于气血流通而病自已”[5]428;非内治为补,外治亦能补,“气血流通即是补,不药补亦可”等观点[5]439。吴氏指出人体毛窍在外,脏腑在内,而遍布于全身的经络系统可以使两者相互联系。药物的药性能通过肌肤、孔窍等处深入腠理,并由经络直达脏腑,从而发挥治疗作用。
1.3 针灸与现代医学相结合
针药结合发展到现代出现了许多新的形式,比如穴位贴敷、穴位注射等。穴位贴敷和穴位注射将药物作用和经络联系结合起来,认为药物和针灸都能调整经络里气血的正常运行,其治疗机制是一致的[6]。
穴位注射是用特定针具将药物注射在相应治病点以达到治疗效果的手段,是针药结合的新型体现方式,临床有效,也丰富了针药结合的内容[7]。但是穴位注射也存在问题,比如注射药物药量计算、注射感染控制、辨证选穴等一旦出现差错,就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临床治疗风险。
由上可见,针药结合理论由来已久,临床疗效确切,但同时,又存在无统一标准,注射药物的种类、药量、频率和疗程缺乏量化指标以及安全问题,因此,将针灸和现代应用技术交叉融合,扩展针药结合的方法和应用范围,研发新型针具,将是创新“针药结合”理论的新热点。
2 纳米材料和技术的发展,使得新型“纳米针具”层出不穷
近年来,纳米技术被社会各界广泛熟知,通过纳米技术研发出来的一系列纳米材料因其具有尺寸小、比表面积高的特点以及在光、声、电、热、磁等性质上有着不同于其他传统材料的理化性质,被广泛应用于疾病检测、药物递送、生物标记等各个领域[8-9]。
纳米材料和针具结合,已研发出不少新型的纳米针具设备。
微针具备皮下注射与透皮贴剂等特点,它采用微电子机械工艺技术制作,尺寸为微米级,外观呈针状,结构复杂,可无痛直接穿透表皮至真皮组织,以促进药物递送从而产生局部或全身作用[10]。微针成本低,能实现无痛给药,还能提高药物生物利用度、降低药物毒性,但同时也有一些局限性,比如载药量小、易变形断裂,如果长时间使用,微生物从开放通道进入组织会诱发炎症、感染等问题。于是,随着材料的更新发展,目前又研发出纳米晶片,它是由99.999 9%的高纯度单晶硅制作而成,针尖直径为纳米级,大小约为头发丝直径的千分之一,成为新型物理促渗方法。纳米晶片相对微针而言对皮肤伤害小,但其凸点短小容易造成起效慢,故可将纳米晶片和微针联合使用以改善彼此缺陷[11]。
胡光迪等[12]参考美国学者的研究,用纳米微针体外实验(小鼠皮肤)导入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研制出关节部位药物导入纳米梅花针和针刺仪。该针参考了梅花针针体点阵分布和纳米微针外形设计,生产出9点点阵纳米梅花针,在人体关节部位可实现透皮给药技术导入双氯芬酸二乙胺治疗急性痛风性关节炎,可有效打开关节部位皮肤角质屏障,利用梅花针的局部振动作用使药物渗入而迅速发挥止痛疗效。
Feng[13]等利用纳米技术将黄芩素结合到水凝胶里,再用水凝胶负载到特殊的针灸针上,通过直接将针插入膝关节到达软骨下骨实现药物的释放,从而进行精准治疗。无论是体外实验还是动物实验,都体现出这种新型针具的治疗效果要优于普通的针灸针,成功地实现了药物的精准释放治疗。
由以上文献可以看到,目前纳米技术与针灸针具结合,可以实现药物负载,产生新型针具,但是针灸针仅仅作为药物负载的工具,并没有基于传统理论发挥针灸治疗的功效,未来的研究方向可充分利用纳米技术来研发新型的“药针”,不仅能实现药物的负载和释放,同时可以利用该“药针”进行常规的针灸治疗,以真正体现“针药结合”理论的精髓。
3 以“针药结合”理论为指导,以纳米技术为支撑,研发新型“纳米药针”
在《针灸大成》卷四、傅仁宇的眼科专著《审视瑶函》卷五和郑宏纲的喉科专著《重楼玉钥》卷下等记载有煮针法或煮针药方对针灸、方药的不同作用,同时对该方法进行了评价,认为诸药能引气味入针内,针药协用可以增加疗效[6]。这就带给本研究团队研发新型药械组合针具的启示,可利用新型的纳米材料和技术手段,将药物直接附着在普通的针灸针身上,医工结合研发新型针具,以达到常规针灸治疗疾病的同时完成药物释放的双重治疗目的。
3.1 纳米技术的选择是研发“纳米药针”的关键
为了将药物附着在针灸针身上并能在针灸治疗时进行药物释放,需要依靠新型的纳米技术和材料作为中间介质。如前文所述的水凝胶[13]就是一种很好的纳米载体,可以把中药成分负载在水凝胶上嵌入针具表面,当针具进入人体或动物体内,药物接触到体液会从针具上释放出来,从而产生针药共治的效果。此外,激光技术也可以在针具上进行微雕,从而为负载药物提供可能。本研究团队利用电化学技术在普通针灸针上电镀了“β-环糊精-水杨酸”纳米涂层,并通过这种纳米涂层成功实现了小分子药物的负载(如盐酸利多卡因),研发了“利多卡因纳米药针”。经过体外实验和高效液相测试,明确该药针可在磷酸盐缓冲液(phosphate buffer solution,PBS)中释放,并定量了每根针灸针负载盐酸利多卡因的药量。经过由碘乙酸钠(monosodium iodoacetate, MIA)致膝骨关节炎(knee osteoarthritis, KOA)小鼠体内实验,证实“利多卡因纳米药针”治疗小鼠膝关节的疗效要优于单独针灸治疗和单独利多卡因穴位注射治疗。此款药针是体现“针药结合”理论的“纳米药针”研发之有益尝试。
3.2 负载药物选择符合“针药结合”理论是“纳米药针”起效的关键
针药结合理论中,针灸和药物疗法是建立在中医理论基础之上的两种不同的治疗手段,依据两者在治疗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针灸和药物的关系可分为同效相须、异效互补和反效制约三种不同类型,而临床中异效互补的应用最为广泛[14]。
中医经络理论认为,经穴给药疗法具备药物经皮吸收和经络穴位效应的双重治疗特性,药物刺激某局部穴位可激发全身经气,具有在局部产生药物浓度的相对优势,并能通过微小血管吸收输送,发挥最大的全身药理作用。经穴给药有别于血管和血液,是以经络和穴位为载体及通道,将药物和经络腧穴整体调节相结合,通过调节体内外失衡的功能状态而实现治疗目的。因此,若要“纳米药针”起效,关键是针对特定疾病药物的选择和载药平台的选择。如本研究者在治疗膝骨关节炎这种疼痛性疾病时,就可选择利多卡因这个局部镇痛药,或者选择羟基红花黄色素A(中药红花提取物)这种具有通经活络功能的中药有效成分。这样可以充分考虑到药物治疗的靶向作用,实现针药结合的“同效相须”或“异效互补”的作用[15-16]。
综上可知,依据“针药结合”理论,引入纳米新型材料和技术,可以研发新型针灸针具,从而起到“针药共治”增强疗效、延长起效时间、缩短疗程,减少药物用量和毒副作用、减少治疗步骤、提高患者依从性等多重目的。目前“纳米药针”的研发还处于起步阶段,有许多未知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索。以本研究团队研发的“纳米药针”为例,纳米涂层材料的选择,负载中药或西药的种类,“药针”治疗疾病的范围、动物实验甚至临床试验的疗效验证都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纳米药针”所体现出的“针药共治”的优势,“针药结合”所产生的巨大潜能和动力,可能成为“医工结合”研究的热点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