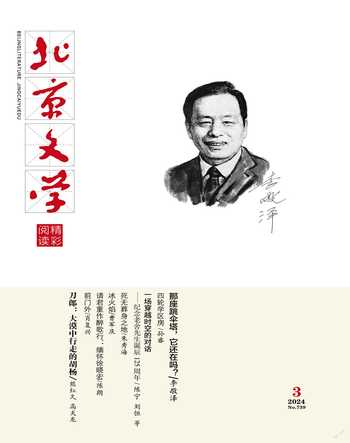亲和力
2024-03-26 05:56敖竹梅
北京文学 2024年3期
“太多了……我根本办不到。”
——但新烫的稻谷酒越添越满,
它還不算太烈;甜而腻,或者
有些后知后觉。热气如雾,浸透
小儿子书生气的脸。
时间还早,铝壶的嘴正吞吐
血缘的恩惠;“喝吧!”不过是
喝一点中国家庭的谦让与和气。
圆桌过于亲昵,钝刀割的猪头肉
尽泛着油脂的贪婪:那熟识的
家族荣光闪闪发亮。
这是第几个烟头?数不清了。
但他的肩头多了几双轻拍的手掌:
压着乡村的,逼仄的情谊。
这便是手足之爱吗?你早已
熟悉了它的价格。连牺牲
都是顺便的牺牲,是祝酒词里
沉默而被当作允诺的牺牲。
鱼骨越堆越高,垒成孩子
眼中的冢。父辈们的谈话应该
进展得很顺利:索要的修辞大概
不需要什么奇崛的招式,况且
它早已进化为怪力的美学。
可以告一段落了。起杯,
再来一次漂亮的配合与展演。
有哪一种抗拒被记住了吗?还是说,
他光荣的使命竟还需要被重复?
节日的闷雷包在爆竹声里:
你满面红光的父亲,在门口拨通了
电话;有些局促,但又沉醉于
某种虚荣和奉献,踌躇地,他清了清嗓
没有看向你,没有看向任何地方。
敖竹梅,1997年生于江西萍乡。
猜你喜欢
当代作家(2023年2期)2023-04-12
金秋(2022年2期)2022-06-02
家教世界(2021年4期)2021-03-09
作文中学版(2018年11期)2018-11-29
民间故事选刊·上(2018年5期)2018-05-18
苏州杂志(2017年4期)2017-09-03
爆笑show(2015年5期)2015-07-09
小学生时代·综合版(2014年12期)2015-01-17
小火炬·阅读作文(2009年7期)2009-0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