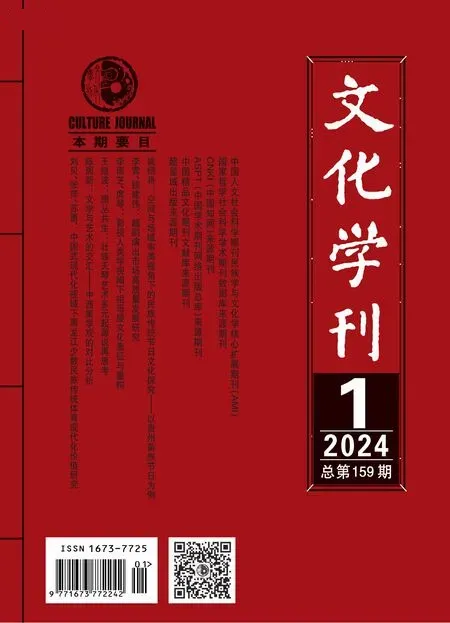空间与场域审美视角下的民族传统节日文化探究
——以贵州苗族节日为例
姚绍将
传统节日的审美体验是在特定时间与空间的独特体验。人们对时间的认识,从理论上,可以分为内在时间与外在时间,柏格森曾将外在时间定义为“空间化的时间”[1]。人们刻画生命经验形式所用的时间也同样占据空间。这样,时间和空间是无法分离分割的,每一种时间,无疑都拥有一个自足的空间。民俗文化或非遗研究普遍认为,节日文化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开启或生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化空间。由于文化与时空所构成的“场”这一总体概念,是由不同的空间和不同的时间抽象出来的,所有生活的空间和时代之中的人生命个体,就呈现出不同的具体的“场效应”情境。对社会文化“场域”或空间研究,譬如布尔迪厄的权利场域;涂尔干的神圣时间与世俗时间;泽鲁巴维尔认为的公共时间与私人时间。关涉社会“空间”的思考出现譬如巴什拉、列斐伏尔、福柯、哈维大卫等现代性的思想者。他们把现代空间的研究深入到人类社会文化各个方面。人类的节日因时间而生成和显现,但是节日时间所生产的文化“空间”凸显了重要的探究价值。人类早期阶段或传统的理解认为节日是特殊而神圣的日子,因此,人类早期的节日多属于宗教祭祀活动型节日,是献祭予神灵的特殊时间与空间。在当下现代性的时空中,传统节日遭遇世俗化或形式化,其神圣的意义正在逐渐变得支离破碎。虽然很多节日都通过集体的、约定俗成的,让繁忙的人放下手头的俗务而得以显现,但人们的意识依然徜徉于技术性的现代劳动节奏里,无充足时间置身多种多样并非以物质生产、交换及盈利为旨归的节庆节日事项中。很多传统民族特色鲜明的节日正面临着现代性的冲击,正如法国思想家巴什拉指出的,亲切空间(Intimate space)和幸福空间(Felicitous space)在现代性语境中似乎必然将“死亡”的现状[2]。西方传统思维把节日分为庄严肃穆型(即所谓的“太阳神文化类型”)和狂欢型(或者套用尼采的讲法而称为“酒神文化类型”),如第一种对应着基督教天主教世界的各种宗教意蕴节日,第二种则如欧洲盛行的狂欢节。然而当下中国许多民族地区的多数节日是庄严中承继着狂欢,嬉戏里不乏虔诚的状态,独存着神圣与世俗交流、日常与节庆的审美转换,以及文化与生境整生性的诗意空间。
一、神圣与世俗的交流场
节日里,人的生命处在特定浓缩的时空中,时间与空间共同构成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场”——神圣的领地。这种“场”与一般性世俗生活形成的场不同,自有不同寻常非世俗“场效应”。这种“场效应”实质上就是独有的民族节日文化效应。在平常世俗的这个场中,人们的生命活动按部就班,时间井然有序,人们的感受也是直线式平淡无奇。人们更多地是如机械般重复性的劳作。我们甚至可以说在世俗的场中生命的感受是很麻木的,犹如一条平直的时间线性的存在,人的生存状态处于意义不明的境况和沉沦的状态。早期迁徙或生活在贵州民族地区的族群,他们居住在高山、深谷、林密的穷乡僻壤,生活十分贫苦,长期过着刀耕火种的艰苦生活。不言而喻,人们的生命系统是不可能直线般地处在这样的生活秩序之中,这不适合生命本身的节奏,那是反生命的现象。从节日的时间和事件转换中生成世俗与神圣的交流场域。在民族传统节日中,巫师、鬼师等等主持的仪式开始,族群进入一个另外的时间——祭献时间,伴随的是围绕祭坛的特殊的文化空间,形成了一个族群的世俗生活场与节日神圣领地的交流场。崇拜者、牺牲与道具,只有在仪式中起作用。“事实上,神圣的与世俗的经常是相互交叉的,无论是人类满足自己最起码的饮食男女之需要的活动,还是较高层次的自我的价值实现活动,都可以根据其不同的指导思想、目的以及其危险性而划分为神圣的与世俗的。”[3]我们“从审美角度来看,仪式是原始宗教的行为舞台,在这舞台上,人们以其精神上特有的神奇和虚幻激发了审美想象力和创造力,并用它们来描绘和捕捉那种处于迷狂状态的审美宗教人生”[4]。有学者认为这个场可以称为民族“记忆之所”(lieude memoire),意指对于某一个群体的“小型社会”展现特殊的历史意义,并通过周期重复的、循环不断的节日纪念活动而不断被神秘化、神圣化的那些文化空间。很显然,有这么一个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空间的存在,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族群人们与祭祀对象的交流。在早期人类每个族群的节日里,族群人们与崇拜祭祀对象的交流可以说是主要的。因为早期人类“万物有灵”或“泛灵论”的思维方式,他们经常通过原始宗教崇拜与万物沟通交流,并且把某些生命迹象认为是祭祀崇拜对象反馈。他们坚信祭祀对象是可以交流沟通的,这种交流沟通在节日时空中格外深刻。这种现象在民族地区很多历史悠久的民族中依然存在。节日中,他们经常无意识或有意识地运用他们的诗性思维,“想象”出一个祖先或神灵“在那里”的美丽地方,并利用祭典、歌舞、咒语、巫词等等与祖先或神灵交流。这种交流不是任何场所都能够存在的,只有在节日综合文化场域中才能存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也认为,所有共同体都有某种神圣的语言(Sacred language),“老的共同体对他们语言的独特神圣性的自信,及因此自信而形成关于他们共同体成员关系的观念”[5],这是一种达到自居中心的媒介。
二是族群人们自己构筑和引发的交流场。人是社会性的动物,按照马克思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交流交往可以说是人类的一个天性。著名社会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指出,各种文化都处在交流之中,文化事件本身复杂的内在连续性,与参与那些事件的人们传递着信息。人与人的交往交流存在于人的任何场景。何况是节日就是共同体之体验,是共同体自身的最完美的表现形式。巴赫金精辟地指出:“一切有文化之人,莫不有一种向往接近人群打入人群与之对话融合,于其间不单是同人们、同民众人群、同广场上的人群进入特别的亲昵交往之中,不要有任何距离、等级和规范,这时进入巨大的躯体。”[6]由此可知,过节最鲜明、最突出的文化意义,就是真切实在地满足与蕴藉性地体现了某个群体和地方社会内外交往交流交融(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迫切内在需要,从而达到认知认同。在人类节日生活中,无论是仪式行为、禁忌规范、情感表达,还是严肃神圣与欢乐嬉戏情境转换,都会突出呈现出凝聚群体关系的高度认同。族群中的人们,平日里忙碌于各类生活上的繁琐杂碎之事,很多时候只是遇见的简单问候交流。人的复杂生命系统有着复杂的生命意识,肯定不会满足于这么简单机械地交流,深层次的微妙的交流是生命的需求。巴赫金的诗学这样写道“在暂时取消了人们之间的一切等级差别和隔阂,取消了日常生活,即非狂欢节生活中的某些规范和禁令的条件下,形成了在平时生活中不可能有的一种特殊的既理想又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这时人们之间没有任何距离,不拘行迹地在广场上的自由接触。”[7]节日之闲暇,经历了不同世俗世事的生命在此亲昵、休憩、嬉戏、碰撞、激励……
在各民族民间节日这个神圣与世俗的交流场中的主要交流手段是仪式与表演。仪式主要是存在于族群与祭祀对象的交流中,特纳在《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中发展杰内普的理论,仪式的第一步就是与日常生活的各种事物的相对分离。譬如苗族的隆重节日“牯脏节”到来,由仪式开启了时间节点,时间节点以视觉仪式标识,从经过节日期待与准备的“门槛状态”过渡到一个仪式世界里,跨越了两个时空概念:世俗的和神圣的。还有就是仪式中包含了太多指向另一个世界的象征和隐喻。这也可以说是人的生命构造的精神时空,从生命体验和审美情感而言,谁也不能否认这种象征和隐喻。节日仪式时间伊始,人们是与神灵、与祖先共舞。苗家人在鼓藏节、苗年、敬桥节等好些节日里,都是身着盛装,祭祀祖先,敲锣打鼓,唱歌跳舞……仪式一方面展开着神圣的时空,一方面派生着歌、舞、图画、服饰等表达情感的“有意味形式”。当然,表演也可以是隐喻的,英国民俗学家理查德·鲍曼通过对大量民间口头艺术的探究后总结指出,表演实质上是一种交流的重要模式。“在这模式中,表演者要对观众承担展示自己交流技巧的责任,而他使交流行为得以完成的相关技巧和效果会受到观众的品评,观众则会通过对表达行为本身内在品质的现场欣赏而得到经验的升华。”[8]节日里两种主要的交流手段在以上两种交流中都存在。如在苗族生活场中有很多出众的表演者或艺术家,然而在节日里,人人都是优秀表演者,每一生命都经历着强烈的愉悦之感。如果说节日里歌舞艺术是通过创造形象或境界来表现美感,那么仪式表演则可以说是通过制造一种态势来表现节日感。在黔东南苗族的仪式与表演交流中都遗留着原始先民的集体意识与无意识,仪式和交流是集体参与互动的,塑造出群体性与自娱性的“群体审美”的民族审美特点。
由此观之,民族节日文化成为研究民族文化的一个最重要的入口或出口(因为一个入口也是一个出口)。“文化表演理论”论认为,节日恰似一个文化交流的舞台,“这个舞台是整个世界:在公共空间,这种审美化无处不在”[9]。它演绎着的所有的(生活的、伦理的、审美的)活动都是生命展开来的本源内在时间和“被表征的外在时间”的交往契合,迎接并行不悖的日常与节庆的审美场域。
二、日常与节庆的审美场
德国著名美育家席勒对人类交流的作用做了深入探究。他强调审美交流是密切关系到人类社会团结的最重要因素;人与人、人与社会出现不和谐状态,人与人之间缺少交流沟通是关键原因。可想而知,每个族群中“小型社会”的交流是很重要的,井然有序或忙忙碌碌的日常生活人们是很少有闲暇的工夫进行交流。而在节日中的交流是族人们之间生命之流的融合,与祖先神灵等祭祀对象的沟通。在闲暇里,体验到生命的小憩美感。可以说,审美是基于交流的,审美就是一种交流,交流场域自然也就走入审美场域。节日审美内容(歌舞审美艺术、宗教技艺等)审美质的拓展,更是使得审美氛围弥漫和渗透了整个节日文化的方方面面,形成一股股审美质流。毫无疑问,再一次证明了神圣与世俗的交流场同时也是一个节庆与日常的审美场。我们知道所有的节日几乎都起源于原始宗教信仰,节庆时空其实就是祭典的神圣的时空,进入日常时空也就是人类又回到那平庸的世俗世界。不考虑深层的文化原因,从苗族每一个节日现场看,正是仪式交流的舞台激活了节日的气氛。在此“场”中,个体的生命、族群整体生命都在特定的时空中狂欢与激荡。而苗族众多节日文化在时空中相续相接有机生成,自成整体系统,影响着民众民间的文化审美气氛。
何为审美场?生命美学提倡者指出“每个人的审美取向、审美追求,与所处的社会文化时空中的生活气氛息息相关,我们把这种社会文化时空中制约社会审美变化的氛围称作审美场”[10]。节日具有地域性(或地方性)和族群特点,这不仅仅是学界对节日文化研究的一致观点,也是人们的普遍观念。由此节日里我们能够感觉到一片别致“气候”或景观:苗族姊妹节、四月八和爬坡节等呈现古老婚恋的生命情感氛围;吃新节、赶秋节和端节等主要体现农事生产的氛围;牯脏节、六月六和二月二等主要生发出宗教祭祀的氛围。总的看来,这些都是节日情感弥漫的氛围,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讨论集体活动、集体情感称这些情感是群体所共有的,那么它们就只能和所有人所共同拥有的某种东西相关联……它的意义就是为所有氏族人所共有……世代更替,它却保持不变。它就是社会生活的永恒要素。自然而然,节日有其自己的活态性质,但也有着历时的文化渊源,历时与共时必然地使得节日文化处在了一个特定的审美场中。“过节本身必有一种溢出了节日当下时(比如‘大年初一’)的、对总体时间势态的鲜明感受,即在过节前有预期(Protention),在过节后有保留或回味(Retention),而且过节前与后之间有鲜明的区别感,好像跨过了某个重要的界限。换言之,这应是一场真实深刻的体验。”[11]
节日里生命意义事件被“被表征的时间”呈现为了重要的带有审美质的生命形式:歌、舞、祭祀仪式、游艺,等等。可以说是生命内在时间的一种诗意的延伸,洋溢着浓厚的审美情调,构造了一个宗教与审美的空间。当然也就不仅仅是功能的空间,而更是诗意的空间。苗族节日里通过一些方式生发成诗意的空间和审美的场域。除上面提到的歌舞等方式,尤其是民族历史感与追忆成为审美场中重要的内容。其与审美场对生,使节日感增强。因此,节日感关联着现在、过去,憧憬未来。节日文化空间里追忆一个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及历史事件,一个行为、一个仪式、某个遗迹,等等,这些所唤起的微妙沉思,成了理解生命意义与情感归属的兴发之源。汤因比曾在《历史研究》说到一个观点,人类早期社会与文明社会的模仿是各不相同的,前者多是模仿祖宗前一辈,后者多是模仿有创造力的人物。此处模仿当然有着追忆的含义。苗族文化多存在模仿祖先的特点。通过这种方式,享受节日的人把他自身的当下在场嵌入共同体或者社会记忆的时空织网中,从而获得自我叩问思虑。由此,节日每一次从历史感或追忆中获得的灵感成就意义事项。历史感和追忆是外在时间的表征方式之一,随着时间的展开,苗族的节日仪式中几乎都有集体历史感与追忆怀旧。毫不夸张地说,苗家人的追忆怀旧,是生命不可或缺的某种情感需求和精神冲动。关乎往昔故事,关乎家园与迁徙想象的审美情愫——人类对那些美好温馨却又回不去的过往的珍视和眷恋。这些方式通过时间构造以充满生命诗意情感的空间,毫无疑问更应该是重要的审美方式。
按照日常理性思维,苗族的节日空间看起来是个功能空间,是一种认知空间,认知的主体是以科学和理性态度来对待物象,认知的目的是实用。然而实质上,各民族的节日审美场的诗意空间却与之不同,它所依据的是主体的直观直觉,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生命强烈的愉悦感和释放感,把对象体验整合为相互关联的生命同一体,生命类推循着一种内在生命的脉络,在诗意的态度中创造出诗意的世界。感性生命氛围压倒了理性生命履历,日常的“熟悉而平庸忙碌”的生命转换到节庆里“陌生而刺激忙碌”生命荡起内在动力的涟漪。
因此,日常与节庆的审美空间从这个视角证明了节日文化造就的审美氛围,作为日常生活的间歇,作为审美在场的体现。平时的世俗的与节庆的神圣的交替运作,使生活节奏得到调适,生命系统(生理的、心理的)得到平衡。节日庆典仪式的审美场,“通过对那些惊人的要素、节日的气氛、诗一般的韵律做出各种出人意料的解释,从而将各种舞蹈和歌唱、物品展示、各种仪式和入会式变成了一种销魂夺魄的体验”[12]。
三、文化与生境的生态场
英国结构功能学派大师拉德克里夫·布朗的人类学理论强调“功能就是一部分活动对整个活动所做的贡献”[13]。这也反映了研究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视角——文化整体论。节日审美文化的各项内容都是一个有机统一体。节日审美文化与民族文化是一个整体。贵州山区的苗族节日文化于交流场和审美场呈现“场”中之生命由世俗时间(日常时间)到神圣时间(节庆时间)循环的动态平衡,生成了交流交往美轮美奂的氛围。而在整个活动中,节日美感的审美质分发弥漫于特定的生境中,与生境构成对生,从而形成宏观的民族化生态化的民族生态审美场(简称生态场)。
人类都生活在各种各样的关系中。各种关系或联系形成的生态场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和谐。民族节日文化里的和谐是皮珀所言极是的“以有别于过日常生活的方式去和世界共同体验一种和谐,并浑然沉醉其中,可以说正是‘节日庆典’的意义”[14]。比如我们可以肯定原始宗教信仰旨在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而黔东南地区苗族的传统节日都与原始宗教关系深厚。苗族很多传统节日及宗教仪式时间是专为祭祀神灵、祖先而保留的,因为在这个时间或仪式中,族群人们的个体和群体生命与神灵、祖先得到“虔诚的交流”,人神关系变得融洽。因此,民族传统节日也是为确认、协调人与神灵(祖先)、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确立的[15]。节日活动(或仪式)的设置、时间的安排以及主题的凝练和演替等,都是特定的族群(人)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为了谋求自身更好地生存发展,调适自身与生存环境的关系的创造性成果。因此,传统节日不仅是特定民俗活动的周期性展演,更是特定族群与生态磨合调适而成的生存智慧、生命理想和民族精神得以不断生成、凝聚、表达、传承、强化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节日活动是一种民族生态活动,传统节日文化是一种生态文化。作为一种生态文化,它调适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的身心间的关系,凸显特定族群的生存智慧。生存与审美交织内濡,民族的生态活动成了审美活动的载体,又成了民族审美活动的内容,逐步构成了谐和完备的民族生态审美活动。“生活在节日中的民族”“活在歌海或舞蹈中的民族”形象地描述了少数民族生存与审美的统一。苗族的节日作为民族生态审美文化,是审美文化的生态化,是生态文化的审美化。它是特定族群生存智慧、生命理想和民族精神的综合表达。总之,少数民族节日审美文化的民族生态审美场是一“天、地、人、神”诗意和谐的宏观场域。
“每一生物都有它自己生存于其中的世界,这是一个它能适应的世界,也是适合于它的世界。(生态学的空间概念)……空间首先是生存空间,与具体生命有关的恰恰是环境,因为正是环境给这一生命提供它可以在其中生存的条件。”[16]各民族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尊重自然、敬畏自然、顺应自然规律、与自然生态友好相处,形成民族与环境对生的适应适合世界。此生态意识、生存智慧及其内濡、内蕴的和谐精神,是民族生态文化的精神内核,在民族文化的绝佳载体传统节日文化中得到了诗意的表达。少数民族生态智慧在节日审美生态化和生态审美化整合中延绵不绝地传承和潜移默化地得到强化。毫不夸张地说,这些既是很多世居民族传统节日文化在风靡全球的现代化和现代性潮流中奇迹般完好保存并独具魅力的重要原因之一,更是贵州苗、侗等民族长期保持较高幸福指数、诗意生存的根本原因。
民族民间传统节日文化生态审美追求首先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指族人在节日里借助各种仪式表达对大自然的崇拜和感恩,追求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诗意生存。正如格式塔完形理论强调的,从由人类和他的环境构成的领域中产生的,实质就是指出人与自然和谐而生成的合适的人格人性。强调不同类型的环境的影响和人们处理它们的方式构成了他们的格式塔。在获得格式塔的过程,人既获得个体性,又获得社会性,因为这一格式塔把他和他的环境结合成一个活生生的统一体,同时又把他作为这种特殊的活物同他的环境区别开来。格式塔是同各种环境交流的形式,人在这一环境中被识别,他及人的文化与该生态环境相适相宜。
格式塔过程也就是同生态自然交流的形式。是一种人个体性形成与自然沟通,耦合共生,“同构同形”的和谐美满感:庄重严肃却又轻松愉悦,敬畏万物,感恩祖先,顺应自然。经节日中的“交融”,过节的人重返与自然、与万物和睦相处的原初本真状态,体验着人与宇宙万物同在共生,及人的精神生命归属感的确认。节日中的民众欣然去接受他们在宇宙万物中的这样一种自由自觉的生活状态和他们在万物世界中的位置。显而易见,传统节日里人与整个外界达到了人是世界中的人,世界是鲜活之人的世界的境地。人不是高高上的刻板形象,而只是天地人神合一世界中一个鲜活的存在者。
四、结语
雷蒙德·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1780—1950》中论述“一种共同的文化发展”时说道“任何文化在其整体进程中,都是一种选择、一种强调、一种特殊的管理照顾。一个共同文化的特征在于,这种选择是自由和普遍的,并且不断重复。这种管理照顾是一个基于共同决定的共同过程,并且此共同决定本身包含着生命与成长的各种实际变化。自然生长和对自然生长的管理照顾是一个互相协调的过程,生存平等的基本原则保障着这个过程”[17]。在作为非遗的传统节日共同文化发展的空间生产中,集中突出的文化空间构造无限协调的空间形象。而正如民族节日中民族生态审美场几个时空维度,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苗族节日所展现绽放的生产、生活及生存图景,都能给予人一种质朴、祥和、神秘、恬淡的生态美感。地域生态化的和谐审美理想,在民族地区大地上,到处都向人散漫着一种无法抗拒的亲和力……审美圈与生态圈既按照自己的本性适情适性地充分发展,又能依顺人的意愿,人与自然各得其所,相处无碍。
在当下呼吁生态主义与反思人类对自然实践的合法性的境况下,“边缘化”民族的传统节日诗意空间中,宏观的生态场包蕴着微观的交流场域和审美场域,而圣神与世俗交流场域是走向审美、走向亲和的第一步,在交流达到理解的基础之上,节日里族群的日常生活与审美理想的发生融合,生成了生态文化与审美文化相统一的常态。这样,民族节日文化的逻辑空间得以生成及发展,可见或不可见的多个交叉互生场域构建了每一个民族能够最为集中标识民族特点的传统节日文化空间的“想象共同体”。不可见的空间无处不在,空间的自我生产更是无限的,正是因其构筑诗性空间“‘民族’因而也变成了起初能够自觉地渴求的事物,而非一个慢慢地显现的视像”[5]。因此,节日在场的精神意识空间与可视的物质空间共同生成了民族栖居的诗意之所。空间中栖居,就是共同体的家园,中国西南各民族诗意地构建着家园,家园也在灵性地构建共同体中的每一个族群和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