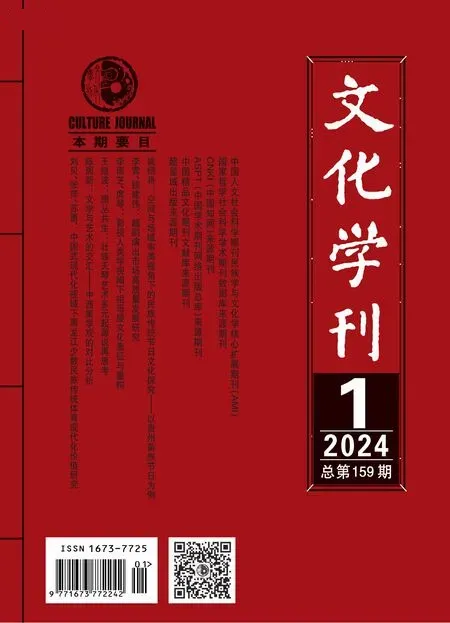大运河流经下的苏州城市空间发展变迁
袁琼岚
一、漕运的历史痕迹
江南运河段河道宽阔,周边物产丰富,沿运河城市借运河航运之势形成了一些中心城市,苏州便是当时江南运河沿线著名的中心城市。大运河在明清时期,漕运作为国之大事,是大运河航运的优先事项。漕运兴盛时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通过运河流淌不息,苏州作为运河沿线城市亦得益于这种频繁的商贸往来。
苏州在明清漕运兴盛时期商贸频繁,手工业发展迅速。随着漕运的深入,大量外地人口迁入,区域内文化融合加速。所有种种,在苏州一段时间内的城市发展上有所映射,考察今天苏州运河沿线建筑样式、功用、分布情况,可以更加清晰地展现漕运时期这股时代洪流对沿线城市的裹挟。
漕运依托河道进行,在明清漕运兴盛时期,漕运经过苏州的河道主要有城内的环城河及城外山塘河、上塘河,外加南郊南下吴江的运河河道。货物整顿集中在城市内进行,故考察漕运兴盛时期对苏州城市发展影响宜集中在古城内及山塘河、上塘河周边进行。与城市发展同时进行的是周边乡镇的繁盛发展,由于大运河对苏州沿运河市镇发展的影响较大,受篇幅所限,城郊乡镇将不作重点关照。
苏州漕运兴盛时期的发展离不开政府主持的水政措施,主要包括对河道的疏浚维护等,吴江塘路是江南低湿地带的杰出水利工程体系,包含的宝带桥、吴江古纤道作为水工设施均得到多次修筑,使用状况良好,运河沿途的溇港圩田在漕运时期得到定期的疏浚治理。明清时期,苏州将城内河道疏浚作为治水重点,据载,明代中后期至清中期,苏州城内河道疏浚没有间断,甚至康乾年间平均七年左右便会有政府组织的疏浚行为(1)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苏州古城河道俨然,三横四直结构的干河系统至今仍在发挥着重要的调节水位等作用,以永丰仓船埠等现存的文保单位,代表了漕运功能完备时期的城内河道形态建制。
仓储设施是苏州城内遗留下来直接关乎漕运的构筑物,在漕运运行时期,各地兴建粮仓储存粮食,大多官仓都建在河道周边,方便运输。苏州当时的官仓主要分布在平江路及城南府衙周边,两地靠近环城河。平江路官仓集聚地靠近娄门,当时娄门外大运河水面宽阔,城东一片浅塘,明代杨循古《吴邑志》载,“今观水之流派,常自阊盘二门入,即西南、西北水也,由葑娄齐三门出”。娄门为水流东流之口,水流可达东海,经苏郡之娄门,至太仓之刘河,出天妃闸以入海,是为娄江。大批量的漕粮可由娄门进行河运或海运分发。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现存丰备义仓旧址是保存较好的清代官仓建筑,是旧时苏州仓储设施的代表。
二、商业与市民生活
苏州城市建设在明清时期得到了迅速发展,其原因之一便是作为中心城市获益于漕运的兴盛,漕运产生了运输中各阶层夹带私货现象、漕粮部分货币化、人口迁徙、商贸往来等直接或间接现象,犹如几股合力指向城市的发展布局。
明代漕运时期的苏州商业发展尤以阊门为盛,明人在各类笔记中有很多记载。“尝出阊市,见错绣连云,肩摩毂击,枫江之舳舻衔尾,南濠之货物如山,则谓此亦江南一都会也。”(2)[明]王心一.崇祯《吴县志》序.清代画家徐扬以写实的笔法在《姑苏繁华图》中展现了这个地区的商业活力。当时大运河河道上塘河、山塘河与环城河在阊门汇聚,这一带商贸形态多样,南北货物齐聚,经济富庶,成为江南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伴随大运河而来的不仅有漕运的船只,南北民间商贸也依赖这条大动脉进行运输,且苏州本身物产丰厚,手工业发达,成为大运河上沿线商贸中心之一。明代开始,苏州成为各地商业聚集之所,商品种类多,辐射地域广。“阊门为苏孔道,上津桥去城一里许,闽粤徽商杂处,户口繁庶,市廛栉比,尺寸之地值几十金。”(3)李果.《让道记》.
明清时期苏州工商业发展迅速,并推动了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导致行业聚集与手工业细化,诸如以苏州丝绸、棉布行业,形成印染、生丝加工、成布等产业链细分行业,且生产地域开始向某一地聚集。“织作在东城,比户习织,专其业者不啻万家”(4)乾隆.《长洲县志》.,“苏布名称四方,习是业者,阊门外上下塘居多”(5)乾隆.《元和县志》.。清代乾隆年间,丝绸业主要集中在城东,而棉布印染业则集中到了阊门外的上、下塘一带,形成了完整的丝织布匹加工产业区。而另外一些地区,则凭借着运河地理优势,成为某一货物的大型集散地,如枫桥米市:“为水陆孔道,贩贸所集,有豆米市,设有千总驻防。”“为储积贩贸之所会归”(6)康熙.《长洲县志》.,行业公会在这些生产聚集区域大量产生。各地商人在苏州的商贸活动除了将苏州物产贩卖至全国市场外,也将各地的特产在苏州这个市场进行销售,故纷纷在苏州新建会馆商会,交流信息,互通有无,“阊门一带,堪称客帮林立”,苏州最早的会馆岭南会馆就位于阊门外山塘街。目前苏州的会馆建筑遗存大体沿运河河道分布,是明清时期商业经济发展的见证。
大运河在明清时期留在苏州的印迹还在于疏通便利的河道交通后,凭借经济的繁荣改变了市民的生活方式,这其中以现山塘历史文化街区最为典型,它是清代完整商业居住社区的范例[1]。山塘街区依傍山塘河而形成,从阊门直至虎丘,两岸房屋紧凑,商业形态完整,清代中期已经成为苏州府城外著名商业街区。《岭南会馆广业堂碑记》记载:“姑苏江左名区也,声名文物,为国朝所推,而阊门外商贾鳞集,货贝辐辏,襟带于山塘间,久成都会。”繁华的盛景包含完整的商业设施:会馆、店铺、公会,修筑了普济桥等道路交通公用设施,富裕的家族在此地定居,并修建义庄、祠堂等宗族社会活动场所,而山塘等地的道观庙宇群与虎丘山一起构成了苏州城外的社会休闲场所。
从宋元至明清,苏州的宗教建筑分布北半城一直多于南半城,且受经济政治影响,多分布于市井生活气息浓厚之地,城区及周边宗教建筑在明清时期主要以佛道及民间祭祀三种为主[2]。宗教生活中的集会活动随着世俗生活的影响,在宗教仪式、集会之余产生了士女游园性质的活动,吴地民众经常在宗教活动中由娱神旁斜横逸出娱人、甚至自娱精神来,丰富市民生活。《清嘉录》尝载吴地有很多道教、佛教节日盛典,士女出游者众,“十九日,为观音诞辰,士女骈集殿庭炷香,或施佛前长明灯油,以保安康”。而这些庙宇宫观所在地,每逢宗教节日俨然成为当下热门出游场所,“观音诞日,有至支硎山朝拜者,望前后已聊缀于途,马铺桥迤西,乃到山路也”。谨以山塘地区为例,山塘地区本身在吸纳五湖四海的外来民众后,习俗纷杂,有众多民间活动,灯会,花市,庙会不断。“吴郡无祀厉坛在虎丘山前,附郭三邑统祭于此。清明赛会最盛,十乡城内外土谷神咸集,游人群聚山塘,名三节会,谓清明、中元、十月朔三节也。”(7)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山塘有宽阔的河道水域,交通便利,商业氛围浓厚,地处城外郭野,野趣盎然,且靠近虎丘这个明清时期著名的士女郊游场所,成为独特的市民游乐文化高地。明代虎丘游观已成规模,是士大夫阶层与普通民众同乐场所:“至今吴中士夫画舡游泛,携妓登山。而虎丘则以太守胡缵宗创造台阁数重,增益胜眺。自是四时游客无寥寂之日,寺如喧市,妓女如云。”(8)张紫琳.《红兰逸乘》卷 2《古迹》.虎丘山自宋后景点没有大变,既是宗教文化场地又人文遗迹众多,明清时期在这里举行的文化雅集不胜枚举,与周边的宗教建筑一起形成山塘宗教游乐场所中心。山塘历史文化街区周边现存的宗教建筑以沿河寺庙、宫观及虎丘山宗教建筑群共同构筑而成,在探究其宗教本源之外,明清时期苏州地区市民阶层的兴起,由此带来的游乐文化对宗教集会的影响不应忽视[3]。
三、西风东来的大运河轨迹
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西方的人、事、物涌入苏州,苏州出现一批迥异于中国传统建筑的西方样式建筑。这类西方建筑在《南京条约》后,在苏州城内大量建成,它们中既有租界区域的住宅建筑,也有西式教会,学校、医院、工厂等公共活动场所,这些平常生活场景中的建筑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来临。大运河作为一条贯通南北的主航道,在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前期在江南段仍发挥着重要的航运作用[4]。在西方观念及事物的涌入途径中,仍在通航的大运河是不可忽视的交通通道。
苏州靠近上海这个早期通商口岸,《马关条约》后成为几个通商口岸之一,西方事物进入苏州时部分直接循运河而来,留雪泥鸿爪在运河两岸。日本租界及关税务司等代表外国侵略势力的建筑遗存就在大运河两岸,它们的选址体现了帝国主义对苏州经济社会文化企图控制之心,日本租界选址的最初设想如下:“先索城内元妙观、城外阊门南濠繁盛之处,继索胥门外坛庙最多地方,后始议定盘门外相王庙迤东空旷地亩作为通商场。”(9)《咨送苏州日本租界章程》,1897年4月23日.除玄妙观为苏州城内繁华地外,其余几处均为大运河交通便利之地,且有赖运河的航运作用,这几处经济也较为繁华。大运河的便利,一直就是日本设立租界的首选,日本曾为是否将苏州沿运河十丈地纳入租界范围和清政府僵持不下,曾在内部文件有此记录:“该地区对我租界占据最枢要之处,码头建立、船舶停泊、货物上下等都须仰赖这个地区,能否管辖,对于将来租界各方面经营有最关痛痒得失之感。”(10)《外务大臣大隈重信致驻上海总领事珍田舍已》,1896年11月16日.同一时期,英国殖民者兴建的苏州关署也是出于类似的考量,把控制苏州进出口的关税务司公署设立在大运河环城河南,是为了拥有更好的交通区位优势,以便更好地控制苏州,摄取中国国民经济成果。苏州洋关对进出苏州口岸的轮船货运及应税货物办理报关、查验、征税、放行、查私等海关业务,在1909年沪宁线铁路全线通车之前,火车货运还没有普及的年代里,大运河仍是苏州关的主要来往通道,苏州关与上海、宁波、杭州、镇江等其他进出口关的联系通道也依托大运河为通道。现在苏州大运河两岸分布的这类在西方政府主导下建设的公用建筑保存良好,他们见证了大运河在漕运之后被帝国主义摄取用来侵略中国的屈辱历史[5]。
进入20世纪后,苏州的近现代建筑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带有西方特色的普通民居与工业厂房是这个时期新增的特色,是先贤们接受西方文化后主动拥抱世界探索民族未来的体现。带有西方近现代特色的民居主要由当时社会上层达官贵人、富商及医生、律师等专业人士兴建,他们较早接触了西方便捷的生活设施,在房屋营造方面趋向选择适合这种生活方式的西方样式,这类近现代民居大批分散在苏州城内外。工业厂房的选址较之民居有更多考量,大运河承担大宗货物运输的功能,是近代很多民族企业家选择在通航河道旁兴建工厂的原因之一,苏州的大运河河道旁留下了一批近现代民族工业的遗存。
从19世纪中期开始,阊门淤积严重,大型船只进城困难,因此,商船选择从寒山寺附近南下,于横塘驿站附近用原胥溪河道作为大运河苏州段主航道,直至20世纪80年代,这条胥江一直是大运河进入苏州的主要航道,见证了大运河作为传播现代思想、实现实业自救渠道的时代通道。政府主办的苏经丝厂、苏纶纱厂,两厂同时在1895年筹建,选址在盘门外青旸地附近吴门桥东首,当时尚为荒地,地价合理,货运成本较低。苏州胥门附近至觅渡桥这段河道周边在20世纪上半叶工厂分布密集,主要原因包含了:大运河沿岸地势平缓开阔可作码头使用,苏州大运河河道联通各乡村,通过船运可深入村镇腹地获取生产原料,水路运输连接的上海、宁波等都市则提供了广阔的销售市场,且离海关较近报关方便[6]。太和面粉厂、鸿生火柴厂等民营企业在这里生产产品并销往全国,如鸿生火柴厂创始人刘鸿生对于在这片区域内建造厂房很是满意,在1920年致苏州总商会的函件中,曾有“该地四面空旷,距离胥门和盘门市厘各在数里之外,水陆交通便利,绝无障碍之虑”等语。苏州民族工业在大运河沿岸蹒跚起步。
四、结语
综上所述,大运河流经下的苏州城市空间变迁,主要涉及漕运的历史痕迹,同时涉及商业和市民生活,展现出苏州城市建设在清明时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原因,并且提及19世纪中后期西方的人、事、物等涌入苏州,苏州出现了西方样式的建筑,最后分析苏州民族工业在大运河沿岸起步的情况,为苏州大运河的历史分析和未来发展等夯实基础。